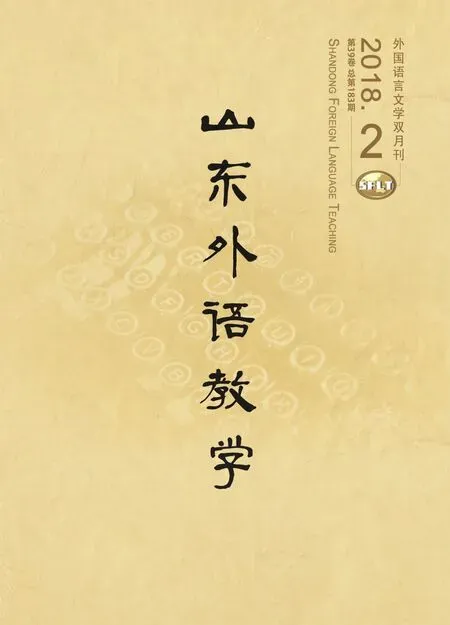英译前后《芙蓉镇》中的权力关系变化研究
——以对胡玉音的聚焦分析为例
汪晓莉 汪方芳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09)
1.0 引言
古华的长篇小说《芙蓉镇》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极“左”路线破坏下的中国农村生活为背景,以女主人公胡玉音的命运为主线,揭示了以男权主义为本质的主流文化对人性的侵蚀。作品中的权力关系无处不在,体现了阶级、群体以及个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辛斌(2003:6)认为,权力是人们为追求自己的目标和利益而采取行动的能力,它也是控制和支配他人、调动各种资源的能力。权力的丧失往往伴随着心理上的丧失,社会中从属群体的绝大多数成员通常根据其亲身经验来认知自己的处境,而无法从社会结构中确认自己的利益。在小说《芙蓉镇》中,胡玉音就是权力和心理丧失下从属群体的典型代表。该作品于1982年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其英译本由戴乃迭(Gladys Yang)完成于1983年。
小说中的人物在权力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聚焦分析来确定。在里蒙·凯南(1989:129)看来,聚焦不仅仅是视觉活动,更是一个包含感知、情感、意识形态等各种精神活动在内的行为系统。具体就胡玉音而言,对其进行聚焦分析可以全方位地展现她的外在行为和内在思想、叙述者和其他人物对她的看法、她对自己的定位以及对世界和他人的态度,从而揭示该人物身处的社会环境和她在权力关系中所处的位置。
因此,本文基于《芙蓉镇》汉英平行语料库,提取所有与胡玉音相关的中文语料及其英译进行分析,从句子层面着手、以聚焦为切入点,考察英译本中胡玉音在权力关系中的地位相较于原文的变化,并对变化产生的原因作出阐释。文章力图回答三个问题:(1)作品原文和译文对胡玉音的聚焦有何差异?(2)英译前后作品对胡玉音的聚焦变化如何影响她在权力关系中所处的位置?(3)导致作品中的权力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2.0 理论背景
英国小说家路伯克曾说:“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要受观察点问题——叙述者所站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支配”(胡亚敏,2004:19)。没有一种叙事方式不表现为某种特定的感知角度,叙事方式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就体现在对感知角度的把握和运用。因此,确认一篇或一段话语的感知主体(或聚焦者)是准确理解、把握文学作品题旨和艺术特点的关捩所在(费维达,1996:92)。
在参照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法国学者热奈特于1969年率先提出了“叙述聚焦”这一概念,力图澄清叙事学界在“谁说”与“谁看”的问题上长期存在的混乱(尚必武, 2007:3)。他根据叙述信息受限制程度的高低,提出了叙述聚焦的三种类型: 零聚焦、外聚焦和内聚焦(同上:4)。在客观审视叙述聚焦理论的基础上,里蒙·凯南(1989:128)高度评价了热奈特的“叙述聚焦”这一术语,但她对热氏的叙述聚焦三分法提出了不同见解。
“聚焦既有主体,也有客体。主体(聚焦者)是根据其感知确定表现方向的媒介,而客体(被聚焦者)是聚焦者所感知的对象”(米克·巴尔著,谭君强译,1995:119)。里蒙·凯南(1989:133)通过沿用巴尔所提出的概念,以两个标准——即聚焦相对于故事的位置和持续的程度讨论了聚焦的分类。聚焦由聚焦者、聚焦对象和聚焦行为三者共同组成。首先,根据聚焦者与故事的位置关系,聚焦可以分为两类,即外部聚焦和内部聚焦:外部聚焦的主体处于故事之外,通常为“叙述者-聚焦者”;而内部聚焦的主体处于故事之内,被称为“人物-聚焦者”。而根据聚焦者对聚焦对象的透视角度,聚焦行为可分为从外在看聚焦对象和从内心看聚焦对象, 分别表现为对人物外在行为的观察和对人物内心活动的透视。其次,从聚焦的持续程度来看,里蒙·凯南(1989:138-139)认为在一篇叙事作品中聚焦可以始终固定不变,也可以在两个起主导作用的聚焦者之间交替变换,或者在好几个聚焦者中间转换。固定的、可变的和多重聚焦之间的区别适用于聚焦者,同样也适用于被聚焦者。
里蒙·凯南(1989:139)还对聚焦现象的感知、心理和意识形态侧面进行了分析,阐明了内部和外部标准在这些侧面中的具体表现。感知侧面是由空间与时间两个坐标确定的,涉及聚焦者的感官范围;心理侧面涉及聚焦者的思想和情感,由聚集者对被聚焦者的认知和情感两要素构成;意识形态侧面常被称为“文本的规范”,由“一个以观念形式看待世界的一般体系”构成,这个一般体系是评价故事中的事件和人物的依据。诸侧面可能主体一致,但也可能通过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聚焦者得到体现。
在小说翻译中,若要实现文艺美学功能的等值,译者必须紧紧抓住叙事这一本质特性,恰当地把握原文作者的叙事技巧,准确地再现原作中的叙事类型(郑敏宇,2001:65)。从叙事的角度去看待翻译,可以研究译者如何从社会现实和变革、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方面去影响叙事(黄海军,2008:58)。聚焦是小说的叙事技巧之一,不同的聚焦形式通常体现着不同的审美意图。文学作品中多元聚焦的变换不仅会使叙事文本篇章结构、布局系统变得复杂,而且会带来文本内涵的增值和不可预测性,再次展示了文学话语具有无限的意义生成可能性(费维达,1996:96)。小说译者根据聚焦类型把握原文的主题,分析它的形式特征并予以传递,从而使译文的叙述特点和意图更契合原文。而小说翻译批评者只有把握原文与聚焦相关的语言形式,才能把握作品的主题并对译文作出恰当的评价。
3.0 研究设计
3.1 语料库简介
本研究所使用的语料库为茅盾文学奖作品汉英平行语料库①的子库——《芙蓉镇》汉英平行语料库。库中中文语料经过ICTCLAS 3.0的分词赋码处理,英文语料经过Treetagger 2的词性赋码处理,中文原文与英文译文经过ParaConc软件处理和人工调整,在句子层面实现了平行对齐。具体库容如表1 所示:

表1 语料库概况
3.2 研究方法与步骤
本文首先用ParaConc软件提取了《芙蓉镇》汉英平行语料库中所有与胡玉音相关的中文语料及其英译,根据里蒙·凯南的聚焦分类标准,按照聚焦者与故事的位置关系、聚焦者、聚焦对象和聚焦行为在句子层面上对语料进行分类②,归纳原文和译文对胡玉音的聚焦差异。其次,从两个方面讨论翻译前后的聚焦变化:一是其他要素不变,单纯聚焦行为的变化;二是内、外部聚焦的转换,聚焦者与聚焦行为均发生变化。接着结合里蒙·凯南的聚焦理论进行分析,总结聚焦变化对胡玉音所处权力关系的影响。最后,从译者的叙述干预和明晰的读者意识两方面具体分析聚焦变化和胡玉音权力变化的原因。
4.0 结果与讨论
4.1 《芙蓉镇》及其译本对胡玉音的聚焦情况及分析
在里蒙·凯南的聚焦理论中,聚焦是由聚焦者、聚焦对象和聚焦行为共同组成的。由于三者联系紧密,我们在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中,除了分别考察,还必须将它们互相结合,才能窥见聚焦的全貌(赵莉华、石坚,2008:232)。因此,基于里蒙·凯南的聚焦分类标准,结合聚焦者与故事的位置关系、聚焦者、聚焦对象和聚焦行为四个要素,本节在句子层面上对《芙蓉镇》及其译本中所有与胡玉音相关的语料进行了分类统计,并得出如下结果:

表2 原文和译文对胡玉音的聚焦情况
如表2所示,原文及译文中对胡玉音的聚焦分为以下两类情况。一是外部聚焦,聚焦者处于故事之外,即叙述者-聚焦者,胡玉音是聚焦对象。聚焦行为分别为叙述者-聚焦者对胡玉音从外在的观察和从内心的透视,展现了胡玉音的外在行为和叙述者对其内心想法的转述。二是内部聚焦,聚焦者处于故事之内,即人物-聚焦者,包括胡玉音和其他人物。他们均从外在观察他人,并从内心聚焦自身(即内心独白)。
从数据来看,首先,原文聚焦为837句,译文聚焦为772句,原文和译文的聚焦总频数相差65。其次,聚焦类型上,无论原文还是译文,外部聚焦频数整体大于内部聚焦;聚焦行为上,原文以内心透视为主,译文以外在观察为主。原文中从外在观察的聚焦行为比率为47.8%(44.2%+2.2%+1.4%),从内心透视的聚焦行为比率为52.2%(31.3%+17.9%+3.0%),两者基本持平,后者比率略高;但是在译文中两者的比率分别是65.9%(62.6%+2.3%+1.0%)和34.1%(25.3%+7.0%+1.8%),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两倍。数据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外部聚焦下,译文相较于原文,从外在的聚焦行为比率上升了18.4%(62.6%-44.2%,变化最为明显),从内心的聚焦行为下降了6.0%(31.3%-25.3%);内部聚焦下,胡玉音的内心独白比率下降10.9%(17.9%-7.0%)。其他数据比率基本保持不变,因而不予讨论。
4.2 聚焦转换下的权力关系变化
通过对语料和数据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与原文相比,译文对胡玉音的聚焦变化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单纯聚焦行为的变化,聚焦者与聚焦对象保持不变。这类变化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主要表现为外部聚焦下,当胡玉音作为聚焦对象时,原文从内心的聚焦行为转变为译文从外在的聚焦行为。二是内部聚焦转变为外部聚焦,聚焦者和聚焦行为均发生变化。主要体现为内部聚焦下胡玉音的内心独白转变为外部聚焦。变化的具体情况及其对胡玉音在权力关系中所处位置的影响详述如下。
4.2.1 单纯聚焦行为变化对权力关系的影响

表3 单纯聚焦行为的变化情况
由表2可知,原文外部聚焦下,叙述者-聚焦者从内心聚焦胡玉音共计262句。由表3可知,译文对这部分聚焦语料除保留外,主要采取了两种处理方式:改变聚焦行为和删减,其中35.5%的聚焦行为由从内心转为从外在的聚焦行为,10.3%遭到删减。原文叙述者-聚焦者从内心聚焦胡玉音,倾向于关注她的内心世界并转述她的内心想法;而译文转变为从外在聚焦,聚焦者将其想法直接描述为行动,关注她的行动能力和支配力。原文从内心聚焦胡玉音所传达的人物的内心想法和意识大多消极悲观,展示出她被压迫、被支配、只知忍受不懂反抗的悲剧人生,说明她在权力关系中处于被动、弱势的地位;译文对聚焦行为的改变和删减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胡玉音在权力关系中的地位。
首先,原文中的叙述者-聚焦者深入胡玉音的意识,将她的想法转述给读者,而这种转述在语言形式上主要体现为自由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一般没有引导句,叙述语与人物的想法之间不存在任何过渡,因此读者可以直接进入人物内心,而人物的想法中体现情感因素的各种主观成分(如重复、疑问句等)也均能得到保留(申丹,2010:104)。在汉语中,自由间接引语在表层结构上往往只有体现人物主观意识的语言成分,而不见叙述者的声音及其意识成分(杨斌,2005:73),所以原文充分表达了胡玉音的意识和内心想法。而胡玉音的“内心生活”多含悲伤、害怕、绝望等消极情绪,读者受到的感染较强,易对人物的坎坷命运产生同情,也能认识到她处于权力关系的底层。相比之下,译文将部分原文的从内心的聚焦行为转变为从外在的聚焦行为,将自由间接引语变成言语行为叙述体,将胡玉音内心所想化成了具体的行为动作。正如王林(2014:301)总结的那样,译者对自由间接话语的加工处理可能会使其变形为其他话语形式,从而使人物的意识流显得太过理性而失真,人物的声音被弱化,原文的叙事效果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译文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胡玉音的内心想法,而更倾向于强调她的行为能力。这种转变削弱了人物受压迫的程度和原文中胡玉音的悲惨命运对读者的情感冲击,从而相对提升了她在权力关系中的地位。例如:
(1)是的,一个摆小摊子为业的乡下女人的世界就这么一点大,她是男人的命,男人也是她的命。
Yes, as a country woman, a stallholder, her world was very restricted.Sheandherhusbandwereeverythingtoeachother.
原句是叙述者-聚焦者对胡玉音外在的观察和内心的透视,体现了她以夫为纲的性别观念和在权力关系中的从属地位;而译文则完全是叙述者-聚焦者对胡玉音外在情况的总结,减弱了她完全从属于男性的感觉,加强了男女平等的概念,提高了胡玉音在家庭中的支配力、即她所拥有的权力。
另外,译文的删减处理减少了叙述者-聚焦者对胡玉音的内心透视,使胡玉音的部分内心想法和负面情绪直接消失,明显减弱了读者对人物的同情和怜悯,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她在权力关系中的地位。例如:
(2)每每想到这里,她就哭啊,哭啊,感到委屈,感到不平,就有了气!
原句中叙述者-聚焦者从内心聚焦胡玉音,将她所受的压迫、她的委屈、她内心微弱的反抗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暗示了她在权力关系中的卑微地位。而译文的删减处理隐藏了胡玉音的内心情绪,也就相对地提升了她在权力关系中的地位。
4.2.2 内、外部聚焦转换对权力关系的影响

表4 胡玉音内心独白的变化情况
从表4来看,原文内部聚焦下,胡玉音从内心聚焦自身(即内心独白)共计150句。译文除保留处理外,对这部分语料主要做出两种改变:转为外部聚焦和删减。在转为外部聚焦的语料中胡玉音仍为聚焦对象,从内心的聚焦行为占35.3%,从外在的占16.0%;被删减的语料占12.7%。
根据里蒙·凯南的聚焦理论,内部聚焦与外部聚焦在感知、心理与意识形态三个侧面均存在不同表现。首先从感知层面来看,空间上,外部聚焦者是鸟瞰式视角,聚焦者处在离对象很远的位置(这也是叙述者-聚焦者的经典位置)进行观察,产生了全景视角,可以‘同时’聚焦‘发生’在不同地方的事情;内部聚焦者是受限制的观察者,人物-聚焦者只能观察到“他”或“她”个人所看到的东西,视野十分受限(里蒙·凯南,1989:139-141)。时间上,外部聚焦是泛时的,内部聚焦同聚焦者所支配的信息是共时的。换句话说,外部聚焦者可以支配故事的所有时间范畴(过去、现在和将来),而内部聚焦者却只限于支配人物的“现在”(Uspensky,1973:113)。原文的内部聚焦下,胡玉音的内心独白是这一人物的局限视角,所观察和感知的只是自身,时间上只展示她当时的心理状态。她消极负面的内心情绪和强烈的原罪意识在没有任何干扰的状态下展现在读者面前,能让人切身感受到她在权力关系中的弱势地位。而译文的外部聚焦下,叙述者-聚焦者在空间和时间上均不受限制,像上帝般观察事物,再将观察到的有选择地叙述给读者。外部聚焦者在全景视角和泛时聚焦下从内心和外在观察胡玉音,使读者的视线随之转移。读者不再仅仅关注胡玉音“现在”的内心想法,同时也会注意到她的行动力和支配力。因此,胡玉音在权力关系的底层位置相较于原文不再那么明显。
其次,聚焦的心理层面体现的是聚焦者的内心和情感,其决定性的要素有两个:聚焦者对聚焦对象的认知作用和情感作用(里蒙·凯南,1989:142)。从认知来看,外部和内部聚焦的对立表现为不受局限的知识和受局限的知识的对立(同上:143)。原文内部聚焦下,胡玉音从内心聚焦自身。因受到认知局限,胡玉音无法获悉一切,从而使读者只能看到她所感知的内容,即她的内心状态多为茫然和不知所措。而译文外部聚焦下,叙述者-聚焦者完全不受局限,对于所描述的世界是无所不知的,对故事中人、事、物的认知都十分清晰。译文直接对原文的内心独白进行转述或者将其化为具体的外部动作、作为事实进行客观描述,使胡玉音不再完全被禁锢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她的内心状态。从情感的角度而言,“外部”与“内部”的对立可以投射为“客观”(中立的,不介入的)与“主观”(受感染的,介入的)聚焦的对立形式(同上:144)。内部聚焦者具有主观性,尤其在原文这样的内心独白中,胡玉音的内心想法和意识完全发挥主导作用,是读者唯一的信息来源。她仿佛面对面地将自己遭受的压迫和伤害告诉读者,以最具感染力的方式让读者感受到她所处的低下地位。而外部聚焦者不介入故事,不使用故事中人物的视角,更具客观性。译文中的叙述者-聚焦者从内心聚焦胡玉音,即转述胡玉音的内心想法;从外在观察胡玉音,即将胡玉音的内心独白化为具体的外在行为。这种由“主观”到“客观”的情感转换,使译文中站在故事之外的聚焦者得以更加中立地进行聚焦和叙述,降低了原文中胡玉音内心独白的情感力度,变相提高了胡玉音在所处权力关系中的地位。例如:
(3)过去街上的人,特别是那些男人们,见了自己总是眼睃睃、笑眯眯的,恨不得把双眼睛都贴到自己身上来……
In the past people meeting her in the street, the men especially, had always smiled at her...
原文在认知上具有局限性,完全是胡玉音的主观情感。读者只能通过她的想法得知她是芙蓉镇上的人们、特别是男性观察和垂涎的对象;而她无力作出改变,在社会和性别权力关系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译文则转用不受局限的外部聚焦者的眼光,从远处客观描述了镇上的人们对胡玉音的问候;且“smile”这一较为中性的词更强调平等,使她不再处于被观察和玩赏的位置。
最后,意识形态这一侧面常被称为“文本的规范”,由“一个以观念形式看待世界的一般体系”构成,这个一般体系是评价故事中的事件和人物的依据(Uspensky,1973:8)。在最简单的情况下,叙述者-聚焦者的意识形态通常被认为是权威的,而文本中所有其他的意识形态都从叙述者-聚焦者这个“更高”的角度得到评价;在较为复杂的情况下,权威的外部聚焦者将让位于若干个意识形态立场(里蒙·凯南,1989:147)。很明显,原文属于复杂情况,胡玉音这一人物同时作为聚焦者和聚焦对象,无疑是意识中心;而译文则属简单情况,外部聚焦下,权威的叙述者-聚焦者是意识中心。人物-叙述者的视点必定带有自身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与价值判断态度。“他”或“她”必定会从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去看待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与之发生与自身身份相符的种种关系,同时讲述自己或多或少参与其中的故事(谭君强,2004:61)。通过胡玉音对自身的聚焦,原文充分展现了她的意识,传达了她的意识形态立场,反映了她对自身、他人和世界的认知和态度,揭示了她在社会和人际权力关系中的被动地位。她的内心独白其实相当于一种行动上的沉默,她只能在想象中观察世界、揣摩他人,而无法发挥能动作用。胡玉音作为意识中心所占据的叙述空间越大,她的被动和弱势就越是显得漫长而沉重。而译文仅保留了原文36.0%的内心独白,删减了12.7%,将另外51.3%(35.3%+16.0%)全部转换为以叙述者-聚焦者为意识中心的外部聚焦,使人物的意识更多地从叙述者-聚焦者这里得到评价。叙述者-聚焦者除了从内心聚焦胡玉音,还从外部观察她,将她的想法直接转为动作,发挥她的能动作用,使她在人际关系之中不再一味保持沉默。叙述者-聚焦者的意识形态“规范”可以通过故事的倾向得到暗示,也可以直接表述出来(里蒙·凯南,1989:148)。译文中叙述者-聚焦者的外部聚焦下,胡玉音的大部分意识被遮蔽,其行动力得到增强,社会参与度有所提高,可见译文倾向于改变胡玉音的弱势、提高她在权力关系中的地位。例如:
(4)不会的,不会的。自己又没有做过坏事,讲过反话,骂过干部。自己倒是觉得老谷主任、满庚哥他们是自己一屋人,父老兄弟。
Impossible! She had never done anything wrong, never said anything reactionary or sworn at the cadres. To her Manager Gu and Brother Mangeng had seemed like her own family.
原文中胡玉音是意识中心,她对自身的遭遇完全无能为力只能担心害怕,对和其他人的关系也只是在心里猜测,她的惶恐不安充分暴露了她被动弱势的地位。译文则转用叙述者-聚焦者的意识对胡玉音的意识进行评价,对她内心的透视力度减弱,而更倾向于从叙述者的角度描述事实和进行理性分析。意识中心的转换遮蔽了原文胡玉音唯唯诺诺的情绪,使她不再完全处于被压迫的地位,相较于原文权力有所提升。
另外,译文对原文胡玉音内心独白的删减更是直接减少了胡玉音的内心负面情绪,对她在权力关系中地位的提升也有一定的作用。例如:
(5)你是作了什么孽啊,要落得这样苦命,得到这样的报应!
原文通过胡玉音对自己内心的聚焦,展现了她的怨恨和无助。而译文的删减导致了这种内心情感的消失,自然会淡化胡玉音的悲苦命运,对其权力的提升有一定帮助。
5.0 原因分析
5.1 译者的叙述干预
在叙事作品中,各种不同的叙述者均可对其讲述的故事与话语进行干预,叙述者的干预又往往与作者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有许多联系(谭君强,2005:210),因此,叙述者的干预或评论在某种意义上可被视为“作者闯入” (Prince,1987),甚至被直接称为“小说中作者的声音”(Booth,1983)。而从小说翻译来看,翻译文本的叙事实际上代表了真实作者与真实译者两种声音。Chatman(1990:75)认为,“叙事文本‘一旦已经完成或出版,就脱离了真实作者对它的控制。’”而在翻译的叙事交际中,译者作为目的语文本的创造者,他的角色相当于源语文本的真实作者(张景华,2007:61)。由于叙事传统的差异和翻译本身的目的性,译者一般会对原文叙事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操纵或改写,因此译文中叙述者的干预更多的是与译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相联系的。
小说翻译研究不仅要探讨应该如何翻译小说,而且要研究译者为什么这样翻译。换言之,就是要把小说翻译的叙事与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联系起来去分析译者对叙事文本的干预(张景华,2007:60)。20 世纪80 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政治氛围的松动,中西的正常交流逐渐增多。英籍翻译家戴乃迭独特的背景和女性身份使她敏锐地捕捉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潮流,并与国外同仁学者重新建立了联系,这些人中不乏在西方女性运动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学者狄利亚·达文(Delia Davin)等(付文慧,2011:17)。与母语文化的重新对接和这些女权主义者的创见性观点无疑给戴乃迭提供了新的文化视角。同时,在中国的长期生活和坎坷经历令她能深切地了解中国女性面临的现实和问题。为了提升女性地位,使全世界都能听见中国女性的声音,戴乃迭付出了不懈努力。作为《芙蓉镇》的英译者,她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不仅体现在对文本的选择上,还体现在具体的文本操控层面和富有性别意识的译介策略上。从叙事层面来看,《芙蓉镇》中的胡玉音作为代表性的女性人物,原文中对其的聚焦外部和内部并行,而译文基本以外部聚焦为主。译者用叙述者的眼光和表达方式,加上自身的女性意识,减少了对胡玉音的内心透视。这种对胡玉音内心想法和意识的局部“隐瞒”达到的效果正是译者所需要的,即淡化深为男权话语所压迫的胡玉音面临的心理扭曲,增强其行动力和支配力,从而提升这一人物原本处于权力关系底层的地位。戴乃迭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另一方面满怀对当时中国女性的同情。在这两种情感的介入下,她借助叙述者所进行的隐蔽干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译文对胡玉音聚焦方式的变化,从而提升了人物在权力关系中的地位。
5.2 明晰的读者意识
耿强(2010:84)认为,通过文学译介使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项系统工程, 要考虑翻译的质量,更要考虑译本的传播和接受,而后者恰恰决定了我们在译介过程中应该如何选材、采用何种策略等。普列汉诺夫(1983: 581)曾说过“为了使一定国家的艺术家或作家对其他国家的居民的头脑发生影响,必须使这个作家或者艺术家的情绪是符合读他的作品的外国人的情绪的”。也就是说,如果英译中国文学所描述的情绪或生活对英美读者并不陌生,那译本获得青睐的几率就要大很多。《芙蓉镇》中的胡玉音从一开始走向社会就是在男性话语之下被压迫的女性,有着深刻的原罪意识,依靠男性并为男性所救赎。这种性别观念的失衡与当时的西方社会截然不同,因此理解胡玉音这一缺乏自我意识和反抗意识的女性人物对提倡男女平等的英语国家读者而言有一定的困难。正如钱念孙(2001:301)在论及中国文学由民族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所碰到的障碍时所说,“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社会生活及思想道德观念,如果离世界文化发展潮流相距甚远,使异国读者感到非常隔膜甚至莫名其妙,也是妨碍文学由民族走向世界的缘由之一。”
译者是沟通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桥梁。因此,为了让《芙蓉镇》英译本更好地为英语国家读者所接受,避免译文与读者的思维和概念产生强烈冲突,译者必须选择一种有效的方式生成新的文本,参考目的语文学的叙事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对源语文本的叙事形式进行转换或改写(张景华,2007:61)。在不改变情节的基础上,戴乃迭有意识地提升了胡玉音作为女性的地位,增强了她独立自主的意识,弱化了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使译文更好地契合西方国家的平等理念,更容易被读者理解接受。这更加利于英译本的传播和国外读者对中国文革期间社会状况的了解。
6.0 结语
本文基于茅盾文学奖作品汉英平行语料库中的子库——《芙蓉镇》汉英平行语料库,提取了小说中所有与女主人公胡玉音相关的中文语料及其英译,在句子层面上进行了聚焦分类和分析讨论。研究发现,与原文相比,译文对胡玉音的聚焦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而使人物在权力关系中的弱势和被动有所削减,地位得到提升。
首先,叙事理论与翻译的结合,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创新性的研究视角。Baker指出, 包括翻译在内的各种叙事既是现存权力结构的生产者,也是其挑战者,因此翻译可能是颠覆性的 (石永浩,2007:43)。聚焦方式的变化,使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可以直接参与到叙事中,而不是置身于叙事之外。译者本身内嵌于叙事之中,根据不同的聚焦方式促进和传播叙事,并借助各种框架设定,根据各自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利益,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来达到一定的翻译目的。通过不同的翻译策略,译者改变了源语叙事中读者、事件和参与者的关系,改变了译者和文本的关系,拉近了译文和读者的距离,也确定了译者和他们所译文本的关系(黄海军,2008:58)。在《芙蓉镇》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戴乃迭加入了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通过改变聚焦方式而直接介入到叙事之中,从而提升了胡玉音在权力关系中的地位。这使英译本更加契合西方国家的平等理念,促进了译文的传播与接受。本研究结合叙事理论考察文学作品的翻译问题,试图拓展翻译研究的视角和范围,是一项富有挑战性且意义重大的工作。
其次,我们认为,胡玉音这一女性人物在译文中的权力地位得到提升,一方面对《芙蓉镇》作品本身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有利于小说英译本的传播。权力关系,无论宏观还是微观,处处存在并且时时体现着社会阶级及群体的矛盾冲突,因此常常成为文学作品的主题,使作品在具有美学价值的同时获得深刻的社会意义(宋海波, 2005:8)。就《芙蓉镇》这部作品而言,男尊女卑的社会大环境下,权力主要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大多处于被支配地位。这种冲突通过胡玉音这一女性人物的经历和命运体现得淋漓尽致,使权力矛盾成为这部小说的主题之一,赋予了作品更多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意义。译文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胡玉音的权力和地位,原文因权力差异导致的矛盾冲突遭到弱化,也让小说所描述的社会现实带给读者的震撼有所降低,损害了小说原本独特而典型的魅力。但译者赋予胡玉音更多的权力,强调男女平等和女性独立,切合了当时目的语读者的思维和认知,降低了他们理解作品的难度。这有利于提高英译本的接受程度和传播广度,给中国文学被更多外国读者理解和喜欢提供了有效途径。总而言之,在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上,译者应将忠于原文和保持原作的魅力置于首位,在此基础上可以根据目的语国家和读者的需求适当地进行一些调整,以便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出去。
注释:
① 茅盾文学奖作品汉英平行语料库共收录已经翻译出版的8部获奖作品及其英译本(截至2014年8月),中文原文总计2190161字,英文译文总计1086025词。具体收录的文本如下:古华的《芙蓉镇》及戴乃迭译本,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及戴乃迭译本,孙力、余小惠的《都市风流》及关大卫译本,凌力的《少年天子》及关大卫译本,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及关粤华、钟良弼译本,阿来的《尘埃落定》及葛浩文、林丽君译本,王安忆的《长恨歌》及白睿文、陈毓贤译本,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及徐穆实译本。库中所有中文语料经过ICTCLAS 3.0的分词赋码处理,英文语料经过Treetagger 2的词性赋码处理,原文与译文经过ParaConc软件处理和人工调整,在句子层面实现了平行对齐。
② 文中所有数据均通过以下两个步骤获得:1)语料收集:利用ParaConc软件,选取“胡玉音”“玉音”“她”“自己”等关键词进行穷尽性搜索,再对所得数据进行筛选,查漏补缺,收集与胡玉音相关的所有原文和译文语料,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2)语料分类:按照聚焦者与故事的位置关系、聚焦者、聚焦对象和聚焦行为在句子层面上对语料进行逐一分类,分别得出原文和译文的数据,保证数据的客观性和有效性。
③ 此处“其他人物”对“其他人物”的聚焦并非指其他人物对自身的聚焦,而是指其他人物在其内心活动中对胡玉音的想法与评价,从而反映出胡玉音在权力关系中的地位,因此列入对胡玉音的聚焦中。
[1] Booth, W. C.TheRhetoricofFiction(2n e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2] Chatman, S.ComingtoTerms:TheRhetoricofNarrativeinFictionandFilm[M].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3] Prince, G. J.ADictionaryofNarratology:TheStructureoftheArtistictextandTypologyofaCompositionalForm[M]. V. Zavarin & S. Witting (tran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7.
[4] Uspensky, B.APoeticsofComposition[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5] 费维达. 虚构叙事作品中的聚焦问题再探[J].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6,(2):92-96.
[6] 付文慧. 多重文化身份下之戴乃迭英译阐释[J]. 中国翻译,2011,(6):16-20.
[7] 耿强. 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出去[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3):82-87.
[8] 黄海军. 叙事视角下的翻译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7):56-59.
[9] 胡亚敏. 叙事学[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0] 里蒙·凯南. 叙事虚构作品[M]. 姚锦清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9.
[11] 米克·巴尔. 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 谭君强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2] 普列汉诺夫. 亨利克·易卜生[A].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C]. 曹葆华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3] 钱念孙. 文学横向发展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14] 尚必武. 叙述聚焦研究的嬗变与态势[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6):13-21.
[15] 申丹. 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6] 石永浩. 《翻译与冲突:一个叙事的视角》简评[J]. 中国翻译,2007,(2):43-45.
[17] 宋海波. 及物性系统与权力关系——对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苍蝇》的文体分析[J]. 国外文学,2005,(4):97-104.
[18] 谭君强. 论叙事作品中“视点”的意识形态层面[J]. 文艺理论研究,2004,(6):55-64.
[19] 谭君强. 叙事作品中的叙述者干预与意识形态[J]. 江西社会科学,2005,(3):209-217.
[20] 王林. 句子上的叙事:谈自由间接话语的翻译处理[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2):294-302.
[21] 辛斌. 语言语篇权力[J]. 外语学刊,2003,(4):1-6.
[22] 杨斌. 英语小说自由间接引语的翻译[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2):71-75.
[23] 张景华. 叙事学对小说翻译批评的适用性及其拓展[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6):57-62.
[24] 赵莉华,石坚. 叙事学聚焦理论探微[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12):230-234.
[25] 郑敏宇. 小说翻译研究的叙事学视角[J]. 外语研究,2001,(3):6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