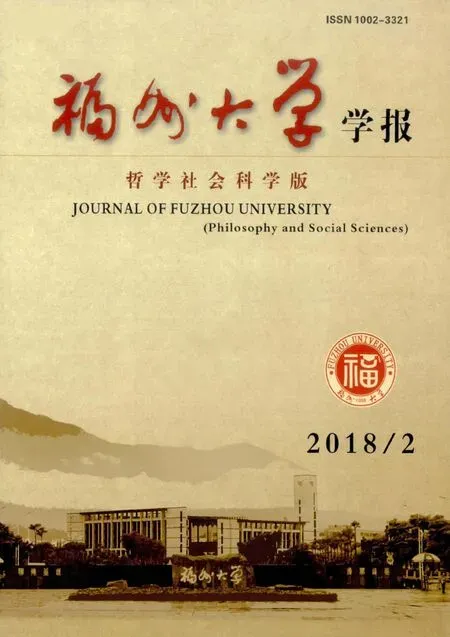旁观者的打量
——清代教外文人涉教诗歌探究
李 莎 吴巍巍
(1.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7;2.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 福建福州 350007)
早在明代末期,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利玛窦等人来华传教,当时的中国人已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和宗教世界有了一定的接触与了解,当时的文人特别是一些上层士绅官员如叶向高、徐光启等也与东来的传教士们有过较近距离的接触,但毕竟时间较短,传播范围十分有限。随着明朝的覆灭以及清初的礼仪之争,最终导致康熙、雍正年间的彻底禁教,失去了这一传播中介,中国人接触西方世界的机会进一步减少,以至时隔百余年,国人对西方异域更加陌生,有幸接触到外部文明的一些教外文人们带着各种眼光、怀着各式心情,借着基督教文化的一角,对以之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进行旁观,用诗笔描摹他们所看到的异样世界。笔者特从部分诗文材料[1]中撷取内容与基督教相关者,在对诗人身份进行补充考证后,将这些诗作的概况按作者的时代顺序整理一番,从中探寻清代教外诗人们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所思所想。
一、诗作涉及的主要地点
诗作所涉及的教会教堂主要集中在香港、澳门、北京、上海、广州这五个地区,且以澳门地区最多。见表1。

表1 部分清代诗人与其涉教诗作
续表1

作者身份生卒年诗名所写地点所涉宗派杜臻官员1633-1703《香山澳》澳门天主教成鹫(方觊恺,迹删)僧侣、反清志士1637-1722《咏大三巴寺》澳门天主教刘世重官员?-1702《澳门》澳门天主教梁迪官员康熙年间《西洋风琴诗》澳门天主教李珠光贡生康雍年间《澳门》(两首)澳门天主教王轸乾隆年间《澳门竹枝词》澳门天主教黄呈兰乾隆年间《青玉案·澳门》澳门天主教汪后来官员1678-?《澳门即事》(第四首)澳门天主教金采香《澳门夷妇拜庙诗》澳门天主教印光任官员1691-1758《三巴晓钟》澳门天主教程廷祚学者1691-1767《忧西夷篇》天主教全祖望学者1705-1755《二西诗》《明司天汤若望日晷歌》北京天主教赵翼官员,史学家1727-1814《同北墅漱田观西洋乐器》北京天主教赵怀玉官员、学者1747-1823《游天主堂即事》天主教陈官诸生乾隆年间《澳门竹枝词》《望濠镜澳》澳门天主教张汝霖官员乾隆年间《寄椗青洲饭罢抵澳》《澳门寓楼即事》之七澳门天主教彭昭麟官员1749-?《澳门纪事》其三澳门天主教潘有度商人1755-1820《西洋杂咏》之三、之八、之十六广州天主教李遐龄学者1768-1832《澳门杂咏》澳门天主教钟启韶举人1769-1824《澳门杂诗》其二、其七澳门天主教廖赤麟诸生1775-1823《澳门竹枝词》澳门天主教张琳《澳门竹枝词》澳门天主教叶廷勋官员1775-1832《于役澳门纪事十五首》之七、十澳门天主教叶廷枢《澳门杂咏》澳门天主教黄德峻官员道光年间《澳门》澳门天主教陈昙诸生1784-1851《十字门》澳门天主教仪克中举人1796-1838《昔游诗效姜白石》其八澳门天主教鲍俊官员1797-1851《行香子·澳门》澳门天主教何绍基官员1799-1873《乘火轮船游澳门与香港作往返三日约水程二千里》香港、澳门苏廷魁官员1800-1878《西洋人汗得能汉语,略解鲁论文义,介通事杨某谒余问字,歌以纪之》单子廉《耶苏》澳门天主教蔡显原《听西洋夷女操琴》澳门天主教邱对颜《澳门》澳门天主教吴友如画家?-1894《调寄菩萨蛮红礼拜堂》上海圣公会郑观应实业家、思想家1842-1922《澳门感事》澳门天主教黄遵宪外交官、思想家1848-1905《香港感怀》其三、《寄女》其三香港圣公会夏曾佑官员1863-1924《绝句》
由表1可见,这些教外文人的出生年代最早的起于明末,那也正是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开始来华传教的时代,不过这部分诗人主要活跃于清初;另有不少诗人主要生活在清代早期的康雍乾时期,当时天主教来华传教虽已近百年,但比起佛道二教两千多年的流传与本土化发展,基督教在时人眼中仍然是属于新奇事物;此外,清末解除教禁后的部分文人也有部分涉教诗歌作品。以下逐次分析这些诗歌所反映出的清代基督教在华发展的一些现象。
澳门在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被葡萄牙人非法圈占,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葡萄牙人经与清政府签订《中葡会议草约》《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两本外交文书,正式占据澳门。而香港的香港岛则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就被英国人强行占走,英国人后来陆续通过1842年的《江宁条约》(《南京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新界租约”)步步蚕食港岛、九龙、新界三地。澳门与香港分别被葡人、英人占据,受西方影响较深,基督教在这两地特别是澳门留下的烙印最为深刻,其中澳门“成为天主教发展远东教务的中心,建立了吸引东方人进教和培养传教士的玛尔定堂”[2]。而清代的文人们一旦有机会离开清政府所统治的封闭、内敛的大陆,也往往首先踏足港澳,观察这两个华洋杂处、中西文化碰撞的地方。而由于雍正年后的教禁,基督教在大陆地区受到严格的压制,港澳尤其是澳门就成了清代诗人观察基督教的主要地区。
上海早在明末就已开教,是江南地区天主教发展最为迅速的地方[3];至于广州,则是大陆沿海的前哨,更是鸦片战争之前唯一一个开放对外贸易的地方[4],借用清代官员王邦畿的《海市歌》来形容,此地真是:“虹霓驾海海市开,海人骑马海市来。”陈永正指出:“清初诗人每以‘海市歌’为题,当以海市喻日渐发达的海上贸易活动,借助神话故事描述其光怪陆离的情景。”[5]早在1844年的《中法黄埔条约》中就有法国天主教可在“五口”之地建造教堂的条款,《南京条约》则进一步确立了广州、上海等开放的五口允许传教,其中上海于1843年开埠,广州则因人民的抵抗,到1859年《沙面租界协定》签订后,才有公开的传教活动。[6]
明末耶稣会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抵达澳门,次年北上端州(广东肇庆),明万历十六年(1598年)抵京;同样出自耶稣会的德国人汤若望的脚步比利玛窦稍晚,他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登上澳门,开始其在华传教之旅,明天启二年(1622年)来到广州,明天启三年(1623年)抵达北京,清顺治八年(1651)授职太常寺卿。观察这二位耶稣会士在华的活动轨迹,正好都经历了从澳门到广东最后到达北京的路线,而这三个地方是明末清初天主教来华开辟的早期重要据点,也都留下了中国诗人对天主教活动的大量观察与记录,这不能不说是以诗证史的又一例据。
从以上诗作所涉的基督教教派来看,当以天主教占绝对优势,仅吴友如、黄遵宪作品论及圣公会,盖因新教进入中国时代较晚,一般的观点认为基督新教来华起于1807年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入华传教,不过徐晓鸿认为早在17世纪,荷兰传教士已跟随荷兰殖民者由印度尼西亚潜入台湾,所以马礼逊来华应视为新教进入大陆的首人,而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台湾的新教传播应当放在时代的最前列。[7]
二、诗作中的教友与传教士形象
在多首诗作中,传教士的形象是这样的:
中有虬须叟,出门讶迎客。来从大西洋,宫授羲和职。年深习汉语,无烦舌人译。引登天主堂,有象绘素壁。靓若姑射仙,科头不冠帻。云是彼孔周,崇奉自古昔。(赵翼《同北墅漱田观西洋乐器》)
这位引导赵翼参观北京天主堂的老人来自西洋,赵翼用“羲和”的身份对其下定义。羲和在神话传说中是驾御太阳的神,《广雅·释天》曰:“日御謂之羲和,月御謂之望舒。”羲和又或为女神,其后代就是太阳,《山海经·大荒南经》曰:“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后来羲和进一步演化为职掌天文的历官。明末利玛窦等西洋传教士入华,引介了大量西方的数学、历法、光学等知识,制造了多种天文仪器,开启了中国天文学受西方影响的新阶段;[8]汤若望在明代崇祯年间曾参与修正历法,至清初又率领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奉教的天文学家成为钦天监的主力,展示了西洋历法的先进之处。[9]明末清初的官员陈名夏、清代学者全祖望就分别用“天官”“太史令”“司天”来称呼汤若望(字道未),如陈名夏《西洋汤道未先生来》:“沧海十万里,来任天官篇。占象见端委,告君忧未然……公为太史令,洛下诚并贤。”全祖望《明司天汤若望日晷歌》:“测天量日真古学,九章五曹远可寻……岂期礼失求之野,欧罗巴洲有遗音……何物耶稣老教长,西行夸大传天心……司天大监汤匦使,若望以通政使掌监事。”[10]
赵翼所见的老传教士不仅精通天文知识,还熟练掌握汉语会话,“年深习汉语,无烦舌人译。”何绍基笔下的在港传教士也是如此:“渐染中华仓圣学,同文福音资考诹。”(何绍基《乘火轮船游澳门与香港作往返三日约水程二千里》)何氏诗中的“仓圣”当指造字的“仓颉”,这些传教士来华后,已逐渐掌握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并且开始了翻译介绍的工作,其中福音文字的译介当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蒋英豪指出,“香港开埠以后,基督教会的传教、教育事业从马六甲、澳门等地迁来香港,香港成为印刷和流布中文《圣经》的中心。”[11]
赵翼诗中的“姑射”典出《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赵氏在教堂中看到壁画上的形象仿佛中国上古神话中的仙人般优美,更妙的是,老人还解释说,这位他们所崇奉的神就相当于中国的周公与孔子,从古至今都受人尊崇,这位传教士真是对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接受心理太为了解了。
又如杜臻《香山山奧》:“扶杖穿屐迎道左,稽首厥角语嗢咿。自言慕义来中夏,天朝雨露真无私。世世沐浴圣人化,坚守臣节誓不移。”这哪里是西洋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分明是士人心中理想的中国臣子典范。这种形象,也与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会士利玛窦、艾儒略等人相似,他们远道而来,仰慕中华,借用明代张穆的《登望洋台诗》来形容就是“西夷近咸池,重译慕大汉。”他们身着儒服、读四书五经,自称西儒[12],以儒学比附天学,艾儒略甚至被时人称为“西来孔子”,而利玛窦逝世后,直至清初尤侗造访北京时都还追奠道:“阜城门外玫瑰发,杯酒还浇利泰西。”[13]杜氏诗笔之下的澳门传教士老者虽有美化之嫌,却仍然是明末天儒合一理想的再现。是以杜氏对其也有很高的期望:“薄海内外无远迩,同仁一视恩膏施。还归寄语西洋国,百千万祀作藩篱。”
杜臻(1633-1703),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曾担任内阁学士,并在礼部、吏部、工部、刑部等处任过侍郎、尚书之职,作此诗时正与另一名钦差大臣石柱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视察广东、福建沿海,其后撰写《粤闽巡视纪略》[14],论述广东、福建的地理形胜与海防情况,杜臻的访澳诗作当可与此专著互相印证。章文钦认为这几句话不只是慰勉老人的恭顺,更是汇报给北京的康熙帝看的。[15]不过很可惜,在坚船利炮之下签订的《北京条约》解除了基督教来华传播的限制之后,这种温文尔雅带有儒士气质的传教士就很少见了,而寄望洋人自甘为中华藩篱更是一厢情愿的空想。
三、诗作中的教会活动
诗人们笔下的教会活动非常热闹,教友包含各色中西男女,特别是像“红鬼子、白蛮娘、夷妇”这样的西方面孔,无不提醒着诗人们这里具有的“半华夷”[16]特色,王轸的《澳门竹枝词》甚至别出心裁,描写了一位葡萄牙少妇在参加教堂礼拜前的心理状态。如:
礼拜三巴寺,番官是法王。花满红鬼子,宝鬘白蛮娘。(屈大均《澳门·其四》)
相逢十字街头客,尽是三巴寺里人。(成鹫《咏大三巴寺》)
三巴门内瑞烟开,夷妇殷勤礼拜来。氤氲人气绕日永,氤氲人气绕莲台。(金采香《澳门夷妇拜庙诗》)
心病恹恹体倦扶,明朝又是独名姑。修斋欲祷龙松庙,夫趁哥斯得返无。(王轸《澳门竹枝词》)[17]
陈永正认为,明清时代歌咏澳门的诗作多以“女尊男卑”“法王尊”为题材,如印光任《澳门记略》里说西人“重女而轻男,家政皆女子操之,及死,女承其业”,这些都是“耳食之词”,[18]是没有根据的言论。如陈官《澳门竹枝词》:“生男莫喜女莫悲,女子持家二八时。昨暮刚传洋舶到,今朝门户满唐儿。”陈官的诗句与唐代白居易的《长恨歌》略有相似,后者歌曰:“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杨贵妃得到唐明皇的宠爱,以至于一家都富贵荣华,但这种重女轻男的思想是建立在对权贵男子的人身依附之上的,其本质仍然是重男轻女,而明清诗歌中的重女轻男显然不是如此。
其实诗人们的言辞虽有夸张的成分,但他们确实注意到相对于大陆境内依然奉行的封建礼教、男女大防,受到西方文化与洋教冲击的殖民地,相对来说,男女间的界限稍微宽松一些,女子的行事也较为便宜,而夷妇(西方妇女)的大胆与自由尤甚,妇女的权利和地位都有相对提高(下文将要提到的关于自主婚姻的诗句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在诗歌中热烈地描绘这一新现象,客观说来,这反映的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和诗人民主意识的提升。
教徒结婚不是凭媒妁之言、不是经三书六礼,而是去教堂由神父主持的:
婚姻自择无媒妁,同忏天堂佛国西。(潘有度《西洋杂咏·之三》)
何时佛前交印去,订婚来乞比邱尼。(尤侗《佛郎机竹枝词》)
戒指拈来杂异香,同心结就两鸳鸯。嫁郎未必他年悔,生子还当付法王。(陈官《澳门竹枝词》)
潘有度是清代乾嘉时期广州十三行的总商,他所见到的是广州教徒自择婚姻的情形,由于雍正年间已经实施禁教的措施,所以潘氏所写的并非华人而是“夷人”(洋人)的结婚形式,他还在诗后特别附注,介绍夷人一夫一妻、不纳妾的自由婚恋风俗,并对此抱以欣赏的态度。而尤侗、陈官讲述的则是澳门的情况,这就与大陆地区大有不同了。
李鹏翥指出,自雍正年间禁教后,“华人教友领洗时,多以葡名入领洗册,并进入澳门城寨内居住,仿佛放弃了中国国籍,进入葡国人的生活圈子里,被称为‘进教’”。李氏并引用了澳门海防同知张汝霖于乾隆十四年(1749)所上的《查禁澳门民人进教密揭督抚奏章》[19]:
惟澳门唐夷杂处,除夷人自行建寺不议外,其唐人进教者,或在澳进教;或每县每年一次赴澳进教。其在澳进教者,或变服,或不变服,或娶夷女长子孙,或藉资本营贸易,或为工匠,或为兵役,或但打鬼辫来往夷人家,亦自附于进教,以便交往。
夫非圣人之书,为名教所必斥,非王者之道,即盛世所不容。况以天朝之人,而奉外夷之教,则体统不尊,且恐夷性之狡,将滋唐匪之奸,则防微宜急也。
朝廷的禁教,拦住了大陆上的普通民众,却拦不住租借地澳门人民的“变通”,他们用葡萄牙语的名字受洗,又进入澳门城寨中居住,甚至改变服装,或与西方人通婚。官府没证据、管不着,虽鞭之长而不及进教之民也。上文提过的陈官《澳门竹枝词》说:“生男莫喜女莫悲,女子持家二八时。昨暮刚传洋舶到,今朝门户满唐儿。”陈永正认为末尾两句的“唐人”可能是指中国人向洋人求婚[20],如果此说为确,则就有可能是当时的华人为进教而主动采取的联姻活动。禁教令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非常荒唐的变形,这些脱离官方管控的法外教民着实令朝廷头疼不已。联想到再过一百多年解除教禁后治外法权、民教冲突遍地开花的景象,不禁令人感叹,小小的一个澳门飞地,其实已是清代晚期基督教发展乱象的缩影与预演。
四、诗作中的教堂建筑及其他西洋事物
至于诗中所涉的基督教教堂建筑(包括内部陈设的风琴等),上文所摘金采香《澳门夷妇拜庙诗》中已有教堂氛围的描写,再如:
峨峨番人居,车过常远眺。(赵怀玉《游天主堂即事》)
堂高百尺尤突兀,丹青神像俨须眉。金碧荧煌五彩合,珠帘绣柱围蛟螭。(杜臻《香山山奧》)
西洋风琴似凤笙,两翼参差作凤形……奏之三巴层楼上,百里内外咸闻声。(梁迪《西洋风琴诗》)
天主堂开天籁齐,钟鸣琴响自高低。(尤侗《欧罗巴竹枝词》)
有别于新教建筑的朴素,多位诗人笔下的天主教的教堂建筑都以高大辉煌著称,广为人知而屡屡入诗的澳门圣保禄教堂(大三巴),则是“巍峨壮观,雕刻精美,三百多年前的造价已达三万两银之巨。”[21]至于清代画家吴友如笔下的上海圣三一堂,则隶属英国圣公会,是其远东上海地区英语圣公会的主教座堂,采用新哥特式红砖建筑风格,故又称红礼拜堂。虽然圣公会不承认教宗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视为新教,但其实“亨利八世的改革保留了天主教的教义、仪式,英国圣公会成为保有天主教色彩最为浓厚的新教派。”[22]圣三一堂的华美壮丽自然也与其它天主教建筑一样在诗歌中再现。如吴友如《调寄菩萨蛮·红礼拜堂》言:“红墙隐隐云中见,琉璃作栋金为殿。”
晚清外交家、诗人黄遵宪曾五次到访香港,《香港感怀》组诗约作于1870年,当时他年仅23岁,还在应考科举的路上徘徊不前,这段时期他正好阅读了《中国教会新报》(《万国公报》)和制造局的译著,人生观已有不小的转变。在港期间,黄氏也把笔触伸向了基督教的世界。
酋长虬髯客,豪商碧眼胡。金轮铭武后(黄氏自注:香港城名域多利,即女主名也),宝塔礼耶稣。(黄遵宪《香港感怀》其三)
宝塔高十层,巍峨天主堂。(黄遵宪《寄女》其三)[23]
身处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黄遵宪把香港总督称为“酋长”,“金轮铭武后”则是将英国女王域多利(按:即维多利亚)比作篡夺唐朝政权的“武后”(武则天,曾先后自上尊号为“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册金轮圣神皇帝”[24]),这两处对英国官员和女王的称谓都是含有贬义的。而“天主堂”写的是香港圣约翰座堂,它是香港圣公会香港岛教区的主教座堂,其钟楼即黄氏笔下的“宝塔”。晚清诗人习惯沿用佛教术语来称呼他们不太熟悉的基督教的人和事,比如上文所引的尤侗的《佛郎机竹枝词》就用“佛”比耶稣、用“比邱尼”代指神父,陈官的《澳门竹枝词》、屈大均的《澳门》其四都以“法王”来指称天主教会的“主教”。
顾卫民将基督宗教艺术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粗略分为四个阶段,其中的第三阶段即是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至 19世纪末,在这一时期“耶稣会努力适应中国文化,无论在宣教方式、语言文字以及图画方面均极力提倡本地化;另一方面,葡萄牙、法国以及英美的建筑及绘画风格都在中国各地出现了,总的来说,后一种倾向超过了前面一种,因此这一时期艺术上的殖民特征是十分浓厚的。”[25]比起那些越来越中国化的佛教寺院,这些外形风格迥异于中国传统建筑的西洋基督教教堂,理所当然地夺人眼球,也成为了众多诗人竞相描写的对象。
杜臻有诗《香山澳》:“西洋道士识风水,梯航万里居于斯。”《明史·列传·外国七》曰:“大都欧罗巴诸国,悉奉天主耶稣教……至万历九年,利玛窦始泛海九万里,抵广州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诸如“梯航九万里”这样的诗句,在明末清初的士人赠诗中屡见不鲜,例如明代几位官员、士人的诗句:
西来九万里,东泛一孤槎。(李日华《赠利玛窦》)
吾爱艾夫子,梯航九万里。(林焌)
西国有异人,其来九万里。(陈宏己)
风航九万里,挟策到中州。(李文宠)
九万里西来,天学开远照。(翁际豊)
君乃舫西海,九万里而至。(郑凤来)[26]
而杜氏到了清代,依然在诗中啧啧惊叹于西洋人的航海技术,并且将之类比于不可理喻的风水之术,这其实也侧面反映了明末清初中国在科学技术上已逐步落后于西方的事实,国人惊叹西人九万里远来中土,自满于西人孺慕中华,却没想过为什么国人不能反向九万里去西方世界看看。
明清时期描写西洋事物而丝毫不涉及基督教的诗歌作品数量远比涉教作品更多,而上文所述清代诸位教外诗人除了赋笔于基督教外,也大多同时描写了其他一些对时人来说既新鲜又好玩的西洋事物。明清文人笔下所记的西洋玩意儿小到眼镜、望远镜、显微镜、玻璃镜、三棱镜、凸透镜、鼻烟、香烟、钟表、照相机、地图、绘画、香烟、纺织品,大到风琴、活字印刷机、火炮、水匮、甚至还有马戏等,如下面几位清代诗人的诗作:
大道粲中天,奇淫出穷海。兹镜西洋来,微显义兼在。(陈子升《咏西洋显微镜》)
神灵应莫测,人力几能通。(林古度《观大西洋自鸣钟刻漏》)
机缄动止那可没理,见者疑同神鬼游。此器徒闻出西域,估客新从舶中得。(彭孙遹《西洋琥珀酒船歌》)
蜂拥而来的西洋新奇事物,其实正是当时西方国家科技领先、物质文明大发展的客观体现,遗憾的是,大部分诗人在其诗作中,勤于描绘、罗列所谓的“奇技淫巧”(如陈子升诗),但也不过慨叹几句神秘莫测、人力不通(如林古度、彭孙遹诗),却疏于、懒于关心这隐藏在背后的中西文明落差,甚至有些极端的时人鄙视这些所谓的奇技淫巧,认为应该通通摒弃,例如,嘉庆道光年间的诗人陈春晓《夷船来》曰:“南风薰,夷船来,皇恩浩荡海门开。海不扬波捧红日,中国圣人知首出。许尔夷船输货实,奇技淫巧悉罢黜。天朝柔远始通商,不贵异物诏诰说。岂知尔土产最恶,阿芙蓉乃腐肠药。”诗人虽然认识到鸦片的罪恶,但却将西洋物产一棍子打翻,并把本应平等的中外贸易看作是皇上的恩典,这种意识上的短板可谓为后来的中西冲突埋下了隐患。
五、诗作体裁与诗歌背后潜藏的文人隐忧
而在创作的体裁上,除了传统的近体诗以外,又有多首诗作都运用了“竹枝词”的形式。竹枝词至少在唐代已经流行开来,原本兴起于四川东部至湖北西部的长江流域民间,中唐诗人对此种诗歌形式多有提及,顾况、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更亲自参与了竹枝词这一民间诗歌体裁的创作,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后世文人以此进行诗歌创作的更多,诗歌的吟咏和创作地点也扩展到了非长江流域的其他多个地区[27],在题材方面,除了常见的对男女爱情的歌咏以外,也不乏对民间风土人情的写照,“历代文士骚人多有以竹枝词形式记述民间风情者,进而以此描画世俗,讽论政事,寄托相思。”[28]
竹枝词形式的运用,也间接可见这些诗人对基督教的态度多为旁观欣赏,是将基督教风物包括传教士本人与其他西洋来的东西等而视之,认为这些同属新鲜有趣的异域风情。单子廉有一首诗作《耶苏》:“远人苟已服,有此等越巫。”章文钦认为,单氏的意思是葡萄牙人若归顺中华,则其所信的宗教也可视为“越巫”一类的“夷俗”。[29]不过从竹枝词的广泛运用来看,不论远人服与不服,都早以作为一种诗人热衷的“夷俗”入诗了。
与之形成反例的是,蒋英豪指出,近代海外记游诗多用竹枝词写成,但是在香港题材上却很少见,仅王韬所作的《吴香圃以香港竹枝词嘱诗口占答之》采用了这一形式,而且篇幅较短,远不及晚清其他海外竹枝词那样长篇累牍、数量庞大,虽然时人也希望读到香港竹枝词,但是“由于香港的历史烙印,都倾向于写较严肃的主题,因此也就较少用竹枝词这种较轻松活泼佻皮的诗体了”[30]。
教外人士除了用竹枝词等轻松的形式外,他们对基督教的理解也主要停留在教堂建筑、演奏器具、传教士的特殊行为等较为肤浅的层面,尚未触及基督教的精神本质,也来不及或者没考虑过其精神特质。借用两句明末清初官员丁耀亢的诗,说到底,这些文人眼中的基督教只是西洋镜下形形色色、光怪陆离、令人神游志移的众多画片中的一张罢了,如丁耀亢《同张尚书过天主堂访西儒汤道味太常》云:“璇玑法历转铜轮,西洋之镜移我神。”成鹫《咏大三巴寺》:“年来吾道荒凉甚,翻羡侏离礼拜频。”成鹫在澳门亲眼所睹天主教发展的兴盛,作为一代名士、反清战士、名僧,他深深地感受到了佛教相形之下的衰颓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威胁。章文钦认为成鹫的诗作《青洲岛》即是以疯狗和饿鹰来隐喻天主教士[31],由此可以想见天主教发展对成鹫这样的传统士人及佛教中人所造成的震撼与威胁。
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生于明末,青年时代即投身反抗清朝的斗争之中,他早年游历廉州(旧属广东,今属广西合浦)时,就已对沿海地区的形势表示了忧虑,在广州、澳门期间,他看到了华洋矛盾,看到了洋人器具的精巧,看到了天主教对民间信仰的争夺,尽管他将洋人来华贸易视为“进贡”,但他却以一名军事家的敏锐眼光, 察觉到了盘踞在此的西洋势力会对广东造成极大的威胁。他的诗歌一再反映了他的这种认识:
赤子兵频弄,红夷舶恐来。边墙殊未筑,潜移默化已先开。此地成云朔,劳君鼓角哀。(《廉州杂诗》其十)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广州竹枝词》其四)
抄官使者三门海,进贡番人万里舟。舶口至今蠔镜失,西洋端恐有阴谋。(《白鹅潭眺望》其四)
广东诸舶口,最是澳门雄。外国频挑衅,西洋久伏戎。兵愁蛮器巧,食望鬼方空。(《澳门》其一)
香火归天主,钱刀在女流。筑城形势固,全粤有余忧。(《澳门》其二)
不过说到对天主教最为反感、警惕性最高的当属学者程庭祚,其《忧西夷篇》言:
迢迢欧逻巴,乃在天西极。无端飘然来,似观圣人德。高鼻兼多髭,深目正黄色。其人号多智,算法殊精特。外此具淫巧,亦足惊寡识。往往玩好物,而获累万真。残忍如火器,讨论穷无隙。逢迎出绪馀,中国已无敌。沉思非偶然,深藏似守默。此岂为人用,来意良叵测。侧闻托懋迁,绝远到商舶。包藏实祸心,累累见蚕食。何年袭吕宋,翦灭为属国。治以西洋法,夜作昼则息。生女先上纳,后许人间适。人死不收敛,焚尸弃山泽。惨毒世未有,闻者为心尽。非族未何为,穷年寄兹域。人情非大欲,何忍弃亲戚?谅非慕圣贤,礼乐求矜式。皇矣临上帝,监观正有赫。
程庭祚(1691-1767),号清溪居士,康乾间著名学者,他对西人“无端飘然来”深表疑虑,认为他们居心叵测、包藏祸心。程氏也对西人的“多智”、算法之精特、“淫巧”、火器之强大深感震惊,发出了“中国已无敌”的惊呼。程庭祚还了解到西班牙人早已吞并了吕宋(菲律宾),则中国也有被其“蚕食”的危险。程式并批评了火葬的西式习俗,说他们“惨毒世未有”。所以究其本质,这些西洋教士的内心“谅非慕圣贤”。不过程氏一时之间也拿不出对策,只能正告说“皇矣临上帝,监观正有赫”。此句典出《诗经·大雅·大明》:“上帝临女,无贰尔心。”程廷祚化用了诗经名句对西洋人予以警告。同样是“上帝”,不过程氏倚赖的是监视传教士的中国上帝。
比程廷祚稍晚的全祖望同样持有较激烈的意见。全祖望(1705-1755),康乾时代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曾前后讲学于绍兴蕺山书院和广东端溪书院,特别是他在广东的讲学对塑造与推动南粤学风的形成颇有助力。全氏既是著名的史学家也是优秀的文学家,著有《二西诗》:
三危旧是中原地,分比苗民尚有存。其在五灯亦无赖,偏于诸部独称尊。诲淫定足招天谴,阐化空教种祸根。安得扫除群孽净,不教西土惑游魂。右乌斯藏。
五洲海外无稽语,奇技今为上国收。别抱心情图狡逞,妄将教术酿横流。天官浪诩庞熊历,地险深贻闽粤忧。夙有哲人陈曲突,诸公幸早杜阴谋。右欧罗巴。[32]
《二西诗》两首末尾分别标明为:“右乌斯藏”与“右欧罗巴”,按古人的习惯,左为东,右为西,所以这两个“右”指的是“西”。蔡鸿生认为,题名中的“二西”是指“西域”和“西洋”,不是地理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乌斯藏”与“欧罗巴”,即指“藏传佛教”与“天主教”。[33]在“欧罗巴”部分,全氏说道:“五洲海外无稽语,奇技今为上国收。”指责西人玩弄奇技淫巧,认为他们另有所图:“别抱心情图狡逞,妄将教术酿横流。”全氏看穿了西人的企图是想让西方宗教在中国大肆传播,即使是一向受人好评的“天官”“庞熊”(西班牙人庞迪我、意大利人熊三拔,两人都是耶稣会会士),全氏也认为他们只有浮夸“浪诩”之虚名。最后全氏重申成语“曲突徙薪”,望众人及早识穿西人教士的阴谋,防患于未然。陈垣认为全祖望的这首诗代表了当时国人的心理,对西人过于怀疑猜忌,以至于连累到了基督教,这是“教之不幸也”。[34]不过全氏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且这种忧虑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已有应验,这不仅是教之不幸,也是中国之不幸。
郑观应有《澳门感事》诗:“澳门上古多莲峰,鹊巢鸠占谁折冲。海镜波平涵电火,山屏烟起若云龙。华人神诞喜燃炮,葡人礼拜例敲钟……外埠俱谓逋逃薮,各于频闻卖菜佣。商务鱼栏与鸦片,饷源以赌为大宗。”郑观应是清末实业家兼维新思想启蒙家,曾撰写《救时揭要》《盛世危言》等著作,在他隐居澳门的六年间,观察到华洋信仰交错的现象背后对应的是葡萄牙人对澳门巧取豪夺、鸠占鹊巢的历史背景,而在这种畸形的政治制度之下,美丽的澳门成了藏匿逃犯、赌博泛滥的地方。
透过熙熙攘攘的信教人群和蓬勃旺盛的基督教文化表象,从清初的成鹫、屈大均到清中期的程廷祚、全祖望,再到清末的郑观应,为数不多的士人敏锐地观察到了潜流下的波涛涌动,正如上文提及的郑观应诗句:“海镜波平涵电火”,中国的大变局早已是酝酿待变了。
六、小 结
自清代康雍年间的禁教之后,基督教在大陆的公开活动多数转入地下,国人对基督教及其背后的西方文明日渐陌生,不少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文化的教外文人大都对其抱以好奇的心态,他们的涉教诗作对基督教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打量,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中西文化的差异与融合,亦可见当时中西历史发展之落差。部分诗人如屈大均、程廷祚等人更以其敏锐的历史目光,察觉到了基督教文化背后所潜藏的危机,对西方人的野心与企图表示担忧。对清代教外文人所作的涉教诗歌进行探究,正是用“以诗证史”的方法,从诗歌的角度考察清代历史发展的轨迹,探寻中西文明的碰撞与冲突。
注释:
[1] 下文所引诗歌凡未标明原诗集者,均参见以下著作。[清]张应昌:《清诗铎》,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赵春晨点校,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王慎之、王子今:《清代海外竹枝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陈永正:《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蒋英豪:《近代诗人咏香港》,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张永芳:《近代诗歌选注》,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钱仲联:《清诗纪事》,南京:凤凰出版社,2003年。
[2] 徐晓鸿:《清代文人诗歌中的洋教与洋俗(一)》,《天风》2011年第11期。
[3] 罗伟虹:《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页。
[4] 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对外开放的四个贸易口岸不断萎缩,至乾隆二十二年(1775),清政府宣布仅有广州能从事对外一口贸易。参见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0年,第26页。
[5] 参见陈永正:《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第198页注释1。
[6] 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7] 徐晓鸿:《基督新教何时传入中国》,《天风》2006年第12期。
[8] 参见林金水:《利玛窦在中国的活动与影响》,《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9] 参见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页。
[10] 全祖望在此诗名下自注曰:“得之南雷黄氏”,按:南雷黄氏当指黄宗羲,黄氏字太冲,号南雷,系明末清初学者。初时汤若望赠黄宗羲以日晷,后来此物辗转为全祖望所有。参见[清]全祖望:《鲒埼亭诗集》卷二,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061页。
[11][30] 蒋英豪:《近代诗人咏香港》,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0,9页。
[12] 参见罗伟虹:《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13] 见[清]尤 侗:《欧罗巴竹枝词(其二)》,尤氏更在诗后附注曰:“利玛窦始入中国,赐葬阜城门外二里沟,曰利泰西墓。天主堂有自鸣钟、铁琴、地球等器。国中玫瑰花最贵,取蒸为露,可当香药。”参见[清]尤 侗:《外国竹枝词·海外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8页。
[14] [清]杜 臻:《粤闽巡视纪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15] 章文钦:《明清时代中国官员对澳门的巡视》,《澳门历史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0页。
[16] 见何绍基《乘火轮船游澳门与香港作往返三日约水程二千里》:“澳门半华夷,香港真外国。”
[17] 独名姑、哥斯:分别是葡萄牙语“礼拜日”与“海岸”的译音。参见陈永正:《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第289页。
[18] [20]陈永正:《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第271,310页。
[19] [21] 李鹏翥:《澳门古今》,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0年,第130,4页。
[22] 党翼鹏、张晓华:《漫漫合一路——罗马天主教与圣公会关系钩沉》,《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1期。
[23] 黄遵宪诗参见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24] 参见《旧唐书》卷六本纪第六《则天皇后》;《新唐书》卷四本纪第四《则天皇后、中宗》。
[25] 顾卫民:《中国基督宗教艺术的历史》,《世界宗教研究》2008第1期。
[26] 参见《熙朝崇正集》,上题“闽中诸公赠泰西诸先生诗初集”,吴相湘:《天主教东传文献》,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 633-691页。
[27] 搜集整理历代竹枝词较丰富的专著有《中华竹枝词》(六册)。雷梦水、潘超、孙忠诠、钟山:《中华竹枝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
[28] 王慎之、王子今:《清代海外竹枝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页。
[29] [31] 章文钦:《澳门历史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30-331,327页。
[32] 全祖望:《鲒埼亭诗集》卷八《西笑集》。参见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253-2254页。
[33] 蔡鸿生:《全祖望〈二西诗〉的眼界》,《东方论坛》2004年第6期。
[34] 陈 垣:《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4-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