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州漫忆系列之一
——潢川,抗战中的孤岛
┃杨峰
开栏的话: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自中华文明在中原初露曙光,河南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3000余年,漫长的文明进程让河南至今仍完整保留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伏羲太昊陵、黄帝故里、安阳殷墟、天地之中、大运河、丝绸之路等华夏文明的核心地标,默默诉说着历史的辉煌。
散落中原大地的文化资源,是文史工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近年来,全省各地政协把文史工作作为服务和推进地方特色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深入挖掘和整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资源,包括历史文化、民族民俗文化以及具有地方特征的自然景观文化,着力打造精品特色文化,探索出了一条文史工作服务地方发展的新路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自本期始,本刊将联合基层政协,开设“人文中原”栏目,让我们心怀敬畏,感受过往的岁月沉淀,沿着历史的足迹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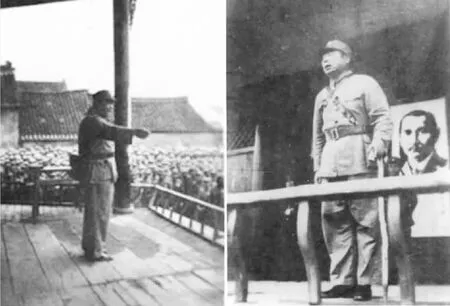
冯玉祥抗战期间在潢川
“孤岛”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一个特殊的现象,指的是在上海被日军占领之后由美英法租界组成的未被日军占领的市区。“孤岛”的存在从1938年淞沪会战结束开始,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被日军占领结束。但是,潢川却是豫南,以至于中原名副其实的“抗战中的孤岛”。我们的孤岛,不是靠外国人的保护,是中国人民、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保护与捍卫的孤岛;我们的孤岛,超越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直至抗战胜利;我们的孤岛,也不是独善其身,而是以自身巨大的牺牲,以人力,以物力支援了全国的抗战,是楔入华东、华中、中原日占区的一枚钉子。
诗人臧克家眼中抗战中的潢川
臧克家(公元1905年—公元2004年),山东潍坊诸城人,闻一多的学生,现代诗人,忠诚的爱国主义者。1937~1939年曾到潢川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在潢川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抗日诗文作品,创作和出版了《从军行》《淮上吟》等诗集及散文集《随枣行》,歌颂抗日军民的事迹。1938年2月20日,《新华日报》发表了臧克家的《孩子们举起了火炬》一文,记录了抗战中发生在潢川的一个片段:
潢川,这小小的地方,也在反侵略的呼声中荡动起来。
孩子们,我们宣传队的同志们用短短的工夫训练成功的少年队伍,他们年龄都很小,五六岁的,七八岁的,十五六岁的就得算顶大的哥哥和姐姐了。我们教会了他们救亡的歌曲,教他们一些别的事情,他们应该知道的。他们日夜缠绕着我们宣传队的男女同志们,亲亲热热得就像自己的哥哥姐姐。
元宵节到了,我们不能放走这个节日。决定要来一个“潢川儿童反侵略大会”。这样讲,孩子们不容易立刻明白,对他们讲“反侵略”就是“打倒日本鬼子”,他们都高兴地笑了。有的已经自备了各种的灯,我们宣传队的同志们也用了两天的工夫自制了许多。
黄昏的时候,人脸上贴着朦胧的黑纱,在这个十日九阴沉的潢川,难得今夜的这一轮明月,逼人似的涌上梢头,给人们一个惨痛的回忆。“新民”大会场上渐渐的人影憧憧了。孩子们高挑着不同式样的彩纸灯,从南城,从北城,带着欢欣和兴奋,在姐姐的提携下,在妈妈的领导下汇聚到这里来。一座空洞死寂的场子顿然涂上了明朗的色调。
为了珍惜短瘦的蜡烛,叫它游行的时候多亮一会儿,带着深色的黄昏,我们宣布开会了。小小的主席立在台上,很有神气地向大家致开会辞。他一点也不觉得渺小,他不为台下的多数听众——军团的学生、警察、形形色色的堂堂男子和成年妇女的注视而显得局促。他很勇敢地把日本兵的残暴当众高声历数,他高举着拳头叫大家一齐起来!接着,有好几位小朋友在大人的扶持中登台演讲,大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潢川的小孩子们团结起来!”
……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臧克家1938年3月底于潢川写的《别潢川——赠青年战友们》更是激励着无数热血青年,从潢川奔赴全国各地的抗日战场:
去了,我驮起/悲壮的感情,/它过重的分量/压得我心痛。/临去我回头望望“沙河”,/水浪曳动着轻舟,/三五匹战马/在饮着清流。/河水它会永远记得,/记得我投给它的眼波,/记得救亡歌声/给它的激动。/白金粒的沙滩,/像一个镜的梦境,/上面印着我们的脚迹/和武装的身影。/残破的城垣,/多少次我登在上面,/一片原野引我的心/到战场,/到故乡,/到遥远遥远我所向往的地方。/我的感情染上了鹅黄的柳条,/染上了萌动的小草,/同着春色/染遍了无际的青郊。/五千年轻人/失去了家园,/五千个胸膛里/挂一副铁的肝胆。/为了祖国,/把生活浸在苦辛中,/为了抗战,/甘愿把身子供作牺牲。/女的是姊妹,/男的是弟兄,/立脚在一条战线上,/我们一点也不陌生。/我要去了,/到漠漠的西北去看风沙,/去认识一个新的世界,/使自己的生命重新萌芽。/也许会到战场上去/面对着血肉的现实,/叫自己的心/受炮火的洗礼。/战神一手/把人间的关系搅乱,/待将来,/再给它一个新的安排。/赠别不须眼泪,/我们都还年轻,/一齐挺起腰来/去拉大时代的纤绳。/将来在碰到时,/用欢喜的泪/去庆祖国的新生,/无妨用长长的话头/细数个人那一段苦斗的历程。
画家吴作人眼中抗战中的潢川
吴作人(公元1908年—公元1997年),安徽宣城泾县人,生于江苏苏州,从师徐悲鸿先生,并参加南国革新运动,是继徐悲鸿之后中国美术界的又一领军人物。
2009年8月10日,“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中“造化天工——吴作人写生作品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行,展览囊括了从20世纪30年代吴作人旅欧学习期间的素描习作开始至80年代的速写《巴黎卢浮宫》等写生作品90余幅。其中,最重要的展品就是吴作人创作的速写《战地值勤》《战地难民》等,这些是在1938年台儿庄大捷后,在中央大学和徐悲鸿的支持下,吴作人与中大艺术系学生孙宗慰以及在武汉的陈晓南、沙季同、林家旅等五人组成“中央大学战地写生团”,赴河南潢川等战场进行写生创作的。这些作品如实地记录了当时我们抗日战场的真实场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1939年年初,战地写生团充满抗日激情的速写画展在重庆举行,吴作人等在前线实地的速写画作引起巨大的轰动。画展给偏安西南,但又十分关心前线、心系祖国生死存亡的重庆人民群众揭开了壮丽的一页。也打动了青年画家们对宣传抗日的爱国主义激情。继这次画展之后,又陆续出现一些战地写生团,不少青年画家纷纷拿起画笔,为伟大的抗日战争服务。随后,吴作人又根据这些素材创作了多幅油画作品,并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战时中国画展”巡回展出,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反法西斯抗战的决心与付出的巨大牺牲。
1939年,史沫特莱眼里抗战中的潢川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一个杰出的与众不同的女性。她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专著,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成为不朽之作。她亲自护理伤员,组织医疗活动,用行动唤醒有良知的人们。她访遍了中国华北、华中的大部分地区,用热情召唤更多的国际友人,一同为中国抗战出力。她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德加·斯诺一起被誉为中国人民之友。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她曾在抗战中的1939年晚秋来过潢川。她的《中国的战歌》一书,真实记录了抗战最艰难岁月中的潢川:
第七章穿越中国心脏地带(1939年晚秋)
……
在大别山西部山脉,我们看到一个地主家的围墙上用白色石灰水写着一个口号:“军爱民,民拥军——潢川青年联合会”。但是我们从来没碰到过写口号的人。好像他们写下了口号,然后逃跑了。我回忆起在立煌曾经碰到三位来自于潢川青年联合会的女学生,在安徽的抗日基地里学习。
……
商城官方给我提供了一支15人的武装护卫队,并带我去了潢川,西北方的一座大城,曾经被日本人占领了3个月之久。我不得不推迟行程几个小时,因为潢川附近的一个游击队刚刚发生了兵变。他们已经3个月没有收到军饷了,缺乏政治训练,有些人甚至跑到了日本人那里;而现在,他们正在抢劫村庄或是打劫过路人。
……
从一群强壮的农民正在训练的平台上,我可以俯瞰整个潢川——一个可以追溯到周朝的古老城市。老的内城位于一座高山上,四周是一道破旧的围墙,并环绕着护城河。我想到了古老的布拉格,中世纪的捷克城堡耸立在山上,蓝色的伏尔塔瓦河在它的脚下流过。在我们后面,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大别山淡蓝色的轮廓落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
突然,人们开始从村庄里跑过麦田。空袭!我们逃到了一片墓地里,蹲在墓碑之间,看着天空。在北边,来了九个黑色的斑点。他们变得越来越大,在我们头上盘旋,然后向南飞去。
下午4点,我们通过了浅绿色河流上的一座桥梁,穿过了古城墙。在城门正上方,有一个口号:“镇压共产主义;他们是苏联走狗!”在墙上还有另外一幅:“头可断,但是心不能被征服!”
内城正处于军事管制。爬上石头台阶,我们穿过了三个军队的哨兵警戒线,每个都要搜查着每一个人。特别委员会的总部在山顶上,被另一排钢铁护栏环绕着。
特别专员麦大富(MaiTa-fu)是一位年轻的军事指挥,他是国民党员,从前是第一战区司令员陈诚将军的副官。他欢迎了我,然后为我们订了餐。在我们在等着吃饭时,他带我们穿过司令部,到了后面一个花园,我们马上发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两丛血红的玫瑰花,装扮着一个巨大而可爱的花园。花园里还有一个年久失修的石桌,周围是石头凳子,在另一边,是一座低矮的坟墓,里面埋葬的是公元前某个朝代的王子。
……
1942年白桦眼中抗战中的潢川
2010年12月30日的 《文汇报》上有一篇白桦的回忆文章《黄国故里人》,道出了白桦眼中抗战中的潢川。这是一段珍贵的历史,这是一段生动的记忆,这是1942年,抗战最艰难的阶段至抗战胜利时关于潢川的记忆:
…………
我出生在与潢川相邻的信阳。1942年冬天,流亡在潢川的二姐突然化装为村妇,拿着买来的良民证,回到日军铁蹄下的信阳。她所以冒险返乡,完全是为了我们兄弟俩的学业,那时我们正辍学在家。我知道潢川离信阳只有几十公里,但那里还挂着中国国旗。
…………
去潢川的路徒步走了两天,进潢川城时已是灯火通明的夜晚,西关的夜市极旺。进城的时候我十分兴奋,无须脱帽鞠躬,而且城门口压根就没有哨兵。于是我就像主人那样大摇大摆地走进去了。当晚,住在南城,一夜都没睡着。早上,急于想看到“故国”的威仪。醒来,竟然大吼一声“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第二天到北城和大姐见面。北城是潢川的行政中心,专员公署就在他们住处的前街。后门紧贴着城墙,黄土城墙上一面国旗在寒风中飘扬。战时的孩子对武器熟悉的程度绝对不亚于职业军人,我一眼就能看出,站在旗杆下那位士兵的肩上扛的是一支汉阳造步枪。我当然知道,比起日军来,中国地方部队的装备差得很远。但士兵身上那套灰布军装给我一种朴素坚毅的印象,我把潢川当做一个坚强的堡垒。也许是因为我与日军不共戴天的缘故,从来都没有对抗战的最后胜利失去过信心。没想到,第二年的春天日军突然扫荡了潢川城,我和所有的居民一起倾巢出逃,田野里全都是羊群般无助的老弱妇孺。眼看就是一场血腥的屠戮,所幸日军只是过路,并未追杀。我这才意识到潢川原来是如此脆弱,仅仅是半个旅团的日军在潢川过路,就把国民党军赶得人仰马翻,潢川城顿时变成一片断壁残垣。后来,整整一个夏天,潢川城出现一种怪异的现象,每到深夜,露宿在院落里、大街上的居民同时被一种幻觉的魔影和怪叫声惊醒,所有的人都像中了魔似地大声狂呼疾走,有关无头鬼作祟的谣传不胫而走,整整闹了半个月之久才渐渐平息。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称之为“夜惊”的群体性精神疾病。

1938年被破坏的叶集至信阳的道路
尽管如此,潢川仍然是豫南的一座避难之城,又是一座中学生之城,平汉铁路沿线沦陷区的孩子有条件的都到潢川来读书。
……
抗战中的自我牺牲成就潢川“抗战中的孤岛”
在79年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潢川,被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既定的武汉会战北线战场之一。这里有过激烈的战斗,那是潢川近代史上最英勇、最辉煌、最值得记录的英雄岁月。潢川在中国的抗战史上也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贡献:
第一,抗日战争中,潢川作为河南省第九区行政首府,下辖了固始等几个县。抗战开始的标志七·七卢沟桥事变中,率先打响抗日第一枪的是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3营,其营长金振中是固始人,其1400多战士,大部分也是河南人。
第二,抗日战争中,河南作为日军既定战略中重要的一环,全省有90多个县沦陷。潢川虽然有过最激烈的战斗,虽然城市也有过短暂的被占据,但它一直在我们军队的手里。
第三,潢川人民牺牲自我,默默地给予中国八年抗战最重要的后勤支援。1947年1月5日《豫南日报》文章《道潢人疾苦》介绍说:“在八年抗战中服役纳粮,吾豫当为全国各省冠,九区为全豫冠,潢川又为九区冠。”
第四,1938年,日军左路军行在固始富金山受阻,其右路军第3和第10师团猛攻固始,一番激战后于9月7日占领该城。接着,两个师团沿公路西进潢川,撞上了国军一代名将张自忠。张自忠从9月9日一直打到9月19日,整整守了10天,比原来预定的坚守7天超了3天,最后在敌人面前又安全撤退。
日军第10师团在攻击潢川时,使用毒剂弹、筒上千枚,毒云覆盖潢川。据参加过潢川保卫战的郭荣昌回忆说:“日本人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轮番向我们攻击,弟兄们穿着短裤,插上刺刀和日本鬼子打红了眼,日本鬼子退下去之后便向我们施放毒瓦斯,弟兄们一看到黄色的烟雾,就赶紧掏出手绢或者是撕下一块布用水、尿弄湿捂住鼻子和嘴巴继续战斗,有好多人就这样倒下去了,但没有一个逃跑的。”一场恶战下来,郭荣昌所在的营仅剩下13人,光着膀子、浑身是血的营长张树清对郭荣昌说:“这13人就归你了,你当班长吧!”
潢川保卫战,为武汉会战备战和全国军民、工厂、学校、物资内迁争取了宝贵时间,亦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和必胜信心,也彻底地粉碎了日本人妄图消耗我们有生的军事实力的梦想。
日本《支那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有:“第二军于(1938年)11月中旬约用十天的时间将庐州——信阳间、商城——麻城方面的兵站线撤完。最大的问题是运送病员,主要因道路关系。”正是我们军队不畏牺牲,坚持抗战,才迫使日本法西斯即使短期内占领了潢川县城,最终也因为无法保证后勤供应及伤病员转运而被迫退出。这正是潢川成为“抗战中的孤岛”,成为楔入日军华东、华中、中原战区一枚钉子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