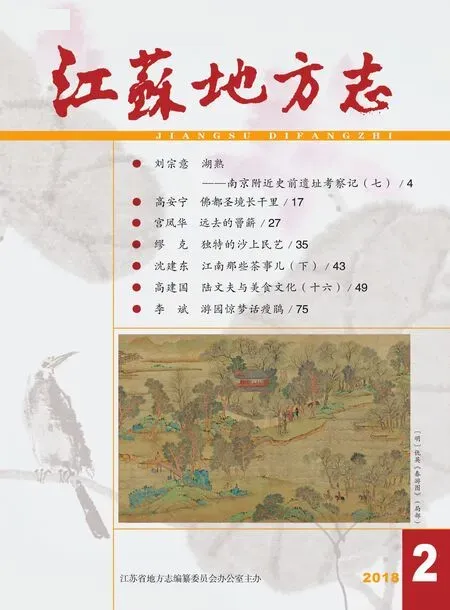南陆北汪
——陆文夫与美食文化(十六)
◎ 高建国

2012年,两位研究生写毕业论文,把陆文夫和汪曾祺,放在一起研究。一位写,《明丽苏北与清隽江南——论汪曾祺、陆文夫作品中的地域文化书写》(李艳敏,山东师范大学),另一位写,《社会民情的不同书写——汪曾祺和陆文夫小说的比较研究》(罗江,沈阳师范大学)。文学研究,将汪曾祺和陆文夫,放在一起比较,这不是个例,许多学者都有这种思路。比如,王景科、颜水生《新时期乡土散文的美学精神》(《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吴炫《穿越当代“经典”——文化寻根文学热点作品局限评述》(《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刘丹《论新时期小说中的“行业情结”》(《宿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8期),陆娴《浅析江苏当代的乡土文学》(《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16期),张光芒《文化认同与江苏小说的审美选择》(《小说评论》2007年第3期),等等,都写到了陆文夫和汪曾祺。美食文化研究,更习惯相提并论,因为他们另一个身份,都是美食家。比如,李芳、吴懿曈《中国现当代饮食散文文化意蕴浅析》(《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10期),张海生、吴玉玉《试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四种“吃”法》(《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S1期),等等。这说明,陆汪二人在文学上,有共同点;他们的美食人生,也有相似性。所以,二人具有可比性。研究陆文夫,会联想汪曾祺。本文从“美食散文的写作”这一角度,对他们作个比较。
一、选题:社会化与私人化
陆文夫与汪曾祺,都爱写美食散文。这些散文,影响广泛,受到读者偏爱。粗读,大同小异,仔细分析,却能看出差别。陆文夫美食散文,最大的特点,就是宏观视角,社会思维,鲜明立场。比如,小说《美食家》,塑造了两个人物,朱自冶和高小庭;介绍了丰富的苏州美食,受到读者赞誉。这部小说在30余年间,能够长销世界各国,这是重要因素。陆文夫谈《美食家》,却回避这些东西,而是站在历史高度,看待小说的美食兴衰。他说,“鲁迅翻开了封建社会史之后发现了两个字:‘吃人’。我看看人类生活史之后也发现了两个字:‘吃饭’。同时发现这吃人和吃饭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历代的农民造反,革命爆发都和吃饭有关系。国际歌的第一句就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这是一句很完整的话,它概括了‘吃饭’与‘吃人’,提出了生活和政治两个方面的问题。百余年间千万个仁人志士揭竿而起,高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去浴血奋战。这一段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会、也不应该忘记。”(陆文夫《写在〈美食家〉之后》)这就是《美食家》的创作动机。可见陆文夫写美食,多为印证历史发展规律。古今美食著作,甚多。似这般高远辽阔的视野,还是第一次。
再比如,当今饭店的菜肴口味,常遇到“今不如昔”评论。美食家们,每每扼腕叹息。但落笔成文,就事论事多。陆文夫能够跳出表象,结合社会语境,揭示矛盾本质。以苏州为例,他说,“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事业的发展,经济交往的增多,苏州的菜馆生意兴隆,日无虚席。苏州的各色名菜都有了恢复与发展,但也碰到了问题,这问题不是苏州所特有,而是全国性的。问题的产生也很简单:吃的人太多。俗话说人多没好食,特别是苏州菜,以精细为其长,几十桌筵席一起开,楼上楼下都坐得满满的,吃喜酒的人像赶集似的涌进店堂里。对不起,那烹饪就不得不采取工业化的方式了,来点儿流水作业。有一次,我陪几位朋友上饭馆,饭店的经理认识我,对我很客气,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即要求那菜一只只地下去,一只只地上来。经理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办不到。’所谓一只只地下去,就是不要把几盆虾仁之类的菜一起下锅炒,炒好了每只盆子里分一点,使得小锅菜成了大锅菜。大锅饭好吃,大锅菜却并不鲜美,尽管你是炒的虾仁或鲜贝。”(陆文夫《姑苏菜艺》)言下之意,菜肴“今不如昔”,不是菜馆厨师的错;而是美食供需,达不到从容与平衡。吃客太多,饭店有限,小锅菜只能变成大锅菜。至于口味,也就可想而知了。

汪曾祺写美食散文,与陆文夫最大的不同,就是多写个人故事,少议社会问题。比如,《吃食和文学》,本是宏观议题,落笔却成了,作家的私人体验。“有一次买牛肉。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中年妇女,看样子是个知识分子,南方人。轮到她了,她问卖牛肉的:‘牛肉怎么做?’我很奇怪,问:‘你没有做过牛肉?’——‘没有。我们家不吃牛羊肉。’——‘那您买牛肉——?’——‘我的孩子大了,他们会到外地去。我让他们习惯习惯,出去了好适应。’这位做母亲的用心良苦。我于是尽了一趟义务,把她请到一边,讲了一通牛肉做法,从清炖、红烧、咖喱牛肉,直到广东的蚝油炒牛肉、四川的水煮牛肉、干煸牛肉丝……”又说,“有人不吃羊肉,我们到内蒙古去体验生活,有一位女同志不吃羊肉——闻到羊肉味都恶心,这可苦了。她只好顿顿用开水泡饭,吃咸菜。看见我吃手抓羊贝子(全羊)吃得那样香,直生气!”(汪曾祺《吃食和文学》)
在这篇散文中,还有一段文字,专门写苦瓜,也是把个人体验,写得惟妙惟肖。“前天有两个同乡因事到北京,来看我。吃饭的时候,有一盘炒苦瓜。同乡之一问:‘这是什么?’我告诉他是苦瓜。他说:‘我倒要尝尝。’夹了一小片入口:‘乖乖!真苦啊!——这个东西能吃?为什么要吃这种东西?’我说:‘酸甜苦辣咸,苦也是五味之一。’他说:‘不错!’我告诉他们这就是癞葡萄。另一同乡说:‘癞葡萄,那我知道的。癞葡萄能这个吃法?’。”又说,“‘苦瓜’之名,我最初是从石涛的画上知道的……石涛的别号甚多,除石涛外有释济、清湘道人、大涤子、瞎尊者和苦瓜和尚。但我不知道苦瓜为何物。到了昆明,一看:哦,原来就是癞葡萄!我的大伯父每年都要在后园里种几棵癞葡萄,不是为了吃,是为了成熟之后摘下来装在盘子里看着玩的。有时也剖开一两个,挖出籽儿来尝尝。有一点甜味,并不好吃。而且颜色鲜红,如同一个一个血饼子,看起来很刺激,也使人不敢吃它。当作菜,我还没吃过。有一个西南联大的同学,是个诗人,他整了我一下子。我曾经吹牛,说没有我不吃的东西。他请我到一个小饭馆吃饭,要了三个菜:凉拌苦瓜、炒苦瓜、苦瓜汤!我咬咬牙,全吃了。从此,我就吃苦瓜了。”(汪曾祺《吃食和文学》)
留心注意,就能发现,以上表述中,都有“我”字。可见,都是汪曾祺亲历的事情。这就是汪曾祺的写作习惯,即使写小说,也会用真人真事。他说,“我写小说,是要有真情实感的,沙上搭建,我没有这个本事。我的小说中的人物有些是有原型的。”(汪曾祺《〈菰蒲深处〉自序》)小说如此,那么他的散文,就更是私人生活地再现了。
二、表达:理念化与情节化
散文一般分为三种:抒情散文、叙事散文、议论散文。陆文夫的散文,说理较多,属于议论散文。所谓理念化,就是注重表达思想,写文章长于说理。这也是陆文夫,美食散文的特色。比如,阐述“美食”概念。他认为品尝美食,就是欣赏艺术。“美食和饮食是两个概念,饮食是解渴与充饥,美食是以嘴巴为主的艺术欣赏——品味。”(陆文夫《吃喝之道》)因而,美食不是简单的吃喝,而是一门艺术。陆文夫说,“食物一旦上升为美食,那就成了一种艺术,其功效就不仅仅是疗饥,而是一种出于生理需要的艺术欣赏。吃的艺术是一种多门类的综合学科;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生理学,心理学的混合体。欣赏美食,就像是欣赏艺术表演。”(陆文夫《人之于味》)对美食这门艺术,陆文夫认为,“欢喜不欢喜,一是要看艺术的本身,二是要看各人的欣赏水平,三是要看各人的欣赏习惯,四是要看在什么场合,什么环境,什么气氛,与谁共赏以及欣赏的频率等等。”(陆文夫《人之于味》)又说,“如果承认美食是一种欣赏的话,那是要眼耳鼻舌同时起作用的,何况宴席中菜肴的配制是一个整体,是由浅入深,有序幕,有高潮,有结尾。荤素搭配,甜咸相间,还要有点心镶嵌其间。”(陆文夫《吃喝之道》)将品味美食,视为欣赏艺术,这种理念,陆文夫独创。不只概念出新,他还将其看成一个系统,涉及多种学科和运作程序。这样的理论,对中华美食研究,能产生启迪作用。
类似的理念化表达,在陆文夫散文中,比比皆是。再比如,《你吃过了吗?》。陆文夫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见面,总会问一声,“你吃过了吗?”他解释说,“人们观念的形成,都和客观的存在有关系,吃是如此的重要,而饥饿又像幽灵似的伴随着中国人,这就使得中国人的许多习俗、观念都和吃有关系,人们把吃从物质的需求,提升为精神的象征,弄得超出了疗饥的范围,成了问候、礼节、尊敬、诚意、大方、财富、权势的表现。”在这方面,农民更胜一筹。由于“中国经常吃不饱的大多是农民,历来如此。古诗里就写过‘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所以农民总是把吃当作礼节,当作庆典,当作财富的表现,用吃喝来示富。中国又是个农业国家,大家都用吃来示富,来表示诚意,当作礼节,一旦缸坛稍满时,怎么能不形成吃喝之风呢?大吃大喝的根源是来自于没吃少喝,是一种低水平的反弹和文明程度不高的表现。”(陆文夫《你吃过了吗?》)在这种表述中,陆文夫很少讲故事。所以,他的美食散文,基本属于“议论文”。即汪曾祺写美食,恰好相反。道理少,故事多,具有情节化和小说化特点。汪曾祺的美食散文,之所以一再重印,奥妙就在这里:好看,娱乐性大于思想性。举个例子,《〈吃的自由〉序》。通篇观点,都用生动故事来表述。比如,“中国的和尚为什么不吃肉,有的和尚是吃肉的。比如《金瓶梅》送给西门庆春药的胡僧,‘贫僧酒肉皆行’。他是‘胡僧’,自然可以‘胡来’,有名的吃肉的中国和尚是鲁智深。我在小说《受戒》中写和尚在佛殿上杀猪,吃肉,是我亲眼目睹。并非造谣。但是大部分和尚是不吃肉的,至少在人前是这样。和尚为什么不吃肉?我一直没有查考过。看了符先生的文章,才知道这出于萧衍的禁令。萧衍这个人我略有所知,而且‘见’过。苏州甪直的一个庙里有一壁泥塑,罗汉皆参差趺坐,正中一僧,著赭衣、风帽,据说即萧衍,梁武帝,鲁迅小说中的‘梁五弟’,也看不出有什么特点。萧衍虔信佛律,曾三次舍身入寺为僧,这我是知道的,但他由戒杀生引伸至不许和尚吃肉,法令极严,我以前却不知道。萧衍是个怪人,他对农民残酷压迫,多次镇压农民起义,却又疯狂地信佛,不许和尚吃肉,性格很复杂,值得研究。”(汪曾祺《〈吃的自由〉序》)很显然,这是用故事,来印证自己的观点。
再比如,《昆明的果品》。写到梨、石榴、桃、杨梅、木瓜、地瓜、胡萝卜、核桃糖、糖炒栗子。写木瓜的时候,汪曾祺说,“木瓜我是很熟悉的,我的家乡有。每当炎暑才退,菊绽蟹肥之际,即有木瓜上市。但是在我的家乡,木瓜只是用来闻香的。或放在瓷盘里,作为书斋清供;或取其体小形正者于手中把玩,没有吃的。且不论其味酸涩,就是那皮肉也是硬得咬不动的。至于木瓜可以入药,那我是知道的。我到昆明,才第一次知道木瓜可以吃。昆明人把木瓜切成薄片,浸泡在水里(水里不知加了什么东西),用一个桶形的玻璃罐子装着,于水果店的柜台上出卖。我吃过,微酸,香脆爽口,别有风味。”写胡萝卜,“联大的女同学吃胡萝卜成风。这是因为女同学也穷,而且馋。昆明的胡萝卜也很好吃。昆明的胡萝卜是浅黄色的,长至一尺以上,脆嫩多汁而有甜味,胡萝卜味儿也不是很重。胡萝卜有胡萝卜素,含维生素C,对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知道是谁提出,胡萝卜还含有微量的砒,吃了可以驻颜。这一来,女同学吃胡萝卜的就更多了。她们常常一把一把地买来吃。一把有十多根。她们一边谈着克列斯丁娜·罗赛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汪曾祺《昆明的果品》)这样的书写,人们不仅读到故事,还看到色彩,听到声音,甚至能嗅到胡萝卜的芳香,感觉到“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的女同学的神态与表情。
汪曾祺写美食散文,为什么频繁讲故事?因为不喜欢“抒情”。汪曾祺把散文,分成抒情和非抒情两种。他说,“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宽,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了……我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所以,他坦言,“我的散文大都是记叙文。间发议论,也是夹叙夹议。”(汪曾祺《〈蒲桥集〉自序》)汪曾祺一生,经历过民国以来,两种社会形态,又辗转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若干地方,学习、生活和工作。丰富的人生阅历,积累的生活故事,就是偌大一笔文学财富。这是“家常”散文,最好的写作素材。
三、内容:虚构性与真实性
一个作家,被说成美食家,要有条件。起码会写美食,字里行间,有油烟味儿。美食文学,一般分两种:一种是虚构美食,比如《红楼梦》笔法;一种是现实美食,比如作者在现实中,吃什么就写什么。陆文夫属于前一种,小说《美食家》就是例子。即使在散文中,写到真实美食,陆文夫也只是,为了论证观点。所以,他很少用细腻笔调,去铺陈繁琐的美食细节。比如,写《姑苏菜艺》,论证苏帮菜三大特点,“精细、新鲜、时令”。陆文夫说,“这三大特点是由苏州的天、地、人决定的。苏州人的性格温和,办事精细,所以他的菜也就精致,清淡中偏甜,没有强烈的刺激。听说苏州菜中有一只绿豆芽,是把鸡丝嵌在绿豆芽里,其精的程度可以和苏州的刺绣媲美。苏州是鱼米之乡,地处水网与湖泊之间,过去,在自家的水码头上可以捞鱼摸虾,不新鲜的鱼虾是无人问津的。从前,苏州市有两大蔬菜基地,南园和北园,这两个菜园子都在城里面。菜农黎明起菜,天不亮就可以挑到小菜场,挑到巷子口,那菜叶上还沾着夜来的露水。七年前,我有一位朋友千方百计地从北京调回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为了回到苏州来吃苏州的青菜。这位朋友不是因莼鲈之思而归故里,竟然是为了吃青菜而回来的。虽然不是惟一的原因,但也可见苏州人对新鲜食物是嗜之如命的。头刀(或二刀)韭菜、青蚕豆、鲜笋、菜花甲鱼、太湖莼菜、马兰头……四时八节都有时菜,如果有哪种时菜没有吃上,那老太太或老先生便要叹息,好像今年的日子过得有点不舒畅,总是缺了点什么东西。”(陆文夫《姑苏菜艺》)貌似写到真实生活,实际上,都是“听说……”的故事、“从前……”的故事,而非亲历。故事本身,可能并不假,但描写起来,却是粗线条,落笔从简,泛泛而谈。可见,陆文夫笔下的美食,虽非虚构,但与真正的“写实”,还有一定差距。
反观小说中的美食,却大相径庭。《美食家》的菜肴,虽为虚构,却写得活灵活现。比如,朱自冶讲烹饪课,说明“放盐”的重要性,能够让人读出,朱自冶的话语节奏与神态表情。朱自冶说,“东酸西辣,南甜北咸,人家只知道苏州菜都是甜的,实在是个天大的误会。苏州菜除掉甜菜之外,最讲究的便是放盐。盐能吊百味,如果在鲃肺汤中忘记了放盐,那就是淡而无味,即什么味道也没有。盐一放,来了,鲃肺鲜、火腿香、莼菜滑、笋片脆。盐把百味吊出之后,它本身就隐而不见,从来也没有人在咸淡适中的菜里吃出盐味,除非你是把盐多放了,这时候只有一种味:咸。完了,什么刀功、选料、火候,一切都是白费!”朱自冶又说,“这放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因人、因时而变。一桌酒席摆开,开头的几个菜要偏咸,淡了就要失败。为啥,因为人们刚刚开始吃,嘴巴淡,体内需要盐。以后的一只只菜上来,就要逐步地淡下去,如果这桌酒席有四十个菜的话,那最后的一只汤简直就不能放盐,大家一喝,照样喊鲜。因为那么多的酒和菜都已吃了下去夕身体内的盐分已经达到了饱和点,这时候最需的是水,水里还放了味精,当然鲜!”朱自冶还举一个例子,“那最后的一只汤简直不能放盐,是一个有名的厨师在失手中发现的。那一顿饭从晚上六点吃到十二点,厨师做汤的时候打瞌睡,忘了放盐,等他发觉以后拿了盐奔进店堂时,人们已经把汤喝的,一致称赞:在所有的菜中汤是第一!”(《美食家》第十章“吃客传经”)这一段内容,堪称烹饪经典,饱含哲理性。日常烧菜,百姓都会放盐;从专业上讲,最难的技术,可能也是放盐。朱自冶的“放盐”理论,完全是虚构的,却如烹饪大师,在传道授业,能够抓住读者的心。这一段文字,细节生动,铺陈详尽;虚构的故事,恍若现实中发生,让你不得不钦佩,陆文夫笔力的老到,对烹饪的理解深度。这样的虚构故事,在《美食家》中,还有不少。因为小说写的美食,实在太“真实”,陆文夫才被冠以,“美食家”头衔。大凡美食家,都是“吃”成的;陆文夫成为美食家,是“写”成的。这是中外美食史上的特例。
汪曾祺在散文中写美食,与陆文夫不同。求真务实,细节生动,不吝笔墨,娓娓道来。所以他的散文,可当回忆录来读。比如《萝卜》,我们读几段。
例一:“扬花萝卜即北京的小水萝卜。因为是扬花飞舞时上市卖的,我的家乡名之曰:‘扬花萝卜’。这个名称很富于季节感。我家不远处的街口一家茶食店的屋下有一岁数大的女人摆一个小摊子,卖供孩子食用的便宜的零吃。扬花萝卜下来的时候,卖萝卜。萝卜一把一把地码着。她不时用炊帚洒一点水,萝卜总是鲜红的。给她一个铜板,她就用小刀切下三四根萝卜。萝卜极鲜嫩,有甜味,富水分。自离家乡后,我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萝卜。或者不如说自我长大后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萝卜。小时候吃的东西都是最好吃的。”

例二:“烧小萝卜,来北京前我没有吃过(我的家乡扬花萝卜没有熟吃的),很好。有一位台湾女作家来北京,要我亲自做一顿饭请她吃。我给她做了几个菜,其中一个是烧小萝卜。她吃了赞不绝口。那当然是不难吃的:那两天正是小萝卜最好吃的时候,都长足了,但还很嫩,不糠;而且是用干贝烧的。她说台湾没有这种水萝卜。”
例三:“我们家乡有一种穿心红萝卜,粗如黄酒盏,长可三四寸,外皮深紫红色,里面的肉有放射形的紫红纹,紫白相间,若是横切开来,正如中药里的槟榔片(卖时都是直切),当中一线贯通,色极深,故名穿心红。卖穿心红萝卜的挑担,与山芋(番薯)同卖,山芋切厚片。都是生吃。紫萝卜不大,大的如一个大衣口子,扁圆形,皮色乌紫。据说这是五倍子染的。看来不是本色。因为它掉色,吃了,嘴唇牙肉也是乌紫乌紫的。里面的肉却是嫩白的。这种萝卜非本地所产,产在泰州。每年秋末,就有泰州人来卖紫萝卜,都是女的,挎一个柳条篮子,沿街吆喝:‘紫萝——卜!’我在淮安第一回吃到青萝卜。曾在淮安中学借读过一个学期,一到星期日,就买了七八个青萝卜,一堆花生,几个同学,尽情吃一顿。后来我到天津吃过青萝卜,觉得淮安青萝卜比天津的好。大抵一种东西第一回吃,总是最好的。”(汪曾祺《萝卜》)文字鲜活生动,细节具有质感。汪曾祺这样的真实描述,类似陆文夫小说的情节描写。可见两位作家,技巧不相上下。只是创作理念,各有侧重。因而他们的美食文章,才会有差异。
四、情怀:直面社会,殊途同归
论证两位作家,美食散文的不同,并不代表二者没有共性。陆汪这一代文人,都有情怀,责任感强,敢于直面社会。既追求真善美,也抨击假丑恶,义利观十分相似。举两个例子——
之一:中国大陆,近年烹饪菜肴,热衷搞视觉造型。两位先生一致认为,这是形式主义作祟。陆文夫说,“中国的菜本来讲究色、香、味,后来有人加了个型,即菜的外形、造型。这一加就有文章了,全国各地大搞形式主义。冷盆里摆出一条金鱼、一只蝴蝶,用萝卜雕成玫瑰,用南瓜雕成凤凰等等。厨师如果不会雕刻,那就上不了等级。某次有人请我吃饭,席面上摆着一只用南瓜雕成的凤凰,那南瓜是生的(当然是生的),不能吃。我问大厨师,雕这么一只凤凰要花多少时间,他说大概要三个小时。我听了觉得十分可惜,有三个小时,不,不需要三个小时,你可以把那只鲫鱼汤多烧烧,把汤煮得像牛奶似的,这是我们苏州菜的拿手戏,何必那么匆匆忙忙,把鱼汤烧得像清水?”(陆文夫《吃空气》)汪曾祺也说,“现在的创新菜却多在形上做文章。有一类菜叫做‘工艺菜’。这本来是古已有之的。晋人雕卵而食,可以算是工艺菜。宋朝有一位厨娘能用菜肴在盘子里摆出‘辋川小景’,这可真是工艺。不过就是雕卵、‘辋川小景’,也没有多大意思。鸡蛋上雕有花,吃起来还不是鸡蛋的味道么?‘辋川小景’没法吃。王维死后有知,一定会摇头:辋川怎么能吃呢?现在常见的工艺菜,是用鸡片、腰片、黄瓜、山楂糕、小樱桃、罐头豌豆……摆弄出来的龙、凤、鹤,华而不实。用鸡茸捏出一个一个椭圆的球球,安上尾巴,是金鱼,实在叫人恶心。有的工艺菜在大盘子里装成一座架空的桥,真是匪夷所思。还有在工艺菜上装上彩色小灯泡的,闪闪烁烁,这简直是:胡闹!”(汪曾祺《作家谈吃第一集——〈知味集〉后记》)
之二:近年的饭店菜肴,质量直线下降。两位作家在散文中,也声讨过这种现象。陆文夫直截了当说,现在的菜肴,“今不如昔”。他认为,“菜的质量如何,原料是决定性的,不能靠采购员的批量采购,许多名菜对原料还有特殊的要求。就说这叫化鸡吧,是公鸡还是母鸡,是活杀鸡还是冰冻鸡,是饲养场里出来的鸡,还是农家的散养鸡?如果是一只冰冻的、饲养场里出来的鸡,完了,再高明的厨师也做不出高质量的叫化鸡。要知道,当年创造了‘叫花鸡’的那个叫花子,他用的鸡是偷了老太婆的一只下蛋鸡,绝不是饲养场里出来的冰冻鸡。中国的名菜大多是有地方性的,大都和地方的物产有关系,物产又和季节有关系,所以说采购原料是很复杂的,有时候是可遇而不可求。”(陆文夫《永不凋零的艺术——吃》)汪曾祺说起此事,更是中气十足,铿锵有力。他说,现在走进饭店,“菜不是从前那个味儿了。原因何在?很多。一是没有以前的材料。前几年,我到昆明,吃了汽锅鸡,索然无味;吃过桥米线,也一样。一问,才知道以前的汽锅鸡用的是武定壮鸡(武定特产,阉了的母鸡),现在买不到。过桥米线本来也应该是武定壮鸡的汤。我到武定,吃汽锅鸡,也不是‘壮鸡’!北京现在的‘光鸡’只有人工饲养的‘西装鸡’和‘华都肉鸡’,怎么做也是不好吃的。二是赔不起那功夫。过去北京的谭家菜要几天前预定,因为谭家菜是火候菜,不能嗟咄立办。张大千做一碗清炖吕宋黄翅,要用十四天。吃安徽菜,要能等。现在大家都等不及。镇江的肴肉过去精肉肥肉都是实在的,现在的肴肉是软趴趴的,切不成片,我看是卤渍和石压的时间不够。淮扬一带的狮子头,过去讲究‘细切粗斩’,先把肥瘦各半的硬肋肉切成石榴米大,再略剁几刀。现在是一塌刮子放进绞肉机里一绞,求其鲜嫩,势不可能。”(汪曾祺《作家谈吃第一集——〈知味集〉后记》)汪曾祺是个温和的作家,落笔的文字,也写得简洁幽默。如此义愤填膺,在其散文中,难以见到。可见有些事情,他是不能容忍的。作为一个真正的美食家,他要捍卫美食文化的纯洁性。
中国的美食家,有很多,陈晓卿(《舌尖上的中国》1、2季总导演)只推荐三位:梁实秋、陆文夫和汪曾祺。鉴别美食家,陈晓卿有标准。他说,“我心目中的美食家,不仅要见识多,味觉敏锐,有好奇心;更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流畅的表达能力和深厚的人文情怀。自梁实秋、陆文夫和汪曾祺死后,国内这种人就没有了。”(孙雅兰《陈晓卿:最好吃的是能慰藉心灵的食物》)陈晓卿本人,也是美食达人,对美食文化体察较深。从上面分析看出,他给三位美食家的定位,是准确的。梁实秋生活在台湾,离我们稍远。陆文夫和汪曾祺,都是大陆江苏人。一条长江,把江苏切成两半,陆文夫在江南(苏州),汪曾祺在江北(高邮,后定居北京),人称中国食坛的“南陆北汪”。他们的存在,很有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沿着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样一个历史轨迹推进的。下一步,中国人还会“美起来”,崇尚生活之美,追求生存艺术,美食家自然也会更多。到了那一天,请不要忘记陆文夫、汪曾祺他们曾经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