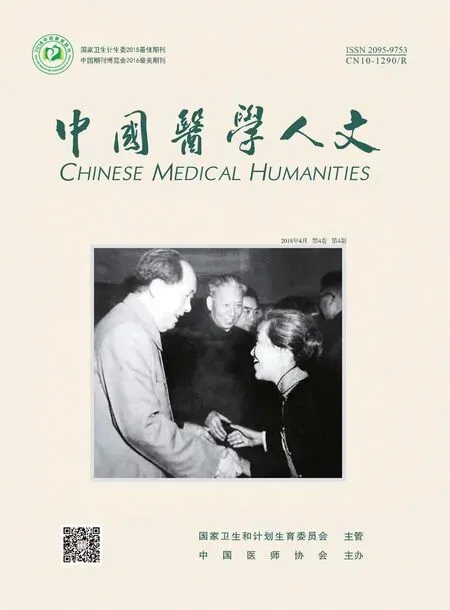六个小故事 六个小脚印
文/高 畅

初 心
有没有天生的医者,我不知道,反正我不是。
小时候的一次重病让我和医院竟有了“缘分”,现在想来当时得的是“脓毒症”,接近感染性休克的我能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活下来,不仅要感谢我火眼金睛锲而不舍一天带我去看三次病的父母,更要感谢帮我找到感染灶那位医生,尽管我不知道她是谁。
那次病后,我变得无比能吃,因为激素的副作用,我变成了小胖子并且一直虚胖到现在,而且成了医院的常客,护士姐姐的噩梦。如果你看见一个淡定的小胖妞一脸认命地看着自己的小手被一针一针地试穿静脉却不见回血,还反过来安慰快要急哭的护士姐姐,那就是我。
那时我想,如果以后当了医生,是不是就不会生病了?看,我做医生的初心就在无数次的扎针和数不清的苦药中发芽了,于是报考医科大学,期间差点转行去当省选调生,但想想从小到大,选科填志愿都是自己按着医生的行头准备的,实在舍不得白大褂、听诊器,也许是开始爱上了,于是傲娇地交了半张白卷,收获了周围师长的叹息和毕业后东方医院的录用通知。
心 惊
对“120”声和电话铃的敏感是从轮转ICU开始的,第一晚值班歇在急诊楼上的一个好久不用的值班房,高低床,简单的褥子,没有枕头、床单和被子,因为跟着主任值班很踏实,盖着白大褂的我睡得正酣,突然一声救护车的声音把我炸醒,可能因为在急诊科的正上方,那尖锐的嘶吼不仅划破静谧的天际,更像一把利爪,生生地把我的脑袋撕开了一道口子,寒毛直竖,心惊肉跳,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手机铃声响起,电话那端传来主任简单的指令“起来,来病号了。”
之后每次夜班,在凌晨两点到两点半之间,“120”的声音和电话铃声都会很有默契地响起,我也从一个开始连呼吸机开关都摸不着的傻妞,慢慢地学会气管插管、中心静脉置管、呼吸机,开始真正意义上抢救病人。取得执业资格后,开始了单独值班的日子,再也不能像之前那般没心没肺地倒头就睡,电话铃、救护车的声音就像是“午夜凶铃”一般,我战战兢兢,不停地学习,因为只有把专业本领练好,才能不那么害怕,才能有底气面对病人,才能不辜负一个个信任你的鲜活的生命。
我时常在想,要多努力,我才能在夜幕降临的时候,面对危重病人不紧张?离那些师长还有多远的距离?如果以后作为上级医生,我是否能给小医生们那样踏实的安全感?
路漫漫。
感 恩
第一个我亲自管理的死亡患者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位年近九旬的老爷爷,巨大的肝脏肿瘤压迫胆管,恶性肿瘤和严重的梗阻性黄疸让他无法进食,小儿子陪老人来到医院,而我成为他的床位医生。
从入院沟通到一次次下病危,家属的配合与理解超乎想象,家人唯一的要求就是让父亲走得不那么痛苦,拒绝手术、化疗,仅基本生命支持,拒绝抢救。
每天查房,老爷爷都会跟我挥个手打招呼,那么平静,那晚夜班,我跟他儿子说:“如果大爷实在难熬,就喊我,给他用点镇痛药。”半夜三点,值班护士来敲门,轻唤我起床,就像发生了什么普通的事情,但还没听完她说什么,我浑身的汗毛都炸开了——“31床的大爷已经开始穿衣服了。”
我迅速冲到床边,和我的慌张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他儿子的淡定,他很抱歉地跟我说:“对不起啊高医生,把你吵醒了,我父亲走了,挺安详的,很感谢你,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开个死亡证明,然后你就去休息吧,我保证早上七点以前我们就离开。”
真的很感恩那一家人,让我第一次单独面对死亡时那样坦然,没有想象中的慌乱,没有哭喊和无理取闹,一切都是那样自然。
怀 疑
一次周末值班,从烧伤科转来了一名严重头面部和呼吸道烧伤的病人,肿胀、焦皮、渗液总之面目全非,就在我准备和家属谈话的当口,原本生命体征还算平稳的患者突然出现了血氧饱和度下降,直线下降。
我第一个反应是“糟了,窒息。”
一面联系耳鼻喉科准备急诊气管切开,一面拿起插管包和50ml注射器冲到床边,“不能等了,先试插,不行穿环甲膜。”
当喉镜进入口腔时,我还是被震惊了,看不见舌头,只有肿成水疱的粘膜挤在一起,中间隐约看到一条缝隙随着艰难的呼吸一开一合,于是对准那条缝隙,送入导管,插管成功了,随着呼吸机的连接,病人的氧饱也逐渐升高,正巧耳鼻喉科的老师赶到。
治疗了三天,病人的病情逐渐平稳,家属也从各地陆续赶来,有他的父母、子女、姊妹,可他们的决定让我乍舌,家属集体选择放弃治疗,签字拔管,拒绝进一步任何救治!
我没有资格站在道德高地去指责他们,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当看到奄奄一息的病人,我还是有一种被“帮凶”的感觉,那天查完房,我早早跟主任请了半天假,逃一样的跑回出租屋,脑子里却总也挥之不去病人那奄奄一息的样子,以至于至今那张床的周围我都不想过去驻足。
我很难过,家人为什么要放弃他,医生不是应该救人,我们又在做什么?也许换做现在的我不会再逃避,但依旧会扼腕,因为和疾病甚至死亡做斗争,是需要医患携手的。
无 力
那是一名多发伤的病人,他干活的铁锨掉进混凝土搅拌机里,当他下意识去抓那个铁锨时,并没有先叫停机器,于是悲剧发生了,他被顺势卷进了机器,一侧眼球损毁,半张面颊被掀开,肋骨多发骨折,多处脏器毁损,血肉模糊,送到我们科后立即建立高级气道,看着前来急会诊的各位主任集体叹气,我知道他的离开只是时间问题。
很快,心跳归于一条直线,面对匆匆赶来的家属,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那张会让家属崩溃的脸尽可能地缝合。午餐时间,耳鼻喉科的孙老师二话不说就下来了,我们都知道这个简单的缝合对于生还毫无意义,但至少能让他尽可能完整地离开。之后我拉着吓傻在一旁的护工阿姨说:“阿姨,我们一起给他擦擦吧。”当把病人交给家属时,一种面对生命逝去而无可奈何的无力感袭来,也许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喜 悦
这是我最乐道的抢救案例,一次中午班,接到了急诊急会诊电话,一个20岁的男孩子,慢性肾衰,常年透析,在公交车上突然意识丧失送来了,查看无意识无脉搏,叹息样呼吸,果断心肺复苏,气管插管,5分钟复苏成功,意识清醒,考虑很可能是高钾所致,因为无法耐受气管插管,遂拔管,自主呼吸好。可是动静脉瘘闭塞了,只能再行深静脉置管,同时联系血透室做好透析准备,给病人纠酸,控制高钾血症,双侧股静脉因为反复置管。全是瘢痕,穿刺难度极大,就在穿刺中病人再次出现意识丧失,立即心肺复苏,建立高级气道,20分钟后复苏成功,意识恢复,更换颈内静脉穿刺成功,稳定生命体征后透析,高钾血症酸中毒逐渐纠正,透析结束时顺利脱机拔管。
短短一下午,两次CPR,困难置管,最终复苏成功完成置管,及时透析并挽救生命。
当置管成功时,肾内科的医生激动地说:“畅,我好想抱抱你哦。”我说:“我也是。”
但我们并没有拥抱,也许是多年临床实战让我们更趋于“冷静”,或者说是一种内心波涛汹涌,外表波澜不惊的职业状态,但类似的喜悦与成就感足以击败一切的犹豫、怀疑、还有可怕的无力感。
也许我们还会面对很多质疑、变革、不公甚至伤害,但只要还想做医生,我们还是医者,就一定会留下一串坚实的脚印。
关于成长,关乎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