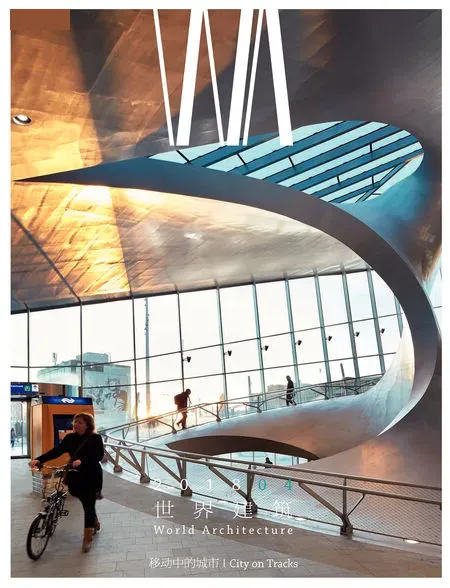当代城市轨道交通综合枢纽理论研究与发展趋势
夏海山,刘晓彤,张纯/XIA Haishan, LIU Xiaotong, ZHANG Chun
1 引言
城市轨道交通已有150多年的发展历史,世界主要大城市都有比较完整的轨道交通系统。有些城市轨道交通运量占城市公交运量的50%以上。例如,巴黎轨道交通承担70%的公交运量,东京达到86%。当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截至到2017年底,中国大陆地区开通城市轨道交通的城市达到了43座。其中开通地铁运营的城市有29座,总里程已经超过3500km。其中,北京、上海的城市轨道交通乘客量超过1000万人次/日[1]。
轨道交通重新定义了城市的空间与时间,也改变了城市活动的模式,轨道交通路网对于城市空间效率起到决定作用。轨道交通枢纽对于城市已经超越了本身的功能,出现一些新的现象和趋势值得研究。当代交通建筑开始由单一的交通功能转变为集交通、娱乐、休闲、商业、居住等多职能为一体的城市交通综合体,为人们提供便捷交通的同时满足多元的城市需求。
在当今网络信息时代城市空间再度分异,作为城市具有特殊引力的轨道交通枢纽,空间强度被不断加强,综合功能不断集聚,成为城市其他空间不可替代的活力集聚点。例如,东京站周边地段空间密度不断加大,最新一期的开发做了更高强度开发计划,建筑面积总计达到300万m2,功能包括政府办公、商务办公、商场等。
作为交通设施的枢纽,目标是更快的乘客集散、更高的换乘效率;作为城市空间的枢纽,目标是更多的人流聚集、更强的空间活力。目标的多元化,导致交通枢纽规划设计的复杂化。因此,在枢纽的选址、空间布局以及换乘衔接方面因不同的认识视角,产生不同的规划设计结果。本文从这几个方面梳理相关的理论研究,旨在通过多重视角的轨道交通枢纽内涵分析,判断未来轨道交通枢纽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2 关于枢纽的内涵、选址与分类研究
2.1 枢纽内涵
国外发达国家从1950年代开始对交通换乘枢纽的规划、设计及政策方面进行研究。1964年日本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新干线,由此发展了“核心型”交通枢纽。随后,欧美国家高速轨道交通相继发展,交通枢纽站也逐渐发展起来。在伦敦、纽约等国际性大都市利用自身铁路交通网络较早发展的优势形成了“更新型”交通枢纽的发展策略,将城市轨道交通、铁路、长途客运以及市内公共交通汇集的复合交通换乘枢纽,与商业、餐饮、娱乐等相融合,最终更新成为一体化综合城市枢纽,实现了立体化的无缝换乘体系,也划分出了许多不同规模与等级的综合枢纽[2]。美国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和华盛顿的联合车站、荷兰鹿特丹中央车站、德国柏林中心火车站都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由于学科专业的视角不同,枢纽的内涵认识也存在差异。以交通的视角,城市轨道交通枢纽的概念为:集有多条轨道交通线路、不同交通方式,具有必要的服务功能和控制设备,为城市对内对外交通、私人交通、公共交通及其内部集散和换乘提供场所的综合性市政设施[3]。在交通运输学科中,强调以轨道交通为主导综合多种不同交通方式,为多种公共交通系统内部换乘提供场所的综合性市政设施。
交通枢纽要实现多种功能空间的高度综合,解决复合功能与运营效率问题。从城市发展的角度,轨道交通引导着城市空间和行为模式的变迁。从规划设计理念上,也出现了如日本的“轨道枢纽城、站街一体化”等新的概念,促动我们更深入的思考枢纽的内在本质。
以城市的视角,结合《中国大百科全书》《美国建筑百科全书》的解释,城市轨道交通的枢纽可以理解为:城市中由于人员密集流动而产生的以交通、商业、服务、住宿甚至文化娱乐等大量城市功能需求汇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包含最基本的市民日常城市生活层面的需求,可以解读为城市生活在具备集中交通换乘功能的城市空间综合体中的集聚,是一个有快速交通集散功能的城市场所。也正是从这种理解中,我们看到了日本“轨道枢纽城”的发展。由于高铁时代时空尺度的改变,轨道枢纽具有城际间快速链接能力,经有机组合而成的城市空间综合体具有独特的中心引力。“轨道枢纽城”就是借助这种由交通因发的中心引力,不断叠合空间功能、强化空间密度、集聚空间活力。
从概念的对比中可以看到,轨道交通枢纽已从单一交通视角向多重的城市视角转变,从单一交通功能向复合的城市功能发展。不仅要满足交通的接驳和换乘要求,还要兼顾人们购物、娱乐、商务、服务等需要,使之成为集多种城市功能于一身的综合体。从站房到外围空间,满足的不仅是出行乘客对交通便捷的需求,而是从整个城市层面满足城市活动的高效性与多样性。
2.2 枢纽选址
随着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和交通的快速发展,国内许多城市的轨道交通体系将发生变化,如何实现不同城市形态下轨道枢纽的科学选址与布局,是近年来轨道交通与城市协同发展的研究重点。
2.2.1 从交通视角
20世纪初,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对仓库最佳位置选址进行研究,随着物流业兴起,以运筹学为基础的模型在物流网点布局规划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大量国内外学者借鉴物流中心选址模型和方法进行枢纽选址布局研究。
轨道交通枢纽布局大多以城市空间结构、土地利用、现有交通网络为基础建立优化模型。一些研究通过不同视角的量化模型分析,探讨枢纽选址的科学性。从轨道系统运行效率出发,格拉雷(Gelareh)等在既定路网基础上研究枢纽的布局方法,建立以系统成本最小为目标函数的轨道交通站间距优化模型[4]。也有从定性与定量结合出发,采用确定性选址和非确定性选址两种方法对城市客运枢纽选址进行研究,前者主要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和专家经验法确定枢纽位置;后者则在有关资料基础上,通过有关指标的量化计算进行定量分析,再根据有关结果进行人机对话,进行综合评价确定枢纽位置[5]。从分析影响选址的主要因素入手,也有通过采用两部聚类法建立选址模型,研究城市枢纽选址的合理性[6]。
2.2.2 从城市视角
轨道交通枢纽布局更多的是在探讨土地利用和城市空间集约与协同问题。如斯内阿迈·哈斯纳比斯(Snehamay Khasnabis)等探讨土地利用和轨道交通枢纽布局二者的关系和相互影响作用[7]。城市轨道交通枢纽从服务城市出发进行空间布局,更应协调好与城市的空间结构、轨网模式和土地利用规划之间的关系,实现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的协调发展[8]。也有一些研究开始关注城市中人的活动行为与枢纽的选址问题。Ustadi等通过调查问卷及测试结果显示:枢纽与家的位置,GPS定位、信息亭、休息椅的数量、数字通信技术管理、行人到楼梯通道的距离、票务员和司机的态度、设备完备程度等因素,可以用于衡量某地是否能成为轨道交通枢纽[9]。
还有学者从时间和参与者的角度对轨道交通枢纽的布局进行探索并建立模型。马里亚诺维(Marianov)和塞拉(Serra)考虑到时间和费用与枢纽选址关系,建立了0-1线性规划模型,并采用Tabu启发式算法求解[10]。雷蒙德(Raymond)等通过在Campbell提出的“P-模型”中加入经济因素,从不同角度对各小区建立相关模型,并选取费用成本这一目标函数来达到最终规划目标[11]。近年也有不少研究基于可达性对枢纽选址和线路优化出发,从乘客角度提出多目标线路优化模型[12-13]。
从上述轨道交通枢纽选址的研究内容和分析要素差异可以看出,视角的不同,导致在城市中枢纽选址布局的评判标准不同。从城市的宏观尺度,更注重枢纽选址的交通作用和土地集约;从使用者的微观尺度,更注重枢纽的可达性、交通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问题。
2.3 枢纽分类
合理的轨道交通枢纽分类有利于辨明枢纽的定位,有助于规划布局、设施资源的配置、交通衔接方式的选择和设施负荷标准的确定,并对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衔接、以及运营管理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各种单一方式的交通枢纽有各自的规范标准,但对于综合交通枢纽等级类别的划分缺少统一权威的标准。目前相关的研究主要针对枢纽的换乘方式、组织形式、服务范围、布置形式、枢纽规模和客流量等指标进行参考划分。
以交通的视角,枢纽分类标准多以交通容量来划分。前苏联学者从枢纽的作用、区位、生产力形式和人口数量等多方面分别对枢纽进行了分类。美国对于交通枢纽的分类较为简单,根据换乘方式的多少分为两类:1~2种换乘方式的枢纽成为运输中心,具有多种交通方式的枢纽则称为综合枢纽[14]。我国有学者在基于国内既有客运枢纽等级划分方法基础上,提出综合交通枢纽等级划分原则,并从枢纽功能定位、能力和占地规模三个方面给出了综合客运枢纽类别及等级划分标准[15]。
从轨道与城市综合开发的角度,我国近几年大规模集中建设实践,对枢纽分类也进行了探索。
有研究针对我国城市综合交通枢纽等级划分方法的不足,根据组团式城市用地布局特点,从城市土地利用与城市交通协同发展的角度,以枢纽承担的城市功能作为划分交通枢纽的依据[16]。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在相应的规划文件中,主要采用枢纽衔接方式种类、衔接轨道线路数量及枢纽所在土地开发类型等指标,划分枢纽等级3~4个等级。深圳轨道交通车站分类体系,主要依据原则有:与常规公交线网接驳的布局结构、交通接驳模式及服务范围、车站周边用地性质,分为综合枢纽站、交通接驳站、片区接驳站和一般换乘站[17]。从分类看出,更强调枢纽定位与城市空间尺度、空间性质和服务辐射范围对应。
相对于以往分类研究关注轨道线路数、线路级别、交通客流数,从当前建设实践来看,开始注重枢纽对城市功能的承载强度,并将其纳入界定和划分的依据。此外,对轨道交通枢纽的核心型与更新型分类,也是从城市视角思考枢纽的功能与作用。
3 关于枢纽空间布局与换乘衔接的研究
从城市轨道交通枢纽空间布局与换乘衔接的研究来看,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轨道交通空间整合设计,二是轨道交通枢纽内部基础设施设计及布局,三是空间内部流线组织。
3.1 枢纽空间布局
3.1.1 从城市空间视角,关注枢纽功能综合性和空间整体性
很多研究从设计出发,通过空间整合探讨轨道交通枢纽空间合理性,有大量文章以案例分析总结空间枢纽如何最大限度发挥枢纽效应,达到合理疏散交通流量,并提出空间整合的设计策略。这些研究总体上归纳轨道交通枢纽公共空间整合设计的必要性,从空间关系、立体化流线组织、功能复合度、空间的规模与形态、服务设施等方面提出设计原则[18-19]。
有研究将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空间理论引入换乘枢纽的平面布置设计,提出按照换乘枢纽流线组织,将设施分为高级中心、次级中心、低级中心,并结合影响服务区进行布局的方法[20]。
针对轨道交通枢纽功能综合及空间复杂,普遍存在环境质量低、导识信息不明、活力不均和整合度不够等问题,很多研究从城市触媒理论、适应性、复杂度等角度分析和解决问题,引导人们基于特定目标进行设计,充分利用轨道交通枢纽带来的大量人流,激发枢纽空间的城市活力;也有从枢纽空间适应性角度,从城市街道和轨道交通枢纽之间的空间,研究枢纽设计如何考虑城市的功能,这与日本的站街一体化理念是一致的。
有研究从空间效率与集约化的角度,强调轨道交通枢纽设计的重点是城市设计、综合步行系统,注重轨道交通综合体内的导向设计,加强轨道交通车站地区的景观环境质量[21]。有研究从使用者的视角,基于“寻路”理论研究铁路枢纽客站空间设计对旅客寻路的影响[22]。
3.1.2 从交通设施视角,关注设施的配备与位置
轨道交通枢纽内部基础设施设计及布局包括各类设施布置方式、设施优化设计、合理性研究等方面。通过枢纽设施布置影响因素分析,很多研究提出了轨道交通枢纽内部设施布置模式,包括立体式布置模式和平铺式布置模式,并采用量化模型研究设施的配置规模,以及各类设施规模的合理比例。哈里亚·穆赫德·伊萨(Haryati Mohd Isa)等调研马来西亚火车站一系列残疾人设施和并确定其是否符合规范[23]。某些研究利用经济学中效用分析法,通过寻找枢纽内存在换乘的任何两种交通方式之间的关键路径,建立枢纽内设施不同布局方案的效用损失模型,以此评价和优化枢纽内设施布局方案[24]。有研究采用点弧变换的方法将枢纽抽象成一个有向行人流网络,以枢纽设施延误计算模型为基础,建立了枢纽设施能力优化理论模型[25]。
从交通功能的视角,关注集中在枢纽内部交通流线系统性,有许多研究利用新技术、新方法建立模型对人流进行预测。杰姆(Cem Kırlangıçoğlu)用行人模拟的方法最大限度地预测潜在的人流[26]。Shuwei等利用模块化神经网络预测北京交通枢纽地区的人流[27]。有些研究以元胞自动机模型和势能场理论为基础,构建了面向设计与能力评价的地铁枢纽站台乘客行为仿真模型[20]。也有些研究借鉴建筑疏散理论中的人流、密度、速度、时间的经验公式,建立模型,定量分析不同换乘形式与换乘客流的关系;以及针对行人流线分析与客运枢纽内部设施布置一体化设计问题,有研究将流线分析方法和系统布置方法(SLP)与系统仿真技术相结合,提出枢纽内部设施布置的最优策略及其优化方案[28]。
通过对国内外单体优化及内部设施布局设计所进行的研究,从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来看,提倡轨道交通枢纽内部空间的整合,向集约化、可持续等趋势发展。枢纽内部设施的设计通过仿真模拟,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了枢纽中人的运动模式和预测人流量,优化设施建设,保障乘客安全。
3.2枢纽换乘与效率研究
客运综合枢纽内各种交通方式的行政主体、立场不同,管理部门不同,难以协调,导致了不少问题,如多种交通方式衔接配合和协调不畅、运能不匹配、乘客换乘不便、换乘次数过多、换乘时间过长等。随着轨道交通分担城市客流量比例快速提升,轨道枢纽己经成为城市交通的核心点,直接影响城市交通效率。根据轨道线路自身的换乘条件、轨道交通与周边各设施衔接优化布局、换乘方案评价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从交通视角,研究主要从衔接模式、运能匹配、衔接线路以及换乘设施的规模衔接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有些研究利用仿真实验进行交通流量管理对相邻街道路网交通状况影响的评估;有研究常规公交与轨道交通衔接布局模式以及一体化协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有些利用相关算法研究最佳接运公交路径;或以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探讨枢纽内各种交通方式之间的换乘衔接模式,以及换乘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在换乘条件方面,有学者以实现乘客换乘距离最小为目标,分析了一种定量的方法为交通枢纽选择合适的几何结构,对轨道交通枢纽设计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29]。Seti等通过仿真人流分析,探索影响交通行为的因素,并提出解决办法以提高交通效率[30]。有研究以成本、运营者和乘客利益最小化为目标,建立公交线路和发车频率的模型[31]。有国外学者通过多式联运时间和熵变量描绘欧洲高铁车站特征,研究换乘效率[32]。
轨道交通枢纽综合开发包括交通设施(包括公交总站、小汽车停车场、自行车停车场和站前广场等设施)和建筑设施(包括商业、办公和居住等设施),这些设施的平面和立面如何布置,将直接影响枢纽的使用效率和功能的发挥。
4 枢纽评价与发展趋势
4.1 枢纽评价
从交通功能视角,有些研究运用时间价值理论对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共交通换乘的协调性进行评价;或通过排队论研究垂直移动设施设计,评价轨道交通枢纽,判断换乘方案的优劣。还有研究城市综合交通枢纽与区域交通及运网的协调性评价,以及与城市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评价,换乘效率评价、可靠性评价、换乘设施评价。有研究通过分析可靠性模型的相关参数,建立研究综合交通枢纽的模型以提高枢纽转运可靠性;有研究釆用模糊评价法、层次分析法等对枢纽进行综合评价[33-34]。
从城市职能及使用者视角,一些城市设计及建筑设计研究更多的是枢纽空间的使用者评价、轨道交通综合体商业空间调查及使用后评价。
综上所述,国内外在轨道交通枢纽换乘及周边设施方面,进行了从换乘设计优化到换乘综合评价,进行全过程分析。通过对各车站客流及交通换乘特征进行系统分析,指导枢纽周边各种换乘设施的布局和换乘交通组织设计,并进行综合评价,优化换乘结构。
4.2 发展方向与趋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轨道交通枢纽选址布局、空间与设施、换乘衔接几个方面呈现的新趋势,此外,枢纽承载更多城市职能的同时,也赋予更多城市文化承载期望。
(1)在轨道交通枢纽布局及选址方面,更多从城市需求角度,发挥轨道交通引导城市发展、调整城市结构的作用。未来枢纽及周边空间将是城市要素流动最频繁,最具活力的地方。
轨道交通枢纽也越来越多地体现与城市功能的整合,城市轨道交通枢纽的空间需要有效地联系城市空间,使地下、地上甚至空中延续一体化发展,充分发挥轨道交通对城市发展的促动作用和对城市空间的激化作用。
日本东京的轨道枢纽带动城市发展的实践非常值得借鉴,各类轨道枢纽以距离城市中心的空间距离进行定位和选址,枢纽带动周边土地开发的密度成梯度变化,不同的密度也与相应的城市功能相匹配[35]。例如,多摩广场站距离市中心23km,二子玉川站距市中心15km,涩谷是城市副中心,涉谷站距离市中心东京站7km,枢纽站的综合开发都有差异化的定位。
1966年田园都市线延长至多摩广场站,经过50年左右的建设开发,以多摩广场站为核心形成很有生活氛围的低密度田园社区,开发的很多养老地产受到欢迎(图1)。
二子玉川站是东急田园都市线和东急大井町线的交叉换乘站,利用换乘枢纽成功进行了商业及办公开发,包括日本最大电商乐天总部落户这里,开发的中央广场商业也非常繁华(图2)。
涩谷有8条轨道线在这里汇集,每天这里的客流量有约300多万,是日本第二大换乘站,涩谷站综合开发将原有地上东急东横线移到地下,地上进行高密度办公酒店商业等综合开发,土地商业利益价值实现最大化,这里已经成为东京IT产业的聚集区(图3-4)[36]。

1 多摩广场站及周边社区开发

2 二子玉川站

3 涩谷枢纽带动周边的高密度开发(图1, 3图片来源:参考文献[36])

4 涩谷枢纽空间组织(图2, 4图片来源:参考文献[35])
(2)枢纽空间呈现4个显著趋势:(a)核心空间均质化:从较单一的等候性候车转变为多向通畅的通过式进出站流线空间,功能布局均质、空间利用均质、使用效果均质,使整体空间活力与集约思想得到体现。(b)换乘空间无缝化:枢纽的换乘模式正在逐步向直接换乘转变,换乘流线清晰、采用立体结构。例如在柏林中央站的设计中,利用中央的十字中庭大厅连接5个功能层就是为了形成可视度高的立体空间布局(图5)。(c)候车空间一体化:轨道交通枢纽综合体中候车空间逐步弱化,呈现与其他功能空间及其衍生空间一体化的特征,普遍采用大空间,灵活分隔。(d)功能空间衍生化:商业空间及文化传播空间已经成为轨道交通枢纽综合体中的重要衍生空间,承载丰富的城市生活和信息,并获得更多的运营收入。日本东京的民营轨道公司西武铁道,在车站空间中的多种经营收入已经超过铁路运输的收入,也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3)交通枢纽自身的效率更加以综合的视角进行评价[37]。城市轨道交通枢纽站换乘效率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换乘的成本、费用、时间、设施、模式、以及评估模型等方面。通过这些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出,改进和优化枢纽站各项换乘设计,可以有效改善枢纽站的运营效率,提升空间使用的满意度。

5 柏林中央站十字立体空间(图片来源:gmp)

6 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地下空间(图片来源:http://bbs.zhulong.com/101010_group_201811/detail10132956)

7 纽约WTC交通枢纽外观

8 纽约WTC交通枢纽室内(图7, 8摄影:韩雨辰)
此外,轨道交通枢纽的竖向发展,特别向地下拓展值得深入研究,由于土地价值、空间效率、文物保护等多种原因,枢纽地下空间具有很大优势。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的宾夕法尼亚车站是地下车站,该车站不仅是纽约市最为繁忙的火车站,也是全美国最繁忙的铁路枢纽,客流量是美铁系统第二繁忙的华盛顿联合车站两倍以上。1962年,宾州铁路公司拆掉原车站大楼建设地下车站,在地面新建宾州大厦和曼迪逊广场花园。2010年再次进行改造,分两期进行。其地下空间支撑了地面高密度的城市空间活动的运行(图6)。
(4)轨道枢纽承载越来越多的城市活动,也承担更多的城市文化承载与传播职能。2004年,圣地亚哥·卡拉特瓦拉(Santiago Calatrava)设计了纽约WTC站方案。这个位于世贸中心“911”遗址以东的轨道交通建筑替代了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被毁的原有地铁站。新的车站以和平鸽的建筑造型,让人们永久铭记和平,也让途径这个特殊地段的人们,能够从空间的感受中获得面向未来的新的希冀与梦想(图7,8)。
5 结论
当代轨道交通枢纽向着交通综合化、功能复合化、性能绿色化发展,其规划设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其演化的内在动因在于城市的发展及人们行为模式的转变,其新的发展特性对枢纽规划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轨道交通枢纽更应当从城市层面考虑规划与设计,其空间整合也包括空间要素整合、实体要素整合和城市要素整合三个层面。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枢纽的设计理论研究也有了多样化、多维度的发展,但整体上理论滞后于实践,至今理论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系统和深化,而且也需要更好地应用到实际工程中。□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年度统计报告. 2017(3):第一期.
[2] 夏海山,张灿,金路. 绿色交通建筑设计创新与BIM技术应用. 华中建筑[J]. 2016(3):128-131.
[3] 朱顺应,郭志勇.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与管理. 东南大学出版社[M],2008
[4] S. Gelareh, S. Nickel. New Approaches to Hub Location Problems in Public Transport Planning[J].Institute Tecno-und-Wirtschafts mathematik,2008:31-37.
[5] 魏恒,任福田. 人-机参与大城市客运选址[J]. 系统工程,1992(4).
[6] 吕慎,田峰. 城市综合客运换乘枢纽选址模型研究. 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07, 24(2):194-199.
[7] Snehamay Khasnabis. Land Use & Transit Integration and Transit Use Incentives[J].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Washington DC, 1997.[8] 甘勇华. 城市轨道交通枢纽空间布局适应性研究[J]. 规划师,2011, 27(6):101-104, 109.
[9] Ustadi M N, Shopi N A M. A Study towards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Hub Characteristics: A Case Study of Northern Region,Peninsular Malaysia[J]. Procedia Economics & Finance,2016(35):612-621.
[10] Marianov V., Serra D. Location of Hubs in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999(3):63-71.
[11] Raymond K Cheung. Impact of Dynamic Decision Making on Hub-and-Hpoke Freight. Transportation Networks[J].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2008,87:49-71.
[12] 郑健. 当代铁路旅客车站设计综述. 建筑学报,2009(4):1-6.
[13] 夏海山,钱霖霖. 城市轨道交通综合体商业空间调查及使用后评价研究. 南方建筑. 2013(2):59-61.
[14] Matsumoto H. International Urban Systems and Air Passenger and Cargo Flows: Some Calculations[J].Journal of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 2004,10(4):241-249.
[15] 漆凯,张星臣. 我国综合客运枢纽等级分级方法的研究. 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 2011, 11(5):17-21.[16] 吕慎,田峰,李旭宏. 基于城市用地与交通一体化枢纽等级体系研究. 交通运输工程与信息学报.2005, 3(1):57-62.
[17] 戴子文,谭国威,戴子龙.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分类及等级划分研究. 都市快轨交通,第29卷,2016(8):38-42.
[18] 郑健. 大型铁路客站的城市角色. 时代建筑,2009(5):6-11.
[19] 麦哈德·冯-格康,于尔根·希尔默. 柏林中央火车站设计. 建筑学报,2009(4): 46-51.
[20] 张琦,韩宝明,李得伟. 地铁枢纽站台的乘客行为仿真模型[J]. 系统仿真学报,2007, 19(22):5120-5124.
[21] Xia H, Li X. Study on Intensive Design of Urban Rail Transport Hub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w-Carbon[M]// LTLGB 2012.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2013:409-415.
[22] 周鑫,沈中伟. 基于寻路理论的铁路枢纽客站空间设计探讨[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11(1):104-109.
[23] Isa H M, Zanol H, Alauddin K, et al. Provisions of Disabled Facilities at The Malaysian Public Transport Stations[J]. 2016(66).
[24] 吕慎, 李旭宏. 城市客运换乘枢纽设施布局效用分析[J]. 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36(6):1024-1028.
[25] 赵莉. 城市轨道交通枢纽交通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D]. 北京交通大学,2011.
[26] Cem Kirlangicoglu. Modeling Passenger Flows in Public Transport Stations[J]. 2015, 12(1):1485.
[27] Wang S, Zhou R, Zhao L. Forecasting Beijing Transportation Hub Areas’s Pedestrian Flow Using Modular Neural Network[J]. Discrete Dynamics in Nature and Society. 2015-6-9, 2015(6):1-6.
[28] 孙宝凤,高晶鑫,贾洪飞. 基于流线分析的客运枢纽设施布置改进方法[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9, 35(12):1637-1642.
[29] Bandara S, Wirasinghe S C. Optimum Geometries for Pier-Type Airport Terminals[J]. Journal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1992, 118(2):187-206.
[30] Setti J R, Hutchinson B G. Passenger‐Terminal Simulation Model[J]. Journal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1990, 120(4):517-535.
[31] Carlos Lucio Martins. Search Strategies for the Feeder Bus Network Design Problem.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998.4(106): 425-440.
[32] Francisco J. Tapiador. Characterizing European High Speed Train Station Using Intermodal Time and Entropy Metrics. Transport Research Part A.2008.10(001).
[33] Zhou X, Yu X, Yang X. The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Urban Public Transportation Hub[C]//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2009:2881-2886.
[34] 孙立山,任福田,姚丽亚. 模糊算法在城市客运交通枢纽换乘方案优选中的应用[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7, 33(5): 470-474.
[35] 北田静男,周伊. 公共建筑设计原理.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36] 酒井良仁. 渋谷駅周辺開発の変遷と東急設計の役割. 近代建築,2013, Vol.67(4): 34-39.
[37] Luca Bertolini. Nodes and places: complexities of railway station redevelopment[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1996, 4(3):331-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