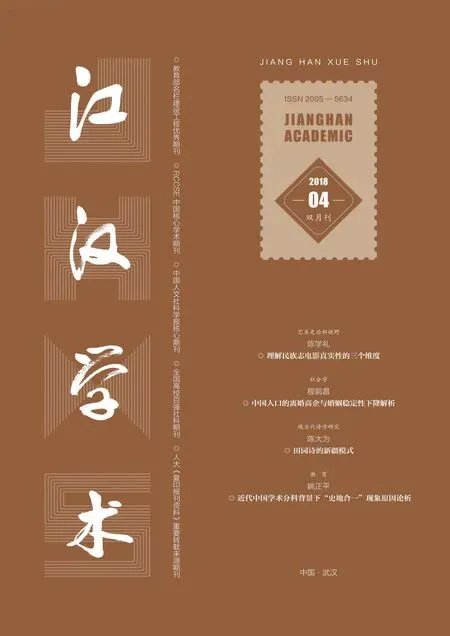秩序伦理与政治稳定
——“秦后第一儒”的社会治理观析论
穆军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杨凌712100)
秩序是人类开展实践活动的前提,政治的首要价值目标就是在人类的公共生活中建立有效的秩序,给社会公众的行为提供明确的预期。汉代是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汉朝成立后,刘邦及其集团从旧政权的挑战者变为新政权的执掌者,行动目标由动员民众、领导王朝革命转变为安抚民心、治国理政。领导王朝革命的行动逻辑与治国理政的行动策略有很大的差异,刘邦君臣在此角色转化过程中面临巨大挑战。在汉初,陆贾作为谋士最早对这一系列挑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陆贾是“秦后第一儒”,在汉帝国成功实现向“儒教中国”转型并完成以儒家为专制国家“精神构造”的过程中,陆贾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陆贾政治思想的逻辑主线是在王朝革命到国家治理的角色转换过程中,统治者如何通过意识形态建设或治国方略的选择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以往学术界对陆贾思想研究主要分为两种研究思路,其一是模块化的研究思路,其二是统合化的研究思路。以上两种思路的缺点分别体现为研究的碎片化和研究主题的偏离。本文将跳出已有研究的思维框架,以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主线,紧密结合陆贾所处的秦亡汉兴这一历史背景,深入探究他通过反思秦政、继承百家思想、重新设计汉初政治秩序建构等过程中形成的治理思想,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形成挖掘优秀传统资源。
一、问题的提出
总体上来说,学术界对陆贾的思想不够重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多。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陆贾思想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研究思路:
(一)模块化的分析思路
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大都是具有一定逻辑关系的理论体系。后人在研究古代思想家的思想时,为了更精准地把握复杂的理论问题,便习惯于将思想家的思想划分为重点不同但互补的子问题加以研究,我们把这种分析思路称为模块化分析思路。模块化分析意味着对整个思想体系的解构与重新整合,是人们为降低问题复杂程度而做的努力。现有的大部分陆贾思想的研究都把陆贾的思想分为道论思想、无为思想、仁本思想、礼法思想、教化思想、经济思想、民族思想以及其他政治思想等几个模块。学者们利用模块化的研究方法把陆贾的思想呈现出来的同时,使陆贾的思想碎片化,没有或者很少能发掘陆贾思想的主题,没能很好地概括陆贾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以某种政治思想的局部板块为研究基点,对整体思想做出的一些评价,由于视野的限制难免得出一些争议较大的结论。例如,关于陆贾“无为”思想的学派归属问题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下。如果长期纠结于这种对现实国家治理贡献性较小的问题上,不仅会导致资源的浪费,而且会使思想史的研究偏离正常的轨道。
(二)统合化的分析思路
本文所指的统合化分析思路与上文的模块化分析思路相对应。研究者基于这种思路对思想家思想的研究,主要侧重点并不在于对思想家思想体系的分解,而重点在于整合。他们往往是在模块化分析成果的基础上,采用一套相关的研究假设或者一以贯之的分析视角,对思想家的思想进行再次的比较和整合分析,以便得出更可靠的结论。在陆贾思想的研究成果中,这种研究思路的成果数量较少,但却代表着陆贾思想研究的发展趋势。徐复观认为陆贾是汉初在文化上启汉室统治集团之蒙的重要思想家[1]53-64。他对陆贾思想的分析主要围绕文化启蒙这一论题展开。他首先根据《史记》及相关史学元典的梳理,论述汉初丰沛集团多军吏、文化氛围差的现状。其次,徐先生指出,《新语》是通俗教育的性质,是陆贾根据刘邦的文化水准所编写的教材。这就从文化启蒙的视角,给《新语》一个恰当的历史定位。最后,徐先生指出,陆贾《新语》针对最高统治者首先提出了“辟庸庠序”的重要性问题,开汉代政府重视教育、举办学校的先河,其文化启蒙的影响尤为深远。徐复观先生的研究视角对后续陆贾思想研究者有很大的启发。刘志伟借鉴了徐复观的文化视角分析模式。他指出,由陆贾代表儒家教统主奏、帝王刘邦伴奏的道德重构与文化复兴序曲,在刘汉初年就已奏响[2]。陆贾所著《新语》,立足于政治文化转型的战略高度,以刘汉王统与儒家教统关系的重构为思考前提,高瞻远瞩地设计了一条以道德重构与文化复兴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战略转型的路线。这种以文化启蒙和文化转型为切入点的分析,相较于模块化的分析思路有很大的进步,能让人们从某一视角深入全面地对陆贾的思想进行认识和评价。但道德重构与文化复兴究竟是不是汉初思想家陆贾所思考和论述的核心问题,则有待进一步讨论。如果核心问题考虑偏颇的话,对思想家思想的把握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
以统合化思路研究陆贾思想的成果还有以下两种:其一,唐国军试图对《新语》进行“整体性解读”“创造性诠释”。他认为:“陆贾的《新语》是帝制时代到来后的第一部中国传统政治学著作。”[3]我们认为这样定位有过度引申的嫌疑。因为陆贾作为汉初的政治家,他作《新语》首先要解决的并不是建构传统政治学理论的问题,而是“如何安治天下”的问题,而且从陆贾一生的履历也可以看出,他更多地是以“政客”的身份活动在汉初的政治舞台,建构政治学理论可能并不是他所思考的重点。至于陆贾对以后中国传统政治学理论的贡献则是后人给予陆贾的“一家之言”而并不是《新语》的核心问题。其二,林聪舜以“建立帝国的深层稳定机制”为视角来论述陆贾的“逆取顺守”观念。他借鉴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对国家与市民社会领导权理论来阐释陆贾的“逆取顺守”观念[4]。林先生比较准确地阐述了陆贾思想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他的观点对于本文写作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林先生论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他只是从“帝国稳定机制”建设这一现实视角来分析陆贾,通过他的成果人们不能对陆贾“逆取顺守”观念产生的过程、这一观念在汉初的具体历史作用、这一观念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等重要问题形成相对完整和明确的认识。
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解决争论的路径不外乎两条:其一,新材料的出现,譬如出土更加权威的版本,或者更为丰富的资料。其二,新方法的采纳,即采纳不同的维度对原有的材料重新观照。增加新材料的难度较大,而新方法的采纳可能更为可行[5]。以往对陆贾思想的研究,尤其是模块化研究思路没有能很好地把陆贾思想与汉初的政治社会环境联系起来。人们对陆贾思想的探究只是局限于《新语》以及《史记》和《汉书》中涉及到陆贾的传记等一些文本资料。笔者认为,要对陆贾思想进行深入全面的挖掘和准确的评价,应该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即把陆贾所著《新语》与汉初的政治制度设计以及陆贾本人的政治活动联系起来,深入细致地研究思想家的观念、当时的政治社会制度和思想家行为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精准地把握研究主题,客观地比较评价,以便让今人对陆贾的思想形成更为清晰、全面的认识。
二、天道伦理:政权合法性的终极依据
统治者要建构长期稳定的政治秩序,必须给自己的统治提供足够的合法性缘由,“合法性……反映了那些寻求统治的人为被统治者接受和认可的程度”[6]。在中国古代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皇帝及其统治集团也会结合具体的政治文化发展情景,从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天的伦理关系来论述政权建构和政权维系的合法性。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引用“五德终始”说作为政权建构层面合法性的论证。“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用“五德终始说”推演论证很好地解释了秦代替周一统天下的正当性。这种论证方式开启了古代王朝合法性建构的门径,对后世影响巨大。“自秦汉直至宋辽金时代,五德终始说一直是历代王朝阐释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7]五德终始说的局限在于它只能较好地论证王朝建立的合法性,对于政权何以长久维系这一更为重要的问题则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汉朝建立之初,在政权建立合法性层面的论证,汉代的君臣都沿用并进一步发展了五德终始说。在政权合法性的长久维系层面,秦朝主要满足于从物质的角度如扫灭六国、一统天下的争霸战争中获得的版图基业和武功威力来论证和彰显其行使权力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论来源导致皇权本身处于不稳定状态。汉初诸帝则在反思秦二世而亡的基础上,从神意的角度寻求道德和智能上的根据以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8]。寻求统治合法性的终极依据,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曲折和漫长的两汉史。
陆贾是汉初儒家思想家中最早试图从终极意义上对政权合法性作出诠释的思想家。他试图在天道与治理原则之间建立起某种逻辑上的关系,从而为他所主张的国家治理原则找到终极的合法性。他把先秦儒学“仁义”“礼乐”等范畴提升到哲学本体论即“天道”的至上高度。“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新语·道基》),陆贾认为天是万物产生的终极来源。由此可见,陆贾试图借古代民众的天命信仰来为统治合法性奠基。天命信仰就是人们把“天”视为宇宙的最高主宰或造化万物的神灵,是一种对人类居于绝对权威和主宰地位的、不可认知与不可抗拒的力量,从而也是君主和一切政治统治的终极来源和形而上学依据[9]。汉初的统治者往往通过宣扬天命观,举行各种敬天祭神仪式来获得民众对其统治的认可与服从。
在借天命信仰确立统治合法性的具体操作层面,陆贾把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家伦理、心性观相结合,建构了汉初最早的天人感应的学说。在天人如何感应这一环节上,他有两个层面的论说,其一是灾异说。“天以灾报恶政,以祥报善政”,“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度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新语·明诫》)自然界的灾异现象,是由于国家管理的治道失败导致的。瘟疫、旱灾、水灾、地震等都被统治者或者反叛者看作上天对统治者的警告。一方面,统治者会下大力气治理灾害,赈济灾民,稳定社会秩序,以提高统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政权的敌对势力也会趁灾难爆发之际,散布谣言,鼓动普通民众起来反抗当朝统治者。这往往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过程的开始。其二是“符瑞”说。陆贾说:“周公与尧、舜合符瑞,二世与桀、纣同祸殃。”(《新语·术事》)在陆贾看来,“符瑞”是天与人沟通的一种方式,是君王统治合法性的体现。
陆贾的灾异谴告论和“符瑞”说开启了汉代天人感应、以“天象”论政的思潮。尽管人们日常所看到的天以及各种天象与代表着政权合法性的“必然之天”存在着某种联系,但归根到底这种天的必然性以及天与现实政权合法性的联系都是人们主观思维的产物。所以,“必然之天”究竟是什么,完全取决于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样的程度上理解和把握了“天”,而不在于天本身究竟是什么[10]。由于抽象思维能力的局限,陆贾同先秦两汉的其他儒家思想家一样,总是把人们日常可以感受到的天、天象与用以支撑政权合法性、代表最高道德法则的“必然之天”混同起来。这就体现出其政权合法性论证的思维局限,即“以经验的方式把握概念和定义”[11]的论证方式。陆贾等汉初思想家没能意识到统治的正当性不在于“天子”是否能够代表“天意”,而在于普通民众在内心的思维过程中对“天子”代表“天理”的深刻认同,并把这种认同转化为责任和义务。直到两宋“天理”论形成之后,我国思想家才完成了这一思想的升华。“天所以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理,不能为天,故苍苍者即此道理之天,故曰:其体即谓之天,其主宰即谓之帝。”“天下只有一个正当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朱子语类》卷二五)
三、“制度伦理”:秩序建构的方向导引
制度伦理是从根本上对制度善的追问[12],是对制度建构和运行过程道德合理性的评价,其主要作用在于为现实的制度安排提供价值指引,以调整并保障制度稳定运行和预期功能的实现。秦后第一儒者——陆贾作《新语》,其主要目的在于为刘邦草莽君臣的政权建设提供儒学价值导引,以纠制秦弊,避免重蹈秦朝二世而亡的覆辙。
首先,制度建构的儒学化转向与汉初统治者的休养生息政策相关。中国古代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肇始于秦,汉朝则总体上继承了这一政治体制,即“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汉书·百官公卿表》)。汉承秦制继续着力于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权建设,同时吸取秦霸道治国、二世而亡的教训,对秦政进行一些小的改造和修补。秦始皇及其继任者诉诸功利(富国强兵、开疆拓土)、暴力或暴力的威胁来为其权力的行使提供正当性。但是,汉王朝比秦王朝先进的是其统治者和思想家重视暴力手段治理国家的同时,从反思历史的视角,发掘出了道德礼制在维系政治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并把它运用到具体的国家制度建设中。陆贾在《新语》中以儒家仁义思想为主,融合儒、道、法等流派思想,提出一系列有利于君主专制的治国方略。这就使得刘邦及其丰沛集团重新审视儒家仁义德教学说在“守天下”阶段的重要作用。这对于促进儒学与政治的结合,促使儒学观念与国家治理相结合起到了积极的意义。曾经厌恶儒士的汉高祖最后以“太牢”重礼祭祀孔子,便是汉初统治者开始认同儒学并把儒家观念引入国家治理过程的重要标志。
其次,儒学的工具化转向与刘邦文武并用的综合治国方略相关。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最主要特色即是强调皇权专制,突出皇权的“地位独尊”“势位独一”。执掌皇权的帝王掌握着制定规则、解释规则和改变规则的最后决定权。在这种体制下,儒家思想家及其所宣扬的治国理政观念要想取得并拓展生存空间,就不得不屈服或服膺于皇权。秦朝的“焚书坑儒”便是儒者与皇权对抗的极端案例。到了汉初,儒家思想家吸取以往教训,逐步放弃了先秦儒家固守道德理想化的生存方式,积极谋求与王权的结合。他们借助王权,通过对民众的教化、官员的选拔等渠道把儒家所倡导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等灌输到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这样,儒家思想不再是少数知识精英所独有的道德理想和价值情怀,而是成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成为普通民众维持日常生活的规则,成为平民走上仕途、实现人生理想的工具。总之,儒学由先秦时期相对形而上的价值,变成了汉初社会人人可用的工具。在汉代,儒学这种工具主义倾向的转变过程中,陆贾可谓功不可没。当然在汉初诸儒中,最早倡导儒学工具主义转向的是叔孙通。他以先秦儒家的礼仪为典范,再加上因时制宜的简化处理,确定了汉王朝的各种行为规范,让高祖刘邦深切体会到作为皇帝的威严和尊贵。自他开始刘邦逐步转变了其轻视儒者的态度。但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说,制定朝仪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真正让刘邦及丰沛集团感受到儒家相对于法家、道家等其他学派的治国理论具有决定性优势的是陆贾。
陆贾把儒家价值系统与现实的君王权力结合在一起,为汉初君主重视儒学乃至后来的“独尊儒术”奠定了基础。陆贾说:“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新语·术事》)在这种权变治理观念的引导下,他以儒家修身、仁义、德治等理念为主体,糅合道家老子的“无为”理念和法家的权势法制理念,为高祖刘邦提出了一套文武并用综合治国方略。在陆贾看来,儒、墨、名、法、阴阳等各家思想都是一种治国的手段,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才是最终的目的。为了实现优良的政治秩序这一目标,他用工具主义的思维,对儒学进行改造,开拓了儒学发展的新时期。
四、教化伦理:秩序维系的根本之策
所谓“教化”,本义原是指“上所施下所效”,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有所改变,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的重要方式。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来看,教化就是中国古代政府及其管理者运用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礼仪等各种手段,来影响民众的思想意识和日常行为,从而确立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建构和维系长期有效的政治秩序。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历来都非常重视教化。中国古代从汉代开始,帝王和地方官吏把教化作为实现国家长期有效治理的主要手段。秦后第一儒——陆贾提出的教化观念治理对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的整个汉初国家教化治理方略具有重要影响。
首先,圣化的君王为教化的主体。陆贾指出人本身具有好利恶难、避劳就逸的天性,因而,教化是必要的。但由谁来进行教化呢?陆贾思想中对人进行了等级划分即分为先圣、君王和一般民众。当他在理论上设计了这些等级之后,教化伦理的前提就完备了。在陆贾看来,教化的任务应该由“先圣”或贤人来承担。“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新语·道基》)同时,在现实的国家治理过程中,儒家思想家又往往把掌握最高权力的君主描述为圣人或者圣人的化身。因此,在陆贾的教化治理观念中,对普遍民众实行教化是掌握绝对权力的君王治国的第一要务。教化的过程也是统治权力从上到下运行的过程。通过教化达到统一思想,培养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顺民,实现统治秩序的长治久安。陆贾强调圣人与君主的合一,以便君主承担起用诗、书、礼、乐等儒家道德观念教化民众的职责。陆贾认为圣人是“统四海之权,主九州之众”的现实掌权者,而不仅仅是像先秦时期孔子、颜回那样或不为政权所用或远离政治的“素王”。圣化的君王用诗书礼乐来教化民众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国家治理秩序的统一,即“同好恶,一风俗”,加强政治控制,增强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即“绝国异俗,莫不知慕,乐则歌,哀则哭,盖圣人之教所齐一也”(《新语·明戒》)。
其次,移风易俗与礼乐规范为教化的主要方式。风俗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域民众的心理意识及其物化形态。它在社会民众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发挥着规约与引导作用,对于民众行为模式的养成和调整起着无可替代的形塑作用。相对于强制性的政令刑罚,风俗的养成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靠主体的内心认同和自觉行动。但从政治统治的效果来看,教化风俗比政令刑罚能起到更长久的效果。历代士人和统治者往往把一些有利于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良风美俗提炼、升华为人人遵循的社会规范,通过移风易俗稳固政治统治根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管子提出“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管子·八观》)。汉初的高惠文景诸帝通过身体力行以及各种激励手段匡正社会风俗,规范人情伦理关系,为汉朝统治秩序的建构和维系做出了巨大贡献。陆贾则是这个过程当中最早的教化政策倡导和推行者。陆贾在《新语·道基》篇中,明确提出教化是圣人所提倡的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备,智者达其心,百工穷其巧,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新语·道基》)在这里,陆贾告诫统治者国家治理中可能会存在“礼仪不行,纲纪不立”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按照儒家的五经、六艺等经典教义施行教化,最后要达到“绪人伦”“正风俗”“通文雅”的目的。在儒家学者看来,“绪人伦”是“正风俗”及其他一切政治行为的基础。“厚人伦,伦,理也,君臣父子之义,朋友之交,男女之别,皆是人之常理。”[13]君臣、父子、朋友、男女等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合理运行所应面对的基本关系。正确处理这几对关系是匡正风俗,建构优良政治秩序的前提。同时,风俗有良俗与恶俗之分,“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荀子·王霸》)秦兼灭六国,建立天下一统的国家之后,采取焚书坑儒等极端和残暴的方式来“匡饬异俗”,试图依赖法制的强硬手段达到统一风俗的目的,但却事与愿违。汉王朝建立初期,民生凋敝,刘邦集团把国家治理的重心集中在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方面,于是黄老无为思想成为主导治理观念。然而,对于美化、齐整风俗,形成维护大一统政治秩序的良好社会风尚这一治国的基本问题,陆贾、贾谊等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却先于统治者提了出来。陆贾认为“圣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录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设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恶,一风俗”(《新语·明诫》)。这里,陆贾借“圣人”之名把统一风俗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通过反思秦朝通过极端的方式统一风俗的做法,汉初统治者和思想家一致认为行礼义、立纲纪的礼乐之教才能在移风易俗的过程中收到百姓徙恶迁善而不自知的效果。在具体的礼乐教育内容和方法的选择层面,陆贾认为应该在京都设立大学,在地方设立学校,对民众实施道德教化,以端正上下级之间的规矩,明确父子之间的礼节,让民众谨遵君臣之间的忠诚道义,使强权不欺凌弱势群体,使多数不虐待少数,让人们改变贪婪的心态,树立清正廉洁的社会风气。
最后,统治者率先垂范是教化的重要手段。中国古代思想家历来都非常重视君主在教化百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把君主确立榜样、率先垂范作为教化的重要环节。君王不仅是良好社会规范的制定者,而且也应该是坚定执行者。他们只有以身作则,亲自践行良好的道德规范,才能更好地教化百姓,最终引导社会风气转向更好的方面。陆贾非常重视君王的行为在整个国家道德风尚形成中的重要影响。陆贾引用历史上反面的例子来论证其观点。他说从前周襄王违背孝道,不孝敬后母,结果当时社会上有好多人效仿他的行为而背叛父母。秦始皇生活骄奢,追求奢靡,大肆征调民力营造高台楼榭。这样,天下豪门莫不争相效仿,建设豪宅大院,因此,陆贾告诫统治者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地去践履优良的德行,为百姓做出表率,引领良好的风尚。
五、结论
梁任公曾说:“秦、汉之交,实中国数千年一大关键也。”[14]这一时期不仅是中国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逐步形成并臻于完善时期,而且从思想史发展来看,汉初思想家的理论体现为先秦诸子百家学说的复兴和相互借鉴、融合特征。这种儒、法、道融合对后世思想的影响尤其深远。徐复观先生认为“不了解两汉,便不能彻底了解近代。即就学术思想而言,以经学史学为中心,再加以文学作辅翼,亦无不由两汉树立其骨干,后人承其绪余,而略有发展”[1]1,因此,无论从政治制度还是从思想理论层面来说,秦、汉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领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大一统政治秩序形成过程中,秦始皇和汉武帝是重要的帝王,而陆贾、贾谊、晁错、董仲舒等则是关键的政治思想家。关于董仲舒的政治思想,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界研究成果颇丰,而陆贾、贾谊和晁错等思想家政治思维所独具的鲜明时代性特点却鲜有学者给予认真的对待并加以系统的总结。陆贾是“秦后第一儒”,是汉初刘邦政权仁义德化政治的启蒙人。他与汉高祖刘邦关于汉初国家治理的“武功”与“文治”、“逆取”与“顺守”等思维和手段的争论开启了儒家探寻长治久安治国理念的步伐。“长期有效的国家治理何以可能”是古今中外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关注的共同话题。时至今日,什么样的政治秩序是优良的政治秩序、如何构建优良的政治秩序仍然是中外政治学理论家构建自身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核心论题。这种核心论题的古今延续也正是思想史研究价值所在。“国家并不受困于自己的过去,但在许多情况下,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前发生的事,仍对政治的性质发挥着重大影响。”[15]中国现在的政治秩序建构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在构建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政治学话语体系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借鉴传统思想家关于治国理政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