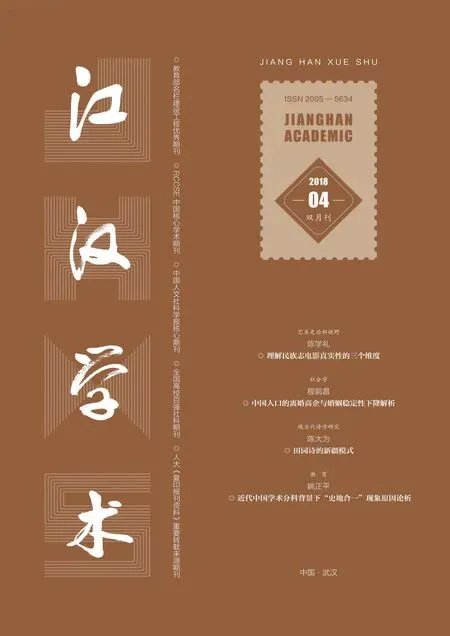论党内法规解释权归属及其法治完善
谭波
(河南工业大学法学院,郑州450001)
一、“党内法规”制度由来及其解释权归属现状
(一)“党内法规”制度由来
关于“党内法规”的提法,在理论上也曾有过争议①,但综合其发展演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其所具有的中国特色,是经过历史选择而形成的,符合中国党情国情。“党内法规”一词最早被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使用,其在当年十月所做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报告中,明确指出,关于“党的纪律”之重申,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1]。实际上,在中共二大上通过的党章已经可以被视作党内法规的雏形。1990年《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以下简称《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得以通过,其中明确规定了党内法规的概念与制定程序等事项。1992年“党内法规”一词被写进党章,即“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2013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得以通过,对党内法规的制定提出了规范化要求,使其步入法治轨道。
2013年党内法规体系完善的另一个标志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以下简称《制定条例》)的出台,这部被称之为“党内法规立法法”的条例,不仅取代了《制定程序暂行条例》,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立法体例对党内法规的立改废释做了较之前更为系统的规定。党内法规就是“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委、中央各部门和省区市党委制定的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的总称”。以其第五章“适用与解释”和第六章“备案、清理与评估”为例,这在原1990年版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中是不曾涉及的,该部分内容也极尽可能地仿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五章“适用与备案”的相关规定,甚至还增加了党内法规的清理与评估制度,立法意识可谓与时俱进甚至超前。实际上这也是使党内法规向国家法律靠拢,同时为两者未来的衔接预设前提。
(二)党内法规解释主体的基本样板分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党内法规正式被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立法过程的完整环节,与党内法规制定相伴而生的就是党内法规的“改”“释”“废”。2013年的《制定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党内法规的解释同党内法规具有同等效力”。这等于从法律效力层面对党内法规做了制度肯认。而决定这种制度运行的根本要素则是其解释权的归属。同时,《制定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党内法规的形式包括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据此,笔者对现行有效的部分党内法规的解释权归属做了相应统计(见表1):

表1 部分党内法规解释权归属一览②
从目前党中央下设的十几个部门行使党内法规解释权的具体情形来看③,比较常见的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作为解释主体的模式,这也与其相应的党内职能有着直接的联系,其制定的党内法规也分别被称之为纪检条规(由中纪委制定)或部门党内法规。有些部门因其本身所具有的议事协调机构或办事机构以及非行使行政职能的性质,其相应的党内法规制定权以及由此衍生的党内法规解释权就此淡化。比如国务院办事机构中的国务院研究室之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前者也属于一般不参与制定行政规章的机构,后者作为研究机构也与前者性质雷同,均无相应的规范制定权,自然也就不存在相应的规范解释权。
二、党内法规解释权归属之问题所在
(一)党内法规解释权归属难成体系
从目前党内法规的效力与种类来看,党章应由党中央做出解释,虽然党章中并没有规定相应的解释权条款。但2016年10月27日由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涉及全党全国性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和解释”。党章作为最高党内法规,其解释权必然要归属于党中央。“准则在党内法规体系中位阶比较高,仅次于党章。”④其内容涉及全党的政治生活、组织生活和全体党员行为,一般由中央全体会议或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批准,但准则中本身未涉及解释权条款。以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为例,两者都没有涉及相应的解释权归属问题。但如上述习近平总书记所做的《说明》所言,只要涉及全党全国性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其解释权还是归属于党的中央委员会。
从“条例”以下直至“细则”,其解释权则由相应的党中央部门行使,但各类党内法规的解释权归属区别也较为明显。其中“条例”涉及某一领域的重要工作或重要关系,内容较为全面,由党中央通过,其解释主体也一般定格为党中央部门。如2007年10月8日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布的《安全生产领域违纪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实际上是对2003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解释,其中规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此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又在2008年6月至2012年3月先后多次就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廉洁自律“七项要求”、违反信访工作纪律、机构编制违纪行为、设立“小金库”和使用“小金库”款项违纪行为、党员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用公款出国(境)旅游及相关违纪行为、违反《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行为、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等方面的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问题进行了解释。根据表1中所反映的情形,关于“条例”的解释权归属主体还有“会同”和“商”某部门的表述,如果制定主体涉及中共中央与国务院“两条线”,这种“会同”有时还存在“有关部门”的模糊性表述,而“商”某部门的表述在2013年《制定条例》通过前后都曾有过,表明这种制度已经为党中央所持续认可,但该制度与“会同”制度的区别仍有待进一步界定。
“规定”调整的党内某一方面工作或党内生活的一般问题,一般由中办或与国办联合发布,其解释权主体自然也涉及相应的行政部门,有时甚至会出现党政联合进行解释或单独交由相应的政务部门解释,而这种联合有时甚至并不讲究绝对的级别对应。
就“办法”而言,其存在“中办发”和“中组发”的不同类别,其相应的解释主体也就此存在区别(参见表2),但也曾出现过交叉的情形,即由“中办发”而由中组部解释,说明这种解释权的归属体制还是依其事务本身的性质而非相应的级别差序。
“规则”是规范党的领导机关的议事程序和工作方法的党内法规,常见的有议事规则、工作规则等等[2]。“细则”一般较为具体,通常是条例和规定的具体落实,依其文件内容特性交由相应的中央部门解释。如中组部1990年8月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试行)》,其最后一条还明确规定,“过去有关发展党员工作的规定和解释,凡与本细则不一致的,均以本细则规定为准”。这里的解释并不必然代表党内法规解释,但很明显也起码应是由中组部或其同级部门做出的相关说明。
(二)党内法规解释权缺乏“适用”的制度视阈
比较《制定条例》与《立法法》,我们可以发现前者“解释”与“适用”被列为一章,从科学性来讲,前者的体例比起后者更易于理解,符合实情。在《立法法》中,法律解释被单列为一章,这也与我国当时立法的法治认识与技术水平相契合。法律解释(立法法中特指立法解释)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渊源,与其他法律渊源存在根本的差别。
“解释”本来也可以被归属为广义上的“适用”之一环,特别是在各种司法解释、行政解释、地方解释等适用类解释方面,“解释”的这种性质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在《立法法》的“适用与备案”一章,相应的法律效力排序规则、规范冲突选择适用规则与裁决规则是典型的适用环节,也是对相应效力问题的一种解释。
对于党内法规而言,道理相同。在党内法规效力方面,除党章在党内法规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外,中纪委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党内法规效力要高于省级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即中央党内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党内法规。而中纪委与中央各部门的党内法规之间如出现不一致,则交由中央裁决;在中纪委、中央各部门以及省级党委发现党内法规与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相抵触或与宪法和法律不一致的,抑或省级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与中央党内法规相抵触的,都可以由中央责令改正或撤销,当然前提是发现主体将此类信息第一时间传递至中央,或启动相应的申请责令改正或申请撤销程序。按照这种效力排序,省级党委进行的党内法规解释之效力也当然低于中央党内法规解释之效力。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章中这种特殊的组织制度规定是决定中央党内法规及其解释的效力高于省级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及其相应解释的效力的根本原因。

表2 部分“办法”类党内法规的解释权归属一览
除了上述存在于《制定条例》中的适用规则,还有一些规定于单个党内法规中的效力规则。以问责制度为例,目前党内法规中与问责相关的共有119部,其中专门规定12部,这些党内法规并没有实现问责机制的统一化[3],而2016年7月8日起施行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最后一条明确规定,“此前发布的有关问责的规定,凡与本条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条例执行”。这种表述实际上仿行于立法中的表述,却有效解决了党内法规的冲突问题,是对《制定条例》效力排序规则的补充,也是在“适用”背景下对党内法规的“解释”做了内部处理的极好样板。有学者在关注党章的解释机制时,就明确指出党章解释的内容应该包括对党章含义的解释和其他党内法规是否同党章相抵触、相冲突的解释[4]。这与上述所提及的“适用”背景下的解释有异曲同工之处。
同时,从外部“适用”与制度契合的角度来看,党内法规解释也尚未做好良好的制度应对,包括党内法规解释与国家法律解释之间的制度联系与效力排位,在可能的机构合并前提下如何解决党内法规解释的制度定位,这些都是我们未能从“适用”角度来考量党内法规解释体系的现实表现。
(三)解释权归属制度缺少统一的制度惯性
除上述广义的解释主体,还存在特殊情况下未规定解释权归属主体的情形,这时就需要采取相应的程序机制来确定相应的解释权主体。2013年5月27日出台的《制定条例》第五章规定,“本条例施行前发布的中央党内法规,未明确规定解释机关的,由中央办公厅请示中央后承办”。这足以表明,在该条例出台之前,存在一些党内法规并没有谈及解释权主体的,而中央办公厅就成为了此时的主体补缺程序的发起者,而中共中央在中办请示后将会进行相应的“确权”。同条还规定了由中纪委、中央各部门以及省级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由其自行解释。但是很明显,这种解释权主体的确定规则也首先要让位于党内法规自身规定的解释权主体资格。
三、完善我国党内法规解释权归属的制度对策
党内法规解释权制度在我国已经得到初步构建,但相比我国立法、司法过程中的相应法律解释或司法解释制度,其不完善的现状十分明显,这也是完善我国党内法规适用制度的具体环节和突破口。
(一)确立党内法规解释权归属的完整体系
党内法规的解释与党内法规一样,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尚未形成的党内法规解释权体系成为我国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不能回避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党内法规的解释权具有层次性,依其所解释的党内法规的效力,应该构建我国以“党中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办公厅—中央其他各机关”为核心的中央党内法规解释权体系,以及省级地方党委为主导的地方党内法规解释权体系。其中,党章由党中央解释,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等依次可以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等相应作出解释,同时还可能商相应的国务院下属机构一并作出解释。在地方层面,由于省级地方党委是制定省级党内法规的唯一主体,根据“谁制定谁解释”的原则,省级地方党委也成为解释的当然主体。这种机制一旦确立,不仅能够让党内法规解释成为一种常态性工作,还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党内法规在其条文中不规定解释主体的情形。而能够确定这种机制的文件,正是目前的《制定条例》,在现有的“适用与解释”一章中可以单列“解释”部分,进一步明确党内法规解释对于党内法规实施的重要性,在其中扩充各级党内法规的解释权规定,对目前的七类党内法规可以按照级别和制定主体的不同进行相应解释机制的设定,确定解释权的归属原则与行使责任。这种体系应该随着党内法规制定权的扩张保持一定的开放性,随着设区的市成为党内法规制定权的试点,更多的党内法规解释权的试验也必须随之展开。
(二)完善党内法规解释权主体的“补缺式”规定
参照我国现行宪法的模式,党章中首先也可以对解释权的归属主体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宪法的第62条和第67条分别规定了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的权力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权力,党章作为党内法规中具有最高效力的文件,类似于宪法作为国家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大法之地位⑤。作为立改释等一系列立法的前期与后续活动而言,宪法的制定因其制宪权的特殊性在宪法之中未有规定,宪法的修改和解释应被视为同等重要的法律适用环节,因此,党章在已经规定了修改权的前提下理应将其解释权也规定进其内文之中。其实,在中共历史上,“二大”至“四大”通过的党章均规定其解释之权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5],这种制度传统应该加以延续,但对解释权主体可以再加斟酌。“党内法规解释工作制度制定机关的选择,应与党内法规解释工作制度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的地位相适应。”[6]基于目前涉及党内法规解释和备案的相应规定都由党中央出台,因此,应以党中央作为建构党内法规解释工作制度的主体。
党章中可以规定自身的解释权主体以及其他不同层级的党内法规的解释权归属原则,以“谁制定,谁解释”为归属原则,按照不同党内法规的效力位阶,分别做出相对细致的规定。就“准则”而言,因其具有特殊的行文表述规则,而不便在其行文本身之中做出规定,但根据前文所提及的解释权归属主体的补充规则,在2013年《制定条例》之前通过的准则,可由中央办公厅提请中央后承办,而在此之后如涉及全党全国性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其解释权应归属于党的中央委员会。但如果不涉及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则仍可以按照之前由中办提请中央后承办的程序加以解决,当然这种规则需要在未来《制定条例》的修改过程中对“准则”这一类特殊的党内法规加以单独确定。其他党内法规大体可以按照各自规定来确定相应的解释主体,而以党章规定的原则为补充。
以党内法规所涉及的内容来进行解释权主体的分类完善也不失为一条改革思路。按照2017年中共中央出台的《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党内法规的解释权主体也可以依组织法规、领导法规、自身建设法规和监督保障法规进行权力归位。以监督保障法规为例,中纪委所做的纪检条规相应解释较为典型,尤其是在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过程中,前文所提及的对若干违纪行为的认定成为中纪委党内法规解释权行使的重点⑥,包括目前中纪委制定的违反“八项规定”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解释。基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刑法化”和中纪委查办案件的需要,针对《纪律处分条例》适用方面的规定被大量解释,但是这种解释一方面需要更系统地涵盖需要解释的法条,按类别进行分类处理,另一方面也需要如刑法修正案般进行编号,提前规划解释对象,保证适用主体在认知上的延续性与统一性,淡化“以释代法”的趋向,使其逐渐成为未来党内法规解释权行使的样板。
(三)保持党内法规解释权与国家法律解释权的“适用”衔接
在党内法规日渐增多的情况下,需要考虑的是当下国家立法层面的法律解释权行使与党内法规解释权行使的协调一致,比如前文提及的由国家行政机关与党内机关联合制定的党内法规。在国家立法的法律解释领域,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司法解释和地方解释共同组成了国家法律解释权的整体。但在党内法规领域,这种解释权的格局并非一一对应。如果从立法解释的角度来看,目前党内法规的解释权也仅仅是做到了这个层面。党内法规在适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解释类型还未有涉及,比如省级党委在相应的问题处理上是否结合地方实际情形有一定的“地方解释权”⑦。当然这种解释和国家立法法律解释权的不同就在于其在党委层面“地方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而这种原则在国家立法领域表现为“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或特殊的效力裁决规则。而在《制定条例》之中,如前所述,也已经存在相应的效力排序规则和裁决机制,需要强化的是如何尽可能使党内法规在保持其“立法解释”机制的前提下,尽可能创设出不违逆上位解释或“立法解释”意图的其他解释,以保证党内法规在各种范围内得到尽可能科学合理的实施。党内法规不同于国家法律规范之处主要在于其制定程序的内部性和适用范围的有效性,因此,需要在解释权的行使上注重国家法律规范相较于党内法规的优位性,即保证党纪合法性的同时,党员首先要遵守同等层面的国家法,其次作为一名党员要遵守党内法规的高标准要求;在解释权行使上务求重视其解释内容的层次性,当然其前提便是在于其条文表述的层次性。
目前,国家监察委员会集中行使监督职能,与中纪委合署办公。在这种情况下,涉及法律监督方面的党内法规的解释又务必考虑与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解释权保持契合。在国家监察委员会逐渐整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部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职能后,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解释权也会囊括原有的一些党内法规解释权、行政解释权和司法解释权的相应特征,从效力上来讲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但在执行层面具有和“一府”或“两院”的解释相对同等的效力,即所谓的“监察解释”,但其着重点在监督权行使领域[7]。
党内法规既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辅助者”,也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者”,在整个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势必起到重要的“排头兵”作用,也起到了难得的昭示作用。未来,为了让更多的党内法规能够在实施层面做到切实可行,对党内法规解释权的制度构建必须及时上路,方可早收制度成效,久久为功。
注释:
①关于党内法规的赞成学说与反对学说,参见李忠:《党内法规建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5页。
②关于此表中涉及的党内法规的最新内容,请参照2018年5月的《中共中央关于涉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党内法规和相关文件专项清理的决定》,其中涉及废止的3件和修改的35件中央党内法规和相关文件。
③党中央各部门主要包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国家监察委员会与其合署办公)、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
④参见2016年11月2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
⑤但同时必须申明的是,各政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党章也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⑥北京大学的黄国珍曾对此做过统计,截至2013年共有8项解释,计86条,13400字,但遗憾的是该统计遗漏了2012年2月中纪委做出的《违反〈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解释》。参见黄国珍:《廉政制度建设的新路径——以“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例》,载《社科纵横》2013年第5期,第86-87页。
⑦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凡属于地方性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制定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作出规定。凡属于地方性法规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进行解释”。关于此一问题,也有学者主张应当取消地方解释,但在目前情况下,仍有探讨如何在适应现有机制的前提下加以完善的必要。参见魏胜强:《论地方国家机关的法律解释权应当取消》,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