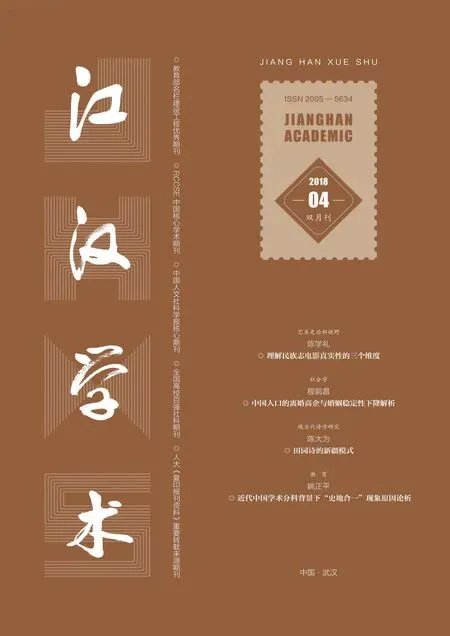论中国早期电影评论中的“西学中源”思潮
——探究“影戏源流中土”的偏执论证
赵轩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上海200072)
1897年,被学界视作中国最早之电影批评的《观美国影戏记》在慨叹“天地之间,千变万化,如蜃楼海市,与过影何以异?”而“人生真梦幻泡影耳,皆可作如是观”的同时,也刻意提及“中国影戏始于汉武帝时,今蜀中尚有此戏”[1]。虽然限于早期史料的匮乏,一时无从断定此文是否可视为论证“影戏源流中土”的发轫之作,但在这之后,影评文字中的“西学中源”(亦即“西学源于中学”之意)思潮绵延不绝。于早期电影批评而言,民族语言的差异反而被无声电影时期电影技术的缺憾所掩盖。大量西方影片流入中国,在给中国观众带来银幕梦幻的同时,也带来了潜隐其间的异质文化压迫。虽然早期电影批评无从呈现“西学东渐”过程中“发扬国粹”“中西互补”“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中国本位”乃至现代化的清晰投影,但此时的电影评论积极参与了哈贝马斯所谓“公共空间”(publicsphere)的构建。《申报》以及沪上兴起的大量电影期刊,已经“不再是朝廷法令或官场消息的传达工具,而逐渐演变为一种官场以外的‘社会’声音”[2]。本文力图在梳理“影戏源流中土”文本历史的基础上,勾勒“西学中源”思潮投射于早期电影批评的话语改造策略,并探究潜隐其间的国人文化心理。
一、“影戏源流中土”的文本表述
1914年,《进步》杂志第53册刊载了一篇名为《活动影戏滥觞中国与其发明之历史》的文章。这一配有多幅图片的文字,实际上意图勾勒中国传统影戏于两百年前传入法国,并最终在欧洲得到民众的认可的传播史:
法国本有之影灯,称为Ombreschinoises(支那影灯),则知其实传自中国。后经开伦谭爱克Carand’Aehe之更造,始名曰Ombresfraneaises(法兰西影灯),乃为法国之影灯耳。中国影灯之传于法国,当在距今二百年前。[3]
在这之后,法国影戏还出现了《萨拉芬断桥》这一历史名剧,这一艺术在十九世纪之后分化出所谓“法国派”与“英国派”等不同风格,文章最后不无唏嘘地写道:
以上所述,为自古时以至十九世纪影灯之沿革。可见进步皆有一定之次序。而由儿童之玩物,变为社会应用之要品。所异者,创自中国,发达而利用之,中国不与焉。其可慨也夫。[3]
这段文章的结尾,实则奠定了“影戏源流中土”论证中的固定思路:一是中土影戏传播西域,并最终演化为西洋影戏发扬光大,必定沿承“进步之次序”;二是创自中国,却不在国人手中兴盛,颇可慨叹。
如同《观美国影戏记》中描绘的“中国影戏”到“东洋影灯”再到西洋影戏的演变历程一样,论证“影戏源流中土”的文字多半倾向从中国传统典籍寻找影戏存续的脉络,以勾勒影戏源流中土,而后发扬于西方的历史线索。
中国影戏的渊源被当时论者最早追溯至西汉武帝时的“李夫人招魂”。除了1897年的评论文字外,周瘦鹃的《影戏话》、程步高的《中国影戏考源》以及程树仁的《中华影业史》都做了相对认真的考证。周瘦鹃在其16篇《影戏话》的开篇中即写道:
考之吾国古昔,滥觞于汉武帝时。武帝以李夫人死,悼念弗哀,齐少翁设帐、张灯烛,帝坐他帐望之,仿佛是夫人。此虽近于神话,或亦为少翁所演之一种影戏。惜后即弗传,未能改弦更张耳。[4]
而程步高的考据貌似更为严谨:
《汉武帝内传》云:“汉武帝李夫人亡,帝思之不已。齐人李少翁言能致之。夜设帐张烛,帝坐帐。自帷中望之,仿佛见夫人相。”此虽未必能断言其为影戏。然察其实,如“设帐张烛以望之,仿佛见像”。虽不提及“影戏”二字,亦与影戏近矣。考诸《桯史》,有秦始皇作鱼龙水戏,汉武益以幻眼、走索、寻撞、舞轮、弄腕影戏之句。则“影戏”二字实始于汉。惜无详实之记载,未能知其底蕴耳。[5]
程树仁文章中的记载与之相类,不过其依据之典籍则是宋人高承的《事物纪原》。除此而外,程树仁还从宋人张耒的《明道杂志》,孟元老的《东京梦华録》,吴自牧的《梦粱录》以及《都城纪事》等笔记散文中,摘引了有关宋代影戏的记载:
有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刻。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以彩色装饰,不致损坏。
凡影戏,京师人初以素纸雕簇,后用彩色装皮为之,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雕以丑貌。其话本与诵史书正同。[6]
当然,上述论者虽然有描摹中土影戏衍变路线的自觉,可惜其考据尚不算细致。
另一方面,“影戏源流中土”论者还多从现存的民俗与民间地方戏中梳理影戏渊源,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周瘦鹃、程步高、程树仁均提及元宵节俗中的走马灯与西人之“惊盘”(活动旋转盘)的相似,程步高还颇为细致地援引范成大《上元节物诗》①中“转影骑纵”自注“马骑灯”的典故,以及姜夔《观灯诗》②:“纷纷铁马小回旋,幻出曹公大战年”的诗句,认为走马灯始于宋代③,“按欧美之活动旋转盘,约发现于十九世纪。则走马灯之发现,远在旋转盘之前”[5]。而何西亚搜集整理的浙西杭湖的民间影戏[7],陈志进回忆的甘肃“灯影戏”[8],洞庭一我整理的湖南省旧式影戏[6]13,均是民间戏曲中影戏渊源的探索。尤其是被黄任之视为“今电影之嚆矢”[6]12的滦州影戏,因其仍不时演出于江浙沪上,受到当时影评者的普遍关注。有论者即称其为“我们土产的影剧”,认为“这种‘影’(俗称影)的组织和戏剧大同小异,相去无几。不过戏是真人唱做,影是傀儡代替罢了”,并最终认定滦州影戏是“中国影的一种”[9]。更有论者认为滦州影戏未尝不是中国人发明影戏的明证,“可惜中国人向来缺乏科学思想,所以没有人把他作进一步的研究”[10]。而电影实业家周剑云则慨叹滦州影戏在历史上未受重视,“可惜当时没有人发明电术,否则传到现在,也可以与欧洲影戏比美了”[11]。
二、“西学中源”说的历史衍变
在中国整个思想文化史上,认为外来之学源自中土的思潮着实算不得新鲜。魏晋时期,佛法东传,中国本土的玄学思想就一度提出“老子化胡”之说,认为西域佛徒均是老君西出函谷关后加以点化,方得正果。道教后来还著有《老子化胡经》,算是“西学中源”说的最早文本表征。在明清之际,一代鸿儒黄宗羲最早提出“周公、商高之术,中原失传而被纂于西人,试按其言以求之,汶阳之田可归也”[12]的想法;而与西域传教士汤若望一同编订《崇祯历书》的徐光启,则在其《测量法义》序中论及西方自然科学时说道:“是法也,与《周髀》《九章》之勾股测望异乎?不异也。”[13]这一认定影响了清初许多自然科学家,清初数学家王锡阐即认为“西学原本中学,非臆撰也”[14]。梅文鼎也在讨论西方“借根法”时认为,中西算学“殆名异而实同,非徒曰似之已也”[15]。加之清朝统治初期,在文化视野上较为开明的康熙皇帝对于西学的大力吸收,上述思想得到官方的首肯。康熙皇帝即认为西洋三角算法,“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16]。徐光启等人编订的《崇祯历书》,一度因深受保守派攻讦而未被大明皇朝采用,最终也被清朝采纳。可以说,明清之际的上述思想为后世“西学中源”说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侵扰,使得如何面对西学成为摆在此时有识之士面前亟待解决之问题。“西学中源说”再次被推到历史前台。洋务大臣冯桂芬认为西洋天文历法、民俗政务均宗于中土,并且不无愤恨地说:“中华扶舆灵秀,磅礴而郁积,巢、燧、羲、轩数神圣,前民利用所创始,诸夷晚出,何尝不窃我绪余。”[17]而被窃之“绪余”,一方面依旧是明清之际关注的自然科学。黄遵宪即通过对西方自然科学的考察,认为:“机器之精,攻守之能,则墨子备攻备突、削鸢能飞之绪余也。而格致之学,无不引其端于《墨子·经》上下篇。”[18]郑观应在其名作《盛世危言》中,对于西学中的“声光化电”作了更多的考据,而最终的结果均是“出于我也”[19]274-275。
另一方面,这种从诸子典籍中发端,找寻西学源流的倾向也论及社会科学。比如西方的政治学说与宗教神学,黄遵宪也将其归化到墨家学说的源流中,认为:“余考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其谓人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汝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18]而像西方的议会制度,多位学者也都认为中国古已有之。陈炽即称:“泰西议院之法,本古人悬轺建铎、闾师党正之遗意,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即孟子所称庶人在官者,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也。”[20]107郑观应认为:“议院乃上古遗意,固非西法,亦非创辟之论。”[19]323梁启超甚至以《洪范》之“卿士”、《孟子》中的“诸大夫”与《洪范》之“庶人”、《孟子》中的“国人”分别比附西方的上议院和下议院,最终认为西方的议会制度“岂能特创,盖必于三代明王遗制所受之矣”[21]。
上述言论的穿凿附会之处自不待言,面对东西方之间并不发达的交流史,为了确保西学中源的言之有据,秉承此说者还必须勾勒中学源流的西传路线,这一传播的达成可能是传说中散轶的上古典籍,比如郑观应所言:“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阙《冬官》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19]242-243;或者是战乱、暴政中造成的人才流失,陈炽即言:“迄秦政焚坑,而后,必有名儒硕彦抱器而西,致海外诸邦”[20]74;甚或是有关上古帝王的传说,梅文鼎就认为,中学向西散播源于尧王命臣子于四方观测天象,其中向西观测的和仲超出了中国的范围,“但言西而不限以地者”。又因没有海路的阻隔、气候的差异、北极的严寒,故而“和仲既奉帝命测验,可以西则更细,远人慕德景从,或有得其一言之指授,一事之留传,亦即有以开其知觉之路”[22]。这般无稽之谈,在当时一度大有市场,陈炽甚至认为:“西人自谓其种实出于印度,而印度之婆罗门种实出于中华。黄帝暮年,巡狩昆仑,弓剑桥山,留此神明之胄,即《山海经》之‘白民’是已。婆罗门者,‘白民’之转音也。则知黄种白种,中西本出一源。”[23]
“影戏源流中土论”明显也犯了这种想当然的错误,限于当时影评人对于电影艺术本质的认知局限,电影的“西学中源”说并未上升到形上层面。即便仅在技术层面论证,许多论者也是仅凭感官认识,甚至望文生义的理解“影戏”;同时,因为幻灯片(东洋影灯)先行进入国人视野,一些论者先入为主地将投射于银幕白幔的影像视为电影的主要技术表征,而将放映机一端的技术沿革完全忽略(前文提及的《活动影戏滥觞中国与其发明之历史》便是一例),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技术认知上的幼稚。程树仁考证中国影戏,其第一渊源竟然是逗弄儿童的“手影”(并且附上马徐惟邦的一幅绘图),对于电影技术认知的单一,由之可见一斑。
历史学家顾颉刚1934年在归纳滦州影戏的艺术特征时,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电影萌生于滦州影戏”的认知做了回应:
在观众看来,它(指滦州影戏,引者注)和旧剧的关系还不如电影为接近。这固是事实,不过实在它的渊源,却和旧剧极深,而与电影简直不相干。这因为是一个是科学的产儿,一个是封建的遗裔,本来是不必强为牵合的。[24]
在顾颉刚看来,滦州影戏与西洋影戏除了剧本取材上有很大差别外,技术上的差别更是突出,他在文章中还刻意比较了两者在用光、成像及立体感等方面的差异。
上述较为科学的批驳,在1930年代方始出现,足见“影戏源流中土论”势力之强大。总之,对于电影技术本质简单化的读解甚或误解,无疑是造成“影戏源流中土”风行一时的原因。
三、“影戏源流中土”的文化心理机制
现在看来,将西方列强的先进科技,归化为诸子典籍中的衍生小术,“西学中源说”背后无疑潜隐着中国传统文化面对殖民文化秩序的一种敏感与焦虑。而将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想象成三坟五典中记述的番外之民,只能视作老大帝国的一场春秋大梦了。这种孱弱的心态受到抨击是一种必然,严复先生即几近尖刻地嘲讽这一思想潮流:“晚近更有一种自居名流,于西洋格致诸学,仅得诸耳剽之余,于其实际,从未讨论。意欲扬己抑人,夸张博雅,则于古书中猎取近似陈言,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羌无新奇”;这些“令人呕哕议论,足见中国民智之卑”[25]。鲁迅先生也写道,“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无非是一种“合群的爱国的自大”[26]。
电影认知上的“西学中源”也是如此。几近与影评界关注滦州影戏之渊源地位的同时,认为电影全由西人发明的声音便一直存在。1911年,即有文章介绍“美国电学发明者易智孙氏”,“近日发明影戏中能唱动之法”[27]。1921年,顾肯夫在《影戏源流考》中即“直截痛快”地宣称“影戏是安迭生(ThomasEdison美人一八四七年生)发明的”[28]。除此而外,更有文章认定美国人狄克孙[29](本是爱迪生的助手)、德国人史克拉达诺夫斯基[30]才是电影的真正发明人。直至1935年电影发明四十周年的国际性纪念活动才让“活动电影是法国禄米埃兄弟发明的”[31]成为较为主流的认定。然而,坚称影戏源流中土的文字并未因此消失,有论者即于1931年写道:“电影人人都说是外国人发明的,但是据我说起来,它的发源却在中国”,北平从前的“纸人影戏”和“现在的影戏,真可说是大同小异。”[32]“影戏的发明确在十七世纪的中国,它不过是中国影子戏的变相罢了。”[33]甚至在为儿童普及电影科学常识的文章中,也有论者宣称“(走马灯)这件玩具,看起来虽然是我国旧有的发明,却不能说它不是近代发明的活动影戏的基础呀”[34]。
由是观之,与普遍意义上的“西学中源说”一样,对“影戏源流中土”的论证,从一开始就蹈入了一种文化偏执,是一种以外来事物的运作范式投射中华传统,却又要维系自身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复杂心态。这其间的削足适履与刻意抬高便不可避免。比如何西亚在分析浙江一带的传统影戏时,明显理念先行地以电影技术框架衡量中国传统影戏,其认为:“所以名为‘影戏’者,以其隔纸相映,若走马灯之幢幢往来,仿佛有如影子之移动然也。此处所以不迳称‘影戏’,而加‘旧’字于上者,盖欲有别于今之电影故耳。”然而这一旧影戏的表演过程中往往伴之以唱段和台词,这让拘泥于无声影戏的作者颇费周章地进行了解释:
旧影戏中兼用歌唱道白,初甚疑之。盖影不能发声,既名之曰影戏,即不应有歌唱。此理至明,而操是业者不能答也。及今思之,电影中尚有文字说明,最近欧美且有演电影时合以留声机唱片者矣。但旧影戏通行于农村社会,农民未能人人识字。此其穿插道白之作用欤。[7]
这其中的矫枉之处并不仅仅源于论者对于电影艺术本质认知的局限,更多的还是基于偏执论证必然面对的逻辑窘境。
针对影戏的“西学中源”说,戏剧家陈大悲即做过一针见血的讽刺:
在美国有许多“东方迷”的批评家恭维我们是发明影戏的鼻祖,于是乎一班夸大狂的侨胞们便沾沾自喜,引以为荣。不错,“滦州影戏”一类的玩艺儿至今还盛行我们的北方各省,的确是发明在欧美各种影戏之先。但是,我们好意思把这种兽皮制成的五颜六色的人畜雕画,高举在手里,对世界各国醉心于银幕艺术的人们,夸耀我们中国民族是全世界首先发明影戏的鼻祖吗?恭维我们为发明影戏的鼻祖原是人家的谦德,我们却不可以骄天之功,硬说这一种将取黑板而代之的银幕艺术就是我们“滦州影戏”的远房外孙。[35]
曹大功也专门针对中国影灯于十七世纪传入法国的论证发表意见:
法国记载影戏的书上说:“一七八四年,欧洲始有影灯发现(并非幻灯),这种影子成功的戏,群众不过说是中国的影子戏,并无感动观众的能力……”照这样看起来,中国竟是影戏真正发明者(?)了。然而影灯与影戏,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中间若无人披荆斩棘,辛苦精英,岂能破空飞渡。我们万万不敢掠人之美,又犯夸大狂的毛病,也随声附和,说是中国发明的。[36]
总之,在上述论者看来,于中国电影而言,浸淫在老旧帝国、地大物博的幻想中,守成于前人旧物而止步不前,无疑才是真正有害的。
当然,将“西学中源”说完全统归于老旧中国的一种文化臆想未尽合理,这一学说风行之初,除却一些保守派利用这一理论拒斥“西学东渐”外,更多的维新派人物则是将其视作一种消解国内人士对抗西学的话语策略。如同“礼失求诸野”的圣人祖训,正因为中西之学有了融通性,借鉴西学也即不存在“数典忘祖”的嫌疑。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对此有很精当的分析:“盖引进‘西学’而恐邦人之多怪而不纳也,援外以入于中,一若礼失求野,豚放归笠者。卫护国故而恐邦人之见异或迁也,亦援外以入于中,一若反求诸己而不必乞于邻者。彼迎此拒,心异而貌同耳。”[37]无论是“礼失求野”的引介西学,还是“反求诸己”的守旧自大,这种“一个旗号,两个阵营”[38]的现状,终究迎合了中国学界对待西学时的矛盾心态,即便是仰慕西学的维新派,也在借西学以变法的过程中达成了自身的文化自足感。梁启超就自省道:“启超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骄之结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39]故而,这种文化心态的存在,使得西学中源说在诸多领域都具备了自己萌生的语境。“影戏源流中土论”亦复如是,面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时的矛盾心态也同样适用于早期影评者。
慨叹影戏虽缘出中国,却未在国人手中发扬光大,是影戏源流中土论的固定思路。许多论者正是意图沿承这一理念,呼吁中国影业的自立自强。较早鼓吹“影戏源流中土论”的程步高、程树仁、周剑云等人皆是影界中人,在民族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的发展上均有自己的抱负和实绩,这也令他们笔下的偏执论调并未执着于中华博大、万国来朝的臆想,而因着眼于当下振兴,更多具备了话语策略的色彩。沈小瑟宣称:“要论影戏的发源,最早的还是我们中国,后来没有人去继续研究他,这样才让美国人占了先”,而其梳理影戏前世今生的目的,则是为了“根据过去,至少也可以把将来猜出几成来。”[40]英之认定滦州影戏是“我们土产的影戏”,其目的也为愤慨:“可恨中国只会故步自封。假若再更形变相,深思追求,未尝不可发明一种惊人的艺术。为什么总抄袭欧美,拾人家的唾沫呢?”[9]周剑云为“滦州影戏”没有机会与“电术”相结合而惋惜之时,其目的更多地是呼吁时下影人“多摄几种好片子把中国人优美的民性,诚朴的风俗介绍给西洋人,也好纠正他们观察华人的错误。”[11]程步高在历史考据之后也慨叹道:
由此观之,影戏之原始于中国。流至欧美,即从而研究之。西影之成功,即为外人所有。犹如活字板、炮火之发明于中国,因我国人之懒于研究,利权遂外溢。我国人发明之,而外国人遂利用之,影戏一端,以足相见。今虽急起直追,亦有望尘莫及之叹矣。[5]
他将影戏比附于四大发明,其吁请国民自强、影业自立的写作目的,无疑较之研究性的考据更具实践价值。
在此意义上,上述认定“影戏源流中土”的论者与陈大悲等批判论者实则是殊途同归的,若以陈大悲的文字作表述,他们的目的实则均是质问:“为什么能够发明‘皮人影戏’的中国人,只会千百年如一日的故步自封?为什么我们自己没有把‘皮人影戏’演进而为现代的电影?我们惭愧还来不及,还好意思自夸吗?”而他们的内心也均是“希望中国影片能够在世界各国影业竞赛市场上,占一个位置”,“就是要把过去与将来,来一个一刀两段”[35]。故而,近乎偏执的影戏源流中土的论证,呈现出“西学东渐”过程中国人面对西方先进科技的矛盾心态,同时也投射出此时中国影人意图促进影业自立、振兴民族电影的渴望。以现时之眼光审视电影“西学中源”论中的科技谬误已不具备多少价值,而梳理这其间的文化心态,总结其吁请自强的话语策略,才是正确评价这一影评思潮的当下性方式。
注释:
①原诗名为《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其中有“映光鱼隐见,转影骑纵横”一句。
②原诗名为《观灯口号》:纷纷铁马小回旋,幻出曹公大战年。若使英雄知此事,不教儿女戏灯前。
③实际上,秦汉时即有蟠螭灯,唐代即有仙音烛和转鹭灯,程步高的考据并不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