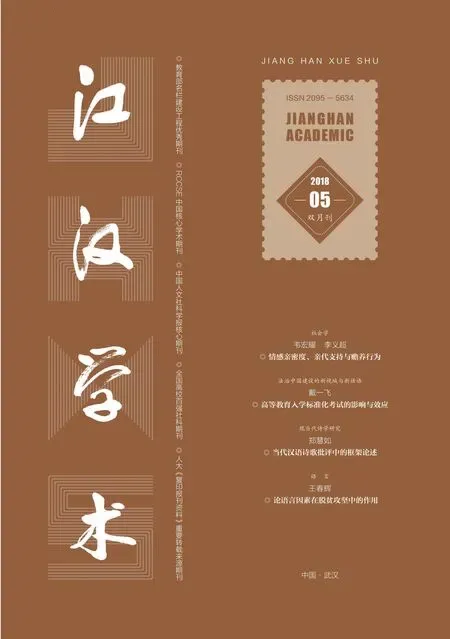当代汉语诗歌批评中的框架论述
郑慧如
(逢甲大学 中国文学系,台湾 台中 40724)
一、问题意识与论述方向
文学批评/评论的论述方式表现论述者的逻辑思考,也是其文学观念、意识形态、美学印迹、人文素养等的整体表现。尤其在学术领域里,具备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必定从问题意识展开论述。不论是以作者的主体意识主导论述方向,还是被评论的文本以其内部脉络引领评论线索而产生最后的文章,经常显现一定的框架。框架很难避免。当代评论界不乏自我标榜不设框架的评论方式,然而一旦以“不设框架”为旗帜,“不设框架”就成了这类评论的注册商标,也就是一种框架。
框架论述的作者必然有心于论述效力,期待自己的评论有人认同,所以不可能完全避免人为的痕迹;换言之,操笔的那个“我”总是主导着论述。而一篇文学评论中,执笔者“我执”的轻重、使用数据的诚信问题,则是其公信力的基础。
发展了百年的汉语当代文学,我们更期待独创、深刻、有洞见、有个性、具备基本学术伦理的作品。问题意识明确的评论,既然有一定的论述方向,必定有所偏重;而有所偏重,也就意味着视野不全面。感染力强的评论,读者群容易向天平的两端倾斜:可能心有戚戚,也可能颇不以为然。然而不论读者是哪一种,成功的文学评论总验证了“全面数据”的无谓。奇妙的是,即使作者和读者都心知肚明,知道任何一篇,或一本文学上的评论不可能真正做到对被评资料、群体或个人滴水不漏的全面检证,然而,愿意坦然承认评论本来就是有所偏执的人,却很罕见。这背后的因素,可能是既定成见、眼入虚妄、道听途说、证据不足、论证过程疏漏等等出在“人”的问题,在人文领域中,就是“‘做’学问”的胸襟和态度。一篇无私、深刻的文学评论,可以从中窥见作者的人文底蕴。
1967年,颜元叔就说过:“文学批评的标准应该是:文学是否达成批评生命的任务。”“批评生命,是考察生命的真相,诠释生命的奥秘。”“文学是哲学之戏剧化。”[1]由颜元叔的个性而自成系列的文学评论篇章,热切、无私、清晰、独断、奋勇,非常有肩膀地扛起文学教育家对时代的使命。今日重读,许多话语仍有警钟之效。当今文学界与学术界的学者、评论家,当钻营一己的学术或文化生命而罔顾“文学批评的标准”时,颜元叔的话语犹如冰水浇背。类似的话语包括:颜元叔认为批评家应该以良知良能区分文学作品的好坏,在其阅读经验中建立价值判断,推开坏作品、为严肃的好作品当尖兵,建立文学价值的尺度等等。①50年前的那些话语,读之犹令人热血沸腾,整个人都精神起来。这,就是一种问题意识,也是一种生命情态,一以贯之的;这样的框架论述,为有志于文学评论者所仰望。
因应学院的升等要求,如今训练有素的学者仰望各种“核心期刊”,许多论点不愠不火或不痛不痒的“严谨论文”应运而生,诸如“某某溯源”“某某考”“某某传播过程”等类的文章,在“核心期刊”中颇占一定数量。这类文章除了具有问题意识与论述方向,主要的共相是戒备森严、防护周到;而其论题则趋向把当代的文学研究写成考据,又尽量不碰触说理,避免动辄得咎的好坏评价。
汉语新诗评论发展逾百年,特种评论形式包括随笔、骂战或论战、序跋、单一诗作的短篇评析、学术论文、专著等。整体而言,现代诗评论朝向周备、稳妥、言人之所未言的方向走。在这个趋向下,我们指望的现代诗评论,既应具备论述方向与问题意识,评论者更应多读书、多思考,护卫人文价值,发愿力挽狂澜,而不只是写个不停。尤其重要的,与其说是客观评价,不如说是遵守学术伦理。
二、现当代诗评论常见的框架论述
文学评论常因在地性而使得同文同种的文字或观念生发出迥异的样态,直接影响评论的姿容。在语言方面,虽然海峡两岸都用“现代汉语”,质地上有许多差别。大陆的现代诗研究角度比较着重作品在大时代的重量和视野,比较会凸显质地上紧张、坚硬的诗;台湾则否,大我、大时代、大格局、大叙述未必是评论者靠拢的对象。
比较台湾海峡两岸的当代诗研究,在相似性上,两岸的当代诗研究经常涌现的共同议题为:新诗/旧诗、内容/形式、都市/乡村、外来思潮/在地传统、感性/知性、自由/秩序、明朗/晦涩等等。在相异性上,两岸当代诗及其研究之别,经常带有某种实质性的条件与特征,而不仅表现为程度、范围,不只表现为事情发生的时间先后。比如,两岸的现当代诗研究或批评,在社会文化空间上都存在着对“中心”与“边缘”的选择,可是两边所侧重的选择与选择的结果刚好相对。奚密论述当代汉诗性质的时候,特别提出“边缘性”[2]。为学术或教育体制所“收编”、规范的现当代汉语诗史撰述,极大程度上仰赖“不规范”“边缘”的论述。
与主流意识形态,与制度化的语言、情感、思维方式保持距离,加以质疑和再造,应该看作是当代诗存在的意义,和它获得生命力的主要保证。从台湾的学位论文观察现当代诗的论文书写,可看出以拈出“值得讨论”的诗人与诗作为其共通性。所谓“值得讨论”,大抵是从已被肯定的诗人与诗作探入,或就已具相当声望而尚待深入讨论的诗人进一步探凿。在“值得讨论”的正向意义中,优秀的论述逻辑清晰,并可让读者体会到诗人较明晰的定位。
现代诗评论中很普遍的现象,是从作者、主题、时间断限切入而开展研究视域。以台湾的学位论文为例,即可见“作家论”之洋洋大观。②常见的评论方式为:论者习于以某些评论家的论述做为范型,再放到历史长河的文学史常识里,然后追溯该诗人的文学养分、诗风谱系,再移位到当代的诠释情境,以扣问相关论题的承继与转拓。
且以有关林耀德的研究为例。在普遍的认知里,像郑明娳、刘纪蕙等具代表性的研究,都指出林耀德是都市文学、政治文学的旗手,特别提到林耀德富含现代性的议题如身体、情欲、科幻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台湾文学史上思潮转变的轨迹。台湾对于林耀德诗创作的共识,约如刘纪蕙所说:“林耀德的后现代是要脱离80年代垄断诗坛的体制,企图衔接上海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台湾日据时代现代主义作家、台湾五六十年代现代派、台湾超现实主义,以迄于台湾80年代他自己所提倡的‘新世代’与都市文学。”[3]都市文学、政治文学、身体、情欲、科幻,这些既定的评论,为林耀德的文学创作划下相当稳定的论述框架,看起来周延而无疑义。既起的研究者,既要在这些视域中匍匐前行,又要有独到的发现,委实相当不易;然而硕士研究生翁燕玲却能在既有的材料上迈出新局。林耀德在以为数惊人的作品主题与文类扣问当代思潮与文学史的同时,很注重作品的质量、大众化、身份位阶等这几个内在有些矛盾的部分,可是在翁燕玲之前,研究林耀德的资料中尚未有所发现。把诗,而不是小说或其他文类,当作追求大众化的手段,虽然林耀德自己说过,许多评论者却置若罔闻。在《八○年代现代诗世代交替现象》中,林耀德说:“追求‘大众化’的梦幻幻灭之后,针对‘质’的思维必须成为我们品鉴诗格、编撰诗史的首要考虑。”[4]翁燕玲不受定型的林耀德研究绑定,能勇于根据第一手资料提出判断。在《林耀德研究——现代性的追索》里,翁燕玲说林耀德:“林耀德向大众靠拢的最积极的尝试,当属现代诗。”[5]这的确是兼具史胆与史识的洞见。此例也可以看出,框架论述对继往开来的研究仍然有所帮助。
三、框架论述的导向作用
框架论述的定性、导向作用,对于被评者形塑的社会评价与心理暗示,经过滚雪球似的传播作用,感染力不可小觑。框架论述画出箭头、喻示方向,或贴了标签;被框定的作者或作品未必有回嘴的机会。假如我们暂且将“标签”一词中性化:被贴上的标签或者是正面,或者负面。在现代诗评论中,被贴上正向标签的人也许就微笑领受、颔首称是,因为对于别人赞美自己的话,总不好再锦上添花;但是被贴上负面标签,则可能烽烟漫起、炮火隆隆。台湾现代诗史中某些口水战的起因就是这样来的,引出了许多论战文章。以现代诗中的论战为题,篇幅已足可写成博士论文。③
框架论述的对特定对象的讨论方式,可能经过一整篇文章的论证,也可能采用点射式的一言定位。而一整篇文章的论证方式,大致有基于文本的阅读和基于对某种思想、理论或主义的认知两大类。为论述方便,我们暂且把基于文本阅读的讨论方式称为“精读式”,而把基于对某种思想、理论或主义的认知的文学评论称之为“标签式”。以台湾当代诗评为例,在“点射式”“精读式”“标签式”的框架论述中,各展现不同的风貌。
点射式的一言定位,比如“诗僧”“诗儒”“诗魔”等称号④。基于文本的精读式阅读,比如洛夫的《论余光中的“天狼星”》、颜元叔的《细读洛夫的两首诗》。基于对某种思想、理论或主义的标签式认知,比如孟樊认为杜国清向表现主义靠拢而以“新即物主义”论杜国清;认为林耀德提倡的“都市精神”与“都市题材”无关,乃从巴特、福柯、德里达嫁接而致,而由此探入林耀德的都市诗学理论;认为1970—1980年代的张汉良,以新批评做现代诗所做的实际研究,主要针对文本做内缘的讨论,因而定位张汉良为“客观批评家”;认为简政珍的诗学理论主要源自以海德格尔等人的看法,而定位简政珍为“现象学的诗学家”。⑤“新即物主义”“客观批评家”“现象学的诗学家”“后现代主义的都市诗学”,即分别为孟樊替杜国清、张汉良、简政珍、林耀德圈定的论述框架。
中国文学批评固有“人格即文格”之说,寓阅读精义于一言的点射论述,表面上说的是作品,内里却往往指涉作者的品格⑥。有一种一言式的断语,下在文章的主标题以总结被讨论对象的风格,但透过整篇文章去论证。例如,陈义芝在其新著《风格的诞生》里,以“长剑错金”总结张错的诗风、以“胭脂苦成袈裟”总结周梦蝶的诗风[6],就是撇去理论包装,直探诗作,精读后再契入诗人情性,结合作品风格与作者人格的观点。然而,即使透过地毯式的精读和诠释,一锤定音的论断都容易失真,何况掐头去尾、横空而至、缺乏前后文的断语。像“诗僧”“诗儒”“诗魔”等称谓,对理解文本没有说明,意义不大,不妨看作迎风招展的旗帜;回顾中国文学史,比“诗仙”“诗圣”“诗佛”等称呼更重要的,是相对应的作品,而非诗人的行为如何“仙”“圣”“佛”。这些仙佛圣魔僧鬼的称谓,不能得知是褒是贬,就算是作者,其实不必笑纳。
台湾现代诗评中,基于文本的阅读,经过一整篇文章论证的精读式论述,洛夫的《论余光中的“天狼星”》和颜元叔的《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有共同点:1.对被评者以负面意见为多;2.被评者都曾撰文回应;3.评者和被评者一度,或永久,因而伤害彼此的友谊。
1961年,洛夫以《论余光中的“天狼星”》全面剖析余光中的创作历程及特色,认为《天狼星》具有气势磅礡、音韵铿锵、意象丰美、技巧圆熟、声色兼备、将抽象概念具象化等优点。然而显而易见的情节与人物刻画使得主题太过强调、语言明白如话,而诗意稀薄。洛夫以细部诗行举证,切中《天狼星》的要害。余光中以《再见,虚无!》一文响应洛夫,以决绝的语调把讨论的焦点从作品本身转到现代主义的弊病,再转到洛夫写诗的偏执上。余光中在文末为《再见,虚无!》点题,以回归中国传统文学与唾弃认知中的现代主义作结。⑦
当年喧腾一时的公案,今天我们如此审视:洛夫的《论余光中的“天狼星”》并未批评《天狼星》“虚无”,如此一来,“再见,虚无!”的“虚无”,在题意上具备了转义与借代的作用。做为“再见”的受词,“虚无”若非指向论战的对手;就是把对手的话当作提醒或警示,指向自己可能或已然的写作历程。假如天狼星论战果真加速余光中回归中国文学传统,而有新古典主义时期的代表诗集《莲的联想》,则其影响只是一时;因为余光中很快创作了艺术评价远高于《莲的联想》、而手法仍偏向现代主义的《敲打乐》和《在冷战的年代》。撇除意气之争及术语上的精确性,《论余光中的“天狼星”》在洛夫的诗论中份量极重,其抽丝剥茧、犀利而精到的阅读,在1960年代的诗人中,是很难得的不凭借理论或学院派而深入诗核的评论。然而即使该文以缜密的观察及褒贬兼备的行文方式,对余光中首次且唯一以626行的组诗结构而成的《天狼星》予以痛击,仍无法抹煞《天狼星》在台湾现代诗史上,无论开创性或美学贡献的位阶。
回到当时这两篇文章引起的回响,余光中的《再见,虚无!》更胜一筹。《再见,虚无!》行文的语气更具煽动性,题目的挥别姿态做足,文辞的心理暗示造成的定锚效果铿锵有力;不像洛夫《论余光中的“天狼星”》一鼓作气钻到对方的文本里,而不在气势或修辞上耍弄。当时台湾的文学环境,虽然即将在1970年代提倡“精读细品”,现在看起来,洛夫的脚步毕竟超前了10年。在余光中的创作历程中,“新古典主义时期”唯一的一本诗集:《莲的联想》才是“麻疹”。《再见,虚无!》一文中所谓的“现代主义的滚滚浊流”,仍然牵引余光中跨越古典与浪漫的过渡时期,步向诗艺的高峰。
1972年,颜元叔发表了《细读洛夫的两首诗》《罗门的死亡诗》《叶维廉的“定向迭景”》等三篇文章,引起洛夫、罗门与其他诗人、学者的响应。⑧颜元叔发表系列的诗作细读文章,用意在对实际的诗作阐释,把新批评的观念与操作方法演示给台湾的现代诗评论界,强调从作品的前后文寻找诗的意义与艺术性,即所谓脉络阅读;但由此而引发关于新诗阅读与诠释的论争。⑨其中,《细读洛夫的两首诗》讨论了《手术台上的男子》及《太阳手札》二诗,肯定洛夫意象语之丰富、奇特与魄力,而质疑内在结构与外在世界的连贯性。颜元叔以“结构崩溃”批评《手术台上的男子》:“手掌推向下午三点钟的位置”的必然性,以及“十九级上升的梯子/十九只奋飞的翅膀/十九双怒目/十九次举枪”的“十九”,为运用自动语言而有凑合之嫌。其后,洛夫《与颜元叔谈诗的结构与批评》提出“情感结构”响应颜元叔的“有机结构”,再以“用抽象语表示普遍状况,以夸张语强调艺术效果”响应颜元叔对《太阳手札》和《手术台上的男子》二诗的意见。从洛夫的文章,可看出颜元叔以新批评从事新诗研究时的局限:对结构与意象的认知过于机械化而导致误读。意象与结构的关系并不遵循既定的规则,而生发在随诗行进行中的语境。
1970年代之前的这类精读批评,在台湾诗界立下典范。类似洛夫与余光中因《天狼星》、或洛夫与颜元叔因《手术台上的男子》而起的笔战,两造都针对同一诗作展开论述,再扩及自己或社会氛围、文化环境、时代潮流等周边议题,即使两方观点不一,或某方论证有问题、部分误读,基本上都极其恳切,也不太借重理论使自己的论调“黄袍加身”。它们展现的评论风范是:对文学现象的最适切评论,应该就诗论诗,就文论文,以提出希望与全面阅读取代笃定的断语,避免误读误解、左支右绌、前后矛盾,力戒混淆、栽赃、歪曲事实。另外,这两个例子警示我们:当被框定的人还活着,负面批评将毒化评论者和被评论者之间的关系。负面的精读评论可能使被框定的对象“起义”,也写一篇文章响应,于是两者交锋。
基于框架论述的定音作用,处理现当代诗而加以定位时,应特别留意:其一,对发展中、变异中的现象不宜骤下断语;其二,评论者应善用标签效应的印象管理,维护创作发展。
四、权力与思维的轨迹
当代文学评论中,握笔的那只手容易让人联想到“春秋大义”,或笔或削,造神、造鬼,影影绰绰地来回浮动各种魅影,格外使人难以置身其外。杨宗翰提及现代诗评论中数据处理的纠葛困境,曾举周策纵的“双重传统”“多元文学中心”为参酌[7]。出于被评论的物件与评论者的时空距离近,“多元”“多方”“多重”的评论视角似乎可以解决难题,事实并不。“多”,还是有角度的问题:例如是从中心向外放射?还是从各方向中心辐辏?如果是前者,权力论述的主轴还是稳定存在,而且向外放射的被评论对象依然有良莠强弱之分,论者的诠释架构无法八面玲珑;而如果论述的角度是从不同文本与作者,四面八方向论述中心辐辏,那么被评论者更显得只是论点的例子,所谓“文本的自足价值”难以凸显,做为例子的文本越显得可有可无。
在现当代诗研究的各种论述中,“史”的背后经常涌动着权力的痕迹。李陀说过:“文学史是任何一种文学秩序最权威的设计师和保护神。”[8]只要文学史出于一人之手,话语权的印痕就越明显。虽然徘徊在文学史外围、对文学史撰述有所期待的专业论述恒常冠冕堂皇:例如“全景式的写法”“地景式的写法”“谱牒簿录式的写法”“传记式写法”“学术辩证式的写法”“文本中心的写法”“多元并存的写法”等等。
当代诗史、史论及相关研究以台湾海峡两岸的学者为主,但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对于当代诗史的关注与研究呈现方式不同:以史为书名的现代诗研究专著集中在中国大陆;而台湾则以较大规模、群策群力的论著编纂,或个别学者不外乎史论动机的专论,暂代酝酿久之的台湾现当代诗史。
概略估计,大陆学者编著,各种冠以台湾、中国、香港等等,或全面系统,或专题性质的现当代汉诗史著,将近二十种⑩。相对于此,台湾的当代诗史著作显得相当沉寂[11];然而不论是台湾文学馆启动于1990年的《台湾文学年鉴》[12]、以研究生学位论文为主力的系列台湾研究丛书[13],还是因学术研讨会而产生的史论式著作、以文体融入台湾文学史中的一部分[14]、作家资料汇编[15],抑或围绕在台湾现当代诗史相关议题的周边文献,台湾学界聚焦在以台湾为核心的当代诗史研究,文献以人文建设的样态存在,已经非常多。
诗史撰述经常遇到的“国族定位”或“意识形态”,一直是学者谈论台湾现当代诗史书写的重要考虑,然而文学与政治因此陷入的漩涡,以及论者出于理想性与政治理念而产生的论述制约,却也是我们必须警惕的。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以“民族文学史大叙述”为根柢,建立强调台湾主体性的台湾文学史;陈芳明引用后殖民论述,做为撰述《台湾文学史》的中心史观;王德威则提出后遗民论述,做为对陈芳明后殖民论述的反动[16]。以“后殖民史观”“后遗民史观”“世界版图想象”为背景而撰写的三种现当代文学史,提供我们观察定向论述的思维脉络如何开展、材料如何使用。
2004年,王德威的《后遗民写作》首次发表,讨论了台湾现当代文学的身份认同与国族想象[9]。“末世”是观察“后遗民”史观的关键词。以后遗民的观点,王德威勾勒了从晚明以降,以遗民与移民为主轴的创作谱系。王德威运用中国文字的歧义性解释“后”和“遗民”,说“后遗民”的“后”暗示一个时代的完了,也可暗示一个时代的完而不了;而“遗民”相容了“失”“残”“传”三种仿佛互相悖离却又互相对话的意涵。于是“后遗民”以既相背又相连的语词嘲弄了“新兴的本邦”,主要用来讨论当代汉语创作以记忆及时间为核心的国族论述[9]。“后遗民”观念是王德威对“想象共同体”的发挥。在集结成专书的《后遗民写作》中,王德威以“后遗民”史观讨论了姜贵、舞鹤、郭松棻、朱西宁、白先勇、张爱玲、陈映真、苏伟贞、朱天心、贾平凹、李永平、骆以军等当代汉语小说家的作品。“后遗民”一词成为术语,以相当的历史意识、文学底蕴、政治内涵,刺激出许多相关研究。蔡建鑫认为,以遗民做为“忠”的隐喻,则在世变下的文学场域里,后遗民不单是初始想法中的身份,更是一种批判视野,它提醒读者留意“遗民”所喻示的忠贞观念的变形,而以“与时俱进”“开放包容”做为一贯的信念。[10]
作为台湾现当代文学史观,“后遗民”和“后殖民”对阵;做为1987年解严后的台湾文学的思潮主力,“后殖民”和“后现代”各据一方[17]。陈芳明撰写《台湾新文学史》之前,多次撰文表述自己的后殖民史观[18]。“后殖民”是陈芳明书写台湾文学史的一贯史观、一贯的方法论;最近陈芳明更以“殖民地现代性”阐述作家的风格,讨论“殖民地文学”的样貌[11]。“后殖民”的“后”,在陈芳明的文章中,表现为“抵抗”与“之后”的意思。“后殖民”是“殖民之后”“抵抗殖民”,在阅读扎伊尔德《东方主义》的震撼下,陈芳明反思以“后殖民”寻找台湾文学的发言位置。陈芳明认为,台湾文学“绝对是属于第三世界的文学”[12]。用“后殖民”的观点,陈芳明诠释了以日据时期为主的诗人及左翼文学家,如杨逵、王白渊、张文环、吕赫若、吴新荣、郭水潭、杨炽昌等等。陈芳明并以“后结构”搭配“后殖民”,以为解释台湾文学的利器。“后结构”的文学思考主要阐释了台湾在1987年解严之后的文学现象与作品,如同志文学、女性文学、眷村文学、原住民文学。在“后学”大兴的1980年代以降台湾文学界,“后殖民”的传播效应与声势似乎大于“后遗民”。[19]
2017年,由王德威主编、哈佛大学出版的英文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王德威在王晓伟翻成中文的序文中,说明该书的史观、旨趣与内容。这本《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英文版,由143位作者、161篇每篇约2000字左右的文章构成,共1060页。时间起自公元1635年明末杨廷筠等,至2066年在韩松笔下“火星照耀美国”的科幻时代;空间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马华、南洋文学。每篇文章的写法,包含一个引题或引语,再下接正题。每篇文章只写一个时间点、讲一件事。王晓伟中译的王德威文章里说,这161个不同的时间点汇成一张“星座图”:包含了文学现象、事件、“出格”的“文”体——例如电影、歌词、演讲词、政府协议、狱中札记。于是《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由时空的“互缘共构”、文化的“穿流交错”“文”与媒介衍生、文学与地理版图想象等四个主题,描述了编者心中:“世界中”的中国文学。[13]
从王德威的序文,得知其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大的特色是“跨”:跨时间、跨地域、跨国族、跨文化、跨文类、跨语系。大幅度、各方面的“跨”,让我们更留意这部现代文学史自我命名的布线方式:“草蛇灰线”[13]。以“草蛇灰线”取代通常文学史必备的纲举目张,用以比喻多处暗藏伏笔的史观,迥异于现当代文学史家以明确直陈的观点挺出自己的方式,因而挑战了汉语文学史生态对于面面俱到的成规。编者期望丰富却不求全、以等待增删填补的千头万绪串联文学面貌、以五花八门的各种文本与现象呈现“史”与“文”的观察叙述,实践心中的文学性。[20]令读者好奇的是:这样的“跨”,如何来区辨这部文学史与诸多孜孜矻矻血汗凝成的“资料汇编”之别?《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年条录法,加上王德威在序文中的说法,更曝显文学史的权力论述。另一层的反思便是:一部文学史岂能仅止于异口异声的材料仓库?文学史,即使材料再不全,也需要撰史者从史学、史才、史料全面撑起,为读者点亮明灯。虽然以“后殖民”的观念阐释台湾现当代文学,与“后遗民”“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类似,可视为各种创作或评论背后无中生有的动力。
尽管这些著称的史观各自旗正飘飘,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却未必脉络化到文学史最核心的文本中。《台湾新文学史》的“后殖民”史观,在论述日据时期文学时内化得自然浑成,然而在论述其他时期的文学时,“后殖民”显得存而不论。“后遗民”在王德威大开大阖的小说研究里,也不具备支配性的力量。例如陈芳明的著作中,屡次撰文致意、多次讨论的余光中、杨牧,用的切入点都不是他在《台湾新文学史》被视为代表史观的“后殖民”,而是美感或主题。是不是文学作品有自行命名的欲望?还是,这个那个的各种术语,或者理论,正是巧扮过的“主题”,而这些权力与思维的轨迹,印证的最终仍是文字不等于真理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它们存在的目的,并非挑战文学史的实存,而是透过不断的重读,保持探索新知以及反省历史的眼光?
五、文本阅读与理论运用
中国文学注重感性的抒发。一篇文学评论或一首诗作,即使徒具饱和的感性而缺乏演绎与思辩的能力,仍然可以很讨喜。文学评论本具有相当的主观性,相同事实、相同文本,透过不同的论者,可能呈现迥异的见解,这时,如果不具体扎根在文本解读上,文学评论的相对公允程度必然遭到质疑。
阅读现当代诗评,最动人的言语经常不是什么论、什么派,而是透过文本精读与阐释之后,闪耀出论述者个人性情与胸襟的文字。这些吉光片羽偶尔会闪电一般划过脑海,诱使我们重读或翻找这位评论者的其他作品。如郭枫说:“牺牲晚年有限的珍贵时日,来写这部新诗史论,对我的创作理想而言其实是很大的侵害。”古添洪说:“桓夫诗底唯美、喻况、若即若离的质量,无法使其走入‘走向文学’的格局,而只能成为‘泛’政治诗。”简政珍说:“对于任何严肃的作家称呼某种‘主义者’都可能是一种侮辱。‘主义’或‘主义者’像产品标示,评者以‘主义’标示作家,意谓他无力洞察个别作家作品里的纤细繁复,将其归于‘大一统’,分门别类以便记忆。”[21]
文学评论者面对不同评论对象或文本,自然会运用不同的术语以彰显论述效果。很多时候,我们在文学评论的学术文章里,看到作者借重某个理论分析或解释其论述。学者运用哪个“理论”,代表他认为那个化约了的思想片段可以佐证他要定名的对象。
“理论”在一篇文学评论中表现的,与其说是这位学者的学养,不如说更是他的态度。“理论”适度缓解了论述者的言说焦虑;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理论”凸显了论述者的言说焦虑。
评论者面对庞杂的数据,经常需要找一个术语让自己的言说显影。那个术语有时是自己美学认知或文学经验的创见,而很多时候来自别人的思想片段。假如一个术语或思想片段越滚越大,以致被抽离思想成形的语境与时空,进而单薄、简化,成为空洞的躯壳,这时“套用理论”便经常以自欺欺人之姿,凌空而至。
“运用理论”不同于“套用理论”。其别主要在于“理论”是否内化于文本,是否和等待诠释的作家或文本融合无间,突出文本或作家的特质。如果是,叫做运用理论;否则即为套用、扣帽子。
术语或理论的作用应该是文本诠释的源头活水,而不是文学买办者的超额消费。拿术语或理论来扣帽子而不深入文本,就好像方便面,简便、口味重、热量高、没营养;一个文学研究者假如罔顾应该被仔细论述的文本,套用各种术语、替别人扣帽子而乐此不疲,则让人联想到《孟子·离娄下》“齐人骄其妻妾”的典故。
理论运用所以“自欺欺人”,关键在于论述者对于该理论了解不足,理论和被评论的文本之间扣合牵强,因而理论被曲解,文本被有意扭曲。当理论的运用不构成熟或内化,就变成干燥的套用;层层的套用与评论里,彰显的往往是隐匿在论文背后的研究对话,而不是文本本身,甚至文本变成研究的附属。在此情况下,诠释一首诗可能变成谋杀一首诗。遗憾的是,至少在台湾学界的期刊学术论文产出模式中,“是不是运用理论”经常在审查过程里被视为等于“有没有研究方法”,假如一篇投稿学术期刊的论文未标明“理论”或冠上一个漂亮的术语,而只是“细读文本”,不但不被采用,还可能被审查人说成学术水平低落──尽管可能读得很有见地。
术语、理论或主义之于文本,本来是辅助的关系,之所以被简化为某段时空文学风潮的总和,一个因素常是对主客观环境理解之异与数据取得难易之别,使得论述者对于自己熟悉的时空反而谨慎着墨,而对于稍远的评论范畴却“信手拈来”。这是一种善巧方便的文学教育方式,无可厚非。例如在台湾学界的共识里,1950年代的台湾是“反共文学”,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文学”,1980年代是“乡土文学”;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在讨论第三代诗歌时,选择以政治、社会等背景与诗界内部的代谢状态,呈现诗史的板块运动,完全不提及西方理论或主义的影响;而在讨论台湾现代诗史的时候,则与台湾对当代文学的教育模式一样,以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对台湾诗界的影响[14]。术语、理论或主义喧宾夺主的另一个因素,也或许出于:当评论者发现自己的论述方向、诠释策略和被评论的对象不一致,甚至材料溢出自己的论定方向时,仍旧视而不见,挥戈为之。一旦如此,这样的定向论述将是当代文学评论很大的遗憾,因为这涉及的是学术诚信。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评论者直接以某某主义将某位作者定位。通常一个创作者不太可能终身只浸淫于某一类主义或思想;倘若只援引被评论对象符合自己评论方向的某一类思想文本,而忽略彰显其他思想的文本,其用心很可议。
文本阅读与理论运用的理想操作,是把“文本”放到“作者”之上,先精读文本,再决定是否用理论、用何种理论去发挥自己看到的文本。在现当代诗的研究中,“文本”先于“作者”时,“诗”顺理成章为论述核心,相关的文学理论、文学观念、文化论述较更内化,语言、意象等“文本”本身的话语命题比“作者”本身更显扬。
六、结 语
框架论述具备“建构”的体质。发展中的现当代汉语诗既在被建构中生成,复在生成中被建构、调整。发展中的现当代汉语诗评论亦如是:一边在文本风格变异、时代风潮所侧重、社会政治文化等外围脉动中左冲右突,一边在纵向的文学史流变和横向的文学理论中找出有新意的表述方式。除了针对文本本身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框架论述充斥着霸权操作的风云变幻,而众多论述其实是各种意识形态交锋的场域。我们这里说的意识形态,不只是政治意识形态而已,文字语言就是意识形态的体现。
面对当代诗的评论或研究成果,我们必须认知:“绝对的边缘”和“清除中心魅影”一样不可能。边缘总是在浮动;客观的定向论述也只是相对于专断评论,在材料上更广博深入、在推论上更周延合理、在学术伦理上更对得起良心。
如何看待当代诗评论的话语权?权力避免不了操弄。经过人为选择、擘画、布局、勾勒的现当代诗评论,在某个层次上,我们必须承认且看开:那些都是戏论,不是真理。它们有局部的事实和大部分的文采、思维、感情的温度,并以之吸引读者,成为人文化成的一部分。大数据之下,谁要怎么说,较诸以往更容易各自招兵买马、各据山头。“谁也不是谁的国王”,1995年的年度诗选序文早就以此为题,何况22年后的今日。此时此刻免不了的“本位”,已经很难一方独霸;聚集许多各自表述的“本位”,则是21世纪现当代诗评论展现“众声喧哗”的方式。因此,在相当程度的政治目的下研究文学,或依据一定的学术理论行使话语宰制权、依照论者个人的美学素养替被评论的诗人做文学史上的定位,这些有所“偏”的表述,是大数据时代正常的评论现象。
在大数据的时代里,我们更需要能带动史料、诠释文本的文学史。纠集众力编成的巨著,如果没有一以贯之的论述姿态,也能叫做“史”吗?比如说,我们认同《四库全书》是一部中国学术史吗?如今有许多电子数据库,大抵都会有收录数据的说明,比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它能叫做中国史吗?我们可以换个角度说,“学案”“百科全书”“作家数据汇编”,以及某些大部头、集合专业领域人士编成的系列论述丛刊,隐含了“史”的企图。
在大数据的时代里,学者对当代文学史撰述的建议,如:对同一现象采取多重相对的观点,以开放、收编、视境融合对治撰史者个人视野的局限等等,在如今铺天盖地、掘地三尺的数据环伺下,操作上的困境已与20世纪末大不相同。假如十几年前现当代文学史的撰述者担心文献不足征而难以支撑自己的论点,那么如今的现当带文学史撰述者担心的反而是:因为资料太多,而要耗费更多心力反复阅读、消化、判断、诠释,以防自己有所疏漏而致判断错误。
透过大量的文本细读为论述打底,掌握被评论物件创作历程的生成起灭,以交错与贯串的史观,综合描述、评价、分析诠释各期作品,并留意各种风格形塑的背景,以文本中可靠而未被发现的细节来支撑论述,从而建构凸显“文本性”“文学性”的现当代诗评论,是我们思索、努力的方向。
注释:
① 同参考文献[1]。相关篇章亦可参考如颜元叔:《朝向一个文学理论的建立》,见叶维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选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76年版第281-303页。
② 若据“台湾博硕士论文加值系统”所收数据,输入“现代诗”搜寻“论文名称”“关键词”“摘要”,得449笔;输入“新诗”,搜寻“论文名称”“关键词”“摘要”,得336笔。若据杨宗翰的分期,以作家姓名为检索值,举证台湾学位论文中的部分研究资料,得“萌芽期”之诗人研究8笔、承袭期之诗人研究15笔、锻接期24笔、发展期27笔、回归期56笔、跨越期6笔。
③ 例如陈政彦的博士论文:《跨越时代的青春之歌:五、六○年代台湾现代诗运动》,高雄:台湾文学馆2012年版。
④ 诗僧周梦蝶,诗儒痖弦,诗魔洛夫。
⑤ 参见孟樊:《杜国清的新即物主义论》,收于《当代诗学》,第3期(2007年月),第48-67页;《为现代都市勾绘新画像──林耀德的都市诗学》,《人文中国学报》,第20期,第319-342页;《张汉良的新批评》,《台湾文学学报》,第27期(2015年12月),第1-28页;《简政珍的现象学诗学》,《台湾文学学报》,第30期(2017年6月),第1-26页。
⑥ 例如郭枫评纪弦:“依附政治虚夸张狂”“把纪弦的文章读完,需要很大的忍耐磨练。不只是因为太长的问题,而是因为论文中东拉西扯让人搞不清头绪,一下子钻进死巷,一下子歧路四出,像似急怒攻心般语无伦次。”见郭枫:《诗活动家狼之独步与现代派兴灭》,《新地文学》,2013年夏季号,第7-46页。
⑦ 洛夫:《论余光中的“天狼星”》,收于洛夫:《洛夫诗论选集》,台北:金川出版社1978年版,第191-216页。余光中:《再见,虚无!》,收于余光中:《掌上雨》,台北:大林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164页。
⑧ 其中,《细读洛夫的两首诗》,原发表于《中外文学》,第1卷,第1期(1972),第118-134页。
⑨ 例如唐文标认为颜元叔:“他的‘细读’的评文,不过是用‘新批评法’对一首诗的文字分析,而并非通过批评文字来响应他的社会文学见解。……批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见唐文标:《天国不是我们的》,台北:联经出版社1976年版,第249页。
⑩ 自1989年古继堂的《台湾新诗发展史》之后,大陆学者陆续出版各种现代诗史著作,如周晓风等:《中国当代新诗发展史》(1993),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1993),谢冕:《新世纪的太阳》(1993),王毅:《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1998),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思潮史论》(1999),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1999),刘扬烈:《中国新诗发展史》(2000),李新宇:《中国当代诗歌艺术流变史》(2000),朱光斓:《中国现代诗歌史》(2000),罗振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2002),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2003),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2003),杨四平:《二十世纪中国新诗主潮》(2004),陆耀东:《中国新诗史 1916-1949》(第一卷 2005,第二卷2007),沈用大:《中国新诗史1918-1949》(2007),古远清:《台湾当代新诗史》(2008),张新:《20世纪中国新诗史》(2009),刘春:《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第二部2010,第三部2013),谢冕等:《中国新诗史略》(2011),林贤治:《中国新诗五十年》(2013),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2013)等。
[11] 台湾学者编著,已出版的现代诗史有张双英:《二十世纪台湾新诗史》,台湾文学馆,2012年版。
[12] 《台湾文学年鉴》第一本由文建会在1996年出版,此后每年一本。目前由台湾文学馆负责。
[13] 其中与现当代汉诗研究有关的,如蔡明谚:《燃烧的年代:七○年代台湾文学论争史略》(台湾文学馆,2012年版)、陈政彦:《跨越时代的青春之歌:五、六○年代台湾现代诗运动》(台湾文学馆,2012年版)。
[14] 如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台北:联经出版社,2011年版。
[15] 最大部头的作家资料汇编为台湾文学馆主事的《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目前收编入此套丛书的诗人包括了张我军(许俊雅编选)、周梦蝶(曾进丰编选)、陈千武(阮美慧编选)、林亨泰(吕兴昌编选)、杨唤(须文蔚编选)、赖和(陈建忠编选)、余光中(陈芳明编选)、罗门(陈大为编选)、商禽(林淇瀁编选)、纪弦(编选)。此前在各县市政府推动下亦出版过为数不多的作家资料编整,如《张我军评论集》、《赖和资料汇编》、《林亨泰研究资料汇编》、《杨云萍文书数据汇编目录》;又如1993年中央图书馆规划策立“当代文学史料影像全文系统”的数字数据活化、1988年由前卫出版社规划的《台湾作家全集》等等,皆保存、记录了台湾作家的作品与文献。
[16] 针对这三种意识形态,研究者阅读、比较,提出“容许差异、避免全称的文化认知”的建议,值得参酌。参见陈逸凡:《神谕或鬼辩:台湾文学史书写中的差异叙事》,高雄: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10年。
[17] 陈大为认为,1980年代以后的台湾文学界,明显陷入后现代的阴影,且迅速形成以“主义”为文学史断代的共识。如罗青、廖咸浩等学者,将1980年代以降的台湾定义为后现代时期;而陈芳明、邱贵芬等学者则倾向于后殖民时期。见陈大为:《中国当代诗史的后现代论述》,《国文学报》,第43期(2008年6月),第177-198页。
[18] 例如《我的后殖民立场》、《后现代或后殖民──战后台湾文学史的一个解释》等文;后来与其他文章集结为专著:《后殖民台湾:文学史论及其周边》,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
[19] 姑以“台湾博硕士论文加值系统”检索结果为例,若在“摘要”、“关键词”、“论文名称”输入“后殖民”,可得博硕士论文719笔;同样的查询条件,若输入“后遗民”,可得博硕士论文13笔。但细部内容仍须验证。
[20] 参见序文所说的,比如:“文学定义的变化是中国现代性最明显的表征之一”“有容乃大”“中国历史的建构不仅是‘承先启后’的内烁过程,也总铭记与他者──不论是内陆的或是海外的他者──的互动经验”等等。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第31期(2017年6月),第1-26页。
[21] 分别见郭枫:《我为什么写〈台湾当代新诗史论〉》,《新地文学》,2013年秋季号,第142-148页;古添洪:《论桓夫的‘泛’政治诗》,收于孟樊主编:《当代台湾文学评论大系·新诗批评》,台北:正中书局,1993,第293-336页;简政珍:《洛夫作品的意象世界》,收于简政珍:《诗的瞬间狂喜》,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1,第221-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