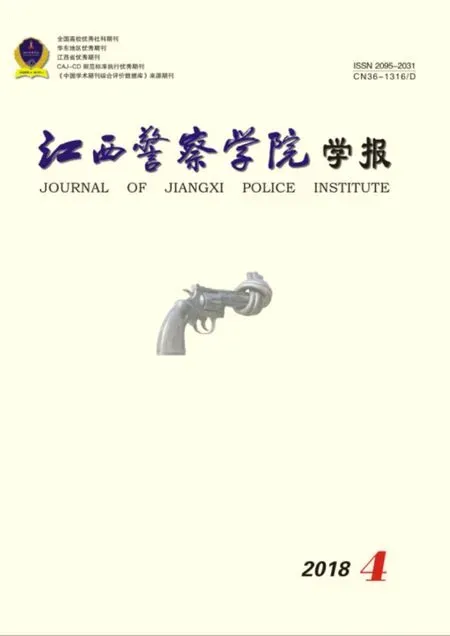内幕交易罪的司法认定问题探究
——以内幕知情人和内幕信息为视角
胡倩玉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更好地研究内幕交易罪的情况,笔者将北大法宝、中国裁判文书网、无讼案例数据库中近十年的有关内幕交易罪的判决书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仔细研究每一份判决书,将比较典型的案例提取出来进行梳理,发现内幕交易案件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内幕交易主体的认定,即内幕知情人的认定问题。譬如在余某某内幕交易案①参见(2014)江开法刑初字第546号。中,余某某是在办理业务过程中,无意看到了后期被认定为内幕信息的资料,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并没有主动刺探相关内幕信息,也就是说并没有利用 “非法获取”的手段,所以不能认定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而法院最后却认定被告人利用窃取、刺探等非法手段获取内幕信息,其行为构成内幕交易罪。本案的争议点在于,利用“无意看到”这种中性行为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能否被认定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即:如何理解“非法获取”。第二,内幕信息的认定问题。譬如在宋某某内幕交易案②参见(2017)鲁05刑初3号。中,辩护人认为吉艾科技筹划收购多斯托克炼油厂的信息只是一个虚假理由,不属于内幕信息,而法院认为该信息符合内幕信息的两大特征,即重要性和非公开性,所以应当认定为内幕信息。另外,在内幕信息敏感期的界定上,也存在意见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起始时间的确定上。辩护人认为内幕信息的敏感期应自收购多斯托克炼油厂方案形成之时开始计算,而法院认为在6月4日申请签证决定赴哈萨克斯坦考察多斯托克炼油厂时,为动议、筹划的初始时间,也即敏感期的起始时间。本文将主要就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展开讨论,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争议问题进行分析,并结合理论界学者的观点,厘清内幕交易罪认定过程中的争议问题。
二、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认定问题辨析
立法上禁止内幕交易、泄漏内幕信息行为,实质意义上是为了禁止那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通过某些方式取得内幕信息并加以利用,以使自己获得利益或者减少损失的行为。[1]345在我国金融领域迅猛发展的同时,证券、期货类犯罪数量明显增加,为了应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立法也在不断完善。除了《刑法》、《证券法》中的相关规定外,还有相继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中国证监会也陆续出台司法文件严厉打击内幕交易。尽管如此,司法实践却没能与立法做好衔接,由于司法人员对相关规定的理解不尽统一,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于具体情况的定性和处理也不相同。
我国《刑法》第180条①《刑法》第180条的规定,内幕交易罪的主体为:“证券、期货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的人员。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笼统地对内幕交易罪的主体作了一个规定,2012年3月两高出台了 《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内幕知情人员、非法获取内幕交易信息人员、内幕信息敏感期等一系列问题都作出了规定②明确了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包括《证券法》74条规定的人员和《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81条第12项规定的人员。对 “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规定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人员。然而条文中的规定并不能明确地指向某三类特定的人群,并且对于以中性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应该如何认定,无法从条文中得知。由于法律规范的规定存在空白地带,导致理论界、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意见的分歧。在公布的法律裁判文书中,以犯罪主体的认定为争议焦点的数量颇多,在比较有名的“杭萧钢构案”中,被告人陈玉兴在与杭萧钢构公司工作人员喝茶聚会时得知了内幕信息,对于得知消息是喝茶聚会之时“偶然听闻”,这种“被动的听到”是否能归为“非法获取”?陈玉兴是否能被定性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同样地,在上文中提到的余某某内幕交易案中,余某某是无意间看到的,能不能认定为“非法获取”?这些问题都涉及“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的认定问题。
通说认为,内幕交易罪的主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内幕信息知情人”;另一类是“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对于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法律规定较为明确,被认为是法律规定的有权知道内幕信息的人员,属于法定的特殊身份犯;对于第二类“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因为我国的法律法规并没有进行明文列举,而只是在《解释》中列举了几种类型,所以在理论界存在较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只包括利用非法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人,比如利用骗取、套取、偷听、监听等方式获取。[2]另有观点认为,“非法获取”应该理解为不应当获得而获得,对于“非法获得”作宽泛理解和解释,即只要是最后获知了不该知道的内幕信息,无论非内幕信息知情人获取信息的手段和方式如何,都属于非法获取。[1]349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不属于《证券法》第 74条规定的人员知道了内幕信息,无论是通过何种途径获得,都应被认定为“非法”。
笔者认同第二个观点。对于“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的理解,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很多理论界的学说争议都是因为各自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有所不同,那么到底应该从哪个角度来论证,对正确认定犯罪主体也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内幕交易罪是在经济不断发展的时期,为了证券、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和市场的公平交易。市场能够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运行和发展,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市场交易者的权益,证券、期货交易才可以有效运转。有观点认为,想要成为内幕交易罪的主体,必须有禁止内幕交易行为的义务来源,而“非法获取内幕交易人员”禁止交易的义务来源是之前的违法获取信息的行为。[3]此观点从义务来源这个角度分析,得出“非法获取”只能理解为用不合法的手段来获得相关信息的行为,笔者并不赞同这一说法,因为获取信息的手段违法,并不是这个罪名关注的重点,我们所关注的是行为人将得到的内幕信息加以利用,从而导致自己获利或者他人利益受损,至于如何得到的内幕信息并没有那么重要。退一步讲,即使获取内幕信息的手段不具有合法性,如果获得信息的人员并没有加以利用,也不能构成此罪名。我们认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应该不仅仅局限于以不合法的方式获知内幕信息的人员,而应该包括所有的不应该知道而知道内幕信息的人员。因为只要这些人员知道了内幕信息,哪怕是被动的、偶然听到的,看似是很正常的行为获知的内幕信息,但若允许他们进行与该内幕信息相关的市场交易行为,势必会对其他没有相关信息的人产生不公平的影响。所以,通过中性行为获得相关内幕信息的行为,也应该被纳入到“非法获取”的范围中。所以,在余某某内幕交易案中,虽然被告人只是无意中看见了相关内幕信息,但是由于余某某不是应该知道该信息的内幕知情人,其已经运用之前无意获得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并且这个行为使其获得了一定的利益,显然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公平。故虽然其获取手段不具有违法性,却要认定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
三、内幕信息的认定问题辨析
在证券、期货交易市场,信息对于每个参与交易的人来说都极其重要,能够先一步获取内幕信息,就能在交易市场中胜出,获得竞争优势。因此在这些好处和诱惑的驱使下,很容易出现内幕交易这种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具体涉案的信息能否成为内幕信息,一度成为认定此罪的关键因素。所以,弄清楚内幕信息的认定标准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确定了标准,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内幕信息。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确定涉案信息为内幕信息,一直都是此类案件的重点和难点。在整理的近十年的典型案例中,关于内幕信息认定的主要争议点出现在内幕信息敏感期的确定,即到底哪个时间段的信息才称得上是内幕信息和内幕信息内容的确定,即符合了哪些标准的信息才是内幕信息。例如,在上海祖龙案①参见(2009)厦刑初字第109号。中,辩护律师认为被告人陈某某作为创兴科技的实际控制人和上海振龙公司的董事长,计划将其控制的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其向专业人士进行咨询,并做可行性分析、计划,具有不确定性,不属于内幕信息,但是法院最后并没有采纳此辩护意见。在蔡某内幕交易案②参见(2015)中二法刑二初字第243号。中,辩护意见称,某B股份停牌前期间不应成为交易敏感期,因为某B股份重组信息不构成内幕信息。而法院认为,2011年11月3日某B股份与某C投资商谈,达成收购重组意向,此时间点即为内幕信息的形成时间。下文将主要围绕以上争议点展开讨论。
(一)我国关于内幕信息立法的规范分析
《证券法》第75条,对“内幕信息”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第一款明确了内幕信息的定义,第二款列举了8条具体的内幕信息;第67条第二款列举了12条重大事件。2012年两高出台《解释》之前,并没有关于内幕信息敏感期的规定,直至《解释》的出台,将内幕信息敏感期的具体内容加以明确规定,填补了司法实践中内幕信息敏感期认定的空白。这么看来,我国立法似乎对内幕信息的认定已经有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但是,证券内幕信息不是单纯的静态内容,而是一个从信息萌芽、发展、形成、持续影响证券交易价格直至最后公开的动态过程。[4]所以,要想准确认定内幕信息,就要重点把握内幕信息的特征,对于内幕信息从萌芽到最后公开过程中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的把握也尤为重要。
(二)内幕信息的认定标准
从上述关于内幕信息的法律规范来看,内幕信息主要有两个特征:第一,“足以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交易量”即重大性,是内幕信息的本质特征;第二,“尚未公开的信息”即秘密性,则是内幕信息的形式特征。对于内幕信息的特征,各学者的观点之间虽然大致相同,但是却有不同的分类标准。有学者认为内幕信息有三个特征,除了以上两个特征外,还有相关性,即该信息与证券发行及证券、期货交易等活动相关联,从法律条文中看,并未对真实性或确定性提出要求。也有学者赞同四个特征:一是尚未公开的信息;二是真实、准确的信息;三是与证券、期货有关的信息;四是对交易市场价格波动起到一定影响的信息。[5]针对以上几种学说,结合法律相关规定和本罪设置的意图综合考量,笔者认为,内幕信息满足三个特征即可,即未公开性、重大性和确切性。
1.未公开性
未公开性也称秘密性,是内幕信息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之所以叫“内幕”信息,就因为该信息具有秘密性,不可随意被人知晓。内幕信息保护的是一种知情权,相关证券、期货市场交易的信息在未公开前,只有少数内幕知情人员知晓这部分内容,这样其他市场交易者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信息一旦被公开,就从幕后变成了公开,所有人都知晓了此信息,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此时,任何人都可以加以利用,而不受法律的禁止。因此,内幕信息是否已经被公开,是判断该信息是否为内幕信息的一个关键,也是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此罪的关键。我国 《证券法》第70条③《证券法》第70条:“依法必须披露的信息,应当在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媒体发布,同时将其置备于公司住所、证券交易所,供社会公众查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试行)》第11条④《证券法》第70条:“依法必须披露的信息,应当在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媒体发布,同时将其置备于公司住所、证券交易所,供社会公众查阅。”,还有两高出台的《解释》⑤《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内幕信息的公开,是指内幕信息在国务院证券、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报刊、网站等媒体披露。”都对内幕信息的公开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关于信息公开,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形式公开和实质公开。从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可以知道,我们国家采取的是形式公开的单一标准。我国实践中判断内幕信息已公开的标准主要有三个:一是在全国性的新闻媒体上公布该信息;二是通过新闻发布会公布信息;三是市场消化了该信息且已作出反应。[6]与此不同的是,在西方国家,存在着一种“有效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某项消息一旦被相当数量的投资者知悉,相关公司的证券、期货价格便会很快地发生变动,或涨或跌,从而来反映证券、期货公司对市场这种消息的感受与反应。也就是说,该理论以实际发生了影响价格变动的结果为判断标准,认定信息是否被公开。此种信息公开的方式即为实质公开。我国有部分学者就比较偏向于实质公开的标准,认为信息从公布到被人们接收,再到消化吸收,不是一瞬间就能完成的事情,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从市场交易者接触到相关信息,慢慢地开始接受信息,并利用信息,从而引起交易市场价格变动的这段时间,都应该是未公开时段。笔者认为,我国的形式公开是有一定弊端的。在内幕信息被公众获知之前,提前掌握内幕信息的人已经了解并消化了相关的内幕信息,在内幕信息正式公开之时,他们已经完全可以在第一时间利用自己已经熟知并分析过的信息来达到相应的目的,而其他交易者才刚开始接收到相关信息,对信息的消化和理解还需要一段时间,也就是说,信息公布的时候,就有人赢在了起跑线上。此时如果允许早就知晓内幕信息的人员利用信息进行交易,很明显对其他人来说是不公平的,这样也背离了当初制定内幕交易罪的初衷。所以,在立法上,应该规定信息公布后的一段时间为等待期,在此期间内,提前获知内幕信息的人员不允许进行与该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交易。
在内幕信息未公开之前,有一段秘密的时间,即在内幕信息形成之日起至内幕信息的公开,这个时间段被称为内幕信息敏感期。只有在敏感期内的信息才能称得上内幕信息,一旦信息被公开,此信息就不再是内幕信息,行为人再加以利用的时候,也不再构成内幕交易犯罪。在《解释》中,规定了一种特殊情况:影响内幕信息形成的动议、筹划、决策或者执行人员,其动议、筹划、决策或者执行初始时间,应当认定为内幕信息的形成之时。所以,在上文中提到的宋某某内幕交易罪案中,马某岳负责为项目中的塔石油寻找油源,实际参与和从事收购的考察和谈判工作,并且参与了最后合作意向书的签订工作,这些行为足以认定马某岳为该内幕信息的 “筹划、执行人员”,其决定赴哈萨克斯坦考察多斯托克炼油厂时,属于动议、策划的初始时间,此时内幕信息形成。
2.重大性
重大性是指内幕信息对证券、期货市场投资者的决策或证券、期货交易的市场价格影响很大。如果某一信息并不能对证券、期货市场的价格产生重大影响,那么也就不会给投资者和交易市场产生影响,进而造成社会危害。我们内幕交易罪不需要规制这些没有影响性的信息,只需要规制那些会对对市场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证券法》第75条规定了内幕信息是对证券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第67条通过列举的方式规定了12项重大事件的表现形式。《指引》第9条规定,如果信息公开后证券市场价格严重偏离于相关指数,那么该信息具有重大性。从以上的法律条文中可以得知,我国采取了价格敏感性这一标准,即内幕信息必须以重大影响实际发生为必要条件。
但是,由于内幕信息的影响力并不能在第一时间作出回应,导致价格敏感性的滞后性,如果仅仅以价格敏感性作为认定重大性的标准有些欠妥。此外,内幕信息在形成之时,会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素在里面,并不意味着今后一定会按照信息的指向发展,有些信息可能在之后没有产生作为内幕信息所需要具有的影响力,但是这些信息的内容发生可能性极大,随时都有对相关市场交易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所以不管最后这种影响是不是能够真实发生,都应该做好提前预防。与此相对应的认定标准是理性投资者标准,有学者认为,内幕信息必须是能够影响交易者进行市场交易判断的信息。如果内幕信息不能对投资者买进或者卖出证券产生影响,那么该信息就不会对市场造成影响,也不会为行为人带来利益。[7]理性投资者的认定标准是以主观标准去判断的,认为应该以重大影响的实际发生为准,这种标准虽然在实质上能更大限度维护公平交易,但是在我国现有的司法水平上,还是很难实际把握和操作的。笔者认为,可以充分利用两个标准的有利方面,以价格敏感性为主要认定标准,辅以理性投资者标准。这样既能在形式上容易把握,又兼顾到实质的交易公平。
3.确切性
虽然我国刑法规定中并没有对内幕信息确切性的相关规定,但是笔者认为,在司法认定中,确切性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特征。在谢某某内幕交易案①参见(2011)浦刑初字第2738号。中,辩护意见认为,内幕信息应当具有确切性,即应当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或者基本确定会发生的情况,信息的内容也应当是准确、特定和确定的。而法院给出的意见是:内幕信息不必是已经发生或确定会发生的事实,确定性应该包含内容的确定性和作用对象的确定性。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内幕信息确切性特征的理解还是存在一定的争议的。
笔者认为,确切性是一种相对确定的状态,不需要达到最终确定的程度。应该对个案分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对于那些具有极大实现可能性的,已经涉及实质性内容的,可以确定为内幕信息的形成时间;而对那些偶然性因素较大,发生的可能性比较低,没有实际性操作的,不宜看作是内幕信息形成的时间。正如上文提到的上海祖龙案中,两个公司的背后,其实都是同一个人在操控着,由其掌握着整个资产重组过程的进展情况,能够清晰地判断和预测信息的形势。所以,在陈某某找到符合相关要求的中介公司,并进入到项目原本筹划的阶段以后,该注资活动在没有特殊情况下,一定会按照原计划顺利进行,具有很现实的发生可能性,此时内幕信息即已形成,一经发布,必然导致交易市场价格上下浮动。而在上文提到的谢某某案中,信息确定的时间点略有差异。证监会将谢某某促成双方面谈的时间5月12日确定为内幕信息形成的时间,而辩护律师认为,内幕信息形成的时间应为5月18日,即重组方案形成之日。笔者认为,本案和上海祖龙案还存在一定的差异,上海祖龙案属于两公司受控于同一个人,内幕信息比较容易确定下来,所以确定相关信息为内幕信息的时间会比较靠前;但是谢某某案中,谢某某作为中介,牵线两公司借壳上市,两个独立的公司之间进行合作,中间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所以内幕信息确定的时间应该在5月18日,即双方初步达成协议以后形成。总而言之,内幕信息必须具备确切性的特征,但是只要求达到相对确定的状态即可。
四、结语
在金融领域迅猛发展的今天,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已经被社会各界所关注,而内幕交易行为严重影响了证券、期货市场的健康运行。我国自1997年《刑法》规定了内幕交易罪以后,立法上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但是仍有一些问题无法从相关法律规定中得到回应。我们通过仔细研读近十年的判决书,并深入分析理论界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厘清了内幕交易罪中的两个关键争议点,对内幕人员的认定以及内幕信息的确定都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标准。当然,内幕交易犯罪的认定问题最后还需要法律上的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