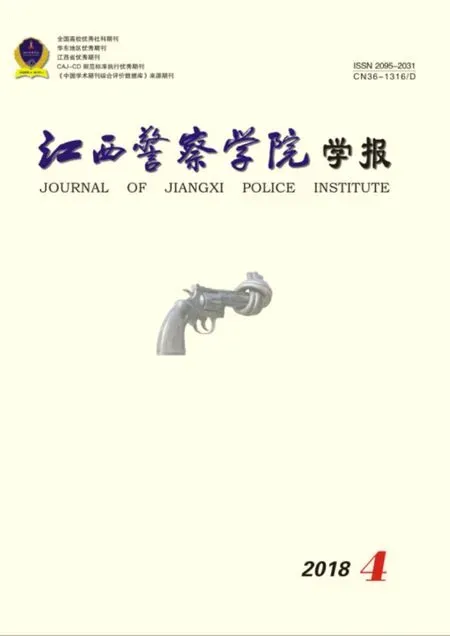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定性研究
——以实行行为为视角
刘 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3)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1:黄安平与黄某(65岁)在桥头边相互辱骂,黄某朝黄安平面部打了一耳光,黄安平遂用拳头击打黄某面部、右胸部,并将黄某往前一推,致黄某的脚绊到地面渔网后仰面倒地,头部嗑碰到地面石块受伤,送至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经法医鉴定,被害人黄某符合外力作用仰面倒地,枕部受力致枕骨骨折,硬脑膜下出血,继发性脑水肿,脑疝形成致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黄安平的殴打、推搡行为一般,被害人的死亡存在突发的介入因素(被推后退被渔网绊倒),此情节应在量刑时予以考虑。黄安平的行为虽然表现为一般的殴打、推搡,但对方是65岁的老人,存在伤害的间接故意。最终,二审法院判处上诉人黄安平故意伤害罪,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①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鄂刑终323号刑事判决书。
案例2:被告人张某甲因琐事与孙某丁发生争执,期间,张某甲用手指戳孙某丁头面部致其受伤,并在孙某丁发病倒地后离开,造成孙某丁死亡。经鉴定,孙某丁符合轻微外伤、情绪激动等因素死亡。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甲实施了轻微暴力,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②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2017)鲁1321刑初25号刑事判决书。
案例3:因吴某挑衅,导致吴某与被告人徐永做发生口角并互相推搡、踢打。其间,被告人徐永做挥手打中吴某胸颈部一下,致吴某倒地且头部后枕部碰撞到地面而死亡。经鉴定:吴某系运动中的头部以后枕部为接触点与静止的钝性物作用致颅脑严重损伤而死亡。终审法院维持原判决,即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徐永做有期徒刑三年。③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51刑终124号刑事裁定书。
近年,上述类型案件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问题,无论在实践中还是理论上都存在极大的争论。其特殊性在于手段轻微而结果重大,二者存在巨大的逻辑反差,一般表现为推搡、踢打、指戳、拳击等轻微手段造成了他人死亡的严重结果,一般将其称为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在司法实践中,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主要有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及意外事件三种不同的处理意见。而刑法理论,基本顺应实践中的三种定性,跳过客观方面的讨论,径直立足在轻微暴力实施者的主观方面,最终往往是分不同的主观类型广泛得出前述三种不同的结论。但是,犯罪成立条件的逻辑性要求客观判断先于主观判断,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的判断同样如此,如果仅讨论其主观方面,则要么直接肯定了该类案件的客观方面要件的存在,要么唯结果而论,忽视了客观构成要件的其他要素,如此,实行行为完全沦为危害结果的附属品,失去了其作为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的存在意义。或可言之,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定性的焦点不仅在轻微暴力实施者的主观认识和意志,更首先在于轻微暴力的实行行为性判断上。实行行为作为基本犯罪客观构成要件的第一要素,是行为构罪的第一道封锁线,必须把好这道关。
二、要义申明:轻微暴力之界定
我国刑法未对轻微暴力作出明确规定,学界也未就该概念的含义达成共识,作为定性的前提,对轻微暴力概念作大致的限定是极其必要的。界定轻微暴力首先必须明确“暴力”一词的基本含义,日本刑法学界对刑法中的暴力的分类值得我们借鉴。日本刑法学界将刑法中的暴力分为最广义的暴力、广义的暴力、狭义的暴力和最狭义的暴力。最广义的暴力,既可以对特定的人实施,也可以对不特定的人实施,既可以对人实施,也可以对物实施,如日本刑法第106条对骚乱罪的规定;[1]广义的暴力必须是以人作为对象,但不要求直接施加在人的身上,[2]如日本刑法中的职务强要罪;狭义的暴力则仅限于对人的身体的有形力,但是不要求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如日本刑法规定的暴行罪;最狭义的暴力,是指足以抑制他人反抗强度的对人的身体施加的有形力,日本刑法第236条规定的强盗罪中的暴力就属于此最狭义的暴力[3]“暴力”一词在我国刑法中也不陌生,如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罪、强迫劳动罪、抢劫罪等等,这些罪名中的“暴力”如日本刑法一样,其在不同的罪刑规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我国学者张明楷接受了上述日本刑法理论对暴力类型的划分,如其指出我国刑法规定的强制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罪中的暴力是最广义的暴力,而抢劫罪的暴力则属于最狭义的暴力。[4]707通过分析不难发现,轻微暴力之“暴力”由于存在“轻微”要素的程度限制,其不可能是最狭义的暴力;由于其存在“致人死亡”的结果要求,不以人为对象的对物的暴力并不能直接致人死亡,其也不可能是最广义的暴力;由于轻微暴力必须是暴力且是轻微的暴力,仅以人为对象但不直接施加在人身上则不足以致人死亡,所以其也不可能是广义的暴力。只有狭义的暴力能够更好地界定轻微暴力的概念。
轻微暴力之“轻微”指称的是行为的暴力程度问题,因此,轻微暴力含义的界定不能忽视对“轻微”的解释。有人依暴力所造成的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将暴力划分为轻微暴力、一般暴力和严重暴力,[5]其认为轻微暴力是指对他人人身未造成任何伤害或者仅仅造成极其轻微的伤害的暴力。有人以行为的手段、方式以及行为人的主观内容,将轻微暴力界定为以非利器为工具、非伤害为故意而对被害人身体实施的较轻有形物理力。且其指出,这种“轻微”是无法达到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6]也有人根据行为的手段、方式和结果严重程度,将轻微暴力界定为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的辱骂、撕扯、推搡等低位暴力行为,[7]且这种暴力行为通常不会造成轻伤以上后果。显然,轻微暴力之“轻微”有结果轻微与手段轻微两种解读进路,本文认为其各有优越性也各存不足。根据第一种观点,实施暴力行为致人轻伤以上结果的就不属于轻微暴力,其回避了手段轻微的事实,有唯结果论的倾向,为本文所不取。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故意与否,并不能改变客观上行为人对被害人身体实施的“较轻有形物理力”的事实特性,主观内容不能决定行为的法益侵害性,本文也不完全赞同第二种观点。综合考量,本文认为第三种观点基本上是合理的,其既考虑了轻微暴力手段的轻微,又未忽略轻微暴力通常的结果的轻微。
综上,本文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从以下方面对轻微暴力作出大致的界定:第一,必须是对他人身体实施的有形物理力;第二,手段必须轻微;第三,一般情况下不足以导致轻伤以上的结果。进言之,轻微暴力就是,对他人身体实施的一般情况下不足以导致轻伤以上结果的有形物理力。不过,日常的社会举止在“正常情况”下是没有危险的,但从这个论断中并不能就推断出,这种社会举止在具体情况下也是没有危险的。[8]因而,一般不足以导致轻伤结果的轻微暴力致死亡结果发生的具体的危险性与可能性需要具体判断。有人根据死亡结果的发生情状,将轻微暴力致人死亡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有实务界论者进行了四种类型的划分,[9]即以危害行为导致死亡结果的原因为切入点,将此类案件大致归为:行为人的轻微暴力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行为人的轻微暴力行为诱发被害人的疾病导致其死亡、行为人的轻微暴力行为与介入因素共同导致被害人死亡以及行为人的轻微暴力行为在被害人行为的介入下导致被害人死亡。本文认为,行为时不同的客观情状,对一般不足致死亡结果的轻微暴力引发死亡结果的危险性或曰可能性的影响不同,有必要对之作不同的类型划分,上述论者的划分基本可取,但是也可以将其整合成以下三种类型:即存在介入因素型、被害人特异体质型、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型。
针对上述三种类型的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笔者目前尚未见到从实行行为的角度对致人死亡的轻微暴力进行研究者。理论上要么仅讨论行为人对死亡结果的预见可能性;要么避而不谈实行行为,直接进行因果关系判断。但是,实行行为具有限定因果关系起点的功能,[10]不确定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因果关系就失去了判断的前提和依据。广义的因果关系判断包括两个步骤:归因与归责,实行行为是归因之事实起点和归责之规范起点。
三、内在构成:实行行为之要素
因果关系判断的第一个步骤是利用条件公式进行事实归因,其表现为存在论意义上的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的条件关联。条件关系表现在“若非P则非Q”的条件公式运用,P与Q之间存在引起与被引起关系。就犯罪的实施进程而言,P是条件关系即事实归因的起点,P和Q分别是作为引起者的实行行为与作为被引起者的结果,实施实行行为而引起犯罪结果。但是,由于条件关系难能对所有条件加以合理区分择取,导致所有条件均属等价且都属于结果的事实原因,因而条件关系在事实因果关系的确定时所起的作用有限。在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上,往往表现为首先根据条件关系对归因范围作出一定的限定,其后在此范围内依据一定的要素确定能够实现结果归因的实行行为。或可言之,条件关系仅有圈定归因的行为范围的作用,之后才进行实行行为的挑选,其顺序基本表现为:结果→条件关系→可归因的实行行为。而且在条件公式的运用中,实行行为P之确定有赖于结合已经发生的结果Q。正如我国学者所言,因果关系中的实行行为,必须也只能从与结果的联系的角度去界定:正是在其与结果之间的内在关联之中,实行行为找到其存在的意义。[11]基于此,作为归因之事实起点的实行行为确定,首先要联系其引起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明确其基本要素。
实行行为要素的确定,第一步便是解释相关法条,明确法律条文对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实行行为的法律要求,究其根本就是实行行为的概念究竟是应当从形式的立场还是实质的立场界定的问题?关于此问题,学界讨论比较充分,而且观点基本明确,即既强调对实行行为概念的形式界定,也注重对其实质侧面的考察。例如,日本学者西原春夫就是从形式侧面和实质侧面两个方面来把握实行行为概念的。[12]大谷实教授指出,确定实行行为,靠是否符合构成要件来决定,……仅在形式上满足构成要件要素还不够,还必须具有实施该行为的话,通常就能引起该构成要件所预定的法益侵害结果程度类型的危险。[13]大塚仁教授在论及实行行为时,也认为该实行行为需要满足构成要件性定型,同时具有引起所定的犯罪结果的可能性,即需要是包含了其现实危险性的东西。[14]
我国刑法学因受苏俄刑法学的影响,在犯罪构成中长期采取危害行为的概念,这一概念包括了行为的规范要素 (构成要件)与行为的价值要素 (危害),[15]其也可谓注重形式与实质的统一。实行行为的概念是在共同犯罪理论中采用之后逐渐引进于德日的,其引入几乎替代了危害行为在构成要件中的地位,但其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基调并没有改变。正如何荣功教授所言,无论从形式上认识实行行为,还是从实质上认识实行行为都应当是必要的。[16]张明楷教授虽然侧重于实行行为的实质考察,认为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没有侵犯法益的行为不可能构成犯罪,当然也不可能成为实行行为。不仅如此,即使某种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性,但这种危险程度极低,刑法也不可能将其规定为犯罪,这种行为也不可能成为实行行为。[17]但是,张教授不可能也并未否定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实行行为的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限定性。因此,陈兴良教授才指出,无论是张明楷教授还是何荣功博士都主张实行行为是形式与实质的统一,关键问题不在于形式或实质两者择一,而在于如何安排形式与实质的位阶关系。[18]不难发现,陈教授坚持形式判断先于实质判断的原则。
关于这一点,大谷实教授也强调:只要以罪刑法定主义为原则,就应以构成要件该当性作为犯罪成立的第一性的要件。只有在确定该行为是构成要件该当行为之后,才能再作实质性判断。否则,就有可能对即便不是刑法所预先规定的行为,但仍以该行为性质恶劣,应予以处罚为由而认定为犯罪。[19]显然,在实行行为的判断位阶上,大谷教授也坚持了形式判断先于实质判断的原则,而且更加注重形式侧面。就形式而言,实行行为一般被表述为行为人实施的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这种界定有助于确定实行行为的类型,确定实行行为所触犯的罪名,其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但是对其不加入实质判断,必然导致实行行为的空洞,沦为概念的循环游戏。条件关系是实行行为与结果两个构成要件要素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而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实行行为并不是明确的形式存在,形式判断优先,即先考察某个身体动作是否符合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给人一种无所适从感,这就要求在与结果关联的层面,考虑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实行行为最终的判断依据仍然是这个身体动作的法益侵害及侵害的危险性。就本文所讨论的轻微暴力而言,优先根据形式规定并不能对其是否实行行为作出合理解释与限制,因为如果不进行实质考察而仅看其形式,根本无从确定某种“轻微暴力”是不是实行行为,是哪个犯罪的实行行为。就此,要么难以继续因果关系的判断,要么仅以被害人重伤、死亡等重大结果来推断行为,如此难言形式优先具有切实的优越性。实行行为的类型化离不开实质元素的填充,或可言之,形式判断的空洞必然以实质的法益侵害危险来填补。因此,在坚持实行行为判断的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相统一的前提下,必然更加强调其法益侵害危险性,实行行为是具有发生结果的一定程度以上的危险性的行为,或者说,实行行为只能是具有法益侵害紧迫危险性的行为,[17]而其形式的构成要件的规定性只具有对实质结论的限定作用。总而言之,实行行为的第一个要素必然是法益侵害的紧迫危险性,其次,必须在形式的构成要件范围内。
三、外在机制:法益侵害危险之判断
虽然,归因是归责的基础,但是,“就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而言,归因并无独立的意义,它从根本上服务于归责”[20]实行行为的法益侵害危险性虽然是一种实质的要素界定,但是不可否认,其根源于条件关系的回溯,而条件关系之实行行为的范围相当广泛,因此,才导致完全根据条件关系进行事实判断的条件说受到了多方面的批判,所以,必须对实行行为的成立范围进行规范限缩,这成为归责的首要任务。规范限缩的合理借鉴就是客观归责理论的第一个条件:制造了不被允许的危险。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言,客观归责论中的制造不允许的危险的内容,实际上是对构成要件行为的规范判断。[21]可以说,客观归责理论企图从法秩序的目的定出确定构成要件行为的范围,是想替构成要件行为找出实质的判断依据。[22]如前所述,实行行为的两个要素分别是法益侵害的紧迫危险性和构成要件的规定性,其二者可分别对应于制造不被允许的危险之“危险”和“不被允许”。换言之,可将法益侵害危险性的规范判断与制造不被允许的“危险”确定等同视之,对后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借鉴予前者,因之,法益侵害危险的判断焦点也应集中于应以何种事实作为判断的资料及应以何种标准出发根据资料进行判断的两个问题。
(一)“危险”的判断资料:行为时存在的全部客观事实
德日刑法理论中,对客观归责理论的“危险”判断并未进行单独、特别地讨论,因客观归责理论与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关于“危险”的判断资料的确定,完全继承了相当因果关系说之相当性的判断资料确定的观点,且通说与日本刑法理论中的折中相当因果关系说基本一致。德国学者认为,作为“危险”判断资料的事实认定时,“法官必须事后(就是在程序中)处在一个构成行为被评价之年前的客观观察者的立场上,并且运用一个有关交往圈子里的理智的自然人的知识,加上行为人的特殊专门知识”。[23]不过,由于相当因果关系说之相当性判断存在主观说、客观上及折中说等三种学说的争议,与之相对应,危险的判断资料也存在三种来源:行为人特别认识的事实、事后查明的行为时的客观事实及一般人认识到的事实。当三者完全一致时,危险判断资料依据上述何者并不存在结果上的差异,所以没有讨论的必要。存在问题因而值得讨论的是三者不一致的情况下,危险判断资料的来源问题。根据德国学者的观点,危险判断的基础并非经事后查明的行为当时客观存在的所有事实,而原则上只是特定群体或领域内一般人在行为当时能够认识的事实。[24]149但是在一般人的认识与行为人的特别认识不一致时,理论上往往倾向于在行为人的认识能力高于一般人时,则以行为人的特别认识为标准,反之,行为人的认识能力低于一般人时,以一般人的认识为标准。先不谈这种例外模式是否合理,这里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一般人认识的确定问题。人的认识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确定一般人是否认识及为其所认识的事实时,必须对之进行类型化,即一般人必须是具有限制条件的类型化的特定社会群体。不过,一般人的限制条件是比照行为人自身的条件确定的,所以增加的限制条件越多,一般人标准越倾向于行为人个人标准,如此则导致客观的危险性判断资料的确定完全依赖于人的主观认识。但是,客观的法益侵害危险性的判断为什么必须依据于主观认识、且是行为人的认识也不无疑问。正如陈璇博士所言:一般人的认识标准不仅在很多情况下毫无存在的意义,而且还可能导致理论上的矛盾与混乱。[24]153-154据此,一般人认识和行为人认识都不能成为实行行为的法益侵害危险性判断资料的来源。
法益侵害危险性的判断资料并不来源于认识,无论是一般人还是行为人,反面观之,其必然来源于行为时存在的一切客观事实。判断资料是主体作出判断的依据,人之行为是事实的存在,行为的时间、地点、方式、对象等外在因素也是客观的实在,其并不以人的认识不同而改变,判断主体作出判断的依据是这些实实在在的客观事实,而不是经过主观加工的行为人或者一般人的认识,因此影响甚至决定着行为的法益侵害危险性的有无与大小的只能是行为时的客观事实。而且,行为的危险性不等于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前者是实行行为本身是否具有危险性的问题,其只能存在于行为时(实行过程中),而后者则可能推及至结果发生时(前),对后者进行事后判断不存在问题,但是对于前者,则只能站在行为时的立场上进行事前预测。易言之,实行行为的法益侵害(紧迫)危险性的判断资料是行为时存在的一切客观事实。不过,案件的审理不可能对行为时客观事实进行回放,所以行为时客观事实依赖于事后的侦查与辩证,行为时存在的一切客观事实就是事后查明的案件客观事实,因此也可以说,实行行为法益侵害危险性的判断资料是事后查明的行为时的客观事实。
(二)“危险”的判断标准:社会一般人立场
判断资料作为法益侵害危险性的判断对象而存在,但是,明确了判断对象并不必然得出合理的判断结论,还必须确定正确的判断标准,惟其如此,才能以有现实意义的标准对对象作出正确的评价。
日本学者大谷实指出,关于实行行为的内容的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有指科学法则上的迫切危险的见解,和行为时一般人所感受到的现实危险的见解之间的对立。由于构成要件是以社会一般观念或社会心理为基础的可罚行为类型,所以应当根据一般人对客观危险的恐惧感来判定。[25]显然,法益侵害危险性的判断存在两种不同的标准:社会一般人标准和科学法则标准。大谷教授站在了社会一般人的立场上,以一般人对查明的行为时的客观事实的危险的恐惧感来判断法益侵害的现实危险性。大谷教授主张该观点主要基于其构成要件的两点规范性(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在第一层次上,构成要件作为行为规范,通过将具有法益侵害之危险的行为予以类型化,并明示于构成要件,使之成为刑法禁压的对象,从而谋求对法益的保护;同时,在第二层次上,作为裁判规范,……以保障行动自由。[26]构成要件作为行为规范,旨在事前告知国民什么行为是允许的和禁止的,因此,处罚一般人不能认识到的危险或者不认为是危险的行为,并不能有效规制一般国民的行动,只有根据一般人标准,才有益于法的不要实施该种行为的命令的执行,以达到防止犯罪的目的。
结果无价值论者一般容易认同科学法则标准。如张明楷教授指出,某种行为是否具有法益侵害的紧迫危险,应以行为时存在的所有客观事实为基础,并对客观事实进行一定程度的抽象,同时站在行为时的立场,原则上按照客观的因果法则进行判断。[4]145显然,张明楷教授也主张法益侵害紧迫危险的判断由来于行为时的所有客观事实,而非一般人或行为人的主观认识,这一点值得肯定。不过,张教授主张的因果法则(即科学法则)的判断标准却值得商榷。其一,危险存在与否,是根据行为时查明的客观事实的一种经验法则上的预测,就具体案件而言,危险应存在于结果发生以前,结果出现后就不存在危险预测的问题,根据因果法则判断,必然得出“凡引起结果发生的行为均制造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的结论,这或许也是张明楷教授主张 “对客观事实进行一定程度的抽象”的原因所在吧。其二,张教授主张,站在行为时的立场上进行判断,且要对客观事实进行一定程度的抽象。但是,一方面,具体案件的实行行为法益侵害危险性的判断,为什么需要对查明的行为时的客观事实进行一定程度的抽象,依据不明。另一方面,抽象的程度与标准难以统一,对行为时存在的客观事实进行抽象判断时,应当舍弃哪些具体事实也难以确定,而且法官的法律素养参差不齐,标准不一可能导致随意出入人罪,有失判案公正。其三,科学因果法则的立场难以完全、彻底的贯彻。一是人类社会中尚大量存在自然科学尚未确定、不能解释的问题;二是客观具体地看,凡未引起结果发生者,皆有其特定的原因,根据因果法则应得出其皆不具有法益侵害的紧迫危险,其不合理性至为明显。因此,张明楷教授在讲到未遂犯与不能犯的区别标准时提出,对没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原因进行分析,考察具备何种要素时会发生侵害结果,在行为当时具备这种因素的可能性。[4]358但是,根据张教授所举之例不难发现,这种可能性的判断主观随意性较大,因而适用可能性极小。
本文倡导社会一般人标准。除前述理由外,还有如下原因:第一,社会一般人标准是客观的,而非主观方面对客观构成要件的渗入。社会现象的对与错、是与非,总是人根据其经验法则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评价与选择,如果认为一般人共同认识的标准是主观的,则在对事物的判断上不存在所谓的客观标准。无论认为客观构成要件首先是评价规范还是决定规范,就实行行为的法益侵害危险性而言,“危险”是法规范视野下的危险,主体选取的作为判断对象的资料是行为时存在的一切客观事实,判断主体是社会一般人,无论是评价对象还是对对象的评价都不涉及主观要素。第二,法律规范必须具有社会指向性,必须具有实在的社会意义,否则其将形同虚设,刑法规范当然也不例外。自然科学领域尚未公之于众的科学发现不具有社会意义,其不可能影响一般人所掌握的经验法则,既使其能够制造紧迫的重大危险,在未被社会一般人认知时,也不能成为规范领域的危险,当然不可能被作为规范评价的标准。第三,实行行为确定未遂犯成立时期的功能遭到多方面的质疑。如有学者指出,鉴于未遂犯中实行的着手处理的是不法的可罚起点,而因果关系中的实行行为解决的是结果是否可以归责于该行为的问题,二者之间存在本质的不同,故不应将实行的着手与实行行为相等同。[27]因此,理论上对未遂犯与不能犯区别的具体危险说的一般人判断基准的质疑,即“一般人认为没有危险,而客观现实存在危险”的矛盾,不能等同适用于实行行为法益侵害危险性的判断基准。
综上,实行行为的法益侵害紧迫性的规范判断(制造不被允许的危险),应以事后查明的行为人实施行为时存在的所有客观事实为判断资料;而其判断标准则必须站在行为时社会一般人的立场上进行。进言之,实行行为的法益侵害危险性的判断,应以行为时所存在的所有客观事实为基础,站在行为时的立场上,以社会一般人的预测为标准进行判断。
四、理论对接:轻微暴力的实行行为性之辩证
实行行为的类型化标准必须能够满足个案中实行行为判断的需要,必须能够合理、有效、完整地分析导致结果发生的行为的实行行为性。如第一部分所述,轻微暴力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其一般情况下不足以导致轻伤以上结果,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导致了他人死亡的重大结果,能否肯定其实行行为性呢?下文就前述三种不同类型的轻微暴力分别进行考察。
(一)存在介入因素型
存在介入因素的情况,理论上一般在因果关系中加以讨论,且其判断的是结果的原因归属问题。此处对介入因素的评析一般依据四个方面的因素:实行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大小、介入因素的异常性及其对结果发生所起的作用、其是否属于行为人的管辖范围。其中,第一个因素显然属于实行行为的判断问题,理论上在因果关系中论述并不妥当,如此必然导致实行行为的虚置,而事实因果关系范围膨胀。而且,如果对存在介入因素型的案件的实行行为一语带过,将会出现(或许已经出现)对实行行为明显成立的案件的实行行为性大加特论,而对上述亟待论证的案件的实行行为性避而不谈的奇怪现象。本文认为,介入因素型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并不能因其有其他因素的介入就忽略实行行为的考察,而直接过渡到因果关系的视域。换言之,实行行为作为客观构成要件的首要要素,其必须把好通往犯罪的第一道关,任何犯罪都必须先确定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和构成要件的结果,在此前提下才能进行归因与归责的判断,存在介入因素型的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也不能例外。因此,存在介入因素型的轻微暴力,其实行行为的判断同样首先需要考察法益侵害紧迫危险性的有无。只不过,由于此处的法益侵害紧迫危险性的判断是站在行为时进行的事前判断,因而此处的介入因素应当仅限于行为时现实介入的各种因素,当然不限于人的行为。
实行行为的危险性就是实行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在行为时的特定时空下,实行行为引起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判断必须考量介入因素的异常性。具体而言,根据行为时存在的一切客观事实,站在行为时的立场上,考察其他因素介入的可能性大小。如果介入因素的介入具有通常性,根据一般人的预测,既使其换个时间实施了轻微暴力,仍然会有介入因素的介入,导致他人死亡,则不容置疑,一般人也会认为行为人的轻微暴力引起他人死亡的可能性比较大,其法益侵害的危险紧迫,肯定这种轻微暴力的实行行为性不存在问题。例如,行为人在高速公路边将被害人猛推至道路中央,使被害人被撞身亡的,显然因高速公路的特定事实,站在行为时的立场上,一般人都会认为行为人的猛推(轻微暴力)行为具有致人(被撞)死亡的高度危险性,必然肯定其实行行为性。如果对被害人施加轻微暴力,正常情况下不足以致人轻伤以上的结果,而介入因素异常出现,当然一般人也难以预测其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可能性,因而必须否定其实行行为性。此外,值得说明的是,实行行为的法益侵害紧迫危险性属于事前判断,必须站在行为时的特定时空条件下,因此,影响实行行为危险性的介入因素异常与否的判断也必须站在行为时,以一般人的眼光去观察。当然,介入因素对结果发生所起作用的大小也是影响实行行为危险性存在与否的关键因素,也必须对之以一般人的眼光站在行为时的立场上进行考察。总而言之,行为时存在的介入因素,属于需要一般人进行判断的、影响行为危险性的客观要素,必须将其考虑在实行行为法益侵害危险性的判断资料范围内。
(二)被害人特异体质型
被害人特异体质型的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比较容易得出轻微暴力为实行行为的肯定结论。在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之中,实行行为是其中心因素,[28]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不影响客观实行行为事实的现实存在。被害人属于特异体质者,无论行为人及一般人是否认识到,都不能否定其特异体质的现实存在。站在行为时的立场上,即使是社会一般人也能够预测到如戳破血友病患者的皮肤、踢打冠心病患者等致其死亡的危险性。换言之,以行为时存在的所有客观现实为资料,会发现,一般人也会认为此类情况只要行为人实施了针对被害人特异体质的特定行为,就能够导致他人死亡的结果。所以,被害人特异体质型的轻微暴力,应当符合规范的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的特征。当然,在死因构成上,致体质特异人死亡的轻微暴力行为只是他人死亡的诱因,而非直接死因,[29]能否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归属于行为人的实行行为,属于因果关系中的归责问题。作为诱因的行为人行为致使特异体质者死亡的危险性是能够被一般人所认可的,其实行行为性不难肯定,只不过这种非直接死因的诱因能否对结果进行归责成为问题。
(三)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型
该类型的轻微暴力一般表现为,行为人对被害人的拉扯、甩手、推攘等导致被害人摔倒、磕碰而发生死亡结果的情况,其一般也包括行为人的非攻击性暴力结合被害人自身失误导致死亡结果的情形。该类案件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原因一般表现为对利器、台阶、石头等的磕碰,该类轻微暴力是否具有高度致害的危险性,必须结合其行为时的特殊情况,站在行为时进行个别判断。换言之,我们应当区分作为模型的实行行为与具体犯罪的实行行为。前者是规范,后者是规范性事实。[30]因而,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型的轻微暴力案件,根据行为时的所有客观事实的不同,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判断的规范标准是统一的。在楼梯上推攘、在乱石丛中拉扯,都存在极度的致人死伤的可能性,而在普通的地面上实施的此类活动则难说存在死伤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对前一类型的轻微暴力,一般人都会肯定实行行为的法益侵害的紧迫危险,所以应当肯定其实行行为性,而对于后一种情况,则不足以引起一般人的恐惧感,不能被认定为规范性的事实,即不存在具体犯罪的实行行为。
五、案例回溯: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之定性
(一)案例1
本案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突发介入因素(被推后退被渔网绊倒),是否只能在因果关系中考察?其二,上诉人导致死亡的一般殴打、推搡,能否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实行行为?就此两个问题本文皆持否定的态度。首先,行为是否存在致死亡结果发生的紧迫危险性是行为时的一切客观情况决定的,上诉人黄安平实施推搡行为时,被害人身边或脚下有渔网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此条件的存在直接影响危险性的判断,本案二审法院也认为“如果现场没有渔网,也可能不会发生本案”,因此必须将此渔网现实存在于行为时的客观情况考虑在危险性的判断中。众所周知,慌乱的后退中渔网极易绊人腿脚致其摔倒,而在被推搡的紧迫情况下,被渔网绊倒的情况更具有发生的可能性,而且被害人是65岁的老年人,站在行为时,以社会一般人的眼光看,行为人的推搡行为无疑具有致人死亡的紧迫危险性,具备实行行为的实质要素。其次,实行行为的形式条件是构成要件的规定性,在肯定了实行行为的实质要素后,必须判断其是否属于以及属于哪个具体罪名的客观构成要件。已如前述,实行行为的形式要素的确定依赖于实质要素,刑法规定了故意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和故意伤害(致死)罪,显然,肯定致人死亡的危险性之后完全能够肯定其构成要件符合性,但是具体符合哪个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必须进行后续的主观判断。就本案而言,上诉人黄安平用拳头击打黄某面部、右胸部,并将黄某往前一推,但是邻里纠纷中轻微暴力下的推搡、殴打并不等于伤害,其行动的“故意”是一般生活意义上的有意,而不同于犯罪意义上的故意伤害的“故意”。换言之,邻里之间由于民间纠纷一方殴打另一方造成死亡,以及其他轻微暴行致人死亡的案件,不能轻易地认定为故意伤害致死。[31]因此,在行为人没有伤害故意的情况下,致人死亡的实行行为就不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不宜将黄安平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但是,根据案件事实,在脚下有渔网、地上有石头的场地上,行为人对一个65岁的老年人实施推搡行为,具有预见致其摔倒而引发死亡的可能性,因此宜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对黄安平定罪处罚。总而言之,本案中,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突发介入因素应在实行行为的法益侵害危险性中进行判断,且其实行行为仅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的犯罪构成,应当对之定性为过失致人死亡罪,显然,二审法院定性错误。
(二)案例2
被害人特异体质型的轻微暴力,符合规范的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的特征。被告人张某甲用手指戳孙某丁头面部致其轻微外伤,此处,法院对其行为的轻微暴力的认定是正确的。无论张某甲能否预见到孙某丁有特殊疾病,孙某丁在事发当时属于特异体质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以此为基础,由于具有正常知识水平的一般人都能预测到,与患有特殊疾病的人发生争执并指戳其面部,有导致其病发并危及生命的极大可能,因此可认定张某甲的行为具有导致孙某丁死亡的紧迫危险性,因此肯定其实行行为。之后,在肯定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判断张某甲的主观方面。审判法院一方面审理查明与人缺乏沟通的被告人张某甲对被害人之前的身体状况,另一方面又判决被告人过失致人死亡罪,至于被告人对被害人的身体状况是否具有预见可能性则未加论证。根据本文的论证逻辑,若果证明与人缺乏沟通的被告人张某甲不可能预见被害人的特殊体质,则属于意外事件,法院对张某甲的行为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性就是错误的。
(三)案例3
该案显然属于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型。被告人徐永做与吴某互相推搡、踢打,被告人徐永做挥手打中吴某胸颈部一下,致吴某倒地且头部后枕部碰撞到地面,就此而言,被告人的行为方式一般仅可能导致他人肉体一时的疼痛,至多造成轻微伤害的后果,符合轻微暴力的成立条件。被害人吴某的死亡是因为倒地后且头部后枕部碰撞到地面,就普通的地面而言,用手朝胸颈部挥打,具有正常知识水平的一般人并不会感到到具有致人死亡的可能性。故可以认定,被告人徐永做的行为不具有致人死亡的紧迫危险性,否定其实行行为的成立,就此应直截了当地否定被告人的客观不法与其主观责任。因此,法院对徐永做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定性不正确。
进而,上述三种致人死亡的轻微暴力,能够肯定其符合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的,则在其后进行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主观方面的判断。在进行条件关系之归因后,根据客观归责理论,规范地判断结果对实行行为的归属。届时,如果否定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直接得出无罪的定性结论,否则,如果肯定实行行为的结果归属,则对行为违法性和行为人的有责性继续考察。就行为人的主观要素而言,如果行为人已经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并对之希望或者放任的,构成故意杀人罪;如果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预见可能性,但是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的,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如果行为人具有伤害的故意,但是发生了致人死亡的结果,则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否则结果属于不能预见的原因引起的(没有预见可能性),是为意外事件,不构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