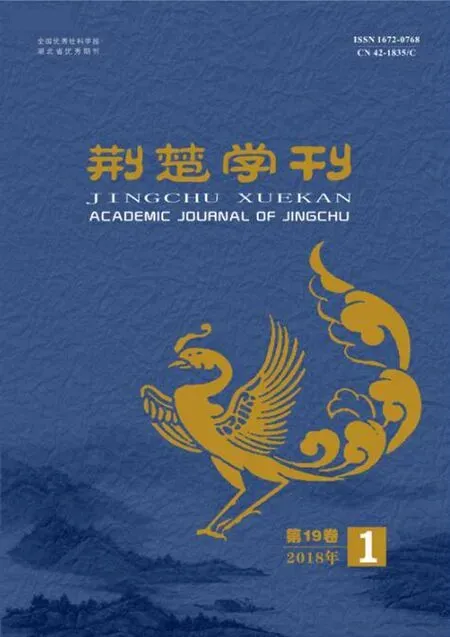怨恨与爱的道德教化论之争
——基于舍勒的尼采现象学之旅的探险(1)
韦永琼
(江苏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拎出尼采在《道德的谱系》、舍勒在《道德建构中的怨恨》里阐释《圣经》中的怨恨/爱(2)的道德教化之论争,两相对勘比较,我们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有研究者曾提到,“早在上中学时,舍勒就非常熟悉尼采格言式的著作,从博士论文直到晚年写作《历史中的人》为止,在舍勒将近三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几乎随处可见尼采思想的痕迹。”(3)笔者推测这里有一种可能是尼采和舍勒都是从“‘宗教感’作为一种纯粹意向”[1]来谈怨恨的,因为“如果我们把宗教当作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话,则其最主要的内容并不在于宗教的条文或形式,而在于一份宗教情操,或简称的‘宗教感’之中。Religiosity一概念来自拉丁文religiositas。作为比religion 再进一阶的抽象概念,religiositas指的就是对神祇的一份‘敬意’”[1]。宗教感之没有对象性而属于纯粹的意向性,在关子尹看来可从舍勒对情感现象学的分析中获得。“这个看似困难的局面,我们可借助M·舍勒的反省去解决。舍勒的现象学强调感情的一面是人所共知的。舍勒认为,传统哲学于理性与感性之间截然的二分,对要探讨‘灵性的结构’这任务来看是‘完全不充分的’。他进一步指出,意向性也可以表现为‘意向的感情’(intentionales Fühlen)的问题。”(4)其次,卓新平在他所著的《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中辟出专门章节探讨了步入现代社会之后神学的“曲折历程”,舍勒在其中所作出的“神学新探的努力”[2]48-57。在对舍勒的天主教神学思想的介绍中,卓氏提到舍勒“受到尼采、柏格森和西美尔等人生命哲学的启发,并通过如下命题来实现生命哲学与现象学之结合:此在只是在抵抗中才得以体验,因为实在乃通过对抗主体体验之咄咄逼人的压力才显现给人,此在成为非理性、盲目的生命本能和冲动的领域,它只能通过一种非理性的抵抗体验来把握,从而与理性把握无关;而某一事物的所在则可被认知主体完全吸纳。”[2]50第三,曾庆豹亦曾指出哲学与神学之间建立联系或彼此反对对方的关系乃起于尼采,他在哲学中将这个已死了的问题重新复活起来了,“尼采是使哲学与神学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死亡又再生的关键性人物。尼采之后产生了现象学、阐释学等等,甚至于最近的保罗氏新神学也是受到了他的影响。神学一定是在尼采之后才有一个新的谈论方式,任何一个避开尼采的谈论神学都形成了可疑。”[3]这里提到现象学-神学的研究绕不过从尼采那里开始,但笔者认为曾氏和之前的研究者一样都忽视了舍勒谈论基督教道德教化的爱是从尼采那里最早关注到现象学雏形这一维度出发的。有来自神学内部的研究诸如《基督教释经学》里亦已指出:“解构来自尼采”[4]。
以往不少研究都讨论过舍勒与尼采关于怨恨或爱的社会道德教化论争,但不同的是,这里从舍勒如何通过与尼采就基督教道德教化之争,揭示其如何发现了尼采的生命现象学之旅为视角进行了探究。通过文本上的详细分析与阐释,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在三个方面不同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是舍勒与尼采都是从基督教道德教化“宗教感”的意向性上来谈论爱/怨恨的;二是舍勒通过复原被尼采拆解了的基督教道德教化而展现出其从尼采那里学到的现象学解释学之道;三是舍勒在尼采之后将生命哲学推进到生命行动现象学的面向。以下将对这三个方面展开细致入微的分析与阐释。
一、尼采与舍勒共同的根基:由《圣经》出发
为什么舍勒研究怨恨要特别从尼采这里开始呢?笔者认为这并非仅仅只是如同舍勒用表面上的文字所说的那样简单。实际上这里有着一个现象学的解构-释经学起源,即由《圣经》出发,尼采和舍勒共同的根基是解读《圣经》的基督教之怨恨/爱的道德教化。在尼采那里,他采取了激进式的进路来驳基督教《圣经》教义,指认其开出“怨恨之花”。而舍勒则通过驳尼采释《圣经》指明其结出“爱之果”。尼采与舍勒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反-正-合的完整回路式的怨恨/爱的解释学-现象学。
(一)尼采的“怨恨”发明
舍勒研究怨恨问题的起因乃在于近代以来怨恨研究起于尼采,尼采是第一个在德语中使用怨恨一词的人,此乃尼采的思想标志之一,但以往并不为人们所普遍发现。在《道德建构中的怨恨》开篇,舍勒以现象学的方法指出:“怨恨就是这样一种体验效果单位”[5]3,它既是先验直观,又是一种人的实际经验和直观体验。接着,他给出了“怨恨”这一专业术语的称谓,使用的是法语词,这一词语在德语文献中为尼采最先使用时是以法语词呈现的。舍勒说道:“我们使用Ressentiment(怨恨)一词,并非出于对法语的特别喜爱,而是因为我们还未成功地将之译为德语。尼采使这个词成了专业术语。”[5]3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这样提到:“道德上的奴隶起义开始于怨恨(Ressentiment)本身变得富有创造性,并且产生价值的时候:这种怨恨来自于这样的人物,他们无法用行动做出真正的反应,而只会通过幻想中的复仇获得补偿。”[6]79舍勒在尼采关于这一专门性词语的解释上指出,他的工作上的进展主要有两点:“其一,在怨恨中涉及的是重视对他人做出的一种确定的情绪性反应的感受和咀嚼,这种咀嚼加深那一确定的情绪,并进入个体的中枢,因而便使这一情绪逐渐脱离位格(person)的表达范围和行动范围。其二,这个词也意味着,这种情绪之品质是消极的,即包含一种敌意的动态。或许,德语词Groll(恼恨)与之吻合,能揭示其中一个基本的意义成分。”[5]3-4
(二)舍勒的“怨恨”转化
舍勒提到:“近代关于道德价值判断之起源的探究堪称寥寥。在少得可怜的探究之中,尼采把怨恨看作道德价值判断的根源。”[5]4是否真如舍勒所说近代对于“怨恨”的研究确实很少?还是舍勒为了与尼采对话,而特别说只有尼采对“怨恨”的思考才是值得深究的呢?我们在此追问的是:为什么舍勒研究人类怨恨的问题要从近代开始而不回溯到古代?其次,自近代以来关于怨恨的研究虽然“少得可怜”,但也仍然还有其他除尼采之外有关怨恨的研究,可他为什么就只将目光锁定在了尼采这里?舍勒特别青睐尼采的怨恨研究的真正深层理由是什么?事实上,古希腊时期荷马的诗作《伊利亚特》等就显现了人类所具有的怨恨意识,有研究表明怨恨的谱系学绝不会仅仅只是从近代才开始出现[7]。
“尼采断言基督教的道德,尤其基督教的爱是最精巧的‘怨恨之花’”[5]4。舍勒指出:“这一论断当然会被证明是错误的;尽管如此,较之同类的探究,他的探究毕竟涉及最本质的问题。”[5]4舍勒引用了尼采《道德的谱系》第一章第8、10、14节的原文呈现在其《道德建构中的怨恨》一文中,这三段引文在舍勒的这一有关怨恨的研究中显得具有矢的性,它既是舍勒展开全部论述的一个由头,同时又是其攻击的靶子。首先,舍勒所引尼采《道德的谱系》第8节的内容“从报复的树干中生长出了一种新型的爱”[5]4,可对照尼采的自述来理解:“事实上,在我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时……在孩提时[我]见到了上帝的光芒。写了第一篇关于魔鬼诞生的哲学文字(上帝只有通过设想出他的对立面的方法来设想自己)。……对于上帝而言,设想一个东西与创造一个东西是同一件事情。然后我得出结论:上帝自己设想出了自己,但是当他创造第二个神性人物的时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首先设想出他的对立面。在我看来,魔鬼应当与神子同龄,而且比神子有着更为明确的起源,两者拥有同一个来源。……[那时]关于恶的起源问题就已经在困扰我了,我很合理地将荣耀给了上帝,将他作为恶之父。”[6]50-51尼采认为复仇或仇恨孕育出了爱,但同样爱也孕育出了怨恨。因为上帝和魔鬼来自同源,而怨恨和爱也属同源。舍勒指出他的目的是“深入讨论[怨恨]这个词所描述的体验单位”,“我们简要地用实事的特征表述或描述来代替给怨恨下定义。怨恨是有明确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这种‘强抑’的隐忍力通过系统训练而成。”[5]6-7“报复本身已是一种体验,基于一种无能体验的体验,这总是‘弱者’所处的一种情状。这种报复的本质中,有一种‘以牙还牙’的意识,它绝不仅是单纯伴有激动情绪的抗反应。”[5]7舍勒将报复描述成怨恨,他通过尼采关于道德怨恨的一段话作为要研究的一个题引,接着就开始了用自己的现象学方法来描述怨恨是如何从报复开始的,报复发生时它是怎样一个样态的体验。继而,舍勒明确指出:“报复感、嫉妒、忌妒、阴毒、幸灾乐祸、恶意,只在随后既不会出现一种道德上的克制(比如报复中出现的真正的原谅),也不会出现诸如谩骂、挥舞拳头之类形之于外的举动(确切地说是起伏心潮的表露)的情况下,才开始转化为怨恨。”[5]10舍勒是在用现象学的解释方法来赞同尼采所表达出来的观点,即是在用现象学的解释、描述和分析的方法来重新诠释了一遍尼采所提出的怨恨观。在对怨恨的本质含义上舍勒与尼采并没有太大差别,或者可以说舍勒所说的爱即尼采所说的怨恨,在这个过程中,舍勒否定了尼采对基督教的“否定”或“敌视”。
二、尼采驳基督、批《圣经》,指认其开出“怨恨之花”
“出生于虔诚的基督教家庭,自幼熟读路德翻译的德语《圣经》”[8]的尼采在《道德的谱系》里是怎么理解怨恨的?在尼采看来怨恨是如何产生的?简略的回答是尼采将其视作奴隶道德的一种表现,尼采其实谈论了一种现代性的普遍道德状况,它是一种大众化的道德,而非贵族道德,这是人类堕落的一种表现,但我们需要从其细节上来了解尼采这一惊世骇俗的观点是如何展开的。
(一)尼采反基督的基督教道德教化背景
在《道德的谱系》里存在着大量的对基督教《圣经》经文反其道而用之处,比如“爱仇敌”,尼采是这样说的:“可以断定的是,只有这里,在地球上只有这里,才可能存在真正的所谓‘爱仇敌’”。原文在此处给出Pütz版注释认为:“这是尼采对《马太福音》第5章第43、44节‘要爱你们的仇敌’一语的新解释”,其解释的意思是“真正的‘爱仇敌’,这是贵族或同样强大的人之间的‘爱’,不同于对弱者的‘爱’(即同情),也不同于弱者对强者的‘爱’”[6]82。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马太福音》的解经本里是这样提到这句经文的释义:“‘要爱你们的仇敌。’这里包括着三重过程,从较低的开始,逐渐升到较高的。在个人身上,我们先有管束身体生命的法则;然后有管束我们的心智和态度的法则;最后才是管理我们属灵部分的法则。……一切下面层次的关系,都可以被提升到那无限之爱——至高荣耀的和煦光中。这是一种伟大的合一,至美的和谐。”[11]
笔者认为,其实尼采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圣经》“解经者”。仅就《道德的谱系》来看,在尼采心目中与他对话的文本是《圣经》,他要做的工作是如何解读《圣经》或如何拆解、解构《圣经》,解构到最后,尼采宣布了他那个众所周知的伟大的判言:“上帝死了!”我们重新回味一下他这句口号意味什么?其实就是平民道德时代的到来,神性道德不可见时将会怎样,这是其惯常使用的反话正说方式。尼采的“解经法”是别一种解经法,正如著名的古典学家耶格尔(Werner Jaeger)所指出的尼采是“一个反基督的传教士。”[10]或可类比于李零一类的解《论语》中给人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是将孔子叫做“丧家之狗”或“丧家犬”似的(5)。但不管是正解还是“歪解”抑或是别一种解,尼采首先是立足于从小浸淫在这种《圣经》吟诵、背记和日常使用的文化里进行思考与反思的。
(二)“人如何认识自己?”:一条可能的尼采式现象学之路
《道德的谱系》开篇,尼采指出:“我们并无自知之明。我们是认识者,但我们并不认识自己。原因很明显:我们从未寻找过自己”[6]47。尼采这里所说的“‘我们从未寻找过自己’,是对《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的颠转:‘凡祈求的,必有所得;寻找的,必有发现;叩门的,必给他开门。’”[6]47尼采继续说道:“因此又怎么可能发生我们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的事呢?此言甚是,我们的财宝就在我们认识的蜂巢那里。我们天生就是精神世界里的蜜蜂,振翅撷蜜,营营嗡嗡,忙忙碌碌,我们的心里真正关心的只有一件事——一定要带东西‘回家’。至于生命,即所谓的‘体验’(Erlebnisse),我们当中曾有谁于此认真对待?抑或曾有谁于此耗费光阴?我担心,我们在这些事情上从来都是心不在焉:我们的心没有放在那里,甚至我们的耳朵也不在那里!”[6]47尼采将“我们”比作“天生就是精神世界里的蜜蜂”,“营营嗡嗡,忙忙碌碌”,至于“生命-体验(Erlebnisse)”却是少有人认真对待过,这一描述使得我们看到尼采“生命-体验(Erlebnisse)”的提法与现象学的体验展现出某种亲缘性。尼采反其道而用拉丁教父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的这样一句名言 “什么会比我自己离我自己更近?”[11]来表达其类似的思想:“有一个句子对于我们是永恒真理:‘离每个人最远的人就是他自己’”,《道德的谱系》给出的页下注指出:“此句是对泰伦提乌斯的喜剧《安德罗斯女子》(Andria)中的句子‘Proximus sum egomet mihi’(我是离我自己最近的人)的颠转处理。”[6]48。这句话自古罗马时期开始就颇为重要,引人思考。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第一部第一编第一章中亦引用了此话来分析“此是的是之问题”即“此在的存在问题”[12],在这一章中接下来的第10节里,海德格尔关联性地提到了舍勒的“位格的人”(person)的“人格是(人格存在)”(6)的问题。因而,这里让我们看到一条可能的线索是在现象学之路径上来探究“人如何认识自己”的问题,从尼采这里往后的现象学领域里,在舍勒与海德格尔那里是一路贯穿下来的。
“位格”是舍勒在其哲学中经常会使用到的一个关键词,就如同海德格尔并不把人直接称作“人”而称作“此在”一样,在舍勒这里他也并不把人直接称谓为“人”,而“位格”就是他从天主教信仰的根基立场上试图解读的人。在《道德建构中的怨恨》和舍勒其他著作中皆有关于“位格”(人)的论述。但舍勒对此的研究仍然是与牧师、神父或神学家的解经、注经式的理解有所区别,即舍勒的本己身份仍然首先是个哲学家。这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在此暂不展开论述。另外,关于同情式地理解、较为准确地把握舍勒的整体思想,复杂之处还在于舍勒的一些个人性的经历不得不考虑在内。就像尼采指认叔本华关于“美来自于无利益心”的观点是来自于其“最为私人的方式”经验出来的一样,其中尼采还将之与司汤达的“美是允诺幸福”的观点作对比,且不无黑色幽默似地揶揄叔本华的“美是无利害心的观赏女性祼体……”,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司汤达在感性审美能力上并不弱于叔本华,但他却活得比叔本华幸福,大概源出于两人对审美经验的理解不同[6]166。
(三)尼采的道德教化要旨:高贵者的品质在于善于遗忘
接着往下,尼采继续说道:“‘出身高贵者’对自己的感觉就是‘幸福的人’,他们不会先去观察自己的敌人,而后人为地构造自己的幸福,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说服,甚至骗取别人相信自己幸福(行为和善端正,身心感觉良好);他们同样知道,他们作为充满过多力量的人就必然是积极的人,他们不会把行动和幸福相分离,在他们那里,行动必定会带来幸福,至于那些虚弱无能的人、压抑的人以及感染了有毒情感和仇视情感的人,所有这些都与他们那个层次的‘幸福’截然相反,在后者那里,幸福在本质上只能被动地出现,即表现为麻醉、沉迷、安宁、和睦、‘犹太教安息日’、頣养性情和舒展四肢。”[6]81尼采认为怨恨是一种内心品质低贱的人才会有的,起于奴隶道德的内在心理,是不可取的,是需要警惕它将人们败坏。他提到:“高贵的人甚至不会长时间地对敌人、对不幸、对不当行为耿耿于怀,这是天性强大和充实的标志,这种天性里包含着丰富的塑造力、复制力、治愈力,还有让人忘却的力量(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现代世界的米拉博,他记不住别人对他的侮辱和诽谤,所以也不存在原谅别人的问题,因为他已经忘记了)。”[6]82原文中对遗忘的贵族性呈现了Pütz版注释:“遗忘对生命起到的是促进和增强的作用,特别是尼采所推崇的歌德就持这样的观点。在歌德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大量这方面的证据,其中一个就是《浮士德》第二部的开头(行4628),浮士德处于神圣的睡眠中,用忘川的水沐浴。”[6]104具有美好品质的人善于忘记,这一点尼采只是有所提及,未展开论证。舍勒似乎也未曾展开进行论述,但实际上遗忘别人在我们身上所施加的不幸事件,对于常人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心理学有研究表明人们总是善于遗忘快乐的事情而恰恰能记住的是痛苦的事情,也就是说那些让人痛苦不堪的记忆才能成为记忆,而在这痛苦不堪里就包含有遭受过的耻辱、包含有怨恨的因素在里面。在尼采看来,这不是高贵品质者的美德,记住痛苦某种意义上就是记住怨恨,然后以一个弱者的立场等着复仇或不复仇。带着这种痛苦的怨恨记忆本身就是一种弱者道德的表现,在尼采眼里,具有超人特质的强人并不会记住那些伤害过他们的记忆,他们并不把它们当作一回事,而总是善于忘记,那些痛苦的怨恨记忆根本就伤害不了他们,他们记不住,所以对他们也不造成伤害。而一旦以痛苦的记忆记住这怨恨的种种事件,其本身对于当事人来说就已经是一种伤害。可能有人会问比如大屠杀一类的血腥残暴惨无人寰的重大事件,难道也应该善于遗忘吗?尼采的这一观点是建立在他的超人哲学的基础上来进行论证的。善于遗忘是建立在他首先是个强大无伤的巨人的基础之上,颇具百毒不侵的意味。
(四)尼采的道德教化新通则:超越之神的到来
最后,尼采给出了他自己的观点:“今天,是什么造成了我们对‘人’的反感?因为我们以人为患,而这是毋庸置疑的。并不是恐惧让我们反感;而是因为:我们在人那里丝毫没有可以感到惧怕的东西;蛆虫一样的‘人’获得了显著的地位,并且蜂拥而来;‘温驯的人’、不可救药的中庸者和令人讨厌的家伙,他们已经学会了把自己当成目的和首脑,当作历史的意义,当作‘上等人’……”[6]86-87。据此尼采认为现代社会已然坏掉了,必须有一个人间神能出来拯救得了它。但始终的,他对人并未失去信心。同时,他也还是信神的:“假设在善与恶的彼岸,真的有上天的赐福者存在,那就让我不时得到些恩惠,让我可以看上一眼,看到一些完美的、圆满的、幸福的、强大的、胜利的,却又能引起恐惧和敬畏的东西!”[6]87尼采用鼓舞士气的口吻说道:“让我可以看到为人类辩护的人,看到可以让人类得到完满和救赎的机遇,正是因为这个机遇的存在,人们还可以坚持对人类的信心!”[6]88,119尼采创立某种新的世界法则的诉求——即他像一个新的神一样取代了古代的神谕和现代基督教的耶稣为世界建立法则,在尼采这里,不是要选择哪一家的问题,而是他作为一个新神宣布了新的世界秩序和法则的到来。世界和俗众都应该听从他的教义的指引,而不是听从古代立法世界或基督教的指引。
三、舍勒驳尼采、释《圣经》,指明其结出“爱之果”
(一)驳“基督教的爱是怨恨产生的原因”“祭司的职责产生了怨恨”等观点,强调指明“怨恨产生自压抑”
舍勒明确指出:“基督教的爱之根基完全与怨恨无关;但另一方面,基督教的爱理念又最容易受已有的怨恨利用,以表达怨恨,用基督教理念来矫饰怨恨感;因而敏锐的目光往往难分辨真正的爱与怨恨选择的表达爱的形式。”[5]62-63舍勒给出注释说道:“如前所述,拉丁教父德尔图良(Tertullian)受怨恨驱使。尼采引用他一段话,在这段话中他强调,天堂里的灵魂极乐在于灵魂瞥见恶人受苦。但他的名言:‘因为荒谬,所以我信,因为不可能,所以我信’(《论基督的肉身》,15章,ANF,Ⅲ,P.525)[13],以及他对古希腊文化和宗教的无节制的态度又表明他之所以利用基督教的价值,目的只是发泄自己对古希腊价值的怨恨。关于一种怨恨基督教的逐渐形成,C.F.Meyer在小说《圣人》中有绝妙的描述。”[5]63此处最后一句说的是“康拉德·费南迪·梅耶(C.F.Meyer)‘圣贤’的短篇故事,绝妙地描写了一个怀有愤恨的基督徒的成长。”[14]舍勒认为不是基督教的爱理念孕育出了怨恨之人,而是这个人首先心怀怨恨,即使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自身未能清除掉内心真正的怨恨的话,他必然会得出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认为基督教的爱理念开出的是“怨恨之花”。舍勒说:“迄今为止,全部人类历史所包含的人类活动的诸类型中,都存在着巨大的怨恨危险,这一危险对于士兵最小,对于祭司一类人则最大,正如尼采恰切地指出的那样,……典型的‘祭司政策’是不通过斗争而是经过磨难去取得胜利的政策”[5]34。接下来,舍勒再次引用尼采所使用过的德尔图良的话“尼采恰切地强调说,德尔图良的《论观照》第29章里的一段话(见《道德的谱系》第49页)是这种变节者怨恨的极端表达;照这段话的说法,天堂里的人享有极乐,而极乐的一个主要源泉,应该在于他们看见罗马的代理执政官在地狱里遭受火焚之苦。德尔图良的‘正因为不可信,才信仰,正因为不可能,才确信,之所以信仰,因为它荒谬’(《论基督的肉身》,ctr.5;praeser,7)这句话把他捍卫基督教的方法,其实是对古典价值的报复的一种继续,总结得实在精辟,是他的变节怨恨的一个典型表达。”[5]36舍勒认为怨恨一定是在压抑之下才会产生的,如果得到及时释放是不会产生怨恨的,怨恨是一种积怨。
舍勒以哲学的和社会学的两条线索对怨恨进行了研究,“这里应该提的问题是:怨恨在基督教伦理建构中,随后又在现代市民伦理之建构中起了什么作用。在此,我们的论断与尼采的判断相去甚远。我们认为,基督价值很容易,也常常被视为怨恨价值,然而,基督教伦理的核心并非源于怨恨的土壤。另一方面,我们又认为,现代市民伦理的核心植根于怨恨。从13世纪起,市民伦理开始逐渐取代基督教伦理,终于在法国革命中发挥出其最高功效。其后,在现代社会运动中,怨恨成为一股起决定作用的强大力量,并逐步改变了现行伦理。”[5]54-55尼采对话的背景是基督教的大众化伦理价值形成之前的状况,而舍勒对话的时代背景则是现代性矛盾愈加突出的时代。这里出现了一个节节退化的情况,即越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后面,怨恨越属于大众伦理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因而,在这一点上舍勒与尼采的观点是一样的,即怨恨属于奴隶道德,而非主人道德。
舍勒首先是通过现象学的方法将怨恨发生的状况进行了描述分析和解释。接着,实际上就进入了他的正题讨论——驳尼采。他的第二个任务是论证基督教的“爱邻人”并非奴隶道德或普罗大众的泛滥化的所谓道德,它也不生恨(不产生怨恨)。第三,他引入其他因素(比如从生物学角度)来分析怨恨产生的原因,进一步得出自己的观点,认为人的怨恨也属生命力量的一种,但基本上属于一种负面能量,有转化成正能量的可能,不普遍。“基督教的爱之根基完全与怨恨无关;但另一方面,基督教的爱理念又最容易受已有的怨恨利用,以表达怨恨,用基督教理念来矫饰怨恨感;因而敏锐的目光往往难分辨真正的爱与怨恨选择的表达爱的形式。”[5]62-63
(二)舍勒注意到了尼采的“双重辩证法”
接着上面对尼采指认基督教爱理念开出“怨恨之花”的批驳后,舍勒提到:“‘辩证法’的原则同样如此。‘辩证法’不仅想通过否定A产生出一个非A,而且还想产生出一个B(正如黑格尔说斯宾诺莎的‘每一界定都是否定’)。”他给了一段注释:“达尔文的学说告诉我们,一切演化本质上都由偶发变种进行的、对无用东西的筛选决定,种群的诸现象传输给我们的,首先是一种正性演化和新种生成的景象;这一景象是一种纯粹的伴随现象,隐藏在这一伴随现象背后的,是纯粹的否定和弃绝。……达尔文的这一学说运用了黑格尔关于‘否定之创造性意义’的学说的基本主题。”[5]37舍勒所启发出来的是让我们看到在尼采那里具有着一种双重辩证法的使用,即尼采的解构圣经手法分为两层:第一层解构,他引出正文原句但却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将其呈现出来的;第二层解构,在第一层的基础上再次从反面来对之进行一番阐释。这种阐释手法从其“上手状态”时就是与原典的本义针锋相对的,或可称作这是尼采所独有的双重辩证法,舍勒仅在此处略有提及但在后文中并未继续展开论述。
(三)舍勒的生命行动现象学表明其在生命哲学流派里“接着讲”
生命行动现象学(Leben Aktphänomenologie)这一词需要作一界定,江日新指出舍勒在《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德文版第90页提到的行动现象学(Aktphänomenologie)(7)吸收了他的导师倭伊铿的生命哲学理论,这种行动主义早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就有传人,即倭伊铿致张君劢的一封信中所指出的:“使予之躬行主义(Aktivismus)而有俾於中国之大民族於万一,予之荣幸何如哉!”江日新在此解释道:“至于‘行动主义’对于张君劢治阳明学的初衷,其影响线索亦历历可循。”[15]江日新在此处花费较大篇幅谈倭伊铿的生命哲学目的是强调舍勒的行动现象学受惠于此,笔者以为或可将舍勒的这一特有的哲学称作“生命行动现象学”。
舍勒提到:“从本质上说,生命是不断成长、壮大、充实的,就是说,并非如一种谬论所言是‘活命保命’,好像出现于成长、壮大、发展中的一切事物只是单纯维持生命力的附随现象,从而都得返回到‘适者生存’。”[5]63舍勒仍然是属于生命哲学流派中的一员,但他为生命哲学开辟出了新的曙光与走向。“照我看来,生命的牺牲无疑是有的,甚至还是更高价值意义上、寓于更高价值之中的生命形式;但并不因此意味着每一种牺牲都是一种促进生命的行动。”[5]63-64舍勒在此给出注释继续解释道:“我有意将阐述限于生命的这一面,并未涉及下列情况:纯粹的精神行动及其法则、对象以及缘于‘生命’的对象之相互关系,都绝不能从生命的可能哲学模式来理解;因而,存在一系列与生命价值和生命行动无关的价值和具有价值的行动。基督教徒的‘安妥’和‘稳靠’在本质上超逾生命及其可能命运之上。但是,尼采提出基督教之爱理念源于怨恨这一命题,不承认上述论断,甚至将真理的观念放到‘生命价值’之下去考察;因此,我们不应以此为前提。我们将仅满足于能够表明,他的论断即便从他的前提(即生命极限是最高价值)去看也是错的。关于‘生命价值’在价值级别中的实际等级,我作过详细的论证,参《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的价值伦理学》第二部分。”[5]64舍勒是在尼采之后“接着讲”,即德国生命哲学流派中,从叔本华、尼采到狄尔泰、奥伊肯(即倭伊铿,舍勒的老师)再到舍勒自己,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主线,从不同角度不同方法建构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生命哲学。相比于尼采的生命权力意志、超人哲学、对基督教的逆向“观照”,舍勒则试图在此基础之上“拨乱反正”,正面叙述基督教道德哲学的意义。同时,他的生命哲学之不同于以往,乃在于他将现象学的方法运用了进来。诚如江日新所界定的,它是“一种精神生活的奋进,是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通过我们行为劳动(Tat,Arbeit)而将顽冥及吊空的世界转化成一活生生富有意义的精神生活世界。”[15]“肯定有一种自由奉献自身生命之财富、生命力之美好的自然充溢的牺牲。每一生物都具有与其他生物(按照这一生物同其他生物的相似特性而分为不同的等级)一同体验经历的能力;通过这一能力,我们有别于一切‘死物’;在这一对照中,我们感到自己与其他生命体一致,利害攸关;面对这些生命体时出现的强烈牺牲愿望,绝不是可从本原自利欲望引导出的单纯的生命获取。”[5]64此处亦可看出舍勒使用生物学研究结果的迁移和理论观点的借鉴。
四、结语
综上所述,舍勒的价值伦理现象学之启发来自尼采的道德价值重估。舍勒指出“尼采准确地意识到,基督教主张信一个高级实在,而不是这个变化的世界,所以它发现柏拉图的思想框架就是信仰者的一种表达;真理不仅超越一切质料之物,而且超越这个充满变化和意见的世界(感觉世界)。地上的生活(洞穴)预先设定了真理之光,人的完满在于不断探索探求真理的本性。”[16]从舍勒与尼采这里,我们看到西方基督教爱/恨的观念,不论是从肯定抑或否定上来看,都体现出了一种对于社会所起到的教化功用,而舍勒从尼采那里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正面复原却同时亦发现了其现象学解释学之道,以此舍勒接续尼采之后的生命哲学,发展了具有其个人特色的生命行动现象学,并从而走向了其后期具有开创性的关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之思的哲学人类学!
注释:
(1) 本文是继《舍勒如何发现了尼采的现象学方法摭探》(载《荆楚学刊》,2017年第2期:90-96)的下篇,二者或可称为就此主题上笔者所做的内外篇探究。“外篇”主要梳理了相关的文献研究;而“内篇”则从舍勒与尼采就此主题上的讨论,以内在文本分析为依据作了些探究。
(2) 这里尼采所谈的怨恨与舍勒所谈的爱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舍勒看来尼采所说的基督教的怨恨其实是基督教的爱,而从尼采那里他让我们看到基督教的道德教化之爱实际已成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怨恨。因而,在本文的语境中展现出来的是谈爱必然是在相对于怨恨的背景下来谈的,而当我们谈怨恨时也必定是以爱作为背景进行谈论的,二者之间具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因而,此处我们以“怨恨/爱”来表示。
(3) 详见张志平:《情感的本质与意义:舍勒的情感现象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页.英文文献可参阅:Stephen Frederick Schneck.Person and Polis:Max Scheler's Personalism As Political Theory,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7.P.16.
(4) “意向性与宗教感”的讨论在以下两种文献中均可寻得。详见关子尹:《意向性与宗教感:从现象学的观点看宗教问题》,节选自靳希平、王庆节等编著,《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 特辑 现象学在中国 胡塞尔《逻辑研究》发表一百周年国际会议》,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第52页;关子尹:《语默无常:寻找定向中的哲学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1页。
(5) 此种类比实际上是较为粗糙的,但仍放于文中乃在于表明笔者的观点认为尼采并非之前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个无神论者,或因他是“反基督”或“敌基督”的因而与我们便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知音。
(6) 参见[德]海德格尔:《是与时》,溥林译,未刊稿,四川大学哲学系。[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56页。
(7) 倪梁康译为“行为现象学”,详见[德]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为一门伦理学人格主义奠基的新尝试》,倪梁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23页。
[1] 关子尹.意向性与宗教感:从现象学的观点看宗教问题[C]//靳希平,王庆节,等.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特辑 现象学在中国 胡塞尔《逻辑研究》发表一百周年国际会议.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45.
[2] 卓新平.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3] 曾庆豹.现象学与神学复旦大学讲座[EB/OL].[2017-07-20].http://www.wxbgt.com/serie_104402.shtml.
[4] W.W.克莱恩,C.L.布鲁姆伯格,R.L.哈伯德.基督教释经学[M].尹妙珍,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96.
[5] 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M].刘小枫,林克,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4.
[6] 尼采.道德的谱系[M].梁锡江,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7] Hren J.The Genealogy of Ressentiment and the Achilles' Heel of Humanitarianism: Thinking with Dostoevsky,Scheler,and Manent on"Love of Mankind"[J].Logos A Journal of Catholic Thought and Culture,2014,17(4):1-5.
[8]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钱春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译者序7.
[9] 坎伯·摩根.马太福音[M].张竹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77.
[10] 耶格尔.早期基督教与希腊教化[M].吴晓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1.
[11] 奥古斯丁.忏悔录[M].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00.
[12]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52.
[13] 舍勒.舍勒选集[M].刘小枫,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1443-1445.
[14]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88.
[15] 舍勒.基督教道德与愤恨[M]//汪民安,陈永国.尼采的幽灵: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尼采.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41.
[16] M·舍勒.基督教的爱理念与当今世界[M]//爱的秩序.林克,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75-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