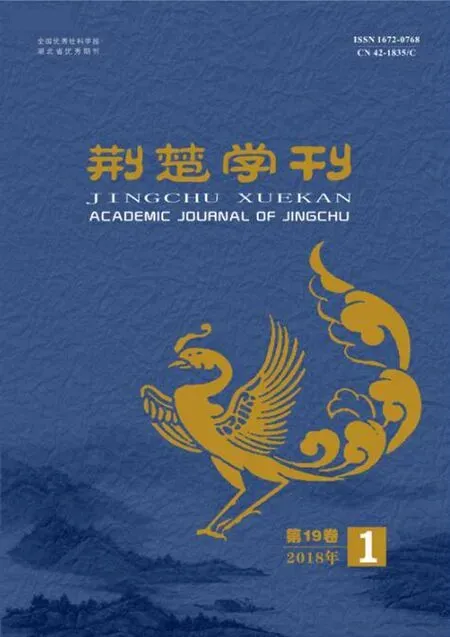乾隆《襄阳府志》中习家池及堕泪碑诗歌的文化沉思
张 婷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襄阳,从东汉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正式建郡治算起,已经有一千八百多年的悠久历史。宋、明、清三代都曾有关于襄阳的正式方志问世,其中清代乾隆年间《襄阳府志》艺文部分收录了历朝历代以襄阳人、事、物为歌咏对象的诗文作品,它们赋予了襄阳这座古城更为浓重的文化意蕴。这些诗文中,尤以歌咏习家池和堕泪碑的诗歌最为典型。方志里集中荟萃了各个朝代对这两处文化遗存的文献记录,这一方面表明习家池和堕泪碑两处的遗存已经形成了丰厚的文化积淀,另一方面也提示着人们应当重视从纵向的历史长河中思考这种积淀的文化意义。
习家池是东汉襄阳人习郁的私家园林。西晋怀帝永嘉年间,山简镇守襄阳之时经常在池上饮酒至酩酊大醉方才离去。站在习家池畔,放眼北眺,不远处,就是茫茫岘山,岘山上有一块堕泪碑,是人们为纪念魏晋之际的羊祜而立。在文化意义上,如果说习家池是出世的清凉地,那么堕泪碑就是入世的航向标。
一
最初的习家池,是繁盛的,只可惜,晋代以后,习家池就衰落了。习家池昔日的绮丽华美和后世的破败荒凉,在唐代诗人孟浩然笔下对比尤为清晰[1]462:
当昔襄阳雄盛时,山公常醉习家池。
池边钓女日相随,妆成照水竞来窥。
江波澹澹芙蓉发,绿岸毵毵杨柳垂。
一朝物变人亦非,四面荒凉人住稀。
意气豪华何处在,空余草露湿人衣。
此地朝来饯行者,翻向此中牧征马。
征马分飞日渐斜,见此空为人所嗟。
殷勤为访桃源路,予亦归来松子家。
当年襄阳雄盛的时候,习家池是何等的风光,水波荡漾间,荷花满池,清香飘散。杨柳袅袅,垂荡在水面,一池春水尽染碧翠。那摇曳生姿的女子竞相在池边看着自己于池水中倒映的倩影,顾盼生辉。然而繁华终逝去,徒留荒草连天。诗歌开篇只简简单单“当昔”二字就直接告诉我们这一切美好都已经是过往,此刻早已经是“一朝物变人亦非,四面荒凉人住稀。”无独有偶,同为唐代诗人的杜审言也有“习池风景异,归思满尘埃”[1]486的感怀。这说明在孟浩然和杜审言的时代,习家池已是破败之象,奇怪的是,晚于孟浩然与杜审言的皮日休却有一首专为习家池清丽晨景所作诗歌,赞美其景[1]494:
清曙萧森载酒来,凉风相引绕亭台。
数声翡翠背人去,一番芙蓉含日开。
菱叶深深埋钓艇,鱼儿荡漾逐流杯。
竹屏风下登山屐,十宿高阳忘却回。
苍翠的连绵群山,迂回的潺潺清流,艳丽的娇俏芙蓉,灵动的调皮小鱼……各式各样的美从诗人笔尖溜出,于纸上尽情氤氲开来,令我们沉溺。更有晚至明代的诗人依然用笔墨绘制了一幅习家池旖旎的美景[1]477:
谷口一径入,苍山四面开。
中有习池水,水碧无尘埃。
泉源初喷薄,交流遂萦回。
飞鸟镜中度,行云天外来。
微风一荡拂,林影久徘徊。
寒光空心性,俯玩何悠哉。
爱此不能去,载歌写中怀。
岘山环抱中,习家池池水碧绿澄澈,飞鸟如在镜中掠过一般。绿树成荫,风过处,树影徘徊。水光潋滟中,人们心旌摇荡,以为这就是习家池最初美丽的身影,事实上,后世诗人笔下的这些美好,早已是多次修葺重建,努力复原的结果,距离它的真迹原貌,即使是无限接近,毕竟也无法完全等同。
人们希望将习家池复原,重现昔日盛况,恰恰是士人对“人生得意须尽欢”无限向往的一种表现。人们希望现世中一切美好都永不落空,希望觥筹交错,欢歌笑语夜夜不绝。可现世里,时空变幻,朝代更迭,在岁月河流的激荡下,很多事情都早已不复当年。曾经的宴饮之地如今已经是“流水成渠稻作畦”[1]500。曾经随微风荡漾摇曳的林影在诗人眼中已成“衰柳”,泉水蜿蜒之处已是“秋风禾黍”之貌。这些变化让诗人无限慨叹“兴亡多少伤心事,只有襄山汉水知。”[1]499因为对现世美好有向往,面对这些变化时才会有惆怅在心中百转千回。
除了习家池的景,还有很多诗人关注习家池的人。史书记载:“诸习氏,荆土豪族,有佳园池,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名之曰高阳池。”[2]1229这习家是荆楚地区的望族,与习家池的习氏名人相比,习家池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竟是一位客人,一位酩酊大醉的客人,他就是山简。山简,字季伦,“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字巨源)之子,永嘉三年(公元309年)镇守襄阳。习家池最灿烂的痕迹留在了山简纵情饮酒欢宴的那段日子里。山简将习家池称呼为 “高阳池”,大有取前世郦食其自号高阳酒徒之意。山简连带着习家池名声大噪,甚至在当时襄阳坊间就有歌谣传唱[1]460:
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
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
时时能骑马,倒著白接篱。
举鞭问葛强,何如并州儿?
这个家伙,醉到连头巾都倒着戴。魏晋风流人士,仿佛都喜欢用纵情任性的醉酒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放荡不羁。这样一种习池醉汉的形象反复出现在后世许多诗人笔下,唐代诗人李白,就有一首《襄阳歌》[1]464:
落日欲没岘山西,倒着接蓠花下迷。
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
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
鸬鹚杓,鹦鹉杯,
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
……
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
襄王云雨今安在,江水东流猿夜声。
诗人开篇就描写山简放诞率真引人发笑的醉汉形象,接着就抒发自己一日三百杯,誓与美酒同生共死的豪言壮语,这与他在《将进酒》中的“会须一饮三百杯”、“但愿长醉不复醒”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李白心中,无论他自己,还是山简,都是宁愿在酒醉的世界中放浪形骸,也不愿意在现实世界里谨小慎微。他们自由自在,“兀然而醉,恍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2]1376甚至到了明代,都还有人仿照歌谣形式写道:“谁家池?高阳池。日暮归,倒接篱。醉如泥,汝为谁?拍手歌,襄阳儿。”[1]477继续追念着习家池醉汉的传说。
还有些诗人,他们羡慕山简的任情任性,感叹自己“长年酒量如山简,却上篮舆恨独醒。”[1]496至于自己为什么做不到如山简那般真性情,诗人也借助诗歌有所抒发[1]473:
山公昔在郡,日醉高阳池。
归时夸酩酊,更问并州儿。
我亦爱池上,眼明见清漪。
二年始再往,一杯未尝持。
念岂公事众,又非筋力衰。
局束避世网,低回绁尘羁。
独惭旷达意,窃禄诚已卑。
因为无法完全摆脱俗世功名的羁绊,所以只能够羞赧地在现世对彼岸的山简报以向往之情,说一句“我亦爱池上”。 对于他们而言,可能在不远的岘山之上,有他们更为看重的东西,那就是堕泪碑。
二
堕泪碑,建功立业的象征。堕泪碑历史上曾经被损毁,但很快得以重建,这也说明建立功业一直是传统士人心头重中之重。
俗世功名的羁绊,对这些以山简为歌咏对象的诗人们来说,并不遥远。史载:“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2]1022羊祜,字叔子,也曾作为将领镇守襄阳。这一点经历,他与山简是相似的。所不同的是,山简是在悠悠习池水畔以狂饮放浪的形象让后人追忆,而羊祜则是在苍苍岘山凭借功德美名令世人膜拜。史载“(晋武)帝将有灭吴之志”,才会“以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但羊祜在镇守襄阳期间,并非按一般武将争取军功的思维行事,他“开设庠序,绥怀远近”,“ 垦田八百余顷”,羊祜刚到此地的时候,“军无百日之粮”,但经过他的治理,军队“有十年之积”。
羊祜本为灭吴而去,他对待吴人“开布大信,降者欲去皆听之”,终结果“自是前后降者不绝”。“人有略吴二兒为俘者,祜遣送还其家。后吴将夏详、邵顗等来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属与俱。吴将陈尚、潘景来寇,祜追斩之,美其死节而厚加殡敛。景、尚子弟迎丧,祜以礼遣还。吴将邓香掠夏口,祜募生缚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甚至羊祜在吴地境内若收割了当地的谷稻之后,必定要以其他方式偿还,正所谓“祜出军行吴境,刈谷为粮,皆计所侵,送绢偿之。”“每会众江沔游猎,常止晋地。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封还之。”最终的结果“吴人翕然悦服,称为羊公,不之名也。”[2]1022
正是因为这样,后世那些常怀建功立业之心的士人才会将羊祜作为楷模,才会沿袭将他和诸葛孔明放在一起的惯例[1]486:
秣马临荒甸,登高览旧都。
犹悲堕泪碣,尚想卧龙图。
城邑遥分楚,山川半入吴。
丘陵徒自出,贤圣几凋枯。
野树苍烟断,津楼晚气孤。
谁知万里客,怀古正踌蹰。
诗人缅怀像羊祜、孔明那样的治世良材、有为将帅,感怀如此贤臣良相愈加难得,想象着当年羊祜在此地厉兵秣马的情形,尽管如今看到堕泪碑有丝丝悲伤,尽管如今昔日的圣贤已渐凋零,但诗人依然会在登高俯瞰旧都时满怀踌蹰,也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像自己凭吊的先贤那样建功立业。
甚至一向以山水田园诗著称,曾隐居鹿门山的孟浩然也感叹[1]487: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诗人虽然在开篇让我们感觉这时光中的朝代更替、人事变迁仿佛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却在末尾一句“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让我们感受到他内心缱绻的情怀。孟浩然没有像陈子昂那样道出自己也踌躇满志想要一展抱负,他只是落泪了。然而他因何落泪,在几百年后尚留人间的“羊公碑”面前,和功成名就、垂范千古的羊祜相比,他的心中究竟在慨叹什么,这一切早已不言而喻。正所谓“山光葱蒨水清冽,天长地久无时别。古人今人空茫茫,唯是功名不能灭。”[1]470以羊祜为楷模,是诗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而恰恰是个人理想与现实间那难以逾越的沟壑才会令人们潸然泪下。
三
习家池,北枕堕泪碑,二者在有些诗歌里会同时出现,有诗云:“临溪犹驻马,望岘欲沾裳……山公不可遇,谁与访高阳。”[1]461所谓“望岘欲沾裳”,就是在面对堕泪碑时回想羊祜的功绩。诗人唏嘘感慨,也希望寻得同路人共访高阳池(即习家池),只可惜山简已成书本中的名字不可遇见,知音已难觅。一首诗中,既有习家池,又有堕泪碑,或许也正显示了诗人在出世与入世间矛盾纠结的心理。
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有两首诗既描写了山公酒醉的形象,也提到了羊祜堕泪碑。奇妙的是,这两首诗中李白对待习池山简和岘山羊祜的情感居然有截然不同的地方。当我们将这两首诗摆在一起的时候,或许就更能体会诗人在出世与入世间纠结的情绪。在《襄阳曲四章》中诗人说[1]464:
襄阳行乐处,歌舞白铜鞮。
江城回绿水,花月使人迷。
山公醉酒时,酩酊高阳下。
头上白接篱,倒着还骑马。
岘山临汉江,水绿沙如雪。
上有堕泪碑,青苔久磨灭。
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
山公欲上马,笑杀襄阳儿。
诗中李白对山简醉酒的钟情跃然纸上,他甚至喊出“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的惊人之语,不必凭吊堕泪碑,无需追求俗世功名,只需醉倒在习家池畔,这倒是与他一贯狂傲自在的形象十分切合。但这真的是纯粹出于内心主动的抉择吗?同样出自李白之手,在《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他却说[1]465:
昔为大堤客,曾上山公楼。
开窗碧璋满,拂镜沧江流。
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
此地别夫子,今来思旧游。
朱颜君未老,白发我先秋。
壮志恐蹉跎,功名若云浮。
归心结远梦,落日悬春愁。
空思羊叔子,堕泪岘山头。
大堤是当年狎客商贾云集之地,山公楼自然指的就是宴饮之所习家池,以“昔为大堤客,曾上山公楼”作为开篇,只一个“昔”字和“曾”字,诗人把自己醉酒欢宴归为了过去,那么诗人现在在做什么呢?诗人在感慨,感慨心中壮志蹉跎难以实现,感慨世间功名如浮云般难以把握,正所谓“朱颜君未老,白发我先秋。壮志恐蹉跎,功名若云浮。”念及羊祜功绩,自己也只有黯然垂泪伤神。一位诗人,同样的景物,却是两种不同的态度与情怀。诗人此前所说的“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究竟是自身主动的选择,还是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而为之?这个问题至此似乎也愈发清晰。我国古代的传统士人,无论嘴上说得多么旷达洒脱甚至狂放,其内心深处总还是想着建功立业的。内心的渴望越强烈,这种纠结与矛盾的痛苦感就更会灼烧内心。
人们在习家池和堕泪碑之间徘徊,仿佛就是在出世与入世当中游走。其实,无论是习家池象征的狂欢与飘逸,还是堕泪碑指代的慨叹,不论是个人的荣辱,还是朝代的兴衰,这一切都会在岁月的长河中渐渐湮没,正所谓“吊罢羊侯庙,来观习氏池…… 古今人不见,半亩自清漪”[1]504、“独有习家池上月,不随江水向东流”[1]504、“兴废不关池畔柳,客归依旧舞蹊头。”[1]499只有那半亩清漪、当空明月和池畔垂柳,是永恒不变的存在。
[1] 陈锷.襄阳府志[M].乾隆《襄阳府志》点校整理工作委员会,整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2]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