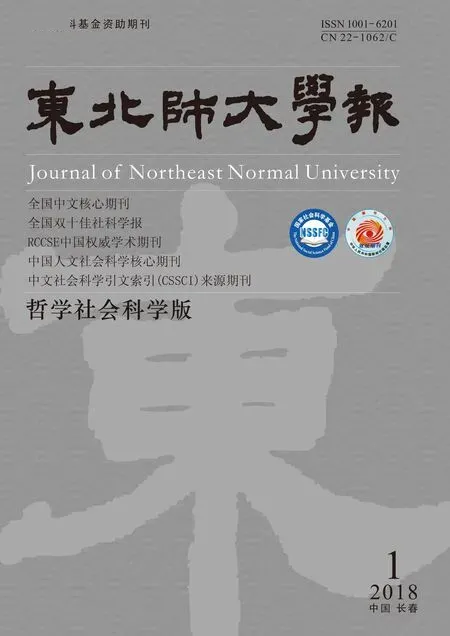萨拉·凯恩戏剧中的生命哲学观
——以后期剧作《渴求》与《4.48精神崩溃》为例
于 文 思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直面戏剧”(In-yer-face)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剧场,它是以打碎生活中的温情,给观众展示残酷场景为特征的一种戏剧形式。其代表作家萨拉·凯恩(Sarah Kane)的剧作以其粗硬的语言、残酷暴力而有冲击力的舞台视觉形象,带给观众震撼心灵的痛楚与净化。通过大量暴力的场景,凯恩着意展示出一种具有生机的“伦理灾难”:“在残缺的肢体间依然有伦理存在,因此对生命与希望的追求也就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的可能性”[1]37。对生命本质的不懈探问是凯恩在其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内驱力,并促使她完成了由前期的“新野蛮主义”(the New Brutalists)向后期“难以捉摸的凯恩”(the elusive Sarah Kane)的过渡。前期的凯恩以阿尔托的“残酷戏剧”为理论依据,注重展现极端暴力的场景,三部作品(《摧毁》《菲德拉的爱》《净化》)中大量的肢解、吃人、死亡的场景带有鲜明的情绪指向,意图用野蛮行为释放出受压抑的潜意识,揭开社会的虚伪层面,真实地面对生命的残酷性。而对生命本质的哲学性探索体现在其后期的两部剧作《渴求》与《4.48精神崩溃》中。事实上,自《净化》开始,凯恩已取消了极富冲击力的舞台行动,取而代之以诗意、朦胧的语言,极简的舞台与人物设计,交错的时空机制,看似凌乱而实则富有节奏的话语结构,构成了对生命从舞台形式到戏剧内容的综合性思考。同时,《渴求》与《4.48精神崩溃》中加入了大量关于死亡的独白式探讨,以“没有角色,只有语言和想象”[2]111的戏剧技巧消解了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边线,揭示出个体具有身心二重创伤的精神体验。
然而,单纯将其中的死亡描写看作是凯恩的“自杀宣言”和“75分钟的自杀笔记”[3]9未免有失偏颇。凯恩对死亡的书写透露出她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并将压抑与释放、快感与创伤、记忆与遗忘、希望与绝望等关系在存在论层面进行探索,流露出生命与死亡具有“同体异构”的特质。凯恩正是抛弃了生命与死亡的二元对立关系,以求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这也重新回望了西方哲学传统,即对“人”的思考。
从戏剧话语到舞台结构,凯恩以审美救赎书写了个体在后现代社会中遗失的事物:“生命”本身。她将生命作为创作主体,在极具爆发性的戏剧张力、抒情的诗意、激越的情感中透出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在《渴求》与《4.48精神崩溃》中,剧中人物只是附属,而生命成为舞台上不在场的永恒主角,同时,生命被“元叙事”隐于文字背后,反而将诸如死亡、暴力、残酷等不可叙述的内容置于台前,通过多重映射隐喻后现代世界中伦理结构的崩坏。例如,《渴求》的结尾有“落入光明……如此快乐。快乐而自由”[4]200;《4.48精神崩溃》中反复提到“记住光明并坚信光明”[4]206,都使凯恩超越了戏剧形式上的暴力与绝望,在“生死”这一极端的二律背反下尝试去克服陷入机械论世界。
在这两部剧中,凯恩将“生死一体而两面”的哲学议题置于戏剧“前文本”,通过特有的时空结构、更为简洁而诗意的话语重构后现代语境下的生命主题。同时,凯恩采用了全方位敞开的极简舞台,使听觉取代视觉成为话语中心。在凯恩看来,生命是可以倾听自身的主体,如果戏剧成为能够“听到一切”的作品,并“使作品对于倾听而言完全透明”[5]127,那么戏剧就会呈现出某种复义性而使观众将自身投射其中。通过意识流般的戏剧话语,凯恩跨越了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边境,弥合了生命时间与戏剧时间的裂缝,在自我追寻、自我救赎之路上传达出她的生命哲学观。
一、生命的延异性:从过去到未来
《渴求》与《4.48精神崩溃》是两部以话语占主导地位的剧作,通过角色间话语的延异,凯恩使语词与生命达到异形而同构。大段的独白与对话论题隐喻了生命处于时间与历史的进程中,“生命历程是某种具有时间性的东西……我们的生命所具有的特征,就是存在于现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6]45-47“延异”意味着生命随意识而不断跳跃,并与他人生命形成碰撞的状态,在戏剧上表现为意识流式的戏剧话语,辅以二声部、三声部式的有声演出,营造出流转而共鸣的效果。正如阿尔托所言:“使有声语言成为形而上学,意味着让语言表达它通常不表达的东西……使语言恢复有性震荡的潜力……”[7]42。《渴求》以语言的韵律感与节奏性来代替文字本身的意义;《4.48精神崩溃》则成为一部消解意义的“元语言”戏剧。
常规话语的消解在时间层面构成了话语与意识的“双声并置”,通过文本拼贴、意义的碎片化,在戏剧形式上实现音乐性、节奏性和诗意性的交融。碎片式的戏剧话语揭示人在潜意识中的印象式画面,它与个人对时间的体悟——流动的、无意识的、循环的——构成了平行结构。时间意识是个体认知自我的原点,因为“它触及了自我本身的这种原构成”[8]533,使个体得以将生命感知为一个连续统一体。这两部剧作打破了时间的连续性,让观众在断裂感中体验到焦虑,反思自我生命的不完备。
在延异性的书写上,《渴求》以由少年到老者的人生交织倾诉展现,而《4.48精神崩溃》则是由黑夜眺望白天的个人时间体验。通过以符号取代人物身份,凯恩消解了“能指—所指”的确定关系,以此颠覆叙事真理的可靠性。随着角色间话语的连接、打断、插入等,《渴求》表现出“叙事可靠性与生命体验悖反”式的生命哲学观,建构起一个晦涩而虚空的生存环境。延异性的终极表达是诗性话语,因为诗是渗透在人本性中的能传达一切显露事物的词汇。
《渴求》以“诗性话语”特征表现了延异性的第一层次。“诗性话语”主要表现为语词的朦胧与非理性、结构的往复、韵律与节奏的流畅、情感的含蓄混沌,以及这些形式特征中包含的生命价值。《渴求》中的四个角色构成叙事上的四重奏,在话语指涉的流转中表现出整部戏剧的流动性。人物在叙述自身时被戏剧化,而其行动中构成的场面又使得时间可以延续,因此叙述行动与其个体生命之间构成一种互文关系。
这种互文关系建构在悬置同一性和连续性的基础上,以语言的支离破碎暗示时间结构看似毫无规律却持续不断的运动,而产生意识的“绵延”效果。柏格森认为,绵延是“不借可以算出的力量而流向一个不能确定的方向”[9]28,并使个体对世界的认知成为其自身真理的唯一来源。生命的延异性同时指向未来与死亡,比如A说“真理是简单的……死亡是一项选择”;C 说:“彻底的精神崩溃是让所有人失望的底线”[4]160等,使无动于衷的冷漠与生命的极限条件相融合。通过知觉,四个叙事声音既保持独立性又处于同一叙事场域内,“把这些成分放在同一领域……就使成分之间的邻近性和相似性成为可能。”[10]40C说:“我要我的肉体感受如同我的心灵感受”,而A 眼前出现一幅一个被战争烧得一丝不挂的越南女孩的凄惨照片[4]160。两种不相关的叙事在感知层面被纳入同一场域,以战争的残酷和龌龊不堪的生存环境展现生命的艰难。不确定性将个体与周围之物形成整体,“我”则寓于时间之中并以虚无、否定的方式去理解生命,即时间被悬置。
《4.48精神崩溃》以“时间悬置”表现延异性的第二层次,即摒弃线性时间,使过去、现在、未来三重时间凝聚于一点。这是一部没有角色名称,没有分场次,只留下大量混乱的独白和对白的戏剧。4.48是指凌晨四点四十八分,此时人们的生理与心理容易达到混乱的极限而产生自杀行为。凯恩以此剥离了生命的时间属性,借“死亡”来唤起观众对生命的珍视。在该剧中,所有的回忆与期望被用以解构话语逻各斯中心主义,经过不断延异而将话语建构成一个不稳定的模型,使“生”与“死”在这一模型中交替反复,并在舞台设计上得以体现。该剧的导演詹姆斯·麦克唐纳采用了并置式舞台:一部分是一位精神患者崩溃时的混乱独白,另一部分是患者与咨询医生。如果将整部戏置于被悬置的时间轴上,看似各自独立的两部分实则是一个具有因果逻辑的整体。四点四十八分是病人醒来的时刻,对死亡的渴望是她疾病的结果;而医生与病人的对话则是她对过去的回忆,是她精神彻底崩溃的原因。将因果置于舞台的同一幕,使过去、现在、未来并置展开,揭开了隐秘于人内心深处趋近死亡与渴求生命的同构。
在因果并置的舞台上,通过回忆,现在将选定的记忆写入其中而呈现在舞台上;通过与未来相连,现在的行为与选择决定着未来的前行方向。因此,《4.48精神崩溃》可以视作凯恩对生死关系的一次反思:只有将生命与死亡置于同一时间结构中,生命才有可以追寻的永恒价值。凯恩关注人普遍的存在状态和死亡,尤其是人性的缺失和精神的绝望,但她赋予虚无以对现实生活的反思与向往,让叙事声音在向着未来流动之中“填之以虚空,满足于无物”[4]175。
二、生命的同一性:从自我到他者
在凯恩的作品中,生命的延续性脉络包含了他人与自我在生命的流动中相互指涉、相互照应,演绎出个体面对生命困境时的“同一性”状态。在《渴求》与《4.48精神崩溃》中,凯恩以取消客体、悬置意义、互文拼贴等,隐喻生命之间界线的消融。通过逐步取消戏剧行动和视觉效果,以原初状态被展示的个体生命之间,在时间上存在着相互联系。《渴求》中的老女人M的悲剧暗示了年轻女子C的未来,年轻男子B的现状又可能是成年男子A的过去;《4.48精神崩溃》中同一个体的过去与现在被分割为经历着同样痛苦的两个人。借这两部戏,凯恩探讨了“同一性”的不同范畴:即不同个体间的交融与自我的不断整合。
《渴求》通过四个生命不同阶段的个体探讨生存的意义,并以不同个体间的相互指涉来打破自我与他者在生命中的隔阂。凯恩以戏剧设计上的模糊性消除这种隔阂:该剧没有场幕划分,没有完整情节和背景介绍,角色也仅以字母来命名。四人的话语指涉实现了由身体意象到文字意象的转变,构成一个无法逃离的生命循环。该循环暗示了人一生所必经的过程,但与正常的线性生命发展历程不同,它是无始而无终的,四人的身份差异构成了循环得以运行的动力,这种动力表现在个体对他者的整合上。而事实上,在这一动力系统中,四人虽在行动力上略有差距,却又在总体上保持了某种平衡,因而使“整合”始终处于一个将来时的状态。剧中唯一渗透出的四个人的确定身份是性别,因此以性别结构来探讨这一循环模式,并分为纵向关系(异性之间)与横向关系(同性之间)。
纵向关系一向被讨论得比较多。比如桑德斯认为,M是一个老女人,渴求从年轻人B那里得到一个孩子;B对M开始时冷漠,后来却被对M的依恋所取代。老年男人A和青年女子C之间是夫妻关系,也是不平等的虐待性关系[2]105。胡开奇则给出了几种猜测:包括“两对夫妇的叙谈,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崩溃或甚至是从未相遇的四个人相互重叠的情感。”[11]298这样,该剧中M—B与C—A两组关系互为指涉,以性别、年龄的错位颠倒构成镜像。叙事模糊了人物的言说与倾听,表现出某种主体间性,使彼此成为对方的参照。同时,凯恩抛弃以身体为标准衡量“存在”,而将生与死置于等价地位,“有的人活着可已经死了……”,因而时间构成了封闭的循环:“因为爱本质上渴望着未来……时间在逝去而我没有时间……”[4]171。在这种结构中,凯恩将个体之间的封闭性与同一性相关联,塑造出两组想要打破生命界限的桎梏关系。而横向关系补充了作为单向度的时间的指向性。凯恩曾提到:M是母亲(Mother),C是孩子(Child),B是男孩(Boy),而A是虐待者(Abuser),那么C—M与B—A就成为同一时间轴上先后出现的节点。M不断朝向死亡,预示着C的未来;而B不停抓住生存的可能,则重复着A的过去。通过动作化的话语,剧作消融了自我与他者之间在暴力、胁迫、纠缠上的界限,从而将四个角色逐渐融合为统一的生命体。
《4.48精神崩溃》中的无角色设置使得生命状态能自由切换,并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交替流动。叙述声音在精神崩溃者、医生和病人之间切换,而这三个声音又实可看作一人。通过在一个确定时间的回忆,过往不断以延异的方式呈现,叙述者被置于叙述话语的中心,并随叙述的循环不断脱离能指链,最终以绵延的形式重叠过去与现在的自我。由此,文字的意义被解构,而生命却以最为本质的形态不断涌向现在。剧终的台词“请打开帷幕”[4]245成为这一循环的结点:这是意识中不可见自我的回归,打破记忆的屏障,真实地进行自我审视。在“自我审视”后面加上大量旁白并辅以缺失的场景,将叙述者置于对话的中心,使观众与叙述者在情感上实现同构。全剧不时出现“自杀”“崩溃”等字眼,将叙述者的伤痛带入观众眼前,并以持续不断的效果作用于观众,从而将伤痛由叙述者自身传达给观众以实现移情。同时,台词大量使用第二人称“你”,不断以高强度的信号冲击注意力紧绷的观众,迫使他们对叙述者的内心世界产生移情效果。在叙述者内心经历大量话语与沉默的交替中,观众将这种内心的挣扎与寻求逐渐转移至自身,与叙述人之间构成生命的循环。同时,凯恩借这种循环模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舞台内外区分,打破自我与他者的界线,让观众走入一次由压抑、孤独、绝望到寻求希望、光明与爱的生命历程。生命的同一性只有在相互理解和转换视角上才得以体现,并达到洞见生命奥秘的效果。
三、生命的循环性:从死亡到新生
在打破个体生命的界线之后,凯恩的深层立意是置生命与死亡于同一循环中,使死亡成为生命的过程而非终点。《4.48精神崩溃》中的叙述者既渴望生存又期盼死亡,以自身为载体构筑生死之间的张力。《渴求》中的四个人以一系列暴力话语与蕴含着对真诚与爱无限渴望的话语相交织,揭示了纵使暴力无处不在,也无法泯灭回归生活的盼望。在经历了《清洗》那种超乎恐怖的舞台设计后,凯恩选择了淡化舞台视觉形象,将死亡置于戏剧的“崇高”层面,从而达到海德格尔提出的“终有一死者乃是那些能够体验死亡本身的人”[12]211。凯恩以“去弊”的方式将死亡与生命同时呈现,并刻意模糊二者的界限,使观众在面对死亡的不可见层面得到情感的净化,在这种具有不可表现性的崇高中看到生死实为一体。
在凯恩看来,当下是一个客体世界凌驾于人类之上的时空,死亡带来的绝望体验成为个人感知主体性必不可少的步骤。通过诗意叙事,凯恩向观众展现了不可言表的生命体验,在原型层面上揭示暴力与生俱来的根源。纵观凯恩的五部剧作,“暴力”主题贯穿始终。区别是:在前三部剧中,暴力表现为死亡将生命从躯体上肢解,呈现出“剥离”状态;而在后两部剧中,暴力则表现为死亡将生命重新赋予躯体,呈现出“融合”状态。《渴求》与《4.48精神崩溃》分别对应着“毁灭与温情”、“求生与弃世”两种与死亡有关的主题,死亡由单纯“去生命化”变为“整合生命”,从而使自身不再具有终结性。
《渴求》以对爱与温情的解构将生命由“生存”推向“死亡”。狄尔泰说:“理解过程所提供的东西从来就是对于生命的各种表达。”[6]73其叙述者以话语将自己的感觉行动化,构成可感知的生命体验。这一不断趋向死亡的运动过程正是在“渴求”的驱使下进行的,即四个角色之间不断期待着向对方的身份靠近却无法达到彼岸。凯恩在设计角色身份时,有意让角色带有某种趋同特质,甚至可以在超性别的层面上达到某种相似。这种相似正是角色渴求他者的原动力,也是生命迈向死亡的初始动力。同时,凯恩所描绘的生命体验带有暴力与毁灭的特征,其形式与内容兼具性变态、违反常规与禁忌,使生命走入不可逆转的绝境。
“不可逆转”的境地是《渴求》文本的表层,而在其下隐藏的“次文本”中则蕴含着凯恩对生命的价值判断。通过建构一系列从封闭到开放的叙事环境,表层文本中的绝境与次文本中的渴求被置于同一对话框架之中循环流动。循环性比前两个特性更强调时间的作用,其表现却以这两部剧作的“无时间性”为特征。时间与生命相联系,“无时间性”是精神分析层面的死亡,它是“力比多循环中的构成性原则”[13]124。四个叙事声音共同特征是“面向死亡而共在”,即处于同一生命伦理层面并具有某种“死亡本能”。剧中的叙事真伪莫辨,它所制造的死亡幻象被还原成了本能,与生存论意义上的死亡含义不同,叙事幻象超越日常的生与死,进入无意识所驱使的死亡本能领域。在该场域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拉康的“镜子辩证法”,它表明个体在有死亡或意识到时间之前,死亡本能就在起作用。正如前文所言,两组叙事声音呈现出相互映射的关系,横向关系的同性别组(M-C、A-B)具有拉康所言的镜像关系;而纵向关系的异性别组(M-B、A-C)则具有包含恐惧根源的破坏关系。C与B分别是女性与男性的年轻时态,亦可被理解为儿童状态(Child、Boy),在他们的反射意象中,M和A就是他们所见到的“主人的意象”,并“就它受制于这个意象而言,儿童就处于死亡的在场中,为死亡意识以及因此而为时间意识奠定基础。”[14]130而M与A在朝向未来的同时代表了时间的消逝与死亡,C与B认可了这个“他物”,也就认可了他们所代表的“无时间性”,成为所认可却永远无法到达的位置。因此,C与B一旦将想象之中的象征(M与A)认可为自己,也就随之将自我代入他者的经验之中。
因此,死亡本能被拉康定义为“在想象与象征的结合点上……构成了人类主体的基础性地位”[14]172,它构成了主体的时间感觉。在剧作中,B与C的时间感觉来自A与M,而后两者的时间事实上是“无时间性”的。C与B对死亡的恐惧与其对自身“身体”的眷恋相关联,他们“从心理上从属于自恋对于损害自己身体的恐惧”时,实则是对死亡的恐惧起源于对身体的损害。C与B的身体被破坏的来源分别是A和M,后者对前者的伤害成为前者对死亡(时间性)恐惧的空间形式,因为C与B已经在无意识中认可了A与M构成的象征域。心灵创伤的因果性决定了主体自身时间结构的形成,无时间性意味着“无限”,而无限是《渴求》全剧中最重要的一份“渴求”。生命的循环性是“无限”的一种表达,然而凯恩先入死境而后渴求新生的做法,是通过死亡联接起了每一个有限性的生命。
在凯恩看来,后现代社会带有精神幻灭与爱的丧失等特质,因而暴力与绝望易成为被描绘的对象。《渴求》中探讨的生与死,是凯恩对后现代精神困境的一次回答,剧中人物的暴力与温情不断交替,用以隐喻后现代社会中暴力主体的转换。通过颠倒、混乱与随机,戏剧行动上的非理性甚至非人性,剧作展现出四个不同个体中蕴含的相同灵魂合为一体的循环叙事。在场的每一个叙事者随时都可以变成叙事的接受者或对象,其情感、话语、行动的指向却始终没有变化。A、B、C、M四人处于同一生命伦理的层面,在生存论意义上可被视为统一个体,暗示四人共同构成了一个大的生死循环。凯恩在看似没有终极意义的循环中以爱与温情建构生命的超越性,通过后现代话语的叙事策略,以剧中角色的身体作为叙事载体,渗透出后现代思潮对生命价值的反思。同时,凯恩以“非理性与理性”、“施虐与受虐”两组关系的相互转化,将无所不在的性与暴力和潜藏于其下的爱与温情加以同构,使生命循环在意识层面一样可以运作。
《4.48精神崩溃》对生命循环性的探讨实则更为具象化,它以“求生与弃世”间的不断转化来加深生命意义的探讨。正如爱德华·邦德评价此剧时说:“(它)已从对死亡、缺失与荒芜的痛苦的描写变成更有意识的生活的深刻探讨。”[2]116《4.48精神崩溃》并非单纯描写精神抑郁者对即将逝去的一切所感到的绝望与压抑,而同样强调她在自我寻求与恢复正常生活之路上所经受的痛苦。叙述者以“我深感前途无望并无药可救……我今年将自己托付给死亡”[4]216-218作为自我陈述的开始,在不断暗示自己死亡的过程中又不断追寻着求生的可能。一方面,医患关系可以作为叙述者的想象产物,“医生”是其求生意念的具象化;另一方面,叙述者反复言说“记住光明并坚信光明”[4]240,这正是凯恩心中真正的生命观的表达:不要被死亡的表象所欺骗,坚信希望与爱才是治愈的方法。通过这部剧,凯恩明确传达给观众:伤痛固然存在却绝不消极,它同样是证明自我存在的方式,人只有在认识到伤痛的意义时才能正视自我,去追寻生命中的希望。
《4.48精神崩溃》亦是凯恩在经历自我反思后对“存在”与“生命”的回答。在《渴求》完成后,凯恩意识到传统的戏剧方式越来越无法表达出极致化的生命体验,最终她选择了全部以语言而非场景展示生命意义。剧中的独白叙事以模糊现实和幻象的界线为切入点,在自己的空间中使一切有形的事物坍塌。凯恩以去场景化的方式将精神世界呈现在舞台上,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了与现实的沟通和与观众的交流。剧本全篇都仿佛是在暴露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医生就像现实世界的代表,在实现与患者内心交流的过程中扮演着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沟通者角色。患者从怀疑医生到尝试治疗,再到承认医生、解除医患对立关系的过程就像是精神失常患者渐渐辨清梦境与现实的差别。凯恩认为“回到心智正常的唯一方法就是将身体和情感、灵魂以及精神相沟通”[2]113,从《渴求》到《4.48精神崩溃》,凯恩不断挑战剧本创作晦涩程度的极限,同时又希望将剧作的深刻意义传达给观众。
《4.48精神崩溃》一剧的结尾在求生与死亡、绝望与希望这一主题上不断出现交替对话的声道,让同一叙述者发出不同的对话,使主题也随之上升。从“别看我”到“注视我”;从“别碰我”到“你抱着我/永不放松”再到更为直接的“我没有死的欲望/从未自杀过”[2]243-245,两种声音的交替不断强化出对生命的渴望。可以说,绝望与死亡是凯恩对生命诠释必不可少的部分,通过死亡审视生命的意义,并使观众更为深刻地领悟到生命中痛苦的必要性与积极意义,是凯恩的生命哲学所追求的。
萨拉·凯恩后期的两部剧作是对她早期剧作内涵更为抽象的表达,流动着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在《渴求》与《4.48精神崩溃》中,尽管绝望、暴力、死亡以更为直接的话语形式冲击着观众,但对光明、爱与希望的渴望也不断强化,凯恩正是以死亡为表层,以生命的意义为指向,构建出她的生命哲学观。在形式上,她打破“第四堵墙”,将观众引向叙述者本身,随同叙述者一起审视自我,直面自我内心的创伤。在内容上,凯恩不断深化主题,使观众意识到伤痛与死亡背后依然隐匿着爱与希望,只有坦然正视死亡的存在,生命的意义才会得以完整。通过生命的流动性、同一性与循环性,凯恩试图在后现代语境下重塑一条自我救赎之路,以对抗人类在面对自我存在时的困境。因此,这两部戏并非如表面般充满幻灭,而是在更深层次上以坦然面对死亡的心态,将个体生命的深度、广度进行延展,在更为广阔的生命层面上它们充满希望。从这一意义上,死亡被凯恩演绎为新生的必经之路,是治疗心理创伤的必要因素。从早期戏剧对恐怖主题的探寻,到后期用戏剧直面创伤,凯恩赋予当代英国戏剧的“暴力传统”以新的内涵,即对生活本质与意义的重新唤醒。
[1] Urban K.AnEthicsofCatastrophe.[J]PAJ.No.69(2001)
[2] Saunders G.Lovemeorkillme:SarahKaneandthetheatreofExtremes[M].Manchester:Manchester UP,2002
[3] Clapp S.BlessedaretheBleak.[M].Observer Review 2 July.2000:9
[4] Kane S.CompletePlays[M].London:Bloomsbury,2006.
[5] Szendy P.Listen:AHistoryofOurEars.tr.Charlotte Mandell[M].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7.
[6] 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M].艾彦,逸飞,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7] 安托南·阿尔托.残酷戏剧[M].桂裕芳,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
[8]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9] 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M].刘放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0]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1] 胡开奇.萨拉·凯恩戏剧集译后记[Z].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2]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3] Laplanche J.LifeandDeathinPsychoanalysis.tr.Jeffrey Mehlman[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
[14] Lacan J.TheSeminarofJacquesLacan1[A].Freud’s Paper of Techniques,1953-195.tr.John Forrester[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