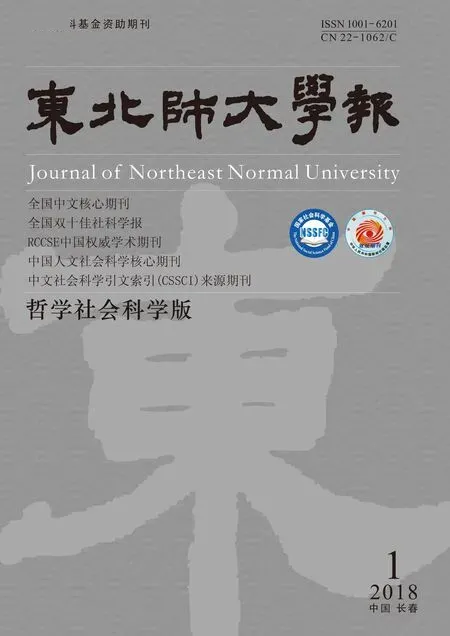德里达思考汉字的方法
曾 军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德里达在他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重要时期(1967至1972年)出版了一系列奠定“解构主义”理论基石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包括:《书写与差异》(1967)、《论文字学》(1967)、《声音与现象》(1967)、《撒播》(1972)和《哲学的边缘》(1972)。非常有意思的是,除了《声音与现象》中没有涉及对中国汉字的讨论外,其他四部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汉字和中国文化,显示了德里达在这一时期对中国问题的高度重视。这也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德里达并不懂中文,却在他的著作中频繁讨论到汉字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文化问题。那么,德里达为什么要去思考一个他并不懂的对象?他是如何思考的?这一思考究竟有何意义?我们该如何看待德里达思考汉字的方法?*美国汉学家王德威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名字叫《想象中国的方法》,因为他研究的是文学,文学是以想象的方式来探索这个世界的。哲学家不同,他的方式是“思考”。
一、德里达为什么必须思考汉字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期间,法国的学术思想极度活跃,一方面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光芒万丈,另一方面则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异军突起。但也就在结构主义如日中天,甚至一度成为“理论”本身而不是“理论之一”之际[1]23,德里达则敲响了结构主义的丧钟。与此同时,被誉为结构主义“四个火枪手”中的三位学者(德里达、拉康(Jaques Lacan)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集体叛逃*在一幅发表在1966年的漫画中,列维-斯特劳斯、德里达、拉康和罗兰·巴特腰围草裙在森林中席地而坐,成为结构主义达到顶峰的标志。但此时,除了列维-斯特劳斯之外,另外三位则早已有了异心,转向了后结构主义。。因此,这一时期也成为法国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型的关键时期。不仅如此,同样是在1967至1968年前后,法国学术思想还正在激进地“向左转”。正是在这洪波涌起的左翼思潮中,以“毛主义”和“易”、“儒”、“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给予法国思想和文化以巨大影响。正是在这一复杂的学术语境中,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出现在众多法国理论家的思想和著述之中。比较著名的当属德里达、拉康、克里斯蒂娃以及与他们有着相同旨趣的众多学者。比如说,拉康曾在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和程抱一(François Cheng)的帮助下研读过中国的古代经典。并在自己的研讨班上,拉康曾就中国汉字展开过专题研讨。克里斯蒂娃早在保加利亚时期就已经接触和学习过汉语,到了法国之后更是与同样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的法国先锋派作家、《原样》杂志主编索莱尔斯情投意合。克里斯蒂娃不仅专门研究过汉语语法,在小说中有大量的中国元素,而且曾随《原样》代表团访问过中国,并撰有《中国妇女》一书,其中也不乏对汉字问题的讨论。此外,比他们更年长一些的波伏瓦早在1950年代就曾与萨特一起访问中国,在其《长征:中国纪行》中也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讲述的“文化普及”的意义上考察了中国的“识字”和“扫盲”运动。正是在这一总体性的时代氛围中,中国文化、中国革命等中国问题才不得不进入德里达的视野;德里达也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涉足自己不懂不识的中国汉字。
在《书写与差异》的中文版代序的访谈中,德里达详细回顾了1960年代法国学界的整体“氛围”:一方面是哲学的“终结论”,即弥漫在法国哲学界的“终结”或“死亡”的喧嚣,另一方面则是政治上的革命或反叛情绪。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对左翼思潮和中国革命的态度是相对比较暧昧并且很明显地保持着某种距离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正当“毛主席语录”在法国满天飞的时候,德里达仅仅在《撒播》一书的《户外工作,开胃小菜,超文本,前奏、书档、饰面·前言》的注释23中,引用了毛泽东“开中药铺”的比喻,而且其所做的解释与毛泽东的原意相去甚远,体现了“五月风暴”时期,德里达对左翼政治的疏离*文中德里达在分析“保存妥当的药房”(a well-kept pharmacy)时,特别引出了“‘中国’药房”( “Chinese” pharmacy)作为例子,并引出了毛泽东《反对党八股》中所开列的第五条罪状,并认为毛泽东反对形式主义时正处于一个非常黑格尔的阶段。随后便是对毛泽东这段论述的一大段完整引文。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德里达此时所征引的是1967年由中国外语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的Selected Work” of Moo Tie-tang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67),Ⅲ,60-611.。与之相反的,则是德里达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青睐,如中国的汉字。对德里来而言,摆在他面前的“一直有两个战场”;而他的理论姿态也是双重的:“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2]4德里达对汉字的关注即与他所开展的“解构主义”事业密切相关。他认为西方思想一直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统治之下,而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与人种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在《论文字学》一开篇,德里达即对题记征引三段引文做出了一个重要判断:“这三条题记不仅旨在关注时时处处支配着文字概念的人种中心主义,也不仅旨在关注我们所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即表音文字(如,拼音文字)的形而上学。”[3]3这正是由卢梭论述、黑格尔确认并在19世纪之后形成殖民主义理论依据的“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的严密的“文明等级论”(hierarchy of civilization)的观念体系:文字类型与民族类型一一对应,并具有严密的优劣等级:象形文字对应于野蛮民族、表意文字对应于原始民族,而表音文字则对应于文明民族。很显然,这一“文化自信”正是建立在将自我确定为“文明”,而将“他者”确定为“野蛮”的逻辑基础之上的。但是经历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西方知识界也开始对这一具有民族歧视性和文化优越论的观念体系展开批判性反思,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即从西方文化和社会各种现象中提炼出“文明走向自己的反面(即‘野蛮化’)”的内在逻辑。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则是试图从语言学切入,通过颠覆“拼音文字优越论”(即“语音中心主义”)来完成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很显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也成为质疑和颠覆文明等级论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近年来,针对“文明等级论”的持续性批判正在促成人文研究的范式的形成。如文学研究中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新的“世界主义”范式;历史研究也正在推动从“世界史”向“全球史”的转型。。
二、通过汉学思考作为哲学问题的汉字
德里达对汉字的最早关注可以追溯到1966年。是年3月,德里达在心理分析学院做了一次演讲,该文以《弗洛伊德与书写舞台》为题发表在《原样》1966年夏季号上。同年4月,德里达又在巴尔马(Parme)举行的国际大学戏剧节组织的阿尔托研讨会上做了题为《残酷戏剧与再现的关闭》的发言,后发表在《批评》1966年7月号上。这两篇文章后收入《书写与差异》一书中。这两篇文章中,均涉及的是弗洛伊德对汉语和汉字的两个重要看法:其一,汉语中对每一个汉字的理解需要在具体的上下文关系中才能确定;其二,汉字是表意文字,不同于埃及的象形文字[2]379,433-434。但是,如果仔细研读德里达著作中有关中国汉字的讨论,我们会发现,德里达所有的讨论都没有直接触及中国汉字本身。他所思考的主要是西方汉学中关于汉字的看法。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德里达先后引述了从卢梭、莱布尼茨到黑格尔再到索绪尔、弗洛伊德、谢和耐、索莱尔斯等一系列学者对于中文、汉字的认识和理解。书中也提到了《易经》等中国典籍,但也只是间接引用,并非直接讨论。真正直接引述中国理论家和思想家著作和思想的,只有在《撒播》中对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引用。对此,我们可以将德里达与克里斯蒂娃相比较,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克里斯蒂娃也在1969年出版了《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一书,显示出这一时期在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型的关键时期,语言学对法国理论的极端重要性。在本书中,克里斯蒂娃试图回答“学习语言学应该从何处入手”的问题,并明确了“对不同的文明里面发展起来的有关语言的思想史作一次系统的回顾”的视角。全书分三部分,分别是“语言学导论”、“语言与历史”和“狭义语言和广义语言”;其中第二部分“语言与历史”的第4节,即是对中国汉字的讨论,题目是“中国:文字是学问”。这一小节对中国汉字的介绍有几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是从现代语言学的视角对中国汉字的分析。因此,从一开始,克里斯蒂娃就注意到了汉语的汉字书写与口语的巨大差异,并从语音、语义和语法等角度剖析了汉字的特点。其二,克里斯蒂娃所征引的材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法国汉学对汉语和汉字的分析,包括戴密微、葛兰言、纪尧姆、梅耶、李约瑟、莱布尼茨、常业、谢和耐、路易·勒康特等等;二是汉语语言学相关文献,如公孙龙的《指物论》、许慎的《说文解字》、陆法言的《切韵》、司马光的《类篇》、郑樵的《通志》、周德清的《中原音韵》等。从这个清单来看,克里斯蒂娃对与汉语有关的中文文献和法国汉学文献的掌握远甚于德里达。其三,克里斯蒂娃此书侧重于知识性的介绍,主要是介绍西方汉学对汉字的基本观点,并结合中国的汉字文献加以佐证,因此,此文并没有表现出克里斯蒂娃个人的汉字观。
与克里斯蒂娃相比较,德里达对汉字的思考特点也比较清楚了:首先,德里达虽然思考的是汉字的语言学属性,但采取的却不是语言学方法。这看上去像一个悖论,实则不然。德里达的问题意识是从哲学而不是从语言学出发的。在德里达看来,语音中心主义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西方语言和文字上的体现。作为语音中心主义的表现之一,就是西方学者站在“拼音文字优越论”的前提下将“非表音文字”贬为劣等语言,进而形成西方思想(包含但不限于现代语言学)中语音与文字、声音与书写、表音与表意这一系列二元对立之间强调语音、声音、表音的优先性,而将文字、书写和表意降格为从属性和边缘性的观念体系。将文字区分为象形、表意和表音是语言学问题,所做出的是事实判断;但褒表音、贬象形和表意,则不再是语言学问题,因为这已经是价值判断了。因此,对价值判断的反思和批判,所需要的武器便不再仅仅是语言学,更重要的是哲学。
那么,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语音中心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否具有严格的对等性?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更多的时候是将逻各斯中心主义与语音中心主义和人种中心主义进行“三位一体”式的认定的。但这样做也会存在理论的疏漏:在使用“非表音文字”的民族国家中,难道就不存在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和人种中心主义了吗?很显然,德里达认为并不完全是。因此,在与《书写与差异》的中译者对话中,德里达强调,“我曾经尝试区分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我以为无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语音中心主义是可能存在的。非欧洲文化中也完全有可能存在给声音以特权的情况,我猜想在中国文化中也完全有可能存在这种语音特权的因素或方面。但中国文字在我眼中更有趣的常常是它那种非语音的东西。只是,在中国文化或其他文化中,赋予并非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声音某种特殊地位也是完全可能的。”[2]11这一表态表明,德里达关心的并非作为语言学问题的汉字属性,而是作为哲学问题的文字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问题。比如说,后来的汉学家顾明栋沿着德里达的《论文字学》阐发了“汉字颠覆口语与文字的主仆关系”因而通过汉字而走出语音中心主义是可能的这一观点*围绕西方汉学中对汉字的看法,顾明栋近年来撰写了大量论文,如《语言研究的汉学主义——西方关于汉语汉字性质的争议》(《南国学术》2014年1期)、《走出语音中心主义——对汉民族文字性质的哲学思考》(《复旦学报》2015年3期)、《重新审视语言的鸿沟——中西文字符号理论的比较》(《原创的焦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汉字的性质新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4期)。。但这却并非德里达关心的问题,他只是从哲学的推论而非语言学研究的事实判断的角度做出判断,认为即便是汉字仍然可能存在某种语音特权。
其次,面对西方汉学关于汉字问题的讨论,德里达是否有能力对这些问题展开回应和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对于并不懂中文的德里达来说,这无疑是有相当难度的事情。因此,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大凡涉及对汉语特点和汉字性质问题讨论和分析的部分,德里达只能大量征引相关的西方汉学文献,进而从中提炼并概括这些文献中关于可能被引入语音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讨论的一些观点;或者在西方汉学对汉字的不同观点中发现“对立”或者“裂缝”,进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让不同的声音发生碰撞与交锋,德里达自己则居于超然争议之外的立场,或者选择与自己观点相一致的看法,作为自己思想的佐证。这些观点虽然并不是所征引的汉学家思想的简单重复,但也并未构成研究的深化。因此,这些西方汉学的材料在德里达的著作中便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位置:德里达只能呈现西方汉学中对汉字的各种看法,但无法展开自己对汉字的思考。德里达所能思考的,仅仅是将这些看法区分为两类:一类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代表的,如黑格尔;一类是可以作为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部分理论依据的,如莱布尼茨。这一表现在《哲学的边缘》中达到了极致。该书有一篇题为《深坑与金字塔:黑格尔符号学导论》*这篇文章也是首先发表于1968年1月16日法兰西学院让伊波利特研讨班,正式发表于1971年的Epimethée。,大段引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历史哲学演讲录》和《哲学科学百科全书》中的对介绍中国汉字的段落。比如说在分析中国的甲骨文时,德里达仅仅谈了一句话,认为黑格尔对汉字特点的三个特点的描述——成规性(或变化缓慢)[immobilism (or slowness)]、外部性(或表面性)[exteriority (or superficiality)]和自然性(或动物性)[naturality (or animality)]——都可以在甲骨文的硬壳上被描绘出来,然后对这三个特点的详细分析完全就是照搬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历史哲学演讲录》中的大段大段的引文。虽然在征引这些相关材料的过程中,也不乏德里达“画龙点睛”式的解构式阅读,但很显然,德里达个人是无法从对汉字的语言学研究角度来做出分析和评判的。
最后,德里达也并非完全没有触及中国问题本身,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已经注意到以“汉字拼音化”(the phoneticization of writing )为方向的汉字改革运动。这正是建立在文字等级秩序观念基础之上的语言改造运动。这是与殖民主义运动中被殖民民族被迫放弃本民族语言和文化而以殖民国家的民族语言作为官方语言的语言现象相一致的,是建立在以西方文化代表先进文化,拼音文化代表优势语言的意识形态对现代性观念的影响上的。汉语拼音化运动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汉字拼音化(拉丁化)”最早可以上溯到清末。1891年,俞樾的学生宋恕提出“造切音文字”一说;1922年,钱玄同、赵元任等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上提出汉字拼音化动议,拟订了罗马字方案草案。此后陆续推出刘复等编撰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吴玉章和林伯渠等编撰的《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等。建国之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推进普通话、汉字简化、汉语拼音化等方案。直到1981年钱伟长主持成立中国中文信息委员会,开展汉字输入法研究,才真正化解了汉语拼音化的危机。虽然德里达并没有直接参与对这一运动的反思,但这一重大的现实问题显然已经进入德里达的视野。在《论文字学》的注释中,他已注意到了载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国际语言学研究》第7期(1958年5-6月号)的《汉字改革》问题[4]323。
通过汉学来思考作为哲学问题的汉字,这就是德里达思考汉字的方法。因为德里达不懂中文,所以他没有采取针锋相对的方式直接介入汉字性质问题的讨论,而是在众多西方学者对汉字问题的不同论述中迂回,寻找思想的分叉处,进而穿透笼罩在西方思想史中浓厚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迷雾。德里达思考汉字的目的也并非要真正学习汉字和了解汉字,而是要引入以汉字为代表的“非表音性”文字来动摇支撑拼音文字的“语音中心主义”的基础,进而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
三、通过汉字解构“文字等级论”
既然在德里达那里,汉字不是或者首先不是以语言学面目出现的,那么,德里达对汉字的理解,以及我们对德里达汉字观的理解也必须暂时将语言学的维度搁置起来。否则,我们便只能将问题意识停留在德里达理解汉字的“懂与不懂”、“对还是不对”这个层面上了。面对语音中心主义的拼音文字的“文字等级论”,德里达通过对汉字属性的辨析解构了基于表音文字(如拼音文字)霸权的“文字等级论”。
如前所述,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开篇即将卢梭的三种文字类型观(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选做了靶子,呈现了西方学术界中的“文字等级论”中的语音中心主义、人种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三位一体的观念体系。在《深坑与金字塔》一文中,德里达更是大量征引黑格尔著作的原文,用以印证一个核心观点:在黑格尔的符号学体系中,语言体系,也即语音体系,要比其他任何符号体系更拥有特权,也更加卓越。因此,口语优于书写、拼音文字优于其他书写体系,尤其是优于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但也同样优于数学书写、优于所有正式的符号、代数、通用书写符号以及莱布尼茨所排列的其他类型——正如莱布尼茨所说,拼音文字优于一切不必要的东西,“指声音”,或“文字”[5]88。因而“文明等级论”在语言学上的反映,即是“拼音文字优越论或特权论”,它是建立在语言文字的客观差异基础上的偏见和歧视。如果想要颠覆这一等级秩序,那就必须要从下面几个角度着手:如何重新评价汉字作为“非表音文字(即非拼音文字)”的“文化劣势”?反之,支撑拼音文字优越论或特权论的理由是否充分?进而,基于语言文字客观差异而形成的文字类型论是否能够置换为文字等级论?德里达通过汉字对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也正在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
第一步,解构“汉语偏见”。何为“汉语偏见”?即是欧洲人所形成的关于汉字的观点和幻觉。德里达虽然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很显然他自己并没有多少研究,而只是凭借他所读到的西方汉学研究中对汉字的一些印象式的描述或研究后的结论,加以汇总而形成的观念*“Although something of the Chinese prejudice of the West is discussed in Part I,the East is never seriously studied or deconstructed in the Derridean text.”,translator’s preface,b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Jacques Derrida.of Grammatology,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Plxxxii.。如将汉字简单划归为与楔形文字之类的象形文字具有同等性质的“低人一等”的文字类型;莱布尼茨认为汉字是“聋子的发明”,认为“中国人要花一辈子才能学好书法”;黑格尔也认为中国的汉字语法不够发达,中国的文化及其文字具有经验主义(自然主义、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数学化抽象)的特点,像汉字这类象形文字,只能适用于“中国文明这种停滞的哲学”,等等;还包括对汉字的“贬低”或“赞扬”的态度,都属于“汉语偏见”。在德里看来来,与“汉字偏见”同时,还有一种可以被称为“象形文字研究者的偏见”,这种偏见“远远不是从人种中心主义的嘲弄出发,它采取了过分赞美的形式。我们尚未完全证实这一模式的必然性。”[3]117
第二步,汉字属性的多重性。汉字究竟是象形文字还是表意文字?抑或两者兼有或者还有其他的属性?虽然德里达自己无法做出判断,但是通过对西方汉学文献的清理,他敏锐地发现,在汉字属性的识别上,无论是将汉字认定为象形文字,还是表意文字,都是有问题的。汉字以其笔画组合而成的方块字的形式,既具有象形的功能,又具有表意的作用;或者有的具有象形的功能,有的具有表意的作用。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已经注意到了汉字构造具有“文”的特点。“文”既具有象形性,又具有表意性。因而,德里达展开了对汉字的辩护:“我们难道因为‘文’这个词表示除狭义的文字之外的许多意思而断定中华民族没有文字?”[3]179到了《深坑与金字塔》一文中,德里达受黑格尔的启发,从汉字的起源和生成的角度来理解汉字的属性。他一方面注意到最早的汉字——甲骨文——已经具有了象形和表意的功能,另一方面还注意到《周易》中卦象的“一分为二”、阴阳组合、生成变易的特性,并天才性地将汉字造字法与卦象联系起来,认为汉字的“象形文字系统”不是简单的寻求与其所意指的自然万物或社会现实的“形象上的相似性”,而是试图采取一种绝对抽象的、化减为最小元素的、还原为最简的逻辑的方式来传达对汉字所欲承载的意义的理解。由此,这一兼具象形和表意功能的“文”更具有了生成性的符号学价值[6]96。我们暂且不论这一关联是否符合汉字形成史的事实,仅就这一类比性理解的思维而言,其实正好应和了由列维-斯特劳斯所建构的“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模式。卦象的符号学运作机制,具有类似“二进制式”的数学原理及“上帝语言”的双重特征,这些进一步强化了不懂汉字的德里达所展开的对汉字的神秘想象。进而,汉字便超出了“原始文字”范畴,进而以“人工语言”的方式参与到对“普遍文字”的想象性建构之中。
不仅如此,汉字的结构复杂性在于,汉字结构组合中还包含着表音的因素。“我们早就知道中文或日文这类有着大量非表音文字的文字很早就包含表音因素,在结构上它们仍然受到表意文字或代数符号的支配。于是,我们可以掌握在所有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发展起来的文明的强大运动的证据。”[3]135这是德里达引述谢和耐的汉字分析时做出的判断。作为一个20世纪的汉学家,谢和耐对汉字的理解比黑格尔要全面,也比莱布尼茨更深入。他不仅注意到了汉字的象形和表意的功能,而且注意到了汉字的表音因素。不过,在谢和耐看来,汉字的表音性与西方拼音文字的表音性有本质的区别:汉字的表音性并不具有支配性地位,相反却是受到了书写的压抑,因此“文字本质上削弱言语,它将言语纳入某个系统”*在本句中,构成与“文字”对应的不是“言语”(speech),而是“声音”,指的是与“书写之文”对应的“口头之语”。这在该书的法文版和英文版中都是一致的。法文原文是“L’écriture ne réduisait pas la Voix en elle-même,elle l’ordonnait à un système”(Jacques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67.P138.),英文译文是“Writing did not reduce the voice to itself,it incorporated it into a system.”Jacques Derrida.Of Grammatology, trans.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P90.。汉字虽然保留了表音的功能,但却从属于或者说受制于汉字的表意功能。因此,汉字的这种以表意性为主、表音性为辅的特点,才使得中华文明成为德里达所说的“在所有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发展起来的文明”。
第三步,将“表意性”、“表音性”置换为“表意价值”和“表音价值”。德里达引述索绪尔将人类的语言分为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并将汉字视为表意体系的代表的思想,指出索绪尔的这一体系的区分是建立在“言文一致,以言为基”的思想基础之上的。由于索绪尔确立了“将言语系统与表音文字(甚至与拼音文字)系统相对照”的目标,使得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里排除了表意文字的存在合理性,“这种目的论导致将非表音方式在文字中的泛滥解释成暂时的危机和中途的变故。我们有理由把它视为西方人种中心主义,视为前数学的蒙昧主义,视为预成论的直觉主义”[3]55。由此,德里达以索绪尔的“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二分法解构了卢梭提出的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的三分法。但是德里达并不满足。因为即使是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二分,也是建立在表音文字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索绪尔是以西方的拼音文字为标准来分析和评价“非表意性”的汉字或其他文字的。因此,所谓“汉字的属性”即是它的“非表音性属性”。这无疑是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偏见。
因此,德里达进一步指出,事实上,纯粹的表音文字或纯粹的表意文字其实是并不存在的。“‘表音’与‘非表音’决非某些文字系统的纯粹性质,在所有一般指称系统中,它们是或多或少常见的并且起支配作用的典型概念的抽象特征。它们的重要性很少取决于量的分配,而更多地取决于它们的构造。譬如楔形文字既是表意文字又是表音文字。我们的确不能将每种书写符号能指归于某一类别,因为楔形文字代码交替使用两个声区。事实上,每种书写符号形式都有双重价值,即:表意价值与表音价值。”[3]132既如此,任何语言,都不可能只具有纯粹的三种语言中的一种属性,而是多种属性不同程度的综合。这也就消解掉了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本质差异,进而完成对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
四、结论:“汉语图形形式的用途”
德里达通过西方汉学中的汉字研究发现,不仅在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之外,还存在基于“非表音性”的汉字而发展起来的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而且通过汉字的象形性、表意性和表音性兼而有之的特点颠覆了西方文明赖以获得优越性和强势地位的“文字等级论”。无论是卢梭的文字类型三分法,还是索绪尔的文字类型两分法,都包含着语音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和学术偏见。因此,在德里达那里,汉字具备了解构语音中心主义的文字等级论的巨大意义。
那么,在德里达那里,汉字是否仅仅具有“解构”的功能,是否以一种绝对的“大他者”的形态与拼音文字格格不入、尖锐对立呢?答应是否定的。
在《撒播》(Dissemination)一书中,德里达以索莱尔斯的小说《数》(Numbers)为例,探讨了汉字以“方块文字”这一图形形式嵌入拼音文字所可能增殖出的意义和价值问题。作为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的先锋派作家,索莱尔斯在《数》中试图以小说的形式呈现他所理解的中国文化中“数字”所具有的不同于计数功能的定位作用。整篇小说包含100个片段,以4段组成一个单位,构成叙事的循环。除此之外,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数》中所穿插的大量汉字了。它们或是前面出现的法语词汇的直译(如“群众”[masses]、“革命”[révolution]、“火”[enflammé]等),或与上下文并没有紧密关联(如“德”、“易”、“道”等)。德里达将索莱尔斯的这种写作称之为“不同写作的异质性”(The heterogeneity of different writings)的“移植”(the graft)。在《数》中,德里达发现的不是零星的汉字嵌入法语的段落之中,而恰恰相反,“《数》中的拼音文字发现自己被移植到了非拼音类型的文字之中。”德里达认为,索莱尔斯在《数》中探索的“汉语图形形式的用途”(the use of Chinese graphic forms)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根据最坏的假设,文本修饰或页面装饰通过一种魅力的增补效果,会使得诗学从某种语言学表征体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根据最好的假设,它的目的就是让设计的力量自己在那些不熟悉其功能规则的人面前直接发挥作用。”[6]356也就是说汉字在小说中的功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对表音文字的语音中心主义的消解;另一方面则是以“方块汉字”象形性和表意性的“图形形式”创造新的意义。这种意义并非由这些汉字的本来意思带来的,恰恰是由汉字自身的模样产生的。德里达在此对汉字“图形形式”的强调,恰恰将自己不懂中文的劣势转化为一种语言交流和文化传播中的具有某种普遍性的“优势”:对方块汉字“图形形式”本身的审美和想象。
那么,德里达是否对自己的汉语认识表示满意?答案也是否定的。他非常清楚自己的研究局限。“不懂装懂”确实是德里达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在一次接受中国学者的访谈中,德里达坦言,他自己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判断的基础是美国及在美华人学者的出版物。从理想的方案来看,德里达认为,真正的“解构主义”,应该是建立在一种真正的“比较文学”或“比较诗学”立场之上。他认为,“兼备所有下述能力的学者少而又少:既熟悉西方哲学,复数的西方哲学(这在西方就已是稀有之物!),又熟知中国传统思想,并且还能准确地掌握所有的民族语言(中文,还有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等)!必须建立一种真正的学科——一种志在培养兼备这些能力者的学科。可是,当今世界上没有一所大学将此当做一个自在的学科在进行建设。”[7]147-148
诚如斯言,德里达思考汉字的方法或许将会是另一种样子。
[1] Jonathan Culler.The Literary in Theory[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2] [法]德里达.书写与差异“访谈代序”[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 [法]德里达.论文字学[M].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4] La reforme de l’écriture chinoise[J]. Linguistique,Recherches internationaies à la lumière du marxisme,1958(7).
[5] Jacques Derrida.The Pit and the Pyramid:Introduction to Hegel’s Semiology[A].Margins of Philosophy[C].translated by Alan Bass.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2.
[6] Jacques Derrida.Dissemination[M].The Athlone Press,1981.
[7] 德里达,郑家栋.与中国哲人对话是否可能?——德里达访谈:视界(第1辑)[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