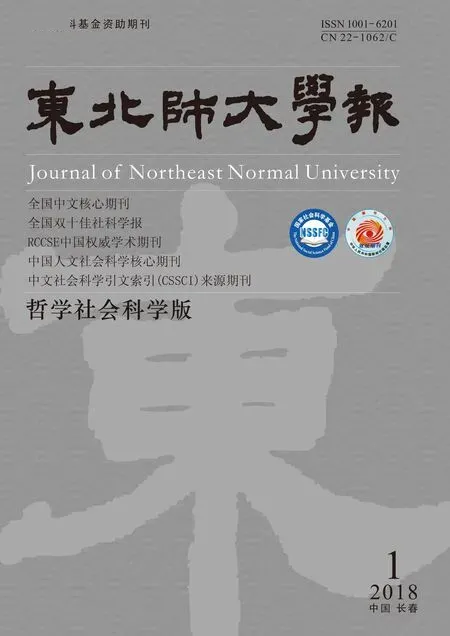《文选》“赋篇”批评三题
许 结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在赋学史上,齐梁堪称“盛世”,尤以兰陵萧氏家族居两代皇室之尊而作用较大,其中“五萧”即竟陵王萧子显、梁武帝萧衍、武帝子萧统(昭明太子)、萧纲(简文帝、武帝第三子)、萧绎(元帝、武帝第七子)均有赋论传世。然其重“赋”,因时尚“文”,所以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称萧梁时“文思光被”“才英秀发”。倘就对后世之影响而言,齐梁赋论又以萧统《文选》与刘勰《诠赋》为最。作为保存七代文章的《文选》,其“赋篇”之选因有以总集存赋的首肇之功,由“选”观“论”,如以“赋”冠首、赋体分类(十五类)并新辟“志”“哀伤”“情”三类目(题材),以及析相如《子虚》《上林》为二赋等,皆多为前贤关注、评骘与质疑。倘从文学之流变审视《文选》之“赋篇”的批评思想,似有未尽之意,兹选其中“首赋”“首京都”与别“骚”一体之“三题”,略陈隅见,以备考述。
一、首赋:文学观之商榷及考源
《文选》包七代之文,分三十八类,其中诗、赋、骚作品居大半,然首列“赋”十九卷(第十九卷并赋与诗),以“首赋”彰显兹体在“文”中的地位,这与萧氏于序文所称“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的文学发展观有紧密联系。然则“首赋”问题,后世颇多质疑,代表人物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下》中批评萧选体例“淆乱”首在“赋先于诗”[1]81,又在《永清县志文徵序例》中有进一步驳斥:
萧统选文,用赋冠首;后代撰辑诸家,奉为一定科律,亦失所以重轻之义矣。如谓彼固辞章家言,本无当于史例,则赋乃六义附庸,而列于诗前;骚为赋之鼻祖,而别居诗后,其任情颠倒,亦复难以自解。而《文苑》《文鉴》从而宗之,又何说也?[1]789
无独有偶,袁枚引唐人说以辨萧选“首赋”之误:
文以赋装头,始于《文选》。刘禹锡曰:“文章家先立言而后体物。”今以赋装头者,非也。[2]407
当然,也有持相反意见者,如桂超万认为:“赋者,古诗之流。《文选》以此居首,其次第有脉络可寻也。”[3]桂氏所言笼统,缺少内涵,袁氏所述唐人说,区分“诗言志”与“赋体物”,探其源,亦同赋为“古诗之流”,论其意,则有文学变迁的意味。宋人项安世说:“自唐以后,文士之才力尽用于诗,如李杜之歌行,元白之唱和,序事丛蔚,写物雄丽,小者十余韵,大者百余韵,皆用赋体作诗,此亦汉人之所未有也。”[4]以诗代赋,实为袁枚引述刘禹锡“先立言而后体物”的当下情境。比较而言,章学诚反对“赋首”编文法更具学理意味。
考述章氏之论,一在《文选》“用赋冠首”影响极大,后世文章总集多取法,视为“科律”;二在赋乃“六义附庸”,故出于“六经皆史”的思想批评萧选“首赋”,关键是“斤斤画文于史外”,而疏忽“太史观风之意”[5]。于是分辨其异,特别是章氏说萧统“彼固辞章家言”,恰呈示出二人的出发点不同:章氏出于经史之学或广义文学观批评《文选》,而萧氏本义则出于“变本而加厉”的狭义文学观编纂《文选》,所以“用赋冠首”恰是割断“太史观风”之诗教传统的尚文思想之表现。从这一意义来看,萧氏“首赋”即“尚文”,这与齐梁风气及文学相对独立于经、史的意识相关。
然则追溯“首赋”之源,宜非创始于萧选,这与汉晋时代赋创作的兴盛以及文集的编纂、史书的著录有着一定的渊承关系。例如范晔《后汉书》著录作家创制的文类,已多以“赋”居前。其中如桓谭、冯衍、班彪等传列其撰述所谓“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桓谭)、“所著赋、诔、铭、说、……五十篇”(冯衍)、“所著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班彪)等,这种现象在《文苑传》中尤为明显,如杜笃、夏恭、黄香、李尤、崔琦、张升、赵壹等传记中,皆以“赋、颂、诔”类模式著录。当然也有不以“赋”居首的,如《王隆传》“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傅毅传》著录“诗、赋、诔”等。也由于在范氏之前有关后汉书的编撰,如谢承等“八家后汉书”均无“首赋”例,很难说这就是东汉人创作及文类观的实写,但其尚文重赋的思潮,也隐然可见。同样,在萧统编纂《文选》之前的文集编例,如挚虞《文章流别集》对“赋”的重视,也可资借鉴,然因文献不足征,所以考查萧选“首赋”与当朝文风的关联,则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而与萧统赋论相关者,萧衍、刘勰最值得关注。据《梁书·武帝本纪》记载,萧子良在金陵鸡笼山西邸邀众宾客于府第,“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称‘八友’。”至梁武帝(高祖)则于“大同中,于台西立士林馆……四方郡国,趋学向风,云集于京师。”又《南史·文学(周兴嗣)传》载:“梁天监初,奏《休平赋》,其文甚美,武帝嘉之。……其年,河南献舞马,诏兴嗣与待诏到沆、张率为赋,帝以兴嗣为工,擢拜员外散骑侍郎,进直文德、寿光省。……周捨奉敕注武帝所制《历代赋》,启兴嗣与焉。”[6]1780可见由齐“竟陵八友”到梁宫文苑,赋才云集,彰显了尚文之风。尽管前于萧统《文选》的总集编纂有杜预《善文》、李充《翰林论》、挚虞《流别论》等,然其父萧衍以帝王之尊所编之《历代赋》(皆亡佚)影响之钜,自无疑义。萧统本人尤好文事,其在东宫时招聚文士如殷芸、刘孝绰、徐勉、萧子范等,刘勰时亦为东宫通事舍人,以致史家赞述“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7]167一方面,东宫文士赞美萧统文章,如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就以汉晋赋家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班固、蔡邕、陈琳、陆机等相比,谓之“深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8]3064另一方面,则有“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9]354、“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10]之说,尤其是东宫通事舍人刘勰“深被昭明爱接,《雕龙》论文之言,又若为《文选》印证,笙磬同音。”[11]10换言之,刘勰《诠赋》论汉大赋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亦正与萧统《文选》首选汉赋同一旨趣。
由此再看萧选“首赋”的文学意涵,关键是赋在“文”中的位置。对此,《文选序》继论文后于“赋”考源云:
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12]2。
其说虽承汉人“赋者,古诗之流”说,然将《诗》的六义之“赋”转向赋体之意,实近承皇甫谧、挚虞赋论,具有开辟意义,其中内涵了视赋体为文士创作之肇端。清人刘天惠《文笔考》辨析《汉志》分类云:“汉尚辞赋,所称能文,必工于赋颂者也。《艺文志》先六经,次诸子,次诗赋……据此则西京以经与子为艺,诗赋为文。”[13]虽然“诗赋为文”,然《诗》三百篇被汉人经学化,而汉代的乐府“歌诗”,皆乐官所制,并无撰述之人,尤其是两汉时期如钟嵘《诗品序》说“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故由楚邦(荀、宋)到汉廷(言语侍从)的赋作成为第一代文士的创作。同样,东晋葛洪于《抱朴子·钧世篇》比较周诗与汉赋,以为“《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秽博富。”[14]155这种赋胜于诗的文学观显然对萧选以赋居首并视为文士创作的代表,自有一定的影响力。
萧统这种“尚文”而首称“赋”的批评思想,在后世文人的赞述间亦可窥其理义。如元人陈绎曾论汉赋体谓“宋玉、景差、司马相如、枚乘、扬雄、班固之作,为汉赋祖,见《文选》者,篇篇精粹可法,变化备矣。”[15]册1,页365明人俞王言谓“艺林之技,首推辞赋”[16]、费经虞谓“赋别为体,断自汉代。”[17]清人王修玉谓“赋固以楚汉为宗”、“《昭明文选》诸赋皆佳”[18]、吴省兰谓“自汉以降,作者迭兴,班志《艺文》列诗赋家百有六,而赋居十之八。东京彪、固之流,后先接踵。”[19]皆与萧选意旨桴鼓相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人赋学复古,创作好拟《选》赋,且多广、续《文选》之编,其批评又偏于“宗汉”并直谓“唐无赋”,这是有“一代之胜”文学史观的重要环节,其中隐蕴着与萧选的承继,更是耐人寻味。因此,前人质疑《文选》“首赋”如章学诚之论,实出于经史之学的视域,故与萧统之“尚文”不侔,从历史的接受意义考察,赋论的“宗汉”以及以汉赋为“一代文学”思想的形成,萧选首录汉赋宜为目前所见最早的创作蓝本,对后世的拟效书写与理论批评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首京都:萧梁赋论与大汉书写
既然《文选》“首赋”源于“尚文”,并为后代学术史视“赋”为有汉之“一代文学”,如果按照时序之变迁,固宜先西汉(如相如、扬雄)而后东汉,先校猎(如相如《上林》)而后“京都”,然则萧氏却以分类法首“京都”而后校猎,客观上形成先东汉而后西汉的时序错位。对此,我们先看《文选》李善注《两都赋》引《公羊传》语:“京师者,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也。”[12]22就汉帝国而言,汉赋就是“众大之辞”,是对国家整体形象的文学化写照,宗旨在如班固、张衡京都赋所说的“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西都赋》)、“惠风广被,泽洎幽荒……重舌之人九译,佥稽首而来王”(《东京赋》)的华夏中心论与万邦协和观。这其中内涵的“物态”与“德教”,奠定了后世辞赋(尤其是大赋)创作由“观物”而“观德”的书写模式。而作为首选汉赋的今存第一部文学总集,《文选》正是这一创作模式的认同者,这其中同样蕴涵着萧梁赋论以书写大汉盛景为宗旨的意味。
萧梁赋论的集中体现,宜在萧衍(武帝)《历代赋》、刘勰《诠赋》与萧统《文选》,其成就也在武帝一朝尤盛。倘考述其背景,继西晋八王之乱而导致“五胡”崛起,衣冠南渡,东晋以降南北分裂,萧梁代齐,试图光复大业,其赋论之隆,堪称其文化中兴的一部分。从主观看,梁武帝确有振兴之意,如开监七年武帝诏:“建国君民,立教为首。……朕肇基明命,光宅区宇,虽耕耘雅业,傍阐艺文,而成器未广,志本犹阙……今声训所渐,戎夏同风,宜大启庠学,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梁书·武帝本纪》)就客观言,萧梁文德武功,亦尝兼备,虽国力未强,也有北伐之举,如“普通中,大军北讨,京师谷贵,太子因命菲衣减膳。”(《梁书·昭明太子传》)而对待“海南东夷西北戎诸国”,史臣亦赞曰“高祖以德怀之,故朝贡岁至,美矣。”(《梁书·东夷传》)[7]46、168、818对应萧选,诚如其序所言选文标准在“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考其源则“伏羲氏之王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李周翰注:“美文功也。”[20]3如此“文功”与“时义”,在唐初李善《上文选注表》中得到进一步的推扬:
昭明太子业膺守器,誉贞问寝,居肃成而讲艺,开博望以招贤。搴中叶之词林,酌前修之笔海。周巡绵峤,品盈尺之珍;楚望长澜,搜径寸之宝。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选》。后进英髦,咸资准的。伏惟陛下经纬成德,文思垂风。则大居尊,耀三辰之珠璧;希声应物,宣六代之云英[16]3。
李善上表赞萧选的“文功”,亦有“时义”,再由此溯推萧选的“时义”,落点于“首京都”的赋学观,又可归纳为“大汉气象”与“周汉礼德”两个方面。
汉大赋之盛,在“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其创作榜样固然如皇甫谧《三都赋序》所说“相如《上林》、扬雄《甘泉》、班固《两都》、张衡《二京》、马融《广成》、王生《灵光》,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焕乎有文,蔚尔鳞集,皆近代辞赋之伟。”[12]641但比较“校猎”“郊祀”类大赋的单一题材,京都赋更能体现“宏博之象”,诚为帝国图式的文学书写,《文选》先京都类又复以班固《两都赋》居首,其用心正在于此。我们可以参照班固《答宾戏》中的一段话,来推测其创作帝都赋的思想:
方今大汉洒扫群秽,夷险芟荒,廓帝纮,恢皇纲,基隆于羲、农,规广于黄、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养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内,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禀仰太和,枝附叶著,譬犹草木之殖山林,鸟鱼之毓川泽。……参天坠而施化,岂云人事之厚薄哉?[21]4228
所言“廓帝纮,恢皇纲”“六合之内”“参天施化”,实与《两都赋》的写作宗旨契合。延承其义,明人吴宗达《赋珍序》认为“山川舆服,卉木虫鱼,缋写自然,忧愉殊致,《三都》《二京》,实苞孕之。”[22]清人孙梅曾引班固《两都赋序》之“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谓“两汉以来,斯道为盛。承学之士,专精于此。赋一物则究此物之情状,论一都则包一朝之沿革。”[23]69近人胡朴安则说“东京之文,兰台体最绵密。《两都》典丽堂皇,平子、太冲拟之皆有逊色。”[24]侧重点或有不同,然尊“京都”而称宏博,殊为一致。所以论赋家才学,周雷《历朝赋衡裁序》例举“平子赋都,给笔札者数年;太冲研京,搜故实者十稔。故能牢笼百态,摇劈群言。既徵博以逞奇,亦积迟以造险。”[25]论赋文体物,方逢辰《林上舍体物赋料序》以为“赋难于体物,而体物者莫难于工,尤莫难于化无而为有。一日长驱千奇百态于笔下,其模绘造化也,大而包乎天地;其形状禽鱼草木也,细而不遗乎纤介。”[26]读京都诸赋,最为典范。由此,萧梁赋论对东汉京都赋的追慕与宣扬,又从两个视点表现,一是对应现实之文的反思,如萧纲《与湘东王书》认为“比见京师文体,儒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一是对文章旧典的效仿与更新,如萧统《文选序》所言“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前论“京师文体”,可于梁京反观汉京,后谈踵事增华,萧选包七代文章而首尊汉京气象,其彰显“文功”,“时义”深明。
如果说赋家笔下所展示的气象是呈现于外的光华,则之所以撑拄气象的却是赋中蕴涵的“礼德”,这是赋体之“铺”(气象)与“藏”(礼德)的奥秘,而萧选首列京都赋的“藏”又可视为“周汉礼德”,乃其追慕与仿效的旨意。考述东汉京都赋的创作宗旨,是追奉“周德”而构建“汉德”的形象书写。班固《两都赋序》自抒彰显“汉德”之义云:
且夫道有夷隆,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12]22。
其言“皋陶歌虞,奚斯颂鲁”,皆拟效《诗》《书》,表彰周德,探其奥秘,则在《西都赋》“周以龙兴,秦以虎视”一语,再比照《东都赋》历述古今圣王“伏羲”“轩辕”“商汤”“周武”“周平”及汉代“高祖”“文帝”“武帝”等,独缺“秦世”,且赋中“东都主人”训斥的对象又正是“秦人”,其要在“暴秦”失“德”,这成为汉京都大赋“非秦”的同一意旨。然则汉继周,又何以奉东汉京都赋为正宗?其答案也在班氏《东都赋》借东都主人口批评西都宾的言说中:“今论者但知诵虞、夏之《书》,咏殷、周之《诗》,讲羲、文之《易》,论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唯子颇识旧典,又徒驰骋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难,而知德者鲜矣。”[12]38这其中又暗藏一历史奥秘,即王莽“篡”政而导致汉室中衰,所以京都大赋既是汉人宣德之文,也是中兴之文。尤其是汉明帝“永平”礼治,更是赋家口碑美事,如张衡《东京赋》继班赋而赞曰:“是以论其迁邑易京,则同规乎殷盘;改奢即俭,则合美乎《斯干》。……民去末而反本,咸怀忠而抱悫。于斯之时,海内同悦,曰:吁!汉帝之德,侯其祎而。”[27]156-157与班固同时的王充在《论衡·须颂篇》中也称颂:“孝明之时,众瑞并至。百官臣子,不为少矣。唯班固之徒,称颂国德,可谓誉得其实矣。颂文谲以奇,彰汉德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与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28]406明乎此旨,清人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二十一谓“秦恶流毒万世,复浮于莽。……莽后仍为汉,秦后不为周耳。实即以汉继周,有何不可”,于卷三十复谓“唐赋小巧,与诗余同成戏具,凡诗内纤俗恶派语,皆可入其体。”[29]381、539其赋体“宗汉”且以为“大汉继周”以明“德”的思想,正源于“秦”、“莽”教训,归心东京,值得关注。对照清人赋文批点,如张衡《东京赋》“昔先王之经邑”的一段眉批:孙鑛谓“东都形势,亦自周来”、何绰谓“东京之本于周,犹西京之本于秦也。所以推周制以为发端。”[30]可谓的评。
从“气象”与“礼德”看萧选首京都的赋文选择,正切合于当时的国运与文运。古代封建王朝以受天之命为立纲之本,尤其是汉人大倡以“五行”配“五德”,国运昌兴受于天而成于人,至南北朝分治,“正朔”颇有争议,萧选奉大汉京都赋为正宗,其意自为明晰。就文运而言,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评述南朝谓“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31]675其“圣历方兴”,诚萧梁武帝所开辟之气象,作为太子,萧统居东宫汇集历朝文章而标举大汉德行,所求正是文章“正朔”,尽管这只是一种历史(旧朝)与区域(非萧梁统治区域的北方)的影写,却不失为驻足文化制高点的雄心。虽然,梁武帝统治后期因心耽佛道,荒于政事,导致“太清之难”使梁朝中衰而颓落,唯《文选》“赋篇”首尊“京都”的大汉风徽,留下了萧梁一朝影写帝国图式的记忆,却是弥足珍贵的。
三、别“骚”一体:赋学史之意义
萧统《文选》所呈示的赋论,在文体论方面除了“首赋”颇受诟病,就算别“骚”亦遭质疑。考《文选》辨体,别立“骚”文两卷,收录《离骚》《九歌》等十三篇作品,并于其《序》中加以明示:
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12]1。
别立“骚人之文”,后世不乏批评,如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认为:“太史公言:‘离骚者,遭忧也。’离训遭,骚训忧,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则赋也。故班固《艺文志》有《屈原赋》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选》,不并归于赋门,而别名之曰骚,后人沿袭,皆以骚称,可谓无义。”[32]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也针对别“骚”为体认为:“汉世校书有《辞赋略》,其所列者甚当。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33]17究其原由,近人高步瀛颇有解释,其于《文选序》“李善”之义疏中,一则释“荀、宋表之于前”谓“此言荀不言屈者,昭明于屈子之骚,当别为一类”;一则释“骚人之文”谓“《汉书·艺文志》有屈原赋二十五篇,骚即赋也。昭明析而二之,颇为后人所讥。然观此序,则骚赋同体,昭明非不知之。特以当时骚赋已分,故聊从众耳。”[34]11,14高氏所言“从众”,宜指当时阮孝绪《七录》始立“骚”目,而异于《汉志》,并开《隋志》分立“骚”与“赋”之途,还有如刘勰《文心雕龙》分篇别立《辨骚》《诠赋》等文论家的意图。
无论被质疑,还是说“从众”,都属皮相之论,因为早在汉世已有刘向、王逸编辑《楚辞》之文,刘勰分立《辨骚》《诠赋》亦非“辨体”之意,且《诠赋》以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其《物色篇》言《离骚》之“触类而长”,汉赋之“模山范水”,又合骚赋而论,并无轩轾。因此,考察《文选》别立“骚”体的意义,还应置放于赋学史的发展与变迁中,方可得其旨意。缘此,近人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卷上《诠赋第八》中的一段言说最值得参鉴:
舍人论文,骚赋分篇,与刘、班志《艺文》纳骚于赋,似异实同。盖刘、班以骚亦出于古诗六义之赋,欲明其源,故概以赋名之也。舍人谓汉赋之兴,远承古诗之赋义,近得楚人之骚体,故曰“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盖以析其流也。至其推究汉赋之本源,以为出于荀、宋,亦具特识。详观汉人之作,凡入刘向所定《楚辞》者,皆依仿屈子之体,以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为主者也。《文选》所载马、班、扬、张京都苑猎诸赋,意主讽谏,而辞极敷张,所谓侈丽闳衍之辞也[35]24-25。
此明“源”析“流”的异同之说,对理解萧选别“骚”而不“并归于赋门”,尤其是其中区分骚“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为主”与赋“辞极敷张,所谓侈丽闳衍之辞”的创作差异,倘移之评述《文选》别“骚”一体,或许更为切合其义。只是刘永济仅立足齐梁赋论向前追溯而观其源与流,而未及萧梁赋论尤其是《文选》立“骚”对后世之影响(即“后人沿袭,皆以骚称”),其意未周,仍有可申述的批评空间。
首先,《文选》别“骚”与刘(向)、王(逸)辑录《楚辞》不同,是总集编纂辑录赋与骚而加以并存,也不尽同于刘勰分立《辨骚》与《诠赋》,其《辨骚》属文章本原,而萧统所谓“骚人之文”却是辨体,诚为赋学史发展中的一重要环节。萧梁时代“儒”“文”相别,“文”“笔”剖分,为其时尚,如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论“今之学者有四”,以“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36]966,此与萧统尚文观一致,所不同者此笼统言“文”,萧选则因“文”分类,故有合辞赋与别骚、赋的不同。这也造成后世学者继承时择取角度发生差异,例如宋人晁补之、洪兴祖、朱熹等编纂《楚辞》,以及清人程廷祚撰《骚赋论》,皆重其异,如《骚赋论》论骚赋之异云:“骚之于诗远而近,赋之于骚近而远。骚主于幽深,赋宜于浏亮。”而合观骚赋者如陈枚等为《古今赋分为五体辨》,区分赋为五体(古、俳、文、律、小),并合骚赋于“古赋”,所谓“如《长门赋》‘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娱’,句法篇法,全似乎骚,……《上林》《子虚》,创为纵横骈织,亦为古赋,效之者扬雄《羽猎》、班固《两都》、左思《三都》、张衡《二京》之类是也”[37],又重其同。问题是,萧选是取法前人如王逸《楚辞章句》而立“骚”,但又有本质的不同,王逸编骚是“依经立义”,萧统别“骚”,则在剥离了其对经义的依存,突出的是“怨慕凄凉”之“文”,而与“闳衍博丽”之“赋”加以区分。从这层意义上,萧选别立“骚”体是由“宗经”转向“尚文”,这对后世“楚之骚”与“汉之赋”的“一代文学之胜”之史观的形成,有重要的前导作用。
其次,既然萧选视骚与赋皆为“文”,又为何罔顾时序而先“赋”而后“骚”,以致前引章学诚之说谓“任情颠倒”“难以自解”,这又得绾合前述“首赋”与“首京都”的问题,以彰显萧统的正统文学观。如前所述,汉代以“京都”为中心的铺陈大赋对前代文章的承继,尤其是“大汉继周”政治观念的确立与历史意识的形成,这其间又包括了“继周”与“继楚”的互为关系。概括地说,汉代赋家一则继承楚人的词章与格调推演出赋体文学,却改变了楚赋抒发个人情怀(如《离骚》)与专为一事一物之歌咏(如《风赋》《高唐》),而拟效周朝政书(如《皋陶谟》)、礼书(如《周礼》)来成就其涵括六合、铺陈事物的创造;一则又借助楚人的情采与体式,改变周人政论与礼制文章并着力于夸饰形容,来成就其以军国大事为题材的文学性创造。宋人程大昌说司马相如赋“上林”,乃“该四海而言之”[38],说明的就是赋写君临四海又具礼德内涵的帝国气象。正因如此,萧选追慕大汉文章,而视“正始之道著”为正宗,“亡国之音表”为别派,国家意志远居个人情怀之上,这才是其别“骚”一体而首冠京都大赋的用心与目的。
再者,萧统别“骚”一体的见解,实与魏晋之世“赋体物”与“诗缘情”的创作风格之辨析相关,在他看来,骚人创作主“情”,更接近于“诗”体,然其视“骚”为有“情”之“文”,在赋学史的发展与变迁中,却有着强力的回响。质言之,自《文选》分立“赋”与“骚”,二者关系在后世赋学史的演变中离合往返,未衷一是,然骚人抒“情”与赋家体“物”,却成为赋学构建过程中二元一体的关系。尤其是自南宋振兴“骚”学,到元明文章辨体再引“骚”入“赋”,形成了“祖骚宗汉”的赋论观,显示出一条继承《文选》而又变之的批评轨迹。如元人袁桷《答高舜元十问》之一“古赋当何祖”问,其回答是:“屈原为骚,汉儒为赋。赋者,实叙其事,体物多而情思少。……汉赋如扬、马、枚、邹,皆实赋体;至后汉杂骚词而为赋,若左太冲、班孟坚《两都赋》皆直赋体,如《幽通》诸赋,又近楚辞矣。”[39]1888祝尧《古赋辩体》更是批评汉以后赋“辞愈工则情愈短,情愈短而味愈浅”,所以在“诗人之赋”“词人之赋”外别立“骚人之赋”,强调“骚人之赋与词人之赋虽异,然犹有古诗之义,辞虽丽而义可则,故晦翁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也。至于宋、唐以下,则是词人之赋多,没其古诗之义,辞极丽而过淫伤,已非如骚人之赋。”[15]册2,页746论者皆视骚“情”为拯救赋体衰败的良方,这形成继萧选后楚骚向赋域的回归。只是这一回归过程中内涵的《文选》别“骚”于“赋”的体性(抒情性),为赋学史伴随“辨体”思潮而产生的“祖骚宗汉”的批评观提供了创作的精神,实在不宜轻忽。
[1]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袁枚著,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五集第一种)[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3] 桂超万.淳裕堂文集:卷2[Z].清同治五年刻本.
[4] 项安世.项氏家说:卷8[Z].《丛书集成初编》本.
[5]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15[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6]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 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8]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9] [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0] 王应麟.玉海:卷54[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骆鸿凯.文选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2]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3] 刘天惠.学海堂初集:卷七[Z].《丛书集成初编》本.
[14] 葛洪.抱朴子[M].北京:中华书局,1954.
[15] 王冠辑.赋话广聚[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
[16] 俞王言.辞赋标义:卷首[Z].明万历二十九年木宁金氏浑朴居刻本.
[17] 费经虞撰,费密补.雅伦:卷4[Z].《续修四库全书》本.
[18] 王修玉.历朝赋楷·选例[Z].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19] 法式善.三十科同馆赋钞:卷首[Z].清光绪十六年刻本.
[20] 萧统编,李善等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2] 施重光.赋珍:卷首[Z].明万历刻本.
[23] 孙梅著.李金松校点.四六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4] 胡朴安.读汉文记[Z].安吴胡氏《朴学斋丛刊》石印本,1923.
[25] 汤聘评骘,周嘉猷等辑.历朝赋衡裁:卷首[Z].清乾隆二十五年瀛经堂藏板.
[26] 方逢辰.蛟峰文集:卷四[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 张衡著,张震泽校注.张衡诗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8] 刘盼遂.论衡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9] 李光地.榕村语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5.
[30] 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
[31]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2] 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二[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 姚鼐.古文辞类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4] 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5]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6] 萧绎著,许逸民校笺.金楼子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7] 陈枚辑,陈裕德增辑.凭山阁增辑留青楼集:卷4[Z].《四库禁毁丛刊》本.
[38] 程大昌.演繁露[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 袁桷著,杨亮校注.袁桷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