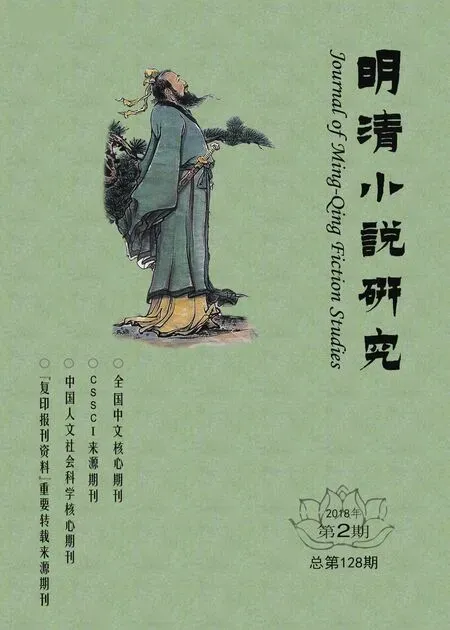西游先声:论唐宋图史中玄奘“求法行僧”形象的确立∗
·郑 骥·
西游取经故事是以贞观间玄奘十七载西行求法史实为源头敷衍开来的。从麟德元年(664)玄奘圆寂不久撰成的《大唐故三藏法师玄奘行状》(下文简称《行状》),到现存最早的百回《西游记》刻本金陵世德堂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问世的万历二十年(1592),西游故事孕育和衍变的历程长达九百多年。期间经由历代编创者的改造,各类文本层累嬗递,相比玄奘取经的历史本事,文学化的西游故事情节显著延展,内涵急遽丰富。
在人物形象方面,对取经队伍和各路神佛鬼怪的巧妙设置和精心塑造,同样促成了西游故事的经典化。因此,以取经队伍为重点,有关西游故事主要人物来源衍变的考证研究一直是西游研究的热点议题。只不过相比孙悟空等更具文学想象色彩、性格特征更显丰满,特别是渊源衍变疑问较多的徒弟,逐渐“丧失”西游取经绝对主角地位且人物形象趋于脸谱化的唐僧,在学界关于上述问题的讨论中并不具备太强的“话题性”。唐僧形象源自初唐西行求法的高僧玄奘几成定论,但相关研究似乎只限于这种笼统论说。换言之,以往研究或关注历史中的玄奘生平遭际,或聚焦文艺中的唐僧人物形象,但都无法圆满解释在漫长的唐宋时代,“玄奘”究竟是如何成为“唐僧”的。
从文本角度看,今存南宋末年刻本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下文简称《诗话》)自上世纪初进入中国学者视野以来,即被看作现存最早且在西游故事衍变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性文本。《诗话》中唐僧的基本形象,显然已是一位富有神异色彩的西行取经僧,殊异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下文简称《慈恩传》)等历史文本着力塑造的玄奘庄严崇高的圣僧形象。同时,猴行者的出现及其降妖除怪、克难渡险的神力和才智尤引人注目,剔除其中的神异外衣,其实质毋宁是历史文本中玄奘西行求法所展现的意志品质和贤才智慧在文学文本中的消解和被取代。这一此消彼长的变化同样是后来西游故事文学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直至最终形成《西游记》小说中作为妇孺皆知的文学经典存在的那个优柔寡断、软弱无能的唐僧。问题是,这种变化是始于《诗话》,还是更早就有端倪?从图像角度看,自1980年以来,在已正式披露的河西①[如图1、图2]、陕北②[图3]、巴蜀③[如图4]等非中原地区12世纪初至13世纪前期约10例所谓“玄奘取经图像”遗存中,取经人已几乎尽数以求法行僧形象示人,并基本伴有多为猢狲形象的侍从和多见驮经的马,组成取经队伍。而很可能作为取经护法神出现的观音、梵王等形象,则与取经队伍一起,清楚反映了这批壁画和塑像记录彼时彼地流传的西游故事这一构图观念。从上述图像与《诗话》在主要人物设置上的高度一致性,又不难看出其自成一体的构图形式已是取经故事文学化的产物,因此相比在历史和文学两性上归属不明的“玄奘取经图像”,这里不妨以更能凸显其文学属性的“早期西游图像”一词重新定名。至于图像本身,尤其是其中观音、梵王等看似边缘但实际上颇具研究价值的角色,我们另有专文讨论。图像艺术既与历史撰述和文学演绎互生关联,也有其自成一体的传播衍变规律,因此除了习见的文图互证,图像本身的发生和衍变同样值得重视。由此先要了解求法行僧是否是玄奘的一贯图像表现,否则就必须探究早期西游图像中这一形象究竟是如何从最初的玄奘图像衍变生成的。

西游故事的孕育和衍变是多种文化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绝不止文学演绎一途。《诗话》的刊行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河西等边地早期西游图像的集中产生,大致都在12至13世纪,这意味着彼时很可能是西游故事最早有系统编创,从而进入“有章有序”时代的关键阶段。换言之,这一时期正是玄奘求法行僧形象最终确立的时代。因此本文大致以12世纪为下限,从文本和图像两方面梳理唐宋时代玄奘形象的衍变,勾勒并还原玄奘“变身”唐僧的历史轨迹。
一、玄奘西行在唐代凸显的历史背景
玄奘(602—664)一生,以贞观十九年(645)返唐为界,可分西行求法和译经弘法两个阶段。前者向来是西游文学研究的焦点,但具体到考察玄奘的历史形象,则不能忽视后者。据《慈恩传》载,贞观十九年二月玄奘返唐后在洛阳初次奉见太宗,就曾提出赴嵩山少林寺译经的请求④。太宗虽未准奏,但同意其“还京就弘福安置”,译经“诸有所须,一共玄龄平章”;然玄奘又担心“百姓无知,见玄奘从西方来,妄相观看”而影响译经甚至造成过失,故“望得守门以防诸过”,实可见其无心眷恋西行成功所获声誉,急盼早日着手译经。翌年七月,在以极快速度进奏初见太宗时受命所撰《大唐西域记》前后几天内,两次上表恳求太宗为其译经作序,终获允准;两年后,太宗、高宗分别撰成著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大唐三藏述圣记》⑤。可以说,在提供了详实的西域情报后,玄奘与唐王室达成了政治默契,其译经事业获得了皇家御制的超高规格。在与皇室最初且具有决定意义的几番交往后,玄奘终于顺利开展大规模译经,而此后与皇室及朝臣频繁的周旋往还(多为称贺谢恩、陪驾顾问之类),实质也是想方设法维系朝廷为译经保驾护航这一既有默契。很显然,对玄奘来说西行不过是一种途径,译经弘法才是终极目的,不与朝廷合作则绝难实现。玄奘19年间主持翻译佛典约74部1335卷⑥,形成了鸠摩罗什以来佛经汉译的又一高峰。同时,凭其印度所学又开启了名噪一时的中土唯识宗先河。客观地说,玄奘无疑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译经和义理高僧。
然而上述种种,却在后世西游故事中烟消云散,仅仅作为途径或方法之一存在的西行经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被无限放大和夸张,逐渐蚕食玄奘本来的历史面目。我们认为,上述现象的产生除了后世的文学想象和虚构,还首先源于一点,即起码出于以下几种原因,相比译经功绩,玄奘西行求法事件在唐人历史记忆中更显凸出。
从构成玄奘历史形象的主要因素看,西行主题的凸显首先正是由于译经弘法主题的衰减。刘淑芬曾有长文从高宗朝清洗旧臣、译业受限、死后改葬、别传长期不传、庙塔碑铭长期未立等层面详尽论述了玄奘晚年的艰辛困顿及其身后的尴尬境遇。玄奘晚年译经多受掣肘,突出表现为高宗显庆年间诏于志宁等六大臣监督译经、随驾洛阳及回长安后迁居西明寺等事,在长达两三年的时间里,他失去了慈恩寺组织有序的庞大译场,甚至几无人身自由,期间仅译出寥寥几部短经⑦。或正因此,玄奘无奈两次提出离开政治中心,分别请往条件不及慈恩译场的少林寺、玉华寺译经⑧。值得注意的是,麟德元年玄奘死后高宗虽表示了哀悼,但随即敕令“其翻经之事且停……自馀未翻者,总付慈恩寺守掌,勿令损失。其奘师弟子及同翻经先非玉华寺僧者,宜放还本寺”⑨,就此解散玄奘译场、遣返相关人员,大量未翻梵本也一律封存于慈恩寺。可见玄奘译经到了后期最多只算勉力维持。失去了皇室的坚定支持,其译业实际也就失去了在上流社会的广泛影响力。加之玄奘久居皇家寺院,又不愿百姓“妄相观看”干扰译场,一般民众对其译经的具体情形大概本就不甚了了。另外,由玄奘奠基、弟子窥基等开创的唯识宗虽有一时之盛,但在华严、净土、禅宗等更趋中国化的宗派并起竞争的局面下,短短三十馀年,传承三代便迅速衰落。除了教条地传习印度有宗教义,执着于精密义理而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等众所周知的原因,还须注意的是,窥基、普光等主要弟子和宗派传人在玄奘逝后多不再参预其他译场,转而游方行化或专力注疏,与玄奘在日每受师命往来宫廷不同,他们似乎迅速疏离了政治和皇权⑩。这其实也印证了玄奘晚年以至身后政治上的尴尬处境。其实,当窥基、慧沼、智周等无法承续“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⑪这一佛教创立和发展的重要传统时,不仅自身事迹不显于后世,宗派传承更是难以为继。唯识式微大大消减了玄奘经义大师的历史形象,这是不言自明的。
其次,玄奘身后,除当时正在编撰《续高僧传》的道宣等为其作传外,冥详《行状》应属私撰性质,流传不广,故在国内未见其踪,今仅存两件日本平安时代寺院写本;《慈恩传》更是辗转流散,直到垂拱四年(688)年才由彦悰整理成书。而在开元以前,上述几种早期玄奘传记或都未能入藏流传⑫。换言之,在玄奘死后数十年内,有关其生平和成就的权威历史文本并未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又据刘轲《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兴教寺玄奘塔年久失修“荒凉残委”,大和二年(828)安国寺僧义林以“塔上有光,圆如覆镜”名义请旨重修,直到开成二年(837)应义林弟子令检所请,才有刘氏此铭⑬。可见此前尚无玄奘碑铭行世。本来,时人通过权威的历史文本可以深入了解玄奘生平,尤其是充分认识其返唐后呕心沥血、孜孜以求的译经事业,然而传记碑铭的长期不传,使其译经弘法史实的传播从一开始就大打折扣,并最终导致玄奘历史形象的偏颇和错位。
最后,初盛唐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对外扩张取得极大成功的时代,面对域外世界,整个社会呈现出“有德则来,无道则去”⑭的极度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这种天下国家的自信在一般民众层面更多表现为对未知世界的好奇,而玄奘返国适逢其时。玄奘返回长安时“数十里间,都人士子、内外官僚列道两傍,瞻仰而立……烟云赞响,处处联合”⑮,竟使之担忧百姓见其“从西方来,妄相观看”,造成不便。加之《大唐西域记》的迅速成书和传播,作为焦点事件的玄奘西行,特别是其中的异域元素,无疑有着重大和持续的社会影响力。
总之,唐代社会对于玄奘西行历险的兴趣和认知大概远远超过其本人更为看重的佛经传译,其历史背景除了后期译业不彰、宗派衰微、有关历史文本长期缺失等,更毋宁是当时社会意识的一种自然选择。
二、唐宋历史文本对玄奘“求法僧”形象的塑造
唐宋时代的玄奘传记不下十数种,又以《行状》《续高僧传·玄奘传》《慈恩传》等为时代最早、记事最详的源头,其主体内容是玄奘西行和返唐后的译经及期间与朝廷的交往,如在十卷本的《慈恩传》中,两者各占四卷半篇幅。三种传记均已包含不少神异叙事,只不过其中仅有被困沙漠时念观音得救和文殊托梦戒贤有支那僧来学法等少数情节与西行有关,更多的还是其圆寂前后得生弥勒净土等事。总体上看,唐代见于《法苑珠林》《开元释教录》等多种相对正式、能够入藏流通的佛教文献的玄奘史传,从情节到内容均未逾上述三种早期传记范畴,西行和译经两大主题平分秋色。不过到了南宋中后期,在两种比较正规的中原佛教史籍中,有关玄奘的历史叙事在保留唐代文本基本规制的前提下均加入了“摩顶松”情节⑯。志磐又在其另一部水陆斋会仪轨中明确定义“译经摩腾竺法兰,求法(玄)奘三藏等诸法师”⑰,这事实上改变了自道宣起玄奘被归入“译经”一门的传统做法,可见玄奘历史形象在宋代已经产生了某种变化。以上所说仅是基于具备精深佛学素养的高僧编撰的中原传世内典,实际上在此范畴以外,尤其是在古代多被视为“信史”的笔记小说和佛教灵验记中,类似情形早已屡见不鲜。
“摩顶松”情节早在开元初年或已形成(说详后)。《太平广记》(下文简称《广记》)卷九二“玄奘”条出于唐人笔记《大唐新语》和《独异志》,后者记玄奘事二则:
唐初,僧玄奘至西域取经,入维摩诘方丈室。及归,将书年月于壁,染翰欲书,约行数千百步,终不及墙。⑱
唐初有僧玄奘往西域取经,一去十七年。始去之日,于齐州灵岩寺院,有松一本立于庭,奘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长;若归,即此枝东向,使吾门人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约长数丈。一年忽东向指,门人弟子曰:“教主归矣。”乃西迎之。奘果还归,得佛经六百部。至今众谓之“摩顶松”。⑲晚唐成书的《独异志》强调“记世事之独异也……神仙鬼怪,并所摭录”⑳,其所记玄奘异事,皆属西行主题。先《独异志》约半世纪成书的《大唐新语》仿《世说新语》分门记事,明确将玄奘列入“记异”一门。按今本所记,未见“摩顶松”事,玄奘之“异”仅体现在“有瑞气徘徊”于其西行所得经像之上㉑,稍显牵强,而据《广记》所载,此书唐宋传本应确有“摩顶松”情节。
《广记》将玄奘列入“异僧”一类,除“摩顶松”外,还记一更重要情节:
沙门玄奘……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经,行至罽宾国,道险,虎豹不可过。奘不知为计,乃锁房门而坐。至夕开门,见一老僧,头面疮痍,身体脓血,床上独坐,莫知来由。奘乃礼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经》一卷,令奘诵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开辟、虎豹藏形、魔鬼潜迹。遂至佛国,取经六百馀部而归。其《多心经》至今诵之。㉒
事出《慈恩传》玄奘过莫贺延碛时的插叙:
初,法师在蜀,见一病人,身疮臭秽,衣服破污,愍将向寺施予衣服饮食之直。病者惭愧,乃授法师此《经》,因常颂习。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虽念观音不得全去,即颂此《经》,发声皆散,在危获济,实所凭焉。㉓授《心经》事今本《大唐新语》《独异志》不存,但类似叙述又见敦煌写本S.2464㉔。此本首题《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并序》,第一部分署“西京大兴善寺石壁上录出,慈恩和尚奉诏述序”,此序所述与上引《广记》“玄奘”条大体相同,差异在于授经地点是与《慈恩传》一致的益州,而非西行途中的罽宾。张石川认为,《广记》为更合西行史实而将地点改为玄奘必经之路㉕。更大的不同是序文出现了《慈恩传》和《广记》没有的玄奘抵达那烂陀寺后,病僧再次现身并称“我是观音菩萨”,言讫乘空而去这一情节,把授经和观音直接联系了起来。我们认为此序是伪托之作,也不太可能源自大兴善寺石壁。首先,S.2464序文后接抄署“不空奉诏译”梵汉对音《莲花部等普赞叹三宝》和所谓“观自在菩萨与三藏法师玄奘亲教授梵本,不润色”的《心经》正文,二者又见S.3178、S.5648、S.5627、P.2322及北大 D118等写本,但序文及其题署仅存于S.2464,是为孤证。其次,窥基于广福寺出家,后入慈恩寺师事玄奘,故称“慈恩和尚”㉖,师徒二人皆与大兴善寺无甚关联。大兴善寺实为不空所驻之汉密祖庭,“大兴善寺石壁录出”的说法或是附会续抄的不空译经而来㉗。最后,整个唐宋时代,内典中的玄奘传记均未见观音授经和向玄奘显示真身的情节,作为义理高僧,窥基对玄奘西行的认知应与冥详、慧立等师兄弟相仿,情节上不至有如此重大的变更。
我们认为序文是对《慈恩传》蜀僧授经故事的改造,具体很可能是在某一更接近《广记》的早期中原版本中掺入了涉及观音的内容。其原为流传于敦煌的一则玄奘取经故事,后来经附会编入不空译经写本,充作灵验记形式的经序㉘。至于改编的发生,或在故事流向西陲途中,或是传入敦煌以后。梅维恒更是直接提出这篇“出现在一个很奇特的《心经》的本子上”的序文就是“《西游记》最早的雏形”㉙。这意味着相比中原地区,有关玄奘的叙事在河西敦煌以更快的速度与西行主题融合,尤其是观音及其化身首尾呼应的两次出现,甚至比《诗话》更接近后世趋于成熟的西游文本,使序文在想象和情节结构方面的文学意味显著增强。
其实,大概由于瓜沙地区与玄奘西行的特殊关系,当地对玄奘“求法僧”形象的认识由来已久。9世纪前期敦煌金光明寺僧利济所作《大唐三藏赞》见于S.6631V(9)等5件敦煌写本,赞曰:
嵩山秀气,河水英灵。挺特瑰伟,脱屣尘萦。乡园东望,竺国西倾。心存宝偈,志切金经。戒贤忍死,邪贼逃形。弥勒期契,观音愿成。辩论无当,慈悲有情。一生激节,万代流名。㉚
全篇除了描述西行情节,赞美求法决心,对玄奘返唐后的译经弘法事业未及一字。从敦煌文献遗存看,早在玄奘生前,其所译经典及御制经序就已开始大量传入敦煌,利济不可能不知。相比之下,与利济同时代的金光明寺僧金髻所作《大唐义净三藏赞》(存S.6631V-8等4件写本),却以“译经九部,定教三时。皇上同辇,群下承规。该通内外,郁为国师”㉛的极高评价概括义净西行返唐后的译经弘法成就。可见早至中唐,玄奘历史形象在敦煌僧人的认知体系中就已不可避免地被贴上了“求法僧”标签。
三、玄奘“行脚僧”形象在唐宋图像中的形成
“求法僧”落实到图像,具体表现为“行脚僧”形象,而后者的确立自有一番过程。《慈恩传》载,显庆元年(656)二月高宗迎玄奘等十大德赴禁中鹤林寺施戒,三日后“复命巧工吴智敏图十师形,留之供养”㉜。这是迄今所知最早且唯一成于生前的玄奘画像记录。又中宗在位时曾为玄奘“制影赞,谥‘大遍觉’”㉝并“复内出画影装之宝舆,送慈恩寺翻译堂中”㉞。此中宗题赞、皇宫“内出”之玄奘画影应即吴智敏所绘,而大中年间(847—860)日僧圆珍来唐所获“大遍觉法师画赞一卷 御制”㉟,盖此玄奘像之摹本。此像久佚,但从用于皇宫供养,又有所谓“影赞”等描述,不难判断应是类似历代佛教祖师像,重在存其形貌、表现庄严崇高的“圣僧”㊱特质的半身或等身写真像。
《开元释教录》记靖迈《古今译经图纪》由来:
沙门释靖迈……大唐三藏翻译众经,召充缀文大德。后大慈恩寺翻经堂中壁画古来传译缁素。靖迈于是缉维其事,撰成图纪题之于壁。㊲
据此,《古今译经图纪》是当时慈恩寺翻经堂“壁画古来传译缁素”的副产品,原为题壁而作。《图纪》共载僧俗译经人112位,始摄摩腾而终玄奘。按其所录玄奘译经数量已达“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㊳之全数,应为玄奘死后其译团成员被遣回原寺不久所作,壁画的创作应在同时。我们认为翻经院玄奘壁画应与西行求法主题相去甚远,而是类似明刻《洪武南藏》扉画[图5]㊴的玄奘译经图像。

情况很快就有了变化。《历代名画记》载,东都敬爱寺“大院纱廊壁行僧中门内以西,并赵武端描,惟唐三藏是刘行臣描,亦成”㊵。据此,这铺武则天时期画师刘行臣绘于洛阳敬爱寺的玄奘像,已是行脚僧形象。这一变化无疑反映了玄奘西行事迹的广泛传播和民众对这一主题的积极接受。
开元元年(713)义净去世后不久,长安也出现了类似情形。会昌元年(841)二月初八,日僧圆仁至长安大荐福寺义净影堂,“见义净三藏影,壁上画三藏摩顶松树”㊶。按前述,摩顶松与玄奘西行有关应是唐人常识。与当时大批求法僧一样,义净西行深受玄奘事迹的激励,故称“显法师则辟创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其间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莫不咸思圣迹,罄五体而归礼”㊷。因此其影堂出现玄奘像也合乎情理。又中唐戴叔伦有《赠行脚僧》诗云:“补衲随缘住,难违(一作维)尘外踪。木杯能渡水,铁钵肯降龙。到处栖云榻,何年卧雪峰。知师归日近,应偃旧房松”㊸。可见中唐时摩顶松已是与行脚僧形象相伴生的一则事典。故圆仁所见玄奘像,显然是西行求法时空背景下的行脚僧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和前述“病僧授经”一样,摩顶松情节作为玄奘历史叙事中时代极早的一则插曲,其基本内容直到元明时代的西游杂剧和小说中仍被保留。
北宋景祐三年(1036),欧阳修曾于扬州寿宁寺见“玄奘取经图”一壁:
寺本徐知诰故第,李氏建国以为孝先寺。太平兴国改今名。寺甚宏壮,画壁尤妙。问老僧,云周世宗入扬州时以为行宫,尽朽漫之。惟经藏院画玄奘取经一壁独在,尤为绝笔,叹息久之。㊹
据此该图应绘于南唐建国初(937)至后周显德三年(956)周世宗亲征南唐并几度攻陷扬州之间。同一时期,画师李文才曾于成都三学院经楼下画“西天三藏真”㊺。稍早于李氏,后蜀明德年间(934-937)赵德玄、赵忠义父子在成都大圣慈寺福庆禅院东侧绘制表现佛法东传场景的变相13堵,“蕃汉服饰、佛像僧道、车马鬼神、王公冠冕、旌旗法物皆尽其妙”㊻,其中理应包括玄奘取经图像,而李氏所画既名“西天”,很可能是受到赵氏父子影响。又苏辙题郾城彼岸寺宋初画师武宗元绘玄奘像诗有“出世真人气雍穆,入蕃老释面清癯”㊼句,所谓“入蕃老释”应即西行途中的玄奘,诗人将其与“气雍穆”的真人相比,突出了玄奘清癯消瘦的行脚僧形象。由上述4例图像,可知五代宋初玄奘形象已和西行取经主题融为一体、密不可分,而行脚僧已是世俗对玄奘的普遍印象。
事实上,行脚僧是唐宋释道人物绘画的重要题材之一。除前揭敬爱寺外,《历代名画记》还记有长安荐福寺、洛阳长寿寺吴道子,慈恩寺李果奴以及景公寺、圣光寺王定等画行僧壁画㊽。宋初黄休复又见成都大圣慈寺唐肃宗干元(758-760)初卢楞伽画、颜真卿题,“时称二绝”的行道高僧像三堵六身,敬宗宝历间(825-827)左全画“行道二十八祖”;以及宝历寺后蜀杜弘义画“行道高僧十馀堵”等㊾。另在晚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壁画和绢纸画中,保存了至少20例很可能是现存最早的行脚僧图像,其基本构成为:一僧背负经箧、手持尘尾及锡杖等法器,脚踏五彩祥云,伴虎而行;行脚僧行进方向上部,几乎均有一小身坐于云中的化佛㊿。据P.4518(39)[图6]、EO.1141[图7]等图榜题,此佛应为有密教色彩且来自西域的“宝胜如来”。又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原出开封的宋初“繁塔”砖雕,与现存河南宝丰县大普门禅寺的北宋中期“大悲观音大士塔”砖雕中,均发现有近似敦煌行脚僧图的伴虎行僧图像〔51〕。关于伴僧而行的虎,王惠民认为其源自最早见于晚唐马支《释大方广佛新华严经论主李长者事迹》的开元时代居士李通玄〔52〕。其实虎为四象之一,很早就被视作有灵性的瑞兽,中国早期的神仙传说中就有不少伏虎情节。《太平广记》收录8卷“虎”故事,多见人虎互化事,而“虎化人”中又以僧道居多〔53〕。又魏晋以来的高僧故事中屡见伏虎情节,如南齐王琰《冥祥记》就载“晋沙门耆域”“晋沙门于法兰”“晋沙门释僧朗”“晋沙门释开达”“晋沙门释法安”等僧行道途中伏虎事〔54〕;唐宋《续高僧传》《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文献亦多载此类故事〔55〕。可见“行僧伏虎”是起源较早、流传广泛的传统僧传题材,故“虎”被阑入行脚僧图像本在情理之中。这些行脚僧从形貌看或胡或汉,反映了历史上传教求法的胡汉人物东来西去的史实。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画史记载还是实物遗存,似均未见唐以前的行脚僧图像踪迹,而其大量出现又在盛唐以后。这事实上正暗合玄奘西行求法故事迅速传播,其行脚僧形象不断深入人心的历史趋势,两者之间很可能是一种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逻辑关系。正因如此,部分学者在研究敦煌行脚僧图像时不可避免地更多关注其与玄奘形象的“同”,而忽视了“异”,甚至径直名之“玄奘取经图”。此外,这种误读的出现大概还受到了广为人知的日本镰仓(1185—1333)后期产生的所谓“玄奘三藏像”[图8],以及1933年西安兴教寺据该像所制石刻玄奘像的影响。

《大唐西域记》和《行状》《慈恩传》等早期玄奘传记很早就传入日本并形成大量新的写、刻版本〔56〕。和中国的情况一样,西行取经很快成为日本玄奘叙事的突出主题,其中自不乏神异性的想象虚构。平安后期至镰仓时代(约12-14世纪)编录的《打闻集》《今昔物语集》《宇治拾遗物语》《撰集抄》等一批说话集中的玄奘故事几为清一色的西行主题。比较典型的如“玄奘三藏心经事”,其与S.2464及《广记》所载授经故事应有同一来源,且从最早的《打闻集》到后出各种说话集,情节内容愈加丰富。尤其是《今昔物语集》所录已点明授经的患病老妇是观音化身,十分接近S.2464《心经序》〔57〕。图像方面,据前揭日僧圆仁、圆珍的记录,玄奘图像东传的时间至迟也在中晚唐之际。日本今存早期玄奘图像,集中于平安后期至镰仓时代,且大多与密教“十六善神”相结合。其中玄奘形貌均与敦煌行脚僧图及镰仓后期“玄奘三藏像”大同小异,更重要的是和玄奘一起出现的还有深沙神[如图9、图10]。日本享保2年(1717)刻本《般若守护十六善神王形体》有一条享和2年(1802)沙门快道的后加注文,注引《谷响集》卷八:“世有金刚智所译《般若守护十六善神》一卷三纸,读之明知非是金刚智笔语,缀文甚拙,想先达依金刚智图画录之,而假金智名矣。”〔58〕快道认同传本《般若守护十六善神王形体》非金刚智原译,而是后人对金刚智所绘“十六善神图”的文字描述。可以确定的是,上述日本玄奘图像应是其行脚僧形象与金刚智“十六善神图”结合的结果,至于结合时间是在二者传入日本后与否,尚不得而知,但结合的机缘应是玄奘曾译《大般若经》六百卷,大概也被视为和十六善神一样的般若护法。
深沙神与玄奘发生直接联系,较早〔59〕可见日僧常晓开成三、四年间(838—839)遣唐所得,他携回《深沙神记并念诵法一卷》《深沙神王像一躯》,并称“唐代玄奘三藏远涉五天感得此神,此是北方多闻天王化身也。今唐国人总重此神救灾成益,其验现前,无有一人不依行者”〔60〕。可见随着玄奘西行事迹和毗沙门信仰的广泛传播,最初作为毗沙门附属的深沙神甚至成了具有独立信仰体系的尊神。常晓所获深沙神像见于12世纪真言宗僧心觉所撰东密重要文献《别尊杂记》[图11],近似伴随玄奘出现在十六善神图中的深沙神形象。心觉称“深沙王”为毗沙门麾下上首夜叉,为玄奘取经所感应,又言其曾为玄奘童子;另有一“深沙神”则是观音所化,曾与深沙王斗法并胜之〔61〕。这种看似复杂甚至矛盾的记载表明唐宋时代应有多种版本的深沙神传说,可见当时深沙神信仰的流布已具一定规模。基于上述缘由,深沙神始得进入玄奘图像和叙事文本,并最终衍变成为西游故事中的沙和尚。

要之,“求法行僧”最晚自12世纪起成为日本叙事文本和图像中玄奘形象的主流,而深沙神和十六善神的出现,则反映了这一形象在密教层面的强化。当然,此种现象的出现既受中国本土玄奘历史形象衍变的影响,也是日本历代僧俗想象和改造的结果。此外,日本传世的另一部分具有肖像性质的玄奘图像〔62〕,则极有可能源自圆珍携回、有中宗御赞的玄奘生前吴智敏绘像摹本。
到了两宋之际,书画鉴赏家董逌《书玄奘取经图》谓:
西京翻经院尝写玄奘游西域路道所经,此图岂传是邪?玄奘陈氏,偃师人,尝至灵岩,方取经西域,庭柏西指,凡十七年,一日柏枝复东指,其徒知师归。当时谓负经东来,常有云若华盖状,所至四人废业。此画皆不及之,得毋不尽传邪?〔63〕
跋文透露了三条信息:第一,长安慈恩寺翻经堂曾绘玄奘取经路线图,北宋末仍为人所知。此图无疑表现西行取经主题,至于其产生时代及与同在翻经堂的“古来传译缁素”壁画有无关系,今不可考。第二,董逌怀疑“此图岂传是邪”,是其所见取经图或与慈恩寺翻经堂玄奘取经路线图类似,规模较大,并非仅有玄奘像而已。联系南唐寿宁寺取经图和后蜀赵氏父子佛法流传变相以“壁”“堵”计数的事实,它们很可能与董逌所见及慈恩寺翻经堂取经图一样,都是再现玄奘西行道路所经的全景式图像。第三,董逌曾任北宋皇家藏书处徽猷阁待制,考书画“引据皆极精核”〔64〕,他既指出图中未及“庭柏”(按同摩顶松)及“负经东来,常有云若华盖状”等,就表明这些题材常见于董氏以前玄奘取经图像,故其有“得毋不尽传邪”的感慨。更重要的是,当时陕北、巴蜀等地已经出现文学化了的新样图像,但以董氏之淹博却未能涉及,恐只能说明新的形式属边地原创而尚未进入中原视野。
四、结论
相比玄奘本人毕生追求的译经弘法事业,他的西行求法经历反而在唐代社会留下更为深远的回响。这一历史错位自形成伊始就奠定了玄奘形象衍变的基本方向。概言之,唐宋历史语境中的玄奘形象从一开始就包涵神异特征,最晚自中唐起,西行求法主题日益凸显,并在世俗文本和西北时空环境中表现地尤为突出。其结果是玄奘“求法僧”的历史形象,逐渐被塑造成型。综合中日图史遗存,已知的唐宋时代玄奘图像有五类:一是源于玄奘生前,突出古来圣僧庄严崇高特质的写真肖像;二是再现玄奘译经场景的译经图;三是与当时大量涌现的行脚僧图像密切相关,类似敦煌行脚僧图,以稍晚的日本镰仓时代所谓“玄奘三藏像”为典型的单身行脚僧图像;四是在上一类图像的基础上加入摩顶松、深沙神等与西行有关的情节或人物,进一步强调西行取经主题的图像;五是重点表现西行道路所经的玄奘西行路线图。其中前两类时代较早,契合早期传记塑造的相对客观的玄奘历史形象。后三类时间跨度大,以“行脚僧”形象的玄奘为核心,通过不同形式表现西行取经主题,清晰反映了这一主题在8世纪以后的玄奘叙事中(尤其在世俗层面)成为主流,而且不断衍变和凸显的历史事实。
一方面,玄奘本身无疑是上述图像的核心人物甚至唯一表现对象,图像内涵大体上也未超越同期历史文本的叙事范畴。也就是说无论图像还是文本,其想象和虚构多属常见的历史或宗教叙事策略,更非主要内容。因此上述五类图像只能称为“玄奘图像”或“玄奘取经图像”,从整体上看与边地稍晚出现、叙事内涵更为丰富且已经文学化了的“早期西游图像”有着本质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诗话》和早期西游图像中求法行僧形象的唐僧就是文学原创,这一具体文艺形象的出现,事实上正是此前四个多世纪玄奘历史形象沿着西行主题不断衍变的最终结果。另一方面,与唐宋时代多数玄奘图史相比,在诸如敦煌写本S.2464《心经序》、日本说话集《今昔物语集》等文本和日本“十六善神图”等图像中,出现了一些使之更趋近于《诗话》和早期西游图像的人物情节增设与变化。其实这一现象正是西游故事文学化初露端倪的过程。总之,玄奘求法行僧形象在唐宋图史中的确立,无疑从一个重要侧面开启了玄奘历史叙事一变而为西游文学叙事的先声。
注释:
① 河西石窟已知6例图像:其中瓜州榆林窟3例,东千佛洞2例,参见王静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文物》1980年第9期)、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7-411页)等;古肃州文殊山石窟(今甘肃张掖市西北与酒泉市交界地带)1例,参见张小刚、郭俊叶《文殊山石窟西夏〈水月观音图〉与〈摩利支天图〉考释》(《敦煌研究》2016年第2期)。
② 陕北石窟已披露1例图像,参见李凇《陕西古代佛教美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192页)。据笔者所知,有关学者最新考古调查发现但未正式披露的尚有十馀例。
③ 巴蜀地区已知约3例:其中四川泸县1例,参见梅林《工匠文居礼、胡僧取经像及其他——四川泸县延福寺北宋石刻造像考察简记》(《广州美术学院60周年校庆教师系列作品集·论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118页);重庆大足石刻群2例,参见李小强、姚淇琳《大足石刻宋代两组取经图简说》(《敦煌研究》2015年第6期)。
④ 同样的请求又见于显庆二年(657)随高宗移驾洛阳期间,亦未获准。
⑤⑥⑧⑨⑮㉓㉜[唐]慧立述、彦悰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8-147、220、206-215、225、128、16、180页。
⑦ 关于玄奘晚年译经等问题,参见刘淑芬《玄奘的最后十年(655-664)——兼论总章二年(669)改葬事》(《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3期)。
⑩㉖ 相关记载,参见[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四《唐京兆大慈恩寺窥基传》及同卷《唐京兆大慈恩寺普光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3-66、68页)。
⑪[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高僧传》卷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8页。
⑫ 刘淑芬《唐代玄奘的圣化》,《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1期。
⑬㉝[唐]刘轲《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四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681页下。
⑭[唐]李延寿《夷貊下》,《南史》卷七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87页。
⑯[南宋]宗鉴编《释门正统》卷八,《卍续藏》第75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360页下;[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二九,《大正藏》第49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295页上。
⑰[南宋]志磐撰、[明]祩宏重订《法界圣凡水陆胜会修斋仪轨》卷二,《卍续藏》第74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791页上。
⑱⑲⑳[唐]李冗《独异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7、“序”页。
㉑[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十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2-193页。
㉒[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九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06页。
㉔ 写本图版参见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19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688-690页)。
㉕ 张石川《敦煌音写本〈心经序〉与玄奘取经故事的演化》,《文史哲》2010年第4期。
㉗ 不空曾“累奉二圣令鸠聚先代外国梵文,或絛索脱落者修,未译者译”([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页)。《房山石经》也存署不空译《梵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参见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编《房山石经》第27册(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430页)。加上大兴善寺与不空的关系,故定第二、三部分为不空译经应无太大问题。
㉘ 陈寅恪在讨论此本《心经序》时,曾结合《太平广记》“报恩类”故事的类似特征,认为许多小说故事最初或源于佛经序文。参见陈寅恪《敦煌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3版,第197-199页)。反之,其实佛经序文也可能源自小说故事。
㉙[美]梅维恒《〈心经〉与〈西游记〉的关系》,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㉚㉛ 张锡厚主编《全敦煌诗》,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6198、6189-6190页。
㉞㊲[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八,《大正藏》第55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560页中、562页中。
㉟[日]圆珍《智证大师请来目录》,《大正藏》第55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107页中。
㊱[唐]彦悰《后画录》,俞剑华编《中国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381、383页。
㊳[唐]靖迈《古今译经图纪》卷四,《大正藏》第55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67页下。
㊴ 目前已知的玄奘译经图像似仅此一例。
㊵㊽[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60、48-58页。
㊶[日]圆仁著、白化文等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记校注》卷三,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74页。
㊷[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卷上,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页。
㊸[唐]戴叔伦著、蒋寅校注《戴叔伦诗集校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27-228页。
㊹[北宋]欧阳修《于役志》,《欧阳修全集》卷一二五,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901页。
㊺㊻㊾[北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4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24,20,5、8、27页。
㊼[北宋]苏辙《栾城后集》卷三《武宗元比部画文殊玄奘》,《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20页。
㊿〔52〕 王惠民《行脚僧图》,《敦煌佛教图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4-97、105-111页。
〔51〕 具体的图像描述,参见孙晓岗《敦煌“伴虎行脚僧图”的渊源探讨》(《敦煌学辑刊》2012年第4期)。
〔53〕 具体的分类论述,参见刘淑萍《〈太平广记〉里的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4期)。
〔54〕[齐]王琰撰、鲁迅辑《冥祥记》,《鲁迅全集》卷八《古小说钩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71、576、592、599、602页。
〔55〕 如“释智聪……隐江荻中诵《法华经》,七日不饥。恒有四虎绕之而已。……聪曰:‘吾命须臾,卿须可食。’虎曰:‘造天立地,无有此理。’忽有一公……曰:‘师欲渡江,栖霞住者,可即上舩。’四虎一时目中泪出。聪曰:‘救危拔难,正在今日,可迎四虎。’……聪领四虎同至栖霞,舍利塔西经行坐禅……众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凶事,一虎入寺大声告众,由此警悟,每以为式。”([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唐润州摄山栖霞寺释智聪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768-769页。)
〔56〕 如《大唐西域记》今存最早版本即京都兴圣寺藏延历4年(785)写本(仅卷一、十二两卷,其馀各卷时代稍晚),现存镰仓早期以前写本至少还有十件;《慈恩传》传世日本古写本则更多。参见余欣《从吐峪沟到法隆寺:〈大唐西域记〉古钞本追寻纪略》(《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08-218、224页)。
〔57〕 有关日本说话集中玄奘叙事的梳理研究,参见李铭敬《玄奘西行故事在日本说话文学中的征引与传承》(《日语学习与研究》2013年第5期)。
〔58〕 快道注文见[唐]金刚智译《般若守护十六善神王形体》(《大正藏》第21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78页下)。
〔59〕 按《慈恩传》载玄奘过莫贺延碛时“于睡中梦一大神长数丈,执戟麾曰:‘何不强行,而更卧也!’”([唐]慧立述、彦悰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页)。前人多以此为玄奘与深沙神发生联系的最早记录,但这里实际仅言“大神”而未具体交代是何神只,因有“执戟”描述,故更有可能是指毗沙门本身。
〔60〕[日]常晓《常晓和尚请来目录》,《大正藏》第55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010页上、1010页下。
〔61〕[日]心觉《别尊杂记》卷五一,《大正藏》第88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611页中-611页下。
〔62〕 如奈良药师寺藏11世纪“慈恩大师像”、1136年僧观佑绘仁和寺本《高僧图像》中所含玄奘坐像等。参见李翎《“玄奘画像”解读——特别关注其密教图像元素》(《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4期)。
〔63〕[北宋]董逌《广川画跋》卷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页。
〔64〕[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59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