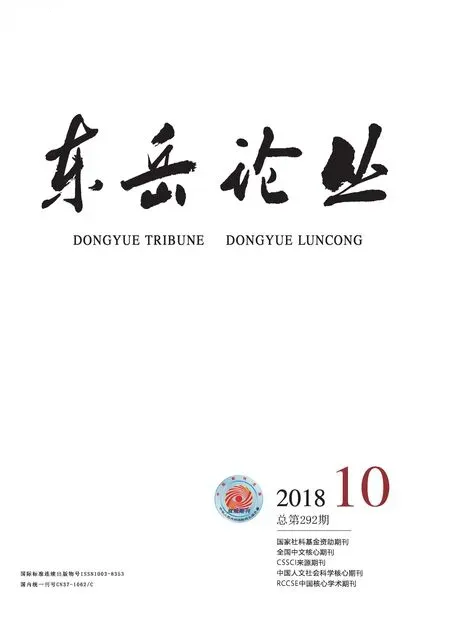辛亥革命时期美国对上海公共租界政策论析
田肖红
(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上海租界作为近代以来中国与列强交往的产物,它的发生、发展及最终走向消亡是一定时期内中国国际关系的体现。因此,国际交涉视野下的上海租界问题研究当具有重要意义。在上海公共租界形成、发展及走向膨胀的过程中,美国是除英国之外的另一主要推动力量,在某些特定事件中,美国所起的作用甚至要大于英国。作为近代中国改天之变的重大历史事件,辛亥革命的冲击力和影响力绝对而深刻,即使是被称为“国中之国”的租界也概莫能外。面对辛亥之变,上海公共租界利益相关各方积极活动并就相关问题展开了新的交涉,而美国在此期间的活动也成为其整体对华政策的重要内容。本文立足于辛亥革命时[注]本文中“辛亥革命时期”,泛指自1911年武昌首义至1913年二次革命结束的时期。有关上海公共租界的交涉问题,通过对美国外交档案的解读,探究和剖析美国政府在相关问题上的态度,希冀有助于深化国际交涉视野下的上海租界问题研究,并为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呈现更加丰富和细致的图景。
一、辛亥革命期间美国对华政策概况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美关系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多年来,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并取得了众多的研究成果。总体来看,学界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问题的研究视角是多元化的,既有从传统的官方决策层面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进行解读[注]赵金鹏:《美国政府与中国的辛亥革命》,《齐鲁学刊》,1994年第3期;崔志海:《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态度的原因分析》,《江海学刊》,2008年第5期;王晓秋:《帝国主义国家对辛亥革命的反应》,《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0月11日,A06版;崔志海:《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态度的再考察》,载《晚清国家与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陶文钊:《美国与中国的三次革命》,《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2期。,也有从传教士的反馈、美国媒体对辛亥革命的反应、商人利益团体的利益需求等角度进行阐释的[注]何大进:《辛亥革命时期的美国传教士与美国对华政策》,《历史档案》,1998年第4期;王静:《“觉醒的中国”: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革命》(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胡素萍:《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对袁世凯及辛亥革命的态度》,《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麦金农:《中国报道——美国媒体与1911年辛亥革命》,载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夏保成:《美国对辛亥革命的反应》,《史学集刊》,1988年第4期;尹全海:《评辛亥革命时美国的“中立”政策》,《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张小路:《美国与辛亥革命》,《历史档案》,1990年第4期。,还有着重探讨美国态度的变化的[注]张静,金仁义:《辛亥革命期间美国威尔逊政府的对华新政策》,《合肥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杨花伟:《试评辛亥革命期间美国威尔逊政府的对华政策》,《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本文根据既有研究成果对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状况作简要概述,以明晰辛亥时期美国对上海租界政策的基本背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响应,清王朝处于崩溃的边缘。针对中国的革命形势,10月14日美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兰斯福德·米勒(Ransford Miller)制定了一份对华政策备忘录,提出美国对华政策的5点基本内容:①由美国亚洲舰队保护长江流域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②将边远地区的美国人转移到外国租界保护;③在中国党派斗争中持“严格的中立态度”;④反对任何一国单方面的军事干涉;⑤遵守《辛丑条约》时各国共同制定的“协调行动”政策[注]Ransford Miller to Knox (Memo),October 14th,1911,Knox Papers,see James Reed,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1911-191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p.114-115.。该备忘录得到了美国总统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的批准,成为此时其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这份文件的基本内容可简要概括为如下几点:武力护侨、中立、列强间合作协调及重点保护租界。由此可以得知,租界在美国在华利益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并成为美国重点关注对象。
对美国政府档案的大量解读表明,自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至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美国政府在中国的各政治派别之间较为严格地奉行了“中立政策”。起义爆发后不久美国政府即认识到清政府的统治难以为继,很快便放弃了对清廷的认可和支持。11月,美国否决了由美国使馆单独为清廷皇室提供庇护的主张,12月又坚定拒绝了日本提出的保留清朝皇帝的建议。此后,在敦促南北和谈的过程中,又对清帝退位采取了一种乐见其成的态度[注]崔志海:《美国政府与辛亥革命》,李廷江,大里浩秋主编:《辛亥革命与亚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73-75页。。对于取代满清的实力人物袁世凯,美国政府虽然青睐有加,但在此期间也并没有给予实质性支持。时任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William James Calhoun)屡次提议扶持袁世凯,并建议给袁氏以财政资助,但国务院坚决主张在贷款问题上“应在中国的各派别之间严格中立。”[注]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as FRUS),1912,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9,pp.102-103,106-110.另一方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和革命政府,曾数次以各种形式联系美国官方代表并力争获得外交认可,但都没有获得回复甚至遭到直接拒绝。
研究还表明,尽管美国政府当时的中立态度较为坚定,但美国在华外交人员对中国革命及各政治派别的态度却不尽一致。以嘉乐恒为代表的驻京外交官倾向于支持袁世凯,对革命政府持不信任态度,而驻南方的外交官如上海和香港领事则对革命政府持肯定态度[注]崔志海:《美国政府与辛亥革命》,第68-69页。。就对孙中山的看法而言,美国官方的文件和报告中多是贬斥词汇,认为他不可以成为中国的领袖人物[注]薛君度:《武昌革命爆发后的美国舆论和政策》,《知识份子》,1987年第3期。。
在中国拥有商业利益的商业团体对中国革命没有将外人在华利益视为攻击目标较为满意,但又对中国革命造成的经济动荡和商业停滞表示不满。最为典型的是积极推动对华贷款的美国银行团在华代表司戴德(Willard D.Straight)的看法,他不喜欢清朝政府,但更愤恨革命。司戴德曾公开表示,清政府“已足够糟糕”,但“反叛者更糟”,“宁愿和满清打交道,也不愿和伍廷芳这样的蠢驴打交道”[注]James Reed,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1911-191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p.122-123.。美国在华传教士对革命的态度较为一致。他们认识到此次革命不同于1900年的“排外”运动,对在华外人采取了尊重甚至是保护的态度。对于革命派建立的共和政府,传教士基本上能给予同情和赞赏[注]薛君度:《武昌革命爆发后的美国舆论和政策》,《知识份子》,1987年第3期。,甚至有传教士积极参与了辛亥革命[注]何大进:《辛亥革命时期的美国传教士与美国对华政策》,《历史档案》,1998年第4期;胡素萍:《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对袁世凯及辛亥革命的态度》,《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美国宗教团体还举行各种活动敦促美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注]夏保成:《美国对辛亥革命的反应》,《史学集刊》,1988年第4期。。美国媒体对辛亥革命的反应是有差异的。在对辛亥革命进行报道的媒体中,大多数对革命不排斥外人和追求进步的政策表示赞赏和认同,并对革命的前景表示乐观;也有不少媒体对中国能否实现共和表示怀疑,还有媒体将革命贬斥为“荒谬绝伦”[注]夏保成:《美国对辛亥革命的反应》,《史学集刊》,1988年第4期;薛君度:《武昌革命爆发后的美国舆论和政策》,《知识份子》,1987年第3期;余绳武:《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政策》,《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
1912年2月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秉持“金元外交”原则的塔夫脱政府开始支持袁氏政府,这突出表现为具有政府背景的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开始对袁氏政府提供财政贷款。但塔夫脱政府直至卸任,都与其他列强一样始终没有给予袁氏政府以正式外交承认。
1913年3月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政府上台后改变了塔夫脱的在华“合作”政策,先是退出六国银行团,接着又单独宣布承认袁世凯政府。同年7月,由于不满袁世凯的专制政策和对外借款,国民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对此,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布赖安(William J.Bryan)给驻华临时代办卫理(Thomas Edward Williams)的指示称,“批准你有关在此次事件中严格地执行不干涉政策的观点”[注]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erican Charge d’ Affaires,July 28,1913,FRUS,1913,p.126.。然而,卫理给国务院发送的函件却不能表明他秉持了“不干涉”政策。他将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所进行的活动视为“叛乱、暴动”(rebellion/insurrection),认为“商人群体反对动乱和二次革命”,“政府很快可以将叛乱镇压下去”。8月底,卫理又很“荣幸”地向国务院汇报称“(北京)政府镇压南方各省叛乱的军事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注]The American Charge d’ Affair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913,FRUS,1913,pp.121-122,127-130.。
1913年11月,威尔逊选中的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到达北京走马上任。芮恩施是民主党政府对华政策的执行者,被认为同威尔逊一样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在上海公共租界问题上,我们将能看到他的表现。
二、辛亥革命前美国对上海公共租界的政策
辛亥革命时期美国对上海公共租界的政策,既是这一时期美国整体对华政策的一部分,也是历史上美国对上海租界政策的延续和发展。
美国是推动上海公共租界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租界诸多大小事宜之中,都能看到美国积极活动的身影。1843年11月,英国在上海取得租地权,开始在上海划定居留区,美国商人也开始在该居留区内租地,上海租界的历史由此开启。1845年,英国领事同上海道正式形成《上海租地章程》,取得对居留区的专管权力,法国也起而仿效。对此,美国的立场是,一方面反对英法等国在上海租界的专管权力,另一方面亦想为本国争得专有区域。1848年,上海道批准将虹口辟为美国居留区。
1853年,受太平天国运动及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影响,美国协同英法商议武装保卫上海外国人居留区,并推动修订1845年土地章程。1854年7月,在美国驻华专员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的参与下,英法美三国驻沪领事正式宣布经三国公使(专员)批准的“1854年土地章程”(即《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注]Correspondence of Humphrey Marshall,H.Exec.Doc.123,33rd Congress,1st Session,pp.213-215,US Congressional Serial Set,Archive of Americana.。不久,居留区又在“防卫”的名义下组建了行政管理机构“工部局”和警察武装“巡捕”,其性质也由此演变为“租界”。1863年6月,在美国驻沪领事熙华德(George Frederick Seward)的努力下,虹口美租界章程签订,确定了美租界四至,并比英法租界更进一步地夺占了中国在租界内的司法权和征税权[注]Burlingame to G.F.Seward,December 18,1866,Papers Relating to Foreign Affairs,1867,vol.1,New York:Kraus Reprint Corporation,1965,pp.430-431,pp.429,439.。此后,在美国首位驻节北京的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的推动下,美租界于1863年10月正式并入英租界,成为“上海公共租界”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面对这一时期在华外侨中普遍存在的将租界“据为己有”的倾向,蒲安臣又提出要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坚持“反让与地主义”,并将该主张统一进其著名的“合作政策”中,还争取到了英法俄时任驻华使节的赞同[注]Burlingame to W.H.Seward,April 18,1863,Papers Relating to Foreign Affairs,1863,vol.2,New York:Kraus Reprint Corporation,1965,p.851.。此后,出于对1854年土地章程的不满,蒲安臣又积极推动制定新的土地章程原则,支持工部局在征税、维持治安等方面对租界内华人进行管[注]Burlingame to G.F.Seward,December 18,1866,Papers Relating to Foreign Affairs,1867,vol.1,New York:Kraus Reprint Corporation,1965,pp.430-431,pp.429,439.。这一时期,美国对上海租界政策的基本原则形成,那就是:支持公共租界,反对专管租界;既与其他列强合作,支持租界的发展和租界面积的扩张,不放过租界问题上任何可以扩充本国利益的机会,又宣称尊重和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凸显与其他列强政策的不同,占取道义上的制高点,谋取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好感[注]田肖红:《蒲安臣对华租界政策考析》,《世界历史》,2013年第5期。。
此后美国在上海公共租界问题上的政策,都是在上述基本原则上的损益和发展。具体而言,美国的行动和政策主要体现在支持并积极推动公共租界面积的扩展、夺占和干预租界内中国司法主权、支持工部局越界征税和筑路、支持特殊情势下特别是战时“租界中立”等方面。以下谨对前两方面简要述之。
1863年虹口美租界章程对美租界边界特别是西北边界的规定并不确切,这为其从西北部扩展租界提供了借口。1873年,时任驻沪美领熙华德提出“重订美租界西北边界”一事,并划定所谓“熙华德线”,但因遭到当时中国地方官员的反对而未能确定[注]蒯世勋等编著:《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6-401页。。1893年,在时任美国驻沪副领事易孟士(W.S.Emens)主持下,中美双方代表拟定《上海新定虹口租界章程》[注]北洋洋务局纂辑:(光绪三十一年点石斋刊本影印)《约章成案汇览》(五),第2874-2878页,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年版;英文本见Municipal Council,Shanghai:Special Report on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Boundaries of Hongkew or the American Settlement at Shanghai,Shanghai:Printed at the “North-China Herald” Office,1893,pp.20-22.。据此,美租界西北边界大致沿“熙华德线”划定,面积也从1863年的346.67万平方米扩展至523.74万平方米[注]《租界·沿革》,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虹口区志》,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4/node2249/node4418/node20198/node20608/node62845/userobject1ai8202.html,2016年10月19日获取。。在虹口美租界实现扩张的刺激下,1896年3月,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作为驻京公使团领袖公使,正式代表列强向总理衙门提出扩充上海租界(包括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要求[注]Denby to Olney,March 25th,1896,in Jules Davids,ed.,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Series III,Vol.12,Wilmington,Delaware:Scholarly Resources Inc.,1979,p.163.。1899年,在驻沪美领古纳(John Goodnow)的积极活动下,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任命与其私交甚好的南洋公学监院、美国公民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作为他的代表之一与外方代表协商解决租界扩充问题[注]John Goodnow to D.J.Hill(Assistant Secretary),April 11th,1899,Despatches from U.S.Consuls in Shanghai,China,Roll.45,No.181.。最终,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势力的推动下,上海租界再次实现大扩张。
美国还积极干预租界内的中国司法主权。1864年,在英国和美国驻沪领事的推动下,在英美租界内组织成立了中国法庭“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以审理洋人控诉华民的民刑案件和违警案件。根据“领事裁判权”原则,在华英美侨民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法律管辖,因此该中国法庭主要审理华人及无约国人民为被告或被控的案件,包括洋原华被案件(洋人为原告华人为被告)。在商讨制定法庭基本章程时,时任美国驻华公使劳文罗斯(J.Ross Browne)及美国国务院对章程内容横加指摘,要求取消其认为与西方法律不相符的内容甚至表示不承认中国法庭的审判权[注]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201页;Jules Davids,ed.,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Series II,Vol.18,Wilmington,Delaware:Scholarly Resources Inc.,1979,pp.184-189,201-209.。1869年,《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经总理衙门及英美公使批准实施并据此在公共租界内成立了会审公廨(the Mixed Court)。此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在华代表屡次要求修改《会审章程》,以进一步扩大其特权。1879年,时任美国驻华公使、前驻沪领事熙华德偕同英国等国驻华公使联合致照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修改《会审章程》的要求并提出了详尽的修改主张,但被清政府拒绝[注]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五),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277,300-301,313-317页。Jules Davids,ed.,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Series II,Vol.18,Wilmington,Delaware:Scholarly Resources Inc.,1979,pp.248-258.。1901年起,驻华美国使领人员协同英国等国在华外交代表再次向清政府提出修改《会审章程》的要求,并于1908年基本获得了中国政府方面的认可[注]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9-420、444页;FRUS,1906,pp.404-407.。在会审公廨实际审判过程中,美陪审官对于中国官员的审判也是肆意干涉,有关此类事例多有记载[注]Jules Davids,ed.,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Series II,Vol.18,Wilmington,Delaware:Scholarly Resources Inc.,1979,p.227.。
辛亥革命时期,美国对上海租界的政策主要体现在以“维护租界安全”为名而采取的政策行动和在租界“会审公廨”问题上为维护和扩大其特权而采取的政策行动。
三、革命的冲击及美国维护上海公共租界“安全”的对策
在武昌首义之前,面对中国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英美即开始筹划保护长江沿岸各租界和外国人居住区的方案。1911年9月27日,美代理国务卿亨廷顿·威尔逊(Huntington Wilson)指示驻华临时代办韩慈敏(Pricaval S.Heintzleman,又译韩思敏),要他指令各口岸美国领事同当地英国领事紧密合作,以便在保护租界时协调行动。威尔逊还告知继任驻华代办卫理,美海军部长也已指示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令其和英国海军及美国驻华领事们紧密合作以保卫租界和外国人居住区[注]“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erican Charge d’ Affaires”,September 27,1911,FRUS,1912,p.162.。
辛亥革命爆发后,美国与其他列强联合宣布“严守中立”。上海领事团唯恐中国革命危害外人利益,于10月18日致函北京公使团,请求公使团同意领事团宣布上海中立。数日后,英国驻沪领事再次代表领事团致函公使团领袖公使,建议“上海口岸中立化”。公使团表示不能同意领事团的建议,原因是公使团所主张的“要在上海周围30英里半径内维持有效的中立,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而且我们各国政府对于这项建议,大致也不会同意”。但公使团还是指示领事团,“你们可以按照形势的要求,订立你们认为适宜的各种保护生命财产与租界安全的办法。”[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9页。11月3日,陈其美等领导“江南革命军”于上海起义,以响应武昌革命。起义当日,上海军政府发布对外通告,声明将尽力保护外人。然而,上海革命军起义的次日,根据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精神,450名美国水兵以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为由登陆上海公共租界示威[注]《民立报》,1911年11月5日,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9页;汤志均:《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701-703页。。美国总统塔夫脱还从菲律宾调集军队至中国以维护在华美侨安全。1911年11月美国驻华临时代办卫理曾致函国务院称,汉口领事团决定由外国军队“保卫租界”[注]“The American Charge d’ Affair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October 11th,1911,FRUS,1912,p.48.。可见,面对辛亥革命的冲击,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政府都将武力捍卫租界作为首选政策。但列强军队最终并没有大批登陆以保护“上海租界”。其原因是,“革命首领们并未蓄意干预租界”,且“外国派兵登陆将极大地激怒中国人”。他们认为,“马上派一艘最大的军舰或几艘军舰,是最合乎需要的”,即只要派出军舰即可起到震慑作用。对于英国政府派兵上海的打算,英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明确表示“没有立即采取该措施的必要”[注]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2-54页。。时任美国驻沪总领事维礼德(Amos Parker Wilder)一面告诫在沪美国人谨慎行事、严守中立,一面奉命同英法德日俄等国驻沪领事一起积极斡旋南方革命政府与北方袁世凯代表的议和。12月18日,南北双方代表在公共租界市政厅正式开始议和。两天后,维礼德及其他五国驻沪领事各自代表本国政府“非正式”向南北代表递交同文备忘录,内称:“本国政府认为,中国当前持续的战乱,不仅严重影响了其国家本身,还严重影响了外国人的物质利益和生命安全。迄今保持严格中立的本国政府认为,有责任非正式地提请双方代表注意尽快停止当前冲突、达成一致协议的必要性”[注]“The American Minister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State”,December 15,1911,FRUS,1912,p.55.。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对于租界应守之规则》,宣布了新政府对租界的政策。根据该规则,“上海公共租界、法国租界二处,行政、警察等权均操于外人之手,应嗣大局底定,再行设法收回。现时华人在租界内,暂不可率行抵抗或卤莽从事。”[注]《申报》,1912年1月1日,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6页。可见新政府采取了“暂时”维持租界“特权及现状”的政策。有了新政府的承诺,列强在上海公共租界内暂未再有大的行动。
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开始谋划建立专制独裁体制,引起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强烈不满。1913年3月,主张建立责任内阁制以限制总统权力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由此同袁世凯决裂,决定武力反袁。7月,被袁世凯免职的江西都督李烈钧组织成立了讨袁军总司令部,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讨袁檄文,二次革命爆发。数日后,陈其美出任上海讨袁军司令,宣布上海独立。袁世凯集中大批军力向讨袁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上海地区斗争尤其激烈。上海公共租界的“特殊地位”,使得上海地区革命党人的斗争又引发了一系列国际争端,其中最要者乃中国军队通过租界问题及将革命党人“驱逐”出租界问题。在这些问题中,都有美国的积极活动。
起初,上海革命军同袁世凯军的斗争主要是在南市进行,但革命军在此处的斗争遭遇失利,被迫转移至闸北地区。闸北部分地主绅商唯恐战争破坏自身产业,乃联合请求租界派兵保护,工部局便借此派出巡捕及万国商团(又称义勇队)[注]万国商团是租界当局为维持其统治而组建的准军事组织,因成员来自多个国家故称“万国商团”。进驻闸北地区,甚至进驻于闸北市政厅。7月26日,美驻华临时代办卫理告知美国务院,驻沪领事团已授权租界工部局发布“反对任何麻烦制造者”、“战事双方都不得大量陈兵市北”的声明[注]“The American Charge d’ Affair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26,1913,FRUS,1913,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9,p.126.。当日,工部局刊发的布告称,“上海西人租界原为贸易而设立,数日前近郊之乱,贸易受扰,界内秩序亦遭破坏,兹特宣告:或在本界,或于本界以北毗连各乡,不准作为行军根据及阴谋计策中点之用。两方面之中国兵弁,无论何方,均须迁出本界北乡之外,以免战事波及本界,而保卫各国守分商民之安宁。且军事领袖与有连带者,无论何党,或文或武,亦应由本界及本界北乡立即迁出,如违定行提究。”[注]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江苏人民革命斗争纪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1页。如此,以“免战事”、“保安宁”为由,在美英等列强的认可和支持下,中国军队进出租界及在租界附近驻兵的权利被剥夺,列强军队进驻了租界之外的闸北地区。对于工部局派兵闸北,北京政府一面表示此举为“防乱”,“与该处商民保全实多”,“本政府深为感佩”,一面又与美公使等商议“深望事平时,此项商团即行撤退”。闸北民众也以“洋兵保护华界,有碍主权”纷起反对义勇队进驻闸北,并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就此交涉。对于中国政府的要求,公使团表示“毫无异议”,工部局也不得不声明绝不“乘危越占”[注]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十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188页,第225-226页,第132页。。随着革命活动的平息,万国商团撤出闸北地区。
二次革命时期,袁世凯政府为缉捕“租界”内革命党人,还同列强展开了持续交涉。陈其美宣布上海独立不久,北京外交部即同公使团交涉,请求使团转饬领事团,使黄兴、陈其美等“离去租界境内”。该请求为公使团所接受。时任美国驻华临时代办卫理向美国务院汇报公使团如此行动的原因是,“为使租界免于卷入冲突,就职于任何一方军事力量的任何人物,都不得将租界作为筹划武力攻击之基地。”上海领事团发布告示称,“严禁任何麻烦制造者匿居租界,但驱逐此类人物应经过领事团的同意”。驻沪美领维礼德认为“驱逐”革命党人出租界应通过“司法程序”进行[注]“The American Charge d’ Affair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26,1913,FRUS,1913,p.126.。7月23日,工部局决议取消陈其美、黄兴等8人“租界居留权”。26日,经领事团核准后,工部局宣告要求黄兴等“离开租界”。革命军失败后,陈、黄二人不得不避走日本。
此后,北京政府外交部又多次以“禁止乱党活动”为名照会驻京公使团及美国公使等,请其饬令驻沪领事转请工部局协助“缉捕”或者“驱逐”革命党人。10月底,外交部请公使团转饬领袖领事将革命党人何海鸣“拿交华官惩办”,公使团同意照做,其中美国驻华代办卫理尤其“力主赞助”中国政府“缉获乱党[注]“The American Charge d’ Affair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26,1913,FRUS,1913,p.126.。11月初,外交部又请卫理等“援照何海鸣案”,饬令领事团将“匿居”公共租界之林虎、李烈钧“捕交华官、按律惩治”。对此,新任驻华公使芮恩施的回复是,“此项案件果能预照向例查出切实相当刑罪,本馆即当按照所请办理,倘无确实刑罪证据,在本馆观之,驻沪领事团对此案应办宗旨,当不外将该二人押送租界之外[注]“The American Charge d’ Affair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26,1913,FRUS,1913,p.126.。芮恩施之意,仍是坚持通过适当的“司法”程序,先经过会审公廨之“预审”,若预审证实上述人等有“图谋扰乱秩序”之证据,必将其“驱逐出租界”。
分析美国等列强在“维持租界安全”名义下采取的行动,其实质是以维护本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名义而维护其特权。租界的存在本身即是对中国主权的莫大侵犯,租界内市政、治安、税收等诸项事宜皆由外人控制并受各国驻沪领事团指导。二次革命时期,美国驻沪领事及租界工部局对革命人物的态度严格奉行了美国政府的政策,那就是在所谓“维持租界安全”的名义下任由甚至是助力袁世凯镇压革命。这由其驱逐革命党人出租界的行动即可窥见一斑。而这一时期列强借机侵犯租界内中国主权最为显著之行动,莫过于接管会审公廨。
四、辛亥期间美国参与接管会审公廨
前文已述,会审公廨设立后,列强并不满足,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在华代表屡次要求修改《会审章程》,以进一步干涉中国司法主权并扩大其特权。借辛亥纷乱之际,英美德等列强便一致行动,全面接管了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使得中国在租界内的司法主权荡然无存。
公廨作为中国政府设在租界内的司法机构,其主审官(即谳员)自应由中国政府任命,《设官会审章程》亦是如此规定的。然而,为自身利益着想,列强对中国官府任命谳员横加干预,美国外交人员也积极参与其中。早在1903年,英美德驻沪领事即有干预谳员任免之举动。这一年,时任公廨谳员张炳枢以“渎职枉法、办事不力”被参劾,沪道袁树勋不得不将其撤职,改派上海法租界公廨谳员孙建臣代理其事。对此,美、英、德驻沪领事竟致函沪道表示反对[注]关于张炳枢被撤职及三国驻沪领事具文干涉的时间,梁敬錞《在华领事裁判权论》一书称是光绪三十年(1904),而夏东元《20世纪上海大博览》则称是1903年。据笔者考证,1903年之苏报案即由孙建成审理,且1904年关炯已出任公共租界公廨谳员,故张炳枢被撤职离沪的时间应是1903年。。其函称,“政务日繁,孙某年老,不能胜任。张某撤差,难予同意,应转令其永留此任,否,亦当暂时留任。”不仅如此,该三国领事甚至在函中提出,“嗣后更换谳员,必须先行知照,俟本总领事等照允,始可办理”[注]梁敬錞:《在华领事裁判权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09-110页。。美领古纳更是踊跃,还多次致函沪道和两江总督魏光焘要求留用张炳枢[注]夏东元:《20世纪上海大博览(1900-2000)》,上海: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张炳枢最终虽不得不离任,但列强力图干预会审公廨司法权的欲望和要求却已经明白地暴露出来。辛亥之际,列强便有了如此行动的时机。
在1911年11月上海光复之前,时任会审公廨谳员宝颐(满人)等即仓皇出逃,沪道刘燕翼遂任命关炯[注]关炯,字絅之,今学者多误名为“关炯之”,本文均以“关炯”称之。为公廨正审官,王嘉熙、聂宗羲为副审官。然而,不几日上海军政府成立,刘道台亦逃至公共租界寻求保护。如此,关炯等谳员的合法性成为问题,会审公廨陷入权力真空时期。值此混乱之际,在沪列强迅速出手,公廨美国陪审官赫德雷立即向工部局提出处理会审公廨问题的六点意见。驻沪领事团协商后一致表示,赞同赫德雷所提意见,并跟据该六点意见拟定了接管会审公廨的通告[注]邓克愚,顾高地:《帝国主义在上海侵夺我国司法权的史实》,《上海地方史资料》(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7月,第125页。。11月12日,驻沪领事团正式发布如下通告[注]《民立报》,1911年11月12日,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0-1151页。:
照得租界华商居民人等,为数甚众。查民刑诉事件,本为特立之会审公堂(廨)办理。兹欲保守租界和平治安,惟有必使会审公堂与押所仍旧接续办理为急要之举。因此立约各国领事,特行出示晓谕居住租界之华洋商民人等一体知悉,揆情度势,凭其职位权柄,暂行承认已在公廨办事之关炯(絅之)、王嘉熙、聂宗羲三员为公廨谳员,仍行随同该领事所派之该陪审西官和衷办事;并准租界上海西人工部局巡捕收管公廨押所。尚有公廨所出业由该管领事签印之民、刑二事传单牌票,后经该管陪审官照例签印之谕单等件,均应出力照办。凡有公堂应持之权炳(柄),亦当极力帮助。为此出示晓谕,仰尔租界华商居民人等知悉……
该通告以所谓“暂行承认”为名行任命公廨谳员之实,谳员任命之权自此落入驻沪领事团之手。一个月后,上海领事团领袖领事致函北京公使团,其中确切讲明了驻沪领事使团在会审公廨问题上采取的新政策[注]《英国蓝皮书:关于中国事务的文书1912年,中国三号》,第111号,第138页,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44-1145页。。据该函件,公廨押所(即监牢)管理、传提嫌犯、公廨经费管理等诸多权力均由工部局巡捕房行使,公共租界内一应案件,无论民刑、轻重、是否关涉洋人,外国陪审官均得陪审,谳员审讯接受外国陪审官之指导,谳员及公廨其他工作人员的薪金均由工部局或领事团掌管,如此种种,使得中国当局在公共租界内本就残缺的司法管辖权几乎全面落入西人之手。该函虽称上述举措乃“权宜措施”,却施行15年之久,期间中国政府几经交涉,要求归还会审公廨,列强却每每以各种理由搪塞敷衍。
对于上海会审公廨完全为列强所操控之事实,民国政府亦有所认识。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所颁布之《中华民国对于租界应守之规则》,宣布了新政府对会审公廨的态度:“上海会审公堂,前此所派清廷官吏,大半冗阘,是以腐败不堪。上海光复后,该公堂竟成独立,不复受我节制,此种举动,理所必争,尤宜急图挽救。外交部自当向各领事交涉,使必争回,然后选派妥员接管,徐图改革。但交涉未妥之前,我军、民不可从旁抗辩,致生枝节。”[注]《申报》,1912年1月1日,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6页。新政府对租界会审公廨的政策,正如其对租界的“整体政策”一样,那就是,“维持现状,徐图更改”。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乘着新政府“无暇兼顾、维持现状”的罅隙,频频活动,将对“会审公廨”的管辖进一步扩大并力图使之常态化。
1912年1月5日,沪军都督府方面正式任命关炯等三人为公廨谳员,以示主权。7月,驻沪领事团以华洋诉讼繁多、谳员训案不暇为由,要求增加襄谳(即副陪审官),并擅自任命了前清襄谳孙羹梅,授之以委任状。时公廨正审官关炯认为“以领事委状莅廨任事”有碍国权,“恐将来会审官之用舍均须听命外人,公廨即不能独立”,遂将此事提交上海交涉使,由之与领事团交涉。然而,领事团方面却是迫不及待了。美国驻沪副领事海德礼(Frank W.Hadley)携孙羹梅突然到抵公廨法庭,欲强使孙审讯案件,被关炯断然拒绝。然而,领事团态度强硬,此事也最终以北京政府的妥协让步而告终[注]石子政:《关炯之与辛亥革命后的会审公廨》,《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4期。。
根据《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对会审公廨断案不满的上诉案件由上海道台及有关国驻沪领事主持。清亡后上海道台不复存在,驻沪领事团接管会审公廨后便自行讨论组织上诉机关。1913年初,领事团拟定会审公堂上控办法,“以总领事一员、正会审官一员、外国陪审官一员会同开庭作为上控公堂”。北京政府外交部闻讯立即向驻京美使等提出抗议,称“上海公堂上诉案件如系华人被告洋人原告,向章准赴道署控告,今道缺既裁,自应改归交涉使管理……现有特设上控机关之说,与历来遵行办法显然不符,如实有此事,本国政府碍难承认”。由于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该上诉办法暂未实行。1914年,根据中华民国新定地方建置办法,沪海道署于上海建制。这年底,根据《会审章程》之精神,沪海道尹杨晟于道署组织上诉法庭,受理混合案件的上诉案件。但是,领事团很快以“道尹公署未经外交团承认为上诉机关,贸然开审,殊与租界治理权有碍”为由,电请驻京公使团向外交部交涉[注]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791页。。最终,由于领事团坚不承认沪海道署为会审公廨之上诉机关,会审公廨断案后,即使有不服者亦无处上诉,租界内华人案件的审判变成了“一审终审制”。
自19世纪80年代起,会审公廨对须移交中国官厅审判之重大刑事案件逐步确立了“预审制”。对于中国官府要求移交的案件必先经由“会审公廨”预审,由外国陪审官断定是否证据充足后再决定可否移送。对于中国政府缉捕、移交革命党人之要求,领事团亦坚持此种“预审”制度。民国政府亦就此种“预审”制同驻京公使团进行了交涉。1913年7月,外交部向驻京美使及其他各国公使提出“取消此种违背定章办法”,“凡遇此等传提人犯事件,毋再要求预审,照章移交中国官厅”。9月,公使团援引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第三十二款,即“倘有中国人役负罪逃入大法国寓所或商船隐匿,地方官照会领事官,查明罪由,即设法拘送中国官”,坚称此项“预审”制度乃条约权利,拒绝了中国政府的要求。11月,中国外交部再次致电美使等进行交涉。中方指出,“中法条约第三十二款系指华人犯罪逃入外国寓所或商船隐匿者而言,与上海会审公堂权限问题然两事,且该约明文亦无司法上预审之字样。”坚持主张,“遇有中国官厅传提租界人犯事件,应即按照向例允许传提,勿再索取认证、要求预审”[注]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十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232-233页。。然而,中国政府的要求被美使等置之不理,会审公廨仍然坚持实行“预审”制度。不可否认,此种制度在事实上对租界内进步人士的进步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使他们得免于遭受独裁政府的肆意迫害和屠杀,但是,从司法主权的角度来看,会审公廨“预审”制是对中国独立司法权的践踏与破坏。
1912年8月,北京政府外交部设立“条约研究会”,为改订新约做准备。该研究会曾就上海会审公廨问题拟定一解决章程,外交部也向驻京公使团提出收回会审公廨的要求,但因北京政府当时尚未为各国所承认而无下文。1913年12月,外交次长曹汝霖正式照会驻京公使团,要求将“上海会审公廨交还中国政府”。1914年6月,经“各国驻京大臣详为酌夺”后,由领衔公使英使朱尔典代表公使团向外交部作出了回复。公使团在复照中称,辛亥年上海领事团接管会审公廨之后,“有数处办公之法,较昔略为改良”,“上海特别交涉员杨晨君,于去年(1913)十二月九日及二十八日致领袖总领事公函内,于交还公廨讨论时,代政府及接续之各政府,应允俟公廨交还之际,将所有此等改良之处,妥为保存”,“各国大臣愿将该公廨交还中国主权,惟应先由贵部正式备文,确行声明中国政府拟将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后所用公廨变法改良之办法,承认实行”[注]《领衔英使朱尔典致外交部照会》,1914年6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8-79页。。如果应允公使团之要求,公廨之各项实权将握于领事团及工部局之手,所谓“归还”则将是徒有虚名。面对公使团如此苛刻之要求,中国政府又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将公使团所提各款详加改进,俾使公廨部分权力能切实归还。但是,公使团又对中国政府之提案非常不满,特别是在有关承审官任命、上诉办法等条款方面,双方争执尤甚。关于公廨承审官之任命,公使团主张承审员“由中国政府委任,由领事团认可”,而中国政府认为,“公廨之员,由中国政府委任”,“将人员姓名通知领团,由外交部会同司法部荐请大总统任命”即可[注]《外交部致领衔英使朱尔典照会》,1914年6月11日,1915年8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1页。。1916年3月,外交总长陆宗舆亲往美使馆会晤芮恩施,就交还会审公廨事与之面谈。芮恩施表示,“政府果能选派具有才识学问之官秩较崇人员为委员长(即公廨主审官),本公使以为,应与上海特派交涉员官秩平等,但按之宪纲秩序,委员长当然列后。该项委员长在官僚中亦应具有识见法律专门学及审判时之公平性质,且中国政府果能设法将该机关增高、责任加重,实与上海大有裨益……今若知中国政府拟派上开人员为委员长,并慎选品端才优之人为副委员长,则美国政府亦愿将会审公堂商交中国政府。贵政府如愿照所商草合同办理,当于选派委员长以前,知会领事团,倘不合宜,领事均可否认。从此贵政府对于该项职员,苟能设法选派最优之人,即无虑不能自由派补”[注]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十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156页。。可见,美使不仅对公廨会审官之选派设置了众多条件,并且还坚持领事团有权“否决”中国政府对会审官的委任。最终,由于美英等态度坚决,中外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交还上海租界会审公廨一事被搁置下来。
分析美国在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事件上所作所为的实质,显然是趁机进一步扩大在华特权。塔夫脱如此,威尔逊也是如此,二者的在华代表及驻沪代理人在此事上的政策和行径也都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威尔逊政府及其驻沪领事在此事上显然不是“单干”,而是和其他列强“密切合作”的。
结 语
从辛亥时期美国对上海公共租界的政策表现来看,美国的根本政策就是维护甚至是借机进一步扩大美国特权和利益,并且是始终奉行了“门户开放”即与其它列强合作的原则。无论是共和党塔夫脱政府还是民主党威尔逊政府,无论是其在华外交人员还是租界侨民,他们都奉行了密切合作以最大化扩展自身利益和美国利益的行动和政策。这与历史上美国对上海租界的政策是一致的。因此,“合作”及“利益最大化”是美国对上海租界问题始终一贯的原则。这种合作既包括与其他列强的合作,还包括其外交代表与在华租界各层势力(如工部局、商民等)之间的合作。而“合作”作为手段,最终服务于“利益最大化”这一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