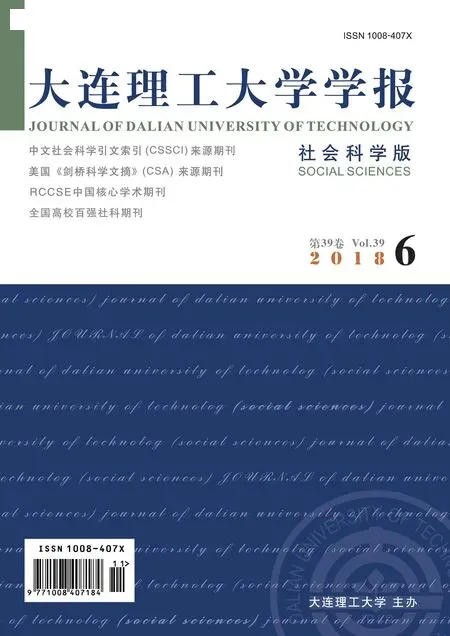《庄子》“工匠精神”美学探研
王 陶 峰
(南开大学 哲学院, 天津 300350)
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质量之魂,存于匠心。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恪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培育众多中国工匠。”工匠精神内涵包括对技术精益求精、敬业专注的职业伦理和工匠主体精神的自觉。
《庄子》中描绘了许多工匠由技入道的寓言,工匠由于技术专精而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塑造了许多技艺高超的工匠形象。如《养生主》“庖丁解牛”,《天道》“轮扁斫轮 ”、《达生》“佝偻承蜩”、“津人操舟”、“吕梁丈夫游水”、“梓庆削木为鐻”、《知北游》“大马之捶钩者”等。固然,庄子是在假借工匠之口阐述他的美学思想,以器物的制作过程来说明得道的方法与状态,其不自觉中隐含了道家对工艺技术——工匠主体精神——工匠职业伦理的认知,而与当下弘扬的“工匠精神”具有契合之处。本文拟在战国工艺审美和技术水平高度发达的背景下,解读《庄子》的技术审美,淡泊名利、敬业专注的职业伦理,工匠人格精神自觉,以及对工艺技术之“道”的美学阐述,管窥庄子“工匠精神”的美学意涵,对当代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一、《庄子》与工艺审美
《庄子》“工匠精神”美学是建立在先秦工艺技术高度发达、战国工艺审美倾向由伦理宗教向世俗生活转变的基础上的。
“工”包括工艺与工匠,即工艺技术和工匠。早期工艺是一种合目的性、个体性、手工艺主导、经验与灵感相结合的技术。工艺是在改造物质生产、制造器物的过程中形成的人类集体技术经验的总结,其中蕴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和工匠精神传承。
只有在工艺技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出深厚的工匠精神和自主的工匠主体意识。工艺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创造的合目的性的善与美的合一,工艺技术之美首先表现在以生产劳动为核心的社会实践过程,凝结在技术产品上,这构成了技术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1]。工艺之美是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功能技术之美。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巨大变革,都萌发于科学理论的新发现和工艺技术的广泛应用,工艺技术的革新促进了民众物质生活的改善、社会进步和人类精神文明的提高。
甲骨文卜辞中出现了“工”。之后,商周时期的工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社会地位,大部分是平民职业工匠家族[2]。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私有制产生,社会分工扩大、阶级社会出现、奴隶制国家的建立,使工匠成为社会中的一个相对固定的阶层,形成了为王室服务得到供养和管理“工商食官”和自主经营“工商居肆”两种生产模式。
商周时期正值我国的青铜时代。青铜器铸造工艺先进,工匠管理制度完善,已经出现了分工合作、标准化、细化的工艺流程。工艺审美由器物、技术、实用价值与形而上的“文”“道”“德”观念相联。周公“制礼作乐”以实现天人之和。《周易》中“制器尚象” “器以藏礼”“尚文修礼”,用“器”来领会和模仿天地之“道”。工艺器物审美观念中象征着周人对天人和谐秩序的追求。
战国“礼崩乐坏”,建立在周代封建宗法血缘制之上的伦理——宗教礼制崩解,生理感官世俗审美兴起,注重工艺浮华雕饰,客观上推动了工艺技术的革新。工艺审美的转向隐含着周代理想社会秩序的崩解和个体欲求的解放。
对工艺审美倾向的转变,诸子深感时弊,主张“以道驭术”,即技术行为和技术应用要受伦理道德的驾驭和制约[3]。首先,不同于儒家的“以礼节文”,道家主张回归原始,保持自我的本真、养生、贵生;《庄子》常以工匠寓言故事为例,来说明体道、养生之法,但客观上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先秦工匠技艺精绝和人格精神自觉的史实,也是漫长的工艺审美中传统历史人文积淀的结果。其次,《庄子》中的技术具有内在的矛盾性,一方面,显示出工艺技术在认识、理解、辨析事物内在规律中的科学价值;另一方面,又反对“为技术而技术”,主张工艺技术应超越日常实用,追求形而上的普遍规律、真理,以技进道。最终,工艺技术要尊重自然物性和符合人类文明之道,技合于道。
二、技合于道
通常而言,道家向往远古小国寡民的“至德之世”,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本性淳朴,遨游山林,自由自在。道家反对文明对人性的诱导,对工艺技术有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和保留。老子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论述工艺审美形而上的哲思,主张“道法自然”“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等。“朴”原初意是未加工的木料,即未经锯凿、未经雕饰的原木。“朴”还有纯朴、质朴、朴拙等意,引申为无知无欲、原始社会未经文明浸染的状态。
老子提出了道与技的一般原则,而庄子则将其具体到实践层面,将技术置于具体的日常感受活动中。庄子曾担任宋国蒙的漆园吏,“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列御寇》)。他可能熟悉当时漆器生产或曾担任相关管理岗位。宋国原是殷商遗民的封国,商人“敬天尚鬼”。宋与楚接壤,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庄子》中记载着大量的工匠寓言,说明庄子不仅是工匠技艺的旁观者、哲学家,而且拥有古老巫——商文化的渊源。
道家认为,文明的发展、人为的机巧使人丧失了本真,技术的革新被窃国者所利用,以道德仁义自饰,视生命如草芥,造成人心浮华、社会动乱。庄子反对这种人为的机巧的“器”,即为了实现个体欲望、功利的目的的“巧伪”,造成工艺的虚伪、巧饰、奢侈之弊,因而否定世俗浅薄之美,否定世俗感官的享乐,轻视世俗的机心。这与工艺为人合目的性的使用价值“善”相背离,与“法天贵真”的“美”相背离。
庄子认为,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不在工艺的结果——器,而在制器者的心思和意图上。他假借“汉阴丈人”之口,认为机械(器)“机巧—机心—虚伪—神不定—不能传道”。“汉阴丈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即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4](《庄子·天地》)
甚至,庄子要断工倕之指,胶离朱之目、摈弃感官之乐,摆脱人为的机巧(器)对人的自然淳朴和本真本性的诱导。“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5](《庄子·胠箧》)
进而,他认为人为的机巧改变了自然物真实的本性,是对其天性的残害。“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成玄英疏曰:“夫工匠以牺尊之器,残淳朴之本;圣人以仁义之迹,毁无为之道。”[5]
因此,在《庄子》中的“技术”分为人为机巧的、违背物性本真的小技(器)和探求本质性的、根源的、绝对的大美,即真正认识探究事物普遍规律的技术。他反对违背自然和物性的巧技,限制机器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对技术导致人的异化,庄子持有一定的警惕。技术的根本价值在于为民众生活服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饱含了《庄子》对人类生命存在价值的深切关怀。
《庄子》所赞颂的工艺技术之道,是在尊重物性和洞察普遍规律中人的力量的展现,是技艺的纯熟、高超精绝中凝结的人类物质劳动创造之美。《庄子·庖丁解牛》中,“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庖丁解牛的过程是写意的和诗性的,充满浪漫主义的想象。他用“触”、“倚”、“履”、“踦”描述庖丁手、肩膀、足、膝盖等,在技术操作中身体伸展的人类力量之美、技术之美。“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音》之会。”(《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的技术程序之美所带给观者的视觉、听觉、触觉的感官感受,升华为艺术的共感,即视觉化和听觉化的“音乐”的节奏和韵律,即技艺之“乐”(悦)。在审美感官上“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制止而神欲行”,用心的理性去理解事物的结构,而并非感官停留外在的表象,感官与心、心与物的合一。进一步,庖丁自叙能达到技艺高境,乃是“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即充分了解了对象的天然形质特征,洞悉对象的自然内在结构,“物性自然”。从而实现了“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遵道而行,实现了技术巧夺天工的境界。因此,他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庖丁所说他好的是道,并不是在技外见道,而是在技中见道。庖丁行云流水、逍遥自在、高度熟练的技巧实现了工匠身心合一、人技合一。因此,庖丁技艺施展的过程,也是技艺精绝而身心协调、解放的过程,是美的展示过程。
工匠是在长期大量技艺练习中,技艺专精,达到心手相应,主体与对象没有距离,化为技术的精熟, 成为无意识而合规律的本能。《庄子》中的东野御车“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梓庆削鐻“见者惊犹鬼神。”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庄子·达生》)大马之捶钩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庄子·知北游》)轮扁斫轮“不徐不疾,得之于心而应于手。”(《庄子·天道》)庖丁“依乎天理(依着事物自然的纹理),因其固然(顺着事物自然的结构)”。工倕“指与物化”等皆是技艺超群的专注于技艺创新的工匠,忘知忘欲,达到熟能生巧、得心应手的神技,凝结着人类的工艺创造和对技术劳动的尊崇。
《庄子》工匠寓言中的技艺不仅是技术的展示,也是道的运行的见证,从道器之道,转变为道技之道,道从思辩对象,进入日常经验的实践领域,技合于道[6]。“道”最初有道路、道理之意,引申为万事万物产生的本源和事物发展的规律。在庄子看来,技术的应用、规则,并不是真正的工艺之“道”,技术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它只是求“道”的入门引导。真正的技术之“道”是形而上的普遍规律与形而下技术应用的合一,又体现在实际技术活动中的程序,是操作层面的“道”[7]。以技进道,道在技中,“技”是技术活动的表层体现,道是技术的理想形态,道是对技术活动中真善美有机统一的高度概括[8]。
而且,技术的应用要合于自然物性、人类生存之道。从技术的层面上来看,“道”有方法、目的、步骤、过程等含义,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术语来说,道蕴含着简单的技术程序,每一步都受到科学规则的支配。技术活动是人在自觉意识支配之下人为的规定的程序化活动,技术知识就是有关人为规定的程序的方式、方法、规则的知识。所谓“技”合于“道”,就是使人为规定的程序合于自然的程序的过程,这意味着使人的生理心理活动过程与自然的程序逐渐同步,达到运用自如、天人合一的境界。
庄子认为,真正伟大的工艺技术是天道合一的技术,即人类在适应、改造自然的物质实践中自发发展的人类的本能才智。技术之道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技术熟悉、掌握事物内在规律和科学知识的自然之道。人的本质力量显现拓展、深化了人类的本能,实现了技术为人类服务的根本价值。因此,有论者指出,“高超的工艺审美创造往往能超越器质而成观念,突破形而下的特殊器质劳动创造之局限,而达于普遍性宇宙人生之道展示的形而上境界,极大地提升了物质生产劳动的精神性价值,提升了工艺品的审美品格。”[9]
《庄子》中的能工巧匠对技术精益求精,从感性自发经验上升为理性洞察普遍规律,技艺实践隐喻为普遍性的日常经验,技与道合一,这在我国“工匠精神”美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工匠主体意识自觉
《庄子》中的工匠依道运技,实现技术与道合一。在技术实践中消除人与技术之间的对立,技术不再是功利性的、目的性的,而具有艺术性、审美性的意味。工匠在技术的体验中得道,超越技术的束缚,实现物我同一,达到与宇宙融为一体的感受。工匠在技术实践过程中获得了对事物规律性认识的“道”,达到了审美创造之境。道技同一的技术实践过程,使身心生命的协调,使内在精神人格从自然到自觉,追求达到心灵自由至乐的审美体验和精神超越,工匠主体意识逐渐自觉。
自古以来,工匠皆以技术专精为安身立命和谋生的手段,将工艺的精能视作天命和一生的追求。工艺审美和科学思维内化为自身心智的充实,外化为主体的德性之美,与现代意义的工匠职业伦理暗合。
由于能遵道而行,庖丁实现了技与道合一。“(庖丁)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庖丁“提刀而立”善刀而自任,善用刀者,也是善用道者。庖丁解牛之后的自得,源自技术劳动之后的精神愉悦与满足。庖丁技术精绝展演的过程,以“牛”隐喻万物,其由个别到一般,由特殊到普遍,掌握了事物的内在结构知识和科学规律。其在技术的实践中获得的不仅是物质性的享受,而且也是审美、精神性的自我存在意识与满足感,实现了由技术到自主的人格境界,即工匠主体人格的自觉。高超的技艺创造打通了器质和物质层面的藩篱,突破了形而下的具体劳动创造的局限,达到了普遍性的宇宙人生展示的形而上的境界,提升了物质生产劳动的精神性价值,得到内心的自由感和充实感,实现了心灵解放至乐的审美愉悦之境。
在另一个寓言中,凝神于技“解衣盘礴”的真画者是一个不重财物、名位、权势,专心于技艺的工匠。“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4](《庄子·田子方》)“真画者”因技艺高超,心灵内蕴,不卑不亢,忘利外物,凝神于艺,忘却一切外在束缚,专心专注于技艺的展现,是一个心灵纯粹的工匠。
工匠在有限的对象中实现精神独立和主体自觉, 隐含了人类从技术的宰制中实现解放的可能性。“佝偻者”忘知、忘己,专精、凝注于外物(蜩翼)之上,非矜其技巧,由技艺的专精呈现虚静之心。“津人”操舟久习成性,适于水性而泰然自若。捶钩者不以功利之心制作捶钩,心系于一用而终成大用。梓庆专一专注于技术精纯,从稚拙到纯熟,发于天然,合于自然。
《庄子》中的工匠主观意识并非有意为了技术精绝,而是探讨在技术中实现理想的“人”的生存状态的策略,使人从“自然的人”到“自由的人”。《天地》“能有所艺者,技也。”《庄子》中的工匠技术操作,不是把技术当作一种生产或制作的技艺,而是把技术操作当成培养自我能力的训练活动,一种协助自我人性的完善和增进自我精神修养的活动。技术实践不是为了完成某个外在于人的目的,而是一个工匠自身和自我主体意识发现过程,是一种具有自我完成、自我实现“意味”的工夫实践活动。工匠享受、参与技术实践的过程,感受到一种自得之乐和精神愉悦,达到无为而自然的理想状态。工匠在技术操作过程中,发现、感受到人的潜能,因此,技术施展的过程成为审美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展示的过程。人在熟练运用技术操作工具所创造的物质世界中,直观感受到“人”自身的力量,从而达到人的自我主体意识觉醒。
工匠从技术经验中获得自我认同,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特质。技术实践的过程从技术的无意识到工匠主体精神自觉,从自然身份的依附到必然独立的自由王国,更意味着主体(人类)在对技术的实践中达至自由与解放。 《庄子》对先秦工匠人格主体精神美的推崇,突破时代局限,肯定人的力量,返归对人本质性的存在,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这正是《庄子》“工匠精神”美学的核心,是先秦工匠精神的飞跃。
四、《庄子》“工匠精神”美学的当代价值
柳宗悦指出,“工艺之美集中体现在日常用品之中,是超越个体之美的社会之美,无我之美。”[10]工艺应用于生活,工艺技术实践过程蕴含着工匠手工的温度和创造,蕴含着人类集体智慧和审美意识。
我国古代文化观念中对技术的轻视和工匠地位的贬低,似乎并不具备诞生西方意义上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条件。《庄子》主张的以技进道,肯定技术具有一定的独立的价值,但他认为真正的绝技不可学,不可用语言传授,唯有用志不分、凝神专注,“心斋”“坐忘”的心术,才能体会,从而导向了神秘主义。因而,庄子的工匠精神美学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和非科学性[11]。
由于中国文化的高度早熟,从而导向对形而上的超越追求,其在技术哲学层面并未产生与西方相类似的技术自律和纯粹的逻各斯。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技术应用在改变生活中的作用发挥和理论层面上的科学总结。李约瑟指出:“道家对自然的认识和技术应用,包含着原始科学的经验主义。但其技术之中一直夹杂着法术,而且,蕴含着只要技术而不求理论科学的精神。”[12]我国古代的工匠依赖世代经验、技术积累所形成对工具的操作个体经验的技能(skill、technique),是前现代时期来自于经验性操作层面的个人体会,与机器大工业化的时代的科学理论知识和相对完备的技术体系(technology)相比仍处较浅层次。但植根于民众生活实用的工艺技术,在实践中被不断发明、改造、升级,创造了中国高度发达的工艺技术体系和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凝结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才智,这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与儒家对工匠和工艺的轻视相比较,《庄子》工匠主体精神的自觉,则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性价值。《庄子》中的能工巧匠,尽管技术源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但是他们能够从技艺的展演中得到身心和精神的审美愉悦,如庖丁。这是审美无功利的“游戏”,是主体呈现出来的精神自觉,是对个体生存价值的肯定和审美高峰的体验。人类从技术(日常经验)中得到快乐,得到生活的乐趣,得到精神的满足,从而实现人性的完美与解放,这在当代技术主导的社会中仍具有启示意义。
五、结 语
《庄子》中蕴含了我国古代工匠精神的美学特质,可简要归纳为:第一,高度重视工匠技术精熟,达到心手相应;第二,工匠对技术专注和纯粹专一的心灵;第三,工匠主体精神从技术实用中达到自由解放。
庖丁、捶钩者、真画者、梓庆是我国古代无数优秀聪明才智的工匠的代表。他们与《大国工匠》中的周东红、高凤林、胡双钱等8位凭借自己的高超技艺、热爱本职、敬业奉献,数十年如一日对技术刻苦钻研、精益求精、追求职业技能极致化的现代工匠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当前,我国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工业4.0”的转化中,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发扬现代工匠精神,重视工艺技术在推动社会进步、改善民众生活中的作用,提高工匠群体的社会地位、加强工匠职业伦理和职业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倡导和建构中国当代工匠精神,从《庄子》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中汲取适合现代生活情景的文化因子,为实现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技术和文化支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