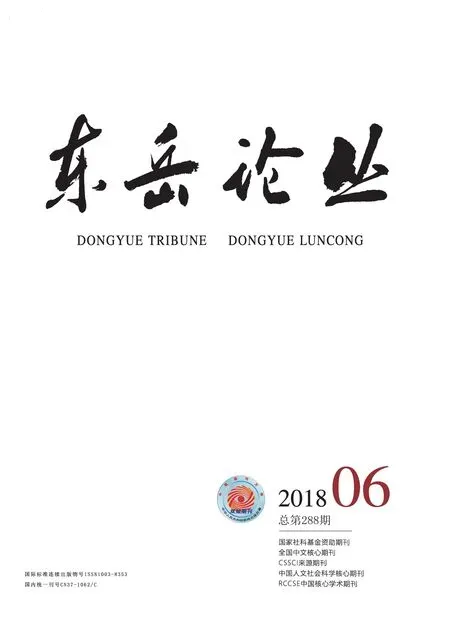20世纪 30年代胡秋原与左翼论争再思考
李金花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20世纪30年代初胡秋原与左翼的论争是现代文论史中最为重要的论争之一。细读文本发现,论战期间胡秋原以马克思主义者标榜自己,苏汶认为胡秋原与左翼是两种马克思主义的论争,而左翼则不承认胡秋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并将其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纵观胡秋原与左翼论争的学术史,1980年代以前论争被定义为敌我矛盾*80年代以前,胡秋原与左翼的研究有李何林《左联成立前后十年的新文学》《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新建设杂志社1951年),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罗荪《雪峰对“第三种人”的敌友观(再批判)》(《萌芽》1958年第8期),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华东师范大学函授部1961年),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高敬增《普列汉诺夫评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等,这些研究中将“自由人”“第三种人”定义为“反动文人”“敌人”,认为胡秋原以资产阶级自由论代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歪曲了马克思主义。;1980年代以来论争被定义为人民内部矛盾*叶德浴:《关于对“第三种人”斗争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1期),存煜、黄桥:《评左联跟“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包忠文:《左联文艺斗争中的几个问题》(《雨花》1981年第8期),陈早春:《鲁迅对“第三种人”的态度怎样》(《鲁迅研究百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苏光文:《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艺思想派别及其消长》(《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倪墨炎:《左翼文坛和“第三种人”关系的始末》(《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这些研究从同路人的角度、统一战线的立场来看胡秋原,大有反对极左思潮,倡导文艺自由的意味。,同时随着史料的发掘,论争面貌得以较客观呈现*胡秋原:《关于一九三二年文艺自由论辩》(《鲁迅研究月刊》1988年第12期),古远清:《胡秋原从“自由人”到“民族主义战士”》(《武汉文史资料》2001年第6期),古远清:《胡秋原回应〈红旗〉杂志的诽谤》(《钟山风雨》2010年第5期),秋石:《胡秋原与鲁迅的论战与纠葛》(《粤海风》2008年第5期),叶浴德:《关于鲁迅扣给胡秋原的两顶“帽子”》(《粤海风》2011年第1期),张宁:《同途·殊途·同归——鲁迅与胡秋原》(《文史哲》2012年第6期),裴高才:《鲁迅与胡秋原惺惺相惜始末》(《红岩春秋》2016年)。这些文献主要是通过胡秋原自述来再次呈现论争中的一些问题。;1990年代胡秋原的普列汉诺夫研究被重新注意到*何梓焜:《评胡秋原对普列汉诺夫艺术理论的研究》,《江汉论坛》,1990年第9期。;新世纪以后的研究集中在从两种不同马克思主义资源讨论论争成因*金理(《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及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徐元绍《盟主的态度,历史的高度——“文艺自由论辩”中鲁迅对胡秋原保持缄默态度原因之探析》(《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贾振勇《左翼文坛的理论斗争及鲁迅的姿态》(《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张景兰《“艺术正确”与历史困境——论“文艺自由论辩”中胡秋原与左联理论家的分歧》(《江海学刊》2010年第5期),黄念然《论左联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4期)。。进一步分析学术史可知,1990年代前对论争性质的判断是囿于意识形态的主观判断,缺少学理分析;进入新世纪虽然从双方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分析论争的发生,但未能区分论争中的学术讨论和政治分歧,论争中存在的非马克思主义资源被忽略了。那么胡秋原与左翼的论争性质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同自由的资产阶级的论争,还是两种马克思主义的论争?双方的论争如果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图谱的,那各自借鉴和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又是怎么样的?今天看来,论争双方在哪些方面围绕论学术的讨论,哪些是政治批判的?本文将从理论角度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一、论争双方各自的文艺批评观及理论资源
(一)胡秋原在论争中的基本观点及理论资源
胡秋原认为文艺本质是生活的形象表现,文学的目的只在表现生活,反对党派的功利文学。早在“革命文学”时期胡秋原指出,“文艺是社会生活真切、深刻的表现。能如此的便是永远不朽的伟作。文学的目的,并不在于教人‘革命’,然而在一个不平黑暗的时代,伟大的作品,也就无不有革命的精神”。“只问是不是正确的反映了人生。这才是批评文艺最正当的态度了。”*胡秋原:《革命文学问题——关于革命文学的一点商榷》,《北新》,1928年5月1日,第二卷第十二期。胡秋原在论争中指出“艺术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生活之表现、认识与批评。伟大的艺术,尽管表现批评之能事,那就为了艺术,同时也为了人生”,“艺术者,是思想感情之形象的表现”*胡秋原:《阿狗文艺论——民族文艺理论之谬误》,《文化评论》,1931年12月25日创刊号。。在此基础上胡秋原进一步提出文艺自由——“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决不是‘至下’,将艺术坠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文化与艺术之发展,全靠各种意识相互竞争,才有万华缭乱之趣”,认为“只有人道主义的文学,没有狗道主义的文学”,正如安特列夫所说,“文学之最高目的,即在消灭人类间一切的阶级隔阂”,暗示着取消文艺的阶级性。胡秋原明确提出反对党派文学,“伊里支说过文学应该是党的文学,强调过哲学之党派性。不过,一个革命领袖这么说,文学者没有反对的必要——然而既谈文学,仅仅这样说是不能使人心服的”*胡秋原:《浪费的论争——对于批判者的若干答辩》,《现代》,1932年12月第2卷第2期。,“革命政党乃至其文学团体,应在原则上承认文艺创作之自由,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作家创作之自由”,“一切的教条,命令‘警棍,加帽子溺爱’,阿好,不仅徒劳,并且首先是腐化并自杀无产者自身的”*胡秋原:《一年来文艺论争书后》,《读书杂志》,1933年2月第3卷第2期。。
胡秋原对功利性、党派性文艺的排斥,自然使他更加注重作品的艺术价值。早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胡秋原提出,“文学的真价值究竟是什么?是我们应该仔细地冷静地讨论的问题;不然,我们不独要误解文学作品,而且很容易在一种有权威的旗帜之下,制造出许多肤浅、俗烂的、挂牌劣货了”。在写作《唯物史观艺术论》时胡秋原指出,“政论的文学在阶级斗争紧张时期愈增其重要,然而阶级斗争并不是永久那么剧烈,它的形式是有变迁,而且阶级的对立也是有消减之时的。所以宣传文学决不是永久的范型的文学,文学除了宣传以外还有其本身本来更固有的特殊而永久的任务”*胡秋原:《唯物史观艺术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392页。,“艺术价值与马克斯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没有直接关系”*[日]平林初之辅:《政治底价值与艺术底价值——马克斯主义文艺理论值商榷》,胡秋原译,《小说月报》,第21卷第1号1930年1月10日。。胡秋原在论战中指出政治价值并不是艺术的全部价值。没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即使是政治的,也是无味的。不过对左翼来说,为了革命牺牲一点理论和艺术价值是可以理解的*胡秋原:《浪费的论争——对于批判者的若干答辩》,《现代》,1932年12月第2卷第2期。。
那么何种作品在胡秋原看来是价值高的作品?真实描写的作品要比标语口号文学有更持久的生命力。胡秋原在写作《唯物史观艺术论》时指出艺术作品只要对生活现象进行客观描写,就完成了艺术的使命,就有很高的价值。苏俄同路人作家描写的革命是光明与贫穷、黑暗、血泪的并存,履行了文艺的本来使命,艺术价值高。尽管同路人的作品在左翼作家看来政治价值低,不过随着政策的改变,被认为政治价值高的作品也会随之失掉地位。那些真实描写革命的作品比那些刻意宣传某种政治观念的作品要有更永久的价值*胡秋原:《唯物史观艺术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412页。。胡秋原因而批判钱杏邨的“非真实批评”,即只看作品是否革命、作品中是否有猛烈的口号,而“不去深入事象之本质;不去广摄社会之全景;不去捕捉大众之心理;不将大众生活中,不在自己的体验中,丰富自己作品之生命;不以健全的意识,敏锐之才能,去认识现代生活中之一切复杂事象;不去努力将大众的行动和所思所感,透入自己的意识,用生动的具体的形象描写出来”*胡秋原:《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拥护》,《读书杂志》,1932年1月30日,第2卷第1期。。
以上就是胡秋原在与左翼论争中的基本观点,对其思想形成的资源探讨则要回到“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在《革命文学问题》中胡秋原首先讨论文艺自由,用布哈林在1924年5月9日苏联中央委员会关于文艺政策讨论会的速记中“文艺自由竞争”的观点来反对左翼对“非革命文学”的排斥。接下来讨论文学的本质。胡秋原以普列汉诺夫以为文艺里的政治不能破坏艺术价值的观点来反对左翼在辛克莱影响下提出的“一切文艺都是宣传”;以沃伦斯基对“那把斯图派”的理论批判来说明将报纸上的论说插入作品的不恰当,文学不都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又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安特列夫、阿尔志跋绥夫等作家的人道主义作品为例,指出文学表现现实即可。这些作品虽然不是某一阶级的工具或武器,但因呈现“真实”,永远感动人。胡秋原以滕森成吉对“文艺和唯物史观”的阐释,说明艺术和政治、法律不同,不是由经济直接决定的,因而艺术具有独立性。最后胡秋原引用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以讨论文学与革命的关系。那些真实表现人生的作品是伟大的预言者和时代的先驱,具有革命性。文艺是不受压抑的,是自由的,超越常识、物质、法规的束缚。布哈林、普列汉诺夫、沃伦斯基、厨川白村等人的理论观念促成了胡秋原文艺思想的形成,但在与左翼的论争中,胡秋原抛弃了“苦闷的象征”,对“人道主义”的态度则是从肯定到嫌弃*胡秋原在《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拥护》(《读书杂志》1932年1月30日第2卷第1期)批判钱杏邨只是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来分析郁达夫,而不谈马克思主义,可见胡秋原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进行文艺批评。胡秋原曾在“革命文学”时期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来讨论文艺自由问题,而在《浪费的论争——对于批判者的若干答辩》(《现代》1932年12月第2卷第2期)等文章中以恩格斯、梅林以及柴特金等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讨论自由问题,且在这篇文章中回应瞿秋白对其“混杂安得列夫‘消灭人类间一切隔阂’的人道主义”批评时指出,“人道主义也是讨厌的东西”。胡秋原在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消灭阶级榨取制度。在论争初胡秋原《阿狗文艺论——民族文艺理论之谬误》(《文化评论》1931年12月25日创刊号)中对人道主义文学的肯定。冯雪峰在《并非浪费的论争》(《现代》1933年1月第2卷第3期)中指出胡秋原对安得列夫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辩护,在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这里冯雪峰从政治立场批判了胡秋原。。
胡秋原在留学日本期间写的《唯物史观艺术论》是中国研究普列汉诺夫文艺观念的第一本著作,兼及评论瓦朗斯基、托洛茨基、列宁等理论家的观点,介绍了苏联、德国、日本无产阶级运动中的文艺论争,讨论了文艺本质、文艺与经济、文艺起源、文艺个性与社会倾向等问题。胡秋原在与左翼论争中对文艺本质、文艺自由、艺术价值与政治价值、真实性与倾向性等问题的理解都可以在《唯物史观艺术论》中找到思想渊源。
胡秋原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解主要来源于普列汉诺夫。其一,文学是形象的思索。普列汉诺夫在《柏林斯基论》中认为“诗是藉形象而思索的”。其二,艺术是人生的反映与再现。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中提出的“五项因素公式说”认为“经济因素诸条件对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是间接的而且是媒介的事实”*胡秋原:《唯物史观艺术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62页,第432-433页,第395-397页,第408-409页,第400-401页,第389页,第387页,第388页。,艺术是对社会心理的反映。不过,普列汉诺夫在讨论法兰西戏剧、绘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时指出要理解艺术如何反映生活,需要理解生活之机构,而在文明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机构构成的重要条件。普列汉诺夫将艺术是生活的反映中的“生活”明确为阶级斗争,并在《俄国批评界之命运》中作了详尽阐释,即社会是由种种的阶级组成的,阶级趣味的变化是与社会关系的变化相关的,最终由社会经济而决定。普列汉诺夫在《车尼尔雪夫斯基》中进一步指出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艺术上也占据支配地位,支配阶级将自己的阶级意识反映在文学作品当中。
胡秋原阅读巴黎公社艺术政策以及卢那察尔斯基、梅林等人的著作后指出,艺术不必须为政府效力,应当给予诗人一定的创作自由,艺术有超出政治之外的东西。胡秋原认为托洛茨基最理解“自由问题”。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指出一些领域党要直接领导,而一些领域要采取合作的办法,还有一些领域只规定方向。“艺术领域不是要党去命令的领域。党能够而且必须去保护并帮助艺术,但是他仅是只间接地领导他。党对于各种真诚地努力行近革命,并且这样助成革命底艺术的造成的艺术团体,能够而且必须另加以信任。无论怎样,党不止,也不能居一种挣扎着而且仅与其他的文学团体竞争的文学团体底地位。”艺术领域应该实行较为灵活的政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党在艺术领域采取自由政策和不过问政策,党必须要适当地注意在什么场合干预,干预的程度如何。联共(布)在1925年发布的《在文艺领域内的党底政策——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指出一方面要援助无产阶级文学的成长,与投降的无产阶级文学做斗争,同时必须同傲慢、欺凌其他文学的无产阶级文学斗争;另一方面要宽容对待中间意识形态的集团,共产主义批评有必要排除文学上的命令和行政干涉,排除半文盲和傲慢、自大。
革命与艺术的关系、文艺的倾向性问题,并不是新的论争。《唯物史观艺术论》中介绍了发生在德国、苏联、日本的革命与艺术、文艺倾向性的讨论。胡秋原认为艺术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且普列汉诺夫和瓦朗斯基使他更深入认识艺术价值的客观存在。普列汉诺夫在《二十年间》《艺术与社会生活》《乌斯彭斯基论》等中认为作品是有艺术价值的,对作品进行思想评价之后,必须进行艺术分析③;还在《无产阶级运动和资产阶级艺术》中指出,曾鼓舞人的革命思想对于现时代的人反而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被厌恶的。艺术的重要价值与政治价值没有太大关系。艺术要有作者的理想,但是更要描写、表现,客观敏锐地观察。瓦朗斯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阶级眼光观察艺术,但是始终不忘记艺术作用中共同的客观价值。那巴斯图派高唱艺术的阶级性、艺术的武器作用,忽略了艺术的客观要素,将阶级斗争作为绝对的标准,认为不会有超阶级的艺术的存在。
胡秋原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源于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指出政论的艺术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政治与艺术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在一些时期政论的批评是很有益的。瓦浪斯基在《为生活认识的艺术与现代》中提出政论渗入艺术的三个条件。其一,著作家的主观,意识和政论,不可损害了艺术的创造。其二,主观的心情须要适合对象的本质。其三,政论与政略同时都要与人类的希望和要求相平衡。关于第一个条件,普列汉诺夫在《亨利克·易卜生》一文中指出在作品中宣传思想是必要的,但它必须成为他的血肉,融化于其身。关于第二个条件,普列汉诺夫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指出思想错误的作品无论形式多么光辉,也没有艺术价值。关于第三个条件,普列汉诺夫在《乌斯彭斯基论》中指出当时社会中的先锋思想由于政治观及观察方法的狭隘,也损害作品的艺术价值。
胡秋原所倡导的真实批评的理论来源呢?普列汉诺夫在《俄国批评界之命运》中指出,美学的任务在“观察各种历史时期,有支配势力的种种法则和态度是怎么样发生的这个问题而已。美学不是宣传艺术永久的法则,而是努力于研究决定艺术之历史底发达所根据的永久法则。”*胡秋原:《唯物史观艺术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28页。普列汉诺夫的《杜勃罗留波夫和奥斯特罗夫》一文在胡秋原批判钱杏邨时被引用,“生活真理在那作品中如何描写,在那作品中究竟表现如何的真实”*胡秋原:《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拥护》,《读书杂志》,1932年1月30日第2卷第1期。,来说明他对作品“真实批评”的认识;原文中普列汉诺夫是用以说明“现实主义的批评”,即“并不强迫艺术家接受什么东西。它对艺术家提出的唯一要求,可以用两个字来表示,那就是真实”,“它表示该民族和该时代的自然愿望越好,它就愈深刻和愈完满”*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曹葆华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94页。。
(二)左翼在论争中的观点及理论资源
左翼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党派性的。冯雪峰指出胡秋原的文艺自由,“是反对文学的阶级性的强调,是文学的阶级的任务之取消”*洛扬(冯雪峰):《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文艺新闻》,1932年6月6日第58号。。无产阶级要将列宁关于文学和哲学的党派性原则应当用在革命文学的创作上,但左翼内部的“指导大纲”,不存在谁对谁的命令,只是讨论;至于对一般的作家和批评家我们不会去强迫他应用,最多只要求认识、研究*洛扬(冯雪峰):《并非浪费的论争》,《现代》,1933年1月第2卷第3期。。瞿秋白认为胡秋原的文艺理论是反对阶级文学的理论,即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在阶级社会里,没有真正的实在的自由*易嘉(瞿秋白):《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现代》,1932年10月第1卷第6期。。
左翼认为艺术价值不是独立存在的,是政治的、社会的,但反对标语口号文学。张闻天纠正了左翼忽视艺术价值的错误倾向,认为并不是一切宣传鼓动的作品都是文艺的作品,“许多揭露现社会的矛盾,描写小资产阶级的没落的作品,可以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品,但可以是有价值的文艺作品”*科德(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文学月报》,1932年12月15日第5、6号刊。。此后,冯雪峰也在理论上反思艺术价值问题:“艺术价值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政治的、社会的价值,是可明白的了。艺术价值就不能和政治的价值并立起来;归根结蒂,它是一个政治的价值。然而正和一切的政治行动的价值是客观的存在一样,艺术价值是客观的存在;也正和评价政治不能根据庸俗的目前功利主义或相对主义的观点一样,不能依据目前主义的功利观或相对主义的观点来评价艺术”*丹仁(冯雪峰):《关于“第三种人”的倾向与理论》,《现代》,1933年1月第2卷第3期。。周扬则重新阐释了艺术价值和政治价值的关系,“不要把党派的文学误解成为‘因着政治的目的而牺牲真实’的,只‘可以替代一张标语或一张传单’而毫无‘艺术价值’的文学。我们认为政治的正确和文学的真实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如果这政治算得上正确的话。我们也并不否认一张标语或一张传单的宣传鼓动的作用,但我们需要更大的艺术效果。”*周扬:《文学的真实性》,《现代》,1933年5月第3卷第1期。
随着艺术价值与政治价值关系的深入讨论,文学真实与政治正确的关系问题浮出水面。张闻天肯定了客观描写真实的作品的意义,指出一些小资产阶级作家描写某一时代真实的社会现象的作品,虽然不是无产阶级的,但也有价值。张闻天之后的左翼批评家虽然肯定了真实性,但仍强调作家的倾向性。冯雪峰指出,除了宣传、煽动文学,革命文学之外,如果能暴露社会现象、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的崩溃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作品,也要利用*洛扬(冯雪峰):《“第三种人”的问题》,《世界文化》,1933年1月15日第2期。。虽然如此,冯雪峰还是指出文艺作品受作者意识形态性质的影响,因而无产阶级作品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有利;资产阶级则在文学中蒙蔽现实歪曲真理。冯雪峰在回应苏汶的误解时指出并不是只有狭义的宣传的文学才是斗争的武器,那些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现实、把握客观真理的作品,也是伟大的武器,但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坚守列宁所说的党派文学的立场上,才能做到。左翼文学的错误在于并不认可中立文学的存在,把有着无产阶级倾向的作品也归入到拥护资产阶级的文学中去了*丹仁(冯雪峰):《关于“第三种人”的倾向与理论》,《现代》,1933年1月第2卷第3期。。
自1928年以后,左翼紧跟日本、苏联的无产阶级运动,引进马克思主义。以上可见,左翼批评胡秋原时主要调动了“阶级理论”和“党性理论”。“革命文学”论争中,后期创造社引入“阶级意识”,倡导阶级文学理论。1928年第4期《文化批判》“新辞源”栏目定义了阶级意识:“同属一个阶级的人们,虽然也有贫富的等差,但其收入的源泉与获得生活资料的式样却是一样的。因这种经济的物质条件,阶级的成员明白在同一的阶级内,他们底厉害关系是一致,而且要与在经济的关系上完全相反的阶级抵抗,更非巩固地团结不可,这种对于共同厉害的自觉,对于他阶级的反目的自觉,称为阶级意识。”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被李初梨引进,李初梨在《自然生长与目的意识》中指出革命的知识分子要从外部将无产阶级意识注入到大众中:“中国现阶段底普列塔利亚文学,本来是中国普罗列塔利亚特在意识战野这方面底一枝分队,所以严密地说来,它应该是无产阶级前锋底一种意识的行动。”*李初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思想》月刊,1928年9月15日第2期。在与胡秋原的论战中,左冀对阶级性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其一,列宁的《论托尔斯泰——俄罗斯革命的明镜》*伊理支(列宁):《论托尔斯泰——俄罗斯革命的明镜》,嘉生译,《创造月刊》,1928年第2卷第3期。周扬《自由人文学理论讨论》(《文学月报》1932年12月15日第5、6号合刊)和《关于“第三种人文学”的倾向与理论》都引用了《论托尔斯泰——俄罗斯革命的明镜》(《现代》1933年1月第2卷第3期)。被左翼用来阐释作家所在阶级的世界观会影响文学作品的意识。其二,瞿秋白又在根据公谟学院“文学遗产”上的材料编译的《文艺理论家的普列哈诺夫》一文中指出,普列汉诺夫不依据列宁反映论而提出的“象形说”,只是照着实际生活描写大致相象的样子,认为艺术只是消极的被动作用,只是阶级和社会心理的被动结果,并不能够反映活泼的复杂的社会斗争,并不是社会的阶级的斗争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艺术一方面反映生活,另一方面是生活的一部分,艺术固然是经济政治现象的间接的结果,是研究社会现象的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材料,然而同时,也还是社会斗争和阶级斗争之中的一部分实际行动,表现并且转变意识形态的一种武器*《文艺理论家的普列哈诺夫》,瞿秋白译,见鲁迅编《海上述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黄芝威在1932年翻译的《普列汉诺夫批判》中批评普列汉诺夫对文艺的阶级性本质没有正确的理解,“关于文学的阶级的机能与文学作品之关系的不正确的见解,从文学的形象的特异性的抽象画,和可以证明普列汉诺夫对于文学上的阶级斗争的辩证法没有理解的,要想从这儿发现超历史的永久的基准的企图”,普列汉诺夫从马克思的公式——“存在决定意识”出发,但不曾依据反映的列宁的理论*IB:《普列汉诺夫批判》,黄芝威译,《文学月报》,1932年第1卷第65号。。
左翼的文学党派性观点来源于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对此一声、冯雪峰、瞿秋白都曾翻译过*一声节译《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发表在1926年12月6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成文英(冯雪峰)在1930年《拓荒者》第1卷第2期上发表题《论新兴文学》,内容是冈泽秀虎《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重译;1932年瞿秋白编译《L.N.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注解中译《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后鲁迅收入《海上述林》。该文长期被译为《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瞿秋白《“自由人”的文化运动》(《文艺新闻》1932年5月23日第56号),周扬《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文学月报》1932年12月15日第5、6号合刊),丹仁(冯雪峰)(《关于“第三种人”的倾向与理论》,《现代》1933年1月第2卷第3期)中引用了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是针对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鼓吹“无党性”“非党性”而写。布尔什维克认为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的美学理论根本错在不彻底的辩证法,把康德美学和费尔巴哈的美学观念混在一起,用“无所为而为”和“生理的欲望”来解释美的观念的发展,没有认识到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康德化的学说”“纯粹艺术论”“超越利害关系的艺术论”“美的分析”等理论,其在本质上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样的,蒙蔽和曲解现实的社会现象。这种观点的形成在于他脱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没有充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文艺理论家的普列哈诺夫》,瞿秋白译,见鲁迅编《海上述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列宁认为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解放自己,摆脱剥削,那么无产阶级的行动都是服务于阶级斗争的。在阶级社会中,是不会有脱离阶级而自由的观点的*《L.N.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瞿秋白译,见鲁迅编《海上述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5页,第236页。。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艺术家受制于资产阶级,受钱口袋的支配。所谓的自由,只是资产阶级的或无政府主义的空谈。生活在社会里,而又要祈求脱离社会的自由,这是不能的。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社会虚伪的自由的暴露,并不是为了创造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而是要使真正自由的无产阶级艺术同虚假自由的资产阶级艺术对立起来。无产阶级的自由文学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为劳动大众服务的。这种自由的文学是用无产阶级的经验创造出来的,由无产阶级自己表达。党的文学原则具体来说,“无产阶级文学不但不是个人或一伙人谋利的工具,而且它不应当带一点个人性质也不应脱离无产阶级底管治而独立。没有‘非党员’的文学家,也没有文学的超人。文学活动应当是无产阶级工作底一部分。它应当是工人阶级前卫军所推动的大机器当中底一个轮齿。文学应成为党的工作底一部分组织的,计划的,统一的,革命的。”*列宁:《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一声译,《中国青年》,1926年12月第6卷19号。
论战后期左翼才回应了初期胡秋原针对钱杏邨提出的“非真实批评”。这时瞿秋白已翻译和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文艺思想*这是国内第一次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对文艺现象的观察方法和宝贵意见翻译进中国。《现实》的翻译对左翼回应当时文艺界的现象有重要意义。尽管该书在瞿秋白去世后才由鲁迅整理公开发表,但是从当时左翼论争的观点中可见,他们已经熟悉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这里不一一考究。瞿秋白在《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的注释中写到“中国的苏汶先生曾经把‘现实主义’解释为客观主义,据他的意见:第一,只要有客观的态度,自然会描写到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的崩溃,以及社会主义的前途。这显然是不对的。恩格斯在这里指出没有阶级立场的哈克纳斯就不能够描写到工人阶级发展的事实。第二,他以为文学描写的‘真实’和政治路线的‘正确’是对立的,不能并存的。这也是错误的。这里恩格斯所指出来的,正是没有正确的政治见解,作家的现实主义就不够充分。巴勒札克因为有了比较正确的对于贵族没落的观察,所以就有更充分的现实主义”(参照鲁迅编《海上述林》,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9页)。以此可知左翼以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观及时回应现实。。其一,瞿秋白在编译《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介绍了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马克斯和恩格斯反对文艺之中的‘倾向性’,不是的,他们只反对表面的空洞的倾向性,反对那种曲解事实而强奸逻辑的‘私心’。这种浮夸的‘有倾向的’,‘有私心的’作品,他们说它是‘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学’。他们所赞成的是‘客观的现实主义的文学’”*《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静华(瞿秋白)译,《现代》,第2卷第6期,1933年4月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反对文学的倾向性,甚至鼓励文学的革命倾向,但是“革命的倾向应当从作品的本身里面表现出来”。因而,在马克思、恩格斯同拉萨尔论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席勒化”,提倡“莎士比亚化”,这意味着反对文学中主观抽象的思想,推崇现实主义的描写——不仅要表现做什么,还要表现怎样做。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文学是在作品中表现革命倾向的客观的现实主义文学*《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静华(瞿秋白)译,《现代》,第2卷第6期,1933年4月1日。胡秋原在《浪费的论争》(《现代》1932年12月第2卷第2期)中反对艺术家将艺术作为政治留声机,“马克思严厉地劝拉萨尔创造戏曲,‘要效仿莎士比亚,不要效仿释勒,不要将许多个性,变为时代精神之喇叭’,就是说不要当一个纯留声机。”不过,马恩并不反映艺术的倾向性,这是为胡秋原所忽略的。不过,可推测胡秋原较左翼更早接触到马恩谈艺术的几封书信。根据裴高才《胡秋原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中记载,胡秋原到日本后,接触到俄、德、法、英、美和日本等国的各种文字译文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朴列汉诺夫主义、佛理采著《艺术社会学》和《西欧文学发展史》等著作,其中以普列汉诺夫的理论为中心,系统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日译书,比较朴列汉诺夫与列宁主义的异同,以及与欧洲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加以比较。在《唯物史观艺术论》里他不仅肯定了文艺自由,而且在思想上形成了自己的信仰,即他崇尚“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称“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其二,恩格斯主张辩证地看客观现实描写的价值。恩格斯没有责备哈克奈斯没有写纯粹的社会主义小说,也没有要求一定要在作品中表现作者的社会思想和政治理想,反而肯定同路人作家对社会主义的宣传有一定的功劳。恩格斯所认为的现实主义,“是不管作者的观点怎么样,而始终要表现出来的”,“作者的意见越是隐蔽,对于艺术作品也就是越发好”*《恩格斯论巴勒扎克》,瞿秋白译,见鲁迅编《海上述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但作家并不是做一架照相机,简单地描写生活,丧失革命的倾向,将文学描写的真实和政治正确的见解对立起来,作家要努力通过文学作品去培养工人的阶级精神。
二、左翼对胡秋原的政治批判及其理论资源
今天看来,以上对胡秋原与左翼关于文艺本质、文艺自由、艺术价值与政治价值、真实性与倾向性的不同观念的考察,以及对双方各自思想资源的追溯,可知两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接受和不同理解,是论争发生的原因。论争双方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那么为什么胡秋原还是被左翼指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取消派”?以下让我们从理论层面来考察*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从胡秋原与十九路军、神州国光社、王礼锡的关系上来追溯对胡秋原的托派指控已经有充分的讨论。这方面文章有胡秋原《关于红旗之诽谤答史明亮先生等》(《中华杂志》1972年8月),胡秋原《关于一九三二年文艺自由论辩》(《鲁迅研究月刊》1988年第12期),古远清《胡秋原从“自由人”到“民族主义战士”》(《武汉文史资料》2001年第6期),古远清《胡秋原回应〈红旗〉杂志的诽谤》(《钟山风雨》2010年第5期),秋石《胡秋原与鲁迅的论战与纠葛》(《粤海风》2008年第5期),叶浴德《关于鲁迅扣给胡秋原的两顶“帽子”》(《粤海风》2011年第1期),张宁《同途·殊途·同归——鲁迅与胡秋原》(《文史哲》2012年第6期),裴高才《鲁迅与胡秋原惺惺相惜始末》(《红岩春秋》2016年)。另外,胡秋原在《第三种人及其他》(《读书杂志》1933年9月第3卷第7期)中的“时代转向”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知识分子转向,考茨基向右转了,而他本人是歌颂向左转向的。不过,胡秋原反对左翼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需要指出的是在裴高才所著《胡秋原传》中记载胡秋原在中学毕业备考武昌大学(武汉大学)之余,阅读了瞿秋白和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资本论解说》即考茨基写于1887年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由戴季陶和胡汉民于翻译到国内,还不涉及到考茨基右转的问题。在实际的行动中,胡秋原曾救助瞿秋白,参与《八一宣言》的润色等等。。
首先从理论上追问左翼对胡秋原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批判。1932年黄芝威译的《普列汉诺夫批判》中介绍了苏联对普列汉诺夫正统论的批判情况。普列汉诺夫哲学艺术上的错误是与他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相关的,批判普列汉诺夫是为了确立列宁主义的正统地位*IB:《普列汉诺夫批判》,黄芝威译,《文学月报》,1932年第1卷第65号。。寒琪在《世界革命文学》中提及了国际革命作家第二次大会之对普列汉诺夫、弗理契的观念论的、机械唯物主义论的克服*寒琪:《世界革命文学》,《文艺新闻》,第51期,1932年4月18日。。鲁迅在翻译上田进《苏联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现状》(1932年11月)一文中介绍了苏联“转型期”对“普列汉诺夫”的批判。瞿秋白在1932年编译的《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中具体介绍了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即他在文艺理论上有很大的功绩,但是他在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影响了他的哲学、文学观点。在哲学上,普列汉诺夫在批判马赫主义的文章里损害了布尔什维克;在艺术上,借批评高尔基文艺作品,说俄国民众是愚蠢的、俄国工人没有革命情绪,又批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文艺政策只是欺骗群众的手段。由此,普列汉诺夫脱离无产阶级,站在“和平革命”的立场上,在1905年后进行着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更一步说,在对俄国历史的评判上,列宁认为俄国革命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推翻封建沙皇制度,反对资产阶级,而普列汉诺夫轻视农民革命的可能性,主张依靠资产阶级走“改良”的道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普列汉诺夫在1905-1917年的革命中,采取的是孟什维克的资产阶级策略,拥护帝国主义战争。不过,瞿秋白也指出不能因为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是“反革命的”“孟什维克的”“无聊的”,就判断他的文艺理论是没有价值的,他承认艺术是斗争的手段,非“超阶级的”,只不过在审美观念上未能摆脱康德的“超阶级”的直觉主义,况且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以前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且参与过反取消派的斗争。
苏联的普列汉诺夫批判影响了左翼与胡秋原的论争,左翼将对文学问题的学术讨论扩大为政治批判,认为胡秋原以“文艺自由”为核心的文艺观的实质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观在文学上的反映。需要指出的是胡秋原清楚地知道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对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的判断,但他认为不能因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的错误而否定他的文学遗产*胡秋原:《关于拙著唯物史观艺术论及其他》,《唯物史观艺术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2-13页。。这恰恰是苏联国内普列汉诺夫正统论被批判的原因,即将哲学、社会学与政治问题相分离。论战之初瞿秋白就在编译《论弗理契》一文时指出,普列汉诺夫用所谓的“科学的文艺批评”对付“党派的文艺批评”,“无产阶级的党派立场是最觉悟的了解到无产阶级的利益的立场,这是合于客观事实的立场。离开无产阶级的立场就是离开现实社会现实的现象,就是离开人类社会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这样,还要去凌空想出什么抽象的无阶级的或者超阶级的科学真理和客观事实,那事实上就要走到资产阶级的虚伪的客观主义方面去。”*瞿秋白:《论弗理契》,《乱弹及其他》,上海:上海霞社校印,1938年版,第356页。瞿秋白率先从政治斗争的立场来批判胡秋原。其一,批判胡秋原的人道主义文学是资产阶级的。瞿秋白承认胡秋原所认为的一切文学存在都是合理的观点,但是问题不在于是否承认种种的阶级文学的存在,而在于为哪个阶级的文学而奋斗。胡秋原的勿侵略文艺在客观上帮助了统治阶级*文艺新闻社(瞿秋白):《“自由人”的文化运动——答复胡秋原和〈文化评论〉》,《文艺新闻》1932年5月23日第56号。《勿侵略文艺》中说明自己不否定民族文艺,也不否定了普罗文艺,只是站在自由人的立场,不主张只允许某一种艺术存在而排斥其他艺术。(《勿侵略文艺》,《文化评论》1932年4月20日第4期)。胡秋原在1979年出版的《文学艺术论集·前记》中说,“我主张文艺自由,反对以任何政治上的党派主义指挥文艺,也就是反对所谓文艺政策。这主要是对当时日益兴起的左翼文学运动而发的”。这一回忆性表述与论争时的表述有差异。,他所倡导的“只有人道主义的文学,没有狗道主义的文学”是错误的。18世纪革命的资产阶级文学之中有人道主义文学,但是20世纪的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有人道主义文学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混合生长,榨取和奴役人民*司马今(瞿秋白):《财神还是反财神》,《北斗》,1932年7月20日第2卷第3、4期合刊。。自由的、民主的、向着光明的、人道主义的文学,会陷落到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和唯心论道德论的泥坑里*《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瞿秋白译,见鲁迅编《海上述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需要补充的是,正如前文所述,胡秋原在“革命文学”时期和论争之初,都是肯定表现生活的人道主义文学的,但是在《浪费的论争——对于批判者的若干答辩》(《现代》1932年12月)回应瞿秋白中已经明确表达了对人道主义文学的厌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消灭阶级榨取制度。其二,批评胡秋原“艺术是思想感情的形象表现,艺术价值依据情感高下而定”的标准,因为这一标准没有说明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这是与他的“自由人”立场相关的。胡秋原这样的理论“恰好把普列汉诺夫的孟塞维克主义发展到最大限度——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旁观主义……”,他的学说是“百分之一百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易嘉(瞿秋白):《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现代》,1932年10月第1卷第6期。。周扬指出胡秋原在口头上拥护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列宁主义,但实际上阉割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他陷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里,从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出发,抹杀文艺的阶级性、党性、能动性和政治的优位性*绮影(周扬):《自由人文学文学理论检讨》,《文学月报》,1932年12月15日第5、6号合刊。。冯雪峰则认为:“胡秋原先生不能了解艺术的列宁的原则,不认识‘虚伪的客观主义’的错误,所以就不能了解关于艺术的武器的作用的那复杂的辩证法的关系,于是乎就至少不自觉地走到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立场了。”*冯雪峰:《并非浪费的论争》,《现代》,1933年1月第2卷第3期。
接下来我们从理论上探寻左翼对胡秋原机会主义和取消派批判的原因。左翼对苏联取消主义的接受早于机会主义。苏联文化界在1924-1925年间对托洛茨基取消主义的批判,从1928年左翼陆续翻译的《ideology战线与文学》《现代新兴文学诸问题》《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第一次无产阶级全联邦大会决议》《苏俄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现状》可以知道。这些文章都介绍了苏联文艺界对托洛茨基取消派的批判*《ideology战线与文学》(藏原惟人、外村史郎辑《新俄的文艺政策》,冯雪峰重译,光华书局1928年9月);片上伸著《现代新兴文学诸问题》(鲁迅译,1929年);《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第一次无产阶级全联邦大会决议》(藏原惟人、外村史郎辑《新俄的文艺政策》鲁迅译,水沫书店1930年);上田进《苏俄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现状》(洛文译,《文化月报》,1932年创刊号)。,即托洛茨基否定阶级斗争激烈时期,忙于政治斗争的无产阶级能建立自身的文化。托洛茨基“关于要经过怎样的路,而全人类底,社会主义底艺术才被创造的事,并无什么理解”*[日]藏原惟人、外村史郎辑:《文艺政策》,鲁迅译,上海:水沫书店,1930年版,第202页,第202页。,他的宣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艺术的方法”是否认艺术上阶级斗争的法则的,“艺术上的托罗兹基主义,便是诸阶级的平和底协同的意思,而主宰的职掌,于是全然剩在旧有的有产阶级文化的代表者的手里”。总之,文艺上的取消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观点。
再来看列宁对机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列宁的《革命与考茨基》于1929年被翻译到中国。列宁批判考茨基只是口头承认马克思主义,考茨基在讨论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时暴露了他的机会主义。他站在自由主义立场谈一般民主,而不谈哪一个阶级的民主,粉饰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抹杀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问题。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只能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不是考茨基所主张的和平地用民主方法。纯粹的自由主义者才鼓吹“纯粹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虚伪的,只保护少数,对群众来说,不能参政、参加集会,没有出版自由,社会主义的宣传家要揭穿这种虚伪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是为了绝大多数被剥削的劳动大众的。虽然考茨基承认阶级斗争,但是不同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他试图站在中间阶级的立场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行阶级合作,维持“社会和平”*V.I.Ulianoff(列宁):《革命与考茨基》,胡瑞麟译,中外文学研究会,1929年,参照《考茨基怎样使马克思成为一个庸俗的自由主义者》《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两章。。在1929年翻译到中国的《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指出考茨基在同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论战时就已经显示出动摇。伯恩斯坦非常喜欢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把现成的国家机关拿在自己手中,而为着自己的目的去利用这个国家机关”*N.Lenin:《国家与革命》,中外研究学会译,上海中外研究学会,1929年,第178-179页,第179页。,而这一观点与恩格斯相违背,即“工人阶级应该破坏击碎和掘去(恩格尔斯所应用的字眼是‘Spiengen’——‘破裂’)整个的国家机关。”伯恩斯坦反对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后的过分的革命。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的批判避免从机会主义角度上分析,说马克思曾说过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政权,但是能掌握,且在反驳伯恩斯坦时说,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要心平气和地解决,而不是暴力打碎。列宁批评伯恩斯坦派主张把在国内外活动的社会民主党统一起来、要求机会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把社会民主党变为改良的民主党,并将“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主义运动中的来的自由”*《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页。1933年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列宁选集》中文版第3卷,译者未署名(这一版本笔者尚未找到,根据北京图书馆编《列宁著作在中国》中的记录)。1921年《新青年》第9卷3号李大钊发表《俄罗斯革命的过去与现在》列宁在文中列了《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帝国主义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国家与革命》,提出建党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1925年中共四大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运动”;李初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的写作涉及《怎么办?》中的观点,等等。综上,可以判断列宁《怎么办?》在中国已经有所接受。。俄国工人运动开展初期,不同分子联合起来,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混入其中,倒向伯恩斯坦,把工人运动缩小为共联主义。列宁主张同“批评派”“经济派”“思想家”等划清界限,同腐蚀工人阶级意识的行为斗争。
以上我们梳理了苏联的取消主义、机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批判在中国的接受情况。从时间上看,早在胡秋原与左翼论战前的192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发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提出肃清党内的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反对派。左联成立以后,先后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1930年8月)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1931年11月)两个文件中提出在文艺战线上同托洛茨基取消主义斗争,反对取消派、艺术至上主义、改良主义机右倾机会主义;又中国社会科学联盟发表的《反社会民主主义宣传纲领》(1930年8月)和朱静我的《取消派与社会民主党》(1930年8月)中都提出要同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和取消主义做斗争。从当时的历史场域来看,左翼对胡秋原的政治批判是受苏联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影响下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文艺批判活动中的一部分。冯雪峰认为胡秋原是“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注意马克思主义的赝品’的名义,以‘清算再批判’的取消派的立场,公开地向普洛文学运动进攻,他的真面目完全暴露了。他嘴里不但喊着‘我是自由人’,‘我不是统治阶级的走狗’,并且还喊着‘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列宁主义’,然而实际上是这样的。这真正显露了一切托洛茨基派和社会民主主义派的真面目!”*洛扬(冯雪峰):《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文艺新闻》,第58期,1932年6月6日。周扬认为胡秋原对文学绝对自由的观点与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对真正自由的文学的阐释背道而驰,和党派性相对立,他对“无党派性”的主张与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等人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本质相同*周扬:《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文学月报》,1932年12月15日第5、6号刊。。
结 语
通过从理论上对胡秋原与左翼论争相关问题的再梳理,可知双方的讨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同自由的资产阶级的论争,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宏大的思想图谱中展开的,但因为双方接受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话语资源,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理解而产生分歧。今天看来,一方面双方的论争是基于学术立场的讨论:胡秋原主要受第二国际普列汉诺夫等影响,强调文艺的独立性、艺术性和真实性,避免文艺沦为政治的工具;左翼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第三国际列宁的影响,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党性和倾向性,以配合革命斗争。另一方面论争中左翼将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扩展到政治上的批判,左翼将胡秋原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取消派”,这是因为中国左翼将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中的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批判直接复制到国内,而胡秋原恰好以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等的观点为理论武器。需要指出的是,论争中胡秋原被左翼批判的人道主义思想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是左翼认为胡秋原政治上有错误的一个原因,而胡秋原于1932年底已将人道主义舍弃,但左翼却未能注意到胡秋原的这种变化,并继续批判胡秋原的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