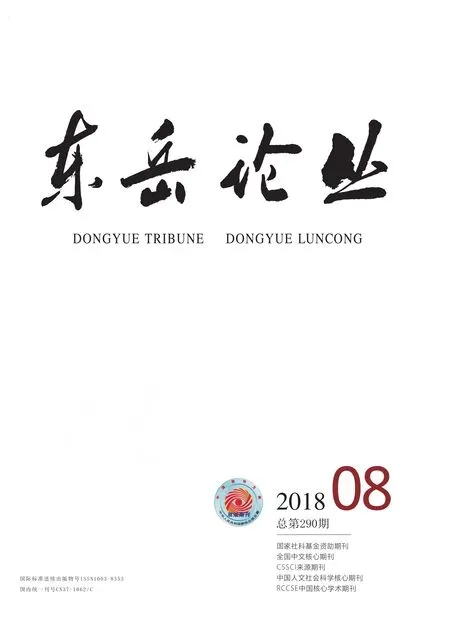“清华八年”:梁实秋挑战型学术人格成因探究
刘 聪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梁实秋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与他相关的大大小小的文学、文化论争有十几起之多,如:与王造时的“孔教问题”论争;与周作人的“丑的字句”论争;引发吴稚晖的“灰色的书目”论争;与胡适等人的《草儿评论》论争;与蹇先艾等人的“新某生体”论争;与郁达夫“文人无行”的论争;与鲁迅“人性”与“阶级”问题的论争;与朱光潜关于“文学的美”的论争;与文协等关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等等。这种且行且战的学术人格,是一种典型的挑战型学术人格。本文试图解析梁实秋的“清华八年”,探究这种学术人格的养成原因。
清华学校(现清华大学的前身)是塑造梁实秋学养和品格的重要之所。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校园文化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品格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如同一个人的成长有童年期一样,清华八年就是梁实秋的学术童年期。它塑造了梁实秋初始期的学术生存心态,这种学术生存心态在他一生的治学历程中,有相对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如同人类的童年经验在人一生中的重要影响。布迪厄在他的社会学论著中将“生存心态”(habitus)①大陆翻译界将布氏的这一概念译为“惯习”([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台湾学人高宣扬在其著作《当代社会理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中将其译为“生存心态”,他曾就这一概念的翻译问题亲自请教过布氏,布氏肯定了这一词的用法。描述为一种“持久的预设及原则”,认为它是行动者内心的制动系统,影响着行动者的行为。同时它还是一种“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随经验而变化,但“初始经验必然是优先的,更为重要。”②[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页。对梁实秋而言,清华八年的教育构成了梁实秋学术心态的基点,它赋予了他中西文化化合基础上眷顾东方文化的文化立场和舍我其谁的领袖意识;而这些心态又使他在面对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而建立起来的新文学场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话语差异,并在不甘平庸中充满了由后起焦虑而激发的挑战意识。
一、立足东方,领袖天下——清华八年的教育导向
清华学校是一所有特殊背景的学校,它是建立在美国退赔庚款的经济基础上,由“游美学务处”—“游美肄业馆”—“清华学堂”发展而来,由一个负责招考学生遣派美国的办事处,发展成一个学制八年的培训学校,这一过程本身暗含着中国与美国之间在留学生培养上的控制与反控制,其本身就是一场中西文化的抗衡。美国之所以能同意退赔庚款,完全是出于从精神上征服中国的文化策略。“1906年,美国伊里诺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校长詹姆士(Edmund J.James)给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备忘录》中说:‘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稿第一卷—清华学校时期(1911-1928)》,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第72页,第267页。他对当时中国大批学生留学日本和欧洲表示十分着急,认为“这就意味着,当这些中国人从欧洲回去后,将要使中国效法欧洲,效法英国,德国,法国,而不效法美国,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推荐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教师到中国去担任负责的地位,而不是请美国人去。这就意味着,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商品要被买去,而不买美国的商品。各种工业上的特权将给予欧洲,而不给予美国。”②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稿第一卷—清华学校时期(1911-1928)》,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第72页,第267页。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为什么要在退赔庚款的谈判中,以赔款必需完全用来培养赴美留学生为条件。
而洞察美国战略的中国当然也不会坐视不顾。由于国内符合赴美留学条件生源的短缺,以及朝廷对于留学生有可能全盘西化思想激进的忧虑,外务部和学部决定筹措设立一个专门的留美培训学校,在学制的问题上,采用了八年一贯制,这是外务部与学部争议的折衷方案。他们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应选派年幼学生还是成年人?是希望学生全盘接受美式教育呢?还是坚持中体西用原则?1909年接袁世凯任的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依据自己随容闳留学美国的经验,主张多派幼生直接留美,以便完全接受美式教育,养成现代人才,回国后分送到全国各府厅州县,进行各地之改革,推动中国之现代化。而学部则秉承张之洞的遗旨,主张应派有国学专长的成年人,以免洋化忘本。”这样经双方妥协,采取一个折衷方法,让学生在国内接受长期的养成教育,然后再赴美留学,这样既可以为学生打下中国文化根基,又避免了完全西化的现象。此外,还要求在美国设立一个“游学生监督处”,就近监督留学生,以免被美国同化*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2页。。
清华校歌中也体现着这种精神:“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然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爰跻,祖国以光。”校歌中所发扬的除了“岿然中央”的精英意识之外,还尤其强调了东西文化化合的治学精神。在《清华中文校歌之真义》中有这样的阐释:“与本校最适宜,且今世最亟需之学术,尤莫亟於融合东西之文化。故本校歌即以融合东西文化为所含之‘元素’。……此吾人所以不妨一日三复白圭也。”④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稿第一卷—清华学校时期(1911-1928)》,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第72页,第267页。从治学的路径上来说,清华的宗旨在最初即与作新文化运动旗手的北大学人群体相冲突,而梁实秋与五四文坛的冲突在这里即已埋下伏笔。
由最初的游美学务处,到后来的游美肄业馆,再到清华学堂、清华学校,直至1928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人走的是一条逐步摆脱西方文化的控制,走向文化学术独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眷顾成为他们削弱西方文化控制,确立民族文化自信心的主要方法。在清华人的眼中,“……清华之成立,实导源于庚子之役。故谓清华为中国战败纪念碑也可;谓清华为中国民族要求解放之失败纪念碑也亦可;即进而谓清华为十余年来内讧外侮连年交迫之国耻纪念碑亦无不可。清华不幸而产生于国耻之下,更不幸而生长于国耻之中。缅怀往迹,曷禁悲伤!所可喜者,不幸之中,清华独幸而获受国耻之赐。既享特别权利,自当负特别义务。”*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稿第一卷—清华学校时期(1911-1928)》,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第11页,第261页。这特别的义务,即是由国耻而引发的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尊重与发扬。
尽管官方意志中的清华应该是东西化合的,但出于让学生适应美国学习生活的现实需要,它的办学方针几乎完全是美国式的,课程的设置、教材、课外活动等全是美国风格的,英语教学是主体,汉语教学则退为其次。这种状态使得清华学校长期处于国内文化舆论的谴责之中。因为清华的课程设置方式,使很多学生无形中蔑视本国文化,崇拜西洋,与官方的意志相左。梁实秋的心理却恰恰相反,对东方文化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深深的眷顾之情。他常常在英文课上捣乱而非常尊重国文老师,并为国文老师受到的与英文老师的不同待遇而不平。正是这一因缘使他在清华学校遇到了一个对他后来的文学生涯影响很大的老师徐镜澄。而梁启超赴清华的一次演讲,更进一步推动了梁实秋的文学步伐,使他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如此,他还参加了清华学校的“孔教会”,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在校学生组织的“孔教会”,他不仅是孔教会的评议员之一,还是孔教会下设的“乡村教育研究所所长”,在引进西方文化的北京大学学生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的时候,他则担任清华孔教会的会刊《国潮周报》的编辑。他强烈批评上海的西方化现象,并说:“我希望我们中国也产出几个甘地,实行提倡国粹,别令侵入的文化把我们固有的民族性打得片甲不留。”*梁实秋:《南游杂感》,《梁实秋文集》(第6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页,第166页。他甚至呼吁即将出国留学的清华学子:“……我愿大家——尤其是今年赴美的同学——特别注意,若是眼珠不致变绿,头发不致变黄,最好仍是打定主意做一个‘东方的人’,别做一架‘美国机器’!”③梁实秋:《南游杂感》,《梁实秋文集》(第6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页,第166页。
综上可知,矢志立足于东方文化立场上的梁实秋,面对胎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学,自然是百般龃龉。梁实秋的儿子梁文骐在父亲去世后,称他父亲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中国读书人,可见梁实秋的这种文化心态贯穿了他的一生。
中国对这批留学生的期望值是非常高的,在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三日(1909年7月10日)外务部给朝廷的奏折中,直接阐明了朝廷对庚款留学生的期望:“造端必期宏大,始足动寰宇之观瞻;规划必极精详,庶可收树人之功效。……”④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稿第一卷—清华学校时期(1911-1928)》,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第11页,第261页。因此清华学校在人才培养方向上,突显出了培养“领袖”人才的目标,即要“足动寰宇之观瞻”。
1914年,梁启超应邀到清华学校作了题为《君子》的演讲,他说:“清华学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底柱。”⑤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稿第一卷—清华学校时期(1911-1928)》,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第11页,第261页。梁启超的演讲词慷慨激昂,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清华学生的期待,这种期待无形中垫高了庚款留学生的社会地位,也可以说是形成了这一批人最初的文化资本积累,“庚款留学生”在尚未真正进入社会场域之前,已经被社会授予了一个高价值的文化符号。这种文化符号使庚款留学生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一份“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这种担当意识,也就是他们在当时的社会场域中的“位置感”——“领袖”。它在当时的清华学校中,形成了一种精神学统,凝结在一批批庚款留学生的人格养成的过程中。
梁实秋是1915年进入清华学校,当时的周诒春校长已经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校训,其内涵与梁启超的演讲互相呼应,感奋了清华学子。梁实秋的同班同学吴景超在1922年9月11日的《清华周刊》上发表了《清华学生安身立命之路》的文章,说:“罗君(即罗隆基-作者注)……曾说过:‘清华学生,个个都有当领袖的责任。’这句话好像说得不客气,其实倒是一句老实话。孔子说:‘当仁不让’,在这种时候,我们不预备出来当领袖,还等谁呢?”*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稿第一卷—清华学校时期(1911-1928)》,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90页。其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可见一斑。在《对清华文学的建议》中,梁实秋引了元遗山的诗句:纵横自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他说:“清华的历史,虽只有十一年,但是很充实;清华的学生,虽前后只有千人,但大半是优秀分子。……在一般混沌的时候,清华做她的领袖事业,在一般狂飙突进的时候,清华退隐潜韬,做她的自修的工夫和监督的责任——这是清华在文化运动里光荣的历史。”*梁实秋:《对清华文学的建议》,《梁实秋文集》(第6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由此可见,梁实秋的人格精神中也渗透着强烈的“领袖”意识,当然,这种领袖意识是指向他的职业选择——文学领域的。而正是这种当仁不让的“领袖”意识,使得梁实秋在文坛上自觉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屡屡挑起文学纷争。
梁实秋的“清华八年”,正逢新文学开疆拓土之时。时势造英雄,一时间,群雄逐鹿。陈独秀在高歌猛进的《文学革命论》中打出文学革命三大主义的口号。胡适则明确倡导:“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295页。再加上周作人《平民的文学》《人的文学》主张的呼应,以及茅盾“进化的文学”的主张,遂使得新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呈现出走向民间和大众化的新趋势。此时的新文学正为文坛生存权而战,对旧文学阵营和各方反对者的态度非常决绝,一如陈独秀在《答胡适之》一文中宣称的那样:“……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08页。新文学在蹒跚起步的时候,是以战备状态面对文坛的,梁实秋曾以“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来形容戒备森严的新文学场。但作为清华留美学子的优越感,使他不可能俯首臣服。
梁实秋的文字最初进入公共视野是在1919年,在这一年,一个迥异于传统文学体制的新“文学场”(literary field)已经初步形成。所谓文学场“就是一个遵循自身的运行和变化规律的空间”,文学场的内部结构,“就是个体或集团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这些个体或集团处于为合法性而竞争的形式下”*[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页。。在布迪厄的理论中,行动者、资本、位置、生存心态、权力、斗争等元素,是构成他理论的关键词,文学场是一个动态的关系结构,其内部没有卓然独立的事物,一切都处于相互关系之中,文学行动首先是个人或者群体的利益驱动下的行为,由此文学场则成为一个“诸多力量较量之场所”(the field of forces),一个“充满了斗争的场所”(the field of struggle)。每一个行动者为在文学场中“占位(position taking)”而采取各种文学行动,并在这些行动中积累起自己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行动者的“生存心态”,也可以说是行动者的性情系统,也构成了行动者的动力系统,与行动者在文学场中的位置感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而作为一个动态的关系结构的文学场,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其不断变动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它的结构是处于不断变动中的,行动者文化资本的积累,可以改换其内部的强弱形势的对比。
循此概念,我们发现,在1919年初步形成的新“文学场”,是一个充满很多可能性的文学场,作家、理论家、作品、派别都是一种全新的组合,很多名不见经传的人“暴得大名”,跃居“文学场”的重要位置。这一现象对很多有文学理想的人来说,蕴含着重大的机遇,他们或者希望能志同道合地被整合进去,或者希望划出自己的势力范围,打出自己的江山,而更有抱负的人,会希望在这一“文学场”尚未稳固的情况下,把自己的文学旗帜插上盟主的位置。总之,这是意味着寻找自己的位置或争夺话语权的重要时刻。
1921年,一个普遍的全国的文学活动开始到来。这一年,梁实秋开始了新诗创作,他的《荷花池畔》《没留神》《一瞬间的思潮》《蝉》等先后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出于对新诗的共同爱好,梁实秋与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新诗的学兄闻一多相识。闻一多的国学根底非常深厚,他追求诗的艺术美,注意新诗的形式打造等都给梁实秋以重大影响,他一度视闻一多为“文艺上的老大哥”,认识闻一多之后发表的二十几首诗,在当时的诗坛上堪称佳作。闻一多对梁实秋的诗歌评价是非常高的,他称梁实秋为“红荷之神”,说:“实秋的作品于其种类中令我甘拜下风——我国现在新诗人无一人不当甘拜下风”*《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第71页。。
梁实秋曾这样界定他们的诗歌主张:“我和闻一多都是把诗当艺术看,着重的是诗的内涵,与胡适先生所倡导的‘工具革命’已经是两回事了。”*梁实秋:《〈论文学〉序》,《梁实秋文集》(第7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732页。梁实秋与闻一多之间惺惺相惜的勉励,让我们感受得到他们渴望在新诗领域不甘人后、峥嵘雄起的理想。
但这一理想并没有如愿以偿。
二、文坛争雄,别立新宗——新文学场内的权力角逐
闻一多和梁实秋创作的诗歌并没有为他们打开一条道路。1921年,梁实秋在《晨报副刊》上只发表了四首诗——《荷花池畔》《没留神》《一瞬间的思潮》《冷淡》。闻一多的诗则只在《清华周刊》上发表过。这种“妆于奁内待时飞”的感觉,对于梁实秋和闻一多来说是太寂寞了。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统计,单从1920年至1922年,“新诗集”就有18部出版。这样一个庞大的诗歌创作群落,无论其成就优劣与否,都足以让后来者颇感沉重。
更严峻的是,当时诗歌创作的原则延续着胡适《谈新诗》的主张:“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新诗除了‘诗体的解放’一项外,别无他种特别的做法。”*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295页,第18页。而当时的文坛法则或者说文学批评标准,正如胡适所说:“简单地说来,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里面。”④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295页,第18页。由此,他把自己提倡的“活的文学”和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视为中国新文学的新传统,也就是当时文学场的法则。遵从这一法则创造的新文学在整体上有一种走向大众的努力,而梁实秋此时的文学观念却与这种法则相背。这就意味着在胡适与周作人所创立的文学法则之下,梁实秋很难得到文坛认可,更不必说要领袖文坛了。因此梁实秋诗歌创作之路,在他自己的眼中,前景渺茫。
在这一年的诗中,梁实秋写道:“我感到恐怖的黑暗,便灭了我手里的纱灯;但是,到海底探珠的人们啊!往黑暗里去求光明的朋友啊!燃着你们的灯光罢!”*梁实秋:《送一多游美》,《梁实秋文集》(第6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其间透露出来的正是对诗歌创作的放弃。闻一多做于同一时间的诗歌评论文章《冬夜评论》中,就称梁实秋为“豹隐”的诗人。以后梁实秋虽然还有诗作,则一者是恋爱中的情思抒发,一者是为了《清华周刊》的编务,其中不乏对诗途无望的感慨。虽然闻一多在美国一再呼唤:“莲蕊间酣睡着的恋人啊!不要灭了你的纱灯”⑥《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第71页。,梁实秋还是告诉他:“我是人间逼迫走的逃囚”,但他仍愿意“扇着诗人底火”*梁实秋:《答一多》,《梁实秋文集》(第6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言下之意就是要“豹隐”,并转而走文学批评的路子。这也是为什么梁实秋始终没有把他的诗集《荷花池畔》与闻一多的诗集《红烛》一起出版的原因。因为他已经志不在此。
1922年5月27日至29日,梁实秋的《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这一篇文章充满了对当时文坛进行理论清算的味道,同时也树起了自己的旗帜。梁实秋说:“我这篇文并非是专与俞君相辩难,实是与现在一般主张‘人生的艺术’和‘平民的文学’的人作一个问题的讨论。……艺术自有艺术的效用。我们为什么要以宗教意识——向善——代替美为艺术的鹄的呢?”在这里,梁实秋的批评指向了新文学场的“普遍性法则”。当时声势强大的文学研究会正以“为人生”为旗帜领导着整个文坛的走向,风靡文坛的“问题小说”就是这一旗帜下的产品,而这一文学观的始作俑者是周作人。梁实秋在文章中旗鼓相当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他的鹄的只是美,不晓得什么叫善恶;他的效用只是供人们的安慰与娱乐。……诗是贵族的,决不能令人人了解,人人感动,更不能人人会写”,而且“诗是贵族的,要排斥那些丑的”。最后的这句话,他所批评的是诗人在诗中使用革命、军警弹压处、电灯、厕所、小便等“丑”的词语现象。受闻一多的影响,梁实秋在诗歌上追求传统文学的精致美感,无论语言还是形式,他都主张以精致典雅为诉求,他这里所谓的“贵族”即是标举这种主张。这篇论文与其说是对俞平伯诗论的批评,不如说是梁实秋对文坛的宣言,文中很少对俞文作针对性的批评,多是自抒已见,俞文只不过是文章的引子。周作人随后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丑的字句》,对梁实秋的观点作了反驳,认为梁实秋有“学衡派”的保守嫌疑,两人互有几篇文章发表,在《晨报副刊》上也算掀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而梁实秋在批评周作人的同时也对胡适加以批判:“……但自白话入诗以来,诗人大半走错了路,只顾白话之为白话,遂忘了诗之所以为诗。收入了白话,放走了诗魂。尤有甚者,即是因为受了各种新思潮的影响,遂不惜把诗用做宣传主义的工具。胡适之等把奋斗、革命、手枪、炸弹、努力,作了诗的原料……诗真可以算是命途多舛了!才从脂粉堆里爬出来,又要到打铁抬轿的手里去了!诗人也真不幸啊!诗人也要服从‘到民间去’的命令吗?艺术是为艺术的,诗是为诗的。平民的诗,我们应当引入诗国,以备一格;作家的诗,我们应该格外的敬礼,禁止摧残。诗的本身是目的,不是手段。”
这样一篇横扫诗坛的批评文字,是梁实秋发表的第一篇规范的文学批评,逻辑上有破有立,旗帜鲜明,初步显示了他文学批评家的素质。这一次牛刀小试对梁实秋应该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周作人的直接“对话”,使他对文学批评的兴趣远超过了文学创作。在20年代初的文学场中,文学批评相对而言还是一块处女地,而且文学批评相对创作而言更有指点江山的强势,更容易获得声誉和影响力。就拿这一篇评论引发的他与周作人关于“丑的字句”论争来说,虽然周作人的文化资本要比梁实秋大得多,甚至两人之间没有可比性,但梁实秋的文学批评观点在新文学场中还是产生了影响,商务印书馆主人在排印新诗的时候,非坚持将“小便”一类字句删去不可。
在新文学场中,文学批评是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小说、话剧、散文、诗歌已经各有公众认可的领军人物,而文学批评领域却是江山未定。梁实秋和闻一多对诗歌的潜心研究,使他们对诗歌批评极为自负,并且对在这一领域首开风气抱有很高期望。
1922年3月,俞平伯的《冬夜》和康白情的《草儿》诗集出版,闻一多立刻在5月作了《冬夜评论》投给《晨报》副刊,已经发表过鲁迅的《阿Q正传》、周作人的《美文》、冰心的《繁星》《春水》的《晨报》副刊,无名之辈很难跻身其间,这篇评论投去后如石沉大海。已经有了独立诗评立场的梁实秋,在闻一多作了《冬夜评论》之后,于1922年8月,作了《草儿评论》一文,文中他说:“现在几乎没有一种报纸、杂志,不有几首新诗,而又几无一首是诗,其鄙陋较之《草儿》更变本加厉了;若一一引而评之,势有未能,所以溯本探源,把始作俑的《草儿》来评一过,实在又是擒贼擒王的最经济的方法了。”*梁实秋:《草儿评论》,《梁实秋文集》(第1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在段话中,身为新诗创作者的梁实秋不仅是对《草儿》这一部诗集,而且对整个诗坛进行了批评,在新诗“几无一首是诗”的断语后面,张扬的是他确立自己话语地位的努力。但这两篇头角峥嵘、别立新宗的评论,写出来后却无处发表。最让他们痛心疾首的是,这一年的9月3日和10月1日,胡适在自己主编的《努力周报·读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评新诗集(一)康白情的〈草儿〉》和《评新诗集(二)俞平伯的〈冬夜〉》,这两篇在闻、梁之后写出的新诗批评,却先于两人公开发表,怎能不让正蓄势待发的闻、梁两人焦虑。
梁实秋把这些情况告知身在美国的闻一多,闻一多在信中说:“最要紧我们在这一年中,可以先多作批评讨论的零星论文,以制造容纳我们的作品底空气。……感谢实秋报告我中国诗坛底现况。我看了那,几乎气得话都说不出。‘始作俑者’的胡先生啊!你在创作界作俑还没有作够吗?又要在批评界作俑?唉!左道日昌,吾曹没有立足之地了!”*《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由于梁实秋在这一时期的书信已经遗失,我们只能根据闻一多的信对他当时的思想做出推断,他与闻一多作为清华文学社的主力,颇有当仁不让与文坛争锋的气势。这虽然加重了他们后起的焦虑感,但他们的行动也因此极富策略,也就是先要以零星的论文冲击文坛,让人们注意并接受他们的倾向,为他们话语的现身“造势”。
这两个别立新宗的长篇诗评,在无法发表于权威报刊的情况下,最终由梁实秋的父亲出资,于1922年11月,以《冬夜草儿评论》为题,作单行本付印。梁实秋在作于1922年11月24日《荷花池畔》里写道:“宇宙底一切,裹在昏茫茫的夜幕里,在黑暗底深邃里氤氲着他底秘密。人间落伍的我啊,乘大众睡眠的时候,独在荷花池腑下的一座亭里,运思游意。……我怎知道,天上可有树,树上可有我底巢?”*梁实秋:《荷花池畔》,《梁实秋文集》(第6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也就是说,在冲击文学批评领域的过程中,梁实秋这种后起的焦虑感是非常明显的,但这种焦虑感也加强了他挑战新文学场法则的动力。
1923年,梁实秋选择了文学批评专业赴美留学,这一选择非常大胆,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留学生,择业的动向大多是富国安邦,因此电光声化等“实业”是最热门的专业方向。而文学是否能够成为一个人安身立命的职业还是一个尚须探讨的问题,清华文学社曾经就“文学与人生”以及“文学是否可以作为一生的职业”等问题做过专题讨论。毕竟从事文学事业所必需的公共媒体和大学等还都处于刚刚起步的时期,当时的新文学阵营中,文学专业出身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在有关20世纪初留学生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是留欧美学生群,一方面是因为欧美等国本身就代表了当时世界文化的进步水平,这为留学生提供了一个有高度的平台;一方面是因为赴欧美,尤其是以清华学校为主体的赴美学生群,在国内就接受了比较完备的基础教育,赴美后所选择的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是西方公认的最高学府,他们留学的过程中能够迅速融入并吸收西方文化,获得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学术起点。因此可以说,在20世纪初的留学生群体中,留美学生是当之无愧的精英群体*参阅郑春:《留学背景与中国现代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而在这个精英群体中,以文学为专业的更是少之又少。
在清华学校历年毕业生专业统计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自1909年至1930年,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的学生中,以“文科”为业的总共有61人,占全部赴美总人数的48%,这个所谓“文科”包括“文学与语言”“普通文科”“戏剧”和“美术音乐”,其中以“文学与语言”为业的只有19人。梁实秋是1923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到这一年,清华赴美学生中选择“文学与语言”的只有3人,而梁实秋这一届的毕业生是六七十人,其中选择“文学与语言”的只有2人,他就是其中一个。在当时大多数人心目中,文学革命虽然使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自由,但是它还是常常被视为一种余业,是专业之外的涉猎,就连非常喜爱文学的闻一多也是以“美术”专业赴美求学,而后审时度势才决定要致力于文学一途。而且,在当时,新的文学观念尚未真正形成,它仍然不脱传统的“文章之学”的范畴,与西方的文学观念尚未形成真正的对话。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从传统中来,基本上都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文章之学”是他们学养的一部分,几乎无人不能谈文章之道术。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那就是新文学是由一大批文学专业之外的知识分子发起和创造的。正如梁实秋在自美学成归国之初,所做的盘点文坛的《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中所言:“胡先生先是学农的,后改习哲学,成为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文学研究并无专攻,至于创作的天才亦甚有限。”周作人作为文坛老前辈,“也并非是专治文学的”,“鲁迅先生的杂感作品的确是很精彩。但是没有大规模的文学上的努力”*梁实秋:《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梁实秋文集》(第6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352-353页。。由此可见,梁实秋的选择虽然是非常大胆的,但这一专业选择上的冷门与国内百废待举的文坛现状之间的巨大反差(虽然新文学已经有了一定的成绩,但规范性的建制尚未形成,一切仍处于运筹之中),给人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豪情。在知识分子们纷纷向西方求取“真经”的时代语境中,梁实秋无疑是怀着为中国文坛求取“真经”的理想赴美的。
在美国,梁实秋与闻一多仍联系密切,他们共同组建的中华戏剧改进社要创办刊物,闻一多写信征求梁实秋的意见,他说:“关于杂志尚有数事当注意:一,非我辈接近之人物如鲁迅,周作人,赵元任,陈西滢或至郭沫若,徐志摩,冰心诸人宜否约其投稿。我甚不愿头数期参入此辈之大名,仿佛我们要借他们的光似的。……五,要打出招牌,非挑衅不可。故你的‘批评之批评’一文非作不可。用意在将国内之文艺批评一笔抹煞而代以正当之观念与标准,上沅又将作五年来之中国新剧,本意亦在出人以下马威也。要一鸣惊人则当挑战,否则包罗各派人物亦足哄动一时。此问题与问题一乃是争点之正面与反面,孰舍孰从,请示知。”*《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页。
所谓“争点之正面与反面”,是闻一多与梁实秋筹划的两种文学行动策略,要么通过约稿的形式,实现与当时文坛的融合,从正面途径进入文坛;要么揭竿而起,以“挑衅”的“批评之批评”的方法,将“将国内之文艺批评一笔抹煞而代之以正当之观念与标准”,梁实秋的回信我们无处可查,但从他以后的行动我们可以知道他取的是后者,即要以自己的文学批评刷新文坛,重塑另一种新文学景观。
在美国的梁实秋接受了新人文主义者欧文·白璧德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推崇东方文化尤其是孔子思想的学者,他的思想使梁实秋更坚定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他的文学批评理论使梁实秋获得了系统的文学批评专业训练。当梁实秋学成归国之后,以传统文化为重心且“术业有专攻”的他,面对受西方文化影响而成长起来的新文学时,挑战性的批评风格也就在所难免了,这也正是他在二、三、四十年代屡屡陷入论争的缘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