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娜拉,还是不成为娜拉
☉[美]李海燕 著 修佳明 译
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为五四一代带来的兴奋和刺激,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翻译文本能与之比拟。自从1918年译入中国后,它一直“在中国发挥着一种催眠式的作用,影响直延伸到下一个十年”。当时的评论者围绕娜拉受困与出走的象征意义展开争辩,讨论娜拉究竟象征同类个体的压迫与解放,还是象征普遍女性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压迫与解放。当时绝大多数的浪漫爱情故事都以出逃作为谢幕;同理,绝少有五四的评论家愿意追究娜拉离家以后的遭遇。当然,鲁迅是个例外,这本戏剧在五四时期被挪用的目的是为了抵制父权家庭,而鲁迅则在《娜拉走后怎样》(1923)中提出尖锐的质问,为这场热火朝天的运动泼上了一瓢令人清醒的冷水。如果家庭是娜拉遭受压迫的根源,那么她的离家就理应是问题的解决,而不是麻烦的开端。鲁迅前瞻性地诉诸社会主义者的论点,直白地点明:经济独立性的缺乏,判定了娜拉走后的命运,不是堕落为妓,就是蒙羞重返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奴役: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
鲁迅指出,娜拉所受到的压迫,不仅针対其女人的身份,而且还涉及财产权遭到剥夺的那一阶级的成员。这就指向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个体自由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它是否要求一切受压迫的社会阶级和群体全部得到解放?五四的自由恋爱渴求者们显然不这么认为。对于他们而言,爱情就是个体自由与自主的终极肯定。他们指认家庭为敌方、相信只要成功地逃离家庭的魔爪、完成自由的结合,这场战役便已大获全胜。年轻的恋人们的梦想,是凭借浪漫之爱的救赎性力量,建造一个更加理性化和人性化的二人群体,即伙伴式的婚烟。但是他们并没有为爱情的内在风险做好准备,也没有准备好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即主观情绪无论有多么丰富、美好和高贵,都无法构成“本身具体的个人所应有的整体性”(黑格尔)。这种对于浪漫之爱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爱情之命运的捉摸不定和虚无缥缈,以及爱情所处的与生活中其他目标、旨趣和诉求相对的地位。鲁迅在讨论娜拉的这篇文章以及1925年所作的短篇小说《伤逝》中,都对以实现个人自主与自由为伪饰的爱情提出了质疑——这种爱情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
为了爱情,子君敢与世界为敌
《伤逝》借用男主人公涓生的回溯性口吻展开论述。故事大约发生在一年前。涓生鼓励他的爱人子君反抗她的家庭并与自己结合为自由的联盟。然而,他们的事实婚姻在经济困境和社会隔绝的压力下迅速瓦解。子君返回家中,不久在羞病交加中故去。叙事从涓生听闻子君的死讯时开始,他的思绪返回了他们从相爱到分离的共度时光。涓生在痛苦追忆之末,把发生在子君身上的全部不幸都归咎于自己。
涓生在与子君展开恋情的初始,独自住在一个破败的会馆房间里,远离家庭,不受家庭义务的羁绊。他是一个自由人,但也是一个孤独者。正如他所言,与子君的相恋把他从清简孤僻的“死的寂静和空虚”中拯救了出来。而对于子君,自由恋爱既让自己得以从叔叔的权威中解脱,也让自己体验到全新的社会交往形式的欢乐。维系这种社会交往形式的,正是黑格尔已清楚阐明的自我否定与自我肯定之间的辩证法。爱情让他们第一次拥有了自我的意识,而且“双方都把各自的灵魂和世界纳入到这种同一里”。当他们处于激情的顶点时,似乎确实单凭这种二项关系就建成了一整个想象的世界,把兴趣、环境以及实际生命与存在的目的塞入了爱情的范畴。两人在肮脏的小巢里拥抱相依,互相汲取支持,抵抗来自外部的压力,包括存心反对的叔叔、势利的邻居和路上的轻蔑眼光:
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她默想了一会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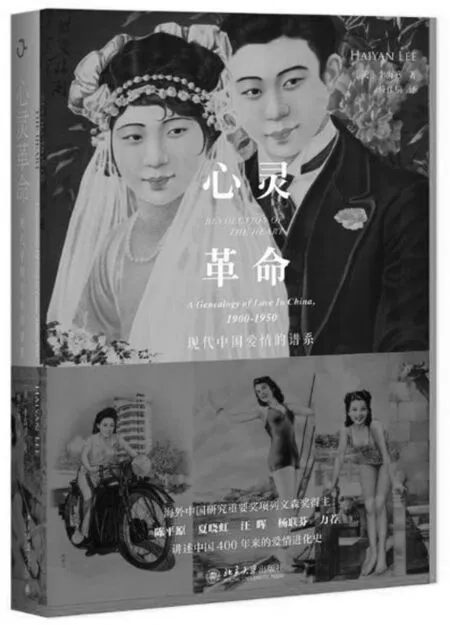
涓生能够相当精确地复述子君的言语。相比之下,他却坦承自己记不清自己如何向她表示爱意。“岂但现在,那时的事后便已模胡。”他只模模糊糊地记得,他单膝跪地,模仿着在电影中看到的西方仪式,不论在当年还是现在都有点令人愧恧。可是他却能详细地复述子君在他发表那些关于自由的演说时,她的肢体和言语上的反应。涓生在自由恋爱中所求之物,似乎更多是自由而非爱情,或者是自我肯定而不是自我否定。特别是考虑到他不愿意为了热情而妥协自己,而且热切地想要把一切抛诸脑后,更可如此判定。他企图用自己“主体性的整体”渗透他人的意识,并“成为他(或她)所追求和占有的对象”(黑格尔),却不愿意把自己投入到爱情的辩证过程之中,接受对自我满足的弃绝。
另一方面,子君却心甘情愿地把涓生作为自己存在的根本。对于两个人浪漫关系的每一个亲密细节,她都历历在目:“她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自然连那使我不愿再想的浅薄的电影的一闪。”由此,除了男性中心的视角外,叙事还向子君对于自由恋爱的不同体验投以一瞥。她在文中得到两次引用,声明了自己的自主权和对家庭的反抗,但是她的发言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仍然是男性叙事者的微弱回音,仿佛他是在通过解放她而间接谋求自我的解放。子君完全沉浸在相恋的过程之中,每天夜里都会重温求爱的场景,并且坚持对于往事的忠实表达——“夜阑人静[……]我常是被质问,被考验,并且被命复述当时的言语,然而常须由她补足,由她纠正,像一个丁等的学生。”——这一切都表明了她对于爱情真正的享受以及对于爱情所承诺之圆满的信心。也正因如此,子君才能够从被叙述者认为“可笑”乃至“可鄙”的时刻中汲取绝大的快乐;而涓生却在这个时刻认识到自己在情绪上的依赖性,并且意识自己是在拿一部分自主权去换取认可与团结。黑格尔敏锐地评价了这种在浪漫事业中存在的性别天堑:
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爱情方面遭遇不幸,她就会像一道光焰被第一阵狂风吹熄掉。
自不必说,女人传奇式而彻底性的降服于爱情,与她们性别本性的关系不大,更多是源于生活施加给她们的可与之竞争的诉求过少,导致她们“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的空间过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子君完全陶醉在她生活的“高峰”里,这让她可以大无畏地直面路人的白眼和与家人的决裂。可一旦抽离了爱情,她的结局只能是悲惨的香消玉殒。
柴米油盐的琐细生活击败了子君和涓生似是而非的信仰
这对年轻爱侣在度过了重重困难之后,终于找到一个僻静的住所安家,子君全心全意地投身到日常的家居生活当中,怀揣着似是而非的信仰,认为他们亲手所造的爱巢,定能许给他们一世的幸福快乐。可是,种种烦恼接二连三地浮出水面,而且并不能以爱情日渐单薄为由简单地解释清楚。涓生失业后,没有能力保护他们的家庭免受贫困的磨难,这当然是他们二人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但是更加原生的问题早已在失业的灾难从外部对他们造成打击之前,就已经初现苗头。在一幕不禁令人联想到《茶花女》的场景中,子君坚持要贩卖自己的首饰,换钱资助安家及添置家具。涓生面对她的提议做出了让步,没有坚决反对。他给出的理由是:“我知道不给她加入一点股份去,她是住不舒服的。”如果将此视为一种投向性别平等的努力,那么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对恋人却切实地采纳了他们的偶像娜拉曾加以反叛的性别化劳动分工。娜拉走出的那个家庭,正是涓生和子君在艰难赢得从“暴政”与“传统”中解脱后所奔赴的那个家。
涓生以一小段笔墨书写了二人共同生活的“安宁和幸福”,给读者带来了稍许宽慰,之后又充满遗憾地指出,子君忙于家务,难以抽身,连谈天、读书和散步的时间也没有。对于日常生活的细碎操心挤掉了爱情更新的空间,这对于子君的面容造成了最为直接的损害。“对于她的[为自己平庸的厨艺]日夜的操心,使我也不能不一同操心,来算作分甘共苦。况且她又这样地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是这样地粗糙起来。”待涓生甫一失业,余下的便只剩艰辛,二人的共患难越来越难以为继。两人心有戚戚的莫逆之感渐渐消失,而当第一个信号出现时,涓生便开始缅怀过去自己在“会馆里的破屋的寂静”中的“安宁的生活”,并幻想着“从新萌芽”:“现在总算脱出这牢笼了,我从此要在新的开阔天空中翱翔。”对于自由的渴望重新燃起,这让涓生立即对子君发起了责难,认为是她使自己无法起飞,无法在天空中翱翔。他越来越频繁地怀念起自己往昔的独处岁月,尽管那曾经是令他恐惧并希望逃脱的所在。如今,日常生活与子君难以割裂地联系在一起,散乱的碗碟和油烟的焦味令他窒息,动物和人类的嘈杂混声扰乱着他的安宁。每日家常的烦扰、拘束与倦厌给涓生带来的不快,总是伴随着他对子君爱意的削减,后者如今已经走下了“坚定而无畏”的新女性神坛,回归到生物性与社会性繁殖生育的庸常王国:
加以每日“川流不息”的吃饭;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构思就常常为了这催促吃饭而打断。即使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她总是不改变,仍然毫无感触似的大嚼起来。
子君终日在单调沉闷的家务中劳作,却让涓生找到了一个不再爱她的借口。涓生深信自己一个人可以生活得很好,于是下定决心,趁自己还能“扇动翅膀”时候,奋力逃出眼下的困境。而他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宣布爱情的废除:
“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在他唯物主义式的顿悟之下,爱情已经不再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反而站在它的反面,成一种迷醉的心灵状态,妨碍了所有真正重要之事。尽管鲁迅在此毫不掩饰地嘲讽了涓生的自恋和虚伪,但结合他讨论娜拉的文章来看,人们很难忽略他对于这种反思实际上所持的认可态度。夹在自由与恋爱的冲突要求之间而无法自拔的涓生,虽然心不甘情不愿,可还是忍心从爱情中撤退,去找回他真正珍惜之物——他的个人自由。涓生的选择或许在道德上是违背良心的,但他却保持了对五四浪漫主义的挚诚,因为恋爱的最终目的是自由。当意识到失去自由比父权压迫更为邪恶之后,特别是对于男性来说,爱情便成为可以即刻丢弃之物。可是,涓生在谈及生存问题时,只道出了一半的真相。除了爱情之外,失业还迫使他陷入到一个私化式生存的境地,这对于往往在公开领域内定义自己基本身份的男人来说,是一种不可容忍的境况。于是,才有了涓生在外面的现实世界中驾驭一种确定身份的幻想,就像“怒涛中的渔夫,战壕中的兵士,摩托车中的贵人”。
子君从一名魅力十足的新女性沦落为一位平庸的家庭妇女,更直接的成因,是这对恋人对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分工的意识形态毫无保留的接纳,而这正是娜拉所反判的对象。“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因为她成了一名私化的个人,这些对她而言已经无用,被迫落入附属的地位之后,“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虽是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涓生在发泄怨怼时,从未想过子君或许也拥有属于她自己的梦想,却受到了他们共同认定的家庭意识形态的压抑。他们所实践的自由恋爱根本不够彻底,因为它只为女人留下了一条唯一的“谋生之道”,那就是走入夫妻式的家庭。可是,日常生活的消磨吊诡式地展现出将爱情作为一种谋生之道的不可能性。子君显然并没有丧失全部的勇气,所以很快就质问了涓生对自己的感觉。涓生则抱着一种对于真理的庄严诉求,坦白了自己爱意的消却,并迂回地暗示了他希望她离开的心愿。他再次搬出易卜生作为自己劝说的武器,把分离描画为两个人全新开始的起点,可并不能说,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在他们破败的小穴外,等待子君的是什么样的结局。最终,涓生进行了忏悔,并得到了作者的宽恕。被他们遗弃的小狗阿随也奇迹般地返回他的身边,而他也搬回会馆的房间,并承认在那里找到的只有空虚。自由在此与“遗忘”和“说谎”发生了可耻的联系,而他曾梦想着重新跨上的新路则“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
笼罩着不祥之感的结尾似乎在暗示,悔恨与悲哀并不能挽救失败的浪漫实验。鲁迅或许可以原谅涓生,因为他虽然后知后觉,总归还是认可了鲁迅所持的对于经济自由之重要性的信仰;但是他绝对无法原谅自由恋爱的乌托邦理想,也无法原谅持续鼓吹自由恋爱的愿景而无视其内在的冲突及其与生活现实之间矛盾的那些人,他们要么是自欺欺人,要么就是在恶意操纵轻信而易受影响的青年。鲁迅在《幸福的家庭》(1924)中刻画的那位丈夫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是一个雇佣文人,怀着纯粹的恶意纺织着“幸福的家庭”的虚假的纱,而对日常生活的庸俗细节不屑一顾,如柴火的价格、冬白菜的储藏、孩子的哭闹,在他眼中视若不见。他努力维护着夫妻式家庭的理想图式,令其带着布尔乔亚的浮华泡沫漂浮在日常生活的泥沼之上,可他却几乎无法在中国大地上找到一块现实的地点,来承载他的故事。同时,他也无法阻止现实生活中顽固而刺耳的碎片打乱他体面的幻想。在小说第一段,鲁迅清楚地表明,这位雇佣文人正在构思一则讲述夫妻幸福生活的廉价故事,这并不是因为他相信这是现实,而是因为他了解如何才能迎合当时的风尚,以便谋取可观的酬金。如果说《伤逝》呈现的是自由恋爱的悲剧,那么《幸福的家庭》则是导演了一出滑稽戏。鲁迅本人的自由恋爱实验表明,它很少能达到悲剧的高度,也不会荒谬到让人们可以嗤之以鼻,并一笑置之。鲁迅之后的作家继续对自由恋爱的生存困境进行夸张化的书写,特别是女性作家,她们开始讲述起子君的故事,并揭露小资产阶级婚烟的虚伪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