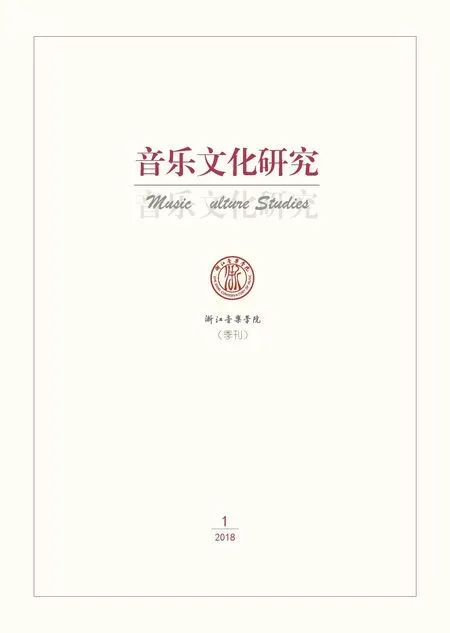摩洛哥哈穆利亚格纳瓦音乐之初探
刘晓倩
格纳瓦音乐在摩洛哥有三大中心,分别是摩洛哥南部的索维拉(Essaouira);阿特拉斯山脉中的圣所穆莱·布拉伊穆(Moulay Brahim);撒哈拉沙漠尔格·切比(Erg Chebbi)的村庄哈穆利亚(Khamlia)。三大中心对格纳瓦有着重要意义,几乎涵盖了格纳瓦音乐的全貌,是现存格纳瓦(Gnawa)身份认定的三个代表性场所。笔者分别于2015年、2016年两次赴摩洛哥进行田野工作,并对这三大中心的格纳瓦音乐进行深入研究。在下文中,笔者主要以撒哈拉沙漠的村庄哈穆利亚为例,对哈穆利亚格纳瓦音乐的组织之一进行一个较为深入的描述。
一、村庄哈穆利亚
哈穆利亚村庄位于摩洛哥的东南部,挨着撒哈拉沙漠尔格·切比(Erg Chebbi,阿拉伯文:),整个村庄约有三百七十人,族源包括格纳瓦人和柏柏尔人。哈穆利亚也被称为黑人村落(Black village)或非洲村落(African village),咨询人穆罕默德·马祖兹对笔者说:
哈穆利亚是伟大的撒哈拉沙漠的一扇门。
而初到哈穆利亚这个位于撒哈拉沙漠的村庄,笔者印象最深的是他们黝黑的肤色。在从穆莱·布拉伊穆到哈穆利亚的长途跋涉中,笔者通过穆罕默德·马祖兹的帮助,能够通过女性村民的衣着清楚地识别所经过的哪个村庄是柏柏尔人,哪个村庄又是阿拉伯人,如果不看女性衣着,根本无法通过肤色分辨其民族,因为他们都拥有较浅的肤色。但当笔者终于到达了哈穆利亚之时,却发现这个村庄的村民全是黑人,这个不同于柏柏尔人、阿拉伯人的族群在哈穆利亚形成了一个类似于社区的成熟村落,有他们独特的起源、文化与信仰。那么,为何哈穆利亚的村民为黝黑肤色?他们与撒哈拉以南非洲有何关系?为什么穆莱·布拉伊穆的格纳瓦艺人肤色较浅,他们之间又有何联系?对于最初所见,笔者认为从肤色上看,哈穆利亚的起源很可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有密切联系。
通过阿卜杜阿里以及对当地的格纳瓦组织领导者扎伊德·乌杰阿(Zaid Oujeaa)的多次采访,笔者对其起源也有了初步了解。哈穆利亚的格纳瓦起源于与撒哈拉沙漠有着长期密切关系的黑非洲。他们的祖先作为奴隶,是通过跨撒哈拉沙漠贸易从中非和西非到达摩洛哥东南部的。而奴隶解放之后,他们作为游牧民族居无定所,四处寻找有利于他们生存的,能够为他们的畜群良好供给的土壤。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格纳瓦开始选择在土地资源相对较好的地方定居下来,于是就出现了不大的村庄,之后,他们又和同样以游牧为生存方式的柏柏尔人通过婚姻的方式融合,从此开始了从游牧到定居的生活,而哈穆利亚村庄就是由此产生的。当他们开始了定居生活之后,收入来源变成了农业、畜牧业以及最近开始发展的旅游业。

图1 哈穆利亚村庄的泥瓦房(笔者摄于2015年)
哈穆利亚的“沙漠之鸽”组织的领袖扎伊德·乌杰阿①告诉笔者,古城西吉尔马萨是中世纪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异常繁荣的原因就在于它位于跨撒哈拉沙漠贸易的路线上,并且是Caravan(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商队)的停靠点。而对于村庄哈穆利亚来说,跨撒哈拉沙漠贸易②影响到的一点就是,跨撒哈拉沙漠贸易中贩运而来的撒哈拉以南的黑人作为奴隶被大量地留在了西吉尔马萨(即如今的哈穆利亚村子一带),而随着奴隶解放,这批解放的黑奴组织起来,在这一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社区,随着时间的推移,成立起来的黑人社区与柏柏尔人、阿拉伯人以通婚的形式相融合,由此产生了一个特殊族群——格纳瓦(即被奴役过的苏丹非洲人的后裔),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先,有着共同的黑奴身份以及跨撒哈拉沙漠的苦难历史。哈穆利亚村庄的村民阿卜杜勒阿里告诉笔者,这就是哈穆利亚村庄的起源。他说:
我们的村庄(已知)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村子居住着柏柏尔人、阿拉伯人以及来自撒哈拉以南的不同部落的人。在哈穆利亚村庄,最出名的就是班巴拉人,我们也称之为格纳瓦。我们是起源于黑非洲的奴隶的后代。
在哈穆利亚这个紧靠撒哈拉沙漠、人口约为三百七十的小村庄,却有两个格纳瓦音乐组织,他们距离不远,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一个独立院落,两个组织分别名为:
沙漠之鸽(Pigeons du Sable)
德斯·班巴拉(Des Bambara)
在下文中,笔者将通过在哈穆利亚的所见所闻所感,对这两个格纳瓦音乐组织之一“沙漠之鸽”进行较为细微的描述,由此探寻如何对哈穆利亚的格纳瓦进行一个合理、准确的定位。
二、初探“沙漠之鸽”
咨询人穆罕默德·马祖兹陪同笔者走在混着沙漠的路上,虽是早上,但这里的温度已经高达四十多度,在这令人烦躁的炎热中我们都没有说话,安静地沿着小路不知目的地走着。笔者时而转过头看向不远处的茫茫沙漠,时而低头看着这发黑的土路,心里感叹那些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是有多么强大的耐受力,能够忍受这种生存环境。一早的温度已经让笔者满身的粘腻,而通常,在哈穆利亚的午后,大部分时间笔者都躲在屋里整理采风资料,不愿出门,就在这胡思乱想间,笔者看到了路边两个紧挨着的牌子,白底黑字,上面有不同颜色的图像,这两个牌子在几乎空无一人的路上孤零零地立在那里,笔者走进看到牌子上的字分别为英文、法文和阿拉伯文。简单的两个牌子却同时包括了三种语言,很显然,如果单纯从这一角度来看,而非深入探究,那么,可以说这个组织是针对游客的。
左侧牌子上的字分为六行,分别写着:
社团(Association)
哈穆利亚(Khamlia)
发展(Developpement)
团结一致(Solidarite)
财产(Patrimoine)
混合学校(Ecole Mixte)
这六个时而英文时而法文的词汇(前三个为英文,后三个为法文)是对这个组织极为简略的概括。对于前面五个词语很容易理解,笔者对其作了一个大略的解释,即这个格纳瓦组织是哈穆利亚的社团,目前致力于发展,其社团成员类似于兄弟会,团结一致,是当地的文化财产。而需要注意的是最后的“混合学校”(Ecole Mixte),为什么在这个笔者所认为的格纳瓦组织中会出现学校?而且写在了大牌子上?对此笔者当时不得其解。
再看右侧的牌子,上面分别写着:
扎伊德的组织(Groupe Zaid)
格纳瓦音乐(Gnawa Music)
哈穆利亚(Khamlia)
沙漠之鸽(Pigeons du Sable)
右侧的牌子也是简单地写着几个词语,笔者同样对其进行一个大致的解释,即这个位于哈穆利亚的格纳瓦音乐组织是扎伊德的,名为“沙漠之鸽”。
三、扎伊德与“沙漠之鸽”
为何会起名为“沙漠之鸽”?沙漠,自是由于其所位于的撒哈拉沙漠,而“鸽子”则是由于其所象征的是和平,而这正是哈穆利亚的格纳瓦族群一直以来所追求的,故这个组织名为“沙漠之鸽”。
“沙漠之鸽”组织的领导人扎伊德告诉笔者,哈穆利亚的音乐是格纳瓦族群的精华,音乐是从他们的祖先那里流传下来的,而纯粹的格纳瓦音乐正是保留在他们的家园哈穆利亚村庄,并以这种传统的方式留存着。扎伊德是“沙漠之鸽”格纳瓦组织如今的领袖,他告诉笔者,哈穆利亚的格纳瓦音乐一直都是父传子承的教育方式。扎伊德·乌杰阿是哈穆利亚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他19岁的时候,他的叔叔赫达·乌波拉(Hda Oublal)——一位出色的格纳瓦乐人,向他介绍了格纳瓦音乐的风格,并传授给了他尕布瑞的演奏技能。当他的叔叔赫达去世之后,将哈穆利亚村落的图标——尕布瑞传给了乌杰阿,由此,乌杰阿成为了“沙漠之鸽”乐团的领导。如今,乌杰阿已有52岁了。他带领“沙漠之鸽”格纳瓦音乐组织参加了很多国际音乐节,曾前往阿尔及利亚、德国、苏丹等地,他告诉笔者,时间的演变并没有影响哈穆利亚格纳瓦音乐的纯度与真实性。他说:
我们音乐的主题是对上帝、先知以及看不到的灵的祈祷。每一个音调、歌词、手势以及节奏都回想起黑人的苦难,他们被释放之希望的主要力量就是:真主安拉。
而值得一提的是,扎伊德不仅是“沙漠之鸽”组织的领导,还是村子中协会的负责人,而这正解释了我们在村口所看到的左侧牌子之意:
社团(Association)
哈穆利亚(Khamlia)
发展(Developpement)
团结一致(Solidarite)
财产(Patrimoine)
混合学校(Ecole Mixte)
正当笔者对这个小村庄的“学校”“协会”有所不解时,扎伊德非常骄傲地为笔者解释了他所创建的这个协会。

图2 哈穆利亚“沙漠之鸽”组织的领导扎伊德·乌杰阿(笔者摄于2015年)
协会(association)其实就是给哈穆利亚孩子们的学校,是在他们正常的,有政府资助的公共教育学校基础上的补充。村子的孩子们在这里学习阿拉伯语、法语和数学。共有四个课室,三间是在村子中有围墙的院子里,而另外一间则是在“沙漠之鸽”组织的旁边,如图3所示:

图3 哈穆利亚的“Ecole Mixte”(笔者摄于2015年)
图3中的建筑物即混合学校,包括三间简陋的教室和一个足球场,在外墙上有一些壁画,另一间在“沙漠组织”旁边的第四个教室则常常有孩子演唱格纳瓦歌曲。孩子们可以选择去上哪种课程,因为正如村民们常常对笔者说到的,在撒哈拉沙漠这个如此炎热的地方,孩子们在户外没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而扎伊德成立的学校激发了孩子们学习的热情。如此,扎伊德在哈穆利亚村庄备受尊重。而他所领导的“沙漠之鸽”音乐组织的盈利方式也并不是固定的。只有当游客购买他们的CD或者自愿在观看表演后给予金钱时,才能够获得收入。其实,在笔者几天来的观察来看,很多游客仅仅只是听听音乐,满足猎奇心,有些甚至听了不到一分钟便离开,而格纳瓦乐人们则要在闷热的屋子里随时准备表演。这些乐人们始终随叫随到,每一天有不同的人,但歌者兼尕布瑞演奏者这一重要角色却基本不变。没有表演任务的乐人在院子中的地毯上或玩牌或休息,他们的表演基本是从早到晚。同时,扎伊德告诉笔者,有时他们的组织也会受到邀请前去表演,比如村中某人的生日或婚礼,抑或摩洛哥节日之时,他们并不会在开始之时便谈好报酬,而是前往表演之后,由主人随意支付。同时,有些喜爱音乐的游客在回国之后,会邀请他们去欧洲演出,虽然这个机会非常少。
扎伊德的格纳瓦组织有18人左右,但是当笔者问道他们分别的身份之时,他们却无法回答,之后,阿卜杜勒阿里告诉笔者,在他们这个组织里,不会称他们为舞者、尕布瑞演奏者、塔卜鼓演奏者或克恰克演奏者,原因在于他们需要学习所有的乐器。所以并不能告诉你说5个人演奏克恰克或7个人是舞者,因为仅仅是在这场表演中是这样的形式。但是尕布瑞演奏者是个例外,因为尕布瑞在格纳瓦音乐中是最重要的乐器。阿卜杜勒阿里的原话是:
唯有智者能够演奏尕布瑞。
在“沙漠之鸽”这18人的组织中,只有3个人能够演奏尕布瑞,而这3人的任务就是歌者兼尕布瑞演奏者。而另外15人则轮流表演跳舞、克恰克以及塔卜鼓。这18个人都为男性,当笔者问到是否有女性成员时,阿卜杜勒阿里告诉笔者:
在哈穆利亚村子,女子做家务,男人挣钱。通常这个组织是没有女人的。但是当萨达卡节日时,她们会加入进来。在这个节日中,女性跳舞,并向真主安拉祈求赐予巴拉卡。
正如阿卜杜勒阿里所说,这个村庄有一个一年一度的节日,人们称之为萨达卡(Sadaka),笔者以及游客所看到的平日里的格纳瓦音乐是从来都不会有女性加入的,如果不是笔者在这个村中待了数日,在这个组织中是没有机会看到女性村民的。

图4 哈穆利亚“沙漠之鸽”格纳瓦组织路边的两个牌子(笔者摄于2015年)
如今想来,第一次与“沙漠之鸽”这一组织的实地接触并不成功,经历了穆莱·布拉伊穆毛瑟姆,并感受到了其中的格纳瓦音乐后,再看这个组织,笔者开始怀疑,是不是其已经变成了进入撒哈拉沙漠的游客必经之路?其纯粹性是否还有所保留?
顺着之前的路牌,笔者来到了一个院落的门口,大门和两边墙上颜色鲜艳的字与画,让这个地方在一片泥砖房中脱颖而出。门的左边墙上画着三种乐器,这三种乐器中的克恰克和塔卜鼓在穆莱·布拉伊穆中出现过,而另外一个则是低音域的三弦琉特——尕布瑞(Gumbri),而右面墙上则是一名身着白色杰拉巴的男子在演奏尕布瑞。
刚刚踏入院子大门,便听到里面传出的热闹的音乐声,熟悉的克恰克和塔卜鼓配着尕布瑞低沉的旋律,笔者走进屋内,看到了一个呈长方形的简陋的房间,房顶由稻草和木头搭制而成,由两个泥土砌成的柱子支撑着,墙面全是由泥土砌成,早已出现了太多裂痕。但就是这样一个极其简陋,甚至房顶都会随时塌陷的房子,却被用心地布置了。四方墙上挂满了他们演出时的照片以及获得的表彰,而两个泥柱上也精心地围着柏柏尔风格的地毯,泥土堆成的泥台环绕着屋子的三面,上面简单地铺着花纹各异的布以及一些靠垫,方便人们坐靠。同时,有些泥座前还摆着小桌子,桌前放着当地用以招待客人的柏柏尔茶。正对着桌子的一面就是格纳瓦艺人表演的地方,地上铺着黑色花纹、红色底面的柏柏尔风格长布,5位格纳瓦艺人席地而坐,中间的演奏尕布瑞,同时是歌者,一人演奏塔卜鼓。
连续数日的相处让笔者对哈穆利亚的这个格纳瓦组织有了更深的认知,而初次所见的误读也消失殆尽,笔者分别对这个组织的领导者扎伊德·乌杰阿,乐人阿卜杜勒阿里(Abdelali)、萨拉姆(Salam)、赫谢姆(Heeshem),哈穆利亚村民乌萨马(Usama)、伊迪(Idi)、阿里·欧巴那(Ali Oubana)等人进行了采访,并在阿卜杜勒阿里的帮助下,分三次观看了这个格纳瓦组织的表演,每次约为40分钟至一个小时。
按照受访人的说法,哈穆利亚村庄中的格纳瓦音乐保留了其最初的形态,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奴隶在被迫的移居过程中带来的音乐。
四、演出过程
“沙漠之鸽”的格纳瓦组织为笔者分别单独演出了三次,笔者选择了以其中的一场对其进行细微描述,选择哪场也是在与受访者的沟通下进行的,首先这场是相对最为完整的表演,其二,这场所选择的是哈穆利亚最为经典的音乐。故笔者通过现场看到并摄录下来的表演为对象,对其动作、音乐以及歌词内容进行一个全景式描写。笔者将演出过程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开场舞蹈、主体歌唱、结束部分。

图5 哈穆利亚“沙漠之鸽”格纳瓦组织的开场舞蹈(笔者摄于2015年)
1.开场舞蹈
表演一般有12人左右,最初,乐器尕布瑞并没有出现,首先上场的是4位手持克恰克的舞者和两位塔卜鼓鼓者,鼓者站在屋子的右侧,给4名格纳瓦舞者腾出一个较大的空间,他们穿着白色杰拉巴,头包白色头巾,鼓和克恰克的节奏随着舞蹈动作的变化而同时发生改变。首先,4名舞者边演奏着手中的克恰克边围城一个圆圈,在节奏的配合下,轻快地挪动着步伐,他们左右脚不断交替,轻轻移动,但始终都保持一个圆形,在移动的过程中,他们不时做出一些动作,诸如蹲起、旋转等,一般情况下在三次蹲起之后会紧接着一个快速的旋转。
大约5分钟后,开场舞蹈结束。
2.主体歌唱
随后,舞者坐回了屋子右侧的石台上,而尕布瑞演奏者盘起腿来席地而坐,坐在了柏柏尔花纹的地毯上,四名乐者分坐其两旁,从左边起,分别是塔卜鼓演奏者、克恰克演奏者、歌者兼尕布瑞演奏者以及两名以手拍打节奏的乐者。而原本的舞者坐在石台上,也用手拍出节奏型,此时石台上坐着6名格纳瓦乐人,一齐配合歌者的演唱。如图6所示:

图6 主体歌唱部分的座位图(笔者摄于2015年)
随着半分钟由克恰克、塔卜鼓、拍手等节奏融合而成的前奏,歌者边弹奏尕布瑞边开始了演唱,其实这时弹奏的尕布瑞还不能称其为旋律,说是弹奏旋律不如说这时候歌者是在以拨弦的形式拨出固定节奏型,此时的歌声在低沉的尕布瑞、聒噪的克恰克声音、清脆的拍手声以及稳定的鼓声之配合下,显得尤为稳重,又稍显无奈。歌者兼尕布瑞演奏者唱一句,其他所有乐人重复一句,典型的一领众和形式。据之后萨拉姆告诉笔者,一直重复的歌词为:
yalwaliwaliy Allah.
意为:神圣的阿拉。
在循环演唱了两分钟后,一名身着白色杰拉巴,头包蓝色头巾的男子阿里·欧巴那走上前去开始跳舞,蓝色头巾是当地柏柏尔人的特色,马祖兹我们常常称他们为蓝色柏柏尔。他并不是黝黑的皮肤,而是较浅的柏柏尔人的肤色。旋律和节奏都没有变化,这名蓝色柏柏尔循环做着一些简单的动作,他保持着缓慢的步伐,双手时而在胸前不断漫无目的地挥动,时而在身体两边大幅度摆动。随着舞者的步伐,尕布瑞的旋律停止了,变成了纯粹的节奏。
整个演出就在节奏、旋律、歌唱、舞蹈中来回变换,演唱方式一直都是一领众合,而很典型,这种音乐风格与撒哈拉以南非洲有关。为了方便分析,笔者通过与乐人的沟通,为每首歌曲都起了名字,按照不断重复的歌词中常常出现的词语。笔者将其中几首列举如下:

图7 尕布瑞演奏者兼歌者(笔者摄于2015年)

表1 “沙漠之鸽”格纳瓦表演的歌曲
单纯看列表中笔者选取出的歌曲名称,可以发现哈穆利亚的格纳瓦音乐的主要内容是赞美安拉、追溯过往。这两点内容很有趣,前者是确定自己的伊斯兰信仰,后者是标明自己黑非洲奴隶的身份,这两种类别的歌曲构成了“沙漠之鸽”组织的主要内容。不论是主唱的歌者,抑或是应和的乐人,在演唱这一连串的歌曲时,在这循环重复中,始终保持着平静与安详,与穆莱·布拉伊穆以及笔者后文中所提到的索维拉私密仪式中的格纳瓦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其实,如果不是通过格纳瓦乐人,就连马祖兹都很难为笔者翻译歌词,对于之后索维拉格纳瓦私密仪式,笔者与马祖兹几乎用了三个整天的时间去翻译,原因就在于这些歌曲不是简单的摩洛哥阿拉伯语,而是掺杂了其他的非洲语言,比如上面列表中的《苏丹尼》就是格纳瓦复合语言。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创造出已经不属于阿拉伯语或者非洲语言的新词。这些零星出现的词使得分辨歌词成了异常艰难的事情。他们没有歌本,亦没有曲本,为了在最初阶段即对哈穆利亚的格纳瓦有相对全面的认知,故笔者希望对歌词有所记录,最初笔者与马祖兹一起聆听录制下来的旋律,希望将歌词记录下来,但很快就发现这样所耗费的时间太多,其实歌词本身并不复杂,因为哈穆利亚格纳瓦音乐的重复循环,导致一句歌词在一领众合的情况下能够重复很多次,但是马祖兹和笔者却每一句都要倒回去重复很多次才能将其准确记录,于是笔者还是以马祖兹作为中间人,通过格纳瓦乐者的解释,由马祖兹翻译给笔者,笔者再总结下来。但就是因为这项工作,让笔者能够对其内容有充分的了解,在这里,笔者将这场演出中对他们而言最常演唱的歌曲《苏丹尼》为例,将歌词记录、展现出来:
Soudani yallah lah Soudani
Soudani yallah lah Soudani yallah
Soudani ya boaalam Soudani
Soudani ya boaalam Soudani yallah.
Soudani baba mimoun Soudani
Soudani baba mimoun Soudani yallah.
译:(笔者整理的马祖兹的解释)
安拉,我们来自于苏丹,
安拉,我们来自于苏丹。
布阿拉姆,我们来自于苏丹,
布阿拉姆,我们来自于苏丹。
弥牟,我们来自于苏丹,
弥牟,我们来自于苏丹。
这是一首一领众合式的分节歌,单独看歌词,有些词会有些困难,不理解其意,不只笔者,包括马祖兹对“布拉阿姆”“弥牟”亦不知其意。这是一首悲伤的歌曲,通常笔者会在格纳瓦歌曲中发现一些词语,以诉苦的形式对安拉、对他们的圣人、灵表达一种被迫迁移的创伤以及失去家园的痛苦,这首歌所表达的正是如此。萨拉姆告诉笔者:
每个词对我们来说都非常有意义。每个音调都是反对奴隶制的证词,同时(我们)向真主安拉、向圣人祷告,为了从铁链中释放出来。
这句话,也解释了很多笔者所看到的表演中的动作和服饰,可以说释放和奴役经历是他们的共同创伤,也是哈穆利亚的格纳瓦音乐的主要内容。再次回到《苏丹尼》这首歌曲,苏丹尼(“Soudani”)其实指的正是苏丹(“Sudan”),此苏丹并非现在的苏丹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Sudan),而是指撒哈拉以南非洲(又称为黑非洲)的广阔的热带草原地区和几内亚海岸的热带草原以北。这种格纳瓦特有的语言,也证实了其在摩洛哥阿拉伯语的基础上融入的非洲语言,也是导致歌词在能够熟练运用阿拉伯语、柏柏尔语、法语、英语的马祖兹眼中都艰涩难懂的原因之一。歌曲每一句都唱到了他们的家乡黑非洲,表达了一种悲苦的思念。而每一句的变化都是出现在他们诉苦的对象上,诉苦对象分别为真主安拉、布拉阿姆、弥牟。真主安拉是伊斯兰教徒眼中唯一的主宰,无须赘言。布拉阿姆全名应该为穆莱·阿卜杜勒卡德尔·吉拉里(Moulay Abdelkader Jilali)或布阿拉姆·吉拉里(Boualam Jilali)。萨拉姆对笔者解释道:
在摩洛哥我们称其为穆莱·阿卜杜勒卡德尔·吉拉里或布阿拉姆·吉拉里。他是一个受欢迎的穆斯林圣人,是白色的超自然实体。
而他们另一个诉苦对象则是巴巴·弥牟(Baba mimoun),是来自于撒哈拉以南的超自然实体,笔者称之为“灵”,弥牟所属的颜色是黑色。真主安拉、布阿拉姆、巴巴·弥牟同时在一首歌曲中出现,并成为格纳瓦群体所诉苦、倾诉的对象。歌词提供给了我们三点信息:
1)格纳瓦族群源自苏丹(撒哈拉以南非洲,又称为黑非洲);
2)歌曲表达的是思念家乡之苦;
3)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体系,虽然他们坚称自己为伊斯兰教徒。
“沙漠之鸽”组织在主体歌唱部分演唱的歌曲正是表现了这种对族群起源的追溯以及对安拉的赞颂。
3.结束部分
“沙漠之鸽”组织的结束部分非常简单,既没有演唱,也没有舞蹈,尕布瑞、塔卜鼓、克恰克以及手掌拍击的声音形成一个固定的节奏型,并逐渐减速,最终一齐结束。
五、所用乐器
在哈穆利亚的格纳瓦音乐中,尕布瑞、克恰克和人声形成了一个鲜明的音层结构。其中,尕布瑞营造出三种音色(a,b,c),克恰克营造出一种音色(d),人声营造出另一层音色,笔者简单呈现如下:
1)拨弦而发出的低沉的旋律音调;
2)在尕布瑞的骆驼皮上用指尖轻轻敲击节奏产生的高/低音;
3)由系于尕布瑞颈部的“色塞拉”发出的共鸣的叮当声③;
4)克恰克发出的稠密而连续的节奏型;
5)一领众和的人声:
马勒姆(组织领导者)富有激情地大声独唱,召唤灵;
其他格纳瓦乐人浓厚响亮的唱和。
以上五个音层结构是格纳瓦音乐中最常见并持续时间最长的结构组合,也是能够召唤灵的最为核心的结构。
1.尕布瑞
尕布瑞,是笔者对“guembri”的直译,而“guembri”的拼写按照的是采风对象索维拉马勒姆阿克哈拉兹和哈穆利亚马勒姆扎伊德·乌杰阿给予笔者的写法,在摩洛哥进行田野工作之时,对于尕布瑞有诸多的叫法、写法,笔者所得到的有以下几种:gimbri,sintir,hejhoujis,hajhouj。可以说,尕布瑞是格纳瓦的灵魂,是格纳瓦音乐中唯一具有低沉的和音音域的乐器,笔者认为,它的声音有些类似于西方的低音吉他,但其所呈现的音乐有着更深的对比度、深度和活力。尕布瑞是无品的低音三弦弹拨类琉特,据乌杰阿介绍,尕布瑞由单峰骆驼皮(现在有时候也会使用山羊皮)、羊肠(现在多以尼龙绳代替)以及木头(白杨木、桃花心木或胡桃木)制成。尕布瑞的演奏技术同时包含了旋律性的声音和敲击的声音,它如窃窃私语,又能引起悲伤;它赞美安拉,又召唤灵。现今,为了方便,很多尕布瑞的弦都由羊肠变成了尼龙绳。

图8 格纳瓦乐器尕布瑞(笔者摄于2015年)
2.克恰克
qraqab(又可记为karkabu,krakebs,chkacheks),笔者将其直译为“克恰克”,是格纳瓦音乐的另一件乐器。乐器的名称是从阿拉伯语根Q-R-B中延伸而来,意为“接近”或“附近”。这影射了奴隶的回忆和他们痛苦的历史,也与虔诚的信仰有关。粗略一看,克恰克就是简单的金属片,相对比尕布瑞,非常简陋,两个成对儿的大的金属响板组合在一起,由多名格纳瓦乐人一齐演奏,每个格纳瓦乐人左右手各持一对儿,通常为2-6个乐人。克恰克约为25厘米左右,形状有点像杠铃,两个金属响板的顶端由金属钉串在一起,另一端是自由、分开的。直杆两段连接着两个类似于锅盖的圆顶,连接在中端的绳子(或皮质带子)围绕着拇指并同时和其他两个手指环绕,以方便在拍打后快速地将自由的那一端分开。每一对都被一个小金属扣固定在一起,如此限制了每一对金属响板能够开合的距离,格纳瓦乐人每只手握着一对儿金属板,金属板中间的绳子分别绑在大拇指和食指、中指上,基本演奏技术为通过同一只手两个金属板打开闭合产生的相互碰撞发声,声音是一种响亮的、金属的“shakashaka”的声音。

图9 手持克恰克表演(2015年笔者摄于哈穆利亚)
3.塔卜鼓
塔卜鼓(tbal)是一种带有一条较大的肩带的大型的低音桶状鼓,用于格纳瓦仪式中的列队游行环节和开场环节。这种塔卜鼓更适合于户外场地的表演,故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其在户外的列队游行环节中担任的角色。塔卜鼓有两种奏法:
1)右手持一个鼓槌击打加左手拍打的演奏法;
2)两个鼓槌击打的演奏乐。

图10 哈穆利亚沙漠之鸽组织中的塔卜鼓(笔者摄于2015年)
结 语
在哈穆利亚的这段时日,笔者尽最大可能去观察、记录格纳瓦族群及音乐,对于哈穆利亚的格纳瓦,阿卜杜勒阿里对笔者说:
一个月前,一些来自苏丹的人在寻找格纳瓦村庄,他们之前去过索维拉。当他们来到哈穆利亚时,他们说我们的格纳瓦是最原始的格纳瓦音乐。
其实,在笔者看来,哈穆利亚的格纳瓦指的既是一个族群,又是指这个族群所表演的音乐。格纳瓦族群起源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以奴隶身份在跨撒哈拉沙漠贸易过程中迁至摩洛哥东南部,并在奴隶制废除后与当地柏柏尔人融合建立了自己的族群。格纳瓦音乐为这个族群所表演的音乐,使用乐器为尕布瑞、克恰克、塔卜鼓,多为带有歌唱、舞蹈的表演,内容以追溯起源、思念家园、赞美安拉为主。在哈穆利亚地区用于日常生活与萨达哈节日中。
在哈穆利亚之时,有时候笔者会听到他们嘴里冒出的“Ismkhan”这个词,穆罕默德·马祖兹告诉笔者,这在柏柏尔语中即奴隶之意,他们会用其来形容自己,这令笔者十分惊讶,在笔者看来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带有歧视之意的贬义词,但他们却时而用其来形容自己。扎伊德告诉笔者,他们并不在乎用带有轻蔑之意的“奴隶”一词来形容自己,相反他们努力所做的是将这个词在他们身上转变成一种积极的授权。其实,虽然笔者一直提到他们黑非洲的祖先,但真正追溯过往,在哈穆利亚格纳瓦之祖先很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地区、说不同的语言、属于不同的民族,作为移居人口,他们是通过语言、物质文化、音乐等为自己塑造一个身份,创造出团结的族群精神。
注释:
①由于当地村民完全不懂英语,对哈穆利亚村民的采访均是通过咨询人穆罕默德·马祖兹的翻译完成,以下村民所说的话为笔者通过咨询人马祖兹的口头翻译,进行一定的书面整理。
②跨撒哈拉贸易界于北非地中海沿岸国家及西非国家之间,是条从8世纪到16世纪末间重要的贸易路线。7世纪以后,阿拉伯人来到北非并控制了撒哈拉商道贸易。8-11世纪为商道贸易的发展时期,11世纪中叶-16世纪末为全盛时期,此后走向低潮。
③ 一般在尕布瑞独奏时能清晰地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