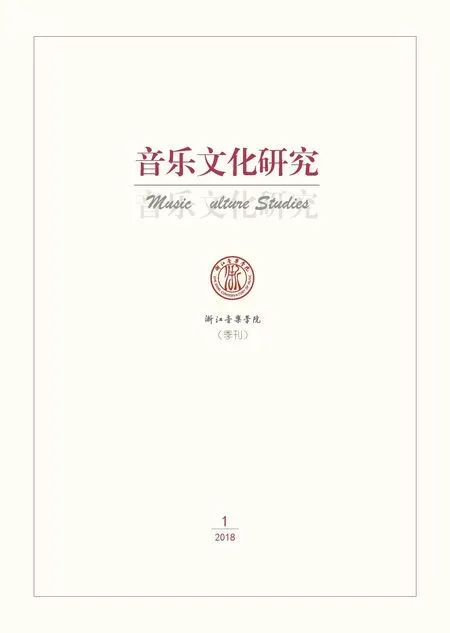丝绸之路上弹拨类乐器的东渐与流变
吴 洁
自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开始,在这条联结东西方文化的丝绸之路上,不同地域间的音乐文化相互交流与渗透。尤其在汉唐这段国际化的音乐历史时期,中国音乐的形成与印度、波斯、阿拉伯、中亚地区有着密切的关联。从历史上记载的弹拨类乐器来看,竖箜篌、“凤首箜篌”、四弦琵琶、五弦琵琶都并非为中国固有的乐器。那么,它们到底自何方?又是如何传入中国的?对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林谦三、岸边成雄等就已对丝绸之路上外来乐器的源流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进入20世纪以后,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赵维平、周菁葆、贺志凌、谢瑾等分别就丝绸之路上的琵琶、箜篌类乐器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通过历史溯源、图像考证,对其传播路径和演变过程作出了深入的探讨。
然而,史料中记载的“凤首箜篌”究竟形态如何?是否为琴头饰有凤首的箜篌?波斯、印度、中国、缅甸的琵琶、箜篌作为同源乐器在东渐的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迁?这些外来的弹拨乐器在进入中国之后又是如何发展的?面对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笔者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上的弹拨类乐器展开整体性的调查。通过史料、壁画的双重考据,进一步剖析其流变脉络和盛衰轨迹,从而论述中国对外来音乐的接受问题。
一、竖箜篌
关于竖箜篌的来源问题,学界目前已形成定说:可溯至古代亚述的竖琴。至于具体传入我国的时间,根据新疆鄯善县洋海墓地发掘的竖箜篌实物可判断,约在公元前7世纪。对此,贺志凌《新疆出土箜篌的音乐考古学研究》(2005)、谢瑾《中国古代箜篌的研究》(2007)两篇博士论文已就其形制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比对,故无复可疑。
从古代亚述浮雕中的角形竖琴来看,主要有水平和垂直两种式样。前者如公元前9世纪尼姆德鲁宫殿中的角形竖琴所示(图1),共鸣箱在底部,弦杆与其垂直,琴弦两端分别系于弦杆和共鸣箱上。前文所述我国新疆鄯善地区出土的箜篌便与其属一脉相承的乐器(图2)。但是,这类形制的箜篌从春秋时期传入中国之后并未得到展开。

图1 亚述尼姆德鲁宫殿角形竖琴(公元前9世纪)

图2 新疆鄯善箜篌(公元前7世纪)
相较之下,后者即共鸣箱在斜面,琴杆位于下端,两者呈夹角状,坐奏、立奏皆可的角形竖琴(图3、4)却在东渐的过程中不断延续和发展。

图3 亚述苏美尔竖琴(公元前20世纪)

图4 亚述尼尼徽宫殿角形竖琴(公元前7世纪)
据《旧唐书·音乐志》载:“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有二弦,竖抱于怀,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擘箜篌。”①这则史料不仅记录了东汉时期竖箜篌在我国的流传情况,并且从乐器的形制和演奏方式的描述中可知它与垂直式角形竖琴的关联。
竖箜篌在传入中国的路径中,新疆作为首及地区,石窟壁画中留下了大量的乐器图像。以公元4世纪克孜尔第114窟后室正壁的伎乐图为例(图5)。左侧乐伎左臂所挟竖箜篌,共鸣箱在斜侧,头部较为尖锐,绘有音孔,弦数不详。右侧乐伎弹奏阮咸。由此形成胡、俗乐兼备的弹拨乐组合。

图5 克孜尔第114窟伎乐图局部(公元4世纪)
此后,竖箜篌进一步东传至河西走廊一带。在甘肃地区的敦煌石窟、嘉峪关魏晋墓中涌现了大量的竖箜篌图像。其中,仅莫高窟中就有200多例,形制上基本延续了新疆地区的式样,但是,乐器的组合形式逐渐多样。例如,在北凉敦煌第275窟南壁天宫伎乐图中(图6),3位乐伎分别演奏琵琶、横笛、竖箜篌。源于印度、波斯两系的吹奏、弹拨乐器在此形成了一组小型胡乐组合。

图6 敦煌第275窟南壁天宫伎乐(北凉)

图7 敦煌第288窟北壁天宫伎乐局部(西魏)
进入西魏以后,乐队的规模进一步扩充。在敦煌第288窟北壁天宫伎乐局部图中(图7),乐伎从左至右依次演奏横笛、竖笛、铜钹、琵琶、箜篌、腰鼓。乐队中,俗乐器仅竖笛1件,其余5件均为胡乐器。胡、俗乐器之间悬殊的比例(5:1)反映出胡乐的来势汹涌,以及在南北朝时期,胡乐器已基本在我国登场的事实。
竖箜篌在凉州一带发展成熟之后便迅速向中原地区传播。云冈、巩义等石窟中都可见其身影。如北魏云冈第12窟中,出现一组竖箜篌与卧箜篌的合奏(图8)。从乐器的形制和演奏方式来看,基本与凉州地区的竖箜篌一致。

图8 云冈第12窟第1组乐伎(北魏)
在经历了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定型阶段之后,竖箜篌在隋、唐时期的宫廷乐舞中得以极大发展,被纳入疏勒、西凉、安国等多部乐中,是乐队配置中一件不可或缺的旋律性乐器。与此同时,在唐代大型经变画和唐墓壁画中也有大量呼应性的体现。据笔者统计,约95%的经变乐队和乐舞图中都绘有竖箜篌这件乐器。并且,它通常与琵琶、阮咸、筝等弹拨类乐器并置于乐队中,形成音色上的考量。
除了乐器数量的骤增,这一时期的竖箜篌在形制上也逐渐完善,有大、小箜篌之分。据《清朝续文献通考》载:
大箜篌,其形如凤。左右共七十一弦。
小箜篌,女子所弹,铜弦、缚其柄于腰间。随弹随行,首垂流苏,状甚美观……按弦乐器可行走弹奏者惟小箜篌一种而已。②
小箜篌的装饰较为精致,体积较小。对此,在盛唐敦煌第225窟南壁,出现了一例不鼓自鸣竖箜篌(图9),其边框彩绘图案精美,弦杆底部坠有流苏状的饰物,透射出当时渐趋华丽的审美倾向。

图9 敦煌第225窟不鼓自鸣(盛唐)
相比之下,大箜篌的体积略大,呈凤形,弦数较多。在中唐敦煌第112窟南壁大型经变乐队中(图10),乐伎抱持竖箜篌,双手拨弦。从乐器的体积和弦数可推断,此例竖箜篌属于大箜篌。

图10 敦煌第112窟特写(中唐)
到了开元、天宝年间,作为历史上胡、俗乐交融的顶峰时期,教坊、梨园两大机构的设立,标示着俗乐力量的崛起。散乐、胡部新声、“新俗乐”法曲等各类胡俗交融的乐舞成为宫廷宴乐的中流砥柱。竖箜篌、琵琶、横笛等一批外来乐器始终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相关的乐器、乐舞组合在唐诗中屡见不鲜。如白居易在《霓裳羽衣舞歌》云:
娉婷似不胜罗绮,顾听乐悬行复止。磬箫筝笛递相搀,击恹弹吹声逦迤……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觱栗沈平笙。清弦脆管纤纤手,教得霓裳一曲成。③
由此可知,在法曲《霓裳羽衣舞》中,竖箜篌与雅乐器(磬)、俗乐器(箫、筝、笙)的组合和配置情况。与此同时,韩休墓、苏思勖墓、朱家道村唐墓乐舞图等也都记录下了竖箜篌在唐代乐舞中的使用情况。
以天宝四年(745)苏思勖墓的乐舞图为例(图11),画面中心为一位胡腾舞伎,11人组成的伴奏乐队位于两侧。左侧6人,右侧5人,每侧乐伎分列两排。左侧乐伎分别演奏琵琶、笙、铜钹、横笛、拍板、伴唱。右侧乐伎分别演奏竖箜篌、筝、筚篥、伴唱、排箫。乐队架构上,胡乐器(琵琶、铜钹、横笛、竖箜篌、筚篥)、俗乐器(笙、拍板、筝、排箫)分庭抗衡。形象迥异的胡、汉舞伎、乐伎齐聚一堂,形象地还原了天宝年间,胡、俗乐交融的盛况。

图11 苏思勖墓乐舞图(天宝四年)
毋庸置疑,竖箜篌这件乐器之所以在隋唐时期的乐队、乐舞中广泛使用,与它的音色表现力密不可分。据唐代诗人顾况《李供奉弹箜篌歌》云:
竖箜篌作为弹拨类乐器,音色柔美,演奏手法变化多端。乐器上可实现易调移音,表现力丰富。另据《大明度经》卷6载:
普慈白言:“愿师为我说佛声,当何以知之?”法来曰:“贤者明听。譬如箜篌,不以一声成。有柱,有弦,有人摇手鼓之,其音乃同,自在欲作何等曲。欲知佛声音亦角。”⑤
竖箜篌不仅在合奏及大型经变乐队中起到装饰旋律的作用,也用于佛教仪式之中,其声堪比佛声。
综观竖箜篌的流变脉络,从亚述的角形竖琴到我国的角形箜篌,它的共鸣箱和头部的弯曲弧度逐渐增大,弦数增多。除了形制上的演变,乐器的组合及功能也在不断发生变迁。从新亚述时期尼姆鲁德、尼尼徽宫殿中的角形竖琴来看,主要使用于节日及欢庆典礼中,并常以齐奏的形式出现,乐器的数量在2件至5件左右。另外,也有独奏形式的苏美尔竖琴。
然而,这件乐器在传入中国之后,独奏、齐奏的形式较少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与各种胡、俗乐器的组合。乐器功能上也从最早的仪式场合转向宫廷俗乐和礼佛之用。并且,伴随着历史的进程,乐队规模逐渐扩大。从汉魏时期3件至5件乐器组成的小型器乐合奏,到隋唐时期20人至30人构成的大型乐舞,竖箜篌始终在其中担当着重要的旋律性乐器。它虽与亚述的角形竖琴、印度的弓形竖琴属于同源乐器,但在东渐的过程中,乐器的性格和功能已然发生了转变。
二、凤首箜篌
关于凤首箜篌这件乐器,它的名称最早见于北魏成书的《十六国春秋》:
天竺国重译来贡,其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圆、都昙、铜鼓等九种,为一部,工十二人。⑥
由此可见,凤首箜篌的传入与天竺献乐有关。在此之后,《隋书·音乐志》进一步载:
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其乐焉。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钹、贝等九种,为一部。工十二人。⑦

图12 印度西孟加拉邦浮雕(公元前1世纪)
据文献记载可知,凤首箜篌传入我国的时间是在前凉时期(公元346-354年)。然而,早在公元前1世纪印度西孟加拉邦的浮雕中就已出现了这种形制的弓形竖琴。如图12所示,该琴首部弯曲,琴杆细长,与音箱相连,缚弦四根。演奏时左手持琴,右手拨弦。在此之后,弓形竖琴东渐我国,并在龟兹地区迅速发展。它最早出现是在公元4世纪左右。在克孜尔第47窟中,一身伎乐手持弓形箜篌(图13)。该乐器音箱呈弧形,琴杆细长,首部弯曲。琴杆中部与音箱下部之间缚弦3根。演奏时右臂挟琴,右手拨弦,左手握琴杆。从乐器的形制、演奏方式可判断,它与印度的弓形竖琴属于同源乐器。

图13 克孜尔第47窟(公元4世纪)
这种形制的弓形箜篌进入新疆地区之后,在龟兹石窟群中大量显现,仅克孜尔石窟就有51例⑧,是壁画中绘制最多的一类乐器。其形制在时代的变迁中发生着细微的变化。音箱扩大,张弦增多,琴杆渐粗。并且,出现双手拨奏的形式。例如,公元6世纪克孜尔第69窟中的一例弓形箜篌图(图14)。其音箱略大,琴体的弯曲弧度增大,琴杆较粗。音箱上绘有6根弦,双手拨弦。对于这种双手拨奏的形式,林谦三在《东亚乐器考》中指出:“这种新奏法当是从西亚系的竖箜篌奏法里采取来的。”⑨

图14 克孜尔第69窟(公元6世纪)
对比同时期印度Mahadeva浮雕中的弓形箜篌可见,乐伎演奏的这件乐器在形制及演奏方式上仍延续了传统的样式(图15)。由此表明,源于印度的弓形竖琴在进入我国龟兹地区之后,其形制及奏法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图15 印度Mahadeva浮雕(公元6世纪)
中唐时期,弓形箜篌的首部开始出现装饰物。在榆林第15窟中,飞天所持弓形乐器琴颈较长,上端饰有凤首。无轸,共鸣箱呈梨形,面板上有缚手和捍拨。横抱、拨弦的演奏方式近似琵琶(图16)。此类凤首装饰的乐器在敦煌晚唐第85窟、第161窟、宋第327窟中都有所显现。并且,在形制上呈现固定式样。即琴颈细长,弯曲,首部绘有凤饰。共鸣箱与琵琶接近,面板上有凤眼、捍拨、缚手。无轸、无弦或独弦。从乐器构造来看,是箜篌与琵琶的结合。学界对此有“凤首弯琴”“弯头琵琶”“弯颈琴”等多种称谓。但是,由于这类按指板弯曲,无弦的乐器并不符合发音原理,因此,郑汝中、高德祥等学者都对壁画中这类乐器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这种弯颈琴是画家的一种构思,想象中的乐器,因为它根本不具备弦乐器的发音构造条件。”⑩

图16 榆林第15窟飞天伎乐(中唐)
相较之下,公元10世纪柏孜克里克第48窟五髻干闼婆奏乐图中出现的一例带有饰首的弓形箜篌形制明确。如图17所示,琴杆上端的“龙首”⑪装饰清晰可见。琴杆与音箱相连,上有弦轸10枚。演奏时左手托琴颈,右手弹拨。其形制、奏法与印度的弓形竖琴一脉相承。
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关于凤首箜篌的形制记载如下:
凤首箜篌,颈有轸。⑫

图17 柏孜克里克第48窟(公元10世纪)
凤首箜篌,出于天竺伎也,其制作曲颈凤形焉,扶娄高昌等国凤首箜篌其上颇奇巧也。⑬
龙身凤形,连翻窈窕,缨以金彩,络以翠藻。⑭
以上三段文字表明,天竺伎中的凤首箜篌琴颈弯曲,呈凤形,有琴轸。另外,在《新唐书》“骠国乐”条中对于凤首箜篌的形制做了进一步的描述:
有凤首箜篌二:其一长二尺,腹广七寸。凤首及项长二尺五寸。面饰皮,弦一十有四,项有轸,凤首外向。其一项有绦,轸有鼍首。⑮
由鉴于此,笔者认为《隋书·音乐志》中记载的凤首箜篌,源于印度的弓形竖琴。前凉时期,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后形成弓形箜篌的形制。相较于文献的记载,首部带有装饰的凤首箜篌图像直至中唐才出现。通过对于上述箜篌类乐器的溯源和流变考察可见,源于古代亚述的竖琴在东渐的过程中,曾以角形竖琴、弓形竖琴、竖箜篌、弓形箜篌、凤首箜篌等不同的姿态出现在西亚、印度、中国、缅甸的历史舞台上。它们虽为同源乐器,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传播轨迹和发展态势。通过对于西亚角形竖琴传播路径的梳理可见,在它的发展流向中:西亚→新疆→凉州→中原,乐器的形制、功能、角色在不断地变迁,并呈现出渐趋兴盛的发展态势。而印度的弓形竖琴在东渐的过程中则停留在了新疆境内,尤其在龟兹地区积聚了大量的弓形箜篌,后传至缅甸得以进一步延伸。
三、四弦琵琶
关于四弦琵琶的来源,据《释名·释乐器》载:“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⑯以及《隋书·音乐志》卷15载:“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之旧器。”⑰可知四弦曲项琵琶是源于西域的胡乐器。至于它的具体来源和传播路径问题,赵维平教授在《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一文已对四弦曲项琵琶的发展流向作出了明确的图式:“犍陀罗→萨桑朝的波斯→于阗→我国中原”⑱,故在此不作赘述。本文将重点从乐器的形制、演奏方式、组合形态入手,对四弦琵琶在东渐过程中的发展与流变展开进一步的考察。
在公元1世纪阿富汗Kandahar地区的犍陀罗浮雕中(图18),左起第四人横抱的这件梨形乐器是可见较早的琉特图像。

图18 阿富汗Kandahar犍陀罗浮雕(公元1世纪)
之后,在公元4世纪巴基斯坦Swat地区的犍陀罗浮雕中(图19),此类梨形琉特的形制已十分明确。阴线刻的四弦清晰可辨,琴颈呈明显的曲折状。这种四弦曲项琉特在萨珊王朝时期传入波斯后逐渐发展、定型成为乌德(图20)。从乐器的形制和演奏方式来看,几乎与犍陀罗的梨形琉特无异。公元3世纪后半叶,随着它进一步东传中国,在天山南麓的于阗地区留下了大量的四弦琵琶图像和音乐文物。从公元3-4世纪和田约特干伎乐陶猴所奏的四弦琵琶可见(图21),梨形音箱上阴刻的四弦、系弦用的覆手,甚至对称的音孔均已十分清晰。

图19 巴基斯坦犍陀罗浮雕(公元4世纪)

图20 波斯乌德(萨珊王朝)

图21 和田约特干伎乐陶猴(公元三四世纪)
通过对于以上不同地域琉特类乐器形制的考察和比较可推断,犍陀罗的梨形琉特、波斯的乌德、于阗的四弦琵琶属于一脉相承的乐器。演奏形式也基本一致,均为横抱,右手拨弦。
北凉前后,四弦琵琶进入河西走廊一带得以进一步发展。沿线的石窟壁画、伎乐陶俑等都记录下了这件乐器的传播及流变过程。其中,仅敦煌石窟中就有689幅乐器图像,列于首位。乐器的形制和演奏渐趋丰富、完善。指弹与拨奏、曲项与直项兼有,凤眼、捍拨以及装饰面板等部位相继精确。例如,在初唐第220窟南壁大型经变乐队中(图22),乐伎横抱的四弦琵琶共鸣箱呈梨形,捍拨与月牙形凤眼清晰,四弦四轸,执拨演奏。

图22 敦煌第220窟南壁琵琶伎乐(初唐)
这种形制明确的四弦琵琶在中原一带的云冈、龙门石窟中亦有大量显现,并与同属波斯系的竖箜篌,印度系的横笛、乐鼓,西域系的筚篥以及我国俗乐器进行组合。鉴于音色上丰富的表现力,故在宫廷、民间广为流传。据《通典》卷142“历代沿革”所载之:“自宣武以后,始爱胡声。洎于迁都。屈茨琵琶、五弦、箜篌……胡舞铿锵镗,洪心骇耳。”⑲自后魏宣武帝开始,对胡乐青睐有加。在此之后,不乏各代帝王对琵琶热衷及奏乐的记载:
帝(北齐后主高纬)自弹胡琵琶而唱之,侍和者以百数。⑳
后周武帝在云阳,宴齐君臣,自弹琵琶,命孝衍吹笛。㉑
大业末,炀帝将幸江都,令言之子尝于户外弹胡琵琶,作翻调《安公子曲》。㉒
在此背景下,涌现了曹妙达、康昆仑、段善本等一批知名的琵琶演奏家,推动了琵琶演奏技术的发展。对此,在白居易的《琵琶引》中形象地描述了琵琶的演奏情形: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㉓
隋唐时期,宫廷燕乐模式的建立使其迎来发展的顶峰。在唐代宫廷十部乐中,除康国乐以外,其余九部乐均配置了这件乐器。另据《通典》卷146“坐部伎”条载:“坐部伎即燕乐,以琵琶为主,故谓之琵琶曲。”㉔琵琶在唐代宫廷燕乐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及地位。它与箜篌、阮咸、筝等乐器构成音色丰富的弹拨组在大型乐舞中担任重要的角色,并且在乐队中的使用数量逐渐增加。例如,中唐第154窟北壁报恩经变乐队中连续排列的两件琵琶。(图23)

图23 敦煌第154窟北壁特写(中唐)
中唐以后,随着舞蹈的盛行,大型经变乐舞场景中开始新增反弹琵琶舞伎的形象。尽管,此类舞蹈形式在我国历史文献中并未有对应的文字记载。但在敦煌壁画中却留下了丰富的乐舞图像。中唐第112窟南壁(图24),舞伎左腿曲膝抬高,右腿单立。左手握琴颈,右手作弹拨状。晚唐时期,更衍生出了反弹琵琶与腰鼓舞的对舞。第156窟南壁(图25),左侧舞伎腰间系腰鼓,双手击鼓而舞。右侧舞伎左手握琴颈,右手执拨,反弹琵琶,背向而舞。尽管,从舞姿来判断,琵琶难以在实际演出中承担乐器的功能。但是,作为一种舞器,它却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

图24 敦煌第112窟南壁(中唐)
晚唐以后,四弦琵琶的演奏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改为竖抱、去拨的形式,并开始走向独奏化。随着演奏技法的不断成熟和发展,明清时期涌现了大量的琵琶流派和演奏家,其影响力延续至今。

图25 敦煌第156窟南壁(晚唐)
通过对于四弦琵琶的流变考察可见,从犍陀罗的梨形琉特到波斯的乌德、再到中国的四弦琵琶,这条以西亚为起点的流传轨迹脉络分明。在进入我国之后,开始从于阗向凉州及中原地区传播。在此过程中,四弦琵琶的形制和演奏方式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乐器的组合形式也逐渐多元。从胡乐器为主的组合形态,到胡、俗兼容的乐队格局,四弦琵琶无论在器乐合奏还是大型乐队、乐舞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乐器配置。唐朝,乐器角色的转变,使其成为执物舞中具有代表性的舞器,由此形成的反弹琵琶舞成为中国与外来乐器、乐舞交融的重要见证,并且折射出四弦琵琶在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对中国音乐所形成的深刻影响,为之后东流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埋下了伏笔。
四、五弦琵琶
关于五弦琵琶的起源,学界尚存分歧,主要有“印度说”“龟兹说”两种观点。持“印度说”观点的林谦三、岸边成雄、赵维平、韩淑德等学者认为五弦琵琶形成于印度,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西域,后至中原。持“龟兹说”观点的牛龙菲、周菁葆等学者则认为五弦琵琶是龟兹当地创制的品种。以下,本文从学界尚存争议的来源问题入手,进一步考察五弦琵琶在丝绸之路上的发展与流变。
据《旧唐书·音乐志》载:“……五弦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㉕五弦琵琶并非中国固有的乐器。然而,关于它的具体来源和传入中国的时间,文献中并没有更多的记载。对此,印度和龟兹地区浮雕、壁画中的乐器图像无疑成为探讨五弦琵琶源流问题的重要依据。公元2世纪后半叶印度阿马拉维提浮雕《脱胎画雕像》中的五弦琵琶音箱为棒状,琴轸呈三上下二式分布。演奏时横抱。相邻的横笛与之形成印度系乐器组合(图26)。公元4世纪克孜尔第38窟右壁天宫伎乐中的五弦琵琶颈部虽有残损,仅见四轸。但乐器的构造、横抱的方式,甚至与横笛的组合都与印度的五弦琵琶如出一辙(图27)。由此可见,五弦琵琶在北魏时期就已从印度传入至我国的龟兹。

图26 印度阿玛拉维提浮雕(公元2世纪后半叶)

图27 克孜尔第38窟右壁天宫伎乐(公元4世纪)
该地区作为西域佛教文化的中心,分布着克孜尔、库木吐拉、森木赛姆等大量的佛教石窟。其中,仅克孜尔石窟中出现的五弦琵琶就多达50例㉖,数量仅次于弓形箜篌。在公元7世纪克孜尔第8窟伎乐天人图中(图28),乐伎横抱五弦琵琶,左手握琴颈,右手拨弦,五枚琴轸呈上三下二式分布。与此同时,这类形制明确的五弦琵琶在印度阿旃陀石窟中也始终贯穿出现(图29)。通过以下两幅五弦琵琶图像的比对可见,无论是乐器的形制、结构比例,还是演奏方式几乎一致。由此可进一步判定两者属于同源乐器。

图28 克孜尔第8窟伎乐天人图(公元7世纪)

图29 阿旃陀第1窟(公元6世纪)
五弦琵琶在龟兹地区发展成熟之后,便迅速向甘肃和中原地区传播。据《通典》卷142载:“自宣武以后,始爱胡声,洎于迁都。屈茨琵琶,五弦,箜篌……胡舞铿锵镗,洪心骇耳。”㉗北魏宣武帝时期,五弦琵琶就已进入中原。对此,在这一时期的敦煌、云冈、巩义等石窟中都可看到它的踪影。
然而,相较于四弦琵琶在东渐过程中的发展和演变,五弦琵琶却始终维持着原有的面貌。例如,在北周敦煌第428窟,龛楣处的两位化生乐伎分别演奏横笛与五弦琵琶(图30)。无论从乐器的形制、组合方式,还是用拨弹奏的演奏形式来看都与印度的五弦琵琶一致。

图30 敦煌第428窟化生伎乐图(北周)
隋唐时期,随着宫廷燕乐体制的建立,它被纳入多部乐的乐队编制。尤其至初唐,十部乐中八部皆用五弦,使用数量达到历史的顶峰。对此,壁画中也有呼应性的体现。五弦琵琶不用于独立及小规模的乐队,主要出现于唐代大型经变乐队,并且常与四弦琵琶形成弹拨组合并置于乐队中,如晚唐敦煌第85窟连续排列的两身乐伎组合(图31)。

图31 敦煌第85窟局部(晚唐)
五弦琵琶作为波斯四弦琉特在东渐过程中于印度地区新生的乐器品种,虽与四弦琵琶同源,但两者的流传路径与发展态势却截然不同。如果说四弦琵琶的发展中心在于阗,那么五弦琵琶的形成关键则在龟兹。该地区棒状的乐器形态甚至对当时的四弦琵琶都产生过影响。梨形琉特在东渐西域进入天山北麓的龟兹段时,它的形制发生了变化。以公元4世纪库木吐拉第46窟伎乐天人图为例(图32),图32上中猕猴所持的曲项琵琶,音箱呈棒状,头部尖锐,演奏时执拨弹奏。图32下中的曲项琵琶也是这种形制,并且这种吹奏(排箫)与弹拨、胡乐与俗乐兼容的乐器组合是龟兹壁画中较为典型的一种组合模式,反映出龟兹乐的配置特征。


图32 库木吐拉第46窟伎乐天人(公元4世纪)
与四弦琵琶在我国的主流地位相比,五弦琵琶的发展态势较为迟缓。乐器的形制、演奏方式、组合形态等在传播的过程中始终未有较大的改变。唐末安禄山之乱以后,由于宫廷音乐地位急剧下滑。加之五弦琵琶与四弦琵琶在乐器构造、演奏方式以及音色上的相近,导致其在宋代以后逐渐被取代,从而走向衰亡。
小 结
综观丝绸之路上外来弹拨乐器的传播与流变,自汉代张骞打通丝绸之路起,西域诸国的音乐文化便纷沓而至。西亚系的四弦琵琶、竖箜篌经丝绸之路进入我国,首及新疆地区后进入河西走廊并横贯中原地带。接着,印度系的五弦琵琶、弓形箜篌也相继传入。它们虽与西亚系的四弦琵琶、竖箜篌属于同源乐器,但其流传轨迹及发展脉络却截然不同。较于四弦琵琶、竖箜篌始终在我国音乐中占据的主流地位,五弦琵琶在入唐之后却极速衰亡,弓形箜篌更是停留在了新疆境内,并未向中原地区延伸。
在这些乐器东传的过程中,印度在其中起着文化枢纽的作用。首先,西亚系的琵琶、箜篌都是经由此地传入中国。其次,这些乐器在进入印度后也都经历了一段本土化的过程。箜篌、琵琶在此都有新的发展。弓形箜篌、五弦琵琶的孕育而生是其印度化的鲜明标志。由此,以西亚为起端的两条传播路径脉络分明。
当然,西亚、印度作为两大音乐文化体系对于中国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此。印度系的横笛、法螺、五弦琵琶、弓形箜篌、腰鼓、都昙鼓、毛员鼓、答腊鼓、羯鼓、狮子舞;波斯系的四弦琵琶、竖箜篌、铜钹等乐器、乐舞构成两支庞大的外来音乐体系,相继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其中,琵琶、箜篌作为两类代表性的外来弹拨乐器,对中国古代音乐具有深刻的影响。
汉魏时期,以琵琶、箜篌两类乐器为主体的乐器组合中,缀有少量的中国俗乐器。由此反映出胡乐文化的强势输入以及我国对外来音乐文化所抱持的开放性的接纳之势。隋唐时期,七、九、十部伎的建立,使得燕乐体制下的宫廷乐队模式更加明确。琵琶、箜篌、横笛、腰鼓等外来乐器在与中国固有乐器的组合中形成胡俗交融的乐队格局。乐器的功能从早期独奏、伴奏之用发展成为乐队中的弹拨组合。这些外来乐器之所以稳站于我国宫廷音乐中,取决于唐人对于外来音乐文化广纳的接受态度和包容力。玄宗朝时期,“胡部登上堂”“诸乐改名”“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等历史事项的发生,迎来了历史上胡俗乐融合的顶峰。这一时期,琵琶角色的转变,演奏方式的变迁,乐器、乐舞组合形态的衍生等都透露出我国对于外来音乐文化已从全面接纳转变为自我文化的形成,并逐步建立起了海纳百川的音乐格局。
注释:
①[后晋]刘昫等:《旧唐书·音乐志》卷29,(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1076-1077页。
②[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94“乐考”,第9402页。
③[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444,(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1110页。
④[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265,(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30页。
⑤引自《大明度经》卷6,中华藏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第242页。
⑥[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卷73,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第79页。
⑦[唐]魏征等:《隋书·音乐志》卷15,(北京)中华书局,1973,第379页。
⑧姚士宏:《克孜尔石窟探秘》,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6,第177页。
⑨[日]林谦三:《东亚乐器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第230页。
⑩郑汝中:《敦煌壁画乐舞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第104页。
⑪关于这件弓形箜篌的名称,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中将其定名为“龙首箜篌”,大象出版社,1999,第177页。
⑫[唐]杜佑:《通典》卷144,(北京)中华书局,1984。
⑬[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37,(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⑭[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44,引[晋]曹毗:《箜篌赋》。
⑮[宋]欧阳修:《新唐书·南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⑯[汉]刘熙:《释名·释乐器》卷7,第107页。
⑰同 ⑦,第380页。
⑱参见赵维平:《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载《中国音乐学》,2003年第4期。
⑲[唐]杜佑:《通典》卷142“乐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3614页。
⑳[唐]李百药:《北齐书》卷8,(上海)中华书局,1972,第112页。
㉑[唐]李百药:《北齐书》卷11,列传三,上海中华书局,1972,第145页
㉒[唐]魏征等:《隋书》卷78,(北京)中华书局,1973,第1785页。
㉓[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435(25)。
㉔[唐]杜佑:《通典》卷146,(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762页。
㉕同 ①,第1076页。
㉖同 ⑧,第116-117页。
㉗[唐]杜佑:《通典》卷142,(北京)中华书局,1984。
——陈竖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