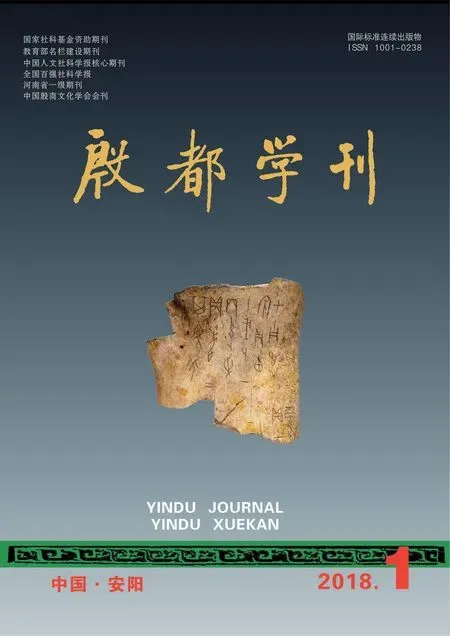对读《子产》篇与《大戴礼记》:兼论先秦儒家思想的两条路径
高瑞杰
(清华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84)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收录有关春秋史事的文献5种,其中3种关于郑国史事,即《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和《子产》,这三种文献中,或涉及儒家的丧祭、称谓等礼制制度、或涉及儒家的德治理念,可谓与儒家息息相关。《子产》篇与前两种纪事体裁不同,是关于“郑国名臣子产道德修养及施政业绩的论说”,李学勤先生指出“全篇主旨有较强的思想性,读起来使人感觉到有与儒家学说相类的色彩”[1],其启发性不可谓不大。历来对子产的学术研究中,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即:子产铸刑书到底是否为儒家所认可?清华简《子产》篇几乎肯定了子产制三邦之命、三邦之刑确有其事。[1]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子产的铸刑书?结合对《子产》篇部分简文重新释读,及与《大戴礼记》相关诸篇的对校,我们可以对此问题重新做一番探讨。
一、《子产》篇部分简文补释及疏解

又“处”亦可通为“虑”,*如《楚辞·大招》曰:“魂乎归来,恣志虑只。”洪兴祖补注云“虑,一作处”,可见二字相通。见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24页。二者皆为鱼部字,《说文》言“虑,谋思也”,[6]即思虑、思谋之意。《大戴礼·文王官人》篇曰:“取平仁而有虑者……平仁而有虑者,使是治国家而长百姓。”[7]王聘珍解“虑,谋也,思也”,即取成德而有谋思者,可谓“治国家而长百姓”之圣人。《周礼》:“长,以贵得民。”郑注云:“长,诸侯也。一邦之贵,民所仰也。”[8]所以取仁德而有谋思于身者,即为“治国家长百姓”之圣君。这里的“身”,可以指对自己审度反省,也可以指对民众关心呵护,于义皆可通。

子曰:君藏玉,惟慎用之,虽慎敬而勿爱,民亦如之。执事无贰,五官有差,喜无竝爱,卑无加尊,浅无测深,小无招大,此谓楣机。楣机宾荐不蒙。昔舜征荐此道于尧,尧亲用之,不乱上下。
此句以君藏玉比之如何使民,从而引出“楣机”的关键在于尊卑有序、上下安位。*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引洪颐煊语曰:“竝,并也。尊卑有序。《春秋左氏传》曰:‘深思而浅谋’。”见氏著:《大戴礼记汇校集解》,中华书局,2008年,第955页。王聘珍释“测”为“意度”[9]。《周易》“阴阳不测之谓神”,应指此意。“信”为真部字,亦作“申”,与“神”相通,即“变化不测”之义,辞例甚多。[10]如此,信亦可做意度、信验解。两句几可互换而读。
不过,仔细对读之下可知两处文献亦有差别。《大戴礼·四代》篇讲“五官有差”、“不乱上下”,强调尊卑有差、上下安位,不得淆乱;而《子产》篇强调上下“相通”,才能和睦周全。尊卑有序与上下相通,意涵似乎南辕北辙。我们可以再看一则材料:
整理者引《说文》“式,法也”,认为“下能式上”即“取法于上”,[11]即此处所言与简1“能信,上下乃周”意涵一致,执政之关键在于“深浅相信”、“上下相通”,上下须有必要的管道去沟通援引。那么,简文所论与《大戴礼》所主张思想是否真的扞格不入呢?我们再看《大戴礼·诰志》篇:
公曰:“诰志无荒,以会民义。斋戒必敬,会时必节,牺牲必全,齐盛必洁,上下禋祀,外内无失节,其可以省怨远灾乎?”子曰:“丘未知其可以省怨也。”公曰:“然则何以事神?”子曰:“以礼会时,夫民见其礼,则上下援。援则乐,乐斯毋忧,此以怨省而乱不作也。”……在家抚官如国,安之勿变,劝之勿沮,民咸废恶而进良;上诱善而行罚,百姓尽于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12]

二、从《子产》篇看《大戴礼》的相关文本争议
若将《子产》篇的“上下乃周”、“下能式上”与《大戴礼》的“上下援,援则乐”相联系,虽然可以使《子产》篇与《大戴礼》维持表面上的一致,但细究之下,《大戴礼》文本本身的矛盾便又凸显出来。事实上,上文所引《诰志》篇“上下援”一句,历来有多个版本,聚讼不断,并非如此简单。孔广森以为当作:
民见其礼,上下不援,不援则乐。
孔氏补注:鲁人之祭也,宫县而白牡,设朱干,击玉磬,僭天子之礼,季氏亦歌《雍》,舞八佾;陪臣阳虎从祀僖公。此民不见礼。上下相援之验也,故以是戒之。不援则乐,犹“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之意。“援”上两“不”字,宋本并脱,从《大训》。[14]
据此,则杨简《先圣大本》本当作“上下不援,不援则乐”,戴震、汪照、洪颐煊等人与其说同:
戴震曰:“则上不援。‘不’,各本讹作‘下’字,今从杨本。不援则乐,各本脱‘不’字,今从杨本。”(上不援,不援则乐。)
汪照曰:“不,别本伪作‘下’。不援,别本脱‘不’字。”(上不援,不援则乐。)
洪颐煊曰:“袁氏、程氏、卢氏本‘援’上无‘不’字。”(上下不援,不援则乐。)[15]
王聘珍以为当作:
民见其礼,则上下援,援则乐。
注:援,引也,谓引而亲之也。怨,谓神怨。乱,民乱也。省怨而乱不作者,《晋语》曰:“意宁百神而柔和万民。”[16]
于鬯等人同其说:
于鬯曰:“宋本其文如此,孔广森《补注》本、洪颐煊《三朝记》注本并据《大训》本增两‘不’字,作‘上下不援,不援则乐’,窃谓非也,惟上下援故云援则乐,若上下不援,安得云则乐乎?孔谓不援则乐,犹‘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之意,然均也、和也、安也,实皆近于援义,殊非不援之义也,则两‘不’字之增反为无义;至汪照《注补》亦增两‘不’字,而又删‘下’字,谓‘不’伪作‘下’,尤谬。《小戴·中庸记》云:‘在下位,不援上。’则直当删‘上’字作‘下不援’,何得删‘下’字而作‘上不援’乎?彼《儒行》记云:‘适不逢世,上弗援。’*按:《礼记·儒行》篇又作:“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郑注:“援,犹引也,取也。推犹进也,举也。”见孔颖达等:《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49页。则上不援,极不美之语矣,要与其改易,何如仍旧无两‘不’字,义自惬,则何事更张哉!”[17]
《中庸》“在下位不援上”,孔疏以为“援谓牵持之也”,[18]朱子以为此句言“不愿乎其外也”。[19]皆言“求诸己”之道,而不愿求之于外。于鬯指出《中庸》所记是“下不援上”,与此处作“上不援”并不相同,且“上不援”如《礼记·儒行》所载,为“生不逢世”之时,所以不可推出“不援则乐”之说,但《中庸》、《儒行》两篇同出于《礼记》,意涵是否牴牾,还需仔细辨析。如《礼记·儒行》“上弗援,下弗推”所记,援、推即为上下援通之意,“上下不援”为末世之情形,则“上下援”即强调一种与时偕行,与人同化的境界,是一种外向求索的态度,由此,此篇从王聘珍、于鬯等人作“上下援,援则乐”,则与之相通;而《礼记·中庸》言“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朱熹注“此言不愿乎其外也”,[19]则是强调一种不茍流俗、反求诸己的境界,是一种向内自省的态度,由此,此篇从杨简、戴震、孔广森等人作“上下不援,不援则乐”,亦比较合理。然而,这两种思维路径都可以从原初经典中找到依据,且二者的版本学依据又基本相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抉择孰是孰非呢?
三、结合传世文献梳理儒家思想“内”、“外”两条进路
其实,如果我们撇开穷究原初经典的“真实性”的迷障,仅从经典文本的传播学角度出发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大戴礼·诰志》篇里所凸显的“上下援”或“上下不援”的矛盾,实际上与儒家本身既有内向寻求又有外向求索两条进路密切相关。如果我们进一步结合《春秋》记载子产、赵鞅“铸刑书”、“铸刑鼎”,推行刑名律法之治,而使民众知道如何茍免,叔向、孔子等人批评其弃礼辟刑而将有祸乱生的史料,或许对此处二者的分歧,有更为洞彻的体悟。
“上下不援”,即追求内向寻求,“反求诸其身”,更多地强调一种自我警束、自省内察。所谓“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礼记·中庸》)的状态,“为学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个人修身如此,反映到政治公共领域,亦只是个人修身省察的推衍而已,“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君子笃恭而天下平”(《礼记·中庸》)“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这样一种状态,强调自觉与自省,反对所谓人为强制的规制与外在的压迫。叔向批评子产、孔子批评赵鞅,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思维理路上而发的。兹引于下:
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左传》昭公六年)
(赵鞅)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搜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赵氏,赵孟与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叔向所述“弃礼征书,民知争端”与孔子所言“民在鼎矣,何以尊贵”异言同义,重礼义教化,则百姓知荣辱、明羞耻,而有尊贵尚贤之心;征诸刑典,则民众但知辟免祸患而无体己之道,只讲利害而无羞耻之心,*杜预注亦言:“临事制刑,不豫设法也,法豫设则民知争端。”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第1411页。如此,人心涣失而社会必坏,不可以久。《孟子·梁惠王》篇所言“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20]其立足点亦在于此。所以施政者需要做的,仅仅是“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即可。
然而,这样一种“向内求索”的态度,从原始儒家开始,便已经为人所怀疑。如宰予与孔子关于“三年之丧”的争论,孔子诉诸于向内安定情感的自省,便受到宰予向外现实利益考量的质疑。[21]这种争论,在子产等儒家先贤的改革举措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与“内向省察”路径不同,子产所驳,与荀子等人所论更倾向于外向求索的态度,为儒学另一脉。子产以为叔向迂腐而驳之以“吾以救世”,作丘赋受人谤讪而辩之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皆出于这样一种外向求索的态度。这种态度开始注重对礼、法的区分,法作为一种独立于内在礼义之外的规范开始为改革家所重视,儒家的革新派不再将刑法作为礼义的一种附属品而羞于启齿,而是将刑名看作是统治人民、稳定秩序的有限措施。这种对刑名的重视,看似是对内在礼义的一种背离,但客观上又保障了百姓的经济与生活安定,体现了其鲜明的“民本”思想,实际上反而践行了儒家“救世”的目的。孔子赞誉子产为“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或因于此。
四、子产等人外向求索路径合理性分析
其实,我们从历史发展维度去分析,叔向与子产的差异也是时代需求所致,子产时代礼义似乎已然无法有效规范现实的社会政治秩序,鲁国“初税亩”、“作丘甲”,晋国“铸刑鼎”,似皆为时势环境所驱使。饶宗颐先生即指出:
叔向与子产论刑书说:“将弃礼而征之书”,子产答书云“吾以救世也”。这时礼已经无法发挥它的功用。世愈乱已成“已然”之局。“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子产之制刑书,即鉴于礼已经无法挽救,故征之于刑书,以法绳之。[22]
这种取向更强调对社会公平和秩序的维护,往往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所以,他们当然会认可礼义对人道德的提升与人格的完善颇有益助,*如子产引《诗》“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左传》昭公四年)即表明其对礼义的肯定。与之相对应,《子产》篇亦有子产“所以从节行礼,行礼践政有事”(简6)的记述。但同时也不能放弃刑法带来的社会效用。施政者欲使社会秩序稳定、人民没有争心,首先要立法以正名: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其民悫;悫则易使,易使则公。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荀子·正名》)
荀子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立法度、制刑名的重要性,只有这样做才可以使奇辞邪说消匿,使民众可以“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如此社会才能更加公平稳定。因此,有法而不议,有典而藏之,使“上下不通”,反而是对公平与秩序最大的破坏:
故法而不议,则法之所不至者必废。职而不通,则职之所不及者必队。故法而议,职而通,无隐谋,无遗善,而百事无过,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听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偏党而无经,听之辟也。(《荀子·王制》)
“上下通”,从人性论的角度而言,还肯定了人学习的作用及“由学入道”的可能性,关键在于对礼法的学习和掌握:
“涂之人可以为禹。”曷谓也?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性恶》)
要承认“涂之人可以为禹”,首先要肯定“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其实这已经揭橥了人有学习、知道“仁义法正”之理,并由此努力践行以得道的权利。需要指出的是,荀子的“礼”与“法”,应该说是从外在层面,对人的行为规范进行制约,其目的,主要指向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公正。所以,“隆礼重法”思想,应为子产与荀子等儒家一致肯定:
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荀子·性恶》)
《子产》篇里体现出的这两种规范的碰撞,更是随处可见。如简5、6载:
整政在身,文理、形体、端冕,恭俭整齐,弇现有[5]桼=(秩。秩)所以从节行=礼=(行礼,行礼)践政有事,出言覆,所以知自又有自丧也。有道乐存,无[6]道乐亡,此谓劼(嘉)理。
这里的“形体、端冕,恭俭整齐”、“行礼践政”等崇尚礼仪之道与后文的“张美弃恶”等行政举措,一动一静,基本构成了子产“宽猛相济”的为政理念。职是之故,礼与法的结合,才是子产与荀子等儒家政治制度建构的真正用意所在。概言之,即立法制刑以使上下相通,而凸显公正;隆礼明义以使上下交而不乱,以维持秩序。如《荀子·儒效》篇所言:
故明主谲德而序位,所以为不乱也;忠臣诚能然后敢受职,所以为不穷也。分不乱于上,能不穷于下,治辩之极也。诗曰:“平平左右,亦是率从。”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乱也。
“不乱”强调“当其序”,“不穷”强调“通于其职列”,[23]君臣相交而需使其“不乱”、“不穷”,表明其理念最终仍以保障社会秩序为旨归。如上所述,在儒家传统中,如果说叔向、孟子这一脉强调德性的自我充廓与养成,则子产、荀子这一路径更强调外在的规范和制约。*按:由此可见,《孟子·离娄下》篇所记子产“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批评“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此等“惠而不知为政”之举,应属传者误记。焦循引赵佑《温故录》云:“此节正辨子产以乘舆济人之无其事也。君子即谓子产,子产,君子之道者也,其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夫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盖能平其政,非务悦人明矣。济涉细事,本不足为执政轻重,而当执政经临,舆卫森严,津吏祗候,卽有往来喧竞,自当静俟轩车,必无辱观听而烦左右者。大夫之乘非小人所得假,其人既众,岂一舆所能用,此必无之理,曾子产而有之。而世徒妄传失实,是则子产不知为政也,是子产将不得为君子也。”可见此条记载与史传所见子产形象差别悬殊,故有赵氏之猜测。引自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第546页。陈来先生即指出:
荀子认为秩序与道德不是从人的情性基础上自然生长起来的,情性的自然状态是不能建立秩序和道德的,人性不足以支持礼制秩序。自然的放任适足以破坏社会,人为的社会导正系统才能建立秩序,君上、礼仪师法、法正刑罚是规范人心和行动的根本条件。秩序是面对自然情性而采取的社会规制。因此人性并不是根本的价值,维持个人和社群的生活有序才是最高的价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社群主义的观点。[24]
我们知道,儒家思想中,本身就兼具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两大因子,现代学人论之颇详,[25]兹不复举。可以这样说,《儒行》篇“上弗援,下弗推”与《中庸》篇“在下位,不援上”分别代表的是儒家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两种倾向,在社群主义者看来,“上下援”自然可使消息相通,上下乃周,如此则民乐而无忧,“省怨而乱不作”(《大戴礼·诰志》);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上下不援”,反求诸己,于是可以各安其位,“自尽其敬”(《礼记·郊特牲》)。儒家本来就有此“上下援”、“上下不援”两条思想进路,因此,无论是子产铸刑书使得“下能式上”、“上下乃周”,还是叔向批评其使上下援使“乱狱滋丰”、“民有争心”,都是儒家传统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充分体悟,参校荀子“隆礼重法”而分殊之,方能把握其背后所秉持之义旨所在。
结语
综上对《子产》篇部分简文与《大戴礼》部分篇章的对读及阐释,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儒家内外分殊的两条思想进路,尤其是《子产》篇“浅以信深,深以信浅,能信,上下乃周”与《大戴礼·诰志》篇“上下援,援则乐”异言同义,皆表明了儒家注重上下相通、外向求索的思想倾向;同时,这种重法明刑、外向求索的儒学路径,与《荀子》诸篇颇多相合,也使我们可以从子产到荀子,梳理出一条迥异于叔向、孟子的儒学思想脉络,这对学术界深入挖掘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以及重估子产在先秦儒学系统中的价值,不无裨益。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推论,楚简与大小戴《礼记》有着密切的关系。[26]依照郑玄《礼记目录》的分类,足本《大戴礼》应亦可分为九类,其中帝系类应包括《五帝德》、《帝系》、《四代》、《虞戴德》诸篇。[27]又《汉志考·刘向别录》云“孔子见鲁哀公问政,比三朝,退而为此记。凡七篇,并入《大戴礼》”,此七篇为“《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闲》”等。[28]通过对上文的梳理可以发现,其可与《子产》篇参校而读的篇章大多出自以上诸篇,亦可觇《子产》篇所作之确凿。其实清华简刚入藏时,李学勤先生即透露清华简里有很多内容可补传世礼书之阙。[29]之后公布的《清华简》(壹)中就涉及大量礼制内容,其中《耆夜》篇涉及到失传已久的饮至礼,《楚居》篇虽讲楚国先祖之事,却与《大戴礼》之《五帝德》、《虞戴德》、《帝系》等篇性质类似。《清华简》(陆)公布前后,李守奎先生就其中《郑武夫人规孺子》一篇所写《〈郑武夫人规孺子〉中的丧礼用语与相关的礼制问题》,[30]亦表明了此次公布诸篇与礼学有密切关系。本文所述《子产》篇与《大戴礼记》的密切关系,适为此推断又做一注脚。
[参考文献]
[1]李学勤.有关春秋史事的清华简五种概述[J].文物,2016,(3).
[2]赵平安.《清华简(陆)》文字补释(六则)[M].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2016-04-16.
[3]贾公彦.仪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64.
[4]荀悦.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2.66.
[5]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上[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743.
[6]许慎.说文解字[M].愚若注音,北京:中华书局,2015.216.
[7]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196.
[8]贾公彦.周礼注疏[M].彭林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4.
[9]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M].172.
[10]宗福邦,等.故训汇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26.
[11]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6.142.
[12]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3.180-184.
[13]赵平安.《清华简(陆)》文字补释(六则)[M].
[14]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183.
[15]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994.
[16]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3.180.
[17]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释[M].994.
[18]孔颖达,等.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672.
[1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4.
[2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01.
[21]邓立光.从《论语》考察孔子所言“安”与“不安”的意羲[A].国际儒学联合会编.儒学的当代使命——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121-124.
[22]陈其泰.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468.
[23]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152.
[24]陈来.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5—126.
[25]张亚宁.1996-2004年中国大陆儒学研究的新进展[J].孔子研究,2005,(3);陈明.保国、保种与保教:近代文化问题与当代思想分野[J].学海,2008,(9);余祖华,赵慧峰,戊戌思潮:中国三大现代性思潮的共同源头[J].学术月刊,2009,(1).
[26]王君.新出竹简与《礼记》研究[J].山东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李灵洁.出土楚简所见与今本大小戴《礼记》相关文献研究[J].复旦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27]李灵洁.出土楚简所见与今本大小戴《礼记》相关文献研究[J].复旦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28]王应麟.困学纪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690.
[29]李学勤.初识清华简[N].光明日报,2008-12-04.
[30]李守奎.《郑武夫人规孺子》中的丧礼用语与相关的礼制问题[J].中国史研究,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