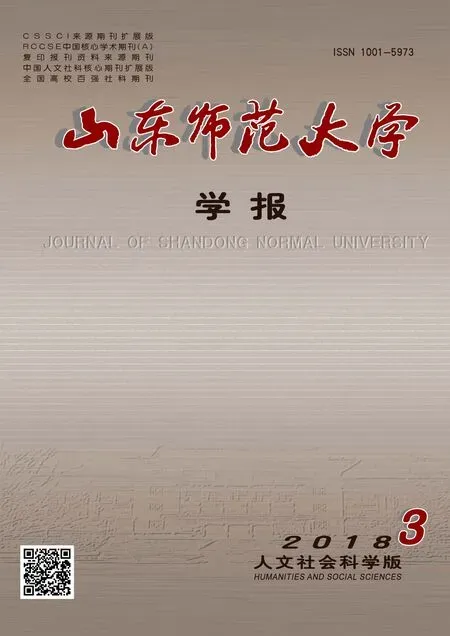人类艺术传播行为法哲学考察*①
马立新
( 山东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数字艺术的滥觞及其迅猛发展,当代艺术秩序发生了剧烈而重大的嬗变。新的艺术秩序一方面呈现出生产与传播方式的无与伦比的自由化、民主化、多样化、多向度化和平等化,另一方面也呈现出日趋严重的致瘾化、低俗化、虚假化和功利化等“高碳”*“高碳”“低碳”这两个概念早已在当代社会语境中从最初的能指“大气中较高、较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引申出一个更普遍、更通识化的所指“不健康、污染、有害”和“健康、绿色、环保” 等涵义。实际上,频繁见之于当代传媒的“低碳生活”“高碳生活”等称谓正是借用了它们的引申语义。下文的“高碳艺术”“ 低碳艺术”两个概念也是借用了它们的引申语义。特征,这些艺术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逾越了艺术伦理,不同程度地损害了各类艺术主体的健康权、财产权或知识产权,因此对其进行法哲学关照就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前沿课题。鉴于此前我们已经对艺术生产权利问题进行了基本的探究*马立新、李攀:《从原子到比特:数字艺术生产权利的量变与质变》,《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6年第7期。,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艺术传播权利的渊源、本体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一
拉斯科岩洞壁画是1940年发现的距今2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绘画遗迹,深藏在法国西南部多尔多涅省的拉斯科地区的石洞内。在岩洞内壁上绘有马、羊、牛等各种动物,形态生动,色调明快,甚至出现了原始人狩猎生活的情景,画中的犀牛、受伤的男子、被开膛的野牛等画面似乎在向人们生动地讲述遥远的历史时空中所发生的一切。除了拉斯科地区,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地区也存在相似的壁画,野牛、驯鹿、猛犸等动物形象被认为是原始人类“狩猎前举行巫术仪式或记录狩猎活动之用”*《辞海·艺术分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293页。。而按照著名传播学研究者施拉姆的观点:“洞穴艺术更可能的解释是为了教育:这些画作或许是成年礼中,部落将神话、图腾及意识传递给年轻族人的媒介。几乎所有的初民文化中都有成年礼的仪式,部落内的青少年通过学习神话和忍受肉体痛苦和疲乏的过程,证明自己有能力担负疲乏之责。”*[美]施拉姆:《人类传播史》,游梓翔、吴韵仪译,台北:远流出版社,1994年,第24页。之后,施拉姆继续将洞穴艺术的思考引向我们感兴趣的方向:“旧石器时代的长者在设计洞穴时,还有更重要的一项目的:即教导年轻人一些事情,并使其永不或忘。旧石器时代的学生没有课本和教室,但他们必须迅速习毕许多重要课程:包括部落的历史和信仰、获取食物以维持部落生存的工具和方法、自然世界的各种迹象等等。这些课程的教导务求深切地铭刻在年轻成人的记忆中,那么,还有什么是比以黑暗的洞穴为背景,使学习情境绝对崭新、无法预期并使人印象深刻更好的方法呢?在洞穴中,老师可以带领学生到达某一位置,使他们能在某种角度或火光的照明下看见壁画而印象深刻;长者可以要求学生爬行过深坑与狭窄通道,然后遽然看见栩栩如生的巨大兽类图而铭记在心。使年轻人牢牢记住这段经验,正是先人选择洞穴作为教学场所的真正目的。”*[美]施拉姆:《人类传播史》,游梓翔、吴韵仪译,台北:远流出版社,1994年,第24页。
通过以上详尽的文字描述,我们仿佛也跟随原始初民一起爬过那黑暗幽深的洞穴,在火光的照耀下欣赏这最早的人类艺术神迹。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在最早的艺术创制中,信息的传播是作为一种重要的目标来存在的,它甚至关系到整个部族的存续,故而在此传播带有一种崇高且神秘的光环。事实上,传播不仅在人类社会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即使在动物界传播也是无处不在且异常重要的。如蜜蜂,它会以空中飞行的轨迹来告诉同伴蜜源的距离。这在群体生活的蜜蜂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种通过信息的传达来维持个体与群体的生存与原始初民的洞中壁画的作用何其相似。当然,二者之间还存在一种本质的区别,那就是语言的产生。“语言的产生是完成从动物传播到人类传播之巨大飞跃的根本标志。”*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页。即使在人类的前语言传播时代,语言传播与动物本能式的信息传播也有本质的区别。“能动性和创造性是人类语言区别于动物界信号系统最根本的特征。人类的语言活动不仅是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进行能动改造这一总体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它还在不断创造和发展着自身,不断开创着崭新的语义世界。”*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页。与动物界的信息传播行为不同的是,“人类能够将对自然和环境的认识作为经验、知识和文化,利用以文字为代表的各种体外化媒介加以记录、保存和累积,并通过教育和学习传授给后代,这是一种效率极高的信息传播方式”*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页。。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传播行为是一种不同于动物界传播行为的更高级的传播类型。
在初步认识了人类传播行为的源头后,还有必要对传播这一概念本身进行界定与梳理,因为它决定着我们的研究脉络与格局。传播一词最早见于《北史·突厥传》:“宜传播中外,咸使知闻。”《唐才子传·高适》曾载:“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为传播吟玩。”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四十六回“宫人颇闻其语,传播于外。商臣犹豫未信,以告于太傅潘崇”等也曾有过相关记述。可见,在汉语中“传播”一词是一个联合结构的词,其中“播”多半是指“传播”,而“传”是具有“递、送、交、运、给、表达”等多种动态的意义。这就指明了“传播”是一种动态的行为,在汉语中常作为动词使用。如传播信息、传播谣言、传播疾病、传播花粉等。在英语中与传播一词相对应的词汇是“communication”,意为“通信、传达、交流、传染”等,但汉语中的传播并不含有交通、交流的意思。*张国良:《传播学原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页。而传播学研究更是一种“舶来品”,它直接受惠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写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17-18页。,而进入中国是晚近的事。国内外学者对“传播”的定义不一而足,库利、皮尔士、施拉姆、霍夫兰、郭庆光、张国良等都从各自的理解上对传播的定义作过论述。而且以上研究是从人类信息传播的整体过程上展开的,各种信息的传播基本上是作为一个研究的整体。在纷繁复杂的传播定义中,我们发现传播学研究者在本质上都将传播看作是一个过程,是一种“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故而在此我们也将传播认定是一个系统的运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所涉深广的社会实践。
在粗略考察了人类传播的源头与传播的概念之后,我们再来审视艺术传播问题。这不仅是因为专门就艺术传播进行的论述还较为少见*马立新:《数字艺术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40-352页。,更重要的原因是随着数字艺术时代的到来,数字艺术的传播范式相比于原子艺术时期已经产生了巨大变化,所以我们更有必要对艺术传播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事实上,正如我们在论述阿尔塔米拉和拉斯科等史前壁画一样,艺术生产本身就带有一种传播取向。它使“人类能够以艺术的方式打量、照看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使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被赋予艺术的意义、情感和价值,进而在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间建构一个艺术世界。可以说,人类的个体和群体是在艺术传播中成长和发展的。在艺术传播的实践活动中,艺术使人成为人,使人超越自我”*陈鸣:《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由此可见,从原子艺术时期以来,传播就成为艺术生产无法绕过的一个命题,艺术传播随着艺术生产的发展,也推动了艺术生产实践的不断前进。纵观世界艺术发展脉络,艺术生产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的阶段。
一是技艺时期,一个艺术生产被认为是一种创作型的劳动时期。在这个时期,所谓的艺术更像是我们今天所指的技术,这种技艺观“将艺术创造与手工劳作混淆起来的同时,更倾向于把雕塑、建筑等造型艺术活动看成是特定技艺的制作性劳动”*陈鸣:《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甚至艺术家也被看作是低人一等的存在,艺术家甚至羞于在自己创作的艺术品上署名或以假名代替*房龙:《人类的艺术》,武汉:武汉出版社,2009年,第119页。。无独有偶的是,在中国先秦时期,中国古人也将艺术泛指各种技艺。“在中国古人看来,艺术是实用型的技能活动,不仅涉及书写、算术的知识,而且还包括射击或驾驭马车的技能、祛除疾病的医术,以及超验性的占卜和巫术。”*陈鸣:《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其后,艺术发展进入了“美的艺术时期”,人类逐渐认识到艺术生产是一种特有的精神生产活动,文艺复兴带来的艺术复兴,是对人的主体性的确认;对于艺术家而言更是其社会地位的赋予,于是我们在这一时期记住了文艺复兴的“美术三杰”、记住了那些令人激动不已的皇皇巨著。1750年德国学者鲍姆嘉通正式创建了一门美的艺术的科学,并赋予其“美学”的称谓,将人类的艺术观念向前继续推进到一个新的时期,即艺术设计时期。这一时期,艺术的观念进一步扩展到了工业设计领域,传统艺术观念中所忽视的设计艺术被纳入进来,进一步扩宽了艺术的疆土,艺术更具备了一种实用价值。当1857年法国印象主义代表作《日出·印象》横空出世后,人类艺术出现了“丑的艺术时期”,各种艺术形式向传统的、古典的艺术创制规则发起挑战。于是,一只夜壶都可以被认为艺术品,在《蒙娜丽莎》脸上出现的胡须也不再是对艺术的亵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更成为荒诞派戏剧的表征。这一时期,艺术的接受者第一次被赋予了主体性地位,接受美学的创立让人们意识到在艺术的传播中艺术再生产的存在,艺术接受者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被动者,而转变为一个能够赋予艺术文本以另一种生命的创作者。也是在这个时期,艺术传播成为一种显学。而起源于照相术的仿像艺术,“人类艺术的生产模式正在向仿真信息编码的可技术复制技术和传媒化的转型过程中,制造出一系列仿像艺术作品,而大众传媒机构的崛起及其在公共领域内所占据的支配性地位,在人类艺术活动中建构起一个面向公共空间的传递环节”*陈鸣:《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页。。这一时期也就是我们要研究的数字艺术时期,数字艺术在此时期因其特殊的传播机制一举超越了以往艺术产品的影响力,成为一种影响最广的数字王国,与社会生活公共空间保持了几乎相当的范围。
伴随着以上五个主要的艺术发展阶段,艺术传播也经历了相应的过程。事实上,艺术的发展演变与艺术的传播是息息相关的。可以说,没有艺术的传播行为,人类的艺术生产只能是个人行为。即使是在技艺时期,艺术生产也只能是以孤立的形态存在的。正是艺术的传播活动使人类历史中的艺术版图乃至文明版图得以拼接成为一个整体。而我们对于艺术传播权利的研究也在此拉开帷幕。
二
我们所谓的艺术传播是之前所说的最广义范畴上的传播,即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而非通俗观念上艺术生产、艺术传播、艺术接受三个过程的一环。按照拉斯韦尔的观点,传播过程分为五大基本要素 ,即所谓的“5W”模式:Who(谁)-Says What(说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向谁说)-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张国良:《二十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2页。虽然其中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如有缺少信息反馈、忽略与社会的联系等问题,但这一模式基本上为传播研究搭建了一个“脚手架”,而我们也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避免拉斯韦尔的模式缺陷,对之进行合理的扬弃,进而去探究艺术传播权利领域中的问题。
“权利是人类文明社会所具有的一种实质性要素。它既是人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是社会文明演化进取中不可少的力量。”*程燎原、王人博:《权利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不论是“天赋权利”还是“人赋权利”,二者在理性逻辑上都承认权利应该是人为了生存与发展的目标而产生的正当需求。卢梭认为权利不仅是每个人生存的主要手段,而且是人的一切能力中最崇高的能力,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特点。*[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46页。在这一点上,英国牛津唯心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托马斯·格林认为权利的形式不是根源于国家权力,而是根源于人的个性和社会的道德性。其中需要指出的是,格林点明了权利是出于人的自然需求和社会需求这两大源头,从哲学的高度解决了价值法学与实证法学曾争论不休的权利来源问题。而根据我们在艺术生产权利部分的研究,艺术生产刚开始是从绝对实用的角度发展而来的,曾经的巫术、壁画、舞蹈都带有实用的目的,只是在后来随着人类生产水平的提高艺术生产才真正成为一种精神生产,但它依旧与现实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6页。同样,与艺术生产紧密联系的艺术传播问题也是遵循着这一逻辑,即艺术传播从诞生之初也是由于决然的实用目的而出现的。这一点在我们刚开始的讨论中就已经证明,拉斯科地区的岩画并非原始初民一时兴起的艺术生产,而是为维护族群的生存与发展、教育下一代而进行的信息的存储行为,它们之所以绘制在岩壁上,无非是因为在幽深的洞穴中更容易将这种信息长久地保存,免受风雨侵袭。这一点也就印证了我们之前所提出的生产的目的在于传播的观点。
在明确艺术传播的权利基本源于人类的自然需求与社会需求这两大源头之后,我们还有必要对这两大源头的具体内涵进行解读。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人类的正常需求构成了人类权利的来源,什么是正常的需求,我们已经在艺术生产权利部分讨论过。但是,对于正常需求的更为具体的类型还有待阐述,因为毕竟对于不同的个体其需求也是不同的,正如作为整体的人类也存在多种正当需求一样。探究艺术传播权利问题,毫无疑问要考虑的是艺术传播主体问题,因为权利必然是人的权利,艺术传播权利也必然是艺术传播主体的权利。而“艺术传播主体是指创造、传递和接受艺术传播客体的行动者”*陈鸣:《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页。。故而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简单的某一艺术传递环节,同样传播也并非简单的信息的传递,还涉及到传播过程中艺术的再生产问题,所以艺术传播远非通俗意义上所认为的那样简单。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在艺术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可以分为艺术生产者、艺术传送者和艺术接受者。同样,艺术传播的权利也存在于这三个主体之间。对于艺术生产者来说,他们是艺术生产环节的主体,毫无疑问有着艺术生产的权利,这一点我们已经阐明,无需赘言。而对于艺术生产主体而言,他们的传播权利从何而来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恐怕我们还有必要以另一种眼光来审视艺术生产的问题,因为“艺术的传播取向是艺术的本质特征”*陈鸣:《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页。。其原因在于,艺术生产在本质上并非艺术家个人的孤立性行为,即使原始社会时期的艺术生产也带有一种固有的传播意图,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其本身就是为传播的意图而被创制出来的。就典型的艺术生产模式来看,艺术家运用各种艺术技巧创作各种感性的艺术形象的过程,就是在生活中寻找灵感并进行加工的过程。而艺术家将之具体化为可见可感的艺术形象并非是为了孤芳自赏,因为如果艺术家创作艺术品只是为了自我欣赏,那么无需将之创作出来而只需要在内心进行自我体味即可。艺术家在普遍吸收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理想中的艺术形象,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向世界呈现自我艺术认知。如梵高穷其一生都希望其画作名扬四海。同样,对于中国古代的艺术家而言,同样有一种积极的入世心态,即使逍遥如诗仙李白,也曾在获得帝王赏识之后,兴奋地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旧石器时代的艺术生产的开放性更是这样,那一幅幅生动的壁画,奇特的威伦道夫的维纳斯都力图与现实生活发生联系,具有鲜明的实用价值。这一切都说明了,对于艺术生产主体而言,其艺术生产行为是一种与世界交流的方式,在本质上是一种说话的权利,是一种融入社会体系的正当欲望,是一种自然的权利,它根源于人的社会性,社会性的人的实践行为必然从根本上是对社会群体的投入。正如匈牙利学者豪泽尔所言:“真正的艺术作品不仅是表达,而是且传播;……艺术家在表达自己感受的时候就是在进行传播,……总是有着某个无名的受者。”*[匈牙利]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134页。也就是说,“艺术创造是艺术家采取的面向他者的一种艺术传播行动”*陈鸣:《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接受美学家伊瑟尔提出了“隐含读者”的概念,这正是对于艺术生产主体在艺术生产中同时蕴涵着传播欲望的证明。
对于艺术传递者来说,他们是艺术传播的主体,他们的传递行为可以分为职业艺术传播与自由艺术传播。*马立新:《数字艺术德性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3页。不论是原子艺术时期的艺术传播,还是数字艺术时期的艺术传播,都是由艺术的传递者作为艺术传播的最重要的环节而存在的。原子艺术时期,艺术的商业性质尚未彰显,艺术传播更多是一种自发的个人行为。正如艺术生产者所期望的一样,艺术传播者在深受艺术品感染后意识到有必要进行信息的共享,将优秀的艺术品传递给社会中的其他个体。这种信息的共享行为在本质上是出于对群体的依赖与融合欲望。事实上,对于人类而言,群体生活是保障其安全性的必要条件,甚至法律惩罚手段也多表现为群体对于个体的疏远和放逐。如果说法律惩罚作用的存在使人有所顾忌并被迫服从基本的社会规范并进而能够不被群体所抛弃的话,那么这种信息的共享行为就是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群体融合行为。这一点我们会毫不费力地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现实的例证。我们往往以某种喜好来形成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比如手机微信朋友圈,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信息的传播圈。在朋友圈中常见的是一种转发行为,这是一种信息的传播与分享。通过分享与传播,我们能够与朋友圈中的其他个体产生一种互动,围绕这一信息形成一个短暂的、小型的话语场域。在充分而热烈的话语交流中,我们感到的是一种与他人保持一种共同喜好的安全感与满足感,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一种群体感。尤其是在数字化生存成为一种常态,现实个体在数字网格中被分割与孤立之后(这种孤立行为与更为便利的交通、通信方式相伴随。在便捷的沟通方式前我们更少面对面去交流,更多是以冰冷的数字符码表达我们的情感),数字表情代替了我们的喜怒哀乐,点赞代表了我们对于一个人的关注,千篇一律的群发信息代替了真诚的问候,这种信息传播与共享行为代替了原子艺术时期的面对面交流,维系并想象出了当下的人际关系。而对于专业艺术传播者来说,他们是出版社、报社、杂志、网站以及工作其间的个体。传播信息的行为对于这些机构与个体来说不仅是出于社会关系维系的必要,而且还涉及更为直接的生存问题。传播信息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权利,这种权利既是命定的又是自主的。试想,如果出版社不能够出版书籍,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之为出版社,同样,如果网站不能供人浏览并随意点击链接的话也必然不符合逻辑。同样,对于就职于这些传播机构的个体,维持其运转是其必然的责任也是其维持生存的权利。由此可见,对于艺术传递者来说,不论是职业的艺术传播还是个人的艺术传播都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他们的传播行为是其德性的具体规定又是其不可剥夺的权利体现。艺术生产者也是遵循这一逻辑。
艺术接受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容否认的被动性。因为艺术接受者在根本上是艺术产品的欣赏者和消费者,即使在数字艺术中,互动性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在遵循这一基本的艺术生产范式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真正期望大众成为艺术生产的主体。“大众既不应该亦无能力把握他们自己的个人生活”*[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刘训练、佟德志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页。,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民主。在艺术接受过程中,“艺术鉴赏者和艺术消费者总是表现出自由选择、个人偏好、自发反馈等特点。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后,艺术公共传播领域的形成,使艺术接受者的艺术鉴赏和艺术消费行为呈现出某种明星热、时尚化和身份感等特征”*陈鸣:《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页。。对于这一点我们毫不怀疑,在当前流行文化领域中这种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即利用某一文化现象而产生的身份认同与区分。青少年往往是这种行为的拥趸,他们会狂热地喜欢上一个明星,并成立一个粉丝群体,喜爱该明星,能够说出该明星的代表作品、个人喜好、生活习惯等相互体认的标志。这成为一种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德]西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72页。,这种艺术欣赏与消费行为在当下满足了一种个性与特殊性的需求。对于艺术接受者而言,他们并非简单的接受者,他们以一种主动传播的方式来表示自己对于艺术品的接受,毕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艺术欣赏与消费并非是一种简单的个人行为。他们需要通过将之传播来寻求一种独特性带来的中心感与共鸣性所激起的归属感。
三
如果说艺术传播主体毫无疑问具有传播的权利,那么艺术传播客体以及艺术传播媒介作为一种客观实体并不具备作为传播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是否就不具备传播特征?这同样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作为艺术传播的客体,艺术品是由具体感性的艺术符号所组成的一种综合体。按照符号学的理解,艺术品是以具体可感的能指来表征形而上的所指,“能指与被意指的事物的关系是任意性的”*[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李幼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5页。,这种关系是通过人的理解来建构的。艺术品在本质上存在一种外向的召唤,使人能够积极参与到艺术作品的理解中,为此伊瑟尔提出了“召唤结构”的概念来指称这种“文本具有的一种召唤读者阅读的结构机制”*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4页。。艺术文本是由艺术符号组成的,而实际上这种文本的召唤就存在于艺术符号中,艺术符号本身就是一个信息源向外传输其所指,这种符号本身就是为他者而表征和存在的。绘画作为一种视觉信号总是吸引我们驻足,这其中既有我们的主动选择,也同样不能忽略这种主动选择的前提是绘画作品的吸引。试想,我们更多时间是在画廊中流连往返,发现打动自己的作品,我们很少能够为自己认定某一种作品并去发现它,在审美接受的过程中,审美效果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艺术品肇其端。与此类似的如音乐作品的音符的主动进入,我们往往在不经意间听到了一首首优美的旋律,影视更是以光的投射来向我们呈现它的样态,这必然也适用于所有可视性艺术品的传播机制,即通过光信号向我们传递信息。从这一点上来看,艺术作品的符号本身就是处在无言的传输中,人只是作为一个较为主动的接受者而存在。除了这种能指的传播特性 ,艺术作品的所指也存在一种传播特性,“英伽登认为作品是一个布满了未定点和空白的图示化纲要结构,作品的现实化需要读者在阅读中对未定点的确定和空白的填补”*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5页。。艺术的内涵与审美价值在本质上是在艺术品与欣赏者内心精神的往还交流中产生的。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不仅表征读者的个性化与特殊化的欣赏特点,同时表征出作为艺术欣赏对象的作品也在与读者进行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共同完成艺术作品的形象的构建和意蕴的传递。
对于艺术的传播媒介而言,其本身既不是一种简单的被动存在,更不是单纯的信息的传递者,而是更为积极地参与到了艺术作品的传递中。正如英尼斯将传播媒介分为“时间偏向型”和“空间偏向型”一样,前者指称笨重不易移动的如石头、金字塔、甲骨文等传播媒介,后者指称如报纸、广播等传播媒介。不同的传播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艺术的内容与形式,以及人们对于艺术作品的感知形式。“不同类型的媒介发生碰撞和更替,必然攸关权力的稳定,甚至可能影响一个帝国或者一种文明的兴衰。”*李明伟:《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9页。按照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信息,是人的延伸。这种观点强烈地驳斥了传统观念所认定的媒介技术本身无所谓好与坏、而在于使用者的使用方法的观点,麦克卢汉认为其“表现了人在新技术形态中受到的肢解和延伸,以及由此而进入的催眠状态和自恋情绪”*[加拿大]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2页。。麦克卢汉将媒介分为“热媒介”与“冷媒介”,其依据就在于不同的参与度与清晰度,这直接证明了媒介并非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传播载体,对于信息的传递乃至生活方式的形成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正如口语媒介更能维持社会结构与文化系统的稳定,因为在原生口语社会中,任何信息只有在反复的口耳相传中才能得到保存,故而先祖的遗训就是一种不变的至上真理。而数字媒介则呈现出一种相反的特性,它打破了这种口耳相传的传播垄断,是一种梅罗维茨所讲的“场景融合型媒介”,“容易打破表演者神秘完美的形象”*李明伟:《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0页。。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我们不难发现儿童所接触的信息能够成倍增加,甚至威胁到成年人在其心中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数字媒介也威胁到了社会所存在的父权地位,在现实层出不穷的对于革命历史的质疑声中,也同样会听到这种声音。所以,对于传播媒介来讲,其本身就是人的延伸,带有人的传播特性或者生就的权利。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艺术传播权利事实上是根源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正常需求,是通过信息的传播来维持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以及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它不同于艺术生产权利的是艺术传播超出了个人范畴而成为一种外向化的传播权利。它是艺术生产主体、传播主体、接受主体甚至是艺术文本、传播媒介所固有的一种先验特性。它如人的生存权利一样,都是固有的且不可剥夺的。从法哲学的角度上来讲,艺术传播权利与人的生命权利一样都是不可剥夺且必需的一种权利,故而从实证法学的角度上来看,应该将之纳入到专门的艺术法律中加以保证在孟德斯鸠提出的自然法中第四条便是“在社会中共同生活的愿望”*[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3页。,故而更印证了传播权利之于人类生存和生活的重要性与作用。传播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之一,“开创了人类交往和社会生活的新方式”*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页。。虽然传播在根本上保证了信息的传递,但是这种对于传播功能的理解未免太过笼统,尤其是在数字艺术传播过程中,传播的作用与意义远非信息的传递那么简单,信息互动环节的出现让我们在受到信息的影响的同时,又根据自己的想象去构建信息的传递内容与方式。
信息的传播行为大体分为职业传播与个人传播。他们主要具有以下功能:(1)群体维系;(2)调节身心;(3)认知世界;(4)权力授予;(5)规范行为;(6)麻醉精神。*张国良:《传播学原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3-55页。其中群体的维系功能我们已经有了颇多论述,质言之,信息的传播让我们能够与他人产生联系,形成一种群体,这一作用甚至存续至今,以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1页。为表征。而艺术的传播能够让艺术接受者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通过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净化”*[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古罗马]贺拉斯:《诗学·诗艺》,郝久新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6页。。艺术虽然是对现实生活的某种加工,甚至加入了一定的虚构成分,但是优秀的艺术品向来是艺术家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必然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艺术的第一目的是再现现实”*[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周扬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81页。,同样在艺术品的传播中必然有着“认识世界”的功能。至于艺术传播能够授予权力则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而且这种权力不太类似于强制性权力。而是一种无形中的话语权力,正如本雅明所言,“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被触及的,就是它的灵光”*[德]本雅明:《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许绮玲、林志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1页。。这种灵光就是艺术品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是黑格尔所谓的“这一个”,艺术在传播中会赋予围绕艺术展开的各个环节一种艺术的圣光,从而使艺术品、创作者、传播者、欣赏者都能沐浴在这种圣光的照耀中,感受到艺术带来的权力。同时,艺术生产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生产,会赋予某种意识形态以权力。“无论个人、组织、事件,一旦上‘报’或登台,即名扬天下。”*张国良:《传播学原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5页。我们细数流行文化所孕育的难以计数的娱乐明星,就会对这种权力赋予功能有所了解。而艺术在传播过程中所具有的规范行为的作用,事实上是与其认知世界的功能分不开的。只有在认知世界基础上才能对世界中的新闻及规范有所了解,同样,世界中共存的行为规范也正是在传播中得到一遍遍强化。在苏格拉底看来,艺术中的美与善是不能分割的,“美必定是有用的,衡量美的标准就是效用,有用就美,有害就丑”*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36页。。从中可以看出,在艺术作品的传播中,接受者会对艺术作品中的信息有所选择,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会与艺术品中的形象在社会行为上保持某种一致性。正如美国“垮掉的一代”效仿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中的出走行为。凯鲁亚克用“狂乱的散文体和没有情节的漫谈描绘垮掉一代‘充满强烈感情’的生活和狂热的旅行……《在路上》为公路文化奠定了基础,凯鲁亚克一直被视为是那些又酷又深沉的颓废派的模板——朋克(punk)、独立音乐人,以及自此之后出现的所有‘酷艺术’的教父”*李彬:《公路电影:现代性、类型与文化价值观》,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年,第61页。。这证明了艺术品在传播过程中对于受众有着行为规范的暗示作用,同样,如果接受者并不认同艺术作品所传达的行为,那么也将在反向度上为他们的行为划定疆界。至于艺术的传播是否会麻醉人的精神这一问题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艺术本身就有高下之分,尤其是在数字艺术时期,各种艺术品层出不穷,同时也产生了诸如黄色淫秽艺术、致瘾艺术、盗版艺术等高碳艺术,甚至艺术作品中呈现出的低俗化、虚假化倾向都是对于人的精神的一种麻醉。正如波斯曼在讨论电视文化时所言:“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儿脑筋,看电视的目的只是情感上得到满足。”*[美]尼尔·波斯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05页。书中描绘了一种可怕但又直接的典型场景: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电视机屏幕闪着幽光,但是面前的观众却没有脑袋!
艺术传播的作用是多样的,它会在原有作用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情况的发展而不断嬗变。以上几种艺术传播的功能自然不能完全涵盖艺术在传播过程中所具有的全部功能与社会影响,况且在数字艺术面前一切瞬息万变,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于艺术传播的社会功能与影像的研究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关注。
四
我们再来讨论关于艺术传播权利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艺术传播权利按照我们的理解是艺术系统中固有的一种特性,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么是否这种权利在行使过程中就畅通无阻高枕无忧了呢?是否我们就能够任意传播我们手中的艺术品而无所顾忌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影响着我们艺术传播权利的行使?根据研究我们知道,艺术传播过程中,艺术传播主体才是权利的所有者,艺术品、传播媒介虽然都有传播特性,但是物的特性不能被称为一种权利。权利的主体只能是人类。自然,也应该从这三类主体中去考察艺术权利传播的影响因素。
对于艺术生产者而言,其艺术生产行为与艺术传播行为是难以割舍的。艺术家在从事艺术生产过程中就已经在内心有了一个“隐含读者”的概念,这其中就包含了传播的雏形。所以影响艺术家在艺术生产中的传播权利的因素首先来自于艺术家本人内在的艺术生产准则、创作喜好、道德标准、创作手段、知识储备等内在价值标准。每一种艺术都有其产生的时代与生命周期,《荷马史诗》只能诞生在人类对于世界一知半解的状态中,但丁的《神曲》也只能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权向神权提出挑战的年代才具有意义,鲁迅的杂文只有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才会显示出令人振奋的战斗精神。虽然对艺术家而言其创作与传播的权利是相对自由的,但是人所处的时代局限性以及人自身的局限性在根本上影响了艺术家艺术生产以及艺术传播权利的行使。我们不能期望但丁能够理解数字艺术,正如量子力学超出了牛顿经典力学的理解范畴一样。在凡·艾克兄弟发明油彩之前,绘画只能以蛋清做颜料一样,数字艺术时期的绘画更超出了现实的物质载体——画布与画框的限制。总之,对于艺术生产者来讲,艺术生产与传播权利是一致的,都受制于其自身的规定性。
对于艺术传播者而言,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传播什么以及怎么传播的问题,他们的传播权利也体现在这两大问题的解决上。职业传播是以传播信息为生存方式的传播行为,其传播权利的行使首先是出于一种经济利益的考虑,传播能够获得更高关注度与经济价值的艺术品,这一规定性也是其传播权利行使的首要因素。在这种因素的影响下,传播主体甚至能出现传播权利的僭越与失范行为。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法律法规的规定性,面向传播行为的相关法律法规构成了传播行为实践的硬性规定,其明确地规定了传播权利的行使原则、行使范围、僭越惩罚等。它为任何传播主体的传播行为划定了显性红线。而传播主体的传播行为的隐性红线则是社会所共存的道德标准,即信息的传播与传播行为必须符合基本的社会伦理道德标准,伦理道德以善与恶的评判形式衡量传播行为的合理性,正如法律法规衡量传播行为的合法性一样。当前虚假艺术的横行,其责任不仅在于这种虚假艺术的生产方,传播方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舆论在谴责这种高碳艺术的创作者时往往容易忽略传播者的责任,须知传播者不是一个被动的渠道或媒介,其作为信息的“把关人”*“把关人”(gatekeeper),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库尔特·卢因于1947年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的。也体现着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于自由传播主体而言,其传播行为借助各种传播媒介已经在传播效果上类似于大众传播媒介。个人传播行为在事实上是一种非营利性的大众传播行为,也要遵循大众传播的相关法律规范。因为不存在经济性因素的考虑,自由传播行为主要出于自己的审美喜好,故而在此影响其传播权利行使的是其对于艺术品的感知程度。当然自由传播行为与艺术生产主体的传播行为在本质上是近乎一致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自由传播者更少考虑经济性因素,这一点是艺术生产主体的传播不能比拟的。我们曾多次见到某些明星的拥趸不计报酬地将他们偶像的作品传播给周围的每一个人,而作为这些艺术品的创作者却在自身的传播中掺杂着或明或隐的功利性。这种自由传播在实际既是传播者又是艺术传播的对象,故而对于艺术接受者的传播权利来讲,其影响因素是与自由传播的影响因素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