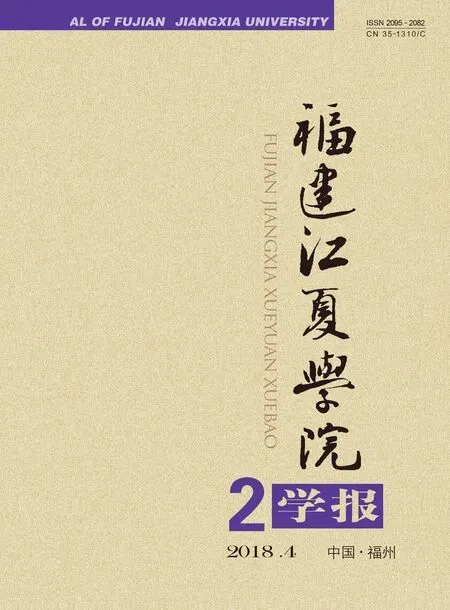论刘知几《史通》的小说叙事观
吕海龙
(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南通,226019)
刘知几《史通》共8次提到“小说”一词,其中《杂说中》①本文这里的“《杂说中》”以及下文先后出现的《杂述》《古今正史》《表历》《补注》《叙事》《杂说下》《杂说上》《六家》《采撰》《书事》《称谓》《载文》《申左》《暗惑》诸篇目皆出自《史通》。本文所涉《史通》引文全部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史通通释》。限于篇幅,不再一一注明。提到的“小说”是指殷芸《小说》一书。此外7次,“小说”一词作为文体术语,与其他词汇构成偏正或联合结构的短语,分别为“偏记小说”(见《杂述》及《古今正史》)、“诸子小说”(见《表历》)、“委巷小说”(见《补注》)、“杂家小说”(见《叙事》)、“短才小说”(见《杂说下》)、“小说卮言”(见《杂述》)。对应这些“小说”术语,刘知几《史通》正文中明确指出的作品共有48部。针对这些“小说”作品,特别是其中的《列女传》《洞冥记》《西京杂记》《拾遗记》《搜神记》《幽明录》《世说新语》等,刘知几《史通》详细阐释了自己的小说叙事观。主要内容有三:一是小说当以“叙事为宗”;二是叙事应以“附于物理”为准;三是小说叙事与历史叙事有“流俗”“雅正”之分。当下学界对刘氏小说叙事观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故本文详论如下。
一、小说当以“叙事为宗”
“小说”在中国古代一直被视为子部之作,唐前论及“小说”,多和“经”部对举,是不“经”之谈,侧重其“说”。先秦诸子散文中,“小说”是与“大达”“智者”之论相对应的语词,如《庄子·外物》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1]类似的观点又见《荀子·正名》曰:“智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2]这一时期,“小说”一词即是指见识浅薄的言论观点。至迟于东汉,“小说”与所谓儒者之“圣人文语”相对举。前者因记录简策之长度少于载录“圣人文语”的“二尺四寸”[3]557,故又被称为“短书”。这一时期,小说一词之内涵与先秦时期变化不大,亦指篇幅短小的细碎之作。就内容而言,多不稽之谈。如《新论·本造》云:“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4]又《论衡·骨相》云:“在经传者,较著可信;若夫短书俗记,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见,众多非一。”[3]112在初唐史臣眼中,小说地位有所提升,成了和儒、道殊途同归的圣人之教。如《隋书·经籍志》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5]1051《隋书》虽然把“小说”提到和儒、道相提并论的“圣人之教”,但在文体观念上,注重的仍是其具有教化作用的言辞。强调的是“靡不毕纪”的“道听途说”。[5]1012其子部“小说”类著录作品25部,由其名目即可见其中大量的都是笑话、语对、辩词类的作品,其次是一些记录水饰、器具的杂书,叙事类的作品寥寥无几。综上可见,唐前虽然对小说的地位是逐步提升的,但就文体层面而言,小说重其“说”的根本属性并没有发生改变。初唐史家刘知几首次提出“小说”当以“叙事为宗”的观点,并结合具体的小说作品、编撰体例、叙事手法以及小说注文对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一)何谓小说的“叙事为宗”
刘知几《史通·杂述》篇开宗明义:“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紧接着又列举出自己所划定的46种偏记小说。最后总结:“案子之将史,本为二说。然如《吕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诸子,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但以名目有异,不复编于此科。”刘氏认为,偏记小说与《吕氏春秋》等子书的不同之处在于,“名目有异”,而共同之处,即“以叙事为宗”。“叙事”一词,其意为何?《说文解字》曰:“叙,次弟也。”[6]69强调一个挨一个,就是按次序排列的意思。又曰:“事,职也。”[6]65最初指职事,后强调所从之事本身。和“事”的两种意思相对应,唐前“叙事“一词连用,其意有二:一是对事物的排列②如《周礼·春官》两处谈到“叙事”。一如“(冯相氏)辨其叙事,以会天位”,指排列年月时节朔望等历法之事。再如“(内史)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指以尊卑秩序安排群臣向国王奏事。这种排列事物之用法,直至唐代仍被沿用。如徐坚《初学记》每一条目的“叙事”部分,即依次罗列群书相关记载。;二是对事件本身或其具体进程的叙述。这个意项较为晚出,为魏晋之后“叙事”所指之主流。③如《三国志·魏书》第十三引王肃语曰:“刘向、扬雄服其(指司马迁)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又《文心雕龙·诔碑》云:“其(指蔡邕)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小说当以叙事为宗之“叙事”,指的主要是对事件的叙述。
(二)小说内容的“叙事”性
刘知几运用“小说”当以叙事为宗的指导思想对其进行分类评价。《杂述》篇视偏记小说为“史氏流别”,并将其分为10类,每类各有其特点,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坚持“叙事为宗”。其中7类者,叙事性尤其显著。一为记作者生活的当时之事。如“偏纪”者,“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二为记录作者所知道的人物及其事迹。如“小录”者,“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则有独举所知,编为短部。”三为记史官遗逸之事。如“逸事”者,“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四为记录作者家乡的人物行事。如“郡书”者,“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五为记录祖先功业,以传后世。如“家史”者,“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六为分门别类,记人善行。如“别传”者,“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则有取其所好,各为之录。”七为记录怪异事物,以广异闻。如“杂记”者,“阴阳为炭,造化为工,流形赋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广异闻。”④该段所有引文皆出自《史通·杂述》篇
此外三类者,亦有一定的叙事色彩。“琐言”类,如刘义庆《世说新语》者,“皆轶事琐语,足为谈助。”[7]“地理书”类,如常璩《华阳国志》者,“首述巴蜀、汉中、南中之风土;次列公孙述、刘二牧、蜀二主之兴废,及晋太康之混一,以迄于特、雄、寿、势之僭窃;继之以两汉以来先后贤人、梁益宁三州士女总赞、序志终焉。”[8]汇历史、地理、人物于一编。“都邑簿”类,如《三辅黄图》者,多记长安古迹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典故。
(三)小说体例的“叙事”性
刘知几指出小说“叙事”之优点:便于采录。他认为叙事有两种方式:一为编年,一为纪传。两者相较,前者容易揉杂在一起,而后者则可非常容易地区分开来。小说作品采用的皆为纪传之体式,同时篇幅较为短小,所以很容易阅览,更容易被史著编选者所采录。如《杂说上》云:“夫编年叙事,混杂难辨;纪传成体,区别异观。昔读《太史公书》,每怪其所采多是《周书》《国语》《世本》《战国策》之流。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若《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之类是也。”
(四)小说手法的“叙事”性
刘知几又于《叙事》篇专门论及夸张、比拟等小说叙事之手法:“诸子短书,杂家小说,论逆臣则呼为问鼎,称巨寇则目以长鲸。邦国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迹,必号龙飞。斯并理兼讽谕,言非指斥,异乎游、夏措词,南、董显书之义也。”在其看来,小说叙事说到逆臣就称曰“问鼎”,提到巨盗则视为“长鲸”,邦国初建就说是“草昧”,帝王发迹一定号为“龙飞”。孔子修《春秋》,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却字字寓褒贬;即使以“文学”著称的子游、子夏不能增饰以片言。南史、董狐记录史事时,则秉笔直书、不加隐晦。然小说叙事,既不能做到指斥其事,却又多陈词套语,虽暗含讽喻,终异乎上述史著的两种叙事原则。刘知几以史著为参照来批评小说叙事手法,这当然有其不尽合理的地方;不过刘氏所论对小说叙事属性的发掘,则彰显出其在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价值。
(五)小说注文的“叙事”性
刘知几甚至看到小说的注文也强调“叙事”性。《补注》篇云:“史传小书,人物杂记,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按:即《华阳国志》),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此之注释,异夫儒士者矣。”刘氏指出,小说家将华美的言辞列为正文,叙述事情的详细经过作为附注。这种注释不同于儒家一派,正如浦起龙此处释语云:“于本文外增补事绪,是注家之变体。”
“小说”作为文体之观念由来已久,可上溯东汉桓谭、班固等人。然由于自身文体的独特性,口传于街谈巷语,集成于稗官之手,内容琐屑,故很难为人重视。同时,这又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创作出现了颇为芜杂的局面。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人们对于小说本质属性的认识不同或者说是偏差所导致。刘知几的贡献在于明确指出小说当以“叙事为宗”,赋予传统小说观以新的内涵,从而逐渐改变了人们小说以记言为主的固有认识;同时,又使得小说文类可以容纳大量传统史传不能收录的材料,为自身发展与繁荣开辟新的道路。
二、叙事以“附于物理”为准
刘知几对小说文体除了提出“叙事为宗”的要求外,还提出小说叙事要“附于物理”的观点。《杂说下》云:
(刘)向之著书也,乃用苏氏之说,为二妇人立传,定其邦国,加其姓氏,以彼乌有,持为指实,何其妄哉!又有甚于此者,至如伯奇化鸟,对吉甫以哀鸣;宿瘤隐形,干齐王而作后。此则不附于物理者矣。
刘知几将《列女传》归入“偏记小说”之“别传”类,认为里面的一些记载“不附于物理”,这比无中生有的捏造还要荒唐。刘氏对小说叙事“附于物理”这一点非常重视。试从五个方面对之阐释。
(一)何谓“附于物理”
“物理”即万物本然之理。“附于物理”,就是指要符合其自身原理。《周易·坤·文言》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孔颖达《周易正义》疏曰:“黄中通理者,以黄居中兼四方之色,奉承臣职,是通晓物理也。”[9]34又《孔丛子·公孙龙》云:“君子之谓,贵当物理不贵繁辞。”[10]282君子之议论,所贵者,在于其合乎万物之理,不在于繁缛的言辞。再如刘熙《释名》卷四:“善;演也,演尽物理也。”[11]何为善者?引申物理,莫不曲尽其情。“贵当物理”本为所谓“君子”言论之高标。
(二)观点产生的内在动因
刘知几对于小说叙事要“附于物理”的要求源自对小说补史之阙的内在需要。《论语·卫灵公》载孔子之语:“吾犹及史之阙文也。”[9]5470是知史文有阙,其来久矣。孰能补?如何补?补的效果又怎样?
一方面,是小说家通过创作小说主动来补史。史官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小说家则向来地位较低,所以就自觉地向史官靠拢,以“补史之阙”的名义抬高自己作品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托名郭宪的《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序》就指出:“籍旧史之所不载者,聊以闻见,撰《洞冥记》四卷,成一家之书。”[12]123又葛洪《西京杂记·跋》云:“抄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13]梁萧绮《拾遗记·序》曰:“删其繁紊,纪其实美,搜刊幽秘,捃采残落,言匪浮诡,事弗空诬。推详往迹,则影彻经史。考验真怪,则叶附图籍。”[12]492伴随着补史之阙,问题也随之而来,正如《文心雕龙·史传》指出:“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14]指责一些著作随意采录传闻以耸动视听而不加考核征实。刘知几则进一步明确指出小说家补史之阙的弊端,《杂述》云:“及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此其为弊之甚者也。”
另一方面,是史官利用小说史料来补史。初唐史家在编撰国史时,其自言采取的做法是以“杂史”“杂传”的名目,将虚妄怪诞之说保存下来以备编撰正史之用。《隋书·经籍志》曰:“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5]962又曰:“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鲁、沛、三辅,序赞并亡,后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5]982
初唐史臣用小说来补史之阙,提出“酌其要”“删采其要”的观点,但是对何谓为“要”,却没有清晰准确的认识与定位,以致在具体创作中出现了一系列较大问题。如《采撰》所举:“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面对纷繁芜杂的材料如何进行选择呢?刘知几提出一套“附于物理”的判断标准。
(三)观点产生的外在契机
小说叙事当“附于物理”之要求,其产生的最直接外在诱因,始于刘知几对于史著记载存在不同的剖析。晋灵公派人刺杀赵盾是春秋时期的一个著名事件。刺客(按:《左传·宣公二年》作“鉏麑”。《公羊传·宣公六年》作“勇士某者”)被赵盾所感动,于是放弃了暗杀,但又不愿意违抗国君命令,最后自尽而死。关于赵盾打动刺客的原因,《左传》和《公羊传》中的相关阐释却有着很大不同。《左传》认为是赵盾勤政尽职,“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9]4053《公羊传》则认为是其“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9]4950的节俭。
刘知几对于两者记载之不同所作的评论,体现出一种“物理”标准至上的原则。《杂说上》曰:
《公羊传》云:“晋灵公使勇士杀赵盾,见其方食鱼飧。曰:‘子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子之俭也。吾不忍杀子。’”盖公羊生自齐邦,不详晋物,以东土所贱,谓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馔,呼为菲食,著之实录,以为格言,非惟与左氏有乖,亦于物理全爽者矣。
刘知几认为《左传》的记载是真实的,而《公羊传》的记载是虚假的,判断真伪之标准即是否“于物理全爽者矣”。刘知几生活于唐代,并没有意识到《公羊传》所记刺客之言,实际上是钱钟书先生所说的“生无傍证、死无对证”“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15]。如果套用现代批评理论来说,刘知几对是否于“物理全爽者”的强调,实际上体现了他对“艺术真实”的重视。故而,对于一千多年前的刘知几来说,能有这种认识还是难能可贵的。
(四)小说叙事要“附于物理”
刘知几以“附于物理”为衡量标准的做法,从史传延伸到小说领域,对小说叙事亦明确提出“附于物理”的要求。其《杂说下》严厉批评刘向作品曰:“伯奇化鸟,对吉甫以哀鸣;宿瘤隐形,干齐王而作后。此则不附于物理者矣。”“伯奇化鸟,对吉甫以哀鸣”的故事不见今日刘向存世之作。曹植《贪恶鸟论》曾云:“昔尹吉甫信用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俗传云:吉甫后悟,追伤伯奇,出游于田,见异鸟鸣于桑,其声噭然。吉甫心动曰:‘无乃伯奇乎?’鸟乃抚翼,其音尤切。吉甫曰:‘果吾子也。’”[16]据这个记载,可以看出里面确有不合情理的地方,比如说孝子被杀变成异鸟等。刘知几极为反对这种死后变为异类的故事。《杂说下》批评扬雄曰:“观其《蜀王本纪》,称杜魄化而为鹃,荆尸变而为鳖,其言如是,何其鄙哉!”刘知几作为正统史家,其观点是对的。当然,在今天看来,小说恰恰允许此类虚构。
刘氏所言“宿瘤隐形,干齐王而作后”者,是指《列女传·辩通传》中“宿瘤女”与“钟离春”的故事,说的是一脖子上长着大瘤的女子与一奇丑无比的女子分别做了齐闵王和齐宣王的王后。据《汉书·刘向传》载:“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17]刘向看到汉成帝宠信赵飞燕姐妹等,便制造出宿瘤、无盐二女的传说,从反面来诠释“红颜祸水”。刘知几认为,这些故事都是不合乎其“物理”标准的。
(五)“附于物理”一说的时代局限性
刘知几之小说叙事应“附于物理”一说的提出,是文史分合过程中补史之阙的必然要求和结果,是历史发展与当时时代的需要。这对小说的内容有所规范。要全面理解这一观点,还必须注意到,刘氏“附于物理”一说还要求把我们今天看来“不合乎物理”的内容也涵盖在内。《书事》云:“怪力乱神,宣尼不语;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圣人于其间,若存若亡而已。”刘知几认为,可以谈论这些若存若亡之事,但是要符合益寿延年或者惩恶劝善的目的和要求。如《杂述》云:“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
小说甚至史著中收录一些在当时史家看来若存若亡、荒诞无稽的怪异之事。如谈鬼论神,统治者借以神化自身、打击对手或愚弄人民。在特定的条件下,人民也借助其曲折隐晦地表达对黑暗统治的不满,甚至通过所谓鬼神的预言来发动起义推翻当时的腐朽政权。但是,从根本上说,这些鬼神故事都是虚妄荒诞的。古代的史家,包括刘知几在内,很难认识到这一点。这是时代局限所致。
三、小说叙事与历史叙事的“流俗”“雅正”之分
刘知几把史书内容的典雅纯正,视为一种史学理想。《称谓》曰:“史论立言,理当雅正。”《载文》云:“禁淫之堤防,持雅之管辖,凡为载削者,可不务乎?”刘知几认为,从事史书编撰的人,要坚持雅正之道。《采撰》盛赞《史记》《汉书》等经典史著云:“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
和史著的“雅正”相对,谈及小说叙事,刘知几则给予其鲜明的标签:“流俗”。《补注》曰:“不能探赜彪、峤,网罗班、马,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刘知几将“委巷小说”与“流俗短书”等而视之,点出了小说叙事的“流俗”特点,并反复予以阐释。要深入、准确把握刘知几这一观点,可结合其对小说叙事的思想、内容、传播途径及与史学叙事本质区别等方面之论断进行分析。
(一)小说叙事思想上多为“异端”
《隋书·经籍志》以为小说与儒、道之思想殊途而同归。《史通》则指出小说乃流俗之作,其为“异端”,此概针对魏征等人的观点而来。刘知几批判锋芒所指,从神话传说到神仙列传以至志人小说,无不在其视域之内。
首先,古代神话传说中关于名人出生的奇异记载,是小说中较具异端思想的部分。如涂山氏化石而生启的故事。又如伊尹产自桑树之事。除了对最高统治者或者政治家的身世好奇外,古代关于人类如何登天,特别是到达月亮或者银河的记载也非常多。《搜神记》卷十四有嫦娥奔月事,《博物志》卷十有海渚之人乘槎达天河事。刘知几对这些记载多有论述,如《采撰》云:“百家诸子,私存撰录,寸有所长,实广闻见。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至如禹生启石,伊产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汉,姮娥窃药以奔月。如斯踳驳,不可殚论,固难以污南、董之片简,霑班、华之寸札。”
限于篇幅,这里仅以伊尹为例对刘氏观点略做评述。《博物志》卷九云:“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于巨迹,伊尹生于空桑。”[12]221伊尹为商代名臣,身世充满了怪异色彩。人们认为其母化桑树后产下他。“伊产空桑”的故事,在今人看来,是一种带有“宗教意义”的“传统观念”,“以树木为神灵并赋予它以祖先意义,不止我国古代如此,古今其他不少民族也是如此。”[18]对于此类记载,刘知几皆视之为“异端”,认为其思想多属诸子杂家一类,与南史、董狐、班固、华峤的史著之作有着根本的不同。刘氏观点有其合理性。
其次,后世充满异端奇说的神仙传记,亦在他的关注视线之内。如《杂说下》云:“观刘向对成帝,称武、宣行事,世传失实,事具《风俗通》,其言可谓明鉴者矣。及自造《洪范》《五行》及《新序》《说苑》《列女》《列仙》诸传,而皆广陈虚事,多构伪辞。”在同一篇又批评说:“夫故立异端,喜造奇说,汉有刘向,晋有葛洪。近者沈约,又其甚也。”
最后,是志人小说。《申左》篇云:“《先贤》《耆旧》《语林》《世说》,竞造异端,强书它事。”《先贤》《耆旧》等书,据刘知几自注,就是指《楚国先贤传》《益部耆旧传》等。《楚国先贤传》,西晋张辅著,书中记载了春秋时期同情政变者白公胜的熊宜僚、东汉时期能够预言洪水何时退却的陈宣等人。[1]《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书中记载魏晋士人轶事琐语,其《任诞》篇多载纵酒放旷、诋毁礼法、傲视权贵、愤世嫉俗的人物。可见,正如刘知几所说,这类小说的思想确有不同于正史之处。
由上文还可以看出,刘知几论及小说著作,多用“苟出异端,虚益新事”“故立异端,喜造奇说”“竞造异端,强书它事”语句。刘氏对小说“异端”之批评,是建立在“新事”“奇说”“它事”认识基础之上的。在刘知几看来,小说思想之“异端”与事件之“新”“奇”紧密相连,互为表里。
(二)小说叙事内容多“调谑小辩”“嗤鄙异闻”
魏晋南北朝出现的志人小说,或记载调笑戏谑的细事琐言,或收录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颇受人们欢迎。风气一起,对国史的编撰也产生很大影响。有写沉溺于饮酒等不良嗜好者。如《世说新语·任诞》写晋人毕卓爱喝酒,甚至因为偷酒而被邻居绑到酒缸上,同时爱吃螃蟹。酒后曾对人说,左手剥着蟹螯,右手拿着酒杯,漂游在酒池中,就足以了此一生。其事后被采入《晋书·毕卓传》。有写饮食方面闹出的笑话。如《笑林》嘲谑初到京城的南方人,大吃马粪、旧鞋,对真正的美食佳肴反而很畏惧,带有几分恶俗的意味。这些记载影响颇大。虽为正史,也有类似内容。如《宋书》提到刘邕爱吃人的疮痂:“邕所至嗜食疮痂,以为味似鳆鱼。尝诣孟灵休,灵休先患灸疮,疮痂落床上,因取食之。”[20]此类记载在今天看来也很有些恶心。
刘知几认为,在史著中记述高阳酒徒、异食癖等是不应该的。《书事》曰:“《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驱蝇而践笔,毕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刘邕榜吏以膳痂,龄石戏舅而伤赘,其事芜秽,其辞猥杂。而历代正史,持为雅言。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闻之者为之抚掌,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瘅恶者也。”刘知几反复强调庸俗甚至恶俗的记载与史著之“记功书过,彰善瘅恶”的追求有着本质的不同,小说叙事和史著叙事存在着雅俗之分,这是小说区别于史著的重要特征。
(三)小说叙事产生并传播于民间“委巷”
刘知几明确指出小说叙事产生与传播的民间性,并将之与所谓的“国史”对立。《补注》篇用“委巷”直接修饰“小说”。何谓“委巷”?字面上是指僻陋曲折的小巷,引申义为民间,同时又含有一种价值判断的意味。《礼记·檀弓上》:“小功不为位也者,是委巷之礼也。”郑玄注:“委巷,犹街里,委曲所为也。”[9]2776往往和鄙俗之事相连。《孔丛子·执节》:“此委巷之鄙事尔,非先王之法也。”[10]373这一点,可结合刘知几对《博物志》《神仙传》《语林》等志怪志人小说的评价来看。
魏晋一些小说打着补史的名义,记载了许多形成、发展并流传于民间的故事。经过长期加工渲染,它们充满了神奇色彩。如张华《博物志》“史补”篇有燕太子丹在白头乌鸦、生角骏马的帮助下,逃离秦国的故事。[12]219葛洪《神仙传》卷六记载了淮南王服用八公之药而成仙的故事。刘知几对这些记载做了评判,认为它们“不凭国史”而“别讯流俗”。《采撰》云:“后来穿凿,喜出异同,不凭国史,别讯流俗。及其记事也,则有师旷将轩辕并世,公明与方朔同时;尧有八眉,夔唯一足;乌白马角,救燕丹而免祸;犬吠鸡鸣,逐刘安以高蹈。此之乖滥,往往有旃。”这实际上指明了小说叙事和史著叙事的区别所在。
志人小说采录的内容虽然看似不像上述那么奇幻,但仍然带有它的民间性和世俗性。《语林》曰:“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当坐,乃自捉刀立床头。坐既毕,令人问曰:‘魏王何如?’使答曰:‘魏王信自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驰遣杀此使。”[12]570刘知几《暗惑》云:“夫刍荛鄙说,闾巷谰言,凡如此书,通无击难。裴引《语林》斯事,编入《魏史注》中,持彼虚词,乱兹实录。盖曹公多诈,好立诡谋,流俗相欺,遂为此说。”在刘知几看来,《语林》所载曹操追杀匈奴使者一事,纯属“闾巷谰言”。所谓“流俗相欺”就是《语林》这一类小说产生的主要原因。历史上的曹操确实诡计多端、为人狡诈,所以民间根据他的这种性格,编造了他追杀匈奴使者的故事。
(四)小说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区别
小说叙事和史学叙事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语言的典雅与否,而决定于是否为实录,刘知几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酒孝经》被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收入“小说家类”,该书今已亡佚。刘知几对其叙事有所评论。《杂说下》曰:“夫以博采古文而聚成今说,是则俗之所传有《鸡九锡》《酒孝经》《房中志》《醉乡记》,或师范《五经》,或规模《三史》,虽文皆雅正,而事悉虚无,岂可便谓南、董之才,宜居班、马之职也?”小说家在创作时,自觉的向五经三史学习,语言上追求雅正,但是他们记载的事件都是不存在的,这是小说家和史家的根本区别所在。
《杂说中》则批评的更为直接:“士安撰《高士传》,具说箕山之迹;令升作《搜神记》,深信叶县之灵。此并向声背实,舍真从伪,知而故为,罪之甚者。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刘峻注释,摘其瑕疵,伪迹昭然,理难文饰。”在刘知几看来,《搜神记》《世说新语》等之所以为小说,根本点就在于其叙事“向声背实,舍真从伪”“伪迹昭然,理难文饰”。
总的来看,刘知几一方面强调小说叙事和史学叙事有着“流俗”“雅正”的不同,但同时又认识到小说叙事对史著叙事的巨大影响,史书中亦有小说叙事的内容。然就根本而言,刘知几认为小说叙事思想异端、内容粗鄙且流播于民间委巷,虽文皆雅正,而事皆虚无,所以说,“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瘅恶者也。”
四、小结
1905年《新小说》第15号“小说丛话”栏目刊登定一的文章,其在对比中西方小说时曾提到,“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现象。此语正如谭帆先生所言:“不幸‘一语成谶’,成了20世纪以来中国小说研究的绝好注脚。”[2]吕景胜等刊发文章《科研政策导向:社科研究应重视本土化》指出:“社科研究忽视本土化的现象日益严重。”[3]当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要重视乃至实现“本土化”,回归古代文学现场,原原本本,看下古人的小说观到底为何,或应成为一条必经之路。刘知几的小说叙事观泽被后世,非止一代。在其影响下的小说创作,自成一脉,其中《国史补》一书更被纪昀誉曰:“在唐宋说部中,最为近正。”[23]刘知几的小说叙事观,不完全等同于西方“虚构之叙事散文”的小说观。当下,中国本位的小说史研究,对之应给予充分重视。
[1]陈鼓应.庄子今译今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753.
[2]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2:416.
[3]王充.论衡校释·谢短[M].北京:中华书局,1990.
[4]桓谭.新辑本桓谭新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9:1.
[5]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6]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7]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182.
[8]常璩.华阳国志[M].济南:齐鲁书社,2010:1.
[9]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0]傅亚庶.孔丛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1]刘熙.释名疏证补[M].北京:中华书局,1975:116.
[12]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3]古今逸史精编[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140.
[1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87.
[15]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8:271.
[16]严可均.全三国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1151.
[17]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957.
[18]赵霈林.兴的源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42.
[19]张辅.楚国先贤传[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24.
[21]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08.
[21]谭帆.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四种关系[J].学术月刊,2013(11):109
[22]吕景胜,郭晓来.科研政策导向:社科研究应重视本土化[N].光明日报,2014-12-22.
[23]永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