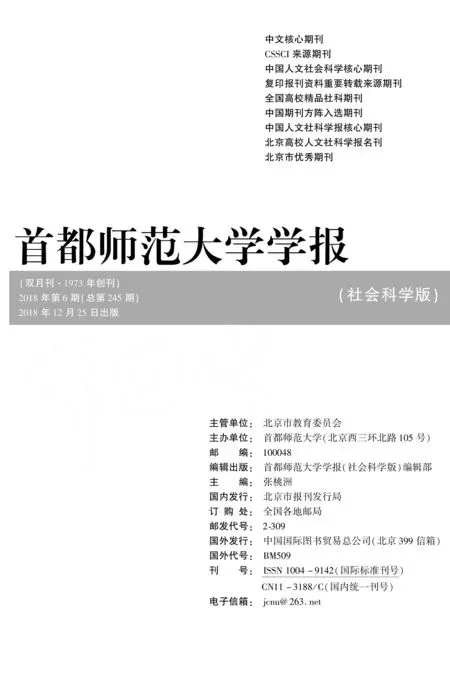论近代上海城市转型的历史与文化
钱文亮
一
近代上海经历了一个从海边县城、因商贸而兴的区域性港市到工商业共同繁荣的国际大都市的特殊历史发展过程。
1843年,英、美、法等西方列强强迫开辟上海为通商口岸、在上海县城的北面设立租界,对近代上海的城市发展产生明显影响。
开埠之前的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南侧的黄浦江畔,为清政府上海县的行政中心,拥有地理条件特别优越的商贸港口。以周长9华里、高2.4丈的环形城墙为界,当时的上海县城地区可分为“城”与“港”两部分。城墙之内的县城“衙署、县学、书坊等公廨布满城厢”[注]茅伯科主编:《上海港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第86-87页。,东门至南门的城墙之外的港区,则是“人烟稠密,商贾辐辏,码头、货栈、商行密布,与城内邑庙闹区成犄角之势”[注]杜黎:《上海开放历史一二三》,载于叶树平、郑祖安编:《百年上海滩》,上海画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不过,当时的上海尽管已称繁荣,且有江南古镇的幽情雅趣,但市容面貌却相当落后,布局杂乱无章,“城厢内外有街巷百余条,但大多狭窄弯曲”,路面高低不平;“同时,沟渠淤积,建筑拥挤,景象破败,几乎没有公共设施”,表现出封建时代中国县级城市的普遍特征[注]朱华:《上海城市发展与规划的历史回顾》,载于苏智良主编:《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1843年11月,根据中英《南京条约》,被列为通商口岸的上海正式开埠。英、美、法等西方诸国的殖民者从此开始占据苏州河入江口两岸和黄浦江黄金水道西岸的大部分岸线,以之作为租界。这些地方当时虽然还是芦苇丛生的浅滩沼泽,交通却极为便利。从开埠到1943年一百年间,西方殖民者以此为中心,一再抓住外交上的有利时机,不断寻找借口进行扩张,最终形成了占地48653亩的租界[注]其中英租界与美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占地33503亩,且不包括1914年以后“越界筑路”的面积47000亩。法租界当局控制区面积有15150亩。详见陈明远:《百年租界的数目、面积和起讫日期》,《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6期。。不仅如此,租界里的西方人还依据《上海土地章程》、《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等成立了自己的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公董局”及其警察武装(即“巡捕”),享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
由于租界占据了中心位置,当上海经济快速发展、市区面积逐渐扩大以后,新的市区只能在租界的外围形成南市、闸北等区域;横梗其中的租界把中国人管辖地区分割开来,形成“三界四方”的特殊格局:英、美公共租界由“工部局”管理,法租界由“公董局”管理,租界之外由中国政府管理。整个上海的城市行政权被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所分割。近代上海特殊的城市框架和行政体系至19世纪90年代初步形成。
上海被迫作为通商口岸城市,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到来在无意间“充当了不自觉的历史工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6页。,使得上海“脱离了原来的发展轨道”[注]何一民:《论近代中国大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与优先发展的条件》,《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4期。。租界的生产生活方式,影响了当时的上海居民,带动了城市的转型。
租界地区第一次获得快速发展的机会,是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先后有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军攻打江南,上海及其周边江浙皖等地区的士绅商贾、官僚百姓竞相逃往租界躲避战乱,人口和财富随之大量流入租界;加上租界当局乘机扩大行政、司法权力及控制面积,租界以惊人的速度繁荣起来。作为城市支柱产业的进出口贸易、埠际贸易、零售商业和金融业,重心开始向租界内集聚。于是,两个新的经济地理概念“北市”和“南市”在上海出现了。北市指新兴的租界商业区,南市即以县城为中心的传统商业区。因为遭受战争破坏,且无有效的市政管理,与“北市”比较,“南市”已经相形见绌。[注]参见朱华:《上海城市发展与规划的历史回顾》,载于苏智良主编:《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第99-103页。
上海租界的近代化首先从市政建设起步。开埠后,因生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租界当局立即修筑堤岸,填埋沼泽河浜,兴建高标准的马路,规划和打造区域陆上交通,在租界区建成了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与此同时,进行整浚港道以及建造码头、开辟公园等工作。这样一来,辖区内“三里五里一纵浦,七里八里一横塘”的水网地貌,便很快被马路、桥梁和街区所取代。[注]罗苏文:《近代上海:多元文化的摇篮》,《史林》2002年第4期。除了道路交通,租界当局还重视市民生产、生活服务类公共设施、公共空间的建设。租界内的西方人直接引进了其母国英、美、法等国的技术,在上海建成了中国境内最早的煤气公司、发电厂和自来水公司,还有通达国内外的电报电话和邮政系统,以及大量的公共娱乐设施。
交通运输的发展和公共设施公用事业的建设,为上海租界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条件。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到20世纪初,以南京路外滩为中心的租界地区已呈现出近代文明的繁华景象。这里不仅成为上海的商业中心,而且道路宽敞,高楼耸立,灯火辉煌,一派大都市的气势[注]有学者认为,1845年《上海土地章程》有关市政建设的若干规定开创了中国近代城市建设的先河,上海租界从一开始就仿照西方现代城市模式建设。详见杨秉德、池从文:《中国近代城市的现代化进程研究》,《华中建筑》2010年第9期。。在进行市政建设的同时,租界当局也将西方的城市管理措施移植于租界内,建立起了纳税制度、市政管理制度、交通规则等,并为这些制度的实施颁布了一系列细则和措施。
至此,上海因租界的存在而不再是单一结构的整体,上海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由此置于一个二元空间:租界、上海县比邻共存[注]罗苏文:《近代上海:多元文化的摇篮》,《史林》2002年第4期。;或者如林达·约翰逊所说,上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城市形态:“二元城市”[注]引自周锡瑞:《中国城市的现代性与民族性》,载于贺照田主编:《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4页。。
相对于租界,上海华界在1895年以前“本无所谓市政。所有清道,路灯,筑造桥路,修建祠庙,举办团防等事宜,悉由地方慈善机关同仁辅元堂经办”[注]蒋慎吾:《上海市政的分治时期》,载于上海通志馆编:《上海通志馆期刊第二年第四期》,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十九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7年版,第1213页。。不过,由于租界市政建设与城市管理的有效,影响了中国的官僚、绅商和市民。1896年,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华界最早的市政机关“上海南市马路工程局”正式成立;1900年春,由上海、宝山两县地方士绅自筹款项,创办“闸北工程总局”,不久“浦东塘工善后局”也告成立。1905年,受清政府“新政”鼓舞,上海县绅李钟钰、姚文枬、莫锡纶等在沪道袁树勋支持下,正式创办“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对人口众多、范围广大的华界进行分区管理,在“形式上是采用当时外侨市政组织中的董事制”[注]蒋慎吾:《上海市政的分治时期》,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十九辑》,第1222页。。而后改组成立的上海城自治公所和上海市政厅,基本沿袭了这套制度。华界的市政近代化受到租界市政建设的影响,历经十余年的建设,华界的闸北等地开始出现比较繁华的近代城市面貌。1914年,阻碍经济发展的县城城墙被全部拆除,旧城区与城外华界、租界连成一片,华界中重要却古老的中心城区也开始了市政建设和管理的全面近代化。
虽然城市建设的规模和成效各不相同,进度也不同步,但一市三治的特殊格局并未分割和破坏城市整体。
晚清时期,租界的发展速度与质量一直走在华界前面,即使到民国初期,在市容市貌等方面,华界仍然落后于租界[注]相对于租界,上海华界迭遭二次革命、江浙战争、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八一三事变”等各类战争的威胁与破坏,正常的建设几度处于停顿状态,这也是华界的城市建设落后于租界的重要原因。参见张笑川:《战争与近代上海闸北城区的变迁》,《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上海的工业、商业和金融活动大多是在公共租界进行,全市大部分的学校、几乎所有报馆,也都是设在公共租界或法租界内。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租界内的外滩原先简陋的建筑更新重造,黄浦江边自北向南,高楼巨厦如群峰突起,与以24层楼的国际饭店、四大公司为代表的南京路楼群形成一个“T”字型,并由此向外辐射,与周围的商贸经营型大楼构成了一幅“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壮观画面[注]参见忻平:《人·建筑·空间·文脉》,载于苏智良主编:《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第117页。,成为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奢华而气派的一种象征。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上海城市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华界对租界的赶超上。1927年7月,直属南京国民政府的上海特别市成立,上海华界因此得到统一规划与治理,市政建设加速发展,市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整体性改观。此后,华界的市区和人口继续扩大,道路建设和公交线路的开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从而与租界一起,将上海城市建设提升到了世界先进城市的发展高度。
在时局动荡、战火频燃的近代中国,由于上海特殊的“租界环境”[注]参见李桂花《近代上海租界环境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及启示》,《上海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与通商环境,形成了大量资金、工厂与人口集中于上海的明显趋势。上海的崛起,是商业贸易、金融业迅速发展的结果,贸易的发展直接引发了城市的工业化浪潮,在整个近代,上海的工厂数量、平均规模、技术和设备,在全国居领先地位;而工商业的繁荣,直接带动了人口规模的扩大,自1852年至1949年,上海人口增长了9倍左右,净增长人口达到500多万人,其中2/3左右是外来移民。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就已经是集商贸、金融、工业于一体的国际大都市,不仅在亚洲独占鳌头,而且在世界上也成为仅次于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的第五大城市。
二
上海并没有北京、西安和南京等古都那样悠久辉煌的历史,但它却从古代一座并不显眼的县城成为经济发达的近代城市,成为亚洲乃至世界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其颇富传奇色彩的崛起与发展本身,恰恰折射出近代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急剧转型的特殊历史进程。
众所周知,中国走出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的国内经济循环而向世界经济体系开放并融入,进而接受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文明体系主要始于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的失败。
在19世纪之前,中国还属于传统的农业社会,以小自耕农为骨干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语)形成农业帝国经济结构的稳固性,并且得到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儒学文化系统的支持和加固。因采取皇室统治的中央集权制,强调专制帝国对“编户齐民”的控制,中国的经济一直是“非竞争性”的[注][美]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处于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之中;“重农抑商”作为安定社会和防止民间权势增大的重要手段,成为专制帝国的基本国策;而且,为保持其“非竞争性”的立场,帝国统治者倾向于闭关自守。这一现象的原因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页。。同时,在儒学“天下国家”观和“夷夏之防”理论的支配下,直到晚清,上至皇帝下到老百姓在“中国是天下的中心”的幻觉中,对世界的认识严重滞后。
而与明清专制帝国大相径庭,自16世纪新航线开通以后,资本主义在西欧诸国迅猛发展,其注重契约与权利、尊重规则与惯例、关注世俗利益等精神取向和品格,带有明显重商主义倾向。其以自由经济为本位,以赚钱致富为荣,提倡竞争——具有那种开发全球市场、实行商品与资本输出并就能源展开争夺的逐利本能。这种逐利本能,导致了鸦片战争,在迫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同时,客观上使一些中国城市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在这些城市中,上海无疑是最重要的代表。
就城市的出现与发展而言,因商兴城、因港兴市是一般规律。早在明清时期,位于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且襟江临海的上海便已成为以商品贸易和手工业生产为中心的城镇之一,在清代嘉庆年间即有“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之誉,而在1835年前来考察的英国传教士麦都士(W.H.Medhusst)眼中,“上海……是中国东部海岸最大的商业中心……即使不超过广州,至少也和广州相等”[注]参见金立成:《“阿美士德”号在我国沿海进行窥探航行的经过与影响》,《上海海运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但是尽管如此,开埠前的上海仍然不能摆脱古典城市形态,其工商业发达程度无法与借贷发达、金融活跃条件下的西方工业城市相提并论。和中国其它普通县城一样,上海的设置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为了商业贸易和工业生产,而是出于清政府在这个地区实行统治的需要。也就是说,开埠前的上海首先是作为清政府上海县的行政中心——县治所在地而存在,仍然是封闭型县城,在体制上处于上海县的管辖之下,并不具有超越县级政区之上的城市建制[注]自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郡县二级制的行政区划体系以来,两千多年间,中国一直只存在一种政区模式,即地域型政区的模式。所谓地域型政区,是指面状的行政区划,即省是国家的区划,县是省的区划,乡是县的区划。在中国古代,城市始终不是行政区划的一种,中国古代社会是积乡而成,而不是积市而成。中国古代的城市最先是作为各级行政区划的中心存在,如州治、郡治、县治等,这些城市既是行政中心,又是经济中心。宋代以后,工商业经济发展较快,在各级行政中心以外又出现了不少经济发达的城镇,方才形成经济中心与行政中心分离的二元化倾向。但是直至清末,经济再发达的城镇也未能冲破封建的躯壳,在体制上依然要受其上级府县的管辖,并未出现超越县级政区之上的城市建制。参见周振鹤:《上海设市的历史地位》,载于苏智良主编《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第82页。,甚至在城市形态上也以圆形的封闭的老城厢为主体。所以,这时候的上海县城,仅仅是国内货物的集散地,扮演的仍然是一个传统商埠的既定角色。其繁华所在实际是城墙之外的港区,在十六铺以南长约2至3公里的黄浦江西侧沿岸。由于商人们赚钱的方法,莫过于长途贩运和贱买贵卖,利润有限,这也决定了城市的人口规模一直在20万左右。[注]参见周绍荣:《租界对中国城市近代化的影响》,《江汉论坛》1995年第11期。
因为中国传统社会“重农轻商”,城市意识相当薄弱,政府只重视征税,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市政管理职能和相应的机构,地方行政官员都不把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所以现代意义上的市政规划和市政建设基本没有。正因为如此,当1843年正式开埠,上海县城仍然保留着江南古镇的幽情雅趣;在城市的管理上,也完全因袭中国传统封建管理方式,城乡无甚大差别。故此,施坚雅才说“前现代中国城市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类型”[注]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徐自立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页。。
不过,上海毕竟又是一个天然良港,有着不同于一般县城的潜在发展优势。其襟江临海的优越地理条件与天生具有的通商优势,早已为处心积虑试图打开中国市场的西方列强所垂涎;所以,当《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美国、法国很快便占据上海县城外交通最便利、发展前景最好的地理位置作为租界,各国洋商更是争先恐后地来此开设洋行、银行,“以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为标志,自1850年代起上海逐渐成为广州以外中国新的对外贸易中心”[注]参见李发根:《论近代上海对外贸易中心的形成——以战争契机与口岸制度为视角》,《上海经济研究》2016年第9期。该文指出,除了太平天国战争对传统贸易格局的打破,1861年汉口、九江和镇江的开埠使得整个长江流域成为上海真正意义上的腹地,才是上海彻底取代广州成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最终原因。。洋商和西方传教士等进入租界后,除了在道路建设、城市规划、生活设施和商业设施方面极力追赶世界潮流之外,租界当局还搬来了一整套与中国传统城市不同的市政组织结构和市政管理制度,在构筑近代城市物质形态的过程中,改变了中国古典城市的结构和功能。具体来说,租界对上海城市演变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它的存在既便利和加强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上海打上半殖民地城市的烙印,与此同时又提供了一个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展览馆”,上海人对其器物、制度到精神的各个层面有了直观、具体的认识与了解;通过租界,中西文化在近代上海直接碰撞、交流与融合,进而形成了影响上海城市的新的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上海面对的实际上是西方近代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空前强大的工业文明。这种影响要而言之,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转变了不少上海人以至中国人的物质观念,使人们接受了工业文明“以商贾为本计”的经济模式与竞争意识,产生了商为“四民之纲”的新的价值观,商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商业成为独立经济部门。晚清末年,清政府出于王朝安危的考虑推行新政,由抑商变为重商,朝野上下一致倡行“实业救国”,在外国资本对华进出口贸易和工商企业兴旺发达的同时,上海的民族工商业也有显著发展。
第二,租界为上海提供了依法自治的城市管理模式,推动了以向租界市政看齐为主要内容的地方自治运动和上海市民自治组织(南市马路工程局、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等)的成立。1927年,上海特别市正式成立,成为与省平行、直辖中央的城市型政区,标志着上海从此脱离了传统行政区划体系的羁绊,在体制上具有了合法的城市建制。
第三,租界内通行国际惯例,具有推动各种产业发展的经济环境;除此而外,在时局动荡、战火频燃的近代中国,上海租界对各类战争与封建军阀势力侵扰具有很大程度的抗干扰性[注]参见李桂花:《近代上海租界环境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及启示》,《上海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加上有效的市政管理和企业管理模式,因此吸引了国内国外大量的资本,上海成为当时中国商业最发达的城市。
第四,租界当局对于租界内不触及殖民者直接利益的言论和行为,一般不加干涉,对当时参与社会发展与社会变革的一些精英人士提供保护,吸引集聚了国内外大量高层次、高水平的文化精英和各类人才,他们在上海兴办新式学校、创办报刊杂志、书店出版社,从事各种科学研究和艺术活动,传播和倡行新思想与新文化。
第五,上海的建筑格局与式样也受到了西方建筑形制的影响。开埠以前,上海地区主要是土木结构的中国传统建筑。受儒家的等级观念和道家摹仿自然、虚实相生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建筑讲究高低错落、对称平衡,以横向铺开的组群式为主,崇尚平面空间尺度的巨大,表现出由“天人合一”观念出发的对大地的亲和力。所以,开埠以前的上海县城其中心是官府的衙门,另外就是豫园、徐园等江南园林,城隍庙、高昌庙、静安寺、虹庙、天后宫等宗教庙宇;而县城的居民住宅也以院落式低层建筑为主,房屋朝向庭院里面,靠院墙连接而呈蜂窝状,以封闭幽深为特征,主要建筑都是中国传统式样。开埠以后,西方人在跑马圈地的同时,也把西式建筑带到了上海。在租界中心商业区,不久便呈现出鲜明的西方景象:“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棂,玻璃五色,铁栏铅瓦,玉扇铜环”[注]黄楙材:《沪游脞记》,转引自苏智良主编《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第197页。。与中国传统建筑不同,西式建筑以砖石钢骨混凝土结构为主导,而且,受宗教文化天堂观念与商业竞争意识的影响,西式建筑以石质梁柱为特点的“柱式”结构,造成了一种上耸的造型和仰望天堂式的布局。在住宅区,西式建筑则追求明亮通风的居住环境与开朗的空间,外表华丽美观,大方实用;和西方人开放心态相适应,租界地房屋的窗户一律朝向街道。受西式建筑的影响,上海的民居建筑很快出现新的特点。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了花园洋房(独立住宅)、公寓住宅、里弄住宅和简易棚户四类民居建筑,其中最多的建筑,是中西合璧式的砖木结构、两层石库门式民居建筑,以及由石库门等普通乃至简陋的房子组成的弄堂。
三
虽然说,西方(近代)文化在上海城市的发展中有重要作用,但这种外力作用不可能脱离上海所扎根的本土文化而发挥影响。固然,中国传统文化有其保守性特征和自我封闭的倾向,但在另一方面,也有善于舍弃固有观念以接受外来事物,吐故纳新的开放传统[注]参见《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纪要》,载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再估计——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1986)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近代遭受西方列强侵略,民族生存发生危机的情势,激发了中国文化开放的一面,这成为上海能够吸收西方文化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近些年的学术研究证实,上海所在的江南地区[注]本文提到“江南地区”的概念,地理范围上等同于“太湖流域地区”。参见陈志坚:《江东还是江南——六朝隋唐的“江南”研究及反思》,《求是学刊》2018年第2期。,开埠以前,在经济结构、社会文化和行为方式方面,已经具有较多的近代性因素[注]参见王卫平:《明清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及其局限》,《学术月刊》1999年第12期;熊月之:《上海租界与文化融合》,《学术月刊》2002年第5期;李伯重:《“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换句话说,开埠之前的上海本已具备飞跃性发展的巨大潜力,而中国的被迫对外开放并加入全球市场,只是上海的潜力得以释放、爆发的一个契机。而这种被压抑的潜力实际上早就形成于江南地域经济和文化之中。历史学家注意到,开埠之前,上海之所以能够从“区区草县”变成“江海通津,东南都会”,这跟清朝康熙、雍正时期开放海禁有关。上海是典型的江南港市。港口盛,上海就盛;港口衰,上海就衰。开埠前的上海为什么不能更“往前一步”?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上海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自主性。朝廷把海禁解除了,上海就发展起来了;朝廷一关门,上海就萧条了。[注]夏斌:《上海,“比虚构更神奇”的城市——专访上海社科院近代上海史创新型学科首席专家周武》,《解放日报》2018年3月16日,第013版。
据此而观之,近代以来上海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其获得了足够自主性。然而仅此一点并不足以解释近代上海腾飞的奇迹。因为同样是作为通商口岸、以租界为主体的商埠城市,如天津、武汉,同样是作为通商口岸、享受了解除海禁、对外开放政策的城市如广州、厦门、威海、镇江、湛江等,其城市近代化的转型和近代化发展的程度就远远不如上海。固然,原因有各种各样,但是除了世所公认的地理优势之外,追根溯源,上海传奇般崛起的深厚基础其实就在江南地域经济和文化之中。
据中国经济史等领域的专家研究,江南地区自宋以降就已经迈入农商社会的门槛,到明清则臻于成熟,具体表现为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市镇网络的形成、早期工业化进程的启动和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出现了商业信用、包买商、雇佣劳动和早期工业化等新经济因素[注]葛金芳:《“农商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宋以降(11-20世纪)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也正因为如此,日本著名汉学家斯波义信才认为宋以降江南社会已经带有更多的“都市化文明”之特征:“8-13世纪的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增长,从而带来了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化。总之,可用一句话概括为:与其说是‘纯农业文明’,不如说是‘都市化文明’含有更多的固有特征,这是延续到19世纪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色。”[注]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5-66页。因为其市场化在整个中国先行一步,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商人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传统的士-农-工-商的顺序,在开埠之前实质上已经是士-商-农-工了。上海社会生活中,商人地位也比农人高。[注]熊月之:《上海租界与文化融合》,《学术月刊》2002年第5期。
有利于上海“接轨”近代工业文明的江南地域文化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江南人在“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注重“事功”的观念影响下所形成的求真务实的精神。许纪霖言:“上海文化传统也有个本土资源:明清以来形成的江南士大夫文化”,“这种文化传统在上海开埠后与西方两种宗教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了。一方面上海江浙文化中的理性主义成分(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和新教传统相结合,另一方面江浙文化中才子佳人的浪漫温情成分又与拉丁文化产生回应,这就使上海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产生了奇妙的对应关系”。[注]许纪霖:《上海文化的反思》,《中国青年报》2003年11月12日。可以说,中国江南文化与西方工业文明的融通奠定了近代上海城市发展最重要的文化基础。与近代工业文明承认世俗生活的合法性、鼓励追求财富的奋斗理念相似,江南地区崇尚物质享受的市民文化在近代也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追逐声色货利,追求新奇,讲究饮食衣着,蔑视礼教,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已是普遍现象。换句话说,工业文明的某些近代因素,在开埠以前上海所处的江南文化环境中,也有类似物或萌芽存在。而开埠以后,来自国内外的各种移民和各类人才中又以江南人占比最高[注]“涌到上海的众多移民中,江浙人是主体,占总人口80%以上。”参见马学强:《近代上海成长中的“江南因素”》,《史林》2003年第3期。,构成上海市民的主体部分。这些因素结合起来,造成了上海成为文化交流、融合的有利场所,带动了上海从传统商埠向近代都市、上海人从乡民向市民的历史性跨越。
的确,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文化发展,起决定性推动作用的主体毕竟是人,是人口的素质。在这一方面,江南地区对于上海的发展居功至伟。
众所周知,江南地区自宋代以后人口就已高度密集,由此造成耕地不足,逼迫江南人民逐渐形成了精耕细作的传统和勤劳敬业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除此之外,巨大的生存压力也迫使大批劳动力转向生产经济作物和从事以丝织和棉纺为主的手工业、商业及其他服务业。江南人民走向多种经营发家致富的传统,可以说无意之间为开埠之后多功能发展的上海商贸业、服务业、金融业和工业等储备了最充分的高素质人力资源,而上海开埠后在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高效而神奇的变化当然也得力于江南地区所贡献的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和职业管理人员。这些江南地区人力因素,是上海腾飞的雄厚资本。
江南地区在文化上对上海城市转型的贡献还表现在崇文重教的民风和传统上。所谓“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关于江南地区科甲兴盛、人文荟萃的论述,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不过,以前的研究往往侧重江南作为著名的“科举之乡”,状元、进士等精英人才在全国的比例很高,而相对忽视了江南地区遍布城乡的家学、私塾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达与繁荣,以及普通民众崇尚读书习文、重视教育的浓厚氛围。据相关的历史研究显示,相对于全国男性低至20%-25%的识字比例,[注]此数据为荷兰学者伊维德(W.L.Idema)的测算,转引自刘永华:《清代民众识字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清代江南男子的识字率将近45%,已经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中接受过县学、府学教育的人数相当可观。[注]参见熊月之:《略论江南文化的务实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而尤为特别的是,不同于传统中国的其他地区,江南许多普通人家的女子在明清时一样能够读书识字。[注]朱恒夫:《刀与水-江南文化的特色——在三峡大学民族学院的演讲》,《三峡论坛》2017年第1期。在上海城市经济的惊人发展中,江南地域的文化为之提供了深厚基础。在笔者看来,这种基础因为结合了长期成长于农商社会所形成的开放心态,就使得崇文重教的江南人多了一些“知书达理”的理性、多元思维的宽容。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人最后选择上海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租借居留地,正是因为这种比较宜人的地域性格。对此,美国学者霍塞(Enest 0.Hauser)的论述足为佐证:“从广州来的英国人对于这个地方觉得很为满意。他们觉得上海人比广州人来得和气,举动较为文明,走过街上的时节,不像在广州一般时常要受到当地人民的侮辱”;第一批到上海的美国人在写给他们本国总机关的报告中也这样描述他们眼中的地方情形:“他们的性情仁慈和平,乐于学习,虽因习俗之所积偏于迷信,但在实际上并没有过分的重视它。”[注][美]霍塞:《出卖上海滩》,越裔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第11页。
四
近代西方列强的战争侵略给中国人的情感造成了一次次屈辱与挫败的记忆,因此,上海城市开埠以来的发展与演变,又始终受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处于中国人创建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与追求之中,在中西、华洋、殖民与被殖民、现代和传统、城市与乡村之间激烈的冲突鼓荡中,上海实际上变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城市,形成了自己复杂而独特的发展历史。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因为租界对中国主权的攫夺,使得上海形成了独特的“二元城市”形态,导致全面的城市规划难以实现,全市范围的资源调动也是不可能的,城市发展出现极不平衡的局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城市改建工作被视为实行现代化进程的首要任务,上海因此被南京国民政府确定为重点开发建设城市,“中外观瞻所系”,受到方方面面的极大重视。南京当局特将原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所辖大片土地划入上海特别市,使上海城市发展有更大空间。而在实行西方模式的城市化进程中,上海城市改建者也竭力保持着城市建设的中国特色和地方特色。上海特别市成立后,曾提出过一个旨在摆脱租界掣肘、改造上海城市布局的“大上海计划”。这个庞大的城市建设规划以五角场为新上海的中心,主要建筑群吸取中国传统轴线对称手法,设想以巨大的中式门楼和宫殿造型突出民族特色,并藉此消除上海中心城区的殖民地记忆。该计划未纳入租界,也避开了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区,实际上属于城市局部地区的开发规划。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该计划主要完成了开辟市中心区、辟建道路网、建造轻便铁路“三民路支线”等三项重要任务。[注]李百浩、郭建、黄亚平:《上海近代城市规划历史及其范型研究(1843-1949)》,《城市规划学刊》2006年第6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回租界,西方人主导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由此终结。面对战后国家重建和复兴的重任,上海市政府专门设立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都委会”——笔者注),负责编制“大上海都市计划”。自1946年底至1949年5月底,该计划共完成三稿,最后交给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市政府集结成册而保存。作为二战后中国大城市编制的第一部城市总体规划,“大上海都市计划”虽然没有付诸实践,但其意义与影响却是深远的。该计划采取行政领导与专家相结合、以专家为主的方式,从一开始就贯穿了当时城市规划界主流的现代主义的理性思想和理念,包括有机疏解、功能分区和区划管理、邻里等理论,并且深受当时完成不久的艾伯克隆比主持的大伦敦规划的影响,对上海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充分而认真的讨论。其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城市规划中仍然得到了延续,其原理、工作方法在学术和实践中得以继承,也为当今上海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工作提供了较好的历史基础。[注]详见张玉鑫、熊鲁霞、杨秋惠、乐晓风:《大上海都市计划:从规划理想到实践追求》,《上海城市规划》2014年第3期;侯丽、王宜兵:《<大上海都市计划1946-1949>——近代中国大都市的现代化愿景与规划实践》,《城市规划》2015年第10期。
结 语
近代传奇般崛起的上海既是工业文明全球化扩张中在东方大地生长起来的“新器官一样的东西”[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也是江南地域文化传统在近代化烈火中的凤凰涅槃;而更为重要的,是上海的城市发展适逢中国由农业社会(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城市社会)的近代化转型期,可谓“时势造城市”。城市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特殊的历史与文化积淀,在这样的两个时代过渡的节骨眼上,作为“江南的上海”成为当时清政府治下的经济“特区”和文化“特区”,进而跃升为“中国的上海”、“世界的上海”,实属偶然之中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