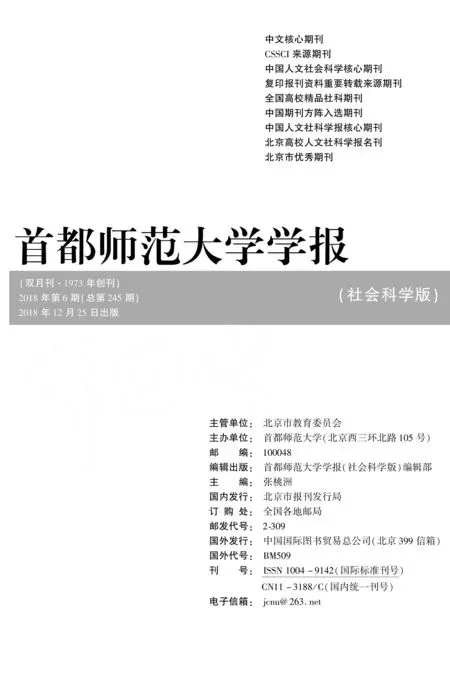先秦儒家乐论两境界
薛富兴
孔子是个音乐爱好者,《论语》中有许多孔子论乐之言论,成为孔子音乐思想之典型表现。同时,在这些看似零散的关于音乐的只言片语中,孔子实际上形成了自己较系统的音乐思想体系。孔子有关音乐的言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礼仪制度,个体理想人格建构,审美。
一、礼乐并举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注]《论语·阳货》,自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15页。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注]《论语·八佾》,第85-86页。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注]《论语·子路》,第174页。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注]《论语·季氏》,第206页。
孔子“礼”、“乐”并举乃在说明:音乐在春秋晚期,在孔子眼里并非独立的艺术形式、审美之具,如今人所理解的那样;而是当时周代礼仪制度体系之一部分,音乐要为礼仪制度服务,而不能仅仅作为娱乐或抒情艺术而存在;但是春秋晚期,周天子中央政府势力衰微,诸侯国坐大,已出现“礼崩乐坏”局面,孔子对此痛心疾首: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注]《论语·八佾》,第85页。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注]《论语·八佾》,第85页。
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注]《论语·季氏》,第206页。
此乃时人不依周礼之规定,随意越位用乐之例。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注]《论语·阳货》,第216页。
所谓“郑声”,实即国家制度文化体系——“礼乐”制度之外,以视听感官愉悦——审美为主要追求的民间音乐。“郑声”的出现,乃先秦重要历史文化信息,它意味着独立于官方礼仪制度之外,相对独立、较纯粹的审美音乐甚至民间文化之诞生。但是,孔子出于维护既有周代礼仪制度文化传统和周天子中央政府权威的角度,对时代之新音乐——“郑声”持根本的反对态度,坚持为周礼服务的雅乐——《韶》、《舞》的权威地位:
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注]《论语·卫灵公》,第198页。
孔子将“郑声”与奸人并举,可见他对时代的音乐新信息、新事物,对来自民间的纯审美之乐从根本上是否定的,未能意识到它的价值。由于孔子将音乐(包括了舞蹈、诗歌)根本地视为周代礼仪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面对春秋晚期“礼崩乐坏”局面,他将 “乐坏”视为“礼崩”之象征,因而进行了严肃的音乐批评,进而谋求通过“正乐”而 “复礼”。因此,孔子一旦有机会就会切实贯彻他的音乐理念,对周礼系统之外音乐的处罚极其严厉: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注]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卷47,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44页。
此乃夫子以乐卫道的极端表现。但是,大部分情形下,孔子对于礼崩乐坏的局面,只能徒叹奈何。他一生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鲜有知音。最后不得已老而返鲁,只好从事整理前代文化遗产的工作。作为周礼一部分之音乐,或为周礼服务的音乐,此乃孔子音乐观之核心。孔子如此要求音乐,也如此要求作为文学、诗歌的《诗经》,是否符合周礼的要求,也是孔子整理《诗经》、取舍其时诸侯国民歌的核心标准: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注]《论语·子罕》,第141页。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注]《史记·孔子世家》卷47,第1559页。
这才是孔子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工作,他依据周代礼仪制度的要求系统地整理前代雅乐,经他整理之后的诗乐,最终被后代奉为经典。孔子无力改变他不满意的社会现状,作为一个书生,他能做到的只是根据自己的文化理想——“克己复礼”对当时所存文化典籍——《诗经》进行整理。有赖于夫子,今天我们才能看到两千多年前的各地民歌;只是由于夫子,我们已无法再见到被夫子删去的当时更多的其它民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合于己者未必不合于人;不合于今者未必不合于明天。多存慎删方为更包容、明智之文化态度。夫子“正乐”与“删诗”之壮举也许并不能成为人类关于文化继承的理想典范。
孔子乐论开创了儒家他治论或功利主义文艺观先河,后代儒家一直用“文”(艺术性或审美价值)与“质”(文艺的政治、伦理性内容)这对范畴来规范文艺,此观念之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
二、理想人格塑造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注]《论语·阳货》,第217-218页。
此则以礼为后,以仁为先之例。孔子的其余言论则以礼论乐居多。在此则言论中,孔子更突出仁之内质,以礼为外,礼属于乐。孔子将礼乐制度与人性建构事业联系起来,而人性建构之核心乃是仁。因此,乐亦当服务于仁之培养。夫子将外在的礼乐制度要求建立在天然的血缘亲情之爱上,建立在内在的文化人性培养上。基于对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制度与人性关系的深刻认识,孔子进一步强调观念文化建设的意义。
切实维护周代礼仪制度只是孔子论乐的一个方面。作为一个观念文化生产者,孔子对音乐功能的理解远超越于其同时代人。音乐作为制度文化建设工具之外,他还见出了音乐作为人类观念文化产品对主体内在精神世界的深刻影响作用——音乐对人心的调节与导引。他自觉地将音乐用于君子理想人格之铸造。孔子在大力提倡维护周礼的同时,也提出了个体理想人格建构问题——君子之培养,将这一事业作为周礼维持的更深层努力,认识到没有社会成员个体内在的心理认同与自觉努力,外在礼仪制度实难以维系。这实际上是将制度文化建设转化为观念文化建设,以自觉的观念文化努力为周代礼仪制度之长期存在奠定坚实的心理基础。具体到对音乐功能之认识,可谓由外而内之升华。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注]《论语·泰伯》,第132-133页。
此处孔子诗、乐并举,说明其时诗歌始脱离舞、乐而成为独立的文学艺术形式。一个人应当通过礼仪教育奠定(“立”)自己的行为规范(规范伦理),用《诗三百》启蒙其社会性情感(“兴”),用音乐完成自己的人格塑造(“成”)。音乐是人格塑造必不可少的要素,且是人格培育的完善性环节。能欣赏音乐标志着个体人格之成熟与完善,何以故?
乐者,音之所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注]《礼记·乐记》,引自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下),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713页。
音乐是一门人际交际的艺术。一方面,人心受到外物(自然与人事)之刺激,感动时会有音乐产生;另一方面,当音乐出现时,欣赏者应当有与之相呼应的能力,这种通过音乐作品能感受其他个体,乃至一个群体、时代内心精神状态(喜怒哀乐)的能力,正是文明社会个体人格必须具备的心理能力、文化能力;有此即可谓“君子”,无此即可谓“野人”。一方面,音乐最为感性,每个有正常听觉感官者均可欣赏,故“其入人也深”;另一方面,音乐又最为抽象,只由声音构成,它考验着每个个体的感受、想像与情感体验能力,此种能力体现了个体,甚至群体精神的发育程度。更重要者,音乐是一种人群交际艺术,心心相应的艺术,故而共同欣赏音乐可促进特定群体内部个体成员间的情感交流、心理认同与秩序和谐。在此意义上,可谓“乐可以群、可以和、可以成”。乐可用以培养个体与他人的心理沟通能力,此能力乃检测特定个体成员人格发育程度、成熟与否之重要标志。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注]《论语·述而》,第121页。
此乃夫子乐论之又一面——将音乐与个体理想人格塑造——君子之德的陶铸紧密结合在一起,是立足于个体理想人格塑造论音乐功能。准此,我们见出音乐价值功能之另一端——音乐对于个体精神成长的价值。夫子为此提出一个完善的君子人格培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制度——德性——艺术审美相互合作,共同构成人格教育三大支柱。若对人格培养作过程性动态描述,则诗、乐正处于个体人格培育之首尾两端:人格教育之始,需由诗教导入,以其可兴发人感性心灵之敏感、天然之善端情愫也;以对乐之爱好而终之,以其陶陶然可醉人以乐也。居其中者,乃社会礼仪规范、良俗美仪之培养。换言之,外在行为规范之培养与内在的自由感性趣味、情操之培养当相辅而行。只有当一个人能培养起对音乐的真切爱好,在音乐世界中体验到这个世界的秩序与情感、本能的触发与超逸之玄思,能自由地悠游出入于其间时,才可谓其个体精神人格成熟了。
完善的人格培育当首先包括行为准则教育——天道、德性与仁爱,此乃君子人格之必要条件、奠基部分。完善的人格培育还当包括精神自由部分——“六艺”(特别是其中之“诗”与“乐”,即今之“艺术”。)。艺术教育关乎个体审美趣味之养成、社会情感之培育与创造潜能之激发,乃君子人格之超越部分。前三项乃不得不如此之人格义务、道德律令;后者则是可“好之、乐之者”的自由部分,是人格培育中轻松愉快的环节。“游”揭示了“艺”之自由性质。简言之,理想人格的培育需要由哲学教育(道)、伦理教育(德与仁)与艺术教育或美育(艺)三者构成。
孔子是在人格培养教育中提及乐与艺。《诗经》本从于“乐”,自孔子对其文字文本之整理与编订后,始脱“乐”而独立,成就了后世独立于“乐”而存在的诗歌、文学。“乐”乃早期艺术原型,“艺”(“六艺”)乃其继之者: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 曰九数。[注]《周礼·地官·保氏》,引自徐正英、常佩雨译注:《周礼》(上),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94-295页。
依今人,“乐”与“艺”所同者在于“艺”,即为抒情或美而存在之艺术;然在先秦,“艺”(“六艺”)之基础义当为“技”——“技术”、“技艺”之“艺”。在此意义上,“乐”比“艺”更近于今日之“艺术”概念。
若对人格培养作静态考察,夫子以为有四端最为重要,那便是“道”、“德”、“仁”和“艺”。“道”谓天地外在之理,“德”谓个体内在之性,“仁”为发之于个体内心的爱他人之德,“艺”谓礼乐之文,即礼、乐、射、御、书、数。此谓完善人格之养成,乃是对这个世界之全方位感知,既要了解外在世界客观的万事万物之理,也要有对主体自身德性之自觉,既要有自我意识(“德”),也要有同类意识(“仁”)。“道”是面向外在世界的知识、哲学教育;“德”与“仁”是面向人类社会自身的伦理道德教育,“艺”则可大致理解为今之艺术教育、审美教育。“艺”在当时是一个综合体系,既包括了音乐,也包括其它实用技术。这里需要特别注意“游”这个概念。“游”之本义为游水、游动,在这里则归结为精神心理的自由无碍境界。理想人格的建构过程,既包括了不得不然的内容,此即所谓“志”、“据”和“依”;但最终当体验为一种随心所欲的“游”的境界,也只有最终体验为自由境界,才算理想人格之真正养成,这样的德性才能持久。这就是夫子为何两处均以音乐为代表的“艺”来收尾的原因。
此言理想人格建构之数端。虽有四端,然夫子未具体解释其各自之具体内涵,故后人无法具体了解夫子之理想人格建构体系。以朱子之论,道乃言万物之所以然者,此盖外在客观之理,德乃道之化于人的内心者。若此,则德并非独立之一端,乃道之主体化;惟仁乃夫子之重心,乃主体人性之核心概念,似足可与道并立者,以为主体之本。仁之发端虽自血缘亲情,然当它由血亲间之自然亲情外推发扬到对非血缘的他人之爱时,其主体部分尚需伦理理性之介入,需伦理理性支撑下的长期培育和固化。故而“道”与“仁”皆乃不得不然者,惟于艺则可成悠游之境界,若夫子所言“随心所欲而不逾距”境界乃又一种心境。故夫子论理想人格塑造实由两个阶段构成:一为做人之不得不然者,于外曰道,于内曰仁;二为人心之可自由者,曰游曰艺。一为信守,一为自由。上述两条,可理解为夫子关于以音乐培养完善人格的整体性见解。总之,理想人格之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有多方面的努力。这其中,“乐”乃不可或缺之重要一环。
对于音乐孔子同时有两方面标准:一是外在的周礼制度要求,二是内在的文化人性培养。乐先属于礼,又服务于理想人性建构。立足于内在的人性建构,而非仅外在的制度建设,给制度文化以观念之基础,此乃孔子的贡献,是国家意识形态向士阶层观念文化之深化。整个孔子仁学当作如是观。[注]关于孔子化礼为仁、孔学以仁为本之讨论,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之《孔子再评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三、审美功能
孔子于音乐不完全是功利主义,他对音乐也有相当内在的意见。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如也,绎如也,以成。”[注]《论语·八佾》,第92页。
此述音乐作品行进的阶段性特征。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注]《论语·述而》,第123页。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注]《论语·泰伯》,第134页。
此论音乐的悦耳娱心之效,这些都是很纯粹的审美评价。在音乐的审美功能方面,孔子也有积极建树。此可证孔子于制度考量、人格教育之外,对音乐又有极内在的趣味与欣赏能力,是个音乐艺术的行家里手。具体地,孔子已然形成一套成熟、可操作的音乐批评模型,这一模型有三种形式。
其一,正面典范个案示例法。
何为佳乐?可以拿成功的具体音乐作品示范于人,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案示范向人们树立正确、成熟的音乐观念。先秦音乐作品中,孔子极力推崇的是《韶》。《韶》亦称《大韶》,相传为舜乐。夫子以《韶》为音乐最高典范,凡三论《韶》: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注]《论语·述而》,第123页。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注]《论语·八佾》,第93页。
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注]《论语·卫灵公》,第198页。
孔子对《韶》作了三方面的推举:一言其能给人带来最大的审美快感,这是最朴素的感性审美经验描述;二曰它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这是对其价值功能理性的高度总结;最后又以《韶》与消极榜样——“郑声”对举,以《韶》为雅乐、正乐,乃符合周礼制度要求,正可为理想之乐代言者,孔子心目中伟大音乐的经典。
其二,要素关系分析法。
这一方法更具体深入地分析音乐作品如何处理核心要素之关系。对音乐要素关系之描述,又有积极与消极两种形式。
积极言之,则曰: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注]《论语·八佾》,第93页。
此可概括为“A而B”。“尽善尽美”乃儒家艺术批评标准之典范话语。质的界定曰“美善兼顾”,或政治(伦理)标准与艺术标准相结合、“文质彬彬”;量的界定曰“理想主义”、“完美主义”,要求对艺术要素之每一端均“尽”其潜能。
消极言之,则曰: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注]《论语·八佾》,第91页。
此则可概括为“A而不B”。中国古代悲剧当为“哀而不伤”之典范,因其悲剧因素未发挥到极致,亦可谓之“正剧”。
无论是积极的描述形式“A而B”,还是消极的描述形式“A而不B”,都体现了对音乐的中和态度,要求音乐作品在处理要素关系时,能体现克制与平和,体现辩证智慧。这是先秦音乐思想最重要观念之一。哲学层面描述之曰中庸之道或曰辩证法;审美观念描述之,则为“和”。“和”的思想在战国时期得到集中、突出的发挥,超越了音乐界,成为具普遍性价值的世界观、人生观,并在后世得到始终如一的继承。
上述两种分析法合起来可表述为艺术辩证法,重视音乐作品中不同要素间之合作关系,不欲让任何一种因素走向极端,此即当时之主导音乐观念——“和”。 始之于音乐的“和”观念在战国时期走出音乐,走向饮食、政治、医学等领域,成为一种普遍性价值观念与思维形式,持久、普遍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此种艺术辩证法持久、普遍地影响了后世各门类艺术批评。
其三,正反对比法。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注]《论语·卫灵公》,第198页。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注]《论语·雍也》,第115页。
文质相对、《韶》与“郑声”相对,各自的特征更为明显,音乐批评之效率便更高。无论是正面经典之推荐,还是反面教员之确定,都标志着音乐艺术的自觉与成熟,这种正反对比的音乐批评给时人与后人以极深刻印象,极大地影响了全社会的音乐创造与欣赏趣味。
孔子所应用的上述三种音乐批评方法俨然已形成一小小的音乐批评模式系统,并为后世所仿效,此可视为孔子对先秦音乐思想的重要贡献。孔子在此进行的音乐批评,诸如典型性作品之推出,对音乐内在要素结构关系之深入分析,均体现了先秦音乐所达到的自觉、成熟水平,乃先秦音乐艺术自觉、审美自觉的重要表现。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注]《论语·卫灵公》,第198页。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注]《论语·微子》,第220页。
孔子以周礼为依据,建立起正统的音乐评判标准。从孔子乐论可以看出,最早的批评是社会学批评,最早的批评观念乃是雅郑,或曰美善。然而,春秋晚期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周天子政治势力衰微,各诸侯国势力崛起,诸侯国君们往往不用心遵守周初制定下来的各项礼仪制度,张扬自肆,随意使用礼乐,原来的制度文化受到极大挑战。“郑声”的出现便是时代变迁的一个极好信号。原来,音乐属于周礼系统,不能随意使用,有场合与等级的严格规定。现在,以声色展示为核心意趣的民间音乐迅速崛起,满足了各诸侯国君们享乐主义的审美趣味,于是,周礼系统之外纯审美的民间新乐——“郑声”大行其道,大有对原来为周礼服务的雅乐、正乐取而代之之势。
立足于今天,我们对“郑声”可有新的理解:从审美自身的发展看,这是值得肯定的新事物,是史前审美意识萌芽后新一轮的审美自觉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华古典艺术审美的发展。它其实是时代之新声;“郑声”不止出现了,而且足以形成对“雅乐”的冲击,这说明春秋晚期,先秦音乐史已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取得了新发展。然而,孔子由于整体上将乐视为礼之具,没有独立的审美音乐观,故而他才坚决反对“郑声”或“新声”这种音乐界的新事物,将它们与“佞人”相提并论。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注]《论语·八佾》,第93页。
孔子在音乐评论中提出的美善兼济原则可谓中国古典艺术评论的普遍性规范,为后代儒家所继承。在这里,一方面,美善两立暗示着审美意识之自觉,另一方面,善又乃音乐批评、艺术批评二分之一、不可或缺的重要标准,表明古典艺术观念中,政治、伦理评价对审美评价的笼罩与牵制,乃是对文艺的功利主义态度。
综上所述,在孔子关于音乐的讨论中,他所建构的三种音乐批评模式已然构成一个较完善的音乐评价系统。其中,符合周礼是第一位的,培养理想的道德人格是第二位的,审美则居于其末。应当说,孔子于此三方面均有自觉表现。孔子以周礼为依据,已建立起正统的音乐评判标准。孔子论乐显示:最早的批评是社会学批评,最早的批评观念乃是雅郑,或曰美善。不能说孔子是纯粹的功利主义。他对诗乐六艺的感受是相当内在的,但他确实同时又是音乐功利主义的自觉维护者,有真诚的功利主义要求。这些在今人看来是很矛盾的东西,对他来说并不成为矛盾。关键在于:他已在内心将它们融为一体,达到了审美需要与政治、伦理功利主义诸求的内在融合。而这,正是我们所达不到的,也许错并不在孔子。
四、从音乐批评到音乐哲学
孔子的音乐评论外在地奠定了礼、乐并举之框架,内在地确立了以音乐作品内在诸要素对立统一、以和为美的基本原则,成为儒家音乐理论的坚实基础。然而,这样的音乐思想何以可能?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墉》、《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乎其周之旧也。”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枫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引自杜预等注:《春秋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00页。
这是春秋时吴公子季札访鲁观乐时所发表的音乐评论,发生于孔子7岁时。如果说《论语》中孔子对音乐的评点要言不繁,季札的乐评则可谓浩大而繁盛。然而,这仅仅是外在形态上的差别,若论其内在精神,则我们不难看出二人的高度一致,因此我们可将季札的这段极有名的音乐评论视为春秋时期孔子音乐思想的时代基础、观念原型,大概不会有错。
然而,季札音乐评论的历史信息还不止于此——孔子音乐思想之基础与先声。如果说孔子在《论语》中明确建立起来的礼乐并举思想作为后人理解音乐何以可能、音乐竟为何物之基本原则并无大错,那么这种原则上正确的东西一旦被一丝不苟地落实在对具体音乐作品的评论上,有时便难免会弄出笑话。
对于季札的这段著名乐评,后人似乎可以从中体会出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一方面,我们不得不佩服季札的音乐素养,他对鲁国乐工们为他呈现的各诸侯国代表性音乐作品的独特音乐风格极为敏感,有极好的判断力,故而能即时下明确断语。这种判断应当是精准的,因而得到时人的广泛认可,否则不可能被忠实记录,并被后人视为乐评之典范;然而另一方面,季札的如此点评似乎又难免让后人感到一片茫然:他对各国音乐作品的风格与其母国历史命运、政治治理状态间做出一种极为严格的对称性描述,以至于后人实在搞不清季札所作的到底是音乐批评,还是政治评论。我们不禁生如此之疑:这两者间难道真的会呈现出如此严密的对称性关系吗?若此,则一国之政治治理,以及作为人类观念文化产品的音乐似乎也太简单了。
这也不能单怪季札,在音乐与政治治理之间建立起一种类神话的信仰,某种意义上说亦乃当时之时代精神:
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注]《左传》襄公十八年,第367页。
晋平公觞之于施夷之台。酒酣,灵公起,公曰:“有新声,愿请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师涓,令坐师旷之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师旷曰:“此师延之所作,与纣为靡靡之也。及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至于濮水而自投。故闻此声者,必于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其国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师涓鼓动究之。平公问师旷曰:“此所谓何声也?”师旷曰:“此所谓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师旷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闻乎?”师旷曰:“不可。古之听清徵者,皆有德义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听。”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愿试听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道南方来,集于郎门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音中宫商之声,声闻于天。平公大说,坐者皆喜。平公提觞而起为师旷寿,反坐而问曰:“音莫悲于清徵乎?”师旷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闻乎?”师旷曰:“不可。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鎋,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今吾君德薄,不足听之。听之,将恐有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听之。”师旷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注]《韩非子·十过》,引自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诸子集成》(5),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5页。
其时,礼乐关系,或者说音乐与其所处时代、环境的关系,被当时人用一个内涵极广的概念——“风”来标识。此“风”既可以是音乐作品之审美风格,亦可以指称自然之风,以及地域、时代之风,比如风俗、国运等等。
起于春秋晚期,以季札和孔子为代表的自觉音乐批评到战国至秦汉间,被提升为关于音乐之一般的音乐理论,一种关于音乐何以可能的音乐哲学。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注]《礼记·乐记》,第712页。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注]《礼记·乐记》,第714页。
古代中国的音乐哲学自此而成熟。它首先是音乐缘起论,由音乐而推之于人心,更由人心而推之于外物,建立起音乐——人心——世界的逐层外推式音乐发生动力框架。这个“物”既可以是社会的,比如时代国运、地域风格,也可以是自然的,比如自然风物、宇宙秩序。因此,比之于单从人心或人类文化论音乐,视野要宏阔、深远得多。
它又是音乐本体论。音乐如何可能?本质上说,音乐需要对自然音(“声”)做两个方面的处理——变化(“变”)与秩序(“方”)之后而转化为一种人工化之乐音(“音”)。所谓“文”便是自然音之人工化,具体地,既要有变化,又要有秩序,方可成为具备审美价值,可以悦耳,进而深入人心之乐音,此之谓音乐。
关于音乐与外物,即具体的国家政治治理状态之正相关关系,即孔子的礼乐并举理念,《乐记》作了很到位的概括: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注]《礼记·乐记》,第714页。
既然音乐的背后是人心,进而是社会治理与民情民风状态,那么对此理念——音乐与人心,进而国政之严格对应性的逆向应用,便是自觉、积极地通过音乐以治理人心,改进民风,此之谓“移风易俗”:
乐也者,圣人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注]《礼记·乐记》,第730页。
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注]《礼记·乐记》,第735页。
《乐记》作者实可谓孔子的深度知音,如果说孔子在春秋晚期面对的是“礼崩乐坏”的消极局面,《乐记》作者则以更积极的心态从正面建构了从音乐到人心再到社会治理的音乐哲学,正面提出通过音乐以培育人心、改进民风的音乐教育理念,这是对孔子礼乐并举思想的创造性发挥。然而,《乐记》的贡献尚不止于此。
在孔子的乐论中,音乐的指涉范围仅及于人类社会,或礼制,或德性。《乐记》所提出的“物”概念,从逻辑上说扩大了音乐阐释与理解之可能性视域,因为此“物”既可以在人类文化范围之内,比如礼制或国家治理状态,也可以在人类社会之外,比如自然之风物、宇宙运动法则。在此方面,《乐记》是高度自觉的。
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注]《礼记·乐记》,第735页。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注]《礼记·乐记》,第721-723页。
《乐记》实可谓创造性继承与创造性阐释之典范。一方面,它忠实地继承了孔子礼乐并举思想,总是从礼制,亦即社会治理的角度理解音乐的文化位置及其功能;另一方面,对于发端于季札和孔子的关于音乐的“和”的理念,《乐记》将它创造性地拓展到人类文化范围之外,作了一种自然哲学的阐释,首先将它理解为天地之和、宇宙秩序,然后才理解为人伦之和、人心之和,并且它将前者,亦即作为天地秩序的“和”理解为社会秩序井然、人心和顺之形而上哲学依据。此可理解为其时之时代精神——战国自然哲学宇宙模式形成在音乐思想领域中的具体体现与独特成果。
至此,中国古代音乐哲学视野可谓达到极致,此后再无突破,某种意义上说甚至亦无此必要,因为《乐记》成功地为中国人理解音乐这一独特的人类观念文化活动及其成果,提供一套从逻辑上说至广至深的理论模型:以音乐为圆心,先及于人心,再及于社会,最终及于天地之和,即宇宙秩序。一种为人心,为社会,进而又为天地间宇宙秩序而存在的音乐,还有比这更复杂、完善,更为宏阔、深邃的音乐吗?肯定没有,也无必要。
从季札和孔子的音乐批评,即针对具体音乐作品风格、成败,以及功能的音乐点评,到《乐记》所建构的音乐哲学模型,中国古代音乐实现了宏观上的理论自觉。如果说季札与孔子的音乐批评代表了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的质朴形态,那么《乐记》所建构的音乐哲学则已极精纯。它所提出的音乐阐释和音乐理论视野,代表了中国人音乐哲学所能达到和应当达到的高度,可谓笼罩万代,惠泽无尽。
现在我们需要反思:今人如何理解音乐?纯音声之美,抑或一时某种情绪之表达?若此,则比之于《乐记》所已然开拓、呈现者,我们在音乐视野、境界方面已大踏步地倒退,着实愧对先贤。诚然,抒情或心理能量的渲泻诚乃音乐之基本功能。然而,只有将音声之和理解为人类对天地秩序之特殊呈现、表达时,我们才不会通过音乐自炫其文化成就,进而在最深层文化心理上原始要终,追求用琴弦探测天地秩序,以琴心、人心、世风与自然之四时节律共振、共鸣,以此超越自我、融入天地,最终因此而自安,这是以音乐谋求终极关怀,斯为乐之至境。这也许正是古代琴师们往往喜将其琴箫置于云水间,以高山流水之境表达琴心琴韵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