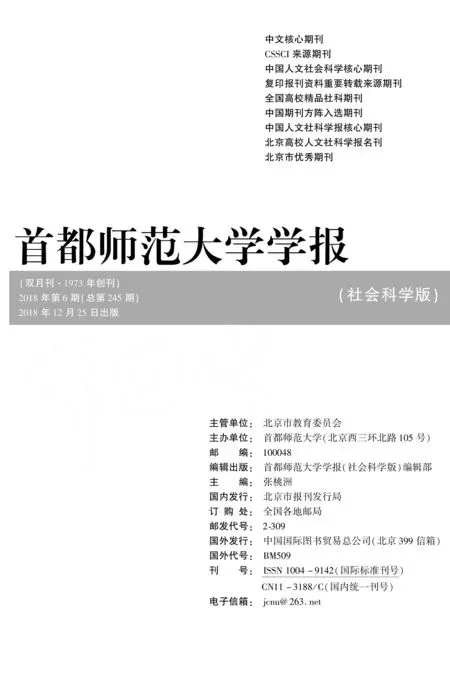中国古代感物美学的“感物兴情”论
李 健
感物兴情作为审美创造和审美体验的一种类型,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感物美学的感发传统。这一传统的典范意义与理论价值十分重大,它是审美创造和审美体验发生的本原之一。感物兴情首先呈现出来的是物、情的出场顺序,“感物”才能“兴情”,也就是说,物在情先,物感发了情。物何以能感发情感?按照传统的解释,人与自然一体,与万物一体,故而,万物能与人产生感应,引发情感的发生。万物之所以能够与作家、艺术家产生感应,还因为作家、艺术家本身就存在着与外物感应的生理或心理的潜质。“感物”为什么能够“兴情”?还应该从作家、艺术家本身去寻求缘由。天人合一,意谓着人与外物能产生感应,可是,在具体的创作和审美体验中情形究竟如何?还应视具体作家、艺术家的具体创作环境、创作对象而定。为什么同样一个事物能够引发作家、艺术家的情感,却引发不了寻常百姓的情感?同样一个事物能够引发这一作家、艺术家的情感,而与另一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不发生任何关联?同样一个事物,在此时此地引发了作家、艺术家,而时过境迁就失去了引发的功能?这都是我们在感物兴情的题旨下应该深入探究的。
物的形态多种多样,既包括自然物色,又包括社会历史、现实及人。物林林总总,纷纭万状,罗列不尽。在中国古代,理论家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首先花工夫讨论的是自然物色,尔后,才逐渐扩展到社会历史、现实和人。他们早早就认识到,不管是自然物色之物还是社会历史、现实之物乃至人(人也是物,一种特殊之物),必须与情相连接才能显示出它的存在意义和审美价值。
一、自然物色对作家、艺术家的感发
自然物色,就是自然界呈现出来的种种景色。自然界的现象纷纭万状,不同季节、不同地域都有不同的物色表现。自然物色使整个世界丰富多彩。刘勰把自然物色的表现说成是“春秋代序,阴阳惨舒”(《文心雕龙·物色》)。由于自然物色本身是有灵性的,并非死寂的,始终关联着人的生活,故而,能够与人产生感应,引发作家、艺术家的情感冲动。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创作观念中,自然物色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主动的角色,它们本身的灵性和美常常能够引发人的审美欲望,引发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欲望。许多自然物色被写进文学艺术作品中,成为具有审美意义的形象。这些形象不一定都是寄托情感的符号(那是“托物寓情”要说的话题),可能是纯粹的自然审美,即发现自然本身的美,赞美自然本身的美。中国古典诗词与绘画中所表现的鸟、兽、虫、鱼与草、木、山、水等意象,在很多情形下,只是引发情感的对象,并不一定是思想的寄托。作为引发情感的对象,鸟、兽、虫、鱼与草、木、山、水等的表现不仅是主动的,而且是充满情意的。它们仿佛百变精灵,左右着作家、艺术家,似乎它们原本就有人一样的性格,人一样的情感、意志。这就是自然物色与人的感应。在感应的过程中,人刹那间回应了自然物色,理解了自然物色,形成一幅幅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妙图景。因此,在古人的眼里,自然物色向来是鲜活的、生动的、富有灵性的,唯其鲜活、生动而富有灵性,人才能产生如此温馨的体验:“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注]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7页。(《世说新语·言语》)
在《文心雕龙》中,刘勰深情地描绘了文学创作过程中自然物色与作家的心灵感应:
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注]王利器校笺:《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8页。(《文心雕龙·物色》)
在刘勰眼里,不仅有生命的动物、植物有灵性,哪怕是没有生命的自然之物也有灵性。就自然界的物色来说,每一种都有它的特征,这些特征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程度地召唤作家,感应作家,使之产生创作的冲动。刘勰紧紧抓住自然物色的特征与人的心灵感应关系,不仅肯定了自然物色是创造行为发生的诱因,而且,还试图探讨自然物色的特征与作家的情感关联。这就把握了文学创作的根本,为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提供了生理与心理的依据。
然而,我们还是不禁要问:自然物色究竟是如何与作家、艺术家产生感应的?又是如何引发作家、艺术家情感发生的?
自然物色之所以能够与作家、艺术家产生感应,是因为自然的灵性与人的灵性存在着直觉契合的关系。这是人长期与自然为伍,与自然交流,最终达成的一种默契。这种关系决定了作家、艺术家与自然的碰撞都是刹那间发生的,根本不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因此,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任何一个感物的过程都是短暂的、瞬间的。古代很多理论家认为,人与自然物色身上都蕴含着一种特别的“气”。这种“气”是天地自然赖以生存的根本。它真力弥满,生机勃勃,不仅是自然的生命之源,而且,也是人类的生命之源和审美之源。正是这种“气”,促成了作家、艺术家与自然物色的感应。故而,钟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诗品·序》)刘勰特别考察了春、夏、秋、冬四季与作家的感应。在他看来,不同季节的不同物色皆能对应于作家的心灵,使作家产生生理乃至情感的回应。春天,“悦豫之情畅”;夏天,“郁陶之心凝”;秋天,“阴沉之志远”;冬天,“矜肃之虑深”。春、夏、秋、冬对应于人的不同情感,这是刘勰对自然物色与文学创作关系所作出的独特概括,但却不是他的发明。因为早在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就已经从经学、谶纬学、哲学等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论证,得出了相关经验性的认识。《诗经》《楚辞》等文学经典从文学创作实践的角度涉及过这样的话题,朦胧认识到自然物色对人情感的感发作用。《诗经》有许多描写季节物色的诗句,然而,这些诗句并非单纯写景,其实都对应于情感,言说的都是自然物色对人的情感的引发。如《卫风·氓》,通过桑叶的变化描写季节的变化,以此展示人的情感变化。“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写夏天。夏天桑叶茂盛,人与之产生了感应,引发强烈的恩爱之情。因此,桑之“沃若”就成为恩爱的隐喻。“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写秋天。秋天桑叶枯黄,引发了人的怨愤情感,同时,人也与之产生了感应,因此,桑之“黄”、“陨”就成为情感破裂的隐喻。《楚辞》多抒写悲愤、思念、忧愁,故而,秋天的意象出现较多。《九歌·湘夫人》有“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章·抽思》有“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九辩》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等等,都是将季节物色与人情感对应的经典之作。探究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大都是物在先,情在后。先是自然物色引发了诗人的情感,然后才有诗人的创作。这些创作的实践对文学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理论有深刻的启发,许多著作试图从理论上解决自然物色对人情感的引发及感应问题,最终在哲学、美学乃至生理学等方面取得了突破。《黄帝内经》对人的血气运行与季节、气候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讨论,从生理和医学的角度界定了人能够与自然万物产生感应的缘由。《淮南鸿烈》和董仲舒延续这一话题,尤其是董仲舒,他明确把四季与人的情感表现对应起来,以喜、乐、怒、哀对应于春、夏、秋、冬,以此阐发季节与人的情感的感应关系。这些,都是文学艺术创作经验的传达和美学观念的表达,对文学艺术创作的意义不言而喻。
自然物色之所以能够引发作家、艺术家的情感,还因为自然物色的特征与作家、艺术家的个性以及此时此地的思想情感达成契合,凝聚为鲜活的审美情趣。既然自然物色都不是死寂的,是富有灵性的,那么,这些自然物色的灵性只有在与人的感应之中方能实现其价值。自然物色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千差万别。其中,有气象宏大的(如高山、大川、落日、雷电、风雨、荒漠等等),有声息细微的(如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等),有有形的(如菊花、蝴蝶、彩虹、云霞等),有无形的(如鸟鸣、气味、微风等),有静止的,有运动的,等等。这些不同自然物色的特征正是作家、艺术家感应的契机。再就作家、艺术家来说,每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这些个性都会作用于创作。我们可以按照古人的分法将之分为两类,一为阳刚,一为阴柔。阳刚者,言语、行为豪放;阴柔者,言语、行为温婉。无论什么个性的作家、艺术家,都能够在自然之中找到与其对应的物色,以促成人与物的心灵感应,完成审美创造和审美体验的过程。李白的个性特征是阳刚的、狂放的,与他这种个性对应的必定是气象宏大的自然物色。因此,在他的诗歌中,我们看到的是黄河、大海、长风、高山。王维的个性则是阴柔的、沉静的,这种阴柔、沉静的个性特征只能对应于细微、宁静的自然物色。因此,在他的诗歌中,我们看到的是松树、泉水、芙蓉、桂花。无论是李白的宏大还是王维的细微,其审美创造和审美体验的形成都缘于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物色对情感的感发,二是个性对自然物色的选择。这两方面相承相应。自然物色的感发在先,个性的选择在后。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物在情先是文学艺术创造和审美体验过程中的真实存在,这种真实存在业已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蜕变为一种固定的类型。也就是说,这种创造和体验的类型是无法改变的。自然物色对作家、艺术家情感的感发,自然物色的特征与作家、艺术家的个性及思想情感的契合,产生了奇特的审美效应。它不仅完成了具有原创性的文学艺术创造,展示了作家、艺术家的独特性,而且,还彰显了自然物色的价值,完成了自然物色本身由死寂到生动、由本色到华丽的伟大转变。
既然自然物色能够引发作家、艺术家的情感,既然自然物色的特征能够与作家、艺术家的个性气质及思想情感产生契合,这就说明,自然物色对创作与审美的引发并不完全是偶然的事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先从自然物色的特征来说,每一种自然物色都有其固定的特征,由这些固定的特征所衍生的美也向人而生,供具有相同或相近个性气质的作家、艺术家选择。再从作家、艺术家个体来说,个性气质是相对稳固的,这种稳固的个性气质导致他们对自然物色的态度也相对稳固。同时,个性气质决定他们对自然物色的选择倾向相对明确,只能选择那些适合自己个性气质的自然物色。对一个具体的作家、艺术家来说,自然物色不可能都与之产生感应,不可能都引发他(她)的创作冲动。作家、艺术家与自然物色感应的必然性体现在:由于气质与个性不同,导致所感应的自然物色也会截然不同;每人都会自觉地寻求与自己个性气质相契合的自然物色,只有这种(类)自然物色才能引发创作冲动。因此,在文学艺术发展史上,往往出现这种景观:一个作家、艺术家可能一生专注于某几种(类)物色,对这些物色的描绘代表了他(她)的创作成就,是他(她)的艺术特色的标志。如,唐代画家曹霸善画马,一生画了很多马,他的艺术独创性和艺术成就也就体现在对作为自然存在的马的传神塑造上。元代画家王蒙长期生活在浙东,曾一度弃官隐居于黄鹤山,正是这些山引发了他的创作欲望。在他的眼里,山美妙、灵秀、温馨,成为他生命的组成部分。因此,他笔下所表现的山,元气磅礴,纵横离奇;山山灵异,充满动感。这就是因为,这些山与他的思想情感产生了强烈的感应。他无法摆脱这些自然物色的深情邀约,只好借助画笔,与山对话。文学创作也是一样。陶渊明喜爱田园,他的诗歌大多受田园物色的召唤;田园的安逸、宁静与他温和、恬静的情感气质与个性特征产生契合,形成心灵感应。因此,他笔下展示的田园都是和谐、安详、宁静的。纳兰性德出生于显贵之家,性格忧郁。他的生活环境和个性气质导致他笔下的自然物色多与京城、宫殿有关,与多愁善感相联。因此,作家、艺术家与自然物色感应的必然性就体现在:每人都会依据自己的个性气质及审美喜好去选择特征相同或相近的自然物色。自然物色引发了他们的情感,自然物色是他们审美创造和审美体验的感发之源。
必然性虽然不能等同规律性,但是,与规律性有关。自然物色对作家、艺术家情感的引发有必然性,存在着一定的规律。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自然物色对情感的引发在根本上又是无规律的。这种无规律就体现在:就一个具体的作家、艺术家来说,随着环境的不同,自然物色对他(她)的感发会有很大的不同。而就所有的创作活动来说,处于同一环境中的作家、艺术家,因其个性的差异,对自然物色的感应也不可能一样;至于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的作家、艺术家,由于自然物色各异,个性有差异,感发所造成的创作差异更多,也更复杂。因此,自然物色对作家、艺术家情感的感发是无规律的。社会现实决定了作家、艺术家的生活环境不可能一成不变,既然环境发生了变化,自然物色必然会有变化。新环境下的新的自然物色同样会感发作家、艺术家的情感,使之产生创作的冲动。这在宋代词人柳永的创作中就有比较鲜明的表现。柳永热爱生活,也热爱自然。长期的羁旅行役,使他的活动区域非常大,亲历的自然物色也非常多。他在汴梁生活过很长时间,在余杭生活一段时间,还曾羁旅淮上之颍州、江南之苏州等地,时间跨度几十年,空间遍布大江南北。就他活动的区域来说,气候差异较大,自然物色各别,因而,展现的情感不同。各地的自然物色召唤他,感发他,与他彼时的情感产生感应。因此,他笔下的自然物色不仅丰富多样,而且鲜活生动,既借助它们表达悲喜,也抒发忧乐。如他写杭州西湖美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望海潮》)。表达的是兴奋之情。他写楚淮风光:“长川波潋滟,楚乡淮岸迢递,一云烟汀雨过,芳草青如染。”(《安公子》)抒发的是羁旅苦辛。他描绘过姑苏的景致:“夫差旧国,香径没,徒有荒丘”,“江山如画,云涛烟浪,翻输范蠡扁舟”,“斜阳暮草茫茫,尽成万古遗愁”(《双声子》),充满怀旧之哀愁。无论欣喜还是哀愁,都是自然物色引发的结果。即使表达哀愁,也掩饰不了他对自然美景的留恋。自然物色成为他精神对话有生命含蕴的美丽的意象。
由此可见,自然物色对作家、艺术家的引发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不可能在一个预设的理论框架下认识它,探索它,给它定性。只有充分认识到它的复杂性,才有可能准确评估它的价值。
二、社会现实对作家、艺术家的感发
社会现实是指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人、物、事,这其中,人是有生命的,物与事是无生命的、死寂的,由于他(它)们与作家、艺术家的生活息息相关,自然而然地成为感发之源。社会现实生活能够引发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还因为他们本来就处于社会生活的情境之中,能够深深体验并理解其中的悲与欢、忧和乐,切实与之产生感应。这一点,先秦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曾经这样记载:“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注]杨坚点校:《吕氏春秋·淮南子》,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9页。表面上,这是说乐教的,强调音乐能够真实展现一个时代的生活和风俗,能够真实表现人的志向、理想与品德。倘若我们剥开其教化的外壳,从创作的角度逆推,就会发现其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感物内容。“声”是声音,在这里指音乐,是音乐家受情感引发创作出来的作品。而“风”、“志”、“德”就是引发之源。“风”是风俗,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社会现实生活。“志”是志向、理想、抱负,这里不是针对个体,而是针对整个社会,是指整个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德”是道德,同样,这个“德”也不是针对个体,而是针对社会,是整个社会受现实(风)的影响所表现出来的道德状况。这些,说到底都是社会现实生活,它能够引发作家、艺术家的情感,使之产生创作的行为。
然而,社会现实是异常复杂的,不同性质的社会现实对作家、艺术家的感发不一样,从而,导致创作与审美千差万别。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有和平、战争、灾祸等社会现象,有亲情、爱情、友情等社会伦常,有生离、死别、聚散等社会遭遇,这些,都能进入作家、艺术家的视野,成为文学艺术的表现对象。综观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无论表现什么主题,也不管这一主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存在着何等差异,而借以展示的大都是类似的社会现实。譬如,通过战争、灾祸来表现政治与人性;通过亲情、友情来展示道德与人伦。因此,钟嵘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霜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注]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3页。(《诗品序》)
中国古代文学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表现极其丰富。由于战争、灾祸所带来的惨烈令人刻骨铭心,极易激发人们的情感,一直受文学家的青睐,因此,描写这类题材的作品很多,艺术成就也很高。《诗经》、汉乐府、建安文学、唐诗、宋词以及明清小说,有许多描写战争、灾祸的经典。在《诗经》中,描写战争最为经典的《小雅·采薇》,其感物兴情的创作意蕴极其鲜明。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常年在外征战的士兵对故乡的思念,对战争(玁狁)的憎恶。战争感发着诗人的心灵,使他创作出这首流传千古的不朽诗篇。对于这首诗,古代儒家有许多附会,《毛传》不可能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只能从政治与历史的角度解释这首诗。在我们看来,《采薇》是一个士兵的“离群”之思。由于玁狁的侵犯,士兵们迫不得已去征战。战场上,尽管战事非常惨烈,也难以掩饰士兵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离乡时,恋恋不舍,杨柳依依;回归时,归心似箭,雨雪霏霏。诗人就是士兵,士兵就是诗人。战争引发了诗人的情感,诗人与此时此地的境遇产生了感应。没有战争,就没有这首诗。
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制造了许多人间灾难,情感刺激之强烈,是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件无法代替的。战争造就了很多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也成就了许多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已经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是创作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古代的理论家非常看重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给作家、艺术家带来的动力作用及成功因素,认为它们对作家、艺术家的影响之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与此同时,他们还深入揭示了这种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左右作家、艺术家创作的心理原因乃是众多人间不平带来的刺激。孔子曾经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屈原也说过:“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惜诵》)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陈述了古代众多的实例:“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注]张少康、卢永璘编选:《先秦两汉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8页。这里的关键词是:发愤、怨。发愤、怨的潜台词是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给人带来的悲哀、愤怒的情感驱动。作家、诗人何以要发愤?何以要怨?就是因为世道不平,现实混乱,使得他们不得不把自己内心的冤屈发泄出来。这就是感物兴情。
动荡、混乱的现实对文学创作的推动,最具代表性的是建安时期。这一时期,诸侯割据,国家分崩离析,战乱频繁。以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等为代表的作家、诗人横空出世,他们真实而艺术地描绘了这个时代,挟带悲慨之风,形成了“建安风骨”。《文心雕龙·时序》评建安文学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注]王利器校笺:《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3页。所谓“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就是指动荡的、混乱的社会现实。建安作家身处这种社会现实,身心深深地被现实刺痛,不得不把内心的悲怨表达出来。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现出一幅幅悲慨的画面。例如,曹操的《蒿里行》、曹植的《送应氏》、王粲的《杂诗》(之一)等描绘的场景,令人刻骨铭心。“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是对战乱的悲愤,不仅充满对生民的同情,而且还昭示创作的感发之源。建安文学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就是因为动荡的、混乱的社会现实生活的感发,与作家的情感实现了完美的契合。
传统的文学理论、美学除了强调诗可以怨、发愤著书之外,还主张穷而后工。这虽然与可以怨、发愤著书有意义上的关联,但是,也有其独特的内涵。“穷”是指作家、艺术家所遭遇的生活磨难。这种磨难不一定都是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造成的,也可能是天灾人祸,对作家、艺术家的感发依然强烈。
韩愈说:
从事有示愈以《荆谭酬和诗》者,愈既受以卒业,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注]周祖譔编选:《隋唐五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荆潭唱和诗序》)
欧阳修亦云: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注]陶英秋编选:《宋金元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梅圣俞诗集序》)
文学成就的高低取决于作家生活磨难的程度。这看似绝对化的言辞背后蕴含着许多意义。创作行为本身是一个心理驱动的过程,心理驱动力越大,对情感的引发就越强烈,给人带来的审美震撼就越大。作家的生活磨难就是一种心理的驱动力,其对创作的感发是无法估量的。
然而,社会现实并非只有动荡与战乱,也有和平与安宁。同样,人的情感遭际也不仅仅有悲伤与忧愁,还有欢乐与喜悦。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社会现实与情感的表现都是多元的,描写欢乐与喜悦的文学作品也很多。其中,较为典型的是《诗经》中的大小雅。这从古人对雅的意义的阐释中可以看出。朱熹说:“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各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会朝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注]朱熹注:《诗集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9页。方玉润也说:“大略小雅多燕飨赠答,感事述怀之作,大雅多受釐陈戒,天人奥蕴之旨。”[注]方玉润:《诗经原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7页。虽然二人都说到雅的教化问题,但是,也非常明确地指出了雅表现的多是燕飨、会朝的内容,也就是说,其中有不少诗歌描写的是聚会、宴饮的欢乐场景。同时,这些诗歌又都是“感事述怀”的结果,即是受燕飨、会朝等社会现实的感发而创作的。例如《小雅·鹿鸣》,先儒在解释这首诗时说:“《鹿鸣》,宴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也。”[注]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唐宋注疏十三经》(一),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11页。这一释义,说明了这首诗表现的内容是描写欢乐的典范之作。它的创作显然是诗人受嘉宾到来时热烈欢迎场面的感发。尊贵客人的到来,迎接的场面自然马虎不得。主人兴师动众,鼓瑟吹笙,举行了最高的欢迎礼仪,以示对客人的尊重。欢迎客人自然少不了美酒,主客之间觥筹交错,情真意切。诗人就是受这种生活场景的感发,写出了如此优雅而昂扬的欢欣之词。从诗歌表达的情意来看,这种感发仍是自然的、自由的。
由此看来,对欢乐的现实生活的描写也出自真诚的感物。作家、艺术家受这种欢乐的感发,同样能创作出不朽的作品。韩愈所说的“和平之音淡薄”、“欢愉之辞难工”,强调艰苦的生活、不幸的遭遇给人心灵带来的震撼,给创作带来的动力,并非说,对和平、欢愉的现实生活的描写一定出不了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因此,这种言论只适用于特定的创作环境,不能成为永恒的真理。
人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主体,本身就是社会现实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人是世间万物最为灵明者,因此,人也是感发作家、艺术家的重要源泉,所有的文学艺术都离不开人,很多优秀的作品把人以及人的身体作为表现的对象。《诗经》有一首《卫风·硕人》演绎女性的身体之美,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描绘“东家之子”之美,皆生动传神。钟嵘对身体美也非常重视,特意将此列为感物内容的一项。《诗品序》云:“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就是强调身体美对文学创作的感发。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爱美而不沉溺于美色,往往能陶冶人的情操,使人同样能获得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的升华。
由此可见,社会现实与感物的关系非常微妙。社会现实中的所有事物由于与作家、艺术家的生活密切关联,都能够成为作家、艺术家的感发之源,进而,成为文学艺术表现的对象。这足以说明,感物兴情包蕴着极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它在文学艺术创作中所起的作用特别巨大,绝然不可忽视。
三、物所主导的物、情律动
感物兴情是物在情先,物感发了作家、艺术家的情感,使之产生创作的行为。整个感物兴情的过程,物都起着主导作用,物决定着作家、艺术家情感的发展方向,规定着创作方向和审美方向。然而,由于物本身非常复杂,对情感的感发也非常复杂,我们无法在一个固定的模式下描述它。由于物大体上可分为自然之物和社会现实两个方面,我们只能结合古人的创作,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探讨由物所主导的物、情律动。
首先,物作为自然之物,之所以能够引发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是因为其鲜活、明丽的生命特征。这种特征能够召唤起作家、艺术家,使之产生创作冲动。由于情感是由自然物色引发的,自然物色不仅充当着媒介,而且,也极有可能成为文学艺术作品的形象、意象,进而成为作家、艺术家情感、思想的隐喻或象征。
自然物色是天地的造化,人也是天地的造化。人生活在自然之中,必然会与自然发生关联。有时,人与自然会产生对抗,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和平共处的。人们叹赏自然物色的美妙变化,敬畏大自然的威严,是因为它给人带来了惊喜,带来了沉思,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诗意的生存空间。自然中有花开花落、风雨雷电、朝霞夕阳、鸟鸣兽吼,仿佛这些自然物色都向人而生,都能与人的情感形成某种关联。因此,刘勰才会说:“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文心雕龙·物色》)一片树叶,一声虫鸣,都会引发人内心的感动,还有什么自然物色不会触动人呢?同时,“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还昭示自然物色的生命特征。正因为自然物色是鲜活、明丽的,才充满生机,才能引发人的情感。刘勰的物色观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理论是吻合的。中国传统哲学向来把自然物色看作是有灵性的,认为它们有情、有性,能表达悲喜,但这并不等同于人类初期的万物有情论,而是人类认识成熟阶段的“天人合一”论。万物有情蕴含着对自然的敬畏,“天人合一”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谐。敬畏是因为认识的不自由,和谐则是认识的自由——那是把握了自然特征或规律的审美状态。既然天人合一了,自然物色就能够与人的心灵感应了。当自然物色鲜活、明丽的生命特征进入作家、艺术家的视野并深深触动他们的情感之时,也就是审美发生之时。在这种情形下,审美体验产生了,审美创造也产生了。与此同时,自然物色的自然属性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然属性开始人化,带动了整个自然物色的人化。自然物色的人化是自然的审美化,它不是对自然物色的雕凿与加工,而是对自然物色的诗意迎合。“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贺新郎》),这就是自然物色的人化。作为自然物色的青山完全成为一个诗意的对象。这种诗意是青山本身具有的,也是作家所赋予的。然而,青山妩媚不是作家情感的主动移入,因而,不是“移情”,而是青山与人的相互感应,是天人合一。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物色不仅仅是自然物色本身,而且还成为人的组成部分,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我们借助于古典诗歌来考察自然物色主导下的物、情律动。在古典诗歌中,自然物色主导下的物、情律动可以分为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自然物色本身虽美,但是,仅是一种自然美,没有特殊的意义,在诗中只不过是充当诗人抒发美的情感的媒介。梁代诗人何逊的《晓发》就是这样一首诗。诗云:“早霞丽初日,清风消薄雾。水底见行云,天边看远树。且望沿溯剧,暂有江山趣。疾兔聊复起,爽地岂能赋。”这首诗是典型的感物兴情。诗人受自然物色(“江山趣”)的感发,将自然物色之美尽情展示在诗中。早晨,即将出发的诗人霎时被眼前的美景吸引。诗中描述了很多自然物色,早霞、初日、清风、薄雾、流水、行云、远树,在诗人的眼里,它们都充满生命的情思。在朝霞的映衬之下,初生的太阳非常明丽;清风吹散了天空中薄薄的轻雾;水清澈无比,倒映着天上流动的云彩;在薄雾之中,遥望天边,依稀能够看到远处婆娑的树影;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是那么行色匆匆!如画的美景,完全感染了诗人。诗人发自内心地赞美它。从诗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早霞像一个艺术家,它使刚刚升起的太阳更美;清风是一个清洁工,它能消除空气中的任何不洁与污浊;平静的水面像一个大荧屏,其中上演着天空与云彩的故事。在这里,没有朋友、亲人的送别、挽留,没有依依不舍的人情世故,只有这些无言的初日、早霞、清风、白云。然而,这些自然物色却轮番展示着自己的美,吸引诗人,召唤着诗人,撩拨着诗人的情感。诗人对这些自然物色的叙述虽然平静而不动声色,但是,自然物色(“江山趣”)的生命意义和审美意义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这首诗生动地展示了物主导下的物与情的律动。物虽鲜艳、明丽,而情却不动声色。这是因为大篇幅的写景遮蔽了情的释放,而情感的欢欣处于若隐若现的状态,只要留心观察,依然清晰可见。
如果说,何逊《晓发》所展示的自然物色只是单纯的自然物色,这些自然物色本身虽美,但除了自然美之外没有特殊的意义。唐朝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所描写的自然物色就不是那么单纯了,几乎所有的物色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或隐喻的意义。这就产生了自然物色主导下物、情律动的第二种情形:自然物色本身不仅美,而且充满意味,是具有象征或隐喻意蕴的审美对象。
从源头上说,《春江花月夜》属乐府古题《清商曲·吴声歌曲》,为陈后主(叔宝)所创,为宫中女学士与朝臣相和之诗。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没有在诗意上沿袭乐府,实是自然的春、江、花、月、夜感发的结果。春天,江潮涌动,波涛万里;明月东升,江天一色;江水环绕花甸,月色下的鲜花像一颗颗闪亮的雪珠。此境此景,感发人心,不得不发抒对自然的爱恋!然而,与何逊不同的是,张若虚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自然物色的爱恋上,而是将自然物色与人在现实中体验到的情感结合在一起,使自然物色具有了独特的意义。因此,与春、江、花、月、夜对应的是人,那是美丽多情的闺中女子。正是由于人的介入,春、江、花、月、夜具有了象征的意义,春、花是年轻、美好的象征,它时间短暂,会很快消逝;月、夜是思念的象征,它情意缠绵,充满忧愁;江水是情感的载体,它不远万里输送着思念。春、江、花、月、夜都是引发情感的引线,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审美意象。这首诗所展示的物、情关系因为有了象征连接,所有的自然物色都不是单纯的,而饱含情感。这些自然物色的奇妙组合,形成了一幅美丽的情感画面。尤为奇妙的是,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的感发下本该抒写自己的思念,可是,他却写闺中女子的思念。这是中国传统的代拟手法。这种代拟手法的绝妙之处就是戏剧化,将情感设定在一个戏剧化的变化之中,让无数双眼睛观察,获取由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在描述这一戏剧性变化的过程中,诗人似乎也是一个旁观者。这一切,都缘于春、江、花、月、夜与诗人、读者的心灵感应。这种感应是自然的、自由的,唯其自然、自由,才显得真诚。因此,在这首诗中,春、江、花、月、夜是感发之源,同时,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美的意象。
诸如此类的情形在古典诗词中不胜枚举。由此,我们也深深体会到物主导下的自然物色与情感律动的审美价值。自然物色虽然是感发之源,在创作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但是,文学、艺术作品毕竟是作家、艺术家创作出来的,所有的自然物色又都处在作家、艺术家的掌控之中,任其驱使。对此,王国维有过一段精妙的言说:“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注]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5页。(《人间词话》)所谓“轻视外物”,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外物的主导作用,否定外物对创作的感发;所谓“重视外物”,也并不是把外物的作用绝对化,认为外物是绝对的主导,抹煞人的作用。在这里,王国维陈述的是创作过程中诗人调和物、情关系所呈现出来的两个方面的状况:一方面是诗人能够自由地调动自然物色、选择自然物色,使之更好地表达情感,所谓“以奴仆命风月”;另一方面是诗人在描写自然物色的过程中,将自己的身心自然而然地与自然物色融为一体,所谓“与花鸟共忧乐”。这样看来,“以奴仆命风月”与“与花鸟共忧乐”是诗人担当的两个角色。这两个角色的区别极其鲜明,一个出乎其外,一个入乎其内。实际上,这两种情形在同一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也是同时存在的。当诗人(作家、艺术家)选择自然物色时,往往“以奴仆命风月”;当诗人(作家、艺术家)沉浸在对自然物色的描绘之中时,又往往是“与花鸟共忧乐”。两者都是感物的本真状态。
感物兴情的感发模式,物主导下的物、情律动并不仅仅存在我们上面描述的两种情形,可能还有其它很多种情形,但这两种却是最根本的。自然物色可以具有象征或隐喻的意义,也可以没有象征或隐喻的意义,仅仅作为一个审美的物象而存在。然而,无论是否具有象征或隐喻的意义,自然物色必须是鲜活、明丽的生命,而这种生命特征的存在才是自然物色与情感发生关联的根本。
其次,物作为社会现实生活对作家、艺术家创作的引发,是由于其本身蕴含着典型而独特的审美意义,能够唤起人们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积累和情感回忆,感发作家、艺术家的审美体验;并且,其本身又具有一定的叙事或抒情能力,能够引发作家、艺术家的叙事或抒情的欲望。这一过程,情感是由社会现实感发的,社会现实进入文学、艺术作品之中,成为文学、艺术作品的一个故事性元素,成为作家、艺术家思想情感的隐喻。
人生活在社会现实之中,感受着社会现实中的形形色色的人,品味着社会现实中的纷繁复杂的事,体验着社会现实生活所带来的喜与乐、忧与愁。社会现实本身是由一个个生命体构成的,能够主导作家、艺术家,引发创作的发生。在古典文学与艺术中,这种情形表现得比较普遍。
杜甫的《兵车行》显然是受社会现实感发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感发诗人产生创作冲动的是士兵出征的场景,并由这种场景反思唐朝的穷兵黩武,表达对和平、安宁的向往。士兵出征,爷娘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泣,哭声直冲云天。这种情形,对人情感的震撼很大。诗人正是受这种场景的感发,进而追问这种场景产生的深层原因。唐朝自开国以来,开疆拓土,贪得无厌,致使“边亭流血成海水”、“千村万落生荆棘”。由于男人出征打仗,只有妇女耕种,田亩里的庄稼长势很差,百姓的生活极为艰辛。士兵们虽然戮力奋战,却遭受种种非人的待遇,“被驱不异犬与鸡”。因此,无论百姓和士兵都厌倦了战争。连年的战争耗费了大量的物资,国库空虚,朝廷只能向百姓课以重税,更使百姓生活雪上加霜。“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由此可见,社会现实对诗人情感的感发非常直接,也非常具体。在社会现实的主导下,物与情的律动所产生的直接效果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怀,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社会现实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看作诗人思想或情感的象征或隐喻。
相比于诗歌,小说对社会生活的描写是直接的、世俗的,社会现实主导下的物与情的律动表现更为显著。《警世通言》有一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写的是风尘女子杜十娘与浪荡公子李甲的情感纠葛。李甲入京为国子生,在教坊司院里偶遇名妓杜十娘,两人“一双两好,情投意合”,“海誓山盟,各无他志”。起初,李甲大把使钱,把所有银两都花在妓院里,囊中羞涩之时,却招来老鸨的嫌弃。老鸨千方百计地想让杜十娘把李甲逐出妓院。十娘心爱李甲,与老鸨争辩。老鸨看到李甲已经当尽了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料想他再也拿不出银两,便以三百两银的较低要价让李甲为十娘赎身,期限十日。十娘为李甲应承下来,之后,便与他商定筹银之事。李甲在外奔波六日,求亲祈友,也没筹到分文。在这种情形下,十娘便将自己平日积蓄一百五十两碎银交与他,让他筹一百五十两便可足数。十娘的诚心感动了李甲的朋友柳遇春,遇春看出十娘是一个难得的奇女子,支持李甲的选择。在遇春的帮助下,李甲很快凑足了一百五十两银,在期限的最后一天交与老鸨。十娘终获自由。一对恩爱情侣踏上了回家之路。由于李甲的父亲一直不满他沉溺于风月之场,他害怕面对父亲。正当内心踌躇之际,新安阔少孙富听了杜十娘的歌声,垂涎她的美貌,巧言说服李甲放弃十娘,并答应赠以千金。突遇这种变故,十娘伤心欲绝。在李甲与孙富约定的交割之日,她打开随身携带的百宝箱,当着李甲、孙富及众多看客之面,将价值万金的珠宝尽抛江中,然后,怀抱百宝箱,举身跳入这滚滚洪流,以死来祭奠她曾经的爱情。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花费了大量篇幅描写李、杜两人的情感,写金钱以及与金钱有关的故事。实际上,这个故事所涉及的人物、情感乃至金钱都是作家思想情感的隐喻。李甲对爱情的追求是出于本能的欲望,不是爱情本身,一旦欲望得到满足,爱情便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因此,当孙富游说他时,区区一千银两就动摇了他曾经的爱情。孙富以金钱为炫耀,将金钱视为无所不能之物,藐视情感。杜十娘当着李甲、孙富的面将众多珠宝都投入江中,实际是羞辱李甲、孙富,嘲讽他们对金钱的崇拜。在她的眼里,最重要的是爱情。既然爱情失去了,金钱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人的存在也没有价值。小说的最后,对人物结局的描写虽然显得多余,但是,也同样是作者思想情感的隐喻。李甲疯了,孙富受到惊吓很快病死了,曾经因为感动于杜十娘的真情才帮助李甲筹银的柳遇春却无意间打捞到杜十娘的百宝箱。这显然是在演绎中国传统的因果报应。李甲、孙富是恶的隐喻,杜十娘、柳遇春则是善的隐喻。在这篇小说中,所有的人物与生活细节都成为隐喻。这是社会现实生活主导下的物、情律动创造出来的审美价值。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受社会现实感发而创作的巨幅画作。其选材之大,古今画坛罕见。汴京(今河南开封)繁荣的社会景象感发张择端,引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使他自然而然地拿起画笔,将清明时节汴京汴河两岸的风俗人情、自然风光尽入画中。画里描绘了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风俗民居,以及熙熙攘攘的集市与街道、弓形的桥梁、川流不息的人群,尤其对人物的描绘独具匠心。据统计,整幅画作共画人物684位、牲畜96头、房屋122栋、树木174株、船25艘、车15辆、轿8顶。所描绘的人物大者不足3厘米,小者却如豆粒。然而,个个形神毕备,不仅衣着不同,而且从衣着上还能看出身份、地位。所有人物、景物以及场景细节都是画家对自己思想情感的隐喻。
自然物色、社会现实作为物,都是审美创造和审美体验的感发之源。它们之所以能够感发作家、艺术家的情感,是因为它们本身鲜活,富有灵性。这种灵性与人一气贯通。人与自然一体,与万物一体,这是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也是感物发生的基础。古人正是秉承着这一传统,才显示出惊人的创造力,进而,使中国古代感物美学立于世界美学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