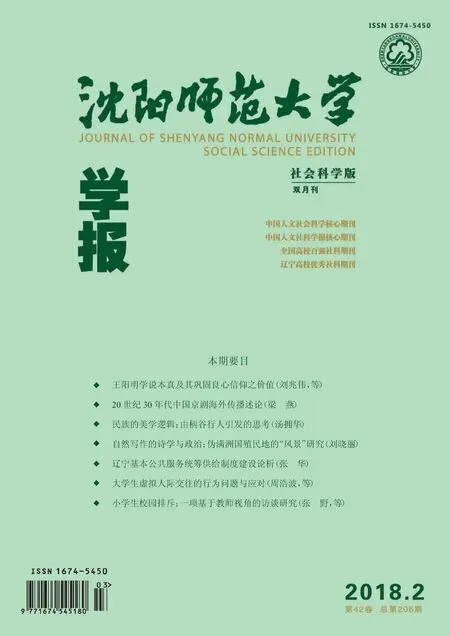自然写作的诗学与政治:伪满洲国殖民地的“风景”研究①
——以山丁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为中心的考察
刘晓丽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近代文明,不仅发明了“风景”,同时发展出有关“风景”的认知装置,产生种种意识形态观念,如使风景成为自然与政治之间的游戏,风景被部署在塑造国家、帝国事业、美好生活等观念中,被帝国主义、国家主义、审美主义、民族主义所征用。在殖民地语境中,风景的这种认知装置展示得尤为明显。笔者的研究计划是以日本殖民地伪满洲国文学为例,系统讨论“风景”如何为各种意识形态所用,产生出复杂的政治和伦理后果。本篇论文以梁山丁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为中心,讨论其中“风景”之意味,因为入侵者/原住民、现代/本土、商业/农业、当下/历史等角度不同,风景在呈现不同的意味,这些意味生成着某种伦理的、意识形态的、生活风格及生产范式的种种观念。由此查看伪满洲国时期烙印在自然风物中的殖民伤痕。
一、关于《绿色的谷》
《绿色的谷》是作家梁山丁(1914—1997年)在1942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初刊伪满洲国的《大同报》。
迄今,《绿色的谷》共有6个版本,有研究者对部分版本进行过比对性考察②《绿色的谷》版本及版本比对研究,详见冈田英树、蒋蕾、牛耕耘、王越相关著述。笔者的研究以版本三为主,辅以版本五和版本六。感谢李春燕研究员、冈田英树教授、王越博士、牛耕耘博士提供相关材料。。
版本一:《大同报》汉语版,连载于1942年5月1日—1942年12月3日;
版本二:大内隆雄翻译的日语版,连载于1942年7月—X年X月的《哈尔滨日日新闻》,结束时间不详;
版本三:汉语单行本版,“新京”(长春):文化社,1943年3月15日;
版本四:日语单行本版,大内隆雄译,奉天(沈阳):吐风书房,1943年7月5日;
版本五:汉语修订版,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5月;
版本六:汉语复刻(1943年汉语单行本)版,见牛耕耘编《山丁作品集》(刘晓丽主编“伪满时期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丛书”之一),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
《绿色的谷》以东北一个自然村落——狼沟(林家窝棚)为中心,描写了各种力量对这个村落的侵蚀与破坏,在铁路修进狼沟之际,狼沟之子——林彪自己解构了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狼沟,把狼沟的土地和依靠土地生存的人们交给了未知的未来。
狼沟的历史,小说如此交待: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年),“林家便占有了这全狼沟的山野。”[1]①本论文中有关《绿色的谷》的引文,均引自版本三:《绿色的谷》,“新京”文化社,1943年,以下不再一一作注。那时林家人在北京居官,到了林家第二代人,虽然中了举人,但厌弃了在北京的宦海生涯,全家迁居到狼沟。狼沟当然不是世外桃源,历经中国现代进程中的各种事件:日俄战争,清朝覆灭,民国建立,军阀混战(直奉战争),伪满洲国成立等。虽然小说最后一句是“把满洲事变的消息捎到狼沟”,似乎小说中的故事时间停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但是如果按小说故事的内在逻辑推算,林彪的父亲林国威战死于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年),当时林彪11岁,之后林彪跟随改嫁到南满站的母亲生活10年,此时他中学毕业后回到狼沟,小说主体故事从青年林彪回到狼沟开始,而此时时间应该为1934年②小说作者梁山丁对故事中时间问题有过这样的说明,“小说最后一节,纯系迷惑警犬而添上的尾巴,故意把小说描写的时间移到九一八事变以前。”见《万年松上叶又青——〈绿色的谷〉琐记》,1987年版《绿色的谷》,第226页。。
1934年林彪回来之前的狼沟,在动荡的近现代中国维持固有秩序延续下来,虽然几经变化,但是土地及人伦关系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虽然狼沟的林家在辛亥革命后开始走向没落:林彪的父亲林国威战死,母亲石桂英改嫁给南满站(以当时的奉天市为原型)商人钱如龙;林彪的叔叔林国华嗜赌懒做,被林国威赶出林家;林家依靠林彪的独身姑姑林淑贞勉强维持。林家把希望都寄托于在南满站读书的林彪身上。但是也正是因为林家的衰落,没有一个合适的当家主人,狼沟林家才没有像“绿色的谷”中其他村落的地主——如老马堡的佟老秀和边门堡的吕大东家主动移居到南满站,以“浮把”③浮把,泛指买空卖空的粮栈、粮户。的头衔和城市资产者争夺、角力,躺在大陆商行代理店的烟榻上长年累月地吞云吐雾。他们离开乡村原有的生活秩序和生活伦理,在城里过着投机商的日子,做着发财美梦。
小说主体故事时间始于林彪回到狼沟。狼沟面临的种种挑战。首先是自然力量的挑战——狼群袭击林家窝棚。狼沟,从这个村落名称可以猜测狼曾经居于此。此地本来是狼的家园,林家人到来之后,驱逐了狼群,建成了林家窝棚。但被驱逐的狼,并不是一种从此消失的自然力量,它们依然有重返家园的行动。原始野性的狼群包围林家窝棚,小说写得惊心动魄,林家的管家霍凤命悬一线之时,返乡的林彪不负众望开枪打死领头狼,狼群四散,救出管家霍凤,也解救出被狼围困的林家窝棚。小说这一段写得特别精彩,狼的野性被渲染得淋漓尽致,但在拥有洋枪的智慧的林家主人跟前,却不堪一击。更精彩的一笔在后面,狼群散了,但不等于狼永远地离开了此地,“东边的天空刷上一层绛紫色,像一只透明的纱幔。几颗星,寒冷地躲在纱幔的后面战栗着,狼仍在远处盘旋,嗥叫不时从深邃的山谷中传来。”伪满洲国的读者,尤其是“弘报处”的文化检查官读到此处,会作何感想④据山丁自己回忆1943年汉语单行本《绿色的谷》的出版经历:书已经印刷出来,“突然接到伪满洲国弘报处的命令:《绿色的谷》一书有严重问题,不许出厂,不许发行,听候处理!”经过出版社调节,最后印上狼“消除剂”大红戳印得以出版。见《万年松上叶又青——〈绿色的谷〉琐记》,1987年版《绿色的谷》,第227页。消除哪些内容,版本研究者没有给出说明。但论文引述这一段,的确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释。另外一点,需要说明:笔者藏有的1943年汉语单行本未见“消除剂”红印。《绿色的谷》出版情况更为复杂,山丁本人的回忆仅仅是依据材料之一。?
其次是民间的胡匪——小白龙袭击狼沟。生活在原始林中的胡匪和狼群一样,充满野性的力量,很难用善恶来描述他们⑤晚年山丁自己说《绿色的谷》要描写的是绿林好汉。见《万年松上叶又青——〈绿色的谷〉琐记》,1987年版《绿色的谷》,第226页。。胡匪和从事农耕的适龄村民身份可以随时转换,狼沟村民大熊掌进了原始林跟随小白龙就成了胡匪,而他的老婆还生活在狼沟,也没有因为是胡匪的老婆被嫌弃,而当大熊掌带着少东家林彪回到狼沟后,又转身成了狼沟的村民。胡匪为生存常常劫掠村庄,也是实情。“小白龙盘踞在狼沟一带,足足有了两个月,就像一批遮天蔽日的蝗虫,黑压压地伏在庄稼人⑥1987年版《绿色的谷》,将“庄稼人”修改为“地主们”。牛耕耘注意到这一点,并指出,改动之后小白龙集团的性质就发生了质变。见《山丁作品集》(牛耕耘编,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165页注释。的身上,吮吸着,舐噬着。”那些亦农亦商的在南满站生活的地主家被洗劫一空,老马堡的地主佟老秀家被胡匪抢了财产,烧了房屋。“边门堡不但烧了半趟街,就是那些没处跑的人家也全叫小白龙裹去了。”当小白龙率领的胡匪袭击狼沟林家时,林家的管家霍凤组织林家窝棚的村民——住在下坎的地户和上坎的地主齐心合力,共同抵御胡匪,打退了胡匪,保住了财产和村民的性命。被困在狼沟的南满站商人钱如龙都禁不住要感叹林家窝棚的这种“伟大的力量”,深深植根于乡村伦理的乡村自治力量。
再次是城市资本的挤压和侵蚀——铁路修进了狼沟。城市资本,在小说中是以南满站为代表,其与自然界的狼群、民间的胡匪不一样,作者在描述南满站时,充满了道德上的嫌恶感。“南满站的市街像蜘蛛网似的伸张着,浪速通①今天的沈阳市中山路,1919—1945年称“浪速通”,中华路当时叫“千代田通”,民主路叫“平安通”,都是当时“满铁”筹建“奉天驿”即奉天火车站为中心按日本风格修建放射状的街道。由此也可以看出,小说中的南满站是以奉天为原型。是一只披着金甲的爬虫,从网的左端斜滚下去,穿过转盘街,一直到商阜地的边沿,它带着滚沸的尘烟,狂暴的哮喘,惊人的速度追赶着年月向前飞奔,几乎吞噬了那些星散于附近的类似苍蝇的屯堡。……柏油马路地下层的洋灰管,汇集着街市各处的秽水,浓痰,粪便,病菌,向那条蜈蚣似的寇河流去。……铁丝网在街的尽头扩张着嘴,高压电流威胁着每个住民的呼吸。”南满站所代表的城市资本的力量,不仅吞噬着乡村,还腐蚀着、污染着乡村,这段描写充满了对南满站的毫不掩饰的嫌恶。以日本大陆商行为靠山的中国买办、地主聚集在南满站,各怀投机发财梦,计划在“绿色的谷”投资铺设铁路,让自己拥有的土地增值。铁路要横穿狼沟,商人、地主们通过计谋买卖土地,将铁路修进了狼沟。南满站是作为狼沟的对立面存在的,作者厌恶南满站、赞美狼沟,小说对在南满站生活的商人和地主们进行了抨击并让他们有一个落魄的结局,而把希望给予了狼沟。地主买办们虽然强行把铁路修进了狼沟,但胡匪抢劫了他们的家乡,铁路投资过程中的舞弊及贪污等被揭穿,这使得商人买办和地主全部破产。而狼沟的林家经历了变故,林淑贞被林国荣所杀,被胡匪绑票的林彪在大熊掌的帮助下回到了狼沟,林彪开始了自己对狼沟未来的规划。
最后是林彪在狼沟的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解构狼沟原有的乡村秩序,让村民自己探索未来。自然力量挑战,民间胡匪的侵袭,没有让狼沟凋敝,反而让狼沟原有的乡村秩序、乡村自治、乡村伦理得到强化。依托于南满站的城市商业的象征——铁路修进了狼沟,虽然作者山丁充满同情安排故事,让南满站那些利欲熏心道德败坏的亦农亦商的地主们和买办商人遭到毁灭之灾,狼沟林家因林彪的归来依然充满希望。但是作者也不得不面对铁路带给狼沟的变化。铁路改变了原有的乡村秩序,乡村原有的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也被改变着,“我不种地了!我去掘煤,去砍木头,去到南满站当苦力,我不种地了!”狼沟村民黄大辫子这样表达自己的愤怒。此时的狼沟不再是以前的狼沟,此时狼沟的主人也不再是以前狼沟的主人,狼沟不再被动地应对各种力量的挑战,而是要自我更新自我改革。林彪对地户们说:“我的土地也并不是我的,我想把它们全部送给你们,只要你们的生活能好起来!你们能……”正如管家霍凤的反应:“少东家!你知道,老太爷立下的家业,多么不易……如今……想不到,到了你手,就一把灰扬出去……”林彪不想再被动地接受各种力量的挑战,自己把狼沟林家窝棚原有的土地秩序、乡村组织“一把灰扬出去”,交给了未知的未来,希望狼沟人自己探索。
二、交错的复数风景与政治隐喻
如果有一种小说分类,可以按照自然景观来概观的话,就像文学史上称康拉德的小说为海洋小说,我们也可以把山丁的《绿色的谷》称为一篇山林小说,而且在伪满洲国的确有这样一种小说分类——山林秘话·谜话②参见刘晓丽《伪满洲国的“实话·秘话·谜话”》,《博览群书》2005年第9期。代表作品有睨空的《大兴安岭猎乘夜话记》(10万字),该作品是笔者系列研究——伪满洲国殖民地的“风景”研究之二分析的文本。[2]。《绿色的谷》中有着山林狼沟的复数的风景,这些复数的风景隐含着不同的意味,同时生成着某种伦理的意识形态的生活风格及生产范式的种种观念。
风景之一:自然野性的生命力与被规划的政治领土
正如前文分析,狼沟有其自己的历史脉络,在这个历史脉络的进程中,狼沟逐渐风景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显现出与某种特定政治共同体的关联。
小说一开始,这样描写秋天的狼沟:
秋天的狼沟,满山谷泛滥着一种成熟的喜悦。
青绿色的粗皮酸梨,被八月的太阳晒红了半面,仿佛擦抹下等胭脂的少女,害羞地藏躲在叶网里。榛子壳剥裂着,在干燥的空气中发着轻脆的响声,澄黄的榛子有的便落在草丛中,甚至被埋在枯叶堆里。肥大的山葡萄成群地拥挂在山谷的深处,黑紫的表皮罩上一层乌光。夜里,西风从寇河上狂吼着经过柳条边,向北刮过来,猛力地摇撼着狼沟的山野,树上结着的累累的山楂、山里红,便被残酷地打下来,散落在山野的各处,有时飞扬着漫在半空。
这段对狼沟自然风景的赞美,有两点引人注目。一是狼沟的旺盛的野性的生命力。“粗皮的酸梨”“剥裂的榛子”“肥大的山葡萄”在太阳下旺盛生长、熠熠生辉,“青绿”“澄黄”“黑紫”的色泽显示出原始的生生不息的力量。二是政治边界——“柳条边”。紧接着太阳下的野性自然,是“夜里,西风从寇河上狂吼着经过柳条边”,摇撼着狼沟的山野。“柳条边”——中国东北的标志性界限——建于清初的土堤,当时清廷为维护“祖宗肇迹兴旺之所”“龙兴重地”修筑这条呈“人”字形土堤,总长度为1 300余公里,其主要用途在于防范汉人进入满洲。政治世界的引入导致在自然的地理上形成了领土意义上的区隔,“柳条边”打破了原始自然的狼沟,在这里狼沟呈现为生生不息的自然与被规划的政治领土的风景。
“柳条边”这条政治区划的边界,本来是清代历任皇帝们都想把这里作为一块满族文化的自留地,然而,随着持续数百年的禁令被撤销,汉族农民大量地涌入该地区,小说中的林家也是一例。小说虽然没有交待林家的族群特征,但是从叙事中可以探知他们是汉人地主。“柳条边”仅仅是一个历史上的政治边界。历经数次变动的东北大地,“柳条边”不再具有实际的政治意义,而野性的自然狼沟却依然生机勃勃。这段风景的隐喻如果与下面另一种风景——铁路修进狼沟对读,更有意味。
当试开的火车驶入狼沟时,小说这样描写:
那些若干年来漫生在草甸上的苇、艾织成的锦席,如今被横切了一刀,分开了,在路基两旁,摇着窈窕的腰肢。当那个钢铁的怪兽——机关车试探着脚步出现在狼沟的山谷的时候,终生不出户的庄稼人惊奇地望着它,女人们恐惧地唾骂着:“现世的魔障,在白天里出现了。”在这种唾骂诅咒中,钢铁的吼鸣每天继续不断地响起来。
1934年的伪满洲国(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正在大力展开铁路建设时期。1933年3月出台的《“满洲国”经济建设纲领》中,明确指出:“铁路建设以经济开发为重点,同时将巩固国防以及维持治安作为目的。”[3]将铁路归为“国”有,由“满铁”承担“国家”铁路建设,出台了《铁道法》;1934年创设了“奉天铁道学院”,“王道来自铁路”的标语口号到处张贴。铁路建设在伪满洲国代表着“国家”政治。铁路修进狼沟,表面上是南满站的买办和亦农亦商的地主们的贪婪发财梦,实质是“国家”政治对狼沟的接管。政治世界以铁路为先锋切开狼沟的原始自然的纹理,逐渐让狼沟成为政治安排中的风景。
风景之二:如画的风景与去政治化的殖民臆想
近代殖民在某种意义上,是给赤裸裸的侵略穿上开发、建设、文明的衣裳,就如小说里所言:“一年比一年更年轻更喜悦的火车,它从这里带走千万吨土地上收获的成果和发掘出来的宝藏,回头捎来‘亲善’‘合作’‘共荣’‘携手’……”①据冈田英树教授考察:日译版的《绿色的谷》删除了这一段。“这里揭露了隐藏在‘日满共存’背后的掠夺,是非常危险的表达方式,所以在大内的译本中都谨慎地用缺字符来表示。”见冈田英树著,靳丛林译《伪满洲国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6页。比这更具有隐蔽性质的是一种貌似无害的甚至无功利目的的审美眼光。
小说《绿色的谷》中,日本以大陆商行的名称出现的,大陆商行经理人是一个影子似的日本人,仅与商人钱如龙喝茶时出现过一次,其次都是电话另一端的人物,只在“线上”,不在现场,却是搅动事件的核心。商人和地主们之所以能产生投资修铁路的发财梦,是源于这个大陆商行经理的多年经营。而大陆商行的女儿美子——一位单纯美丽的日本少女——成为狼沟的观察者。
美子是一位崇拜大陆、赞美大陆、被大陆迷惑的日本女孩,她“仿佛是大陆的一个狂热的情人似的”。她与狼沟林家窝棚少东家林彪相恋,是因为林彪来自狼沟,带着大陆山林的气息,同时林彪可以带着她领略大陆美好风光,甚至定居于她热爱的狼沟。美子仰慕地听着林彪描绘自己的家乡:
(狼沟),像这样的春天那里遍地种植着大豆、高粱、小米,山谷长着杏、枣、杨魁、梧桐,开着紫色的丁香,粉红的拾叶梅,红白小花的季季草,遍山谷能看见黄色的蒲公英。
秋天,满山谷结着榛子、野葡萄、山里红、山梨,奔跑着野狐、黑熊、斑貂、紫貂,田野里收获金黄似的黄豆、红壳高粱、白玉谷子、小粒芝麻、长穗苞米……满堆满垛。
这里是林彪的描述,更是美子期待看到的风景——美丽、富饶、美轮美奂的如画世界。这是审美者看世界的方式,用如画的美学观念来看新土地——赞美地看、充满视觉愉悦地看。风景如画,首先清洗掉的是人,风景中没有人的痕迹,没有劳作的痕迹,这是一块无人的自然景观,不是政治领土。其次如画风景给人以梦想,来这里看看,来这里居住,来这里开启新的生活——桃花源式的生活。异乡的土地任凭视觉去审美,任凭他者来规划,这背后隐藏着殖民者的文化特权、文化神话,但是这些霸权,都是被优美风景所柔化。
以审美的目光替代政治控制,这是殖民者发明的“风景神话”。如画风景,无人认领,等待着宗主国的国民来欣赏、移居、开启新生活。被军事征服的“满洲”大地被风景化,作为新移民的生存场所,随“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计划”而来的新移民,没有道德负担,却迎来了“开拓者”的美名。《绿色的谷》中的大陆商行的经理及其女儿美子,以这样的心理坦然地居住在“满洲”。而且美子作为无害的审美者,被“满洲”青年林彪爱恋着。同时,如画风景的观念,让殖民地原住民减弱被强占的刺疼,审美貌似无害。更重要的是,风景如画的观念,还塑造着殖民地知识分子看待自己家园的眼光,用一种外在于我的态度对待家园,或赞美或评判。小说中林彪看待狼沟的态度,不同于一直生活在狼沟作为狼沟山林看护者霍凤的态度,林彪在南满站受教育10年,对家园又爱又痛,他赞美地看待家园,已经与日本女孩美子一样具有了审美者的眼光,但是他不同于美子的是,他是狼沟这块土地的后代,对这块土地及依赖于土地生活的人们负有特别的责任,这个责任让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无法挽救狼沟时,把狼沟的土地交给狼沟的每个人,让他们自己探索未来。
风景之三:风景利润与殖民资本
南满站的商人钱如龙这样描绘自己的视觉经验:“(南满站)没修铁路之前,这儿只不过是几家马架,自从铁路修成了,就变得像现在这样繁华、热闹。说起来,铁路这东西真够得上个怪物。”山东流民钱如龙,借着殖民者的经济殖民进程发了财,同时被调动起更大的发财欲望。生活在绿色山谷里的地主们,也透过火车、铁路与南满站世界互动起来,在他们眼里土地被重新想象,不再是赖以生活的家园,而是可以赚钱的筹码。
老马堡的地主佟老秀和边门堡的地主吕大东家移居到南满站,开始盘算着如何让自己拥有的土地带来更大的利润。他们一开始仅仅是交易土地上出产的粮食,加入城市资本的流转,很快他们看到土地还可以带来更大的利润——开发带来的土地增值。大陆商行的买办商人钱如龙提议在狼沟一带修建铁路时,他们立即成为修筑铁路的股东,家园变成了地图上的发财规划,山谷、山峰都变成了摇钱树,变成了可以带来更高利润的砝码。
在写字台上铺着一幅狼沟一带的地图,绿色的山脉在东北部漫布着,像无数条麟质的爬虫似的。山峰宛如钱形的疥疮,长在麟质的皮肤上,寇河弯曲着从爬虫的间隙行过。
吕大东家关心的是,铁路是否能修到自己家的边门堡,最好能从家门口经过,他讨好着修路技师和钱如龙,盘算着“这条铁路倘能修成,从边门穿过,边门堡的兴隆指日可待……”
殖民体制不仅携带各种观念,同时还调动殖民体制两边的人们的各种欲望,这些被调动起来的各种欲望交织在一起推动殖民进程。殖民进程不仅仅是单向、静态的过程,而是各种观念各种欲望混杂的方向不一的进程。殖民地有产者的发财欲望被调动起来后,会主动寻求与殖民者资本合作。小说中的地主吕大东家是这样的资产者,希望借助殖民资本发财。而已经发殖民财的大陆商行买办钱如龙,在与大陆商行经理聊天时,夸张地形容那绿色山谷的壮美和价值,“肥沃的土地,丰富的宝藏”,希冀殖民进程更快进行,把铁路修进“绿色的谷”。
在这里殖民地的有产者发明一种新的风景——可以带来利润的风景。但是这些只做发财梦的殖民地的人们,并没有看到,殖民者的殖民开发进程其实与他们无关。这些殖民者买办商人的利益甚至性命生死也不是殖民者关心所在,当他们的土地家园被胡匪小白龙烧掠时,殖民者并不在意;他们因为自己的贪婪舞弊破产时,也没有人关心他们的生死。殖民者往往不过是叫这些人看到一个发财的影子,调动起他们的贪欲,协助殖民进程,随后便把他们推上了毁灭的道路。
风景之四:看不见的风景
生活在狼沟林家窝棚的人们,不论是地主还是佃户——林淑贞、霍凤、于七爷、黄大辫子、疤瘌眼,他们不会把狼沟看作风景,他们过着一种围绕狼沟自然节奏而建立起来的生活,与狼沟的万物浑然一体,与狼沟的草木息息相关,他们守护狼沟的土地,守护自己。
狼沟的主人林家人,是山谷土地的主人,是下坎①狼沟的林家窝棚,在空间上分为上坎和下坎,地主林家住在上坎,佃户及贫民住在下坎。所有佃户的家长,但地主林家与下坎贫民们有着非常复杂微妙缠结的关系:林家第二代人林国威娶了下坎小户人家的女儿——马贩子的女儿石桂英;林彪与下坎佃户姑娘小莲相恋。林家人以看守狼沟为最高责任,林淑贞为了守住林家的荣誉和产业,与管家霍凤因爱恋发生肉体关系,却义无反顾地作出自我牺牲,无怨无悔地过着毫无个人生活可言的日子。正因为林淑贞的苦苦支撑,狼沟原有的秩序、生活形态在各种变动中能一直维持着。就连林彪在对佃户们演讲时也说:“土地就是我们的生命,无论谁,离开土地就等于自杀……”林家管家霍凤,因为与林家守护者林淑贞有染,被林淑贞的哥哥林国威赶出狼沟,在采木公司做保镖,却一直心念着狼沟,犯着怀乡病。霍家三代生活在狼沟,为林家管家,已经与狼沟与林家有一种类似血缘似的联系,只有生活在狼沟的土地上,与林家人在一起,他才能安心生活。当他得知林国威阵亡后,“在一个恬静的黄昏,走回狼沟。他并非对于林家的产业有了什么妄想,实在是在想看看狼沟的念头压过了旁的欲望。”
于七爷一家三代生活在狼沟,与林家三代有交往,感激地租种林家的土地,与狼沟的土地、与土地上生产的粮食、与林家人有着特殊的情感连带关系,因为收割的高粱遭雨全部糜烂,心生绝望。于七奶奶,明知胡匪来袭,却仍然留在浸透着创业血汗的生身之地迎接死亡。
当然狼沟不是田园牧歌式乐园,这里有着各种各样的苦难和压抑人的观念。贫穷是下坎的日常状态,还有对女性的歧视、对主人的无限忠诚、对狐仙的绝对崇拜等顽固观念,狼沟人与狼沟土地相依相存,过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嵌在“绿色的谷”中的生活。当铁路修进狼沟,切开的不仅仅是狼沟的土地,还有这些嵌在土地上的人们的生活。他们对新的生活样式毫无准备,不知所措。在狼沟生活三代的黄大辫子,当知道铁路线路已确定,狼沟的一部分土地通过欺诈手段卖给了大陆商行时,他本能的反应是:“我们不种地干什么呀……,我们一向是靠东家活着,靠土地活着,我们没有地能活吗?”
三、风景政治学
透过前文介绍的《绿色的谷》版本,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事实:第一,1942—1943年有4个版本之多,说明该小说深受伪满洲国时期出版界的关注;第二,小说的日文版仅仅比中文版晚两个月刊出,几乎同步,日语读者或者是日本人非常期待这部小说。
正如前文分析,狼沟不是单纯的自然景观,而是与某种政治领土、政治想象连带在一起的,这种连带如一张纸的两面不可分,但不同目光投射到此,会结出不同的政治伦理后果。
讨论《绿色的谷》的出版,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伪满洲国文艺政策事件,即1941年3月23日,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发布了《艺文指导纲要》,确定了伪满洲国文艺的基本方针为——八一宇、独立文艺,即“我国文艺以建国精神为基调,并藉此显现八一宇的巨大的精神之美”,“以移植于这一国土的日本艺文为经,以现住各民族固有的艺文为纬,汲取世界艺文的精华,织成浑然独特的艺文。”②参见刘晓丽《异态时空中的精神世界——伪满洲国文学研究》(修订版),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的附录一《艺文指导纲要》。当时伪满洲国时期出版界之所以欢迎这部小说,多种版本刊行,与小说中浓郁的地方色彩、地方风俗、地方风景不无关系,至少看到《绿色的谷》和伪满洲国基本文艺方针的关联性,看到其可资利用的资源——独特风景——“独立国家”。其实就在《绿色的谷》出版单行本之际的1943年,伪满洲国文坛开始提倡“满洲独立乡土文学”,号召文学去描写“壮美的大自然”“朴素的风俗”“高扬这乡土之爱”,希望通过“独立色彩”的文学作品育成独立国家,而“壮美的大自然”“朴素的风俗”“高扬这乡土之爱”也是小说《绿色的谷》内容的一部分。
当时为什么要如此积极及时地出版日语版《绿色的谷》,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释,本文这里提及一点——“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计划”,即1941年完成来“满洲”开拓政策的第一期计划,1942年进入计划完成的第二期。当时由于多种原因,这个计划受到阻扰难以为继。开拓民的悲惨生活也不时地传入日本本土,一些以“满洲”农业开拓生活为题材的作品③例如:上野市三郎的农村作品集《县城の空》,“大陆开拓文艺恳话会”编《大陆开拓小说集》,“农民文学恳话会”编《农民文学十人集》,“满洲移住协会”编《潮流大陆归农小说集》,此外,还有一些朝鲜人用日语写成的大陆开拓小说,这些作品多数为大陆开拓唱赞歌,但会不经意间就流露出开拓生活之艰苦。,描写了天寒地冻的恶劣的“满洲”生存环境。重塑“满洲”大陆形象,成为部分日本知识分子和伪满洲国官员的议题,为此,“满洲文话会”在1941年编辑了随笔集《大陆的相貌》。多重身份的翻译家大内隆雄及时地翻译出版了《绿色的谷》,在某种意义上与《大陆的相貌》相应和。美子和林彪以审美者的眼光看到的美丽风景,“壮美的大自然”“朴素的风俗”为重塑“满洲”形象助力,甚至会打动那些欲动未动的要前往“满洲”的日本农民。
当然,上述殖民者的意图未必是作者本人的意愿。恰恰相反,时隔40多年后,作者本人表达了与之完全相反的观念,这是一部写于1942年日本统治最黑暗时期的抗日民族主义小说,“那是寒凝长夜寂无声的1942年,我下决心要写一部以家乡狼沟农民武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4]山丁本人计划写成如萧军《八月的乡村》那样的抗日文学作品,但是因为自己身居伪满洲国没有祖国那样的出版环境,而且大内隆雄没有与他联系就翻译并在《哈尔滨日日新闻》上连载刊出日语版,这些都对他的创作企图产生了影响;同时,山丁还回忆了该书被审查的过程,遭到扯页处理的出版命运,自己也被迫因此于1943年逃亡北京。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在两个方向上解读该作品:一是抗日爱国主义作品,如李树权撰文《多彩的乡土画卷与爱国者的呐喊——论梁山丁的小说创作》;二是阶级矛盾阶级抗争作品,如王建中撰文《阶级抗争图乡土风俗画——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可以说,这些解读坐落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转型期,非常有意义。这些研究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学,打捞出尘封已久的《绿色的谷》,让这部作品与解放区的革命文学遥相呼应,纳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版图。
今天我们重新考察《绿色的谷》,既要看到伪满洲国当局对该作品的政治盗用及如何盗用,同时也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把作品紧紧系在民族和阶级的观念松绑。重回作品原点,不是回到1987年的修订版,而是回到1942—1943年的初版及出版语境,探寻作品内部蕴含着的多种可能。
[1]梁山丁.绿色的谷[M].“新京”:文化社,1943:11.
[2]刘晓丽.伪满洲国的“实话·秘话·谜话”[J].博览群书,2005(9):34-38.
[3]“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分论:下[M].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译.长春:吉林省内部资料准印证第 90098 号,1990:327.
[4]山丁.万年松上叶又青——《绿色的谷》琐记[M]//绿色的谷.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