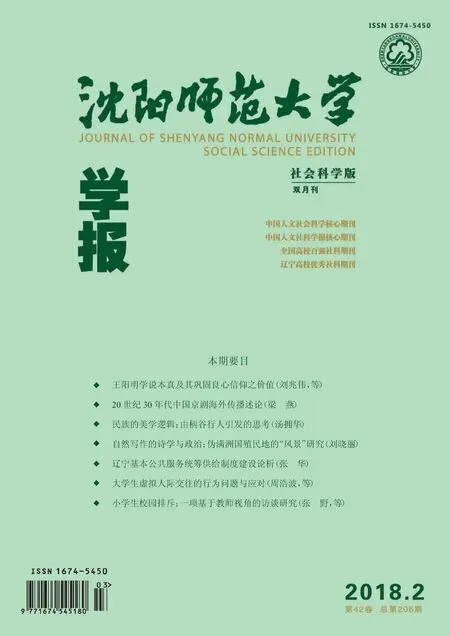东亚殖民主义理论及其细节
主持人语:我们之所以提出“东亚殖民主义理论”,源于20世纪80年代国际人文学开始流行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该理论强大的解释力有覆盖所有殖民经验的趋势,而让学术界忽视它所遗漏遗留的问题——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殖民地。后殖民主义是一套基于欧洲帝国主义及其殖民地的理论话语,主要以英法两国和其后美国实行的新帝国主义及其殖民地为考察个案,不但未把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殖民地的问题纳入研究范围,而且还把日本视为欧美的“他者”。赛义德的《东方学》开篇即指出东方是欧洲的他者,日本作为东方国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殖民地一道纳入了东方他者。由此,我们需要新的操作性理论来描述东亚殖民主义的现象及问题,清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思想及操作方式与东亚殖民地多种多样的抵抗方式。
日本向近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同时成为东亚唯一帝国主义国家,之后经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到一战时与英、法、美三国一同确立了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地位,库页岛、北海道、冲绳、台湾、朝鲜、伪满洲国先后沦为其殖民地。日本在模仿西方殖民方式的同时,还承接了古代东方的文教传统,对不同的殖民地采取不同的殖民操行;而且像朝鲜和“满洲”殖民地,本土文化因其历史原因在很多方面高于殖民者的文化,受殖者中的文化人在殖民地“文教政策”的庇护下,即时地表达出殖民地的生存状态,而不像西欧殖民地通过殖民者或者殖民者二代克里奥尔人才能让殖民地的生存样态得以表现。东亚殖民地文学——尤其是在地文化人的文学是构建东亚殖民主义理论的重要元素,特别是多种多样的抵抗文学——例如反殖文学、解殖文学、抗日文学等都超出了后殖民主义理论解释的范畴,并有望为全球去殖民化运动提供新的思想资源、理论视野。
本期专栏三篇论文都具有理论自觉,从不同维面进入东亚殖民主义理论及其细节。汤拥华教授的《民族的美学逻辑:由柄谷行人引发的思考》一文,解读后殖民理论代表之一日本学人柄谷行人的理论。柄谷行人来自东方却不属于第三世界,他所面对的问题更加复杂,既有反省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东亚的近代疾病——由民族主义滑入帝国主义,同时还有作为东方人的西方霸权的受难及抗争的记忆。该文在肯定柄谷行人理论的反省性、复杂性和原创性同时,提出一种新的思考路径——民族与美学互为反思、各自独立性,“彼此形成视差之见,以激活历史与理论、现实与乌托邦、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等一系列矛盾”,借理论与历史的双重自觉,为以民族为中心的话语实践保持反思与自我批判的可能性。刘晓丽教授的论文《自然写作的诗学与政治:伪满洲国殖民地的“风景”研究——以山丁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为中心的考察》和何爽博士的论文《殖民经济“统制”下的文学想象与精神抵抗——伪满洲国文学中的工人形象书写》从“风景”和“劳工”两个细节进入东亚殖民主义理论。山丁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中“风景”意味多样,在入侵者/原住民、现代/本土、商业/农业、当下/历史等角度观照下,既是现代殖民的装置,也是消解殖民的装置,具有双重力量,而且世世代代生活在“绿色的谷”中“看不见风景的人们”还具有消解“风景—装置”的原始力量,这种种复杂性展现出东亚殖民地文学的独特性,而不仅仅是西欧式的“风景的发现延伸到哪里,杀戮和同化就延伸到哪里”。“劳工”形象也是伪满洲国文学中常见的群像,没有协商余地的极速的“现代化”“文明化”是所有殖民地的特征之一。这样的“跨越式”现代化瞬间改变了毫无准备的本土人的生活方式,随之而来的是非人的劳作、极度贫困和道德堕落,但唯有在东亚殖民地因殖民者的“文教政策”这种生存状态得以即时表现。这些作品借着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殖民地官方文化系统中,瓦解殖民地“现代化”“文明化”的幻象和假象,以此种方式构成抵抗文学之一种。
特约主持人:刘晓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