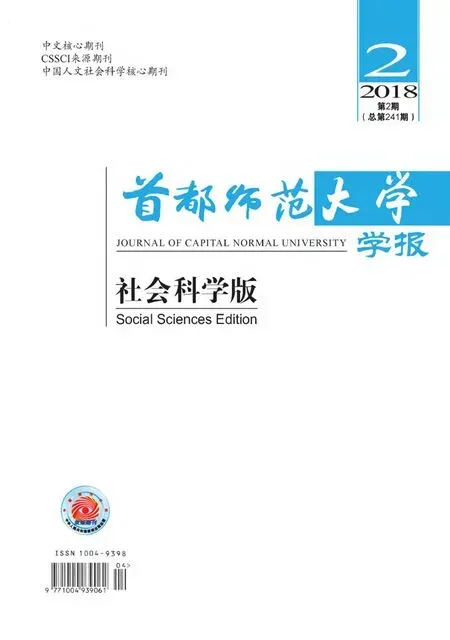从“先验认识论”到“话语事件”
——福柯话语理论对康德先验人类学的批判
牛宏宝 舒志锋
康德是启蒙哲学的代表,福柯则称得上是启蒙现代性最著名的反思者,这种在启蒙问题上的对砳性态度不妨视为二者的另一种关联。实际上,福柯青年时期曾经翻译过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并将这一翻译及其导言作为他的副博士论文*该副博士论文一直以打印稿的形式存放于法国索邦大学,直到2008年才由巴黎Vrin出版社出版。英文版见:Foucault. Introduction to Kant’s Anthropology. Los Angeles: Semiotext(e),2008.。在福柯此后的理论写作过程中,康德不时浮现于其笔端,其中明确涉及到康德哲学的著述有:《词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71),《什么是批判》(1978),《何为启蒙》*福柯的《何为启蒙》有法文、英文两个版本,都是依据1983年法兰西学院第一堂课的内容。法语本主要是课程的前半段,而英文的部分则侧重于课程的后半段。具体可参见弗里雷德·格霍:《福柯考》,何乏笔译,华东师范大学2017版年版,第160页。(1983)。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完成了《何为启蒙》这一学术演讲后不久就去世,这一文本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福柯的终结性文本。因此,无论是在学术起始时期,还是在学术思考的最后阶段,康德始终是福柯关注的对象。在国内外已经有不少研究指出了福柯理论中的康德“成分”以及福柯对于康德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具体参看Gilles Deleuze: Foucaul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p.60;Colin Koopam:Genealogy As Critique—Foucault and The Problems of Modern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3,p.14;Marc Djaballa: Kant, Foucault,and Forms of Experience,New York: Routledge,2008,p.14.德勒兹认为,福柯在几个基本面上是不同于康德的:“(福柯所研究的——引者注)条件与实际的经验相关;他们是在“客体”以及历史构型(historical formation)一边,而不是在普遍的主体一边”(Gilles Deleuze. 1988. Foucaul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60.);同样,科林·库普曼认为福柯的批判哲学并不是对康德哲学的复制与照搬,而是做了转化(transformation):“福柯并不对可能性的先天条件感兴趣,这是康德对先天人类思想一般化探讨的中心。相对而言,福柯对限制当下思想的可能性的历史条件更感兴趣……福柯将康德式的批判从先验计划转向了历史(也就是说,人类学以及谱系学)领域。这一转换使得福柯在与康德的计划保持重要联系的同时也改变了这一计划。”(Colin Koopman.2013. Genealogy As Critique - Foucault and The Problems of Modern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15)。于奇智认为:“从康德问题到福柯问题的变迁,是思想事件之间的‘新陈 代谢’……福柯问题脱胎于康德问题,‘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是福柯对康德人类学的丰富和发展。”(于奇智:《从康德问题到福柯问题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但是对于福柯话语理论中康德先验人类学批判向度却少有涉及。本文尝试从文学语言的“僭越冲动”与话语的“事件属性”两个方面,对此进行开拓性清理与分析。
一、限制性原则与康德哲学及现代认识型的建构
福柯认为,在18世纪末西方的知识空间经历了一场剧烈的震颤,由表象所维持的知识秩序开始失去统一的合法性,图表所划定的同一与差异秩序也面临着崩溃的局面。这一切的发生均表明我们已经无法通过表象来完整地把握与描绘“物”,亦即“词”与“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认识型变革。在古典时代,表象对于物的完整描绘并不存在障碍,表象与物之间是相互显明的,在目光的浏览中,物对表象呈现为透明状态而无丝毫的晦涩。然而在18世纪末,物开始逃避表象而遁入不可见的深处,成为表象与目光无法触及的“物自体”。与此同时,古典时代的财富分析、自然史与普通语法各自开始向经济学、生物学以及语言学等现代学科形态转换。这些学科的自我建构并不依赖于表象所整理出来的图表与秩序——这些更多的是由视觉所主导的外部形态描绘,而是隐藏在表象之外、物之深处的劳动、生命与语法。因此,在现代时期,使得财富分析成为可能的,并不是古典时期的“被表象的欲望对象”,而是不可被还原为表象的“抽象时间”,即现代经济学上的“劳动”;我们对自然的描绘与分析,不再依据表象所呈现的自然诸要素,而是自然内部固有的“关系构造”,即现代生物学上的“生命功能”;而使得语言分析得以成立的,不再是“语言表象诸表象的方式”,而是语言的“内在结构”,即现代语言学上的“语法”*[法]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10页。。毫无疑问,无论是劳动、生命还是语法,它们都逃避着我们的目光而变得不可见,福柯将它们称为“先验物”(transcendantaux)。由此,“词”与“物”的关系由表象的平面模式向“经验—先验”、“可见—不可见”的深度模式转换,并且在这一深度模式中,先验成为经验、不可见者成为可见者得以被表象与呈现的前提与条件。正是在这些二元分立所拉开的间距之中,现代知识得以被复合与生产出来。福柯将这种转换称之为“知识基本形式”的变更,亦即古典时期的以“表象”为核心的古典认识型向现代时期以“先验”为核心的现代认识型的转变。
可以看到,18世纪末的现代认识模式成型的关键在于绕开表象而去询问表象得以可能的根据与条件。康德在1787年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处理知识有效性的问题时,选择了同样的路径。与传统观念学将所有知识安放在表象空间并且通过表象的分解与组合来阐释知识的形成不同,康德所要询问的是两个逻辑表象得以联结的可能与条件问题。前者是一个纯粹的分析问题,而后者却涉及到表象与表象之间的综合问题。对于此一问题的解决,康德没有直接诉诸于表象,转而去确定表象的界限、基础与权利。同样,康德没有将知识的有效性的担保设定为表象的经验性给予,而是以先验范畴这一不可见的知性形式与结构作为知识秩序得以可能的根本保障。因此,在福柯的分析中,生物学、经济学与语言学等现代学科的自我建构模式与康德的哲学论证模式若合符节,康德的批判哲学成为现代认识型的哲学陈述。
“经验-先验”的知识建构模式背后所隐含的对权利与根据的探寻,实际上亦是对限定与边界的考察,现代认识型与康德哲学更为深刻的沟通其实在于二者都遵循了有限性原则,福柯在《词与物》的前身《康德实用人类学导论》中即已指明*Michel Foucault: Introduction to Kant’s Anthropology. Los Angeles: Semiotext(e),2008,p.117.。康德批判哲学产生的基本语境即是传统形而上学的破产。传统形而上学的无限视角所带来的反而是其在哲学与科学领域的全面失信。康德的基本哲学策略即是放弃这种“无所不能”,转而确定每一领域自身的边界,并且为每一领域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在这起作用的是深刻的自我限制原则。自我设限即为自我命令与立法,因此其自身的合法性不假外求,而是在自身的有限性中进行自我奠基:知识的有效性恰恰是在折回现象学领域中才得到辩护;道德与自由也只有在“知识所让出的地盘”中才得以重获尊严;对于判断力,康德同样也只在反思领域才谨慎地赋予其以先天原则。“折回自身”与“奠基自身”的限制性原则同样在现代学科的建构中起着主导作用,福柯认为,生物学、经济学及语言学的实证性同样也是奠基于人本身的有限性,亦即人必有一死的肉体、人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以及人永远无法掌握的时间*[法]福柯:《词与物》,第410页。。正是这些人自身的匮乏与有限驱动着现代学科不断地自我建构与探寻。在康德哲学与现代认识型的建构中,无论是折回“有限自身”,还是将立论的基础与根据立于有限自身,其所凸显的都是主体自身。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深刻感受到康德哲学与现代认识型的人类学意涵:主体成为了哲学思考的中心与视点,并且正是从主体知、情、意这些“广义的认知能力”的区隔与彼此限制出发,现代哲学与学科的研究领域才得以分配。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主体性原则同时也是一种有限性及人类学原则,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哲学与文化思考的“三位一体模式”。
二、文学的“僭越—界限”与人的“非思—外部”
以限定性为核心原则的“经验—先验”的认知运作模式可以概括为“我思—有限”的认知原则。在现代哲学语境中,“我思”是有限范围内的“我思”,同时有限亦因“我思”而得以可能。缺乏有限性的设定,则会使“我思”变得无效;若无“我思”的推定,则有限性亦不能建立,因为所呈现的将是一个无边界的完全裸露的物性世界。“我思”与“有限”共同规定了现代文化中人的存在模式及对人的思考方式。但从福柯的考古学的立场来看,这两条原则并非如自身所宣称的那般清晰与坚固,看似自足的“我思—有限”之下,其实潜藏着一个“非思—外部”基础。福柯认为,在现代认识型对“人”的思考中,并不能从“我思”推出对“我在”的笛卡尔式的肯定。“我思”总是要绕经“先验场域”才能确立自身的合法性,进而才能推定存在的肯定性。表面上看,这一确认是由“先验自我意识”的综合功能给出的,属于“我思”的范围,但康德始终强调“自在之物”在经验性材料给予中的“自因”作用。这一“未被言明之物”在我思开始之前即已经起着奠基作用。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认为所有寻求先天原则的行为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二律背反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在为“有条件者”寻求“无条件”的存在,而只有“超感性基底”(“自在之物”的另一个身份)的出场才能摆脱这种矛盾,所有的先天原则最后都以依存“超感性基底”的方式来求得自身的绝对有效性*[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因此,“自在之物”远不是一种“放逐”状态,而恰恰是使得先天原则得以可能的奠基。福柯将这种状态描绘为“我思”旁边永远潜伏着“非思”,“我思”始终面临着“未思之物”:“语法”这一“先验物”处于话语之深处并不断地向我们的目光与意识退隐,“语法”构成了主体无法企及的“大他者”,语言规则于人之言说就犹如不断后撤的地平线,主体始终不能将“我说”等同于“语言”。以此类推,我们始终无法将“我劳作”等同于“劳动”这一抽象时间,以及将“我活着”等同于“生命”这一机体功能,它们于主体而言都是有待实现之物、未尽之物,并不完全向“我思”的表象显明。我思的表象想要对其实现完全的把握只是一种徒劳,因为总有源源不断的非思之物向意识涌来。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认识型不能脱离“劳动”、“语法”、“生命”这些“先验物”来限定“人—主体”,它们本身是人之型构的一端。因此,“我思”不得不与“非思”相伴,这甚至成为其根本的宿命:“相关于人,非思就是他者(l’ Autre):兄弟般的和孪生的他者。”*[法]福柯:《词与物》,第425页。现代的“我思”并不导向“我在”的确证,开启“我思”即意味着永不停止去同化、意识化“非思之物”,这甚至成为现代“我思”运作的根本机制:“如不把思的存在一直分叉至那不进行思的一切的惰性骨架,那么,现代我思就不能把物的整个存在归并到思。”*[法]福柯:《词与物》,第422页。在现代的哲学思考中,黑格尔现象学中面对自为(Für sich)的自在(An sich),叔本华哲学中的无意识(Unbewusste),马克思唯物主义中的异化的人,胡塞尔哲学分析中的沉淀物,均是“非思”的替角*[法]福柯:《词与物》,第426页。。因此,“非思”成为了“我思”永远无法超越的外部,是“我思”未曾规定亦无法规定的无限。对于“我思”的有限性原则而言,“非思”的这种“外部”与“例外”,是其永远无法摆脱的“潜在僭越”:非思性的外部总是先于人而存在,成为现代文化思考人之存在方式无法亦不能抹去的背景:“它们起着先决基础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人将自身聚集并且回忆起自身,以此来获得他的真理。”*[法]福柯:《词与物》,第426页。对于以“我思-有限”作为立身原则的“人”而言,非思-外部无疑是其最为深刻的讽刺以及最为严峻的挑战,从“非思-外部”出发,距离“人之死”只有一步之遥。
由于主体形而上学在现代文化思考中的策源性地位,现代经验基本被“我思—有限”的经验所覆盖,“非思-外部”经验则被视为“疯狂”或“非理性”而不断地被边缘化。福柯认为,唯独在现代文学经验中,人的“非思-外部”这一黑暗物质成分才得以被检测出来。这是由产生于18世纪末的现代文学的独特自虐特征所决定的。现代文学既非透明的符号体系,亦非语言叠加而成的作品。文学在对“语言”与“作品”的拒绝与偏离中而摆明自身:其是围绕着语言的持续“摆荡”与“振动”。因此文学不可能如语言那般成为意义的载体,亦非作品那般成为言说主体的所在。文学与语言及作品都拉开了距离,仅朝向于自身而无任何指派,因此在本源上清空了意义并且消散了言说主体。任何传统意义上的言说与书写范式都不适用于对现代文学形态的阐释,某种程度上,现代文学以拒绝本质与意义的方式维持自身的缺席状态:“词语把我们引向了一种将会成为文学的永恒缺席的门槛。”*[法]福柯:《什么是文学》,尉光吉译,见《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重庆出版社2016年版,第87页。文学对语言秩序的拒绝,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对文学自身的拒绝;文学对语言的施虐最终指向的是对自己的暴力。福柯认为,自现代文学诞生以来文学给予自身的唯一使命恰恰是“刺杀文学”:“在使用文学语言的时候,拒绝实施或说出对文学系统的、彻底的谋杀以外的任何事情。”*[法]福柯:《什么是文学》,第88页。现代文学所有的言说都只是在重复俄狄浦斯与俄耳甫斯的命运:僭越与死亡*[法]福柯:《什么是文学》,第91页。。
现代的文学书写成为一种对界限的僭越行动,二者展开如禁止与引诱那般的对抗游戏:僭越无休止地逾越和再逾越界限,而界限则不断将僭越所撕裂的开口闭合并迅速将界限向前推移:“使得僭越再次回到那不可逾越的地平线上。”*[法]福柯:《福柯文选(一)》,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页。语言秩序成为文学的攻击目标,语言界限成为其操作的对象与空间。亵渎、重复、自我指涉、语言拼贴、取消修辞这样一些文学手法只有在此意义上才能得到完全的理解:即都指向于既有意义体系、叙事空间及言说主体的摧毁与谋杀。但无论是对语言意义的消散抑或是言说主体的取消,都是文学语言在“外部操作”的结果,而非置入任何“内部思考”所致。“内部思考”是在时间维度上的意义叙事,外部操作指向的空间维度上的语言布置。前者是意义的生成活动,而后者是对语言本身的操作及对既有语言规则的暴露。福柯认为,现代文学书写“等同于自己展开的外在性”*Michel Foucault: The Foucault Reader, Edited by Paul Rabinow, 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84,p.102.。
文学语言的界限操作、僭越冲动以及外部布置最终让主体重回临界状态、体验自身的界限所在。展开在其眼前的不再是自身形象的坚固而是可怖的深渊与黑暗。文学以对语言的极端运用而形成对人之存在与界限的探寻,人的“非思-外部”基底被裸露出来,文学的僭越经验所遭遇的恰恰是最为深刻的哲学问题。福柯认为:“从被体验和经历为语言之语言的内部,在其趋向于极点的可能性的游戏中,所显现出来的,就是人‘已终结’了,并且在能够达到任何可能的言语的顶峰时,人所到达的并不是他自身的心脏,而是那限制人的界限的边缘:在这个区域,死亡在游荡着,思想灭绝了,起源的允诺无限地退隐。”*[法]福柯:《词与物》,第501页。文学表达的僭越冲动及其对语言秩序的顽固对抗,成为先验人类学最为深刻的挑战。作为人立身根基的有限性最终成为了人之终结的契机。
三、 话语的事件分析及其康德先验人类学批判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对于现代思想中的人类学批判不再诉诸于文学经验中“界限”与“僭越”的相互纠缠与冒犯,而是转换为对话语本身存有的事件属性的考察。福柯能将独属于文学语言的僭越经验扩散至关于话语事件属性的分析,关键在于二者存在着深刻的关联:僭越作为对边界的迫出及对规则的打破,本身即是一场事件,或至少具有事件的质地。事件本身即代表了一种极端与特异状态。福柯认为,对既有叙事单位系统的清除,首先促成的即是“让某陈述的‘特异性’(singularité)即事件性重新回归该陈述”*[法]福柯:《福柯文选(二)》,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在福柯看来,无论是话语事件,抑或是其他事件,其最为核心的特质均是其本身的独一无二,亦即不能被划归于任何现存的秩序或体系。这种不能予以规定的特性并不表明特异性是一个缺乏内涵的空无,而恰恰表明其丰富性与可能性已经溢出现存体系所能涵盖的范围。以特异性为核心特征的事件本身即具备不断生成的可能性,据此,我们可以将“话语-事件”界定为话语不断地被唤起、重织、拓展、交叉的生成运动过程,其所展现的是话语在分配与布置中的无限可能性。福柯分别以话语的对象形成、句法类型(陈述方式)、语义要素(概念)、运作可能性(策略)四个方面对话语的配置规则进行描述与限定,但正如这不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共时性分析一样,话语的配置规则所指向的亦非一个规则的统一体,其所形成的乃是一个“差异与离散的控制系统”,“一个不可化约的多元性规则”*[法]福柯:《福柯文选(二)》,第68页。,意在揭示话语得以播散与生成的“话语空间”。
福柯对话语的事件性的考察具有明显的康德人类学批判向度,主要体现在:其一,将康德的“先验知识”作历史化理解。康德的先验人类学得以成立的最重要的前提是“先验”的超历史性。这种隔离与超越向度是其先天性的保证,并使其相对于经验而言处于优越地位。福柯对于话语的“先验性”理解的独特之处在于将其置于历史的运动之中,从而给予其历史的限定。福柯反复强调,话语的历史先验知识是一个处于时间中的可转换的扩散系统,呈现为一个拓扑学式的结构,具有事件容量;历史的先验知识并不是一个超越时空、凌驾个体经验之上的先验架构,它本身就处于话语的群落中,生长于话语的裂缝、交叉与替代之中。话语分析的目的并不是要穷尽话语,将言说的话语变成不再言说的“沉默的思想”。话语分析始终是在话语实践之中,始终具有话语状态。无论从哪个层面而言,福柯都否认话语具有康德意义上的先验属性;其二,将“经验—先验”的综合知识生产机制替换为“事件—事物”的话语知识布置模式。福柯认为,由话语的事件分析所建立的话语实证类型,展现的是话语得以生成的条件状况,但这并非话语存在状况的全部揭示。福柯认为话语并非孤立的超验“主权”,而是与非话语的其他实践紧密相联,比如与技术、经济、社会、政治等实践存在诸多关联,它们是话语的使用范围及得以展开的所在。它们虽然是“非话语实践”,但是最后都以话语为承载或介质,因而在陈述层面构成了话语系统的“事物”部分,而此部分与表明话语“出现的条件与范围”的“事件”部分,一起构成了福柯所言的“档案”:“我想起了档案(archives)这个词,这不是指某种文明或使这种文明免于湮灭无闻的遗迹所保存下来的总体文本,而是一系列规则,它们在文化中,决定着某些陈述是出现还是消失,决定着它们的持存和它们的解体,决定着它们作为事件和事物的悖论性存在。”*[法]福柯:《福柯文选(二)》,第54页。在此,康德意义上的以先验主体的统一功能在“经验—先验”这一间距进行协调与运作而产生的“综合知识”,被福柯代之以在“事物-事件”的悖论性中交织与渗透而成的“话语知识”。只不过,前者充满了张力,需要先验人类学的设定方能维持与成立,而后者却是一个具备生成、衍化与扩散性质的话语集群,其后并不存在一个先验人类学的“理想视域”。
福柯的话语事件分析对康德先验人类学体系最为致命的打击在于引进了“非连续性”的叙事模式。事件之所以在线性叙事中隐匿不彰,是因为事件本身代表了偶然与断裂,传统的连贯叙述模式无法将其归纳到既有的叙事秩序,无法愈合由事件的非连续性所带来的“开口”。对于传统的线性叙事而言,非连续性被视为残缺乃至危险,那些以分散的“事件”形式出现的“决策、偶然事件、创举、发明”,是“被回避、被抑制、被消除”的对象。线性叙事与先验主体有着密切的关联。福柯认为在“思想、知识、文学”不断增加断裂的今天,具有普遍与整体性质的“线性历史”成为了“辩证秩序”与“意识哲学”最后的避难所。线性叙事与先验主体形成了某种联盟:线性叙事为先验主体提供蛰居之所,而先验主体则以其超时间的视角来整和历史事件,为线性叙事的连贯性与有效性提供绝对担保。线性史观将康德批判哲学中的“我思必然是我思”化身为历史叙事中的“我说必然是我说”,先验我思主体被代之以先验叙事主体*[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页。。福柯重新激活历史的事件属性,将断裂与非连续性重新带回历史现场,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关于历史的叙事,使得线性叙事被彻底消解,对于先验叙事主体亦是釜底抽薪。
四、从“话语—事件”到“批判—启蒙”
在现代文化中,启蒙叙事成为最重要的线性叙事。启蒙叙事给出了人类文明演进的路线与方案,描绘了文明战胜野蛮、先进摆脱落后的辩证图景。所有的历史事件与历史时刻都只有整合进启蒙这一连续与整体的叙事之中才能被赋予意义。启蒙的理想即是要建立一个关于人类进化的无所不包的体系:“各式各样的形式被简化为状态和序列,历史被简化为事实,事物被简化为物质。”*[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4页。启蒙叙事成为了先验主体与线性叙事的合作典范:先验主体为启蒙思想家提供了形式逻辑这一计算世界的公式,具有先验性质的普遍秩序成为启蒙叙事的终极参照,先验主体则寓居于启蒙这一超级线性叙事之中。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福柯将话语分析的使命定位为“剥离思想史的一切先验的自我欣赏成分”,以此来“挽回我们在一个多半世纪中所失掉的东西”*[法]福柯:《知识考古学》,第225页。,因为距离福柯所在年代(1960年代)一个多半世纪之前的正是康德所在的启蒙时期(1780年代)。
启蒙毫无疑问是一场发生于历史时空中的“事件”,其表明了我们自身对当下时态的关注并且勇于自我革新,代表了一种不屈服于权威的批判态度。福柯认为,康德将这种从宗教改革精神中生长出来的“批判态度”改写成为“批判问题”,二者差异在于,前者是一个需要反抗勇气的具有实践与伦理学维度的问题,而后者则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一旦将“批判”认识论化之后,那么批判的责任就转变为“对认识的认识”,批判的锋芒也就只限于认识论范围了。弗雷里德·格霍(Fédéric Gros)认为,康德的此种做法实际上是将“拒绝服从”这种抵抗姿态进行了打压,使得这一“非智性姿态”被按照先验哲学的要求归纳到知性的轨道,其结果即是:“‘如何不被如此这般地治理?’的提问完全被另一问题‘我可以认识什么?’所掩盖。”*[法]弗雷里德·格霍:《福柯考》,何乏笔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4-165页。自此之后,“认知的历史模式之合法性研究”这一模式主导了对启蒙的分析,这一分析程序的关键在于建立了理性对理性本身的审查模式(康德意义上的“理性批判”既是从理性出发来批判,亦是对理性本身的批判)。此一理性审查,所暗含的实则是监督与被监督、治理与被治理的威权模式,因此产生着权力效应。而居于理性法庭之上的则是那个大写的先验主体,其成为此一审查机制的制高点与发令者:“自我一旦被提升为先验主体和逻辑主体,它就会构成理性的参照点和行动的决定性因素。”*[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第23页。当合法性论证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论证模式之时,也正是大规模的治理到来之际。治理开始全面渗透到公共空间、共同体、医疗、教育、家庭乃至思维的方方面面。知识与权力开始互相渗透为一个织体,任何的知识分析都难以摆脱权力的纠缠,而权力本身也借由先验主体与知识进行“真理政治学”的统治。
福柯认为,我们只有重新将启蒙“事件化”,才能绕开知识与权力所布设的陷阱。福柯的“事件化”勘探从考古学与谱系学两个方向进行:考古学探查即发掘知识与权力相互替代与支持的知识—权力网络,辨别“强制机制”与“知识要素”之间的关系与联络,在其被接受的历史语境中具体把握与分析知识与权力。因而考古学分析最终识别的并非是一般与普遍的知识与权力,而是具有限制性与实证性的特殊知识与特殊权力机制。谱系学分析则是对考古学所析出的实证性进行独特性分析,试图恢复该实证性得以出现的条件,而不是将其纳入某一整体与序列,从而否认其原初性与先验性。因此,无论是考古学分析抑或谱系学考察,均是从事件的特异性与实证性出发。据此,我们可将启蒙的事件化处理概括为展开对启蒙的历史条件、界限与排斥状况的描述,在历史的时空与语境中进行重新把握,进而确立启蒙的“实证性”*[法]福柯:《福柯文选(二)》,第196-197页。。福柯这种对于启蒙的处理方式,与对话语分析的处理方式有诸多吻合之处,甚至可以说,“话语—事件”的描述为福柯的启蒙事件分析提供了一个基本参照。
当我们以启蒙事件的特异性及实证性来质疑启蒙合法性论证的有效性之时,其实也在质疑着那一绝对与唯一的先验主体的权力效应。因为启蒙的合法性赋值正是由先验主体来执行的。因此,我们不应仅仅停留在对启蒙的历史—哲学的考察与勘探,同时也应转向对于作为主体的自身的批判。但这一批判不再是康德式的确立先验人类学的合理性内核,而是去发现主体存在的界限与条件,并进而探索超越这一界限的可能性,亦即,这里所探索的并非是一种主体与权力相互支撑的模式,而是自我之自由得以可能的策略。福柯认为,我们不是在“主题性探索”或“理性形式”的分析中来激活我们自身的可能性维度,而是在“使我们所思、所说、所做都作为历史事件来得到陈述的那些话语”中来确认自身的“持久创造原则”*[法]福柯:《福柯集》,杜小真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539页。,福柯认为自身对自身的历史—批判调查的特殊性在于,它们永远与确立的话语载体有关*[法]福柯:《福柯集》,第542页。,“批判—启蒙”的问题最终又回到“话语—事件”的分析之中。
五、结语
综上,在文学时期与《词与物》中,产生自现代文学的僭越与死亡经验,成为福柯重审现代认识型之“非思—外部”性质的重要开口;在《知识考古学》中,话语则因其“事件”属性而成为福柯反思先验人类学的理论资源。但在目前的国内研究中,福柯话语理论背后的哲学意图基本被忽略。诚如以上论证所示,福柯话语理论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甚至可以说,福柯在其关于话语讨论的初始即有着明确的哲学与思想史指向,即对于康德先验人类学及其所主导的现代叙事的反思与批判。这一哲学与思想史意图在由文学的“僭越”向话语的“事件”的扩散过程中得到完整的呈现。福柯正是通过不断恢复“陈述”与“话语”的事件样态,来抵抗传统思想史透明、还原与线性的叙事,并以此摆脱康德先验人类学的意向规制。这为我们重新阐释康德人类学视野中的美学提供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