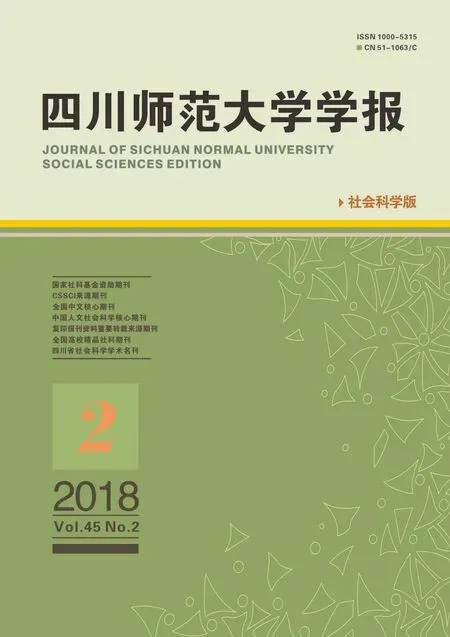《天子游猎赋》的文本书写、知识来源与思想传播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从口传、甲骨、金石、简帛到纸张、电子载体,只要具备了声音、文字、图像的任何一种形式,就会将读者纳入其所要表述的文本世界,最终使得后世研究者纠结于故事真伪、文字异同等问题,而较少关注在此基础之上形成、存在于文本之外的“文化”、“文明”层次的事情。本文主要谈两个问题:第一,文本之“内”的文字抄撰与流变;第二,文本之外的“文化”、“文明”的形成与传播。
汉初赋作,在文本形成过程中,会涉及到文本书写、文本改编以及赋家的知识来源、赋作体现的思想传递问题。本文即以《史记》记载的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例,展开讨论。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司马相如此赋,《史记》、《汉书》的记载明确称为游梁时的“子虚之赋”与后来专门献给汉武帝的“天子游猎赋”(《汉书》称为“天子游猎之赋”),《文选》析为《子虚赋》、《上林赋》两篇。为方便研究,今从《史记》、《汉书》旧题,统一称此赋为《天子游猎赋》。
一 文本之“内”:作品的多次改编与加工
一部(篇)文学作品自其产生进入流传渠道,其文字并非完全固定下来一字不易,而是有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改编、加工或重写。这个工作的实施者,可能是作者本人,也可能是其同时代或后世之人。这是古今文学作品的一个普遍规律。现以《史记》所载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例进行说明。
第一,同时代人改。
《史记》、《汉书》、《文选》对此赋题名、分篇之差异性载录,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史记》、《汉书》收录的此篇《天子游猎赋》完全可以分为两篇独立定名。问题是,被《文选》分出来的《子虚赋》,与司马相如游梁时的《子虚之赋》是一种什么关系?刘跃进先生以为,司马相如游梁时的《子虚赋》,是《天子游猎赋》的初稿;《上林赋》即在此基础上加工润色而成,故可称为《子虚上林赋》[1]72。此说有合理之处。
据此赋内容,可知以下四点。其一,从主旨上看,司马相如游梁之《子虚之赋》,主要谈诸侯园囿;他为汉武帝所写的《天子游猎赋》,以“天子”事上为中心。《史记》、《汉书》所记此赋,上半部分谈楚、齐诸侯田猎事,下半部分谈天子游猎事,确实符合司马相如所言“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之言[2]3640。其二,从内容上看,司马相如本来所言之“为天子游猎赋”,其内容实际上包括天子、诸侯游猎事,并非单纯的“天子游猎”。此据司马迁所言“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2]3640,“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2]3689可知。其三,从篇章上看,最初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实际上包括司马相如游梁时的《子虚之赋》全篇(即后来《文选》定名的《子虚赋》,但内容并非司马相如最初的全文),以及他后来续写、《文选》定名的《上林赋》。也就是说,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实际上是在他游梁所作之《子虚赋》基础上续写的。其四,《史记》、《汉书》所录《天子游猎赋》,亦非司马相如最初原文,而是司马迁根据时代需要进行了删汰。所以他说:“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2]3689司马迁所“删”者,当为那些“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之“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的内容。然而,《索隐》引颜游秦之说,司马迁所言“删要”的意思,乃是“不取其夸奢靡丽之论,唯取终篇归于正道耳”[2]3689。颜师古从之,谓:“非谓削除其词也,而说者便谓此赋已经史家刊剟,失其意矣。”[3]2576大、小颜之说,仅为推测,其实并无版本依据。据司马迁“删取其要”之意,笔者以为,司马迁收此赋时,当因其篇幅过大,已经有所删削。
由此我们认识到,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在同时代因为时代观念问题,“非义理所尚”,已经被其他收录者所删汰。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天子游猎赋》,即《史记》所载之文,删汰之前的全文究竟什么规模,因资料缺乏,已经无法得知。
第二,东汉班固及其此前人改。
《史记》形成之后,其版本文字多有变化,其中的《天子游猎赋》亦受到影响。有些文字变化,显然是班固《汉书》之前的事。而班固收录此文,或又有改易;至唐颜师古注《汉书》,则又有变化。
例一:
《史记》:齐王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2]3641
《汉书》:齐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田。[3]2534
《文选》(胡刻本,后同):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畋。[4]119
《史记》:“齐王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畋。”其中“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五臣注本《文选》同《史记》[5]卷四。《汉书》、李善注本《文选》作“悉发车骑与使者”。李善注《文选》曰:“本或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非也。”[4]119李善注《文选》,多据《汉书》正文字,此处所言“本或云”,显然针对的是当时所见其他版本之《文选》,而非《史记》中的赋文。据此可知,李善《文选》注本文字,乃据《汉书》(或与《汉书》文字相同的其他文本),无他本《文选》“悉发”下“境内之士备”、“车骑”下“之众”数字,且李善注并未参用《史记》所载之赋文。《汉书》与《史记》录此赋之文字差异,应该是班固或此前人删改所致。
例二:
《史记》:仆乐齐王……[2]3641
《汉书》:仆乐王……[3]2534
《文选》:仆乐齐王……[4]119
此处《史记》、《文选》同,《汉书》异于二者。五臣注本同李善注本。这说明《文选》版本并未完全采用《汉书》文本的文字。如果《史记》文本的文字并非唐人所改,则《汉书》表述与《史记》的差异,必为班固或其前人所改。
例三:
《史记》: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射干……[2]3642
《汉书》: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3]2535
《文选》: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4]120
《史记》所言“蕙圃衡兰,芷若射干”,《文选》五臣注本同《史记》[5]卷四;《汉书》、《文选》作“蕙圃,衡兰芷若”。李善注本从《汉书》说,而五臣注本所用文字与《汉书》不同,证明当时对此有不同说法。梁玉绳以为《史记》“射干”为流俗所增;而又引《学林》之说,以为“此段皆四字一句,于文则顺,于韵则叶,《汉书》去之,遂不成句法”[6]1414。据《文选》五臣注本有“射干”推测,《史记》文本必非后人妄增;又据《汉书》所载《天子游猎赋》此句前、后文“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珉昆吾”,“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阤靡”,“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柟豫章”[3]2535,皆四字句看,《史记》有“射干”为是。《史记》与《汉书》比较,前者为“古”,后者为“今”,李善注本从《汉书》,不从《史记》,是厚今薄古。据此推测,《汉书》阙“射干”,当为班固或其后人所删。
第三,东汉至唐历代读者所改。
东汉以后,尤其是唐人注《史记》、《汉书》、《文选》,多信《汉书》之说,而对《史记》中的《天子游猎赋》文字多有改易。这一点,梁玉绳《史记志疑》、王念孙《读书杂志》皆有考证。
例一:
《史记》:射麋脚麟。[2]3641
《汉书》:射麋格麟。[3]2534
《文选》:射麋脚麟。[4]119
按:《史记》、《文选》“脚”,《汉书》作“格”。颜师古注《汉书》曰:“格字或作脚,言持引其脚也。”[3]2535这说明颜师古看到的《汉书》文本有作“脚”的情况。梁玉绳怀疑《史记》文字未必是当时原文,亦或后人改易,故以为当从《汉书》颜师古校定之文[6]1414。然从颜师古看到当时《汉书》文本有“脚”者看,《史记》文字未必经人改易,不过颜师古采取了其中的一种说法而已。由此可知,《汉书》文本中的《天子游猎赋》之“格”字,必班固之后、颜师古之前人所改。
例二:
《史记》:又恶足以言其外泽者乎![2]3642
《汉书》:又乌足以言其外泽乎?[3]2534
《文选》:又焉足以言其外泽乎?[4]119
按:《史记》“恶”,《汉书》作“乌”,《文选》作“焉”。“恶”,疑《史记》本如此。《史记·苏秦列传》有“恶足以为塞”[2]2752,知《史记》有此用法。
“泽”下,《史记》有“者”字,《汉书》、《文选》无,而五臣注本有“者”字[5]卷四。五臣注本的说法未知何据,然由此知《文选》李善注本从《汉书》本。据常理,《史记》文本不可能据五臣注本回改文字,则《史记》有“者”字是。《汉书》文字乃班固或其后人改,唐人从之;与五臣注本文字不同的李善注本,其说或亦有所据。
例三:
《史记》:诸蔗猼且。[2]3642
《汉书》:诸柘巴且。[3]2535
《文选》:诸柘巴苴。[4]120
“诸蔗”,甘蔗;“猼且”或“巴且”,芭蕉。此处乃读音不同所致,疑“猼”乃西汉时期西南方人读音;“巴”乃东汉以后北方人读音。梁玉绳以为《汉书》、《文选》之文乃后人妄改[6]1414。
以上诸例说明,一篇作品,乃至一部作品在形成之后,其文字必然经过同时代人、后世历代整理者的多次改易。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不一而足。但这足以使我们认识到,文本之“内”的抄撰、流变情况,非常复杂。我们在进入文本,研究其中的版本文字差异之时,有时候只能根据个人学力、学识做出一个符合个人学术观点的判断,但这并非一定就是最佳定案,只能算是一个符合研究者本人或者其所在时代学术认识的结论。就此而言,古书版本校勘,是一项非常艰辛而困难重重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时候不得不需要跳出“文本”,考察文本之“外”的学术情形:即文本形成之后,在接受与传播领域带来的文化、文明交流。
二 文本之“外”:作为语言交流中介的作品
据称扬雄有一部小学著作《方言》,介绍了汉代不同地域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称呼。此书一个特点,就是将汉代东南西北不同地区的方言纳入进来,近似于一部字典。多数文字,有利于用来解读汉赋作品。
事实上,汉赋作品,大多使用了各地方言。例如《汉书》所载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中,有“下属江河”,注引文颖曰:“南方无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谓之河,诗赋通方言耳。”[3]2536司马相如此赋中,从南方的楚使子虚口中道出北方之语,与其说是子虚通北语,毋宁说是汉初赋作中已经有南北方言融合的趋势,因此文颖称“诗赋通方言”。
按照史书记载,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作于游梁之时,后来的《上林赋》作于长安,但二者不仅皆有汉代各地方言,而且多有域外之语。尤其是《上林赋》,作为皇家园林,体现了当时东南西北、域内域外广泛的联系,故《文选》注引晋灼之语曰:“此虽赋上林,博引异方珍奇,不系于一也。”[4]126
(一)域内
司马相如此赋中的某些称谓,体现了域内四方的密切联系。
1.境内四方结合之语
(1)《史记》:魚 亙魚 瞢螹离。[2]3658
《汉书》作“魚 亙魚 瞢渐离”[3]2548,《文选》作“魚 亙魚 瞢渐离”[4]124。
《史记正义》引李奇曰:“周洛曰鲔,蜀曰魚 亙魚 瞢。出巩山穴中,三月溯河上,能度龙门之限,则为龙矣。”[2]2662
“魚 亙魚 瞢”,乃北方之无是公,将南方蜀地之方言用于北方。
(2)卢橘夏孰,黄甘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郁棣,榙木 沓荔枝,罗乎后宫,列乎北园。[2]3671
《汉书》、《文选》文字与此稍异。
“卢橘夏孰”,《文选》注引应劭曰:“《伊尹书》曰: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卢橘夏熟。”[4]126箕山,今河南登封、山东鄄城各有箕山,知此说属于北方无疑。
“黄甘橙楱”,《文选》注引郭璞曰:“黄甘,橘属而味精。楱,亦橘之类也。”[4]126引张揖曰:“楱,小橘也,出武陵。”[4]126武陵在长江以南。
“枇杷”,《文选》注引张揖曰:“枇杷,似斛树,长叶,子如杏。”[4]126南北地区皆有。
“楟奈”,《史记索隐》引张揖曰:“楟奈,山梨也。”[2]3672引司马彪云:“上党谓之楟奈。”[2]3672知此为北方之物。
“梬枣杨梅”,《文选》注引张揖曰:“杨梅,其实似縠子而有核,其味酸,出江南也。”[4]126知此为江南之物。
“樱桃蒲陶”,“蒲陶”,即今之葡萄,原产于西域,一般认为张骞出使西域后传入中国[7]45,但或者也有其他更早的传入渠道。
“榙遝荔枝”,《文选》作“答遝离支”[4]126,《文选》注引张揖曰:“答遝,似李,出蜀。”[4]126引晋灼曰:“离支,大如鸡子,皮粗,剥去皮,肌如鸡子中黄,味甘多酢少。”[4]126二者皆南方之物。
在此,司马相如是将南方之物与北方之物、西南之物与东南之物甚至域外之物并列言之。司马相如赋作于北方,除了说明梁园确实有此类植物,还说明南方对此类植物的称呼亦被北方熟知。这说明,司马相如赴梁学赋以及后来作赋,不仅仅使用了他较为熟悉的蜀地方言,而且大量使用了当时中原、西北、江南地区熟悉的事物。
2.方言进入官方语言系统
(1)《史记》:行乎洲淤之浦。[2]3658
《文选》同《史记》,《汉书》“洲”作“州”[3]2458。
扬雄《方言》:“水中可居为洲。三辅谓之淤,蜀汉谓之嬖。”[8]78
司马相如此处将“洲淤”连言,是合方言为新词。如果将“洲”视作官话,那么三辅之“淤”与之结合,无疑是靠近京城的三辅方言有进入官话的趋势。
(二)域外、域内结合之物
此处所言“域外”,主要指的是汉王朝统治区域以外的地区。
(1)《史记》:檗离朱杨。[2]3643
《文选》注:“张揖曰:檗,皮可染者。离,山梨也。郭璞曰:朱杨,赤茎柳也。善曰:盖山之国,东有树,赤皮干,名曰朱木杨柳也。”[4]120
《文选考异》:“注‘善曰盖山之国东有树’,袁本、茶陵本‘盖’上有‘有’字,无‘东’字。案:二本是也。此所引《大荒西经》文,依善例‘曰’下当有‘山海经曰’四字,二本仍皆脱。”[4]866今《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盖山之国。有树,赤皮支干,青叶,名曰朱木。”[9]413“朱木”后无“杨柳”二字。据文颖注,疑《山海经》旧文当作“朱杨”二字,“木”为“杨”之误,“柳”为衍文。
据司马相如赋,“朱杨”当为南方植物,而《山海经》则曰《大荒西经》之“盖山之国”有此木。“盖山之国”虽不明具体位置,相对于汉王朝而言,或本为域外之物。
此以域外、域内之语混用。
(2)《史记》: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2]3643
《文选》:“郭璞曰:‘蟃蜒,大兽,似狸,长百寻。貙,似狸而大。犴,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蟃,音万。’善曰:《山海经》曰:‘鸟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又曰:‘幽都之山,其上有玄豹。’郭璞曰:‘黑豹也。’”[4]120此处所言“白虎玄豹”,皆见于《山海经》,前者出《西山经》,后者出《海内经》。“鸟鼠同穴之山”,在邽山以西二百二十里处,《山海经》说:“渭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9]64此地即秦汉之首阳,西戎所居之地。“幽都之山”,在“北海之内”,《山海经》说:“黑水出焉。”[9]462疑在先秦时期小月氏国境内。
此上属于将域外之语用于域内。
(3)《史记》:兽则牜 庸旄貘犛。[2]3667
《汉书》作“其兽则庸旄貘犛”[3]2556,《文选》作“其兽则 犭 庸旄貘牦”[4]125。
《史记索隐》引张揖曰:“旄,旄牛,状如牛而四节生毛。貘,白豹也,似熊,庳脚锐头,骨无髓,食铜铁。音陌。犛音狸,又音茅,或以为猫牛。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毛可为拂是也。”[2]3668
《汉书》颜师古注:“庸牛即今之犎牛也。旄牛即今所谓偏牛者也。犛牛即今之猫牛者也。”[3]2556
“庸”,《汉书·西域传》:“罽宾国,……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玑、珊瑚、虏魄、璧流离。”[3]3884-3885“封牛”,即“犎牛”,知此当主要为域外之物。此以域外之物作为域内之语。
“旄牛”,颜师古以为是“偏牛”,即黄牛与牦牛杂交所产之牛。主要产于藏区,属汉王朝统治区外之物。
“貘”,《说文解字》:“貘,似熊而黄黑色,出蜀中。”[10]457知此乃蜀地之物。
“犛”,颜师古以为“今之猫牛”,同今之牦牛,“徼外”,即塞外、边外,知其亦汉王朝统治区外之物。
在此,司马相如将汉代蜀地及其与之接壤的吐蕃之物写入北方皇家园林赋中,体现了南北、东西、域内外密切的经济联系。而域外、域内四方之物进入汉赋作品,则又具有体现文化传播的意义。
三 《天子游猎赋》的知识来源与思想传播
如果按照《文选》分篇法,可以将《史记》中的《天子游猎赋》之上、下部分,分别称为《子虚赋》与《上林赋》。二者关于校猎的描写,却有雷同之处。
《子虚赋》子虚之言:
其上则有赤猿蠷蝚,鹓雏孔鸾,腾远射干。……于是乃相与獠于蕙圃,媻珊勃窣上金堤,揜翡翠,射鵕鸃,微矰出,纤缴施,弋白鹄,连鴐鹅,双鸧下,玄鹤加。[2]3643-3653
《上林赋》无是公之言:
然后扬节而上浮,陵惊风,历骇飚,乘虚无,与神俱,辚玄鹤,乱昆鸡。遒孔鸾,促鵕鸃,拂鹥鸟,捎凤皇,捷鸳雏,掩焦明。[2]3681
“翡翠”,据颜师古说,乃红羽、青羽之鸟[3]2534。
“孔鸾”,《史记集解》引郭璞曰:“孔,孔雀也。鸾,鸾鸟也。”[2]3648
“鵕鸃”,《汉书音义》以为似凤;司马彪以为即山鸡[2]3681。
“焦明”,《史记索隐》引张揖说,此乃似凤之西方之鸟[2]3681。
这段材料较有意思,所以列出来比较一下。子虚言“鹓雏孔鸾”,无是公即言“遒孔鸾”、“捷鸳雏”;子虚言“揜翡翠”,无是公即言“掩焦明”;子虚言“射鵕鸃”,无是公即言“促鵕鸃”。
这段相似度颇高的文字表述,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本来就是不同时期的二文拼接而成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此类异方珍奇,多非司马相如亲见之物,而是他在为文需要情况下的虚构之物。
但是,这种“事物虚构”,必然也有一定的“实物”做参照。从其学赋的背景看,应该有多重的知识来源。
首先,《天子游猎赋》中保存有大量蜀地事物,显然这些词汇来自他本人在蜀地时的学习与见闻。司马相如为蜀郡成都人,《史记》记载他:“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2]3637《史记索隐》称:“文翁遣相如受七经。”[2]3638这些记载,足以说明司马相如早年在蜀郡接受了很好的教育。
其次,《史记》又记载,“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2]3637。可以说,司马相如免官赴梁,遭受了一定的经济、政治损失,却为其学习辞赋写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梁王卒时,“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但他却是“以赀为郎”。他离开京城赴梁,主要是为了学习辞赋,所以《史记》说他离开的原因之一是“会景帝不好辞赋”[2]3637。问题是,司马相如赴梁,对其学习辞赋有何意义?由此处记载分析,可知两点:第一,司马相如从游“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为其了解东方齐地、江南吴地的语言奠定了基础;第二,司马相如的《子虚之赋》是在“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之后的产物,这说明他在梁地的这段时间基本上掌握了辞赋写作的技巧,并为其撰写辞赋储备了素材。
最后,司马相如之所以辞官赴梁,是因为梁地有不亚于京城的一切条件。据《汉书》记载:梁孝王藩国“多作兵弩弓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梁之侍中、郎、谒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亡异”[3]2208,2209,这或者是司马相如勇于辞官的外因。即如对学习辞赋较为有益的自然景物而言,梁孝王园囿绝对不亚于皇帝园囿。《汉书》记载梁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3]2208,其中珍奇动植物亦或不亚于京师,这也是司马相如能够熟知诸多动植物的重要原因。
解决了以上问题,我们就能明白,为何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包含着域内四方、四夷甚至域外等众多事物。这在思想、文化传播上给我们如下启示。
第一,汉初文化、文明的传播,与经济传播的速度一样,是非常迅速的。虽然有人考证,葡萄是张骞之后传入中国,但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提及葡萄,说明葡萄的传入可能不止西域一条途径,与蜀地接壤的西南方向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传入渠道。这样的话,作为经济作物传入的葡萄,进入汉初赋家作品,则具有了东西方思想、中外文明交流的意义。
第二,西汉统一之后,中国内地四方的语言、文字、文化的传播同样迅速。秦统一虽然短暂,但文字的统一,为内地人民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至汉初,这种交流的成果之一,就是各地方言或进入官方语言系统,或虽保留着本地方言称谓,但已经为各地人民所熟知。身在梁地的司马相如,非常娴熟自如地使用南北方言,即说明了这个问题。
由此我们想到一个问题:汉初赋作,之所以受到欢迎,除了能够体现汉王朝思想、文化的统一,还有利于上层贵族和各地人民了解其他地区珍奇异物和语言习惯,满足了人们对知识的学习欲望。
第三,进一步分析,从《天子游猎赋》体现的语言文字与事物的交流看,早期中国与域外文明交流的发达程度可能远超我们今天的想象。有人认为,商代鬼方、周代犬戎的驾马御车,就与中亚草原上的卡拉苏克人密切相关;今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有卡拉苏克晚期青铜器,说明可能有融入周文化的卡拉苏克人文明[11]48。这是一种非常大胆的推断。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司马相如时代汉王朝与中亚、南亚、西亚甚至西欧、北非存在着一定的文化、文明交流。
总之,一个文本形成之后,学术研究者关注的是如何商榷真伪,而普通民众关注的则是该文本所承载的文化思想及其社会价值。就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而言,后世文献学家关注的是其文本文字的正误,而文本阅读者则从中看到了知识的学习与思想的传递。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如何实现从史料(文献)进入文本,继而跳出文本,观察史料(文献)在文化、文明交流过程中产生的思想内涵,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可以说,清代乾嘉考据学派之前的中国学术,极少考虑文本内部存在的各种复杂性问题。即如明人印书多改字,并非他们无知,而是他们更看重文本承载的义理,而非单个文字的正讹。唐宋以前的经学、文学、史学,无不如此。这一点,需要我们在开展学术研究的时候,除了关注文本之内的“文字”,还要关注文本之外的“义理”。古代中国对文本的观念,并非后世乾嘉学派或疑古学派那般较真文字之真伪,而是更关注“义理”层面的传统建构问题。
[1]刘跃进.秦汉文史论丛[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2]司马迁.史记[M].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五臣注文选[M].影印本.台北: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1981.
[6]梁玉绳.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
[7]〔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8]周祖谟.方言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93.
[9]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0]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1]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