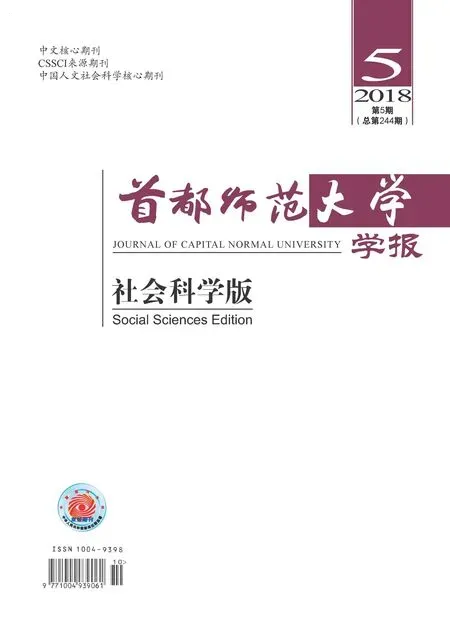浅谈全球史的史料问题
——以明清鼎革史的西文原始史料为中心
董少新
史料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和依据。按照与研究主题关系的亲疏,史料可大致分为原始史料(一手史料)和间接史料(二手史料)两类。原始史料因其与研究对象关系直接而更具可信性和说服力,故向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使用原始史料是科学的历史学研究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否充分使用原始史料也是评价一项研究成果优劣的标准之一。
那么,强调宏大叙事的全球史书写,是否也要以原始史料为基础呢?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回答。首先,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范式,以原始文献为基础也是全球史的一项基本要求。但另一方面,以宏大叙事为目标的全球史,研究对象涉及的空间往往会跨越多个区域,相关的文献也往往涉及很多语种。任何历史学家的能力都有局限,无法在有限的一生中掌握、阅读浩如烟海的、涉及大量语言的原始史料。我们目前看到的全球通史类著作,基本上是以各自的理论框架和视角来组织二手资料而成的,这实在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情。
全球史作为一种理论方法,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其他具体的历史问题研究中。这种以全球史的方法和视野考察具有全球性的事件、人物、社会组织、思想、商品、物种、疾病等具体历史内容的研究路径,我们可以称之为“全球专史”。以疾病史为例,天花、梅毒、鼠疫等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的疾病,是全球专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但一些普通的、传播范围有限的疾病,便很难进入全球史研究者的视野。研究天花的全球史,需要考察天花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情况、影响、治疗和预防,因此也就会涉及到各种语言文字写成的原始史料,史料的数量亦很庞大。对于任何研究者而言这仍是极大的挑战,但这一研究仍需以原始史料为主体和基础。其他如白银的全球流通、瓷器的全球流传、某种世界性宗教的传播等,都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发掘原始史料。
全球史以具有全球性质的那些人类历史内容为研究对象。这里的全球性体现在跨区域、跨国界的传播、交流、互动和影响等方面。一些对于国别史而言非常重要的内容,由于在全球性方面比较薄弱,而无法被纳入全球史的书写框架中。例如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三省六部制,便很难在全球史书写中被凸显,但位于中国历史边缘的明代海禁政策,却会受到全球史学者的更多关注。全球史和国别史是历史研究的两种不同路径,视角不同,研究侧重便有差异,每一种路径都会导致一些历史内容被凸显,另一些历史内容被遮蔽。
那么,在全球史兴盛的当下,我们如何合理处理全球史和国别史之间的关系呢?又该如何有效地把中国史放入全球史的脉络下加以研究?这些问题学界已有一些讨论,[注]可参考葛兆光:《在全球史潮流中,国别史还有意义吗?》,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全球史、区域史与国别史》,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9页;江湄:《重新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史”之中——全球史与中国史研究的新方向》,收入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6-181页。而本文尝试以一个一般认为是纯粹的中国史的个案——明清鼎革为中心,从西文原始文献的角度分析它的全球性,并将其作为纳中国史入全球史的一个示例;同时,本文也借此例略作展开,简单谈谈学界尚较少讨论的全球史的史料问题。
一、从全球史的视角看明清鼎革:必要性和可能性
明清鼎革是17世纪中国历史上的最重大事件。我们可以将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檄文并起兵反明作为明清鼎革的起点,把康熙元年(永历十六年,1662)南明永历朝覆灭视为明清鼎革的正式完成之年。这前后近半个世纪中,中国战火纷飞,社会动荡,政局变换频繁,百姓生灵涂炭,农民军推翻大明王朝,紧接着满清入关并最终完成了对大明王朝的征服,定鼎中原。百余年来,中外学界从明朝灭亡、清朝开国、明清战争、农民起义、南明史、郑成功家族等多个角度,已对明清鼎革做了深入研究。[注]关于明朝灭亡史,参见Albert Chan(陈纶绪), The Glory and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2.关于明清战争史,参见孙文良、李治亭:《明清战争史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关于明末农民战争史,参见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修订版),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关于南明史,参见顾诚:《南明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司徒琳:《南明史1644-1662》,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钱海岳:《南明史》十四册一百二十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关于清朝开国史,参见[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薄小莹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孟森:《满洲开国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但以往的研究囿于中国朝代兴替的范畴,基本上未超越国别史或双边关系史的研究框架。
然而,在东亚各国区域联系愈发密切、全球网络进一步发展的17世纪中期,发生于中国本土的这次重大政治变局必然会影响到中国周边,甚至引发全球关注。因此,我们有必要突破国别史的框架,将明清鼎革视为整个东亚的区域事件,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把它看做是当时的全球性事件。扩大研究视野不仅可以让我们观察到朝鲜、日本、越南、琉球、欧洲诸国对明清鼎革的态度,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关系的演变,以及明清鼎革对中国周边、亚洲和全球的影响,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在世界历史发展脉络中认识中国历史。
在国别史的框架下研究明清鼎革,则汉文和满文史料已基本能够满足需求,而如果在东亚区域的背景下研究明清鼎革,则必须扩大史料范围。即使是原始史料,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史料书写者的主观立场,正因为如此,我们便不难发现,有关明清鼎革的满文史料记录着征服者的雄心、胜利的凯歌以及统治的谋略,汉文史料记录下的则是血泪、悲愤、悔恨、哀怨与反省。同样,朝鲜、越南、日本、琉球方面的史料,也会各有自己的关注侧重和立场倾向,从各自的角度出发观察天朝上国的动荡和变局,并思考各自的处境和应对措施。
作为与后金政权接壤的明朝朝贡国,朝鲜很早便被卷入了明清战争中。在《朝鲜实录》和《燕行录》中,我们都可以读到大量有关明清鼎革的资料。[注]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有关明清鼎革的内容主要见于该书第8、9卷。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100册),《燕行录续编》(50册),东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2008年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关于朝鲜燕行使对明清鼎革的看法,参见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尤其是该书的前七章。这期间的越南正处于内战,而内战双方先后与明和清都有联系,南明弘光、隆武、永历诸朝也曾“屈尊”向越南求助,安南即曾派遣300舰船往广东协助抗清。我们可以在《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等越南文献中读到此类信息。[注][越南]吴士连等撰:《大越史记全书》,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其他如柳江居士《北史新刊全编》《北史总论》,邓春榜《通鉴辑览便读》,增田贡《清史揽要》,阮登选《史歌》,以及《大南实录》《钦定越史通鉴纲目》《邦交录》《历朝宪章类志》等,都有相关内容。相关研究参见牛军凯:《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2年版;陈文源、周亮:《明清之际中越关系的演变与抉择》,《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1期,第61-66页。明朝朝贡国琉球的文献《历代宝案》也保存着他们对明清鼎革的观察。[注]蔡铎等编:《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第一、二辑,厦门:鹭江出版社,2012、2015年版。相关研究参见杨彦杰:《明清之际的中琉关系》,《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18-23页。一海之隔的日本密切关注中国局势,而13世纪遭蒙古征伐的历史记忆,使日本对满清的动向更为敏感,德川幕府积极收集有关中国动态的情报,其中相当一部分“唐船风说书”被编入《华夷变态》中。[注]林春胜、林信笃编,浦廉一解说:《华夷变态》,东京:东方书店,1981年版。相关研究见石原道博:《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の研究》,东京:富山房出版株式会社,1945年版;孙文:《唐船风说:文献与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松浦章:《海外情報からみる東アジア―唐船風説書の世界》,大阪:清文堂,2009年版;年旭:《南明情报的日本传播及其东亚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0期),第90-102页。这些资料是我们从东亚视角研究明清鼎革的重要参考。
以往学界大都从双边关系的角度使用这些史料,但如果我们综合利用这些中国周边国家材料来从东亚视角研究明清鼎革,就会发现明清鼎革不仅仅是中国一国的历史事件,而且是17世纪整个东亚的重大事件,对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造成重大影响,也深刻地改变了东亚国际政治秩序。传统的以中国为政治、文化、经济和礼仪中心的国际秩序遭到削弱,朝鲜、日本和越南都曾一度宣称自己取代明朝中国而成为文化中心,成为中华的继承者。[注]参见王鑫磊:《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随槎录〉的史料价值 ———兼谈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意识”》,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19-29页。
同样,如果将西文资料引入明清鼎革史的研究,不仅在理解这场战争过程时多了一种考察的维度,而且有助于我们把这场发生于东亚近代早期的政治变革置于全球史的背景之中,探讨当时的西洋人对明清易代的看法,西洋各国在对华贸易和传教政策方面的调整和应对,以及东亚的政治变革信息传入欧洲后对其社会文化造成的影响。
在明清鼎革期间,曾有数十名西洋传教士传教于中国十余省份。他们不仅是这场大变局的见证者、亲历者,有些更是参与者。例如,曾经为明朝修订历法、置办火器的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见证了李自成攻陷北京和稍后清军入关及顺治皇帝登基,清朝看重其才能,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并负责铸造西洋火炮;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类思(Ludovico Buglio)和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跟随张献忠军队,目睹了其嗜血成性的残暴;耶稣会中国副省北部会长傅汎际(Francisco Furtado)、南部会长艾儒略(Julio Aleni)分别经历了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动荡;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亲历了清军征服浙江南部地区;葡萄牙耶稣会士何大化(Anónio de Gouvea)不仅目睹了自己一手创建的武昌传教驻地的覆灭,随后在福州也亲历了清军进入福建剿灭隆武政权,以及郑氏海上势力对福建沿海的侵扰;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曾德昭(lvaro Semedo)、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el Boym)和瞿纱微(Andreas Xavier Koffler)为南明诸政权效力,终无法反转危局,等等。更有多名耶稣会神父和修士,在兵荒马乱之中死于非命,如费乐德(João Rodrigues)、万密克(Michael Walta)、梅高(José Estevão de Almeida)、谢贵禄(Tranquillo Gracete)、陆有机(Manoel Gomes)等。
这些传教士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在如此动荡的局势下中国传教事业何去何从。这也是他们对中国局势极为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在华耶稣会士急需向欧洲教会上层及政、商各界汇报中国情况,以便上层对在华传教和贸易政策做出及时的调整。因此,这批在华传教士以欧洲文字撰写了大量的报告、书信和专书,向欧洲传达有关明清鼎革的各类信息。这批资料主要以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写成,有相当一部分留存至今,目前分藏于欧洲各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
由于语言工具的缺乏,加之资料收集难度大,在以往学界对明清战争史的研究中西文文献远远没有被充分利用,例如孙文良、李治亭《明清战争史略》仅有两处引用卫匡国《鞑靼战纪》中译本,司徒琳编的《明清之争:史学史与史料指南》[注]Lynn A. Struve, The Ming-Qing Conflict: A Historiography and Source Guide,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8.中也仅收入《鞑靼战纪》。对西文文献利用严重不足是导致明清鼎革史研究仍无法真正突破本土框架或双边关系框架并从全球史的角度考察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又有个别几部有关明清鼎革的传教士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如何高济先生重译卫匡国《鞑靼战纪》,以及新译帕莱福(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鞑靼征服中国史》、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鞑靼中国史》,[注]帕莱福:《鞑靼征服中国史》,鲁日满:《鞑靼中国史》,卫匡国:《鞑靼战纪》,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但更多的传教士文献仍未进入明清鼎革研究者的视野,对传教士相关文献的系统整理仍是空白,更没有出现系统利用西文文献研究明清战争史的论著。
二、有关明清鼎革的西文原始文献概览
现存有关明清鼎革的西文文献数量很多,可大致分为几类:1.传教士根据亲身经历所写的书信和报告;2.涉及明清鼎革的耶稣会中国年信;3.在华传教士撰写的有关明清鼎革的著作;4.在欧洲或美洲的教士根据在华传教士提供的资料编撰的作品;5.有关明清鼎革的欧洲文学作品。在这几类文献中,越是靠前的类型越具有原始文献的性质,而后面的类型往往以前面类型的文献为参考材料。因篇幅有限,本文仅选取部分第一类型的文献略加介绍,作为本文讨论的基础,其他几类文献我将另文阐述。
(1)郭纳爵《鞑靼入主中华纪》[注]Ignacio da Costa, Relação da entrada dos Tartaros nesta China, tomado do Imperio, Xén Sí, Octubro 30, 1645. BA(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下同), JA(《耶稣会士在亚洲》档案文献,下同), 49-V-13, ff. 267-300v.
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Ignácio da Costa, 1603-1666)约于1638-1650年间在陕西传教,1643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占西安时曾被抓获,后获准在西安继续传教。这份报告为葡萄牙文,写于陕西,篇幅长达68页,似从未出版过。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藏有18世纪抄本。郭纳爵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详细叙述了1644年10月至1645年10月期间,阿济格、吴三桂率领的清军在河南、陕西和山西一带追剿李自成农民军的经过,以及在此过程中西安、绛州、蒲州等传教住院和教务所受到的冲击。郭纳爵用第一人称叙述,而叙述的角度,则是站在农民军这一边来观察清军的到来与征服,所以对农民军的节节败退、李自成的穷途末路,有着十分细致的描写。从立场上看,郭纳爵称呼李自成及其农民军为匪徒,又在对鞑靼人的习俗描写中透露出鄙夷的心态。显然,作者的立场仍是倾向于刚刚灭亡不久的大明。郭纳爵作为明末农民起义的亲历者,还曾写过一份有关李自成农民军的长篇报告,但不知存世与否。
(2)安文思《四川省的毁灭及四川教会的丧失》[注]Gabriel de Magalhães, Relação da perda, e destruição da Prov(incia), e Christiandade, de Sú Chuén, e do que os P(adres) Luiz Buglio, e Gabriel de Magalhães passaram em seu cativo. 1649, Pekim. ARSI(罗马耶稣会档案馆), Jap.-Sin. (《和汉文献》)127, ff. 1-36.
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的这份报告,学界比较熟悉,因为19世纪后期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古洛东在上海徐家汇获得该报告的一个抄本,并以此为基础撰成《圣教入川记》(1918)一书。[注]古洛东:《圣教入川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安文思的这份报告根据其与利类思的亲身经历而成,揭露了张献忠的大量暴行,是对中文史料的重要补充。但该报告似未出版过,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是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和汉文献中的手稿。这份珍贵的报告与郭纳爵的报告一道,成为来华耶稣会士所记录的明末农民起义的最重要文献。[注]荷兰汉学家许理和曾以耶稣会士的文献研究利类思、安文思在张献忠朝廷中的活动,见Erik Zürcher, “In the Yellow Tiger’s Den: Buglio and Magalhães at the Court of Zhang Xianzong, 1644-1647,” in Monumenta Serica (《华裔学志》), Vol. 50 (2002), pp. 355-374.
(3)阿泽维多《1642-1647年间中国的战争、起义、皇帝之死以及鞑靼进入中国报告》[注]Manuel de Azevedo, Relação das guerras, e levantam.tos, que Ouve na China, morte do seu éperador, e entrada dos Tartaros nella, desdo anno da 1642 atê o de 1647, do Visitador da Prov.a de Jappão, E da Vice Prov.a da China. 关于这篇文献的研究,参见Davor Antonucci, “The ‘Eastern Tartars’ in Jesuit Sources: News from Visitor Manuel de Azevedo,”i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58, No. 1-2 (2015), pp. 117-132.
该文献现存至少四个葡萄牙文抄本。前三个抄本藏于耶稣会罗马档案馆(ARSI, Jap.-Sin.126, ff. 31-78, ff. 79-127; Jap.-Sin 123, ff. 181-207v),其中第一、第二为从澳门寄到罗马的原本;第四个抄本藏于葡萄牙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BA, JA, 49-V-13, ff. 1-49),为18世纪中叶根据耶稣会澳门档案馆藏抄本抄写而成。
编者阿泽维多(Manuel de Azevedo, 1581-1650)是葡萄牙耶稣会士,曾长期在东南亚和印度传教,1642年被任命为耶稣会日本和中国传教区巡按使,随即来到澳门,直至1650年在澳门去世。这期间正值中国政局最为动荡的几年,阿泽维多不时收到曾德昭、毕方济、傅汎际等在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发来的相关报告。这份写给耶稣会总长的报告,便是在这些报告的基础上整理、编纂而成的。报告中大量直接引录在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的报告,因此它具有一手文献的性质。
这份长达近100页的报告,内容的丰富性超过卫匡国的《鞑靼战纪》,包括中国社会的悲惨处境(其中引述了一部分安文思的四川报告);隆武朝的情况,提及了隆武皇帝写给毕方济的信;永历朝的情况,尤其是庞天寿在拥立永历登基过程中的作用;李成栋的归附,永历朝反清复明事业出现生机;曾德昭和瞿纱微前往肇庆永历帝的宫廷;满清部队攻陷广州,以及曾德昭的遭遇;满清部队攻占海南岛;澳门在这期间的遭遇。尤其重要的是,这份报告还包括了几个小节,讲述周边国家——日本、安南、交趾等——对满清入主中原的反应,使得该文献比其他此主题的文献更多了一种跨越国界的区域特征。
(4)《1647年中国消息》[注]Nuebas de los Reinos de China de ao de 1647. 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这一文献由四封写于1647年的书信组成,分别为耶稣会士聂伯多、艾儒略、何大化写给在马尼拉的同会会士的书信,以及隆武皇帝写给毕方济的书信。此四信均为西班牙文抄本,现藏于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这四封信虽然总共只有4页,但却极为重要,因为它们是隆武朝与天主教密切关系的直接证据,而且也向我们揭示了耶稣会通讯信息从福建传至马尼拉,再传到美洲和欧洲的渠道。以往学界对永历朝与天主教的关系多有研究,也发掘了一批原始文献(见下),而对弘光、隆武两朝与天主教的关系一直不甚清楚。这两个南明朝廷虽然存在时间短,但与天主教关系密切,其中尤其是毕方济一直在为南明王朝恢复中原四处奔走。这四封信是研究弘光、隆武两朝与天主教关系的一手文献。
(5)三种站在永历朝的立场来叙述的文献。这几份文献的内容多有重复,但详略各异。前两种未知作者名字,后一种为卜弥格所撰。它们所依据的都是瞿纱微、卜弥格等人的报告,而瞿纱微和卜弥格又是永历朝的追随者,所记内容以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为主,且其作者往往直接把卜弥格、瞿纱微等人的书信抄录其中,因此它们具有一手文献的性质。
(5.1)佚名《1648年中国皇后、太子及其他皇室成员皈依圣教记》[注]Anonymous, Relação da Conversão a nossa Sancta Fè da Rainha, & Principe da China, & de outras pessoas da casa Real, que se baptizarão o anno de 1648, Lisboa, 1650.
这份葡萄牙文文献于1650年在里斯本出版。1938年博克塞在《澳门与明朝的覆灭(1644-1652)》一书中,刊布了注释本,同时还发表了其他3种1651年的相关文献。[注]C. R. Boxer, A Cidade de Macau e a Queda da Dinastia Ming (1644-1652), Relações e Documentos Contemporaneos Reproduzidos, Anotados e Comentados, Macau: Escola Tipográfica do Orfanato, 1938.该文献分为六章:第一章为鞑靼军队进入中国之缘由及中国当时情势概况;第二章主要讲南明诸朝的建立以及传教士在南明的活动;第三章讲述皇后、皇太后等五位后宫的领洗(洗名分别为Anna, Helena, Julia, Maria, Agueda),以及皇子的诞生,其中抄录了皇太后致瞿纱微神父的一封短信。第四章讲述永历皇帝派遣使节至澳门,答谢天主赐福并招募葡兵,其中收录了永历皇帝颁给耶稣会巡按使神父、澳门兵头和委黎多的诏书;第五章讲述鞑靼人的一些习俗,以及他们想统治中国的原因;最后一章讲述鞑靼人对在华耶稣会士及中国教徒的态度。
(5.2)佚名《中华帝国及其天主教情势纪略》[注]Anonymous, Summa del Estado del Imperio de la China, y Christiandad del. Por las noticias que dan los Padres de la Compaia de Iesus, que residen en aquel Reino, hasta el ao de 1649. Impresso en Mexico: En la Imprenta de Juan Ruyz, Ao de 1650.
这份西班牙文文献于1650年在墨西哥出版。华裔耶稣会士陈纶绪曾根据马德里国家图书馆藏本(codex 2369)翻译成英文并详加注释,于1981-1983年发表于《华裔学志》,[注]Albert Chan, S. J., “A European Document on the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1644-1649),” in Monumenta Serica (35, 1981-1983), pp. 75-109.黄一农先生在研究焦琏时使用了陈纶绪的译本,并将其中部分内容翻译成中文。[注]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337页。
该文献的内容与前一文献有一些重复,但更为丰富和详细。它首先描述了天主教在华发展概况,尤其是汤若望在崇祯宫廷中的传教活动,包括《进呈书像》在宫廷传教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宫廷贵妇的领洗;接着叙述农民军攻陷北京,崇祯之死和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并提及汤若望受到满清重视,朝鲜使节拜访汤若望;也提及福建穆洋传教的多明我会士,还简要阐述了日本对中国剧变的反应,及荷兰、葡萄牙与日本关系。接下来,叙述了1647年鞑靼人攻陷福建,成为整个中国之主,以及隆武与毕方济的关系,这一部分抄录了隆武皇帝致毕方济的书信,与(4)中提及的隆武至毕方济书信为同一封,但文字上略有出入;接着叙述毕方济在广州的遭遇。再接下来,也是该文献的最重要部分,则是转录瞿纱微的报告,叙述人称也改为第一人称,讲述内容包括永历称帝、与绍武的矛盾,招募澳门葡兵,永历后宫的领洗,以及太子的出生与领洗过程。此处虽与前一文献多有重复,但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提及永历皇帝亲母马太后(洗名玛利亚)为“妃”(concubina),亦提及洗名为朱莉娅者为王太后之母,以及说永历公主之死是因为其非正室所生,因而遭天主所罚,而太子为正宫所生,因而受到恩宠。该文献最后讲述庞天寿、瞿纱微等奉命率团澳门之行,与前一文献亦大体相同。
(5.3)卜弥格《永历王室奉教纪略》[注]Michael Boym, Breve raconto de la conversione delIe Regine della Cina. Col battesimo del figlio primogenito dell’ Jmperatore. e dalteri progressi de la S. Fede in quel Regni, Havuto daI P. Michele Boim della Companhia de Giesu, 1657. BA, JA, 49-IV-61, ff. 326-336; 702-712.
卜弥格的这份报告,是他作为永历朝使节返回欧洲后所写的,所依据的是他本人以及瞿纱微在永历朝中传教的经历。我所掌握的文本为意大利文抄本,有两种,藏于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与前两份文献相比,所讲述的内容虽大略相同,但这份文献较为简略,抄本只有21页。该文献于1652年在欧洲出版,有法文版、拉丁文版、意大利文版、波兰文版乃至英文版,颇有一些影响。其中波兰文版翻译自法文版,近年出版的《卜弥格文集》中译本收入的这篇文献,即是从波兰文翻译而成的。[注]卜弥格:《卜弥格文集》,张振辉、张西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9-265页。
(6)[曾德昭]《鞑靼围困广州纪事》[注][Alvaro de Semedo] Relação do que se passou no cerco de Quantum pelos Tartaros; e do que os Padres obrarão, e padecerão nesse tempo, e quando se tomou, 1653. BA, JA, 49-V-61, ff. 252v-260; 668-675v.
这份葡萄牙文报告作于1653年末,有两个18世纪抄本,藏于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约16页的篇幅。虽然该文献没有署名,但是因为使用第一人称叙述,而且其中提到了毕方济、瞿纱微等神父,据此判断,作者应为当时亦身处广州的曾德昭。此报告主要叙述了鞑靼人攻陷广州的过程,以及这期间这几位深处广州战乱之中的西洋传教士的遭遇,其中包括毕方济的去世。该文献所述均为曾德昭之亲身经历,故尤为珍贵。
(7)努内斯《鞑靼进入海南岛纪事》[注]Joam Nunez, Relação da entrada dos Tartaros na grande Ilha do Háynán: As Guerras que tiverão com os Chinas naturais da Ilha, e dos grandes trabalhos, e perigos de vida que passaram os 4 P. P. que nella estavam pregando o S(an)to Evangelho.15 Dezembro 1649. ARSI, Jap.-Sin. 126, ff. 155-164v.
这份葡萄牙文手稿文献藏于耶稣会罗马档案馆和汉档案中,共计20页,完成于1649年12月15日。作者为葡萄牙耶稣会士努若翰(João Nunes, 1613-1659)。努若翰于1647年到达海南岛传教,亲历满清军队攻占海南岛。这份报告就是努若翰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其中详述了几位耶稣会士在战乱中的遭遇。该文献具有补充中文文献的价值。
(8)佚名《鞑靼汉军对澳门圣保禄学院的侮辱与亵渎》[注]Jnformação e relação das injurias e dezacatos que os Chinas atartazados fizerão à Jgreja e Religiozos do ColIegio de S. Paulo, em 17 de Agosto do anno de 1658. BA, JA, 49-V-3, ff. 199-203v.
满清攻占广州、控制广东之后,新的问题出现在澳门葡萄牙人面前。虽然澳门从支持南明转而向清朝投诚,[注]参见拙文:《明清鼎革之际的澳门》,《澳门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19-30页。但满清驻军却给澳门市民生活带来了侵扰。这份文献比较有趣,讲述的是鞑靼汉军骚扰在圣保禄教堂做弥撒的妇女教徒,以及由此引发的教堂神父与鞑靼汉军官员之间的矛盾。该文献为6页葡文手稿,作于1658年8月17日,藏于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
以上罗举的西文原始文献,并非全部,但已大致能够呈现其对明清鼎革史研究的重要性。这些原始文献虽然大都被寄回欧洲,但仅有少数被公开出版,因此被阅读的范围及其影响相对有限。然而,以这些西文原始文献为基础,产生出一系列“半原始”文献或二手文献,这些文献尽管在准确性、真实性方面可能不如西文原始文献,但影响力更大。
最直接使用这些西文原始文献的是耶稣会中国年信。17世纪来华传教的耶稣会每年都会向位于罗马的耶稣会总部发一份年度报告(Carta Annual年信)。[注]关于17世纪耶稣会中国年信,参见拙文:《17世纪来华耶稣会中国年报评介》,《历史档案》,2014年第4期,第128-132页。几乎每一份1618年至1662年间的耶稣会中国年信都包含有对明清鼎革期间重要军事、战争、政治、动乱等方面的介绍。如果将这些内容抽离出来,则可以大致构成一部传教士眼中的明清鼎革编年史。其中1643-1654年间的年信,记录的有关明清鼎革、明清战争内容尤其丰富。相较于卫匡国、鲁日满等耶稣会士有关明清战争的著述,耶稣会中国副省年报所涵盖的时段更长,内容更为全面,也更为详细,描述了很多细节和经过。从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正式入侵明朝开始,至萨尔浒之战、宁远之战、徐光启练兵、己巳之变、吴桥兵变、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清军入关、南明政权的抗争、郑氏政权的反清复明及其最后失败等内容,在耶稣会副省年报中都有大量描述,且对满汉研究资料具有补充意义。
来华耶稣会士的这些报告和书信,成为其他传教士相关著作的主要参考。这些著作有一些是来华耶稣会士撰写的,其中尤以卫匡国的《鞑靼战纪》[注]Martino Martini, 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in qua, quo pacto Tartari hac nostra aetate Sinicum Imperium inuaserint, ac ferè totum occuparin, narratur; eorumque mores breuiter describuntur cum figuris aeneis, Amsterdam, 1654.影响最大,在17世纪即有十余种欧语版本,[注]Henri Cordier, Biblioteheca Sinica, vol. 1, Paris, 1904, pp. 623-627.是欧洲人了解明清鼎革的最重要文本。其他如何大化《远方亚洲》相关章节,[注]Antonio de Gouvea, Asia Extrema, Segunda Parte, Livro 1, Capitulo 7; Livro 2, Capitulos 2-5; Livro 3, Capitulo 3; Livro 4, Capitulos 4, 8; Livro 6, Capitulos 12, 13. BA, JA, 49-V-1, 40-V-2.以及他的《中国分期史》最后一部分,[注]Antonio de Gouvea, Historia da China dividida em seis idades tirada dos Livros Chinas e Portuguezes com o continuo estudo e observaçoens de 20 annos, em a Metropoli de Fó (Kien) a 20 de Janeiro de 1654. Com hum apendix da Monarchia Tartarica. Biblioteca Nacional de Madrid, mss 2949.鲁日满《鞑靼中国史》,[注]François de Rougemont, Relaçam do Estado Politico e Espiritual do Imperio da China, pellos annos de 1659 até o de 1666, Lisbon, I. Da Costa, 1672. Historia Tartaro-Sinica Nova, Leuven: M. Hullegaerde, 1673.毕嘉《鞑靼占领期间的中国教会史》,[注]Joannem Dominicum Gabiani, Incrementa Sinica Ecclesia, a Tartaris oppgugnata, accurata et contestat narratione, Wien, 1673.聂仲迁《鞑靼占领中国史》,[注]Adrien Greslon, Histoire de la Chine sovs la domination des Tartares: ov l’on verra les choses les plus remarquables qui sont arrivées dans ce grand empire, depuis l’année 1651 qu’ils on achevé de le conquerir, jusqu’en 1669, Paris, 1671.利奇《本会在华传教士事迹》,[注]Vittorio Ricci (1621-1685), Hechos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el imperio de China, APSR(圣玫瑰省档案馆, Avila)China 1, 1667.均为明清鼎革史的重要史料,但仅就在欧洲的影响力而言,这些书远比不上卫匡国的书。此外,在欧洲或美洲的教士根据在华传教士的书信、报告和著作撰写了多种有关明清鼎革的著作,例如帕莱福《鞑靼征服中国史》,[注]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Historia de la Conquista de la China por el Tartaro, Paris, 1670. English translation, London, 1671.杜宁-斯珀特《1641-1700年中国史》,[注]Thoma Ignatio Dunin Szpot, Collectanea Historia Sinensis ab anno 1641 ad annum 1700, ex varijs documentis in Archivo Societatis Existentibus excerpta duobus Tomis distincta, Tomus I, ARSI, Jap.-Sin. 104.杜宁-斯珀特《中华帝国史》,[注]Thoma Ignatio Dunin Szpot, Historia Sinarum Imperii, ARSI, Jap.-Sin. 102.巴托里《耶稣会史》之中国部分,[注]Daniello Bartoli, Dell’ Istoria della Comagnia di Gesu, La Cina, Terza Parte Dell’ Asia, 1663.均包含有明清鼎革的内容,尤其是帕莱福在墨西哥完成的《鞑靼征服中国史》,内容可谓所有此类著作中内容最为丰富者,亟待学界对其加以更深入的研究,考证其信息的来源,及其所述内容的可靠性。大量有关明清鼎革的消息传到欧洲以后,引发了广泛关注,其中的一些内容甚至被改编成戏剧,在欧洲接连上演,例如荷兰冯德尔的《崇祯》(1667),[注]Joost van den Vondel, Zungchin, of Ondergang des Sineesche Heerschappije. Amsterdam: Joannes de Wees, Boekverkooper op den Middeldam, 1692. 关于该剧,参见Manjusha Kuruppath, Staging Asia: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Amsterdam Theatre,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61-116.英国赛特尔的《鞑靼征服中国》(1675)。[注]Elkanah Settles,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London, 1675. 关于该剧,参见Jeannie Dalporto, “The Succession Crisis and Elkanah Settle’s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Vol. 45, No. 2, Europe and Asia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ummer, 2004), pp. 131-146.此类文学作品无疑扩大了明清鼎革信息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面。
三、西文明清鼎革文献的全球史意义
上述仅是所有现存与明清鼎革有关的西文文献的一部分,还有更多的文献需要我们进一步调查补充。这些西文文献的作者来自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波兰、意大利、法国等地,文献涉及的空间范围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整个东亚,其撰写、出版和流通的范围则更为广阔,包括亚洲、欧洲乃至美洲。因此,我们说这些记录中国明清鼎革的历史文献具有全球性质。
可能会有学者认为,这些文献所记载的明清鼎革内容大都已在中国汉文和满文史料有记载,而且更为详尽,甚至可能比西文文献记载得更为准确,因此西文文献对明清鼎革史研究的价值不大。但我认为:第一,这些文献记载的内容很多都是传教士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具有原始文献的性质,传教士所观察到的内容,对汉文满文文献是重要的补充,扩大了明清史研究的史料范围;第二,在华传教士在撰写这些内容时,有自己的立场和视角,与汉文、满文的立场互不相同,因此这些西文文献可以让我们深入考察传教士对待明清鼎革时期各政权、战争、社会动荡等方面的观点。第三,这些西文文献全部是写给欧洲人看的,目的是让欧洲教会、政界、文化界、商业界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剧烈变化,因此这些文献对于我们研究欧洲本土各界对中国观念、态度的转变,其传教政策、商业政策的调整,以及中欧关系的转变等,均具有重要意义;第四,这批史料对于目前学术界的一些热点问题、热门话题,例如《清史》修撰工程、新清史等,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因为无论何种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观点,都需要建立在多元化的、立体的、扎实的史料基础上。第五,也是我本文最想强调的方面,即这批涉及多个欧洲语种西文文献能够使明清鼎革史具有了全球史特征。发生在东亚、中国的这一场剧烈政治、社会变革,被大量以欧洲文字记载下来,并传播至欧洲,在欧洲产生了影响,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说明清鼎革是一个全球性历史事件。这些文献有助于我们用全球史的视野和方法,突破原有的本国改朝换代的研究框架,把明清鼎革史放在全球背景中加以研究。
明清鼎革的西文史料具有全球性质,这一属性同时也是明清鼎革本身具有全球性的体现。本文通过对有关明清鼎革的西文文献的介绍和阐述,希望强调在全球史的研究中,尤其是在全球专史的研究中,原始文献的重要性。这一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实证意义上,也表现在视野和方法意义上。文献与其所记录的内容一样,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如果说全球史书写是对人类历史的时空的一次空前拓展,那么同时也应该是对人类历史的史料在时空维度上的拓展。与某一历史现象相关的史料具有全球性质,是该历史现象具有全球性的标志之一,也是我们以全球史的视野和方法对其加以研究的基础。综合利用本土史料、周边史料和西文史料来从全球史的视角研究明清鼎革,可被视为这一观点的典型个案。
——以河北大学图书馆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