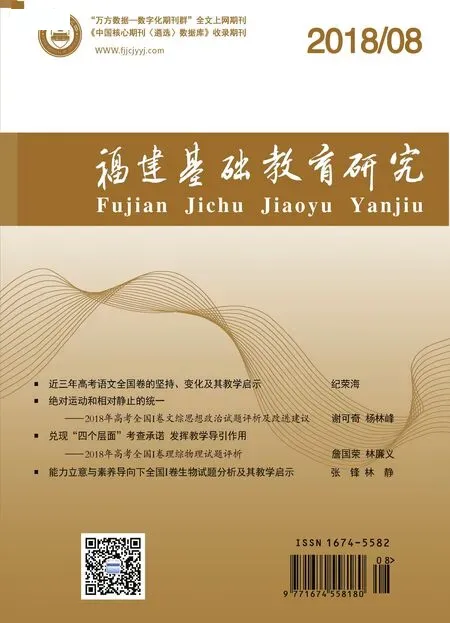学贵有疑 疑而后得
——从陈日亮对《鸿门宴》的一处质疑说起
苏宁峰
(厦门第一中学,福建 厦门 3610 0 3)
全国著名特级教师陈日亮在他的《语文教学归欤录·上卷》中谈到他解读教学文本的习惯做法:
所有的精读课文,我几乎都会通篇采用“句问点批”的方式,先“自己提出些问题来自己解答”(叶圣陶语),来训练语感,设置问疑。长期以来,揣摩语言,设问自答,已成了我读文听话、识鉴一切语文行为的习惯。[1]
学贵有疑。善疑者必是善思者,善思者,常能于人们熟视无睹处发现思想之新异深长;于文字纷披芜杂处洞见意脉之流转运行。陈老此法,于他而言,积久成嗜,化为自觉。无论是阅读还是听课,其所秉持者,为其“一字未宜忽”的谨严态度;为其“细心会本文”的沉涵熟复。这样深入亲切的文字揣摩,带契出来的疑与思,皆自有豁然开朗之光。前段时间,陈老在指导福建省名师培养对象时,就《鸿门宴》一文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刘邦入咸阳后的一切行为部署,乃是一件军国大事,作为谋臣的张良怎么会不知道?还问“谁为大王为此计者?”
这问题确是新异难解,一时难倒众人。新异正在于我们思维常为经验惯性所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难解则在于若只囿于课文节选之章节,则因信息有限而必致无解。然细思陈老此问,还真非寻常细节。北师大教授、著名的《史记》研究专家韩兆琦评价张良时,称他是鸿门宴上刘邦集团的“导演”:
在鸿门宴上,刘邦一方的每个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是张良事先安排好的:诸如刘邦见项羽时说话的那种谦卑、恭谨;樊哙闯帐时说话的那种正义凛然。[2]
这种导演的角色事实上还包含了张良安排的对付项羽集团的“以柔克刚”的隐忍策略。既然韩先生也评价如此,那么,“导演”张良竟不知刘邦入咸阳后的部署大事之事实,则当更加可疑。
一、稽古探微:史传之“史笔”与“文笔”
古人撰史,重实录精神,也重道德劝惩。宋代吴缜在《新唐书纠谬·序》里则概括到:
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3]
因有实录,讲文采,则史传有“史笔”与“文笔”之讲究。“史笔”是“以文运事”,讲究“信实有征”,欲求“信信疑疑”;文笔是“因文生事”,讲究“绘声传神”,欲求“增饰渲染”。而《史记》笔法则兼融“史笔”与“文笔”。古人之“文笔”,常在于“叙事增饰”与“记言增饰”。叙事增饰多见于叙事细节。比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之细节,钱钟书在《管锥篇·史记会注考证》的相关条目下,如此评说蔺相如秦廷智斗的“文笔”:
此亦《史记》中迥出之篇,有声有色,或多本于司马迁之增饰渲染,未必信实有征。写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是何意态雄且杰!后世小说刻划精能处无以过之。[4]
钱先生认为,蔺相如此传奇细节只是未必信实的“文笔”,如果是求真的“史笔”实录,那未免如儿戏。其文曰:
使情节果若所写,则樽俎折冲真同儿戏,抑岂人事原如逢场串剧耶?[4]
另一种“记言增饰”则常见于记载历史人物之言谈心理。古之史官,常以全知视角虚拟悬想,揣摩人事,钱钟书说:
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4]
这种行文涉笔成趣,踵事增华之事遍诸史传,《史记》亦然。即以《项羽本纪》篇言之。清代周亮工在《尺牍新钞》中质疑说:
余独谓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余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5]
二、考证答疑:张良确乎“不闻其事”
对照上述“史笔”与“文笔”之别,“导演”张良不知刘邦入咸阳后之军国大事,显然不属于“增饰”之“文笔”,而属于追求“信实有征”的“史笔”之属。显然,它需要考证。而考证的方法可有二。
一是“四维一体法”。即北大著名学者吴小如说的:
至于我本人,无论是在课堂上分析作品或写赏析文章,一直给自己立下几条规矩。一曰通训诂,二曰明典故,三曰察背景,四曰考身世。最后归结到揆情度理这一总的原则,由它来统摄以上四点。[6]
二则“互见法”。互见法本就是司马迁首创的一种与纪传体相适应的编撰历史的方法。靳德俊在他《史记释例》总结此法说:“一事所系数人,一人有关数事,若为详载,则繁复不堪,详此略彼,详彼略此,则互文相足尚焉。”简言之,即一事关涉众多,则散诸数篇,参错映照,互见互补。于《史记》书中,“互见法”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司马迁在行文中明示的,比如,《秦始皇本纪》说“其赐死语,具在《李斯传》中”;又如,“鸿门宴”事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做主体记录,有详细记述,其余则分散记录。比如,在《史记·留侯世家卷二十五》中就记载:“项伯见沛公。沛公与饮为寿,结宾婚。令项伯具言沛公不敢位项羽,所以距关者,备他盗也。及见项羽后解,语在《项羽》事中。”另一种是司马迁没有声明互见而实际存在互见的,此为暗示。
以“互见法”之明示、暗示搜检“鸿门宴”之张良刘邦事,则需检索项羽(《史记·项羽本纪》)、刘邦(《史记·高祖本纪》)、张良(《史记·留侯世家》)、樊哙(《史记·樊郦滕灌列传》)、陈平(《史记·陈丞相世家》)、范增、项伯等人物传记与事迹(注:所引的资料皆本自于韩兆琦主译之中华书局《史记》,下不为注)。今搜检资料,列点而论不求定论,只谈可能,不揣简陋,就正方家。
查《高祖本纪》,刘邦入咸阳后,为事有三:一是“封存府库,还军霸上”:“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还军霸上。”二是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三是听鲰生建议,守关拒内,欲霸关中。此三事,张良所不知者,独第三件。然正是这第三件事,事关战略,事启鸿门,不可等闲视之。细查互见之诸篇,其原因约可从如下几点思考归结:
(一)张良与刘邦的关系
考查张刘关系,则聚焦于从他俩相识到“鸿门宴”时。此问题的查考主要范围在《史记》的刘邦、张良与项羽的传记中,而他俩相识经过以张良的《留侯世家》记载最为详细。
《留侯世家》记载:陈涉等起兵后,张良也聚百余人,势力小,欲投靠当时自称为“楚假王”的景驹,在路上遇到了刘邦。时在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
十年,陈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馀人。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从之,道遇沛公。沛公将数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属焉。沛公拜良为厩将。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
“厩将”只是管马的官。然此次相识,张良出谋,刘邦善用,初次短期合作良好。此后张良随刘邦到薛地见项梁,张良请求项梁立韩成为韩王,项梁同意。于是张良便离开刘邦追随韩成,只是势力不敌秦兵,只好往来游击于颍川一带。时在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
他们第二次相遇在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刘邦奉楚怀王之命西略秦地,至韩国故地轘辕时。
沛公之从雒阳南出轘辕,良引兵从沛公,下韩十余城,击破杨熊军。沛公乃令韩王成留守阳翟,与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关。
在《高祖本纪》中,张良也只在此时出场。文仅一句:“因张良遂略韩地轘辕。”而张良在《项羽本纪》中的出场,则要更迟至鸿门宴时。然此次相遇相随,张良乃是以韩王臣子的身份随从刘邦征战,所以才可以理解课文《鸿门宴》中张良回答叫他离开的项伯说的那句“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
此后张良随刘邦征战立功,至鸿门宴前,史载大事两件:张良献计,攻破秦峣下军,直捣咸阳;刘邦入止秦宫,欲留居贪占,张良谏止。
简单梳理这一时段张刘关系,目的在于明察背景,揆情度理,考量其关系与信息交流的相关性。其间,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
1.张刘关系所处时期
韩兆琦概括张良一生轨迹:(1)帮着刘邦与秦朝斗;(2)帮着刘邦与项羽斗;(3)帮着刘邦与功臣斗;(4)还要留着一份心思与刘邦、吕后斗。截止“鸿门宴”前,张刘关系当正处于“与秦朝斗”之分期,也正是他俩关系的初识期——这种初识期还存在一年左右的睽违空档期的。从情理上说,刘邦对张良的信任也处在初建期,虽有彼此相得之感,但距离全面信任尚需时日。此时存在刘邦未必告诉张良所有军国大事的可能性。
2.张良其时的外臣身份
张良是韩国世家公子,有着强烈的韩国情结。《史记·留侯世家》载:“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再后,博浪沙刺秦,再后,劝说项梁复立韩国,自己追随韩王游击。直到刘邦征战韩国故地,张良才以外臣的身份跟随刘邦,破峣军,入咸阳。这种外臣的身份一直沿续到项羽杀死韩王,张良彻底投靠刘邦为止。
从情理上说,作为韩国复国运动积极分子的张良,其具体的征战动机与刘邦还是有着歧异的;而作为外臣的身份,张良与刘邦间也应当存在着无形的信任隔阂的。刘邦有些事未必说,不便说,甚至不能说,以及张良有些事不便问,不能问,这些都是符合情理的可能。
3.刘邦的行事风格
刘邦自起兵征战,一直归制于他人。至“鸿门宴”时,先从项梁,后从楚怀王。其率军征战,多受命于上级,基本无谋臣之需。直到他奉怀王之命独立率军西略地、攻咸阳时,他才逐路收纳郦食其、张良为其谋士。他布衣豪杰的草莽出身又让他在征询听取谋士意见时,常随性而为,偏听专断,并不周全熟虑,也并不周知于人。
先以课文节选的《鸿门宴》片段为证。课文《鸿门宴》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其中刘邦说守关拒纳诸侯的主意是出自“鲰生”(浅陋无知的小人),这显然是刘邦推诿责任且轻慢骂人的话。以“互见法”查检这个片段,在《高祖本纪》中,这“鲰生”变记为“或”(有的人):
或说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今闻章邯降项羽,项羽乃号为雍王,王关中。今则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关,无内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益,距之。”
此“鲰生”(“或”)谁人不详,此种战略大事,刘邦与谋者亦只是无名氏,亦且只谋及一人;及其施事,亦未见周知他人;可见刘邦谋于人行于事,亦见随便。及事发突然,乃诿过于人,转信张良。此种行事风格并非孤例。试再举他例以证。
《史记·留侯世家》载:汉三年(公元前204年),刘邦被项羽包围在荥阳,形势危急。谋士郦食其建议分封东方六国之后,以牵制削弱项羽势力。刘邦当即同意施行,让郦食其“趣刻印”。随后,张良从外来,问“谁为陛下画此计者?”然后再分析“八不可”,刘邦则“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其听事行事迅变,可见其未必专询于张良。
(二)张良之身体问题与处世哲学
咸阳守关拒内诸侯之战略,张良不闻其事,当还有张良自身的原因在。
首先,外在显见的原因是张良的身体问题。
《史记·留侯世家》有两处载:
“张良多病,未尝特将也(没有领兵独当一面),常为画策臣,时时从汉王。”
“留侯从入关。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谷,杜门不出岁余。”(就整天学习道家的导引吐纳之术,不吃五谷杂粮,几乎有一年多闭门不出。)
多病之身,纵使时时,亦难免疏缺。其不闻其事,亦有客观上的可能。
其次,深层内在的原因是张良的处世哲学。
从张良的处世哲学角度观察其行事风格也是理解“张良不闻其事”的一个重要角度。论张良形象,其实为黄老思想智慧的化身。
黄老哲学讲究“以柔克刚”“隐忍低调退让”“清静无为”以全其“养生”之生存智慧。张良一生就是践行黄老思想的一生。论隐忍以柔克刚,则宋代杨时评论张良可为参考。杨时说:“老子之学最忍,他闲时似个虚无单弱的人,到紧要处发出来使人支吾不住,如张子房是也。子房如峣关之战与秦战连和了,忽乘其懈击之;鸿沟之约与项羽讲解了,忽回军杀之,这便是柔弱之发处,可畏!可畏!”而若结合鸿门宴事来论,则韩兆琦对“导演”张良处世的评论可看:
张良所导演的刘邦集团应对项羽集团的策略,最主要的是就是“以柔克刚”。当前的形势对我们不利,我们就得隐忍,要设法保存实力,要在隐忍的过程中显示自己一方的正义性,以争取各路诸侯,乃至项羽阵营中一部分人的同情、支持,从而积蓄力量,以求日后的反攻。以今天的“谦卑”“无为”,是为了达到日后的“无不为”。结果刘邦在鸿门宴化险为夷。[2]
有着这样黄老思想的张良在处理与刘邦的关系上,明显地有着无为养生的超尘智慧:他给刘邦出主意,少见主动,多是响应,或是别人先提他再跟进,比如,刘邦入止秦宫,先是樊哙劝,樊哙之后张良再跟进;他不谋利争权,相反往往在封赏、权力面前退让,他与刘邦保持一定距离,保持一种“半朋友、半宾客”(韩兆琦语)的关系。因此,以这种逻辑推论,刘邦听信了“鲰生”意见,却没有告诉张良,那么可想而知,张良肯定也不会没事找事地去掺和、去介入、去问明。这是张良不闻其事的可能的主观原因。
三、学贵有疑:审问慎思,终见经纬
以上陋见,虽经一些资料查证,所见有限,终难得确论,故言只是可能。今写就呈奉,期就正方家。在此过程中,给笔者印象最深的则是陈日亮的质疑精神与发现的慧眼。读书常带疑问,面对权威也当如此。事实上,《史记》中还有不少问题存在。以清代梁玉绳撰写的《史记志疑》为例。他在“自序”中就说“然百三十篇中,愆违疏略,触处滋疑”。即以课文节选之《鸿门宴》片段来说,就有多处。比如:
《鸿门宴》:“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在这一条下,梁玉绳指出:
案:项伯之招子房,非奉羽之命也,何以言报?且私良会沛,伯负漏师之重罪,尚敢告羽乎?使羽诘曰‘公安与沛公语’,则伯将奚对。史果可尽信哉!
《鸿门宴》: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7]
在这一条下,梁玉绳指出:除了鸿门与霸上的距离有疑问外,其事于情理上也很是可疑。他引明代学者董份的话说:
当时鸿门之宴必有禁卫之士诃讯出入,沛公恐不能辄自逃酒。且疾走二十里亦已移时,沛公、良、哙三人俱出良久,羽在内何为竟不一问,而在外竟无一人为羽之耳目者。矧范增欲击沛公,惟恐失之,岂容在外良久而不亟召之耶?此皆可疑。[7]
梁玉绳还指出《史记》在称呼上的失误,比如“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足以当项王乎?”句中,刘邦与项羽当时俱未为王,“史乃预书为王”,这样的失误本篇中“凡书王者三十八,似失史体”。
以上种种,均是质疑精神所见。读者胸中有自在精神,则终见文字之经纬脉络。若一味盲信盲从,则必如清代赵翼在《论诗》诗中所说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