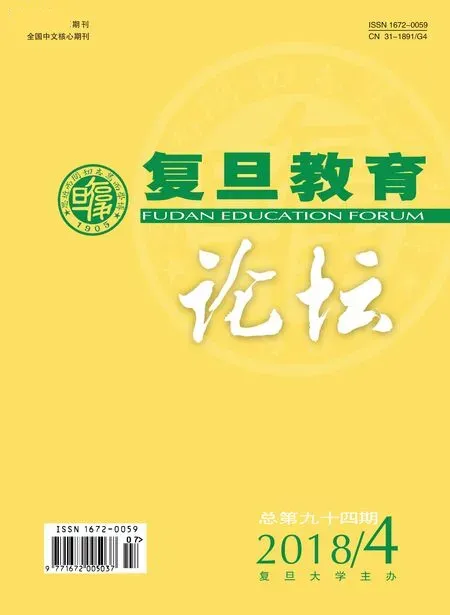教育法治建设迈上新台阶
庆年
近期参加了两个会。一个是2018年大学法律事务研讨会,有来自全国56所高校的80多名法律事务工作者参加。他们围绕法律事务部门的功能与定位、新《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施行的成效与问题、法律事务信息系统建设、师生关系中的权益保护以及大学法律事务同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研讨会是“民间性”的,召集人调侃地说,是微信群友的线下见面会。对此,笔者多少有些意外。这是不是表明中国大学法治建设正走向组织化的阶段?尽管大学法律事务机构的组织化形式各异,规模和专业化程度很不同,但从无到有,就是一个大进步。当然,研讨会不具有“官方色彩”,换一个角度解读,或许说明,大学对法律事务机构的认识还没有真正达到组织“自觉”的阶段。因为在当前社会文化语境下,“官方色彩”是组织化的“标配”。
另一个会是上海市法学会教育法学研究会换届会议暨专题研讨会。国内教育学社团中的教育法学分支组织早就有了,而法学社团中的教育法学分支组织却是近年来才有的,且国内还不多见。上海市法学会教育法学研究会换届,第二届理事会成立。理事会成员包括有法学研究者、教育学研究者、各类学校涉法工作者、法官、律师以及教育行政机关法规部门的公务员。从第一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中可以得知,上海市教育法学研究会在跨学科研究、跨界对话、重大问题攻关、专题研究、教育法治宣传、政策咨询、构建研究平台等方面,都有所展开。第二届理事会计划有更多的作为,更有效的运行,更深入的拓展,值得期待。会议所进行的专题研讨,围绕近十年上海教育诉讼案例展开。在历时的观察中,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教育法治的进步与面临的挑战。
如果说两个会议的召开,打开了一个观察教育法治面上推进的视窗,那么两个事件的发生,则提供了一个放大器,使笔者能从点上去感悟教育法治意识的觉醒。一件是校园性骚扰案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年初某校有女博士实名举报某教授性骚扰。清明时又有某校几位同学实名举报20年前大学老师性侵一位女同学,导致该女生跳楼自杀。由此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围绕防止校园性骚扰,人们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从难于启齿到实名举报,从高校个案到演绎为公共事件,反映的是社会对正义的追求,对推进教育法治的呼唤。
另一件是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的修订。成立于1979年4月的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2004年2月才有章程。2014年12月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新章程经校党委常委会和校长办公会正式审议通过,然而并未正式公布,据悉是因为共识不足。2017年7月,修订过的学术委员会章程经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并正式公布。2018年6月,学术委员会章程再次修订,并经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公布。章程制定、修订的时间维让我们看到,强化制度的效力正在成为北京大学的主动行为。
两个会议、两个事件,可以说为透视我国教育法治建设的进程提供了材料。笔者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跨入新时代,教育法治正在迈上新的台阶。依据就是,无论个体还是组织,无论政府、社会还是学校,主体意识正在形成。从集体的无意识到集体的有意识,无疑是个飞跃。当然,现实离理想的状态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一点毋庸讳言。我们还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本期“新论”栏目刊发了四篇文章,探讨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问题。这也是教育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议题。理性认识新时代的新要求,是我们前进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