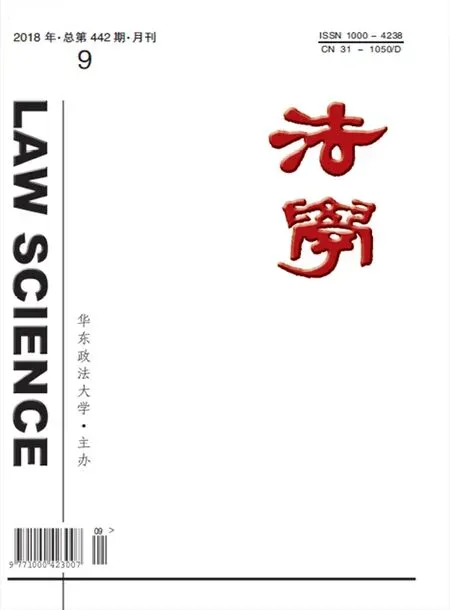保单现金价值强制执行的利益衡平路径
●武亦文
在司法实务中,当作为债务人的投保人无法清偿其对债权人所负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可否申请法院对投保人与保险人签订人寿保险合同所形成的保单现金价值强制执行,这一问题已成为近年来司法实务中的争议焦点。以下几个案例反映了法院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处理态度。
案例一〔1〕参见“吴建诉殷秀芳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1102执异字36号执行裁定书;“何井成与国长东、何春影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吉0303执异8号执行裁定书。:投保人A在保险人B处投保了一份分红型人寿保险,保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为投保人之女C,生存保险金受益人为C,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A。后因投保人A未履行其对于债权人D的到期债务,经债权人申请,法院冻结了其保单现金价值。后C提出执行异议,法院撤销执行裁定,理由如下。第一,本案中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尚健在,投保人(债务人)不享有对于保单现金价值的请求权,强制执行影响了异议人的财产权益。第二,投保人购买保险的时间先于人民法院有关借贷纠纷裁定的作出时间,投保人购买保险的行为没有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法释〔2010〕8号)的相关规定。
案例二〔2〕参见“贺传林与济宁市明坤化工有限公司、常立明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执复132号执行裁定书。:投保人A与保险人B签订分红型人寿保险合同。被保险人为投保人A之妻C,合同未明确约定受益人。后投保人A未履行其对于债权人D的到期债务,经债权人申请,法院裁定提取、扣留保单中的现金价值。保险人B对于执行裁定提出异议,法院经审查认为,由于保险合同未到终止时间,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也无任何解除保险合同的意思,法院不应以强行解除保险合同的方式提取保单的现金价值,可先对保单现金价值予以冻结,待提取条件成就后再行提取,〔3〕由于本案投保人拖欠保险费,且已经超出了宽限期,保险合同进入了中止期,法院所称的条件成就是指如果两年中止期届满,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情形。但可提取、扣留投保分红部分的收入。
案例三〔4〕参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滨州分公司追偿权纠纷执行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执复119号执行裁定书。:投保人A与保险人B签订了一份分红型人寿保险合同,被保险人为投保人A,保险合同未指定受益人。后投保人A未履行其对于债权人C的债务。经债权人C申请,法院强制执行A所投保的人寿保险合同中的保单现金价值。保险人B不服裁定,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法院维持原裁定,理由如下。第一,本案所涉及的分红型人寿保险虽以人的身体和生命为保险标的,但由于投保人可通过解除保险合同提取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保险单本身具有储蓄性、有价性,为投保人所依法享有的财产权益,并构成投保人的责任财产。第二,保单现金价值在法律性质上并不具有人身依附性和专属性,也不是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所必需的生活物品和生活费用,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5号,以下简称《关于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5条所规定的不得执行的财产。第三,在作为投保人的债务人不能偿还债务,又不主动解除保险合同以偿还债务的情况下,法院有权强制代替被执行人对该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予以提取。
上述三个案例均涉及作为债务人的投保人无法清偿对外债务时,法院可否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径直裁定对保单现金价值为强制执行。在上述三个案例中,法院判决结论及理由存在较大差别,在法律对保单现金价值能否强制执行未作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司法实务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存有较大分歧,而这对案件当事人的利益影响甚巨。由于人寿保险对受益人、被保险人及其遗属而言均能发挥一定的生存保障功能,这些主体与人寿保险合同具有直接的利益关联,法院在案例一中正是以此为理由之一作出不能强制执行保单现金价值的裁决。但是对于投保人的债权人而言,保单现金价值又具有保障其债权得以受偿的责任财产属性,〔5〕参见[日]砺波久幸:《税收征收机关对人寿保险合同权利的强制执行》,《税大论丛》第17号,第179页。故法院在案例三中即遵循此种思路,认定对保单现金价值可强制执行。但在司法实务中,针对保单现金价值进行强制执行的案件,往往是保险人作为异议人提出执行异议,〔6〕参见“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九江中心支公司、余胜初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赣0428执异3号执行裁定书;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宿迁中心支公司、王建与宿迁国泰汽车销售公司、刘淑侠等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1311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丰润支公司、李长朋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冀02执异481号执行裁定书。这与理论界所强调的“强制执行可能损害被保险人以及受益人等利害关系人利益”存在一定程度的事实出入。尽管理论界的担忧在现实中也有所体现,但这也反映出对于保单现金价值的强制执行问题,现有研究视角尚存在某种程度的局限性。
对于法院能否强制执行保单现金价值问题的回答,需从如下几个层面进行思考。其一,法院能否适用针对存款等财产的强制执行规则处理保单现金价值的强制执行问题。如果能够适用,则此时法院显然是将保单现金价值作为投保人自身的固有财产看待,但此种解决路径是否合理?如果不能适用,则法院应适用何种强制执行规则?法院的强制执行是否可被定位为代位执行程序,抑或是在承认债权人可代位解除保险合同的基础上对于保单现金价值进行的强制执行?其二,投保人所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是否具有专属性,债权人可否代位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其三,如果承认债权人的债权应该得到保护,债权人通过代位权的行使固然能使自身债权得以满足,但是此种情形下会发生人寿保险合同解除的结果,这将对被保险人、受益人等利害关系人的期待或者期待权造成损害,因而是否存在其他更能实现这些主体之间利益平衡的处理方式?下文将对这些问题逐一求解。
一、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2条所规定强制执行规则适用于保单现金价值的否定
现行法并未明确规定保单现金价值可否强制执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2条〔7〕《民事诉讼法》第242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情况。人民法院有权根据不同情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被执行人的财产。”规定法院可对被执行人的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进行执行,这些财产均具有债务人固有责任财产的属性,与债务人享有所有权的金钱及动产相似。虽然债务人的存款表现为其对银行所享有的债权,但存款这一债权不同于其他债权,我国法将债务人的存款也作为债务人的金钱予以处理。〔8〕严格来讲,对存款等财产的执行也属于对债权的执行。但在我国,人们习惯于将这些债权看作债务人的金钱或动产,因而将其纳入了对金钱或动产的执行之中,而没有将其纳入代位执行的范畴内。(参见谭秋桂:《民事执行原理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页。)此外,有观点认为储蓄存款所有权归属于存款人,银行对储蓄存款只有保管义务而无所有权。(参见李平:《保单现金价值强制执行规则》,http://www.zhongyinlaw.com/Arc-v.Asp?ID=412,2017年12月13日访问。)虽然从“占有即所有”原理进行观察,此种看法存在偏差,但这从侧面说明储蓄存款的归属问题具有特殊性。事实上,只是由于仅有金钱财产适用“占有即所有”规则,储蓄存款所有权才被视为由银行享有,如果抛开这一规则,银行对储蓄存款并不享有所有权。但对于保单现金价值的强制执行问题,该第242条未明确提及。由于该条对可强制执行财产的范围仅作了列举性规定,并未排除其他可强制执行的财产种类,那么在解释上是否意味着保单现金价值也可被纳入该条中“等财产”的范围呢?在司法实务中,有法院即认为“被执行的财产包括但不限于存款、债券等,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9〕参见“中国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泉州中心支公司执行异议案”,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2015)狮执异字第28号执行裁定书;“刘献涛诉杨传杰、王馨惠案”,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安中执字第230-4号执行裁定书;“康立强与孙伟财借款纠纷执行案”,吉林省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长汽开执恢字第10号执行裁定书;“中国平安人寿保险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金执复字第3号执行裁定书。进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42条对保单现金价值进行强制执行。在理论层面,有学者认为保单现金价值类似于投保人储蓄在保险公司的存款,〔10〕参见马向伟:《人寿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可以被强制执行》,《人民司法(案例)》2016年第17期;叶启洲:《债权人与人寿保险受益人之平衡保障——德国保险契约法上受益人介入权之借镜》,《月旦法学杂志》第255期(2016年);卓俊雄:《保单借款与强制执行相关法律问题之研究》,《保险专刊》第31卷第4期(2015年);张冠群:《从美国法观点论保险契约(保单现金价值)可否强制执行》,《保险专刊》第32卷第3期(2016年)。以此类推得出法院可强制执行保单现金价值的结论。
《关于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2条对于可被认定为强制执行财产的标准作了规定。首先,以占有或登记为标准,“被执行人占有的动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属于强制执行的范围。其次,对于未登记的不动产权利(未登记的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则依据土地使用权的审批文件和其他相关证据确定权属,进而判定相应财产可否被强制执行。最后,如果有关财产为第三人所占有或登记在第三人名下,自权利外观而言,这些为第三人占有或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财产权并不归属于被执行人,自然不应对这些权利予以强制执行,否则将构成对第三人权利的侵害。但是如果“第三人书面确认该财产属于被执行人的”,“第三人占有的动产或者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也可被纳入强制执行的对象范围。显然,保单现金价值并不属于该第2条前两款规定的情形,而是属于为保险人这一第三人所占有的财产,如果对保单现金价值进行强制执行,也应适用该第2条第3款的规定。但在司法实务中,法院往往以保单现金价值构成投保人的责任财产而对其予以强制执行,《关于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2条事实上系从程序法层面就哪些财产属于债务人所有予以明晰。因此,从实质层面而言,某一财产可否被强制执行,本质上还应探寻该财产的权属问题。对保单现金价值需明确的是其所有权究竟归属于哪一主体。
(一)保单现金价值的归属界定
关于保单现金价值的所有权属性存在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投保人所有说”。该说认为,保单现金价值所有权实质上属于投保人。〔11〕参见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理解适用与实务指导》,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652页;卓俊雄:《人寿保险契约强制执行》,《月旦法学教室》第163期(2016年);同前注〔10〕,叶启洲文;周庆、奎亮:《法院能否强制执行人寿保险费》,《人民法院报》2010年12月23日第7版。这种观点认可保单现金价值为投保人的责任财产。在司法实务中,有法院即持这种观点。如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公司追偿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系基于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所形成,是投保人依法享有的财产权益,并构成投保人的责任财产。”〔12〕同前注〔4〕。而在“朱建国、范喜芹与郭殿全买卖合同纠纷执行案”中,法院甚至认为:“本案案涉PX6号保单,因投保人是腾莉,在保险合同解除前,该保单的现金价值应属于腾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0211执异8号执行裁定书。如果承认保单现金价值所有权属于投保人,构成投保人的责任财产,那么法院可直接强制执行保单现金价值。第二种是“保险人所有说”。该说认为,保单现金价值并非为投保人所有而是由保险人所有。〔13〕参见郭宏义:《人身保险要保人之何种权利得作为强制执行之标的》,《保险专刊》第32卷第3期(2016年);同前注〔10〕,卓俊雄文;张涛、卢巧艳:《法院不应强制执行人寿保单现金价值》,《江苏法制报》2015年11月12日第00D版。依此观点,法院自然不得直接对保单现金价值强制执行。第三种是“投资权益说”。该说认为,保单现金价值是投保人所享有的一种确定的投资权益。〔14〕参见“王文东执行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执复字第112号执行裁定书;同前注〔4〕。
笔者认为,保单现金价值应归保险人所有,即在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之前,保单现金价值在性质上可归类为保险费,其所有权归属于保险人。
首先,从最基本的民法原理观察,保单现金价值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适用货币财产“占有即所有”的规则,在保险公司受领保险费给付时,保单现金价值部分的金钱所有权就移转至保险人,保单现金价值所有权并不归属于投保人。因此,即使是持保单现金价值归属于投保人观点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保单现金价值所有权在形式上属于保险人。〔15〕同前注〔10〕,叶启洲文。不过单纯从此点论证保单现金价值所有权归属于保险人,并不足以否定法院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42条对其进行强制执行,因为在储蓄存款合同中,当存款人将存款交付至银行时,银行也获得了存款的所有权,但这并不妨碍法院将债务人的存款作为债务人的金钱予以强制执行。
其次,从人寿保险合同中保险费收取的技术角度观察,之所以会产生保单现金价值,是因为人寿保险中保险费的收取采取平准保费制的结果。一般而言,随着被保险人年龄的增大,被保险人所承担的风险越高,基于对价平衡原则的要求,作为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投保人也应该缴纳更高的保险费。但为了保费收取的便利以及缓和投保人年老时缴纳保险费的压力,保险人将后期所应收取的更高的保险费分摊至前期收取的保险费中。从此点观察,前期超出自然保费部分的保单现金价值具有预付未来保险费的属性,以弥补后期未缴足的保险费,〔16〕参见[日]田口城:《为被保险人利益的保险准备金与保单现金价值》,《生命保险论集》第162号,第272页。只要保险合同未被解除,无法认定保单现金价值归属于投保人所有,进而构成投保人自身的责任财产。此时应当认定保单现金价值所有权仍归属于保险人所有。〔17〕参见[日]肥塚肇雄:《人寿保险合同中保单现金价值的规整》,《保险学杂志》第607号,第123页;参见[日]山下友信:《保险法》,有斐阁2005年版,第652页;同前注〔16〕,田口城文,第296页。
最后,“投资权益说”事实上混淆了保单现金价值与投保人通过人寿保险所能收取的分红的区别。保单现金价值是由于人寿保险合同存续期限较长而采取平准保费制的结果,而投资权益指的是投保人通过分红型人寿保险所能得到的红利分配,保单现金价值与投资权益存在明显区别。或许有观点认为,实践中存在投保人欠缴保险费时,保险人以保单现金价值垫缴投保人所欠缴保险费的情况,依此可证明保单现金价值所有权归属于投保人。但是,之所以保单现金价值可用以垫缴保险费,乃是因为投保人享有保单借款权。也就是说在投保人欠缴保险费时,此时相应金额的保单现金价值即相当于自动转化为保险人给投保人的借款,以支付投保人对保险人所欠缴的保险费。〔18〕在理论上,保单借款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动垫付保险费的借款,第二类是由保险人主动向保险人申请的借款。同前注〔5〕,砺波久幸文,第214页。由此可见,在投保人未解除保险合同之前,保单现金价值所有权实际上归属于保险人。
在司法实践中,当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42条裁定执行债务人(投保人)在保险公司处的保单现金价值时,其实质是以储蓄存款的思维看待保单的现金价值。〔19〕正是因为如此,许多保险公司在对强制执行程序提出异议时多会主张:“保险公司在经营范围内依法经营保险业务,不从事存款业务,被执行人在异议人处没有存款,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1条及相关法律规定,异议人无法作为此案协助执行的主体。”参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莱芜分公司、何庆文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执复291号执行裁定书。但是人寿保险合同中的保单现金价值与存款具有如下本质区别。
首先,法律关系主体不同。储蓄存款合同只涉及存款人以及银行等合同双方当事人,而在人寿保险中,除了投保人与保险人这一对合同当事人之外,通常还存在被保险人以及受益人等保险合同关系人。人寿保险合同通常是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其涉及第三方利益主体。〔20〕参见邵杰:《人寿保险合同现金价值执行之立法规制——以日本〈保险法〉受益人介入权制度为例》,《上海保险》2017年第2期。
其次,给付义务的确定性不同。在储蓄存款合同中,银行等金融机构负担的是到期还本付息的义务,实为一种具有履行期限的给付义务,该给付义务具有确定性。而在人寿保险合同中,虽然保险人确定性地负有危险承担义务,但是该金钱给付义务却会由于条件是否能够成就而具有不确定性。具体而言,保单现金价值的返还以投保人或保险人分别行使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或法定解除权这一停止条件为前提,〔21〕虽然有观点可能指出,投保人所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实质上是一种随意条件,条件的成就具体表现为当事人的作为或不作为,因此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名为附条件债权,似乎具有不确定性,实质上是一种确定性的债权。关于随意条件问题的讨论,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9~131页。自表面观察,上述观点具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在人寿保险合同存续期间,当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人的给付义务被确定下来,保险事故的发生阻却了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条件的成就。因此,保险合同的解除也并非完全取决于投保人,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并非是确定的债权。此外,有学者甚至还认为,在投保人对保险人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之前并无债权存在。See Isadore H.Cohen, Attachment of Life Insurance Polices, 26 Cornell L.Rev.217(1941).保险金的给付以保险事故发生为停止条件,由于该条件发生与否具有不确定性,致使金钱给付义务也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有法院判决认为:“根据《保险法》第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在保险期内,投保人可通过单方自行解除保险合同而提取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由此可见,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作为投保人所享有的财产权益,不仅在数额上具有确定性,而且投保人可随时无条件予以提取。”〔22〕“丁转申请复议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执复字第107号执行裁定书。这一观点似有待商榷。
最后,法律后果不同。在储蓄合同中,存款本息的返还最多只是被认定为存款合同因履行而终止,属于储蓄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常态。而在人寿保险合同中,保单现金价值的返还以合同解除为前提,而保险合同的解除并非是一种常态。尽管法律赋予投保人任意解除权,但除非在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所依赖的客观情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投保人一般不会行使解除权,因为保险合同的存续对于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都是有利的。正因为如此,实践中当法院裁定对保单现金价值进行强制执行时,保险公司往往会提出执行异议。〔23〕参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新乐支公司复议案”,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石执审字第00070号执行裁定书;同前注〔19〕,“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莱芜分公司、何庆文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而在对债务人存款进行强制执行时,无论是活期存款还是定期存款,存款人均可以随时提取,只是提前支取定期存款将使存款人丧失较高的定期存款利息收益,〔24〕同前注〔13〕,郭宏义文。《商业银行法》第29条规定:“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银行等金融机构一般不会提出异议,因为这是其固有的合同义务。而在保险合同中,向投保人返还保单现金价值并非保险人所负的固有合同义务。
因此,在人寿保险中,对于保单现金价值无法适用针对储蓄存款的强制执行规则。由于对保单现金价值的强制执行意味着保险合同的解除,保险人将丧失保险合同存续所带来的利益。而且保险人在协助完成执行行为后,可能面临投保人对其提起非法解除保险合同之诉且败诉的风险,而对于储蓄存款的强制执行并不会导致此种结果。由于法院的执行行为实际上已干扰了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的正常商业交易,因而保险公司往往会提出执行异议,而银行则很少提出。
(二)保单红利可依《民事诉讼法》第242条予以执行
现实中大量存在分红型人寿保险合同,此类人寿保险的投资属性非常明显。在此类保险合同中,保险公司将收取的保费用于投资,并将产生的收益分配给投保人,该收益在未分配给投保人之前由保险公司占有。笔者认为,法院可对保单红利径直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42条予以强制执行。人寿保险中所产生的保单红利类似于投保人储蓄于保险人处的存款及其利息,投保人对保险公司享有类似于储蓄合同中存款人所享有的债权请求权,两者均属于确定性的债权,不存在因条件的成就与否而导致债权是否发生的问题。对于保单红利的强制执行,不会产生保险合同被解除的后果,保险人仍能享受保险合同存续所带来的利益。
实际上,在司法实务中许多法院已明确了这一点。如在“贺传林与济宁市明坤化工有限公司、常立明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中,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涉案三个保险合同,其中尾号为3和7的两份合同分红分别为2 297.34元和5 911.14元,可以依法提取;对于三份保单的现金价值,由于合同还没有到终止的时间,保单的双方当事人也没有解除合同的意思,法院不应以强行解除保险合同的方式提取保单的现金价值,可以先对保单的现金价值予以冻结,待提取条件成就后再行提取。”〔25〕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执复132号执行裁定书。显然,在此案中法院对人寿保险合同所产生的分红与保单现金价值的强制执行作出了明确区分。
二、代位执行规则适用于保单现金价值的摒弃
为便于论证,本文对代位执行与一般意义上的强制执行进行区分。〔26〕广义的强制执行实质上包括代位执行,但本文对一般意义上的强制执行与代位执行作区分讨论。上文所讨论的强制执行客体主要是被执行人的财产和行为,〔27〕虽然债权、收入、存款、动产、不动产都属于强制执行标的物,但与这些财产权益存在明显不同的是,债权并非被执行人所显示拥有的财产,只有当次债务人履行了对于债务人所负之债务时,其才可转化为实际财产。参见张晓茹、许藤:《执行债权的法理基础与法律构造——兼论代位执行法理之缺陷》,《河北法学》2011年第8期;同前注〔8〕,谭秋桂书,第277页。强制执行程序中的当事人仅仅涉及原审判程序中的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而未扩展至其他第三人。在代位执行程序中,法院执行的客体主要是被执行人对第三人所享有的债权,虽然债权也可归入被执行人的财产,但由于代位执行牵涉到案外第三人,其执行程序与一般的强制执行程序存在差异。因此,对其有作单独讨论的必要。〔28〕许多民诉法学者对一般强制执行程序与代位执行也作了详细区分,指出二者在执行客体、执行法律关系、执行程序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参见郭兵主编:《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343~344页。
(一)保单现金价值强制执行程序被定位为代位执行程序的可能性
代位执行制度已被我国司法解释所确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501条规定:“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对他人的到期债权,可以作出冻结债权的裁定,并通知该他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他人对到期债权有异议,申请执行人请求对异议部分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利害关系人对到期债权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处理。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到期债权,该他人予以否认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9〕该条继承了1992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0条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通知该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该第三人对债务没有异议但又在通知指定的期限内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根据该条规定,一般认为代位执行需满足以下条件:(1)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2)债务人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3)申请执行人提出申请;(4)该第三人对债务没有异议但又不在通知指定的期限内履行。〔30〕同前注〔28〕,郭兵主编书,第345~346页。
在保单现金价值强制执行案件中,执行申请往往是由债权人提出。在投保人未解除保险合同的情况下,保单现金价值所有权归属于保险人。此时,投保人对保单现金价值所享有的权利至多只能被认定为附条件的债权。因此,在执行程序中,对保单现金价值的执行不宜被定位为一般意义上的强制执行,其应适用债权执行程序中的代位执行。在现实中,当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对债务人的保单现金价值进行强制执行时,其符合上述代位执行程序中的第(1)项和第(2)项条件,至于“第三人无异议”这一要件,在目前的保单现金价值执行案件中,由于法院未能清楚地以代位执行的思维启动执行程序,多数情形是法院直接对其进行强制执行。〔31〕事实上,在司法实务中部分法院是以一般强制执行程序的思维对保单现金价值进行强制执行的,因此在执行保单现金价值之前未通知保险人向债权人履行。
如果认定对保单现金价值的强制执行适用的是代位执行程序,其中的第三人即保险人。此时,在法院启动执行程序之前需满足“第三人对债务没有异议但又不在通知指定的期限内履行”这一条件。如果保险人行使异议权,则法院的代位执行程序即无法启动。在一般的强制执行程序中,虽然也存在案外人异议程序,但其存在于执行程序开始之后。换言之,这种情形下的案外人无异议并不是执行程序启动的前置要件,这与代位执行程序中要求第三人无异议是启动执行程序的前提条件存在明显不同。之所以如此设计,是由于代位执行程序牵涉到案外第三人,赋予第三人异议权可以保障其权利不受执行程序的侵犯。
如果法院适用一般意义上的强制执行程序,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不需以保险人无异议且未履行义务为条件。在实务中,对于保单现金价值强制执行案件,保险公司往往会提出异议。而如果适用代位执行程序,可将保险人在执行程序中的异议提前至执行程序开始之前。此时,若保险人提出异议,法院应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27条处理,〔32〕参见张卫平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要点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391页。如果保险公司认为原执行裁定存在错误,可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救济。
(二)保单现金价值强制执行程序被定位为代位执行程序面临的障碍
1.可突破的障碍。在理论上,对于代位执行的客体是否限于到期债权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未到期债权也可成为代位执行的客体。〔33〕参见杨荣馨主编:《强制执行立法的探索与构建——中国强制执行法(试拟稿)条文与释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66页;沈德咏主编:《强制执行法起草与论证》,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法释〔2011〕195号,以下简称《规避执行的制裁意见》)第13条〔34〕该条规定:“依法保全被执行人的未到期债权。对被执行人的未到期债权,执行法院可以依法冻结,待债权到期后参照到期债权予以执行。第三人仅以该债务未到期为由提出异议的,不影响对该债权的保全。”也将未到期债权纳入代位执行的范畴。然而,即使承认未到期债权也可成为代位执行对象,但由于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并不是附期限的债权,因此不存在讨论其返还请求权是否到期的问题。事实上,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是附停止条件的债权,在所附停止条件成就前,这一权利至多只能被认定为期待权。问题在于,附停止条件的债权这一期待权可否被代位执行。对此,在理论层面一般认为对附条件的权利也是可执行的,只要在条件成就时权利内容能被特定化即可;〔35〕参见[日]仓泽康一郎:《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的法律性质与强制执行》,《法学研究》第66卷第1号,第70页。此外,虽然期待权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但期待权具有处分效力。期待权的处分效力主要表现为可转让性、可质押性、可继承性,〔36〕参见申卫星:《期待权基本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页。强制执行是处分效力在程序法上的体现,其决定了期待权具有强制执行的可能性。〔37〕Vgl.Creifelds, Rechtswörterbuch, Auf l.16, C.H.Beck, 2000, S.74-75.转引自申卫星:《期待权研究导论》,《清华法学》2002年第1期。在比较法层面,例如在德国、日本,附有条件而条件尚未成就的债权也可成为代位执行的标的。〔38〕同前注〔8〕,谭秋桂书,第281页。
2.不可突破的障碍。然而,在对未到期债权进行强制执行时,需对未到期债权进行冻结。〔39〕《民事诉讼法》第501条规定,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对他人的到期债权,可以作出冻结债权的裁定,并通知该他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而对于未到期债权,可先予冻结,待债权到期后再进行执行。参见赵晋山、葛洪涛、乔宇:《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16期。由于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是附条件债权,即使承认可对期待权进行强制执行,相比于未到期债权,这一附条件债权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举轻以明重,既然对未到期债权适用的是冻结措施,那么对保单现金价值自然也应适用冻结这一执行措施,以等待条件成就之时,对保单现金价值进行提取。但若投保人始终不解除保险合同,则债权人的债权将永远无法得到满足,此时即使承认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这一期待权可成为代位执行的标的也并无实际意义。除非是直接承认代位执行的标的可扩展至保险合同解除权,进而认定法院可强制解除保险合同。在司法实务中,部分法院即认为法院可解除保险合同。“在投保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且怠于行使或不能行使保险合同的解除权时,法院有权代为投保人(本案中的被执行人)行使解除权。”〔40〕“中国平安人寿保险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14)金婺执异字第1号执行裁定书。但问题在于,将代位执行的标的扩展至解除权这一形成权并无正当性。在理论层面,强制执行程序实质上是以当事人所享有的实体权利为基础的,且“只有请求权的实现才涉及强制执行程序”。〔41〕江伟、肖建国:《论我国强制执行法的基本构造》,《法学家》2001年第4期。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无法将代位执行的客体扩展至具有形成权性质的保险合同解除权。〔42〕参见前注〔13〕,郭宏义文。此外,一般认为合同解除权这一形成权本身并未包含财产价值,法院无法对其进行执行。〔43〕参见[日]山下友信:《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与民事执行、债权人代位权》,《金融法务事情》第1157号,第8页。
尽管在理论层面存在将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纳入代位执行程序的可能性,但由于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这一期待权最终能否具体化取决于保险合同是否被解除,因而问题的关键仍在于保险合同解除这一停止条件如何发生。
三、债权人代位行使投保人之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的可能性分析
上文对代位执行这一路径进行了讨论,在现行法层面还存在与代位执行制度相类似的债权人代位权规则,二者具有共性,〔44〕由于债权人代位权与代位执行存在许多相似性,二者具有可替代性,因而可能造成制度重叠的问题,笔者在此并不探讨债权人代位权与代位执行的替代问题,而仅从实证法的规定出发分别展开讨论。其目的均在于通过将债权效力扩展至第三人实现债权人的债权。〔45〕参见丘志乔:《代位权与代位执行:并存还是归一对我国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思考》,《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如前所述,人寿保险合同在被解除之前,保单现金价值在其性质上可被归类为保险费,保险人对其享有所有权。但投保人对保单现金价值仅享有期待权层面的返还请求权,且是附停止条件的权利,其停止条件为人寿保险合同的解除。该停止条件的存在使得投保人所享有的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仅仅表现为一种期待权。理论上认为,代位权行使的客体须为债务人既得的权利,如果仅仅是一种期待权,〔46〕私权以其成立要件之已否全部实现为标准,分为既得权与期待权,既得权的成立要件已完全实现,一般的权利均属既得权;而期待权的成立要件将来有实现之可能,如附条件的权利。参见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则不得代位行使。〔47〕参见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陈荣隆修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页。美国多数法院也持相似观点,即在投保人没有为一定行为以使保险公司对投保人产生负债之前,债权人不得强制执行保单现金价值。〔48〕同前注〔21〕,Isadore H.Cohen文,第 217页。因此,如果作为投保人的债务人不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以解除保险合同,则投保人并不享有现实的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此时不产生能否代位行使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的问题,法院自然也无法对保单现金价值进行强制执行。因此,对于保单现金价值的执行,问题的症结在于投保人所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能否成为债权人代位权行使的对象。
我国《合同法》第73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首先,自文义解释出发,现行法将非属于债权的权利排除出代位权的客体范围,那么具有形成权性质的保险合同解除权能否成为代位权的客体?其次,即使承认形成权可成为债权人代位权客体,由于《合同法》第73条将专属于债务人的权利排除出可以代位行使的客体范围,因此还必须探讨投保人所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是否具有人身专属性。
(一)作为形成权的解除权可否成为代位权的行使对象
我国《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1999〕19号,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一)》)明确限定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对象为债权。而投保人所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的性质为形成权,那么是否意味着解除权这一形成权也不能成为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对象呢?
首先,自目的解释角度而言,代位权制度的存在目的在于保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因此,只要是有助于保全债务人责任财产的权利,均可成为代位权的客体,如果仅承认债务人对于第三人所享有的债权方可成为代位权的客体,将人为限缩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对象,不利于对债权人权利的保护。因此,在理论层面亦应认可撤销权、解除权等形成权为代位权的客体。〔49〕参见史文才、宋迎春:《债权人代位权制度比较研究》,《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5年春季号;吴祖祥、李焚:《代位权法律制度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35页;同前注〔5〕,砺波久幸文,第202页;[日]酒井一:《债权人代位权——以债权法修改委员会提案为中心的考察》,《立命馆法学》第339~340号,第120页。如果对《合同法》及《合同法司法解释(一)》中的代位权对象作目的性扩张解释,投保人所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亦可成为代位权的行使对象。〔50〕同上注,韩世远书。其次,自比较法而言,代位权的行使对象并不限于债权。如《法国民法典》第1166条规定:“债权人得行使其债务人的一切权利与诉权,专与人身相关联的权利除外。”〔51〕《法国民法典》,罗结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0页。按照该规定,债务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均得成为代位权的行使对象。在日本,也认为代位权所针对的对象并非仅限于请求权,亦包括解除权。〔52〕参见[日]斋田统:《对债权人代位权意义的考察(一)》,《迹见学园女子大学管理学部纪要》第7号,第55页。因此,解除权等形成权也可由债权人代位行使。不过判断投保人所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可否由债权人代位行使,还需考虑这一解除权是否具有人身专属性,以及其是否只能由投保人行使。
(二)投保人所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是否具有专属性
专属权是指专属于权利人一身的权利,其可被进一步划分为“享有之专属权”〔53〕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第734条规定的终身定期金合同中的终身定期金权为典型的享有层面的专属权。该条规定:“终身定期金之权利,除契约另有订定外,不得移转。”与“行使之专属权”。享有层面的专属权不得让与或继承,但可代位行使,与代位权并不冲突。而行使层面的专属权专由权利人意思决定,不得代位行使。〔54〕同前注〔46〕,郑玉波书,第71页。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8条第2款所规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即属于行使层面的专属权。〔55〕《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8条第2款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此外,如果某种财产权表现为以人格上法益为基础的权利,则其属于行使层面的专属权,亦不得代位行使。〔56〕同前注〔13〕,郭宏义文。《合同法》第73条但书条款所指称的专属权也是行使层面的专属权。〔57〕参见崔建远、韩世远:《债权保障法律制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那么,投保人所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是否具有权利行使层面上的专属性,殊值探讨。
1.自投保人意思自由视角的考察。有学者认为,合同订立、解除或终止等得丧变更合同效力的行为,与订约人权利义务及经济利益息息相关,关系到订约人的表意自由,除非其行为符合诈害债权的情形,他人不应干涉。〔58〕同前注〔13〕,郭宏义文。因此,投保人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只能由其自己行使,债权人代位权客体无法扩展至合同撤销权和解除权。在我国司法实务中,有法院也持类似观点,如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玉田支公司、宋贤良等与刘泽民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中,法院认为:“目前投保人并未与复议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玉田支公司解除保险合同,且该合同仍在履行中,故河北省玉田县人民法院要求复议人协助执行扣划投保人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玉田支公司的保险款项至河北省玉田县人民法院势必造成双方所达成保险合同的强制予以解除,显然违背自愿原则。”〔59〕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冀02执复47号执行裁定书。
然而,此种观点从表意自由的角度论证投保人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属于行使层面的专属权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在债务人对次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时,债务人亦享有是否要求次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意思自由,而如果尊重此种自由权的运用,将导致债权人的权利遭受不当损害。既然《合同法》认定此种情形下债权人可代位债务人行使其债权,那么也不宜直接以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牵涉投保人的表意自由而否认保险合同解除权可成为代位权的行使对象。〔60〕日本的相关司法实务否认了投保人基于自由意志享有的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为身份法上的一身专属权。参见[日]仓泽康一郎:《伤害保险合同中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的强制执行与债权人解除合同(大阪地裁昭和59年5月18日判決)》,《法学研究》第65卷第8号,第135~136页。
2.自《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12条的观察。《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12条以列举的方式对何为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进行了解释,该条规定:“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是指基于扶养关系、抚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退休金、养老金、抚恤金、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
首先,《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12条规定仅提及人寿保险,但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言,人寿保险应指的是相对于财产保险的一类保险,人寿保险自身无法作为一类权利。不过,人寿保险却包括了一系列的权利集合,如投保人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保险合同解除后投保人所享有的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享有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而该第12条并未指明其具体是人寿保险中的哪一种权利。
其次,自条文解释角度而言,该第12条将人寿保险与退休金、养老金、抚恤金相并列,似乎意指该条所称的人寿保险特指人寿保险金,那么投保人所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自然不在该条规范之列。不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15〕21号,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的规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可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第三人行使。因此,即便是保险金请求权也不具有人身专属性。
再次,即使承认投保人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属于该条规范之列,但由于人寿保险属于商业保险,其不同于旨在维持当事人最低限度生活水平的社会保险。由于人寿保险投保人所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由他人代位行使,并不会对当事人的基本生活保障产生影响,也自然不必承认投保人所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的专属性。
最后,即便承认人寿保险合同具有人身专属性,由于其保险标的通常是被保险人的身体或生命,因此在探讨人寿保险的专属性时,也应从被保险人的视角出发,而非承认投保人对人寿保险的相关权利具有人身专属性。质言之,如果认为人寿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专属于投保人,则会得出本人对于第三人的人格权具有专属性这一逻辑混乱的结论。〔61〕同前注〔10〕,卓俊雄文。
3.从规范目的出发的考察。自体系解释角度而言,投保人对人寿保险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并非人寿保险合同所独有。按照我国《保险法》第15条的规定,无论是人寿保险合同还是财产保险合同,投保人均享有这一任意解除权,也就是说投保人所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事实上与人身权并无直接关联,也并无专属性。不过,有观点认为,人寿保险合同中之所以赋予投保人以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还存在其他考量。由于人寿保险合同期限较长,投保人在投保之后可能会因自身各方面的情况发生变化而不愿再继续投保,因此赋予投保人以任意解除权,该任意解除权是投保人基于其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地位而享有的专属权。而事实正相反,这一目的解释方法实为人寿保险合同不具有专属性提供了佐证。之所以赋予投保人对人寿保险合同以任意解除权,即在于为投保人提供一个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是否维持保险合同效力的机会,当投保人无足够的责任财产以清偿其到期债务时,投保人继续维持人寿保险合同效力的经济基础即已丧失。此种情形下应承认投保人负有解除保险合同的义务,因为即使投保人不解除保险合同,也会面临将来无法支付到期保费的窘境,在人寿保险合同两年的效力中止期经过后,保险人也很有可能解除保险合同。同时,解除合同的行为仅仅与投保人自身的经济状况相关,并不具备人身专属性,可由债权人代位解除保险合同。
综上,投保人对人寿保险合同所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并无专属性,〔62〕参见叶启洲:《保险法实例研习》,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431页。对于《合同法》关于代位权行使对象限于债权的规定,可从目的性扩张解释角度将其扩展至解除权等形成权。因此,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可成为代位权行使对象。
四、保单现金价值强制执行案件中的利益平衡
在人寿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受益人经常会出现分离的情形。如果允许债权人无条件地代位行使投保人所享有的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以满足自己的债权,〔63〕参见[日]福岛雄一:《对保单现金价值强制执行的考察——以东京地裁平成10年8月26日判决为例》,《行政社会论集》第12卷第1号,第129页。将会减损被保险人与受益人所期待获得的利益,〔64〕在投保人保留了受益人变更权的情形下,受益人享有事实上的期待;如果投保人在保险合同中明确放弃了受益人变更权,则受益人所享有的权利成为一种期待权。同前注〔5〕,砺波久幸文,第191页。使得受益人只能通过另行订立一份人寿保险合同获得保障,这将导致额外的缔约成本。〔65〕同前注〔10〕,叶启洲文。在司法实务中,许多法院即以代位解除保险合同将会损害第三人利益为由否定此种情形下法院可强制执行保单现金价值。〔66〕参见“虞春燕、黄友录等与陈敏借贷纠纷执行案”,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温执复字第36号执行裁定书;同前注〔1〕,“何井成与国长东、何春影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在前述案例一中,法院认为:“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尚健在,投保人(债务人)不享有对于保单现金价值的请求权,强制执行影响到了异议人的财产权益。”〔67〕同前注〔1〕,“吴建诉殷秀芳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法院因此撤销了原强制执行裁定。同时,由于人寿保险具有长期性,一旦保险合同被解除,考虑到年龄、健康等因素,被保险人可能很难再缔结新的保险合同,因此存在继续维持原合同效力的必要性。〔68〕参见[日]李鸣:《对保险金受益人介入权的考察——从保险实务看介入权在保险法上的解释问题》,《法学政治学论究》第88号,第44页。一旦解除保险合同,作为债务人的投保人只能获得小额保单现金价值的返还,这与保险事故发生后所能获得的高额保险赔付存在巨大的差额。〔69〕参见[日]栗田达聪:《人寿保险债权相关利益调整》,《保险学杂志》第608号,第120~121页。无论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债权人的主体身份是否分离,都意味着要通过牺牲投保人一方(包括被保险人及受益人)的巨大利益满足债权人的权利,而这可能与比例原则并不相符。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债权而承认债权人可代位解除保险合同,将使得保险合同订立的主要目的可能落空。〔70〕同前注〔35〕,仓泽康一郎文,第70页。即使不考虑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利益的存在,〔71〕有学者指出,由于在保险事故发生前,投保人本身享有保险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受益人的地位非常不稳定,受益人的利益可能仅是一种期待权,甚或只是一种期待。对于受益人而言,使其丧失受益权的主体究竟是投保人还是投保人的债权人无任何区别,所以受益人地位的丧失并不能成为阻碍投保人的债权人代位解除保险合同的理由。参见岳卫:《人寿保险合同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的强制执行》,《当代法学》2015年第1期。在人寿保险合同中,如果被保险人死亡,由于保险金对于依赖被保险人生活的遗属也具有保障功能,如允许债权人无条件地解除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的配偶等遗属也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72〕同前注〔35〕,仓泽康一郎文,第65页。因此,虽然债权人依法理可代位行使投保人对于人寿保险合同的解除权,但是债权人对自身正当权利的行使应存有一定限制,以避免对其他主体的利益造成过度损害。
(一)对若干可能解决路径的否定
1.区分人寿保险是否涉及第三人利益。以保险合同是否关涉第三人利益的实现为标准,判定保单现金价值可否被强制执行。〔73〕在比较法层面,美国部分州成文法的规定与此种思路类似。See Ariz.Rev.Stat., §§ 33-1126(2008); Md.Code Ann.,§§ 11-504(2005); N.D.Cent.Code, § 26.1-33-36(2013).如果在某一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是同一主体,且并未指定受益人,被保险人也无遗属依赖于人寿保险的保险金生活,那么债权人可代位解除该保险合同,并申请法院对保单现金价值予以强制执行。否则,即应否认代位解除保险合同以强制执行保单现金价值的可能性。〔74〕在此种方案之下,易诱使投保人通过与保险人订立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转移财产或是将受益人由自己变更为第三人、进而逃避债务履行现象的产生。See Melvin D.Hill, Exemption of Life Insurance Cash Surrender Values from Bankruptcy Proceedings in Maryland - In re Posin, 22 Md.L.Rev.70(1962).
2.区分是获利型人寿保险还是生活保障型人寿保险。区分获利型与生活保障型的人寿保险,债权人仅能对获利型的人寿保险代位行使解除权,进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75〕同前注〔71〕,岳卫文。
3.权利滥用情形下代位解除的禁止。在债权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情形下,若存在权利滥用情形,则可通过禁止权利滥用规则禁止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而判断是否存在权利滥用情形,应以双方利益衡量为标准。〔76〕同上注。“权利的行使,以是否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应就权利人因行使权利所能取得的利益,与他人及社会因权利的行使所遭受的损失,比较衡量定之。若权利的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极少,而他人及社会所受损失甚大者,得视为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77〕1982年台上字第737号民事裁判书。转引自梁上上:《利益衡量论》,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84页。当债务金额与保单现金价值相比明显较小时,通过利益衡量可认定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将构成权利滥用。〔78〕同前注〔71〕,岳卫文。
4S=(b+e+h)+(d+e+f)+(a+e+i)+(c+e+g)=(a+b+c)+(d+e+f)+(g+h+i)+3e=3S+3e,所以有S=3e.由此可以得到:
4.引入介入权制度。即在债权人代位解除保险合同时,受益人或被保险人遗属等利害关系人可在向债权人支付相当于因保险合同解除所能受领的保单现金价值后,取得投保人之地位,以避免保险合同被强制解除。我国法并未明确提及介入权制度,〔79〕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时,对于投保人的债权人申请扣押或强制执行保单现金价值问题的处理,曾试图引进介入权这一制度。《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17条规定:“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当事人以其解除合同未经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同意为由主张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已向投保人支付相当于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款项并通知保险人的除外。”其在某种程度上肯认了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介入权的存在。在比较法上,德国和日本的保险法对介入权作了规定。例如,2008年通过的《日本保险法》第60条规定:“(一)扣押债权人、破产管理人以及死亡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以外的人解除保险合同时,在保险人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后,发生合同终止的效力;(二)受益人(依第一项进行通知时,除投保人之外,限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亲属以及被保险人)在征得投保人同意后,在第一项中所规定的一个月的期间经过之前,受益人向债权人支付相当于保险合同解除后保险人需支付给债权人的保单现金价值后,并且受益人将此告知保险人,此时不发生保险合同解除的效力。”
在处理债权人与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冲突时,对于以上处理路径笔者并不赞同。首先,通过区分人寿保险合同是否关系到第三人利益,判断债权人可否代位解除保险合同及法院可否强制执行保单现金价值,虽然具备明确、可行的操作标准,但本质上仍然是以受益人等第三人的利益更值得保护的观点看待这一问题。而且,当保险合同是利益第三人合同时,债权人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其次,区分对待获利型人寿保险与生活保障型人寿保险也并不可取。如今的人寿保险合同集投资与生活保障功能于一身,无法将此种复合型的人寿保险确定无疑地归入其中的某一类别。〔80〕同前注〔69〕,栗田达聪文,第122页;陈炫宇:《债权人得否代位要保人终止人身保险契约》,《法令月刊》第67卷第3期(2016年)。况且获利型与生活保障型属于主观判断范畴,两者并无明确的界定标准。〔81〕同前注〔69〕,栗田达聪文,第121页。
再次,规定在债权人滥用权利时,禁止债权人可代位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也不具可行性。在实践中,更多情形下债权人并不知道其行使代位权将导致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权利受损,更谈不上债权人恶意行使权利,因而很难将其归入权利滥用范畴。即使将权利滥用构成要件予以客观化,但对于客观化的权利滥用标准也难以把握,最终也只能通过民法的诚信原则等基本原则诉诸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解决。
最后,引入介入权制度能否解决债权人与被保险人及其遗属、受益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也存在疑问。介入权制度本身即可能存在缺陷,由于被保险人遗属或受益人有可能并无稳定收入来源而依赖于投保人生活,〔82〕同上注,第115页。其本来就是经济上的弱者,〔83〕同前注〔10〕,张冠群文。尤其是当被保险人遗属或受益人为未成年子女时,即使他们主观上有意愿行使介入权,在客观层面也无法有效行使该项法律权利。当然,笔者在此并非完全否认介入权这一制度,在下文提出的最优选择中,介入权规则仍然可作为配套措施予以适用。
(二)最优方案之证成:债权人代位行使保单质押借款权
无限制地承认债权人代位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将会侵害受益人等利害关系人的期待利益。尽管债权人享有代位权这一权利,但是债权人这一权利的行使与最终达到的目的之间可能并不成比例关系。质言之,在保单现金价值执行案件中,债权人代位权这一路径并非最优方案,也并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
比例原则本为宪法、行政法等公法领域中的原则,但在私法领域中亦有适用空间。按照比例原则的要求,手段与目的之间应符合比例要求,所选择的手段与目的之间应具备相关性,即所采用的手段应有助于目的的达成。同时,在所有有助于目的达成的手段中,应选择对基本权利损害最小的手段。〔84〕参见纪海龙:《比例原则在私法中的普适性及其例证》,《政法论坛》2016年第3期。在保单现金价值强制执行案件中,以债权人代位解除保险合同进而对保单现金价值进行强制执行,从而满足债权人的债权并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在此类案件中,对于债权人欲实现其债权的目的而言,其实现手段应有多种。其中,债权人代位解除保险合同并非对其他主体权利侵害最小的手段,还存在其他对受益人等利害关系人利益侵害更小的选择。
在人寿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享有一系列的权利,包括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保险合同解除之后的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保险合同存续达到一定期限后的质押借款权。〔85〕有学者形象地指出人寿保险是一系列选择的“打包”,这些选择包括解除保险合同、向保险人借款等。See David T.Russell, Stephen G.Fier, James M.Carson, Randy E.Dumm,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Life Insurance Policy Surrender Activity, 36 Journal of Insurance Issues 36(2013).此外,在分红型人寿保险中,投保人还享有红利分配请求权。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保险合同解除之后的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均在我国现行法中有直接的反映,红利分配请求权则属于分红型人寿保险所固有的权利,无需再经立法肯认。而对于投保人所享有的保单质押借款权,我国《保险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但实务中一般均承认投保人所享有的这项权利。〔86〕参见“张淑清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唐山分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2015)北民初字第1884号民事判决书; “赵贵云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石家庄分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正定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冀01民终9147号民事判决书;“郑岗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西藏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6)藏01民终385号民事判决书;“陈锋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0612民初4703号民事判决书。例如,《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寿险保单质押贷款业务有关问题的复函》(保监厅〔2008〕66号)第1条明确规定:“保单质押贷款是长期寿险合同特有的功能,是指投保人在合同生效满一定期限后,按照合同约定将其保单的现金价值作为质押,向保险公司申请贷款。”〔87〕《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寿保险保单质押贷款问题的批复》(银复〔1998〕194号)第2条对办理保单质押贷款应遵循的原则要求作出了明确规定。许多国家或地区均对投保人所享有的保单质押借款权利予以承认。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所谓“保险法”第120条第1项规定:“保险费付足一年以上者,要保人得以保险契约为质,向保险人借款。”人寿保险投保人之所以享有保单质押借款权,〔88〕关于保单借款的法律属性在理论层面存在争议,主要观点包括“预支现金说”“附有抵销预约之消费借贷说”“权利质权之消费借贷说”“解约金一部先付说”“质权说”“要保人特殊权利说”等。同前注〔10〕,卓俊雄文。是因为人寿保险存续时间较长,而投保人的经济状况在合同存续期间可能发生无法预见的变化,此时投保人固然可以行使其任意解除权以获取保单现金价值,但其后果是导致保险合同的解除。然而,如果承认投保人享有向保险人申请获取相当于保单现金价值数额借款的权利,一方面可避免保险合同被解除的后果,另一方面又可解决投保人资金困难的问题。〔89〕同前注〔5〕,砺波久幸文,第214页。
笔者认为,当作为投保人的债务人不能清偿其到期债务时,法律可承认债权人享有代位投保人行使保单质押借款权的权利。由于保单质押借款的金额以保单现金价值为基准进行计算,其与保单现金价值在金额上大体相当。如果说债权人可代位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并以合同解除后所能获得的保单现金价值实现自己的债权,此时保单质押借款同样可用以实现债权人的债权。同时,其可避免保险合同被解除的后果,使得受益人等利害关系人对人寿保险合同所抱有的期待不至落空,以此平衡债权人与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利益。相比于债权人代位行使解除权,此种处理方式也可兼顾保险人对维持保险合同所具有的期待。由债权人代位解除保险合同,固然可满足债权人的受偿需要,但是保险人对投保人也享有保险合同中的债权,其表现为保险费分期缴纳的请求权,保险人的此种债权也需保护,允许债权人代位解除保险合同剥夺了保险公司享有的维持合同存续的利益。因此,尽管债权人代位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可在现行法中找到支撑,但在存在其他更优的选择时,则不应优先选择这一路径。
不过,其仍然可能面临以下质疑。一是保单质押借款权的代位行使,固然可解决债权人债权受偿的问题,但既然投保人陷入经济困难而无力对外偿债,其也可能无法履行向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这一债务。在保险合同两年的效力中止期届满后,若投保人无法缴纳欠缴的保险费,保险人将享有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这与投保人代位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所产生的最终效果并无差异。二是即使不考虑投保人对于保险公司所负担的保险费缴纳义务,若借款本息超过保单现金价值时,保险合同也会发生自动终止的效果。〔90〕参见[日]仓泽康一郎:《投保人借贷》,《Jurist》第766号,第55页以下。转引自前注〔35〕,仓泽康一郎文,第76页。该质疑观点虽具有一定道理,但是相比于直接代位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而言,由债权人代位行使保单质押借款权对于保险人、投保人、受益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损害是最小的。首先,在债权人代位行使保单质押借款权时,保险合同并未被解除。虽然投保人此时可能因为无法缴纳保费从而致使保险合同面临效力中止的境况,但在两年的保险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投保人仍可能恢复债务清偿能力,此时其可偿还对保险公司所欠缴的保险费及相应借款。其次,此种处理方式也能与介入权制度有效衔接,在投保人无法偿还借款或保单质押借款本息金额超过保单现金价值时,若受益人等利害关系人存在维持保险合同的意愿,在投保人不反对的情形下,可通过行使介入权避免保险合同被解除。〔91〕依《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17条,自文义解释角度观察,该条中的介入权只存在于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之时。但是由于受益人等利害关系人行使介入权取代的是投保人的地位,依“举重明轻”的解释规则,既然在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时,受益人等利害关系人都可以行使介入权以阻止保险合同的解除,那么在保险人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时受益人等利害关系人自然也享有介入权。再次,即使在两年的保险合同效力中止期经过后,保险人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导致保险合同被解除,以致受益人等第三人的期待利益落空,这也无可厚非。因为此种情形下保险合同的解除已为《保险法》所明确规定,属于合同的正常解除,受益人等第三人的利益在此种情形下没有必要予以特别保护。在保单质押借款本息金额超过保单现金价值时,即便会产生保险合同自动终止的结果,其也属于人寿保险合同终止的常态,避免了第三人直接介入保险合同。更重要的是保险人的利益并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害,由于投保人所享有的保单质押借款权已经正常行使,此时保险合同的终止将使得保险人在保单质押借款本息范围内免除对投保人保单现金价值的返还义务。
因此,债权人代位投保人行使保单质押借款权可避免债权人或者法院直接介入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解除保险合同,如果投保人无法偿还对保险人的质押借款,保险合同效力的终止完全是保险合同当事人自身行为的结果,而不会产生第三人介入当事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将合同解除的表象,这将有利于减少当事人之间纠纷的发生。〔92〕相似观点参见前注〔35〕,仓泽康一郎文,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