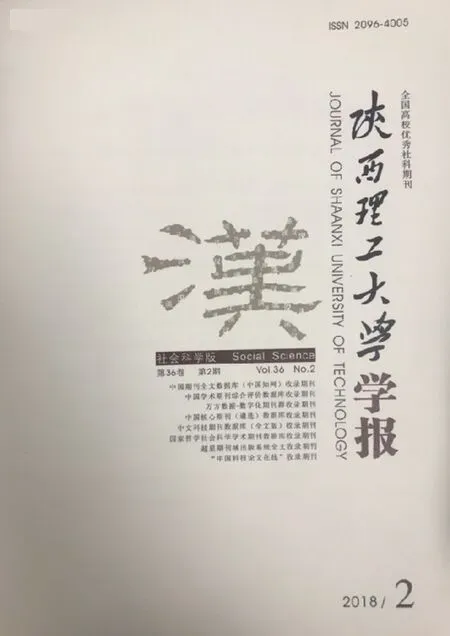论古代戏曲互动接受的艺术效果
汪 超
(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古代戏曲的接受场域附着浓郁的地域色彩和文化特质,同时呈现出场域形态的“多元化”与效果生成的“动态性”。“多元化”是指戏曲接受的参与主体纷呈,涉及文人曲家-艺人演员-读者观众等,他们或评点切磋,或同场观演,力求戏曲观演的最佳效果。“动态性”则指戏曲接受不同于诗词鉴赏停留于审美效果的静态呈现和文本“价值”的表现,而更重视不同主体、不同场域、不同方式的“对话”,涉及文人的评点交流、舞台本的改编传播,场上演出时艺人之间、艺人与观者之间的舞台互动等,都会推动戏曲效果的直接生成,所以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互动也促使即时效果的精彩呈现。
目前学界对于古代戏曲的接受研究渐成热点,如赵山林《中国戏曲传播接受史》总论戏曲艺术的传播接受,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侧重经典文本的接受研究等,但对接受效果的关注不多,仅有吴秀琼《<哈姆雷特>的语体风格及其戏剧效果》等文。古代戏曲接受效果形成的丰富内涵显然值得深入研究,这并不是简单套用西方文论的接受理论,进行古代戏曲接受阐释的具体实践,而是二者存在共同对话的理论平台。古代曲家如何面对戏曲“活”的综合艺术,构建起丰富精彩的效果理论阐述,本文试图梳理这一问题的重要内蕴和时代意义,从而展现古代戏曲“活”的艺术生态效果。
一、戏曲文本效果的接受解读
传统文学文本的接受多局限于作者-文本-读者的单线路径,至古代小说又增加了说书人、书坊主等角色。古代戏曲的接受形态则更为丰富,涉及戏曲文本的传播接受与剧场舞台的观演反应,戏曲接受呈现出文本与场上效果的双重表现。围绕戏曲文本展开的效果审视,则有文人曲家自我创作的效果期待,文人读者群体对于文本的鉴赏评点,艺人观众对于剧情的感应共鸣等,都是基于戏曲文本的文学元素得以铺展,从而实现戏曲接受效果的互动演绎。
一方面,古代戏曲文本承载着曲家的无限寄托,他们对此呕心沥血而成的文本,赋予不同程度的效果期待,希冀得到读者观众的普遍认同。不少曲家意识到戏曲效果实现的艰辛与波折,故而感叹“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期待“知音君子,这般另做眼儿看。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琵琶记》[副末开场])。另外,“有欢笑,有离折,无灵异,无奇绝,按父子恩情,君臣忠直,休言打动众官人,直甚感动公侯伯”(《新刊重订出像附释标注赵氏孤儿记·第一出副末开场[满江红]》)。清醒认识到戏曲效果的直接影响。有些文人曲家甚至注意到隐含效果的实现,并在文本创作之初即已明言,如《荆钗记》“新编传奇真奇妙,留与人间教尔曹,奉劝诸人行孝道”(《屠赤水批评荆钗记·尾声》)。“荆钗传奇会编巧,新旧双全忠孝高,须劝诸人行孝道”(《新刻原本王状元荆钗记·尾声》)。明确提出希冀达到“劝人行孝道”的戏曲效果。
另一方面,戏曲文本效果的能否实现,还需与接受群体进行互动交流,这既有文人读者的接受评点,又有艺人观众的心灵感应。
其一,文人曲家费尽才华而成的戏曲作品,能够得到同行文人的击节赞赏,可谓既是对文本效果的直接认同,又是对自我才情的高度肯定。同时作为作者的曲家也十分珍视读者的评点反馈,孔尚任曾十分明确地说出:“读《桃花扇》者,有题辞,有跋语,今已录于前后。又有批评,有诗歌,其每折之句批在顶,总批在尾,忖度予心,百不失一,皆借读者,顺笔书之,纵横满纸,已不记出自谁手。今皆存之,以重知己之爱。至于投诗赠歌,充盈箧司,美且不胜收矣,俟录专集。”[1]1对于文人读者各种方式的回馈表示出“知己之爱”的重视态度。可见,孔尚任一语道出文人读者的效果回馈,体现为“投诗赠歌”和“评点论析”等外在形式。梁辰鱼《浣纱记》曾风靡一时,王世贞有《嘲梁伯龙》:“吴阊白面冶游儿,争唱梁郎雪艳词。”[2]625此外还有汪道昆《席上观吴越春秋有作凡四首》、胡应麟《狄明叔邀集新居命女伎奏剧凡玉簪浣纱红拂三本即席成七言律四章》等,都直接赠诗表示观戏之后的欣赏态度。有些文人并不满足吟诗叹赏,而是开始动手评点剧本,展开对戏曲文本的情绪表达和冷静思索。评点文本体现出文人曲家自我情感的自然流露,如《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第十四出《堂前巧辩》红娘责备老夫人一段尾批:“这丫头是个大妙人。”[3]150有时读到情节生动或文辞美妙之处,直接简言“好”、“妙”的欣喜之情,抑或“我欲赞一辞也不得”[3]150。有时甚至为之手舞足蹈或是悲伤流泪,如汤显祖评《西厢记》第四折《佳期》:“读至崔娘入来,张生捱坐,我亦狂喜雀跃。”[3]237
古代戏曲文本效果的实现,从读者尤其是文人阶层的接受内容而言,大致表现在对于戏曲主题和文笔才情的欣赏。洪昇作《长生殿》第一出《传概》[满江红]即言:“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那论生和死。……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4]1所以刚问世时便有人称“是剧乃一部闹热《牡丹亭》”,洪昇对此创作宗旨的评价“以为知言”[4]1。汤显祖《牡丹亭》中杜丽娘超越生死的情感追寻,巨大的艺术魅力震撼无数青年男女,娄江俞二娘反复诵读并再三品味,终而悲情过度断肠而死,汤显祖听后也伤感不已作诗痛悼:“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5]710这些“天下有心人”的女性读者,都是感于爱情的知赏共鸣。对文笔才情的肯定同样如此,不少文人曲作极尽铺衍藻丽之能事,如屠隆《昙花记》《彩毫记》等剧,“学问堆垛,当作一部类书观”,而被时人称为“才士之曲”,他们希冀的是“奇文共赏析”的审美效果。[5]20
同时,多元纷呈的接受效果又逆向影响戏曲文本的再创作,身为作者的文人不仅在意读者的评价意见,而且邀请他们直接参与戏曲文本的修订润色。汤显祖早年创作《紫箫记》,好友孙如法就曾转告:“尝闻伯良(王骥德)艳称公才而略短公法。”汤显祖对此表示“良然”,并且希望日后“当邀此君共削正之”[6]171。清初洪昇创作《长生殿》经历十六年的润色修改,完成《沉香亭》到《舞霓裳》再到《长生殿》的转变,前一次转变正是接受懂词曲的朋友毛玉斯的意见,认为与屠隆《彩毫记》近似故而“排场近熟”,“因去李白,入李泌辅肃宗中兴,更名《舞霓裳》”。后一次华丽转身则是好友兼“第一读者”徐麟的意见反馈,并且经常一起“审音协律,无一字不慎”[5]1,所以才有“爱文者喜其词,知音者赏其律”的文本效果。[5]228
其二,文人曲家对于文本效果的主观期待,不仅在于读者群体的鉴赏评点,而且还有艺人观众的感应共鸣。孔尚任创作《桃花扇》“十载经营,三易其稿,博采遗闻,入之声律,一句一字,抉心呕成”,可是待他带入京城希冀为人所识,却是“借读者虽多,竟无一句一字着眼看毕之人”,孔尚任为此“每抚胸浩叹,几欲付之一火”[1]2。即使如此他还是“转思天下大矣,后世远矣,特识焦桐者,岂无中郎乎?”而当看到“金斗班”元宵演出时,特别赞赏“《题画》一折,尤得神解”[1]2。后来孔尚任不断看到自己作品得以精彩演出,并且受到观众的普遍认可,“群公咸集,让予独居上座,命诸伶更番进觞”,同时“座客啧啧指颐”,孔尚任也“颇有凌云之气”[1]2。呕心沥血而成的作品终究获得好的戏曲效果,也是曲家颇为欣慰之处。
当然,文人曲家精心创作并且希冀的效果期待,还需演员的精彩演绎和观众的会心领悟,才能促使戏曲效果在此互动交流中完美实现。明末杭州女演员商小玲最擅长演《牡丹亭》传奇,每次演到《寻梦》、《闹殇》等出戏时,仿佛身临其境而泪痕满面,终于在唱到《寻梦》“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时,一并想起自己的相同遭际,悲痛地倒在舞台上香消玉殒。《牡丹亭》一经演出就会招致妇女争相观看,为此而被诋毁为“导以淫词,有不魂消心死者哉?”因为“炽情欲,坏风化”而一度被禁毁[7]29。这恰从另一方面透露出女性观众对《牡丹亭》的会心领悟,正是由于其富于强烈的艺术震撼力,才触发观众的感动而引起轰动效果。
文本效果的互动交流有时也会存在某些误解和不畅,读者对于作品的误读不解,以及演员对于作者文本的妄加改动,也使得文本效果的实现形成不同层面的错位和受阻。汤显祖作《牡丹亭》招致当时不少文人曲家不合格律的批评,认为难以获得较好的舞台效果,故而他们纷纷动手改编才引起汤显祖的不满。洪昇《长生殿》因为“伶人苦于繁长难演,竟为伧辈妄加节改,关目都废”。为此洪昇特意叮嘱“当觅吴本教习,勿为伧悮可耳”[5]1。孔尚任作《桃花扇》一时轰动,不少文人曲家技痒难耐并动手改编曲本,“顾子天石读予《桃花扇》,引而申之,改为《南桃花扇》。令生旦当场团圆,以快观者之目;其词华精警,追步临川。”孔尚任也不得不表示遗憾之情,“虽补予之不逮,未免形予伧父,予敢不避席乎。”[1]1此外,演员根据舞台演出的需要,也会对文本进行删节改动而引起作者的不满,“优人删繁就简,只歌五六曲,往往去留弗当,辜负作者之苦心。今于长折,止填八曲,短折或六或四,不令再删改也。”同时,对于戏曲文本中的说白部分,“旧本说白,止作三分,优人登场,自增七分;俗态恶谑,往往点金成铁,为文笔之累。今说白详备,不容再添一字。”[1]9作为作者的文人曲家针对互动过程的错位误解,不得不表示出自己的明确态度。
戏曲文本效果的实现还与出版流通领域的书坊主有关(明清时期不少曲家同时身为出版商,如汪廷讷等),他们主要着意外在形式的精益求精,如印刷纸张的选择、刻工技艺的苛求、文本字体的斟酌等,试图促使文本效果臻于完美,希冀为读者所悦目赏心。其中戏曲文本的图像本为辅助说明之用,使得内容表现得多样化和形象化,正因为此,不少文人曲家与书坊主开始讲究文本图像的处理,如晚清著名的戏曲出版家刘世珩出版《暖红室汇刻传剧》,就是聘请当时名家为剧本增加补充精美的图像,“旧有绣像图画,皆室人江宁傅晓虹(春姗)所模。无者补画。画者,钱塘汪待诏社耆(洛年)、长沙李贰尹仲琳、休宁吴县尉子鼎、吴县周布衣乔年。”[8]2戏曲文本的画像不再仅是作为简单的补充,而是融入戏曲文本成为效果实现的重要拼图。
古代戏曲在其发展的相当一段时间内,随着文人群体大量介入文本创作,使得戏曲效果的实现大多停留于文本层面,与读者交流密切的文本效果得到放大,成为案头把玩赏读的文学作品,而失却戏曲场上效果的另一特性。戏曲作品一度成为文人曲家自我宣泄的载体,如屠隆感于才高背弃而作《彩毫记》以李白自况,抒叹心中满腹牢骚不平之气,故而被评价为“学问堆垛,当作一部类书观,不必以音律节奏较也”[9]20。这或许也是文本效果过于彰显所带来的弊端。
二、戏曲场上效果的演赏互动
戏曲效果更具特色地立体呈现还在于立足剧场舞台,围绕艺人-观众、艺人-艺人、观众-观众等主体之间的演赏互动,实现动容、动心、悦目、赏心的多元形态。不过,不同演出场所形成的演出效果也各自不一,如勾栏瓦肆、厅堂楼台、酒楼茶肆、虎丘西湖等地,外化为观众的会心一笑、或鼓掌欢呼,或低眉抽泣、或呐喊震天,都是以舞台为中心表现出的不同戏曲效果。
舞台剧场效果的精彩实现,既有艺人自身的修养熏陶、技艺精湛,又有艺人与艺人之间的心有灵犀、同台对戏,艺人与观众之间的情感沟通、演赏互动,同时作者主观的剧本设计即已关注舞台演出的需要,冷热场的调剂、文武戏的中和等,以及剧场布置,舞台道具、背景、服饰、化妆等斟酌,都为舞台效果的最佳呈现铺垫准备,成为共同影响场上效果的诸多元素。
其一,“曲之工不工,唱者居其半,而作曲者居其半也。”故而“作曲者与唱曲者,不可不相谋也”[10]179。舞台效果的精彩演绎与文本创作的前期铺垫密切相关,文人曲家同样究心于戏曲文本场上效果的实现。明末清初阮大铖《石巢戏曲四种》、李渔《笠翁十种曲》等剧,都着意结构关目的新奇、舞台表演的闹热,从创作者角度介入场上效果的多层建构,有的甚至直接参与指导戏曲表演并提出修改意见:“是书义取崇雅,情在写真,近唱演家改换有必不可从者,如增虢国承宠、杨妃忿争一段,作三家村妇丑态,既失蕴藉,尤不耐观。其<哭像>折,以哭题名,如礼之凶奠,非吉奠也。今满场皆用红衣,则情事乖违,不但明皇钟情不能写出,而阿监宫娥泣涕皆不称矣。至于舞盘及末折演舞,原名霓裳羽衣,只须白袄红裙,便自当行本色。细绎曲中舞节,当一二自具。今有贵妃舞盘学浣纱舞,而末折仙女或舞灯、舞汗巾者,俱属荒唐,全无是处。”[5]1洪昇分别从情节处理和舞台表演方面指出乖违“崇雅”、“写真”的审美标准,从而难以实现其预期设想的场上效果。
其二,艺人在场上表演的精彩与否同样关系效果期待的实现,他们或完全忠于剧作者的本意兢兢表演,或根据舞台演出的需要动手删改,对于戏曲场上效果实现起到较为关键的作用,故而元代胡祗遹从形态举止到歌唱表演提出“九美”之说,明代潘之恒《与杨超超评剧五则》总结出“度、思、步、呼、叹”的表演五要素,都意在探究提升艺人的表演技艺,达到最佳的舞台形象与表演状态。
艺人不仅要求自身技艺水平高超,而且艺人与艺人之间也须艺逢对手,才能取得较好的场上效果。《消寒新咏》记载了不少优秀的艺人搭档,如集秀扬部小旦倪元龄与贴旦李福龄,“年岁相若,身材颉颃,即技艺亦相上下。”“元龄宜笑,福龄善哭。”“论怡情,福龄少逊元龄之风致;论感怀,元龄不如福龄之逼真。各有好处,不容没也。”最难得的是二人“同歌合演,如《水漫》《断桥》《思春》《扑蝶》《连厢》以及《忠义传》之扮童男幼女,彼此争奇,令观者犹如挑珠选宝,两两皆爱于心,莫能释手。斯诚一对丽人,可称合璧者也”[11]64。二人之间不仅心心相惜而且艺逢对手,高手之间的心灵默契铸就了场上经典的表演瞬间。
其三,从观者层面而言,“楼上所赏者,目挑心招、钻穴逾墙之曲,女座尤甚;池内所赏者,则争夺战斗劫杀之事。”[12]254虽然来自不同的地域、阶层导致关注不同的欣赏目的,但是场上效果的追求无非两个层面:既要“看戏”又要“看艺”。“看戏”重在戏曲表现内容即情感体验而言,如《清忠谱》《桃花扇》等反映现实的作品曾引起明末清初的观众强烈反响,但有些观者对戏曲内容早已烂熟于心,所以这时更在意“看艺”即领会表演者的技艺,如“静如处女,动若脱兔;重如泰山,轻若鸿毛”的形体美,“声要圆熟,腔要彻满”,还要“眼灵睛用力,面状心中生”,“有意有情,一脸神气两眼灵。”潘之恒说自己“观剧数十年”,而“今垂老,乃以神遇”[13]44-45,已经上升到讲究神交的境遇。清末谭鑫培演出《天雷报》(《清风亭》),观者“并肩累足,园中直无容人行动之余地”,无非欣赏谭鑫培的精彩表演,“慷慨激烈,千人发指”[14]5120,还有谭鑫培扮演的张元秀痛斥忘恩负义的张继保一节,引得观者“视台上之张继保,如人人公敌,非坐视其伏天诛,愤气不能泄,故竟不去”,直到张继保被天雷击死,观者“乃相率出门。时雷雨方来,霑塗颠踬者,踵趾相错。早去刻许可免,而人人意畅神愉,虽牵裳蒙首,扶掖而行,而口讲指道者,……咨嗟叹赏,若忘饥饿,天雨道滑不顾者,评笑百出,旁观疑痴”[14]5120。当然二者也有不合之处,如彭天锡“多扮丑净,千古之奸雄佞倖”[15]202,与清末名净黄润甫等,观者既为其所演人物而深恶痛绝,又为其表演技艺之高超而欢呼叫绝,在看戏与看艺的分裂冲突中获得强烈震撼的舞台效果,真是“作戏者疯,看戏者傻”。[16]88
故而,艺人-观者的互动演赏影响场上效果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艺人的精彩表演带动观者情绪的变化,铺展较强的舞台效果;另一方面观者的欣赏反应也影响艺人的表演,甚至促进他们技艺的提升。
艺人的精彩表演带来轰动的场上效应多有记载。袁中道《游居杮录》记载万历年间一次演出:“极乐寺左有国花堂,前堂以牡丹得名。记癸卯夏,一中贵造此堂既成,招石洋与予饮,伶人演《白兔记》。座中中贵五六人皆哭欲绝,遂不成欢而别。”[17]81清代王载扬《书陈优事》记载陈明智饰演楚霸王时,在场观众“皆屏息,颜如灰,静观寂听”,等到结束才“哄堂笑语,嗟叹以为绝技不可得”[18]198。张岱《陶庵梦忆》记载演出《冰山记》时“声达外,如潮涌,人人皆如之。杖范元白,逼死裕妃,怒气忿涌,噤断嚄唶。至颜佩韦击杀缇骑,嘄呼跳蹴,汹汹崩屋”[15]271。可见艺人的精彩表演所带来的震撼效果。
观者的欣赏反应也反过来影响艺人的场上表演,所以不少艺人十分在意观者的在场情绪。程长庚“性独矜严,雅不喜狂叫,尝曰:‘吾曲豪,无待喝彩,狂叫奚为声繁则音节无能入。四座寂,吾乃独叫天耳。’客或喜而呼,则径去”[19]725。认为观众如果随意喝彩则会影响表演的顺利进行,从而导致“音节无能入”的尴尬效果。潘之恒《鸾啸小品·技尚》记载无锡邹光迪家班表演时,“主人肃客,不烦不苛,行酒不哗,加豆不迭。专耳目,一心志,以向技,故技穷而莫能逃。”[13]44-45正是如此环境才有利于艺人才能的最佳发挥,“拜趋必简,舞蹈必扬,献笑不排,宾白有节,必得其意,必得其情。”[13]44-45艺人的精彩表演同时又使观众深受熏染,出现“坐中耳不宁倾,目不宁瞬,语交而若有失,杯举而亟挥之”[13]44-45。这样良好的互动效果直接推动戏曲艺术的最佳演绎。
观者的在场态度和反映也大概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无论是喝彩欢呼还是羞辱倒喝,都会影响艺人现场表演水平的发挥,如徐珂《清稗类钞》记载清末北京皮黄戏演出场面:“贩夫竖子,短衣束发,每入园聆剧,一腔一板,均能判别其是非,善则喝采以报之,不善则扬声以辱之,满座千人,不约而同。或偶有显者登楼,阿其所好,座客群焉指目,必致哗然。故优人在京,不以贵官巨商之延誉为荣,反以短衣座客之舆论为辱。”[14]5107另一方面观众水平的高低和评价的优劣,也能促使艺人不断提升自我技艺水平。观众的水平越高,评价要求越苛刻,也反过来督促艺人更加出色地呈现最佳艺术效果。李渔《闲情偶寄》所云“观者求精,则演者不敢浪习”[20]74。正是说明观演相长的互动现象。李开先《词谑》记载明中叶艺人颜容在《赵氏孤儿》中扮演公孙杵臼,虽然他“备极情态”,“喉音响亮”,但还是“听者无戚容”,于是下场后“左手捋须,右手打其两颊尽赤。取一穿衣镜,抱一木雕孤儿,说一番,唱一番,哭一番,其孤苦感怆,真有可怜之色,难已之情”。故而再演出时则是效果大变,台下“千百人哭皆失声”[21]353-354。更有甚至明末南京戏班中兴化部的马锦,为扮演好《鸣凤记》中严嵩角色,马伶去北京宰相顾秉谦家中当三年仆人,“察其举止,聆其言语”[18]202,归毕再演终究惊倒四座。
因此,舞台效果的最佳呈现既是艺人与观者之间互动而成,又可以说是他们之间默契的结果。艺人还要紧扣观者的心理,形成台上台下的心灵契合,才能实现最佳的舞台效果。焦循《花部农谭》记录花部剧本《清风亭》与昆剧剧本《双珠记》的不同效果,回忆自己年幼观剧前天演《双珠记天打》“观者视之漠然”,第二天演《清风亭》则“其始无不切齿,既而无不大快。铙鼓既歇,相视肃然,罔有戏色;归而称说,浃旬未已”。说明从主体创作层面,效果的影响因素还有花部“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22]229。所以作者考虑爱憎分明的情感要素、合情合理的戏剧结构、入木三分的人物塑造,都是紧扣观者的欣赏心理,才能取得较好的戏曲效果。此外,不少戏曲的结局也可谓作者、演员、观者共同默契的结果,无论是大团圆的结局,还是如“戏文之首”《赵贞女蔡二郎》的结尾是蔡伯喈弃亲背妇并为暴雷震死,都是强烈爱憎下的一种默契通合。观者与演者之间的约定谋合,才能促成震撼人心的强烈效果与戏曲呈现。
三、结语
通过对文本效果与场上效果的双重梳理,文人曲家、艺人演员、读者观众之间的多重互动,基本展现出古代戏曲接受效果的独特魅力,如《西厢记》《牡丹亭》等经典作品的登台亮相,都是“列之案头,歌之场上,可感可兴,令人击节叹赏,所谓歌而善也。若勉强敷衍,全无意味,则唱者听者,皆苦事矣”[1]9。经过案头与场上不断地润色删改,真正做到“十年磨一戏”,慢慢形成文本效果与场上效果俱佳的审美状态。
同时,古代戏曲的接受效果也为我们提出很多值得深思的命题,这既是对古代戏曲演变的审视总结,又是对当下戏曲发展的借鉴参考。比如当下戏曲界不少作品演出问世后,各种新闻报道或评论刊物中专家好评如潮,但是却无法实现与之对应的票房收入,专家的好评与所获的奖项无法弥补其舞台效果的迷失。所以,如何实现专家叫好与观者叫座的理想效果、剧本效果与舞台效果的完美融合等,既是戏曲接受效果研究的重要内容,又是当下戏曲界共同发展的时代命题。
[参考文献]
[1]孔尚任.桃花扇[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
[2]王世贞.嘲梁伯龙[M]//弇州山人稿:卷四九.四部丛刊本.
[3]伏涤修,等,辑校.西厢记资料汇编:上册[M].合肥:黄山书社,2012.
[4]洪昇.长生殿[M].徐朔方,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5]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M].徐朔方,校笺.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
[6]王骥德.曲律[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
[7]史震林.西青散记:卷二[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7.
[8]刘世珩.汇刻传剧自序[M]//暖红室汇刻传剧:卷首.贵池刘氏暖红室刻本.
[9]祁彪佳.远山堂曲品[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
[10]徐大椿.乐府传声[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
[11]铁桥山人,等.消寒新咏[M].周育德,校刊.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
[12]包世臣.都剧赋[M]//赵山林.安徽明清曲论选.合肥:黄山书社,1987.
[13]潘之恒.与杨超超评剧五则[M]//汪效倚,辑注.潘之恒曲话.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
[14]徐珂.清稗类钞:十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张岱.陶庵梦忆[M].蔡镇楚,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3.
[16]王梦生.梨园佳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15.
[17]袁中道.游居杮录:卷四[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18]焦循.剧说[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
[19]陈澹然.异伶传[M]//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
[20]李渔.闲情偶寄[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
[21]李开先.词谑[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
[22]焦循.花部农谭[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