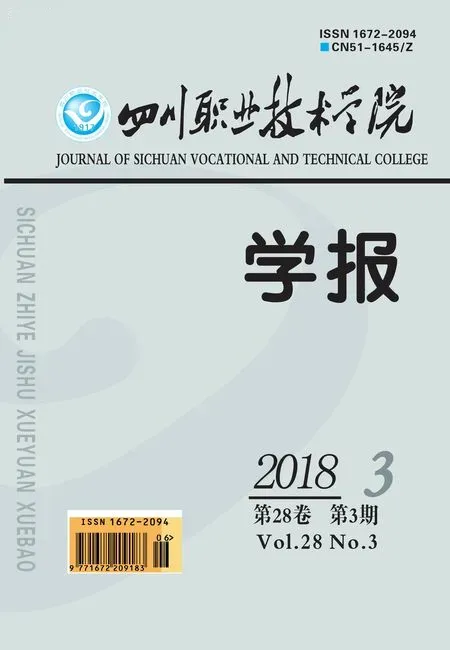四川方言多功能词“走”的用法及语法化
欧雪雪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四川方言里的“走”除了和普通话的动词“走”意义、用法一致外,它还可以作介词,类似于普通话里的“从”和“到”。鉴于方言“走”的用法比较特殊,本文将对“走”的基本用法作细致描述,并厘清“走”的语法化过程,通过和其它方言作比较来揭示“走”不同于普通话的特殊用法。
本文语料主要来自笔者对自己母语的调查和内省。发音人情况:1.陈云祥,女,1947年生,成都市西航港人。2.张开琼,女,1966年生,四川广安人。
一、“走”的用法
(一)“走”作动词
“走”在四川方言中和普通话一样,是个常用动词,古代为跑义,今为行义,在句中主要作谓语,如“我们走路过去”。但在四川方言中,“走”除了作谓语外,还可以作补语,如:
(1)你把车子开起走嘛。
(2)你把这本书带起走。
(3)你不要盯倒别个看,快点做起走哟。
(4)不要等他了,我们吃起走嘛。
以上例句中的“走”虽然都做补语,但意义有所不同。其中,例(1)(2)的“走”是句子的语义重心,表示事物的“位移”,意义较实。我们也可以将句中的“起”省略,直接说成“开走”、“带走”而不影响句子的原义。而例(3)(4)中的“走”不再具有“空间位移”这一实义,只表示“动作的趋向”,意义明显虚化,它只能和“起”连用,表达“某个事件继续往下进行”这一语义。
(二)“走”作介词
介词是汉语虚词里的一个大类,根据语义功能,内部能够分为很多小类,如介引处所、时间、对象、方式、原因、范围等各类介词。四川话里的“走”作为介词,能够引介处所和时间。
1.引进处所
“走”引进处所,表示起点,表示经过的路线、场所,只用于口语,如:
(5)你走哪儿回来的?—我走图书馆回来的。
(6)你走这页开始看。
(7)走这儿开始,一个个挨倒去检查。
(8)小偷是走墙上翻进来的。
(9)我走江北机场坐的飞机。
(10)他走后门进来的。
其中,例(5)(6)(7)表示动作的起点,例(8)(9)(10)表示经过的路线,都是指空间。“走”作为介词,后面跟表示处所的词语,在句中作状语,用来引进事件发生的地点场所,既可以是处所代词,如例(5)(7)中的“哪儿”和“这儿”,也可以是处所名词,如例(10)中的“后门”;既可以是大地点,如例(9)中的“机场”,也可以是较小的地方,如例(6)中“这页”。但在“从东到西”、“自四川到重庆”这样的格式中,“从/自”不能换成“走”,使用范围比较狭窄。
另外,我们需要注意,“走”引进处所时,既可以引进起点,也可以引进终点,如在“你走哪儿来”和“你走哪儿去”两句中,前一句中的“走”相当于“从”,引进起点,后句中的“走”相当于“到”,引进终点,意义完全不同。“走”到底引进起点还是终点,需要依据具体的语境来判定。
2.引介时间
(11)这封信走上个礼拜就寄出去了,到现在都还没得消息。
(12)这房子是走上个月开始装修的。
(13)他走去年子就开始生病了。
“走”引进时间时,后面常常跟表示过去的时间名词,暗含从过去到现在这一时间段中事件没有完成或保持某种状态不变,如(12)暗含“房子还没装好”这一信息,(13)暗含“病还没好”这一信息。同样,“走”也不能用于“从...到...”的结构中,如“从早上到晚上”、“从昨天到今天”。
3.“走”和“从”比较
吕叔湘在《现代汉语八百词》(2016:130—131)对介词“从”作了以下三种解释:
①表示起点,又细分为:a指处所、来源,b指时间,c指范围,d指发展、变化。
②表示经过的路线、场所。
③表示凭借、根据。
我们先来看一组例句:
(14)a我刚走街上回来。/b我刚从街上回来。(表示起点,引进处所、来源)
(15)a他走去年就开始工作了。/b他从去年就开始工作了。(表示起点,引进时间)
(16)a我们走小路去近些。/b我们从小路去近些。(表示经过的路线、场所)
(17)*这件事你要走实际情况来考虑。/这件事你要从实际情况来考虑。(表示根据)
从以上例句我们可以看出,“走”在四川方言里作介词,类似于“从”,但两者还是有明显区别:“从”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可以引介时间、处所、范围等,而“走”只能引进“时间”和“处所”,不能引进范围,不能表示凭借、根据,范围十分狭窄。“走”在四川方言里作为一个“动介”两用的词,动词的使用频率大大超过介词,因而人们更习惯采用纯粹的介词“从”,而不是“走”。
二、走的语法化
在谈“走”的语法化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对语法化和虚化的概念以及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简单介绍。语法化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语言理论,Millet在1912年首次使用了语法化这一术语。国内学者吴福祥对之进行了本土化的解释:“语法化指的是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产生和形成的现象。典型的语法化现象是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语或结构变成无实在意义的、仅表语法功能的语法成分,或者一个不太虚的语法成分变成比较虚的语法成分(2004,吴福祥)。”而虚化现象是汉语语法发展的一种重要现象。蒋绍愚认为,由实词变化虚词,词汇意义变为语法意义就是虚化。实词虚化和语法化虽有相似之处,但并不等同。吴福祥曾指出两者之间的差别:“语法化关注词汇或结构,甚至也关注语用法如何演变为语法形式,而实词虚化是训诂学术语,主要针对语义而言,包括词义消失产生语法意义、语义抽象化、泛化、弱化等(2002a)”。根据当代的语法化理论内涵,可以说实词虚化研究只是语法化研究中的一部分。
汉语中,几乎所有的介词都是从动词虚化而来的,但虚化程度不一样。有的虚化程度较高,完全丧失了动作、行为等义,变为纯粹的介词,如“从”、“当”;有的虚化程度较弱,保留了部分动作、行为的意义,因此在现代汉语的词类中存在着大量动介兼类的现象,四川方言里的“走”就属于后一类。“走”本身是一个表“行”义的动词,但在四川方言中又如何虚化为表示经过的路线、场所的介词呢?刘坚(1995)指出“许多实词的语法化过程都是句法位置改变和词义变化两方面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四川方言中的“走”也遵循这一规律,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句:
(18)兔走触株,折颈而死。(《韩非子·五蠹》)
(19)公子纠走鲁,公子小白奔莒。(《吕氏春秋·贵卒》)
(20)孩儿每出外闲走,被军人笑骂。(《新编五代史平话·汉史上》)
例(18)中的“走”用的本义“跑”,其后不带宾语,是不及物动词。例(19)中的“走”意义发生了变化,是“奔向某地”之义,其后可以跟宾语,表示“走”这一动作行为的方向,但仍含有“奔跑”之义。例(20)中的“走”意思已经和现在一样,为“行走”之义。王力认为“走”当“行路”讲最早产生于明代,而据杨克定(1994)考证,“行走”义产生的年代至少可以提前到唐五代时期。是否还可提前,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无论如何改变,以上例句中的“走”都含有“空间位移”这一实义,句法结构为“S+V+(O)”,在句中作主要动词,不管是词义还是句法位置,都没有发生变化,这时的“走”还不具备虚化为介词的条件。我们再来看以下几个例子:
(21)我走外婆家去。
(22)你走哪儿回来哟?
(23)我是走电视上看到这个消息的。
(24)她走上个礼拜起就不和我说话了。
我们分析(21)—(24)可以发现,“走”的句法位置发生了变化,开始出现在“S+V1+O1+V2+(O2)”的连动句中,这就满足了上文提到的“语法化过程中,句法位置发生改变”的条件。但语法化必须还同时满足“词义变化”这一条件,下面我们就来具体来分析“走”词义的虚化。
在例(21)中,“走”处于“V1”的位置,后面跟处所名词,表示“走”这一行为、动作的方向。V2由表“往、到”的“去”充当,V1和V2是同义词,都具有“移动”义。但由于“走”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都处于“V1”位置,意义开始虚化,使我们有了重新分析的机会。《汉语方言大词典》将该句中的“走”解释为动词“往、到”的意思,而卢小群的《湘语语法研究》(2007:166)却将它分析为“介词”,表动作、行为的方向。夏俐萍(2004)认为把“走”既看成动词,又看成介词的用法,是“走”字虚化的开始。我们认为,该句中的“走”应该分析为动词,但已经具备了向介词虚化的句法条件。
例(22)中“V2”还是由表“行为动作”的动词“回来”充当,“移动”义明显,但“走”的“移动”义却开始弱化,不能再分析为表“行走”的动词,而应该理解为介词“从”。此句中的“走”开始成为介词了。
例(23)中,V2由和“行为动作无关”的动词“看”充当,不再具有“移动”义,“走”后面跟方位短语,只表示动作的来源、出处,无实义,说明它已经完全虚化。
例(24)中“V2”不再具有“移动”义,而且“走”后面开始跟时间名词,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与动作行为完全无关。“走”由表空间上的“位移”转变为表时间上的“位移”时,虚化过程就彻底完成了。
“走”从结构“S+V+O”再到“S+V1+O1+V2+(O2)”,逐渐和其它动词连用,形成连动句,并随着该句式的长期使用,“走”逐渐固定在“V1”的位置,意义渐渐虚化,再随着“移动”义的完全脱落,“走”字的虚化就完全完成。夏俐萍(2004)将湖南方言中的“走”语法化过程梳理如下:连动句→接与行动有关的动词→接与行动无关的动词→从(时间名词)。四川方言中的“走”语法化路径也大致相同:普通动词→意义较实的连动句→意义较虚的连动句→介词。
三、与其它方言比较
(一)“走”作介词
“走”作介词是一种特殊用法,普通话里不这样用,但在南方地区,“走”作介词的用法非常普遍,但并不完全相同,我们先来看“走”作介词时在其它方言的用法。
1.“走”引进时间
湖南(夏俐萍,2004)
(25)走他病伽起,他冒笑过。
(26)走早晨到夜里,都热得要死。
丹阳(蔡国璐,1994)
(27)走旧年起我就开始上班了。
2.“走”引进处所
扬州(王世华,1996)
(28)走三元路到文昌楼。
成都(张一舟等,2001)
(29)你走哪儿回来的?
丹阳(蔡国璐,1994)
(30)走格里到过里有五十公尺。
从例(25)—(30)我们可以看出,“走”作介词,其共性是都能引进时间或处所,但用法有所差异。如在湖南、丹阳和扬州话中,“走”可以用在“走...到...”结构中,表示时间或事件的持续,相当于“从...到...”或“自从”。石毓智(2006:124)曾提到“语法化是一个程度问题,判断一个词的语法化程度高低有几个标准,‘可出现句法环境的扩大’就是其中之一。”“走”在上述方言中可以用在“走...到...”的结构中,出现的句法环境明显扩大,而四川方言没有这一用法。这说明,在四川方言中,“走”作介词的使用范围十分狭窄,语法化程度不如其它方言。
(二)“走”作语气词
“走”的特殊用法除了作介词外,还可以放在句末作语气词,这在其它方言很少见到,目前见于正式报道的只有晋南万荣、临猗和宁夏银川、灵武等。如:
(33)我跟上你找他走(李树俨等,1996)(银川)
(34)你连我装车走。(李树俨等,1999)(灵武)
(35)走地里走。(吴建生等,1997)(万荣)
从以上例句我们可以发现,“走”作语气词时,主语只能是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表示一种祈使语气。李莺在《中宁话的“走”字句中》(2005)提到“中宁话”中“走”的虚化过程。他认为:“‘走’字处于动词后补语的位置上表示趋向,后来由于表行动行为的意义主要由第一个动词充当,“走”的“行”义就开始虚化,不再作补语,而虚化成了语气词”。根据以上所述,中宁话“走”的语法化路径可拟为“趋向动词〉趋向补语〉语气词”。四川方言中的“走”也可以放在句末作补语,如“你从昨天看的那集看起走”。但该句中的“走”意义虽然虚化,却仍具有一定的趋向意义,不能省略。它不具备中宁话完全虚化为语气词的条件,而是必须和“起”连用共同作补语,表示事件继续往下进行,因而语法化路径应为“趋向动词〉趋向补语”。
通过和其它方言作比较,我们发现“走”作介词的用法在南方方言中比较常用,只是虚化的程度有所不同。而虚化为语气词的用法却很特殊,只在少数方言中存在,这也体现了语言在演变中的共性与个性。
结语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四川方言中“走”的语法化路径有两条:一是出现在连动句中,虚化为介词;二是出现在“动词+走”的结构中,作趋向补语,具体路径为趋向动词〉趋向补语。前者在南方方言中比较常见的,后者在甘肃、陕西等少部分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变成语气词。“走”的用法如此丰富,很有可能与四川复杂的方言有关。四川方言发源于古蜀语和古巴语,但三百多年前,“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使得四川涌入大量的外地移民,他们带来的语言与四川本地方言接触融合,逐渐演变成今天的四川方言,因而四川方言中有许多外来成分,如湘语、客家方言等。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四川方言中的“走”和湖南方言中的“走”用法几乎一样,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猜想:走的介词用法是否就是湘语的遗留。当然,这还需要大量的理论事实作为依据,这里仅作为一种研究思路进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