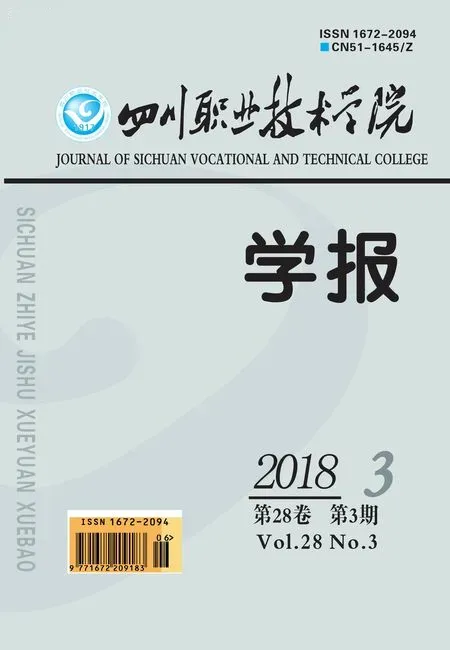蒂姆·伯顿电影的文化研究
孙健风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24)
一如柏拉图著名的“洞穴寓言”,光影世界尽管可以“无限趋近于生活的渐近线”[1],但这是一条始终“无限趋近”却永远不到达的“渐近线”。它可以惟妙惟肖地呈现表象世界,但究其实质,却只能作为现实世界的镜像投射。因而作为一个电影理论者,对影片的解读,不仅是专业化的电影欣赏,而且是电影的揭秘——将一部影片放置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之中,以发现其中的“秘密”。尼采预言:“现代人已经开始预感到那种苏格拉底式的求知欲的界限,因而在茫茫知识海洋上渴望登岸”[2]。如今人们真的登上了这个多元解构的社会彼岸,但随之而来的也是荒诞不经、封闭孤独的生存真相。知识失去了自身的合法性与客观性,人类陷入价值体系崩塌的恐惧中。
自俄狄浦斯开始,个体似乎就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在与生存背景的疏离中摇摇欲坠。在蒂姆·伯顿的电影中,特立独行的人物与怪诞诡异的环境之间总是存在着巨大张力,存在的或逝去的“畏”里蕴涵着深刻的悲哀。孤独与喧闹、恐怖与狂欢、黑色与童话。伯顿的影片是古老悲剧的具体变形,个体在此遭遇虚无荒谬,并进行存在沉思,最终通过“是”的过程意义完成自我身份和价值归属的确认。
一、崇高悲剧
悲剧肇始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其有如下界定:“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3]。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通过模仿生活,让人产生恐惧与怜悯,从而使心灵得到宣泄净化。到了西方文化颠覆者尼采那里,悲剧则通过展示个体的痛苦与毁灭,让人产生独特的审美快感。悲剧是与酒神狄奥尼索斯放纵力量结合的产物,悲剧精神的真谛乃是酒神精神中狂放不羁的迷醉和不可遏制的生命冲动。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中指出崇高是一种强烈的艺术效果,“如同作品给予读者强烈的情感震撼、思想冲击,以及雄浑、庄严、激越的情感体验”[4]。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崇高是生命力受到瞬间阻滞后强烈迸发产生的愉悦,内在于我们的心中。电影中,与“崇高”品质紧密相关的是恐惧,恐惧存在于人类原始的天性中,常常以悲剧的形式外化出来。故而,崇高悲剧带来的情感冲击力和思想震撼力是电影在文化层面的功薄蝉翼。
蒂姆·伯顿的电影作品深受爱·伦坡哥特恐怖小说的影响,离经叛道的晦涩恐怖之下往往涉及永恒的悲剧主题,展现出难能可贵的“问题意识”。荒诞反叛的个人风格表象下是其问题意识的深刻性和批判性,他的影片多有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斗争,更有在此基础上对于人性、人生、人世的敏锐思考和对悲剧主题的不断叩问。在蒂姆·伯顿那里,崇高的悲剧既是对人类社会现实的理性升华,又是人自身对于现实社会悲剧的一种文化把握。
有限生命个体的人类总是在无限繁杂的生存荒原中遭遇各种问题,蒂姆·伯顿也是如此。面对与生俱在的问题,蒂姆·伯顿用自出机杼的影片手法道出某种原初的真理。动画短片《文森特》是人类幼年在生死临界点上的悲剧沉思。影片中的小男孩挣扎在死亡的路上,回首望去是生的一边,共处一室的蝙蝠和蜘蛛,黑暗中的灵感幻想以及如影随形的孤独。文森特有着清醒的自我认识,试图依靠阅读和绘画来压制头脑中的邪恶念头,但却不受控制地要把自己的狗制造为僵尸狗。这些或明晰或潜隐的人性根本特点,使得文森特的生命一点点衰弱、枯竭。死亡是什么?和生命截然对立的那一边是什么?文森特其实茫然无知。他沉迷于爱·伦坡的小说世界中,被妈妈流放在命运的城堡中,陪伴他的只有妻子的画像。随着体力的衰竭,恐惧、孤独、疯狂在他的身边蔓延、笼罩。惊慌失措中,文森特看到了自己的僵尸奴仆,听到了棺材里发出的呼唤声,墙壁倒塌后,露出了妻子的骷髅手臂。他下意识地吟诵出爱·伦坡的恐怖诗篇《乌鸦》,在想象中向已逝者求助,希望爱·伦坡能教会他如何淡漠坦然地跨入恐惧的门槛。但没有回答。不言自明,这部对未知世界充斥着恐惧,又对人类自身的局限性充满讽喻的悲剧试图阐明死亡问题:“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5]。人是向死而生的,人类的根本处境必然是死亡处境,但同时死亡也是生命的转换与继续。
提倡艺术的拯救作用,从席勒到浪漫主义美学家都有过危言高论。蒂姆·伯顿在他的影片中作出努力,试图在悲剧中为人性、生命、希望等价值理念寻找确立方式。当祛魅的时代丧失神性的来世普度后,个体生命面临的是赤裸裸的时间侵袭。《僵尸新娘》就是讲述生命必须面临的终点选择问题,如何解释之,是一个对生的意义阐释的大问题。物质性生命的消耗和经验世界的空乏是丧失彼岸世界后文化艺术中的大“畏”。《僵尸新娘》中艾米丽在地狱中苦苦等待爱情的降临,时间冰冷而漫长。但她却极力否定时间从而否定死亡,在赤裸的无意义状态下,希望爱情救助其一无所有的生命。然而往事如烟,人鬼殊途,维克多与维多利亚已然为他们的生命寻到了本质意义,悲剧就此而生。死亡的序曲中,艾米丽开始直视自己一无所有的赤裸真相,并用自己的而非神的目光阐明真相。那深藏着属于本性的美好东西突然复苏,她摘下戒指,化作蝴蝶飞舞飘散。生命获得了永恒性的意义救赎,流逝的时光变成了似水年华,悲剧也变得澄明崇高起来。蒂姆·伯顿以艾米丽的身份不停地思索寻找,希望借助“畏”的悲剧意识,去拯救不断逝去的时间、被戕害的人性以及礼崩乐坏的文明。
蒂姆·伯顿并不沉浸于个体生命的具体场景和遭遇,而是以超越的的目光在悲剧的基础上进行整体性的审视。于平淡无奇中发现奇迹,在繁芜中看出纯粹,在消逝中察觉不灭的本质并奋力接住它;生命历尽磨难,在蓬勃阔大的经验中深谙悲剧意义的丰富,震荡、生长、悲恸、苦难,都在时间的飘逝中,在难以言表的崇高中如歌如泣。
二、存在沉思
对人类生存处境的苦苦探询,对生存于斯的人的意义的不舍追问,一直是东西方文学艺术中长盛不衰的论题。胡塞尔说,“最伟大的历史现象就是为自我理解而拼搏的人类”[6]。然而随着时代的雨疏风骤,随着现代理性对灵魂、意识、彼岸世界等超验世界的冲击,人类赖以生存精神栖息之处开始变得荒草萋萋。愈发强盛的科技文明将人从地球上连根拔起,致使他深陷精神迷惘的贫困年代。自我身份的归属、价值的认知以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都变得模糊不清,孤独个体的限定性展露无遗。在切身体验的飘摇困境中,在精神迷惘的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在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那里,诗人应“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在世界的黑夜里道说神圣”[7]。在光影的荒原世界中,导演“诗人”则以不同的手法、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蕴涵“存在性”主题的表述,意欲现实救赎的方向,彰显了电影这一艺术样式的美好品质。
对于生存处境的存在沉思,大体上是从否定和反叛开始的。在蒂姆·伯顿的审美世界里,透过那些噩梦、纷乱、诡谲、怪诞的极致描写,是对传统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颠覆改写。面对荒诞世界无以自处的迷茫,面对精神世界的虚空和有限生命的耗损,自我存在意义的明确变得至关重要。因此无论是黑色还是童话,伯顿的影片里都贯穿着对分崩离析的现实之忧和人在孤独处境中的存在之思。质询荒原,探问意义。伯顿的内心依然企盼寻找自我,以是他和影片中人物共同踏上了剖析自我危机症结的旅程。
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便身陷海德格尔“在”之问题的囚牢。《查理与巧克力工厂》中,威利·旺卡一直竭力探究确认自己的身份和归属,却一再遭遇存在主义语言所说的“人被孤零零地抛到世间所要面对的存在问题”[8]——生的意义、死亡困惑、人的局限性等。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些终极性的“大”问题主要由神话、宗教面对,影片中却直落在威利·旺卡的身上。如同卡夫卡的异化小说《城堡》、《审判》一样,影片故事主要发生在巧克力工厂这样一个隔离封闭的空间。儿童时期,主人公简单的愿望一次次挫败,饱受亲情伤害而坠入恐惧与虚无之中。在他者那里遭受压制,威利·旺卡在成年后便逃离群体的喧哗,紧闭工厂大门,试图在与世界的隔离中确立自己的存在。然而孤立的个体注定无法抵御意义丧失的沉痛,威利·旺卡选择让特定的少数群体进入自己的世界,但其怪异的选择方式依然暗示着一种精神紧张。进入瑰丽莫测的工厂后,孩子们陷入无可奈何的孤立无援中,只能被动接受威利·旺卡上帝般的安排。伴随荒诞的歌舞,每一个有着性格弱点的孩子都变成了“单数”,在孤单和不幸中,直面生的艰难和存在的敌意。与此同时,威利·旺卡也似乎不由自主地卷入一种事件中,不得不等待着一个让其害怕的了断。影片最后小男孩查理承担起保卫人类美好天性的责任,与其说是美好愿景的达成,不如说是蒂姆·伯顿某种责任心的演绎。
很多时候,人在本质上孤独受挫的、最初的愿望会在人生的诸行无常中积垢、变形、湮灭。存在主义哲学家基尔凯戈尔讲过一个故事:某个对自己生命心不在焉的浑浑噩噩者,在一个晨曦煦和的早晨醒来却发觉自己已然死去,他才知道自己的存在。在影片《大鱼》中,蒂姆·伯顿不断用浪漫离奇的幻想思考表现人生价值,从而提醒、确立存在的意义。年轻的爱德华不愿在偏僻的小镇中籍籍无名地活着,不愿以丧失自我存为代价融入司空见惯的平淡模糊中。于是在缺乏上帝提供价值标准的情况下,爱德华投身冒险,他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有拯救世界的崇高使命,也能够找到普遍真理。爱德华以童话的方式把自己的故事延展成一个细节繁茂的寓言,以期将自己的存在状态展示给儿子。这一点和《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爱丽丝如出一辙。爱丽丝从人类世界的喧嚣烦扰中掉进兔子洞,躲避了包括父母在内的他者带来的“客体化”威胁。在奇幻异境,爱丽丝别无选择地以承担拯救群体的方式进行存在之思。他人是地狱,但群体性社会带来的某种“异化”更为令人心生恐惧。因为没有价值体系参考,个体往往会被裹胁在一种不可知的力量中,比如阶级、功名、理念,甚至是喧哗的群体性梦想。在影片《大鱼》和《爱丽丝梦游仙境》中,蒂姆·伯顿俨然是一位哲学意味浓厚的画师,他把各种场景塑造为冷气弥漫的画面,借助扑朔迷离的叙述方式,将耀眼的瞬间印象定格、拉长,时空穿行无阻,生死交替,造成了无法把握虚无世界的整体效果。
在蒂姆·伯顿的影片中,追寻存在本身的个体常常陷入无法判断自我行为意义和有效性所在的尴尬处境,显得悲哀而可笑。但此种境遇的冷酷和绝望,如同黑色童话一样,恰好是“存在”的荒诞常态。伯顿以他对存在的严峻审视给观众以生命警醒,帮助我们重新沉思存在的问题和意义丧失后的生死问题。
三、过程意义
在这样一个失去普遍信仰与拯救的时代,在文化与艺术世界跋涉的大师们,除了展现那些无以逃避的崇高悲剧和存在沉思,同时也在建树。海德格尔曾著书解读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故乡》诗作:“这是一个贫困的时代,它处于一个双重的匮乏和双重的不之中:在已逃遁的诸神之不再和正在到来的神之尚未中”[9]。如何找到穿越混乱时代的路径?是否能够澄清围绕人类的存在之迷雾?这需要用超越的目光和不同的叙述方式来探寻。如同加缪的西西弗斯一样,由对传统终极意义的探询,转变为一种新的确立——“过程”意义。这是思维方式一次艰难的转换,包含了对存在的无限性和人的局限性的洞察,是人与世界关系的重新考量界定。与之相伴的是转换路径上大师们的艰难行进和痛切之感,他们带着坚毅的面容,高擎艺术的火把在荒原上进行美的建构和过程意义的追问,以拯救凌乱的精神审美家园。
古希腊西西弗斯的悲剧精神是在失去终极意义的确定性之后对生存过程意义的肯定。蒂姆·伯顿不是哲学家,他并未对这种“过程意义”提出多少明晰的理论构想,而是借助其电影人物的行为方式给出价值指向。类似古希腊俄狄浦斯般不可理喻的命运敌意总是贯穿在伯顿的黑色童话寓言里,或是无可躲避的死亡,或是力不能及的分离,或是时乖运蹇的困苦。而洞察荒诞处境的伯顿式人物,则选择以一种不败的姿态,在走向失败、走向死亡、走向终局的行动过程中保持优雅与从容。
黑白传记片《艾德·伍德》里,蒂姆·伯顿铸就了一个在人类困境之路上艰苦寻求的行动者形象。艾德·伍德是个痴狂的电影爱好者,从出生到死亡,电影贯穿了他的一生。然而他注定是个毫无电影才能的平庸之徒,不具备丝毫拍摄电影的天赋。作为电影人的漫长生涯中,他没有拍出一部值得一提的电影作品。身处上帝(天赋)缺席的世界,艾德·伍德努力寻找并确立一种价值支撑,站在荒谬世界的对立面,做着如西西弗斯一样无功的徒劳:站在山顶,目睹刚推上来的巨石再次滚落到山下,无计可施。拍摄完《忽男忽女》后,艾德·伍德无不意冷心灰地说:“我是不行了,我拍了部有史以来最差的电影”。面对充满荒谬的黑色世界,人类的主体理性此刻显得力不从心。但即便如此,艾德·伍德却依旧满怀热诚地尝试一切与电影相关的事情,写了无数剧本,导演并监制了十多部影片。艾德·伍德将诗意的想象赋予西西弗斯这一古老神话,并躬行实践了自己的人生价值选择——在不断推动巨石上山的过程中确立意义。作为生命的重要支撑,意义经历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从人生故事的结尾转移到了故事的进行之中。在无望的情况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当下的感悟和认知替代对未来的张望和窥探,无惧意义与生俱来的定局性和不可理喻性,让其转向自身,使得整个过程充盈丰润,然后意义便会降临在当下的每一刻。黑白胶片中,蒂姆·伯顿让艾德·伍德超越生死的同时,也超越意义并驾驭意义。
现实世界总是以实用法则在理性、权利、道德的层面压抑人的自我意识,遮蔽精神的广阔性。“在文明的掩护下,以进步为口实,人们已经将所有可以称之为迷信或幻想的东西,一律摒弃于思想之外;并且禁绝了一切不合常规的探求真理的方式”[10]。同为传记片的《大眼睛》里,玛格丽特画出了那些有着悲伤大眼睛的小女孩。但迫于男权社会,也屈服于内心恐惧,玛格丽特选择隐瞒他人,躲在画室里对可能的结果视而不见。失败的婚姻经历在玛格丽特的生活中投下阴影,男权和自我都对她形成束缚,成为无法逃脱的生命桎梏。拘囚自我局限的樊笼,意义永远模棱两可。反抗权威,确立价值,当务之急便是突破旧我的困囿。度过隐忍痛苦的八年后,玛格丽特走出画室,如同那些有着大眼睛的纯真孩子一样,对充满名利的成人世界说了声“不”。但是,成人世界的趋同趋利成就了皇帝赤身裸体的谎言,坚持真言的孩子说出事实的代价就是被现实世界抛弃到永恒的孤独中。玛格丽特在追求意义的路径上不断遭遇孤独和质疑,路的尽头也并不全是光明。但“不”的背后,“是”始终沉浸在她的心灵深处。不再将价值的追求放在客观目的上,而是换一种方式提问,坚守当前的处境,把意义的可能性放在“是”的生存过程中。纷乱动荡中,如堂吉诃德般单枪匹马却毫不犹疑地挑战风车,“是”成为行动颠扑不破的依靠。在“上帝已死”的年代,这就是从追问终极目的意义到肯定过程经验意义的价值转变。
生活的复杂内在往往暗藏锋机,显露峥嵘时便会将人推向隐秘的绝境。在蒂姆·伯顿的电影思考中,无论是黑色的感性还是理性的童话,无论是细腻的叙说还是荒诞的演绎,其本质上依然是把存在之意义从终端拉回到过程的尝试。在这一点上,他和海明威的圣地亚哥以及加缪的西西弗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结语
面对人类的精神失乐园,蒂姆·伯顿用他的影片发出了迷离的慨叹。“黑色”是一种隐喻,蒂姆·伯顿在他的作品中毫不掩饰对于神秘、诡异、恐怖的偏爱。无论是大量暗色系和对比色的运用,还是对死亡虚无主题的赤裸展示,都类似于战后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像风格。然而它又确确实实只属于蒂姆·伯顿一人,在于其独树一帜地用“童话”的方式构建出一种孩童直面真相的审美体验。童话是成人的寓言,光怪陆离想象和奇幻诡谲的故事既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人类原始本能的展露。美与丑,善与恶、孤独与受挫、恐惧与虚无、存在之美好与过程之温馨,终将从童话书里走出来,走到每一个长成大人的孩子身边。可以说,面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断壁残垣,蒂姆·伯顿用自己独特的电影手法记录下了对于孤独、温情、戕害、死亡、信仰等等的沉思默想,自如地在艺术与商业之间变换游走。
最后,无论是西方的、还是本土的文化理论,最重要的意义,始终在于开启思想与想象的维度,而非封闭、束缚了思想的飞扬。阅读一部电影,最为重要的还是自己独一无二的观影感受——智性与感性的结合。逃脱语言的囚牢后,再光怪陆离的光影剪切,也不妨碍建构一个供观影者主体想象自由驰骋的空间,因此毋须惧怕创造性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