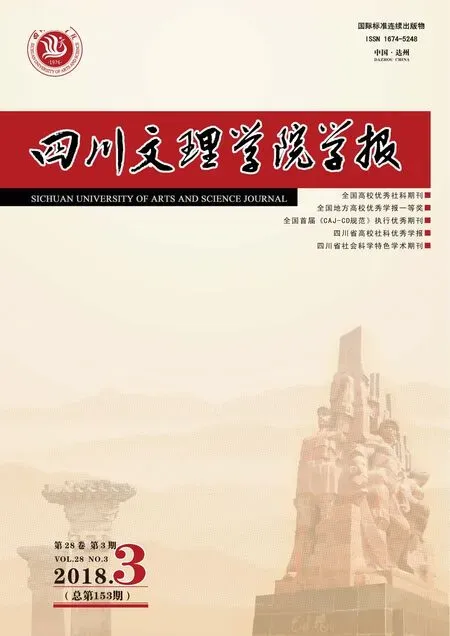生存的焦虑
——卡夫卡小说中“权威”与“内疚”写作主题探究
刘宗岱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卡夫卡是著名的犹太裔作家。城市布拉格就像一位长着许多只爪子的母亲将他牢牢抓住,卡夫卡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布拉格度过。当时的布拉格是一个政治与文化的大熔炉,民族意识和民族运动一直在这里发生着,这些造就了布拉格复杂多元的文化氛围,在此期间成长的卡夫卡也有着比一般人更为复杂的文化身份,文学写作是卡夫卡对于自己内心不断探索的过程。相比于复杂动荡的社会环境,卡夫卡的家庭生活对他的文学创作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卡夫卡的父亲身体健壮,专横而独断。相比之下,身体瘦弱的卡夫卡因为内敛的性格和文学喜好而无法继承父亲的经商事业,因此总不被父亲喜欢。被卡夫卡视为他生活先决条件的写作,在父亲看来却是不务正业,故而白天工作深夜写作成了卡夫卡的生活常态。卡夫卡的小说、信件、日记很难区分,三者中都有着他内心的独白,但往往是通过“变形”之后隐藏在文字之中。写作之于卡夫卡是对父亲为代表的权威的挑战,是他内心对于工作和生活受到写作影响的内疚意识的体现,这也就是卡夫卡小说中重要的两个主题。
一、叙事特点
卡夫卡身上体现着传统写作模式和非传统写作模式的融合。就传统而言,卡夫卡的大部分文学作品篇幅短小却包含了作者对于生活的深刻思考,与其说是讲述一个故事,不如说是对于生活中瞬间感触的直接记录。卡夫卡的写作带有极为浓重的寓言色彩,他写作的素材基本都来自于他的生活体验,通过寓言中的象征和隐喻来展现他的精神世界。动物是卡夫卡所钟爱的题材,《变形记》中的甲虫,《地洞》中的鼹鼠,《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中的猴子,《女歌手约瑟芬》中的老鼠,均以动物为故事主人公,从动物的视角来叙述事情的发展,进而反映出深刻的思想命题,这是寓言的典型特点。就非传统而言,卡夫卡的小说基本都是不完整的。“一切闯入我脑子里的东西都不是有头有尾地闯入,而是在什么地方拦腰截取。”[1]16《城堡》《诉讼》《美国》三部长篇小说缺少完整的叙事过程,在短篇小说中,人物缺少完整的形象,人物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丰富立体的形象,而是被抽象成了一个个符号,宏大而富有层次感的场面在卡夫卡的小说中也不复存在,环境的作用被淡化,但人物内心的直接感受得到了拔高和放大。卡夫卡忽略了人物的外在形态,而是通过语言来对人物的心理进行更加细致和深入的刻画。而卡夫卡自己对这种片段式写作给出了解释:“结尾的难处是这么产生的:哪怕是最短小的文章也要求作者进入一种自我满足和忘我潜心的状态。从这种状态走出来步于日常生活的空气中,没有强有力的决心和外界的鞭策是难以办到的。所以与其将文章圆满结束,平静地花出去,还不如在此之前,接不安的推动力挣脱出来,然后反过来用双手从外部来完成结尾。”[1]28这种片段式写作将他直接的感受记录了下来,思考瞬间的价值因此而得以确立。
在现实中对于卡夫卡来说,写作只是一个副业,时间和精力的限制让他没有办法像法国的福楼拜等专职小说家可以专心用文字来构筑规模宏大的文学世界,故而表达自我的情感和想法就成了第一位的要求。另外,小说、日记、信件是卡夫卡最主要的三种创作形式,然而这三者之间很难划分出明确的界限,“他的经验世界和文学世界之间没有界限。生活中一切都是他的写作素材”,[2]日记和信件都是属于较为私密性的文本,和社会公共开放的空间相对,日记和信件的共同点都是倾诉情感、暴露隐秘。而卡夫卡的日记并不“满足于个人经验的直接表达,而是通过努力将这些经验‘变形’为故事”。[3]卡夫卡片段式的写作使得每一个故事都有着自己突出的主题。
二、卡夫卡作品中的不同主题
当时卡夫卡身处的捷克布拉格是政治、文化不断动荡和交汇的中心,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并没有赋予卡夫卡一个明确的文化身份定位。公司任职的生活和家中父亲的专横严厉让卡夫卡对于权威这个词语过度敏感,卡夫卡写作中充满了对于权威的探索,具体体现为由《判决》所体现的对于权威的探索和抵抗,以及《变形记》所体现的内疚意识。
(一)对于权威的探索和抵抗
《判决》是卡夫卡对自己感到满意的第一篇作品:“因为这是从我身上自然而然生下来的产儿。”[1]106《判决》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作为商店主要经营者的儿子格奥尔格将自己将要结婚的消息和一些生活杂思写成一封信,并借此机会对父亲表达长久以来欠缺的关心,父亲在被格奥尔格抱到床上之后勃然大怒,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了格奥尔格,并判处格奥尔格死刑,作品以格奥尔格跳河作为结束。
《判决》这篇作品在看似荒诞的情节反转背后其实是表现了卡夫卡对于权威的探索和反抗,而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发现任何对于权威的改动都是不可能的。在作品中,格奥尔格的父亲以前在商店里最主要的决策者,父亲就是权威。但是在格奥尔格的母亲去世过后,父亲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有着对于全局的把控能力。商店在格奥尔格的经营之下在规模和收益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而父亲在家里穿着睡袍,以一个垂垂老矣的形象在小说中登场。格奥尔格在家中像照顾小孩子一样照顾父亲:“年岁可不饶人。店里的事,我不能没有你,这一点你很清楚。但是,要是开店有损于你的健康,那我明天就关门,再也不开张。可这又不行。我们必须给你安排另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不是小改,是要彻底改。”[4]41在这个情境中,儿子格奥尔格完全是处于一个支配者的地位,与其说是对父亲进行劝说不如说是直接下命令,用父亲的口吻对父亲说话,这是格奥尔格对于权威的探索。他在能够打理好商店时便想对父亲的生活进行干涉,甚至是彻底的改变,这是格奥尔格对于以父亲为代表的权威所进行的挑战。
除此之外,订婚其实也是格奥尔格的一种抵抗方式,通过婚姻从而逃脱在这个家庭中的生活,从父亲权威统治下的逃离也可视作为消极的反抗。这和后来的情节和两者地位的极度反转形成了对比。格奥尔格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降低父亲的地位,使得父亲对于商店、生活甚至是自己的身体都失去自己的控制。但是在格奥尔格看来本是对于父亲的关怀、成功经营的才能、对未婚妻的爱情、对于朋友的关心,在父亲眼里却变成了强者对于弱者的怜悯、对自己劳动成果的剽窃、被女人用性所诱惑,对于朋友失败的鄙夷。而剧情在格奥尔格给父亲盖被子处达到了转折点,“这里‘covered up’(盖上)一词又有埋葬的意思,父亲显然明白儿子这个词的用意”,[5]父亲一下子从床上站了起来,用手撑着天花板做出顶天立地的姿势来对格奥尔格的挑战作出回应,父亲健壮的体格从小就给身体瘦弱的格奥尔格带来压迫,而此刻站在床上的父亲在空间高度上几乎充满了房间,两人的相对空间位置也在这一刻发生了对调,这个突然起立的动作是父亲将权威突然夺回,从心理上战胜了格奥尔格。“如果我被判决了,那么我不仅仅被判完蛋,而且被判决抗争到底”,[1]77格奥尔格在此刻依然没有放弃抵抗,拒绝沟通交流成为了他的战术。当父亲展现出体格上的优势时,格奥尔格却以“你是个滑稽演员”回应,当父亲自以为非常了解那个远在莫斯科的朋友时,格奥尔格却用数之十倍的“一万倍”进行回应,这两句冷嘲热讽是格奥尔格试图通过开玩笑的方式来抵抗父亲权威对自己内心世界的伤害。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当格奥尔格意识到父亲一直用看报纸作为掩护来监视自己时,他意识到这一切其实都是在父亲的设计之中,就像父亲所说的“而我的儿子则欢呼着,走遍全世界,他缔结了一桩又一桩其实是我打点好的生意”,[4]49格奥尔格发现自己自始自终都没有成功地摆脱过父亲,父亲用现实真相击碎了格奥尔格的内心的幻想,他的内心防线在此时崩溃了。对于格奥尔格来说,任何现实经过思考加工就成为了谎言,对于父亲来说谎言经过权威的确证却能够成为真理。格奥尔格对父亲所做的一切不再是建立在亲情基础上的伟大牺牲,而是成了现实上的自我幻想。
《判决》是卡夫卡对以父亲为象征的权威所做出探索和挑战的代表作,是“他生命中持续不断的关于权威和负疚的个人之间斗争的第一次发泄”,而这种以弱小来探索和面对强权在《城堡》《审判》等长篇小说中都得以复现。《判决》可以看作是卡夫卡的精神离线,这一次对于权威的探索让卡夫卡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父亲的权威不存在任何真正改变的可能性。
(二)内疚意识
《变形记》讲述了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在一觉醒来过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不仅丢掉了工作而且在这个家庭中以一种微妙的身份生活,在经历了父亲掷苹果的攻击和访客的嫌弃之后,在家人绝望放弃的氛围中最终逝世的故事。
内疚意识是《变形记》的重要主题之一。在卡夫卡的日记和随感中,明确地记录了他本人对于无法平衡生活中写作和工作的苦恼和焦虑,“一个中的最小的幸福也会成为另一个中最大的不幸”。[1]87写作完全是卡夫卡的私密空间,一直坚持的写作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父母的承认和看重,“我坐在我的房间里,房间就处在整个寓所的噪声大本营中”。[1]79家庭中的写作环境是如此的糟糕,只有拿着薪水的正经工作才能够得到承认,因此《变形记》中那只甲虫可以看作是卡夫卡的一次精神世界的探险——如果自己在家中明确宣布坚持写作而放弃现有的工作,那将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呢?在作品中,卡夫卡将自己的精神角色幻化为一名叫做格里高尔的旅行商人。格里高尔和卡夫卡本人有很多相似之处,白天的工作都能给他们带来超过个人所需的报酬,而在独处的夜晚他们才能够面对最为真实的自己。格里高尔晚上在卧室里自己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卡夫卡并没有交代,不过格里高尔晚上所做的事情和卡夫卡在现实中夜晚进行的写作同样都是不被父母承认的,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对白天挣钱工作的一种逃避。因此,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而丢掉工作可以看作是卡夫卡用写作代替正经工作之后的变形,此处“变形”有三层含义,第一是卡夫卡的精神角色变形成为格里高尔。第二是变回原形,即抛却掉自己不情愿的工作和平时伪装出的面容,显现出一个真实的自己。第三是自己的形象在家人和公司秘书长眼中的变化——从正常的人变成了被人嫌弃且不被理解的甲虫。“我的幸福,我的能力和所作所为的每一种可能从来都存在于文学之中”,[1]96这里可以看出卡夫卡对于文学写作是如此的执拗,然而这样的偏执确实会影响白天的工作,也不能满足父母的期望,个人的偏执此时让父母以他们的标准对卡夫卡做出所谓“正确”的判罚,这会让卡夫卡产生内疚,特别是“他们的外加世界反复告诉他们自己做错了事情的时候”,[1]72通过心灵的自我斗争会明白自己的错误所在,而内疚和救赎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会不可分割地出现,因此,内疚意识是《变形记》的主题之一。
黑暗可怖的形象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有着突出的地位。《变形记》中,甲虫的形象也同样如此,黑色,坚硬的颚,畜牲般的发声,对于腐食的偏好,这些都让甲虫的形象中增添了不少恐怖元素,这样丑陋的形象可以看作是他内心中对于自己的惩罚。格里高尔并不喜欢旅行商人这一份工作,“我选了个多面艰辛的职业啊!”[4]89对于工作奔波和工作量的分配不公,足以看出他的厌恶之情。虽然格里高尔厌恶这一职业,但这份工作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因此他在厌恶的同时也害怕失去它。失去工作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就从家里的支柱变成了寄生虫,家庭中的地位发生了反转。情节在此处出现了矛盾,同时也出现了格里高尔的第一次内疚意识——甲虫并没有吓跑人们而获得自由,而是留在卧室中应付着公司人员和父母亲的催促,并且急于开始一天的工作。卡夫卡的日记(注:引文中的“他”即是卡夫卡本人)中写到“如果有谁问他,他想要的到底是要什么,他可就答不上来了,因为他(这是他最强有力的证明之一)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由的概念”,[1]26卡夫卡厌恶现有的工作是因为对写作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影响,然而生存仍然是卡夫卡必然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因此最好的结果不是因为写作而完全放弃工作,而是在工作能够养活自己的情况下完全不影响他的文学写作。《变形记》中,格里高尔正是因为变成了甲虫而彻底丢掉了工作,因此心中便产生了一种内疚之感,这就是格里高尔变形之后不逃走而仍争取保住自己这份工作的原因。
产生内疚的第二个原因,源于他对家庭的冷漠的态度。日记中写到“他不是为他个人而活,他不是他个人的思想而思索。他好像在一个家庭的强制性之下生活着思索着,这家庭虽然充满着生命力和思想力,但是根据某个他所不知道的法则,他的存在对于这个家庭具有一种死板的必要性,由于这个他所不知的家庭和那些他所不知的法则,是不能放他走的”,[1]89卡夫卡在家庭中没有自由,像一个囚徒,而家庭更像是一个可以供他随意进出的监狱,“栅栏的铁条互相间间隔足有一米宽,他甚至并没有被监禁”。[1]96和父母之间冷漠的关系以及他自身内敛的性格使得家庭就像是一个监狱,而父亲则在家庭中承担着典狱长的角色,要“帮助”卡夫卡改掉写作这个习惯而专心致志地工作。卡夫卡生活在家庭之中就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他是维系家庭完整必要的一部分,因此他的放弃工作和离开势必会带来道德和心理上的谴责,而《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留在家接受妹妹的照顾,“必须保持安静,用耐心和最大的体谅来减轻家人由于他目前的状况而引起的倒霉和难受的心情”,[1]99并且用床单遮住自己免得惊吓到家人即是这部分思考的呈现。
产生内疚的第三个原因,是对于父亲的畏惧。父亲不仅是家庭的一部分,更是家里的最高权威,这一点把他和母亲、妹妹们区分开来。卡夫卡生性敏感,父亲的一举一动在他的心中构筑起了一个不可撼动的权威形象。“我又瘦,又弱,又细,你又壮,又高,又宽。在更衣室里我已经自惭形秽,而且不仅是对你,而且对全世界,因为你在我眼里是衡量一切的标准。”[1]101自幼瘦弱的体格就给卡夫卡带来了一种自卑,而父亲健壮的体格给卡夫卡带来了压迫感。同样在思想上:“我的一切思想都处在你的压力之下,那些与你的思想不一致的思想同样如此,而且尤其突出。所有这些似乎与你无关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带上了等待你即将说出的判断的负担;要忍住这个负担,直到完整地、持续地形成这种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1]104与父亲在现实和精神的较量上,卡夫卡潜意识中就把自己定义成为了一个失败者,父亲的生命意识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卡夫卡很容易就意识到了撼动父亲权威的不可能性。这种畏惧混合在了卡夫卡心灵的土壤之中,以至于从这里生发出的所有思想都暗含这一层畏惧的心理基础。“由于不可能进行平心静气的交往,于是另一个其实很自然的后果产生了:我把讲话的本领荒疏了。”[1]169因此当父亲在场时,卡夫卡沟通的能力受到了压制,《变形记》中变成甲虫之后的格里高尔再也没有尝试通过文字的形式和家人进行沟通便是证明。由于父亲的绝对权威,父亲的话在卡夫卡听来就像是一道道判决,“我永远蒙受着耻辱,或者我执行你的命令,这是耻辱,因为它们只对我起作用;或者我不服从,这也是耻辱,因为我怎么可以不服从你呢?”[1]199这种心理暗示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父亲的出现就会激起卡夫卡心中的内疚。
三、结语
“几乎每一个有写作能力的人都能在痛苦中将痛苦客观化”,[1]77卡夫卡的作品正是他自己痛苦反省的结晶。对于权威的探索贯穿了卡夫卡的一生,父亲的形象成为了卡夫卡挥之不去的阴影,而由此产生的内疚也在卡夫卡许多作品中得到复现。权威和内疚是卡夫卡一生中两个不断撞击着他心灵的因素,正是由于这样的碰撞才得以产生《变形记》《判决》等一系列优秀的作品。经典就是因为它能够从许多角度进行阐释,卡夫卡的大部分作品没有结尾,卡夫卡的思维融合了读者的理解就成为了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阅读体验。卡夫卡用文本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权威和内疚始终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因素,他用写作的方式反抗和逃避,而我们呢?
参考文献:
[1] (奥)卡夫卡.像地狱的沉沦[M]//卡夫卡散文菁华.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2] (美)桑德尔·L.吉尔曼.卡夫卡[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8.
[3] 李 军.出生前的踌躇——卡夫卡新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7.
[4] (奥)卡夫卡.卡夫卡短篇小说经典[M].叶廷芳,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
[5] 曾艳兵.论卡夫卡《判决》的叙述策略[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5):2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