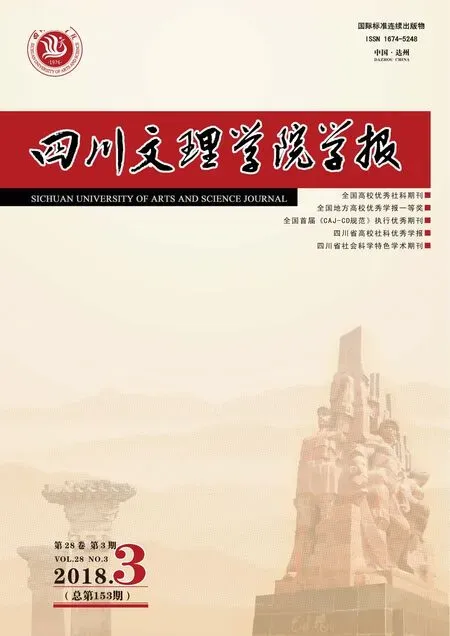“巴渠民歌”在“巴人文化”中的地位及影响
李玥欣
(四川文理学院 音乐与演艺学院 ,四川 达州 635000)
一、“巴渠民歌”与“巴人文化”
“巴渠民歌”既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个时空概念,更是一个人文概念。建立于四千年前的“巴国”,大致区域从嘉陵江上游附近的渠江流域延续到整个川东、川北和川南地区,早期的祖先巴族人在这块广袤的区域生活、繁衍所建立的“巴人文化”,成为当前巴渠文化的一个重要历史组成部分。“巴国”也常与现在的“巴山渠水”“巴山渝水”“巴山蜀水”等概念相对应;时空概念上的“巴渠民歌”,与从历史上的“巴国民歌”到当前的巴渠地区几千年来所流传的民歌相对应,在这个地处大巴山脉深处的“巴国文化”中,不仅孕育了后来繁荣的“巴蜀文化”,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巴人文化”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后,终于被民族融合与更大意义上的国家统一所消融。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巴人文化”不仅影响了南江、万源、巴中、大竹、宣汉、内江、渠县等区域人们的生活和历史,还在当代以“巴渠民歌”的形式,继续流传于巴蜀地区。“巴人文化”在千百年的流传中,不仅创造了具有深刻历史积淀的“巴国民歌”,也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当代“巴渠民歌”——成为古代“巴人文化”在当代的历史“遗存”。
“巴人文化”中的民歌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依然渗透在当前的“巴渠民歌”中。无论是民歌的题材,民歌的艺术形式、风格,还是歌词的具体特点与衬腔运用,都很好的体现出了古代“巴人文化”的精髓,这些主要集中在社会生产、劳动活动、爱情理念、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内涵,很好的折射出了“巴人文化”中的历史信息。在这些具有浓郁的原生性的民歌中,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与自然生产、社会生存与历史繁衍方面的密切关系,保持着对于传统山歌、对歌传统以及历史传承等内涵的联系。“巴渠民歌”中既有展现委婉、细腻的情感特征,也有体现当地人们在劳动、工作时的豪放、爽快的节奏特点,既包含了各类不同场面、场合下使用的劳动号子、薅草锣鼓等形态,也包含了刚劲强悍、振奋人心、抒情有度的风格特点。[1]因此,“巴渠民歌”的现代歌曲形态通过对不同歌唱情境、歌唱方法与审美、娱乐等内涵的吸收,形成了不同时期的民歌文化在现实中的传承与发展。“巴渠民歌”由于几千年来基本围绕着这一地区展开,在近代才与红军的歌曲、陕北民歌发生一定的联系,所以无论是在民歌的既有形态、音乐特色、风格特点,还是在民歌使用的声腔、唱法、板式、曲调等方面,都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性”与“封闭性”特点。因此,“巴人民歌”在传承方式、结构方式等方面与“巴人文化”生活、生产的紧密相联,不仅成为当代“巴渠民歌”得以传承的基础,也是这一地区形成特有的流畅、质朴的地域民歌风格的源泉。在这些具有地方色彩和风情内涵的歌曲中,浓郁的民间曲调具有传统型的音乐形态特点,在艺术风格方面也保持了传统地域文化的特点。“巴渠民歌”中不仅具有很强的地域方言和口语特点,不同类型的“巴渠民歌”中还常在曲调运用中凸显出地域性的衬词或衬腔特点,因此产生了很多即兴性的特点。[2]这些都使得同一首巴渠地域的民歌在演唱时容易产生不同的风格特点——不同地区、不同演唱者、不同的即兴特点,都会形成不同的具体歌曲风格,对于后来“巴渠民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使“巴人文化”中的原始素材与“巴渠民歌”的即兴性、灵动性发展,成为不断创新、发展的因素之一。[3]
二、巴渠民歌的本体特点对“巴人文化”的意义
巴渠民歌在当前已经记录在案的有两万多首。其中有100首民歌能够代表不同地域、时期的文化特点,本文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后,发现这些巴渠民歌中的音乐本体特点与歌词要素,都与历史上的“巴人文化”具有密切的联系,体现出地域文化的一般发展规律特点。
首先,巴渠民歌中的结构逻辑与曲式形态特点,体现出了独特的巴蜀地域文化和“巴人文化”印记特点。比如,通过分析这些歌曲的本体结构后发现,单乐段不仅是巴渠民歌中最为常见的基本曲式形态,也是包含了很多即兴性、自由性的散曲所常用的形态。而且,这些单乐段的结构观念具有“概数”的中国传统哲学意味——正如“九”还代表着完美、而不仅仅是9个部分一样,“单”除了具有具体数字外,还具有传统文化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哲理意义。在单个乐段结构的前提下,这个结构中的具体乐句和生成形态可以是千变万化的,在结构的单一方面,也往往体现出变奏、即兴规则等都参与之内的特点。在这个结构理念基础上,后面还可以展开为更大规模的二段体、三段体、变奏体、自由体等结构形态,但是这些结构间没有非常严格的界限。
其次,在乐句的旋法方面,也具有巴蜀文化的独特特征——两句体的重复、变奏、分裂、融合等技法。“巴渠民歌”的这种旋法特点占所有作品旋法比例的四成多。上述平行关系的展开技法与结构逻辑一样,在具体实施中可以进行多种不同形式的变化,不仅旋律可以进行多种衍生,所使用的衬腔也可以发展成乐句,从而使乐句的旋法与结构特点都体现出更为自由性的特点。巴渠民歌中的这种旋法特点体现出了对比性原则的影响——这种来自“巴人文化”传统中的自由性和即兴性精神,一直被融入到现代“巴渠民歌”的创作中。
再次,在歌词设计与曲调方面,也体现出对延续性与对比性的注重——“起、承、转、合”原则,被贯穿在作品的逻辑观念中。这种占到作品比例近三成的逻辑观念,不仅体现出“巴人文化”中以“四”为特点的对称逻辑传统,也体现出在作品的陈述中,注重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映射特点。当然,以“三”为美的逻辑观念也折射出不同乐段结构和作品精神呈现的并列与再现传统。无论是“赶五句”和“再现五句”,还是其他形式的音乐展开与表达方式,都体现出作品的结构与传统。“巴人文化”中的自由性格、真诚情怀,都体现在多样性的前后唱句对比与延续过程中。
三、巴渠民歌对“巴人文化”传统音阶、音调的折射
“巴渠民歌”对“巴人文化”的语言音韵也具有一定的传承意义,折射出了这种地域语言的独特魅力特点。
首先,“巴渠民歌”中的调式、调性特点与音乐中使用的独特音列结构特点,成为“巴人文化”折射的方式之一。巴渠民歌中的曲调调式主要呈现出传统五声音阶基础上的细节变化特点——四声音阶为主的巴蜀音乐调式特征。巴渠民歌中使用的这些四声特点的调式,不仅形成了不同的调性色彩,也在音阶风格和歌曲的地域性方面,能够折射出巴蜀文化对于人们现实生活的本质意义——这些巴渠民歌中使用的具有四声特点的音列,不仅是“巴人”在多年的延续、繁衍过程中形成的,也是具有不同具体形态和个性化变化的。这些深受巴蜀当地语言、方言影响的四声音调,为了配合旋律发展中的歌词音调特点,而不得不放弃对五声、七声音阶的既有结构,这些常用的徵、羽、宫、商这四个音中出现的频率也有所差异,而且在出现的频率和位置重要性方面的差异性还是很大的。在四声音阶中,最多见的是徵和羽音,这两个音构成了不同的徵音调式和羽音调式结构,徵音、羽音的运用也占到全部音的八成左右。与之同理,这些巴渠民歌中使用最多的是徵调式、羽调式,宫调式、商调式和宫、商调式音的出现很少。五声调式音阶之所以成为四声音阶的音响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淡化了角音、角调式的运用。上述后者三个音、三种调式的出现已经是较为少见的现象。[4]
其次,调式骨干音的出现频率改变和调式常见音序列的改变,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巴渠民歌”的风格特点。由于可以以不同音列的方式对巴渠歌曲进行演唱,所以在民歌中那些可以根据具体音的位置、具体出现频率的音所进行的节奏、时值组合,就会对既有的民歌音乐和风格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产生与传统民歌的差异性特点。对于调式中不同骨干音的运用,有助于区别调式的风格和旋律样式特点。音阶中的四声系统及骨干音的特殊、多样性组合,也会让整个音阶风格都产生极大的差异性特征,可以凸显多样化的地域文化特点。通江民歌中的《叫我唱来我不推》就带有很强的徵音色彩和独特的调式文化特征;万源民歌《太阳落西垭》中则是以商徵羽三个不同的骨干音作为组织调式的基础,成为带有混合商调式与徵调式色彩的民歌形态。这些地域性的民歌,展现出了差异性很大的文化色彩,恰恰也都能推断出“巴人文化”在几千年历史演变中的延续性。
再次,这些巴渠民歌中还蕴藏着深刻的历史信息——犯调手法的运用,衍生为当前的混合转调手法。如,《幺姑娘大不同》中,就通过对旋律中的特殊调式色彩音的运用,对特殊调式音程的运用,产生独特的地域色彩意义,也形成过渡性的转调效果。在大竹佛歌《报恩经》中也采用了#F徵调式与#F商调式并置的犯调技法。而这些正是历史上的犯调传统在发展中的精神延续,体现出“巴人文化”对“巴渠明个”的影响和意义。
四、巴渠民歌对“巴人文化”的地方音韵与生活习俗的影响
巴渠民歌对于“巴人文化”中传承下来的地方音韵与生活习俗都有很多视角的折射,具有影响后来巴渠民歌风格与文化的意义。
首先,在巴渠民歌的歌词中还有地域性语言色彩与生活习俗的传承。巴渠民歌中所使用的大量的衬词与衬腔,就是地域语言、音韵的具体体现。[2]在这些具有现代气息的巴渠民歌中,巴蜀地域色彩的衬词和衬腔依然能够体现出“巴人文化”影响的普遍性,且在具体的语言和音乐方面,都呈现出新的风格特点。无论是一般性特点的语气性衬词如那个、这个、嘛、唻、啰、哪、呕、喔、哎、咧、哟、哦、嗬、哟嗬、啷个、里格、底格等等……还是那些重复性衬词或称谓性衬词,都体现出巴蜀地域性语言中的感叹词、语气助词的方言性、音调性特点。这些使用的衬词不仅与现代巴蜀语言比较接近,还常常以单音节、双音节或多音节的形式出现在多种不同的民歌歌词中。而且这些衬词也会以不同的形态特点被穿插在巴渠民歌的不同歌词中,在演唱过程中体现出典型的四川地域性的语言色彩和文化习俗特点。
其次,在巴渠民歌中使用的这些衬词还可以独立的体现出语言音韵特点。这些衬词在脱离歌曲的旋律后,也可以以独立的形式、高亢的语调、起落的音韵,表达出民歌中的内涵。巴渠民歌中的人们生活、风俗习惯以及娱乐活动、生产生活等都与“巴人文化”保持着一定的延续性特点,从而也具有历史性意义。当前的四川语言颇富南方音调特点,但这些不同的区域中的衬词在历史上则融合了南北方的民族语言特点和东西部的地域语言特点,在历史上曾经经历的多次民族融合与政治融合,也都体现在这些歌曲的唱腔、歌词中。无论是巴渠民歌中的音调还是音韵,都既可以将不同的乐句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在一起的作用,也可以形成富有变化的旋律线条形态,凸显歌词中的文化意义,还可对不同的旋律片段形成补充、“画外音”的作用。这些衬词表达了不同的情绪、不同的内涵,对于巴渠民歌的风格也具有装饰性的润腔意义。在这些歌曲的音韵表达中,也可能造成富有特殊情境下的独特唱腔和相对稳定的特征,从而形成历史上的巴渠民歌“范式”。但是这种突出时代语言、地域特征和生活习俗的巴渠民歌,也会随着融入不同时代、地域的山歌、号子等体裁而逐渐改变既有形态和风格——但同时也有很多“范式”得以相对稳定,有些稳定曲子范式的核心要素就是:语言、衬词和衬腔。在这首巴渠民歌中,特殊的节奏音型还合着规律性的节拍律动,配上既遵循巴蜀地域语言的规律的多样性衬词,又遵从了并不严格的语言音节特点。这些富有变化性的自然音节特征,不仅增添了的衬词表达力与感染力,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衬腔的稳定性风格和对于艺术形态的点缀意义。
再次,在巴渠民歌反应巴蜀地域的民风、民俗、民生方面,不仅曲调以音乐的形式展现出独特的感染力,还在作品的结构与表演中,也体现出衬腔与歌词的亲和作用,具有非常本土化的表达效果,同时也可以实现巴渠民歌有规律而又变化无穷的创造性传承、发展。节奏型、节拍律动的丰富性,不仅体现出富有变化的巴渠民歌中的本体元素,也体现出在生产、生活场面中使用的劳动号子,包括船工号子、搬运号子、上滩号子、打夯号子等的场面性、情景性特点。这些鲜活的节奏音型不仅体现出节奏的相对自由,还体现出这些规范的节拍组合中富有变化的思维特点。而且这些包括三连音、五连音、七连音、切分音、附点音型、连音音型在内的音型,往往结合着巴渠民歌演唱中的颤音、跳音、抹音、倚音和滑音等形式展现出千变万化的生活场面和生产情景,体现出民歌与现实生产、生活的联系性。
五、结语
“巴人文化”中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内涵与历史积淀,都在历史发展中以新的音乐形态、音乐技法、内涵表达形式,贯穿于巴渠文化的发展中。巴渠民歌作为巴蜀区域的文化形态之一,不仅可以透视出这一区域的历史,也可以透视巴渠民歌这一体裁发展的大致特征。巴渠民歌是新时代语境下对于“巴人文化”中音乐文化遗产的发扬,也是对于巴蜀地域历史上不同文化的扬弃,因此对于整个巴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都具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陈正平.巴渠民间文学与民俗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52.
[2] 筝 鸣.“巴山背二歌”的音乐美学特性探究[J].音乐探索,2008(1):14-17.
[3] 陈正平.巴渝古代民歌简论[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108-112.
[4] 黄 涛.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曲词探源及旋律形态研究[J].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02(3):7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