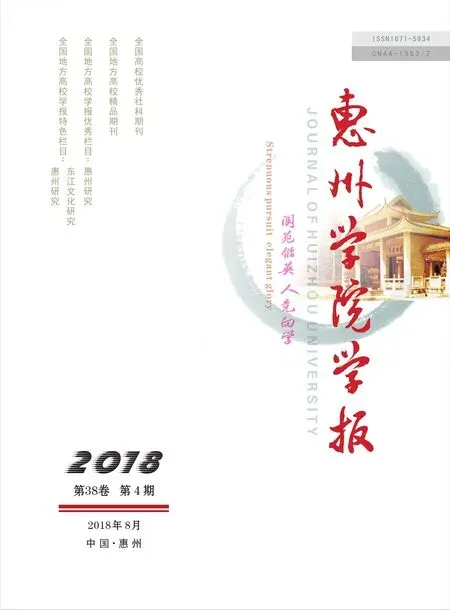北魏前期农业人口构成及其管理制度探究1
周升华
(江西艺术职业学院 基础教学部,江西 南昌 330044)
北魏拓跋氏为鲜卑族一支,世代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业。在占据中原前后,拓跋珪开始着眼于农耕生产的发展。然而,由于拓跋鲜卑统治下的诸部民受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农业人口极其有限。所以,北魏初期依靠国家强制力量,把以血缘为纽带的诸部民,通过离散、分土和定居的办法,变为地域组织关系下的农耕人口。随着拓跋鲜卑君临中原并巩固统治以后,拓跋氏统治者通过迁徙、镇压和招抚等手段,陆续把其他政权各种降附人口纳入自身农业生产发展当中。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与社会关系的进步,北魏前期统治者对各类农业人口施行了符合自身发展的多种管理制度。
一、北魏前期农业人口构成
(一)离散的诸游牧民
拓跋鲜卑世居草原,畜牧业一直居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史载:“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1]1。随着拓跋氏统治区域的扩大,逐步进入中原之际,统治者渐渐认识到农耕的重要性。因此,在拓跋珪复代国后,于登国元年下诏息众课农,史载:“二月,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1]20。拓跋珪选盛乐作为课农地,是因盛乐位于阴山之阳,黄河之北,有着良好的农耕条件和基础。“息众课农”即为解散各游牧部民,使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关于“息众课农”,《资治通鉴》也有相关记载,“代王珪徙居定襄之盛乐,务农息民,国人悦之”[2]3360,从中可知,“众”指国人,所谓“国人”,就是拓跋氏统治下的游牧民,他们身份不同于奴隶,属于平民阶层,包括拓跋鲜卑本部和其他被征服或吞并的诸部。拓跋氏在长期的发展和壮大过程中,统治下的游牧部落不仅数量众多,且种族繁杂。在成皇帝拓跋毛时,拓跋氏已经建立了草原上“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1]1的强大部落联盟,到桓帝猗迤时“诸降附者二十余国”[1]6,并曾一次性迁徙十万余家于陉北地区。昭成帝什翼犍时期,拓跋氏统治下的各部落人口数量更是急剧上升,并把四方来附的杂人统称为“乌丸”,“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分为南北部,复置二部大人以统摄之”[1]2971。拓跋氏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断征服和吞并其他游牧部民后,拓跋珪继息众课农后进一步散诸游牧民为编户人口,史载“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1]3014。拓跋珪登国初年的息众课农只是一个开始,之后,随着拓跋珪平窟咄、尽收刘显部、获十万余库莫奚与破高车袁纥部二十余万等军事胜利后,更多的降服部落成为解散部落组织和课农的对象,其中归降后的贺讷部就是如此,史载“其(贺讷)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1]2812。拓跋珪离散游牧民使其从事农业生产的措施意义重大,为其后的军事的胜利、生产结构的调整与社会性质的转变等奠定了基础。
在解散部落组织进行课农的同时,为解军粮不继,拓跋珪命东平公元仪在河北五原至于棝杨塞外实行屯田,这是北魏最早关于屯田的记载。皇始二年夏四月,拓跋珪又因军中缺粮,复调正在围攻后燕邺城的元仪前往钜鹿屯田,“徙屯钜鹿,积租杨城”[1]29。后来,这些屯田的士兵还遭到普隣的袭扰,“普隣六千人,伺间犯诸屯兵”[1]29。北魏早期屯田的劳力来自什么人,史籍没有确切记载,但知道的是,从登国元年息众课农到登国九年实施屯田,时间跨度为十年,这足以肯定军中屯田人口主要来自离散后的游牧部民。不过,拓跋氏的屯田也许就是“息众课农”的延续,而屯民则大概是亦兵亦民。天兴年后,拓跋珪更选屯卫,加以完善屯田制度,并施行“计口授田”的办法,向耕种者征缴赋税。
拓跋氏进入中原后,为了发展农耕,继续离散游牧民并实行计口授田,更多的游牧民转变为北魏新的农业人口。平定中山后,拓跋珪曾迁移大量俘虏到京师集中农耕,史载“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1]32。紧接着,拓跋珪诏命“内徙新民耕牛,计口授田”[1]32,把他们集中控制在畿内之田并督课生产。史载“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1]2850。可以说,基于北魏初期地广人稀的前提下,拓跋氏以充实京畿地区人口而发展农业为目的,至少到拓跋焘时,大量的游牧民被转变为农业人口。拓跋珪天兴二年“破高车杂种三十余部,获七万余口”[1]34,天兴三年,“高车别帅敕力健,率九百余落内属 ”[1]37,天 兴 四 年“ 高 车 别 帅 率 其 部 二 千 余 落 内附”[1]38,天兴五年“越勤莫弗率其部万余家内属,居五原之北”[1]40。这些被征服的游牧部落,后来大都被离散,“太祖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1]2309。拓跋珪的继任者拓跋嗣,在永兴五年徙越勤倍泥部二万家,在大宁施行计口授田,泰常三年“徙冀、定、幽三州徒何部于京师”[1]58。拓跋焘破高车、柔然后“列置新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1]75,其众达百万,真君八年“徙定州丁零三千家于京师”[1]102,如此等等。
可以说,北魏初期,由于农业生产区主要集中在京畿及周边狭小地区,以及农业经济刚刚起步,农业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且以离散的游牧民为主。但需明确的是,北魏前期游牧业向农业转变过程中,尤其是北魏立国初期,游牧部民成为农业人口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大量的游牧业部民依然被固定在各牧场或其他地区从事游牧业,他们被称为牧户或牧子。随着北魏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各政权降附人口逐渐成为为北魏农业人口的主要力量。
(二)各政权降附人口
各政权降附人口主要指战场上的俘虏和主动归附的人员,这类人口基本是北魏统治中原前的各政权统治下的汉族以及北方汉化的原有农业人口。北魏前期处置降附人口的措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迁徙为主,后期以就地招抚为主。
西晋以来,由于北方政权更迭,战争频繁,社会动荡,致人口急剧下降,“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着盖十五焉”[1]2849。为抢夺农业人口、发展农业生产和巩固被征服地区的统治,北魏前期统治者陆续迁徙大量人口到各地区,尤其是京畿及代北地区。拓跋珪天兴年“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1]34;拓跋嗣泰常三年“道生至龙城,徙其民万余家而还”[1]59;拓跋焘破北燕后,“徙营丘、成周、辽东等六郡民三万家于幽州”[1]81,太延五年“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1]90,真君九年“徙西河离石民五千余家于京师”[1]102。拓跋焘统一北方后,与南方刘宋政权形成对峙和拉锯之时,为了充实北方地区农业人口,开始大规模地迁徙南方平民于河北地区,真君六年“徙青徐之民以实河北”[1]100,灭刘义隆将王章后“迁其民五千家于河北”[1]100,正平元年伐南后,“以降民五万余家分置近畿”[1]105。这些所谓的“代迁户”对北魏农业贡献巨大,魏明帝时元晖论政曰:“国之资储,唯寄河北。饥馑积年,户口逃散”[3]572,可见,北魏河北百姓承担着政府税赋的主要来源,由于灾荒,他们四处逃散,而这些逃散户口应包括前期大量的代迁人口。据统计,从北魏立国到统一北方期间,大小移民数不下200次,涉及人口数量大约150万之多(西晋以来人口数量多以户或家为单位,具体数字难以估计),以杜佑《通典》考证西晋太康初北方人口为245万余户为据,可知北魏前期迁徙人口之多。这些移民大多都是汉族人口以及汉化的少数民族人口,有着丰富的生产经验和熟练的耕种技术。毋容置疑,在北魏前期农业生产发展进程中,各政权降附的大部分人口都陆续成为北魏控制下的农业人口。
北魏前期统治者在控制和掌握各政权降附人口方面,除了实施“移民”战略外,还注重招抚,尤其对主动内附人口,并且他们大多数被就地安置。拓跋珪天兴二年,“陈郡,河南流民万余口内徙,遣使者存劳之”[1]36;拓跋嗣时,“氐豪徐騃奴、齐元子等,拥部落三万于雍,遣使内附”[1]58;拓跋焘幸纽城,“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赐复七年”[1]77。随着北魏统治策略的转变,在拓跋焘统治以后,对归附民更是采取怀柔政策,《资治通鉴》载“白曜欲尽以无盐人为军赏,郦笵曰:‘齐,形胜之地,宜远为经略。今王师始入其境,人心未洽,连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怀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白曜乃慰抚其民,各使复业”[2]4134,,太和年成淹赞慕容白曜之功曰:“安抚初附,示以恩厚。三军怀挟纩之温,新民欣来苏之泽”[1]1121。
由上可知,北魏前期迁徙和安抚的人口可谓数量众多,规模空前。拓跋氏统治者通过强有力的军事手段及其他措施把他们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手中,使之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人手。《魏书·地形志上》载“正光以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太康,倍而已矣”[1]2455,以此为据,当时北魏总人口达500万之多,其中主要人口为农业人口,除了拓跋宏迁都洛阳后争夺的南方人口外,其大部分来源于北魏前期各政权降附的人口。
(三)各依附民
北魏前期存在着大量的依附农业人口,他们不是政府直接控制的,而是掌握在私家手中,他们在主人土地上耕种,缴税或服役。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前后,由于中原地区长期实行宗法关系下的“宗主督护制”,形成自成一套的坞堡林立的防御体系,各豪强宗族势力把持地方政治与经济特权,势比一方诸侯,对拓跋鲜卑也往往采取抵制和反对态度,从而控制着大量农业人口,《北史》载李显甫“豪侠知名,集诸李家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3]1202。史载“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1]2855,北魏前期依附民之所以众多,认为有三种原因包含在此史料当中,一是基层管理组织三长制尚未建立;二是荫附民不需承担政府劳役;三是豪强地主的逼迫。北魏前期统治阶级上层拥有依附民的现象较常见,所谓“民多隐冒,三五十家始为一户”[2]4270。《魏书·周观传》载:“真君初,诏观统五军西讨秃发保周于张掖。徙其民数百家,将置于京师,至武威,辄与诸将私分之”[1]727,《魏书·咸阳王禧传》载“田业盐铁遍于远近,臣吏童隶,相继经营”[1]537。
北魏前期大多数统治者尤好佛教,致使佛寺院大兴,并形成一种特殊的寺院经济。寺院里占有广袤田地的上层统治者成为僧侣地主,而那些在寺院田地被迫劳动和受剥削的众多底层僧人,被称为“僧祗户”和“佛图户”。《魏书·释老志》载:“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榖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祗户’,粟为‘僧祗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1]3037,以上说明,这些僧祗户和佛图户身份卑微,地位低贱,大多为躲避天灾人祸和官府赋税徭役才隐入寺院,成为寺院地主剥削下的农业人口。据李亚农先生分析,“所谓佛图户就是没有人身自由的隶属佛寺的农民;所谓僧祗户就是在佛寺的荫庇下,可以避租税的普通农民”[4]。拓跋焘灭佛远动中,寺院沙门曾大量被捡括成为平民,“魏主诏罢沙门年五十以下者,(以其强壮者,罢使为民)”[2]3867,并禁止“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不得容匿”[1]97,从拓跋焘释放寺院僧人来看,足以说明大量劳动人手依附于僧侣地主和贵族阶层,成为他们的依附民。
综上,北魏前期农业人口构成庞杂,属性不同,在不同时期各占比重不等,立国之初以离散部民为主,随着统一北方的进程,各政权降附的原有农业人口逐渐占主导地位,虽然部分人口荫附在私家,但相对较少。
二、北魏前期农业人口管理制度
(一)八部帅制
拓跋珪平后燕后,迁徙山东各州俘虏于京师,之后更选屯卫加以管理,所谓屯卫,即管理屯田的统领,且特诏曾负责屯田的卫王元仪还京,这种管理农业人口的措施,其实就是后来八部帅制的雏形。到北魏天兴元年,制定畿内之田,其耕种者明确为八部帅监管,“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至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1]2850。八部帅管理下的农业人口,之初基本上都是拓跋鲜卑离散的诸部民及“计口授田”的俘虏。北魏初期之所以形成八部帅制度,认为有以下两点原因,其一,离散部民的传统血缘组织关系被打破,各部族势力被削弱,部族首领难以接受而反抗。《魏书·外戚上·贺讷传》载:“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1]2812,由于分土定居,以贺讷为典型的各部酋长不愿解散其原有部落组织关系,极力抵抗,但拓跋珪实行以地域定居的统治意志并未为之动摇,而是针锋相对,即用武力强制的办法加以推行,最后贺讷因舅之故,又没有军职,才得以终老家中。其二,拓跋鲜卑早期落后的奴隶制度。登国元年,拓跋珪复代国后,依然实行二部大人统治策略,分南北部各统辖,以长孙蒿为南部大人,以叔孙普为北部大人。为了镇压各降民,最好的办法就是高压的军事管理,如前引“太祖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高车部落世为游牧民,种族强悍,由于不从使命,遭到区别对待。可见,拓跋统治者依靠落后且野蛮的奴隶性质的八部帅制,强行役使各游牧部民从事农业生产,使其成为控制下的农业人口。
北魏前期,至少在高宗以前,原来的八部帅最终成为农耕社会组织的官吏,史载高宗太安三年“以诸部护军各为太守”[1]2975。北魏初期对大量的移民大都采取八部帅制集中管理,如拓跋嗣时计口授田的越勤倍泥部,就是如此。拓跋焘征讨高车、柔然回到京师后,“列置新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1]75,派刘洁、安原和古弼镇抚,把他们集中安置,统一监镇从事农牧业劳动,这依然是八部帅制管理制度的延续。正平元年拓跋焘伐宋,“以降民五万余家分置近畿”[1]105,第二年,这些南来移民在中山企图叛逃,被州军平息。近畿即是中山地区,这是北魏实行八部帅制管理农业人口的集中区域。可见,北魏初期,八部帅制管理下的农业人口既有诸部民,也包括各降附民,通过八部帅制加以集体控制和监管,对于反抗者,实行野蛮的镇压。所以,魏初的八部帅制管理下的农业人口似比“农奴”,身份地位较低,且人身受到严格控制。
随着北魏封建化进程的迈进,到拓跋珪天赐元年,当初离散的部民已经无法辨认宗族,而且一些部族后代子孙已失业,被给予特殊照顾,“诸部子孙失业赐爵者二千余人”[1]42。当北魏沿着封建化道路继续渐进,官爵制度逐渐被调整和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逐渐趋于汉化,且汉族士人不断充进官僚体系和改变过去以武将为主的官员格局之后,八部帅制度慢慢地颓废,以至最后消亡。天兴元年十一月,北魏命吏部郎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十二月八部帅更名为八部大夫,史载:“置八部大夫……其八部大夫于皇城四方四维面置一人,以拟八座,谓之八国”[1]2972。八部帅由原来的军事统领变为政府官员,“以八国姓族难分,故国立大师、小师,令各辨宗党,品举人才”[1]2974。太宗时八部减为六部,“置天地四方六部大人,以诸公为”[2]3706,到世祖时又减至四部,“司卫监尉眷、散骑侍郎刘库仁等八人分典四部”[2]3761,最后在高宗太安三年五月,长期管理农业人口的八部帅最终成为各地方郡的长官,之后,北魏初期设立的八部帅再也不见史载。
(二)郡县编户制
北魏定户籍和颁均田法后,北魏前期各类农业人口基本上成为政府控制下的郡县编户齐民,当然,均田后的郡县编户制与之前的郡县编户制,无论在户籍、赋税、受田等有着本质的不同,本文所探讨的为均田制前的郡县编户制。
北魏早期统治者对主动内附的人口就注意招纳与抚慰,史载拓跋珪“初拓中原,留心慰纳……军之所行,不得伤民桑枣”[1]27。拓跋珪注意招抚,除了取得民心,另外一个目的就是维持当地农耕生产和生活秩序。北魏统一北方前后,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北魏政府更加重视对农业人口的控制,并接受和保留中原地区的地方郡县制。拓跋珪进攻后燕常山时,“自常山以东,守宰或走或降,诸郡县皆附于魏”[2]3434。这些归降的郡县,拓跋氏实行承袭旧制,就地接管的办法,安置百姓,维持生产,并注意减轻农民负担,史载“大军所经州郡,复赀租一年,除山东民租赋之半”[1]31。皇始三年,拓跋珪遣派官员巡视州郡后,为了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始耕籍田”。到拓跋珪天赐六年,由于人口增多,北魏开始对县进行整编,不满百户县罢撤,“初限县户不满百户罢之”[1]41。北魏拓跋珪统治后,随着郡县控制量的不断增加,为了有效控制和管理,拓跋统治者创立官吏巡查制度,选派官员到地方纠察不法,问民疾苦,劝课农桑,史载拓跋嗣时,诏“今东作方兴,或有贫穷失农务者。其遣使者巡行天下,省诸州”[1]57,拓跋焘太平真君元年“辛亥,分遣侍臣巡行州郡,观察风俗,问民疾苦”[1]93,拓跋濬遣穆伏真等“巡行州郡,观察风俗。入其境,农不垦殖,田亩多荒……”[1]115。
北魏前期除了就地控制郡县编户民,还迁徙或转变降服人口到各郡县成为农业人口。世祖拓跋焘曾把山胡转为平民,“诏山胡为白龙所逼及归降者,听为平民”[1]84,“平民”即普通百姓,应该就是纳入郡县管辖。真君六年,拓跋焘征讨西境各叛胡后,这些少数民族胡人都编入郡县,“西至吐京,讨徙叛胡,出配郡县”[1]98。除此之外,还专门设郡集中安置新民,北魏攻克刘宋青、齐州后,史载“显祖平青齐,徙其望族于代”[1]1089,《资治通鉴》也载:“魏徙青、齐民于平城,置升城、历城民望于桑乾,立平齐郡以居之,自余悉为奴婢,分赐百官”[2]4149,北魏统治者对南移新民,按照身份和等级的不同,区别对待,世家望族立平齐郡安置,称为平齐户。拓跋弘为了取得民心,把原先编入郡县管辖的张永的残废俘虏,放免回南方,“天下民一也,可敕郡县,永军残废之士,听还江南”[1]129。
北魏初期处于奴隶制发展阶段,拓跋统治者通常把大量的俘虏分赐给臣下,成为隶户、牧户等杂役贱民,北魏统称为杂户。随着北魏封建化进程的加快与农耕社会的进步,拓跋统治者逐渐把这些贱民纳入政府,成为郡县编户。北魏初期,曾征调人口专门运输缯帛,史载“天兴中,诏采诸漏户,令输缯帛”[1]2850,这些人后来成为官府的细茧罗谷户,但不直接隶属郡县管辖,且赋税混乱,致使杂、营户遍于天下,“魏初禁网疏阔,民户隐匿漏税者多。东州既平,绫罗户民乐葵因是请采漏户,供为纶绵。自后逃户占为细茧罗谷者非一。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1]2013。由于杂营户的庞大,严重影响政府赋税,所以仇洛齐上奏取消,纳入郡县,《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时引杜佑语曰:“景穆帝一切罢之,以属郡县”[1]3905。到拓跋宏时“班乞养杂户及户籍之制五条”[1]151,大量杂户放免为平民,包括平齐户沦为杂户的,如兵户将少游等,成为郡县编制人口。
前面谈到北魏初无乡党之法,唯依宗主督护制,大量人口依附豪强,田地荒芜,导致政府税收严重缩水。因此,北魏前期政府与豪强始终存在农业人口的争夺,如拓跋焘诏“其令州郡县隐括贫富,以为三级”[1]83,拓跋濬针对田地荒芜,民多流散,诏“其容隐者,以所匿之罪罪之”[1]115。拓跋弘时期开始实行“三长制”,史载“初立党、里、邻三长,定人户籍”[3]101,对豪强依附民大力捡括和附实,纳入郡县管理,“遣使与州郡宣行条制,隐口漏丁,即听附实,若朋附豪势,陵抑孤独,罪有常刑”[3]106。
综上可知,当北魏不断君临中原广大地区、农业人口急剧上升后,由于早期的八部帅制不断地颓废,郡县编户制管理农业人口的制度成为主导地位。当然,北魏均田制前的郡县编户制相对之后的有着本质不同,究其根原主要有三点:一是新旧社会生产关系的交替,处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中,不同地区社会制度、生产力水平发展不平衡;二是地方行政机构尚未完善,尤其是县以下的基层组织缺乏,同时,没有建立有效的户籍制度,户口错乱,赋税不均;三是北魏前期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对边远地区与地方豪强势力缺乏有效统治,加上地方守宰徇私枉法,官富勾结,隐冒人口,压榨百姓;四是天灾人祸不断,百姓饥馑逃难,人口流动频繁,户口难以造册簿计。然而,总的看来,北魏施行均田制以前,广大农业人口大都编制在郡县系统,承担着北魏政府的主要赋税和劳役。
需要补充的是,北魏均田制前的郡县编户制,也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尤其在初期。拓跋珪迁都平城后,便草创国家典章制度,命“邓渊典管制、立爵品”,并以汉族士人崔玄伯总裁。地方州郡县各设刺史、太守和令长,“刺史、令长各之州县,以太守上有刺史,下有令长,虽置而未临民”[1]2974,“虽置而未民”说明地方长官皆为虚设,他们并没有去赴任,《资治通鉴》在相同的记载后有“功臣州者皆征还京师,以爵善”一句,这不但印证了长官虚设,更说明所任者皆是北魏功臣,何为功臣?当然是北魏初年多因征战而立功者。到拓跋濬太安三年,随着八部帅制的诸部护军转为郡太守后,地方郡县官员多为军功者出身。因此证明,北魏前期的郡县编户制继承了早期的八部帅制军事性质,究其原因,主要与北魏初期处在落后的奴隶制阶段以及军事立国思想有关,同时,由于当时郡县编户民基本来自降服人口,叛附无常,如太宗时上党民杀太守,“上党民劳聪、士臻杀太守令长,相率外奔”[1]53,世祖拓跋焘时“高阳易县民不从官命,讨平之,徙其余烬于北地”[1]101,促使北魏统治者采取强有力的军事手段加以镇抚。
三、结语
北魏前期农业人口成分复杂,阶级属性和身份等级各有不同,且来自不同民族和种族,其中以汉族人口居多,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北魏以前各政权统治下的农业劳动者,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共同承担着北魏前期的主要赋税,推动着北魏农业生产的不断进步,为北魏中期推行均田制与汉化改革,以及向封建社会过渡奠定了坚实基础。由于北魏前期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以及畜牧业向农耕经济双向转变的社会复杂阶段,加之长期的对内外战争和拓跋氏的尚武思想,形成了符合自身实际并带有军事性质的农业人口管理制度。同时,在不同发展阶段,北魏前期因地制宜,因时制策,通过配合劝课农桑、捡括户口、加强吏治和打击豪富等一系列措施,对农业人口管理政策不断补充与完善。可以说,北魏前期的农业人口管理制度有很多的缺点和漏洞,但是,从掌控大量农业劳动力和转变社会生产方式,以及保持粮食和国家稳定来看,它有着其他政策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