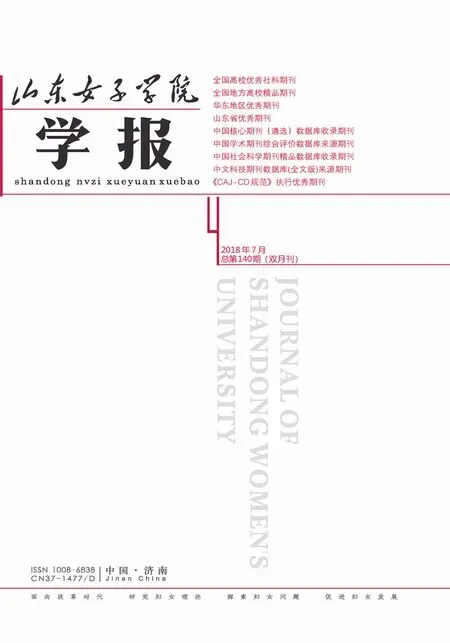知识女性多元话语的媒介呈现
——基于近代女性报刊的考察
姜卫玲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在中国近代特定的时代语境下,林宗素、陈撷芬、秋瑾、何震等知识女性跻身报刊界,通过报刊活动表达她们在文化、身份、政治以及职业方面的多重诉求,勇敢发出了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突破了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女性在话语表达方面的重重限制与深深禁锢。作为新型知识女性群体的杰出代表,她们在思想上最早觉醒,并通过自身的实际行动大声疾呼兴女学运动,主张妇女权利,不断追求自身解放;作为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毫不回避自身责任,积极承担起作为国民对于国家的责任;作为报刊活动的践行者,她们搭乘上近代社会转型的传媒发展快车,借助女性报刊(或自办报刊,或参与报刊编辑,或向报刊投稿)展开激烈笔战,表达女性自身在文化、身份、职业与参政等方面的多重诉求,为争取女性的自由与平等权力而大声疾呼,以图实现女界自立,得到社会积极响应……在她们身上,集中呈现出属于近代先进知识女性群体的多样化的复杂特征。本文透过尘封已久的近代女性报刊史料,力图用历史的原场与原貌去还原属于女性的多彩生活,重点探讨女性报刊图景所呈现出的文化、身份、职业以及参政等方面的女性话语。
一、女性话语界定及文献综述
女性话语是指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社会群体所表达出来的以各种文本形式和意识形式存在于社会历史时空里的那些“话”。简单来说,女性话语就是女性的言语。具体来说,女性话语是指站在女性的立场,以女性的独特视角来审视有关女性自身生存与发展问题的话语表述。王鑫曾在其专著《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女性启蒙》中指出女性话语所包含的双重含义:一是指“女性自己的声音”,即“女性运用语言,书写、表达、言说自己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内的情感、思想、体验以及与社会构成的某种关系”;二是指“有一套男性的‘女性话语’”,即“男性站在自我和女性的双重立场上对女性的书写、言说和表达”[1]。本文中的女性话语主要指的是第一种含义。
在一定程度上,女性话语的表达与呈现既是“女性主体意识的反映”,也是“女性对男性传统话语霸权的反抗与反拨”[2]。究其实质,对女性话语问题的探讨不但反映了女性对外部世界及社会的感知与判断,也反映了女性对自身价值观念的认知。因此,女性话语问题实际上凸显出了女性自身主体权力的重要性,女性正是通过自身主体权力的发挥来体现其在社会与历史中所处的具体地位。
近年来,在以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有关中国妇女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到了女性话语这一重要话题。杨永忠、周庆对女性话语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女性话语问题的提出实则反映了“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社会群体的觉醒,是以女性自己的声音对女性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描摹的结果,是女性对自身现实生存状况的展示”。女性话语的表达与呈现不但是“女性群体自我意识觉醒的需要”,更是“女性自身精神力量和存在价值的具体体现”[2]。朱颖、廖振华从媒介传播角度对女性话语权进行了具体界定,提出女性的媒介话语权是女性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表达自己对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意见和观点的权利,它不但包含着“女性受众的话语权”,也包含了“女性传播者的话语权”[3]。乔以钢与刘堃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女性话语形成的具体过程,指出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是“女学”话语还是“女权”话语,它们都是作为民族国家话语的工具而存在的[4]。
此外,王秀田以20世纪初期的女性社会职能和角色定位为研究基础,深入探析了在男女话语中“贤妻良母”的性别差异,指出知识女性对“贤妻良母”的认同与超越,并探讨了女性“贤妻良母”话语产生的具体渊源[5]。杜芳芳通过对晚清时期《女子世界》中呈现出的女权思想与教育主张的考察,指出其塑造和推崇的新女性形象促使沉梦在封建文化中的女性意识逐渐觉醒[6]。谢天勇、张鹏以《妇女时报》为个案,通过详细梳理该报对民国初年女性参政话语的具体表述,指出商业性报刊是如何呈现女权运动以及在知识与伦理之间作出的价值评判[7]。李晓红则以《妇女杂志》《女子月刊》等女性报刊为基本史料,在详细梳理现代上海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间关系的基础上,探讨了“现代中国知识女性发声的过程以及女性话语的形成过程”[8]。万琼华通过对民国初年报界对女子参政运动者的视觉再现与女子参政运动者对报人言说反再现的考察,指出女报人在争取女性政治话语权过程中虽一直处于被男性打压的状态,但却能积极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9]。
现有成果既有宏观视角的综合研究,也有丰富翔实的个案研究,不但纲目清楚,而且从女性报刊与女性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考量近代社会史和社会性别史,可以说是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但是,总体上对女性报刊图景中知识女性话语形成与呈现之间的整体现象背后的规律和本质缺乏深入探究。从古至今,中国妇女从来都不是孤立无援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她们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在清末民初强国保种的特定历史语境下,部分知识女性得以进入报刊媒介所制造的“公共空间”,成为国家、社会、民族、思想以及文化领域中被“言说”的具体对象。女性话语由此就成为了女性表达自己的观点、建构自身主体话语的一种语言权力。知识女性借助女性报刊这一彼时影响力巨大的媒介通道将自身并不强大的“声音”勇敢表达出来,反映了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境遇,其从“无声”到“有声”的发声过程值得关注。
二、知识女性多元话语的媒介呈现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之一的女性报刊,因为“其形构的公共空间,对于改变国人的思维、言谈、写作定势以及交流方式”以及“新闻的讲求时效,记者的好奇搜隐”,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与描摹了“社会情状的原生态”[10],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的关键时期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透过女性报刊具体文本内容的深入解读,可以“跨越时间的限隔,重构并返回虚拟的现场,体贴早已远逝的社会、时代氛围”[10]。同时,在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跨越的过程中,女性报刊既承担了启蒙中国女性、引导其思想解放的重任,描绘了女性生活的世相图景,又在表达与捍卫女性话语权方面,肩负着女性话语建构的使命,参与了从传统女性话语向现代女性话语的转换。
在西方女权思想影响与妇女解放吁求推动下,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知识女性通过展开笔战——或向报刊投稿、或自办报刊等方式,为女性伸张自我权利高声疾呼、奋起反击并得到社会积极响应。她们借助报刊媒介,或抒情怀古、表达见闻,或激扬文字、力参国事,高呼妇女解放和民族救亡,争取平等自由,冲破一直以来被拘囿在深闺里的束缚。她们打破报刊中男性话语的垄断,勇敢发出了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向社会表达了属于女性的独特主体话语,从寻求女性独立到人格平等,再到充分认识到男女的性别差异,使女性由过去的“被看者”转变为现时主动的“发声者”,努力建立了一个属于女性自己的话语表达空间。
(一)文化话语:兴女学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广大妇女一直深受父权制思想的束缚,在家庭、社会中一直是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的。“男性应刚,女性应柔;男子是主动的,女子是被动的。这种哲理,看来浅薄可笑,谁知他竟支配着三千年来的历史。”[11]在文化教育方面,女子不识字、没有文化竟被冠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美名”。在这种迫切需要革新的社会背景下,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们超越了传统社会划定的既定空间,自信满满地步入了社会公共空间。同时,她们凭借自己的既有学识与见识在报刊上公开表达属于女性自身在教育方面的文化话语,并与当时拥有话语权的男性精英所倡导的“女学”运动形成了呼应,一时间,掀起了颇为壮观的“兴女学”运动。
1898年7月,中国女学会在上海创办了《女学报》,这是我国第一份由女子主办、以女性为目标读者群的女性报刊。该报自创办起就以启蒙妇女思想为根本宗旨,主张无论男女都应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并经常发表由知识女性写作的论说文章。比如《论女学堂当与男学堂并重》《论中国创兴女学实有裨于大局》《劝兴女学启》等明确提出要“提倡女学”“开通女智”“讲论女德”。作为该报十八位女主笔之一的康同薇,深受其父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影响,深刻认识到了“女学”与培养“贤妻良母”之间的紧密关联,并在其所从事的报刊活动中为实现“兴女学”这个远大抱负而作出种种努力。“欲为起化之渐,行道之先,必自女教始”,“夫女学不讲,而几以防盗之法防之,日望天下之贤母教其子,淑妻相其夫,孝女事其父……不亦难乎!”[12]
1899年,年仅16岁的陈撷芬得到父亲陈范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上海成功地创办了《女报》(后改名为“《女学报》”)。该报以为广大女性服务的女性报刊为定位,响亮发出要致力于传播“女学”、践行“女学”的呼声。这正如陈撷芬在《发刊词》中所指出的:“今中国二万万女子,盲其目,刖其足,樊笼其身体,束缚其智慧。方且不能识字,何论读书;方且不能读书,何论学与权”[13],主张妇女要从封建桎梏下翻身获得解放,争取自由与独立的权利,大声道出了中国女性之从未言出之言。
1903年4月,胡彬夏在日本留学期间,和林宗素、曹汝锦等十多位女学生发起并成立了妇女团体组织——“共爱会”。此后,她还在《江苏》“女学论丛”栏目上发表《祝共爱会之前途》《论中国之衰弱女子不得辞其罪》等论说文章,提出要“振兴我女学,教育我女子”“排斥女子无才为德之谬训,脱去古来酒食是仪之习惯”[14],对传统性别关系进行了猛烈抨击,表达出了其较为激进的“女学”主张。在她看来,振兴“女学”,强调女性的社会责任是“女学”运动的重要内容。同时,她还激励妇女要冲破社会性别的藩篱与拘囿,接受新式教育获取知识以寻求自身的独立与自强。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知识女性不仅参与到报刊编辑活动之中,有些还成为报刊媒介的实际掌控者,担任报刊主编之职,这就使得女性话语从男性话语的垄断中逐渐剥离开来。她们借助报刊媒介挥斥方遒、指点江山,对社会发生着一定的影响,“从女性立场对中国男权历史文化的批判,显示着现代大众传媒主题的深化以及知识女性的成长”[8]。在面对当时纷繁芜杂的社会发展形势时,她们强调要通过学习来提升与丰富自己。客观上来讲,“女学”运动的兴起对提高晚清时期广大女性的文化素质以及增长女性见识等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从而使更多的女性成为了既能胜任传统家庭生活中相夫教子之责的“贤妻良母”,又能具有鲜明民族与国家观念的社会“新女性”。其中,以康同薇、裘毓芳、陈撷芬、林宗素等为代表的杰出女性在家庭中男性成员的支持与帮助下,踏着父兄、丈夫或亲友的足迹走上了社会舞台。她们通过创办报刊、兴办学校来传播“女学”话语,主张女性与男性一样要接受教育、打破封建传统旧观念、砸碎钳制妇女的枷锁与桎梏,力争获得解放与自由。虽然,此时女性主笔或女性编辑等报刊媒介从业人员在报刊舆论界发出的声音还比较微弱,但她们毕竟突破了女性在言论方面的禁锢,发出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女学话语,为后来轰轰烈烈的女学、女权以及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动力,指引了前行的方向。
(二)身份话语:倡女权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先进知识女性在“开新耳目,拓其心思,张其能力”目标的引领下,不但迈出了家门,还踏出了国门,走向了更为宽广的社会空间。她们当中有的赴海外留学,学习西方文化、掌握先进科技;有的游历各国,饱览异国风光、感受奇风异俗……这极大地拓宽了她们认识世界的视野。“从基本人权的严重缺失,到争取男女同权,更进而与男子一道,为现代国家的国民所应具备的各项权利努力奋斗”[15],妇女的生存状态较之以前有了明显变化。她们在艰难地迈向独立自主的历程中,力图借助时代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契机来摆脱传统女性在自我身份归属方面的盲点与认识上的误区,竭力通过报刊活动书写属于女性自己的历史话语,表现出重塑女性自我社会身份的强烈意愿。一方面,她们非常重视报刊媒介的思想启蒙功能,高度肯定女性在家庭中所担负职责的社会价值。如陈撷芬在《女学报》上先后发表了《兴女学说》《女权与文学》《男尊女卑与贤妻良母》《普告同志妇女文》《男女之比较》《婚姻自由记》《独立篇》等论说文章,在提倡“女学”基础上,大力传播女性自立的理念,倡导女性应该拥有的各项权利。另一方面,她们又试图突破传统女性社会身份的束缚,强调女性与男性在社会身份上的平等,试图重构一个男女平权的理想社会,在近代社会公共空间里呈现出属于现代新女性的多重风貌。知识女性利用所掌控的女性报刊媒介,站在舆论舞台的前台大声表达女性的看法,试图摆脱传统封建社会一直以来女性要承担更多家庭责任的要求。
女性报刊作为女权运动的言论平台和宣传动员工具,以“倡女权”为主要目标,并将“倡女权”与爱国救亡运动以及民主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号召妇女要能积极参与到“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事业之中。因此,社会上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知识女性们都能代表女界及时发言,表达她们对于国家事务的具体看法。与此同时,在整个社会从政治层面讨论女性作为国民一份子对国家与民族责任的时代背景下,部分男性知识精英提出了“女国民”的称呼,主张妇女应该同男性一样对国家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对此,知识女性群体积极响应并认同这一社会身份,开始重新思考自身的家庭价值与社会价值,勇敢承担起作为“国民一份子”对于国家的责任。例如,胡彬夏在担任《妇女杂志》主编期间,接连发表了十多篇以“女性道德”“女性职责”等为主题的文章,高声呐喊“中国妇女按照科学新知来主持家政,教育儿童,或以西方妇女为楷模以建设自己的小家而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贡献出一份力量”[16],力图以一种建设性的意见展现作者心中“二十世纪新女子”所应具备的精神风貌及其应该履行的家庭与社会职责。
女性报刊图景中呈现出来的知识女性群体对身份话语的表达,重新界定了女性在家庭与职场生活之间兼具的现代性身份。一方面,女性报刊大力提倡女子走职业化的道路,不仅初步建构了现代都市女性身上所具有的完全区别于传统女性的全新社会身份,也勾勒着其逐步走向社会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也搭建了与世界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女权思想交汇的话语平台,鲜明地表达出女性在“倡女权”方面的身份话语。但是,有些从家庭“出走”、思想上已经初步觉醒起来的女性在重建传统的性别关系、探索自身新身份方面困难重重。陈撷芬在女性身份认同与主体建构方面展现出一种家庭与社会的调和立场,最终却因现实条件的种种限制和个人激进思想的退潮而重新退回到封建家庭,选择继续传统女性的身份。曾在社会大舞台上叱咤风云、独领风骚的秋瑾,尽管猛烈抨击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所遭遇的种种不平等待遇,提倡女性要走上社会从事相应的职业以实现经济自立,却又提出“幼而事父母,壮而事舅姑,长而育儿女,固其本分之事”[17],倡导女性还是要担当好传统宗法家庭的社会角色,要能够操持家务以照顾好家庭。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彼时女性群体在寻求自我独立身份诉求以及获取女性权利方面的任重道远。
(三)职业话语:立女业
在西方新思想与新观念的影响下,知识女性逐渐摆脱封建旧家庭的束缚,在争取社会权利、改变传统两性关系和秩序的社会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女性启蒙者的角色。“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等思想的传播让一部分女性重获自尊,她们开始从愚昧无知状态中逐渐清醒过来,陆续走出闺阁,接受新学,步入社会领域。她们除了在情感婚姻和命运掌控方面有了一点主动的权利外,在其社会职业选择上也突破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尤其是生活在大都市之中的知识女性在学校与社会的多种规训手段下被形塑为各种职业角色,陆陆续续在服务、商贸、教育、医疗、文化、传媒、科研等行业初露锋芒。由蒙昧无知到初步觉醒、由柔顺屈从到为未来命运的自我抗争,由无主体状态到确立鲜明的女性意识……她们不再是闺媛村妇,而是逐渐成长为引领社会新风尚的时代“新女性”,表现出了自信与时尚的一面。
同时,部分女性先觉者在对女性群体进行启蒙的同时,又把女性启蒙纳入到了整个时代所在的政治、思想与文化的启蒙语境当中。吕碧城不仅为女子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女性参与具体报刊活动开了历史先河。1904年,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她,由于才华横溢,受到英敛之的赏识,进入天津《大公报》报馆工作,成为我国较早以新闻业为职业的女性之一。面对国家民族的苦难以及妇女生存的艰难境地,她发出了“眼看沧海竟成尘,寂锁荒陬百感顿。流俗待看除旧弊,深闺有愿作新民。江湖以外留余兴,脂粉丛中惜此身。谁起平权偕独立?普天尺蠖待同伸”[18]的呐喊,打破了女性自古以来的喑哑无声状态。
部分知识女性从之前只知在家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成长蜕变为“为稻粮谋”的职业女性。如张竹君、徐自华、何香凝、张默君、尹锐志、沈佩贞等凭借自身的努力与奋斗,成为了她们所从事行业的佼佼者。在报刊媒体呈现的女性职业话语的直接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妇女认识到相夫教子的居家生活不再是女性生活的全部依托,“孝女”“贤妻”“良母”也不再是女性的全部社会角色。因而,她们更多地开始考虑到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进而关注到属于女性自己的人生价值,尤其注重自身人格与经济的独立,在一定程度上也摆脱了传统女性对于封建家庭的依附性而具有了现代新女性的独立人格。这些在思想意识上觉醒的知识女性,以独立自主的人生姿态站在女性立场,从女性自身角度出发,追求男女平等和自由独立。
(四)参政话语:述女政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妇女界提出了女子参政的明确要求。以唐群英、张汉英、张昭汉等为代表的女权精英不但成立了“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同盟会”“中华女子竞进会”“湖南女国民会”“浙江女子策进社”等妇女参政团体,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要求男女平权、争取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为中心的女子参政运动。在引领妇女解放运动向纵深发展的同时,她们还积极创办女性报刊,通过报刊表达女子参政的合法性以及通过国会、宪法迅速实现的迫切愿望。1912年11月,神州女界协济社在苏州出版《神州女报》。该报站在女界立场发表了数篇宣扬女子参政的论说文章,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张昭汉在其发刊词中强调,男女平权首先是男女在教育上要平等,“顾欲权之平,必先平教育。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苟能受同等教育,则尧舜人人也,吾亦人也,人奚分于男女?”[19]此外,唐群英还主持创办了《女子白话报》。该报用文字浅显的白话报道了与女性相关的大量政治知识,响亮提出女子参政权利实现的根本之法在于开通女界智识的思想主张,引发当时社会上众多妇女思想上的共鸣。
据不完全统计,在1912年至1913年两年间,新出版的女性报刊有17种之多。这些刊物大多数是由积极参与政事运动的精英知识女性所创办的,报刊内容主要是侧重于对女性政治权利的表述,强调男女应该具有同等的社会身份。此外,这些女性报刊还尤其重视报道西方妇女参政情况,如日本女子学校章程、外国杰出女性传记、欧美妇女为选举权及参政权所作的斗争介绍等,对我国女子参政运动起到了一定的鼓舞和示范作用。在世界各国妇女参政典型案例的直接示范下,知识女性联系中国国内实际情况,发出“现虽处黑暗之世,然二十世纪民权、女权均大发达,我二万万女同胞,终必有参政之一日。诸姊妹其勉之!他日国魂复苏,女界独立,当不忘英国妇女筚路蓝缕之功也”①的强烈感慨。在女子参政运动中的女权精英们以激进态度评判时局的变化,大声提出男女要同享政治权利的要求,表达女性力争参与政事的强烈政治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此时知识女性的思想意识以及性别觉醒的程度。她们对报刊作为舆论工具在女性运动中的重要作用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并通过报刊这个女性话语表达的公共平台,扮演女界舆论领袖以“立言”,品评社会形势与政治格局方面发生的变动,力图争取在政治领域内妇女应该具有的平等地位及其相应的政治权利,体现出妇女参政意识的觉醒及其对女子参政的强烈渴望。虽然民国初年女子参政运动以失败告终,但是女界精英在响亮表达政治话语、要求参与政事的呼声推动了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进程。
三、结语
在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社会语境与政治宣传的现实需要中,知识女性透过女性报刊传播新知识与新思想,宣传男女平等,尤其是呼吁女性在文化教育、身份认同、职业选择及参与政事等方面发出了属于女性自己的主体“声音”,试图以自己的女性责任话语建构其突出的主体身份以追求自身在政治方面的各项权利,表现出其自身独特的应对方式与策略。同时,在此过程中,她们也完成了自身社会角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并得以快速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人”群体,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其进步意义不可低估。
注释:
① 参见刘瑞容的《贺英国妇女得选举权文》,载《女子世界》1904年第7期。
参考文献:
[ 1 ] 王鑫.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女性启蒙[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4.
[ 2 ] 杨永忠,周庆.浅论女性话语[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4,(4):17-19.
[ 3 ] 朱颖,廖振华.当代女性媒介话语权缺失探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8,(8):227-230.
[ 4 ] 乔以钢,刘堃.晚清“女国民”话语及其女性想象[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41-50.
[ 5 ] 王秀田.20世纪初期女性话语中的“贤妻良母”[J].石家庄学院学报,2008,(4):89-92.
[ 6 ] 杜芳芳.晚清期刊《女子世界》中的女权思想及其教育主张[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7,(6):68-72.
[ 7 ] 谢天勇,张鹏.新知识与旧道德之间:民初《妇女时报》女性参政话语的媒介表述[J].国际新闻界,2012,(12):107-114.
[ 8 ] 李晓红.女性的声音: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381.
[ 9 ] 万琼华.视觉再现与反再现——以民初报人对女子参政运动者的言说为中心[J].妇女研究论丛,2013,(1):72.
[10]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3.
[11]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
[12] 乔素玲.教育与女性: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与杰出女性觉醒(1840~1921)[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113.
[13] 陈撷芬.发刊词[J].女学报,1903,(1):1.
[14] 胡彬夏.祝共爱会之前途[A].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Z].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354.
[15] 张朋.近代女性社会主体身份的自我建构:以康同璧为个案研究[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82.
[16] 王秀田.民初知识女性的角色认同:以胡彬夏为个案[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37.
[17] 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M].上海:三联书店,2006:20.
[18] 刘纳.吕碧城评传·作品选[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108.
[19] 张昭汉.《神州女报》发刊词[A].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Z].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295.
——参政妇女的社会性别意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