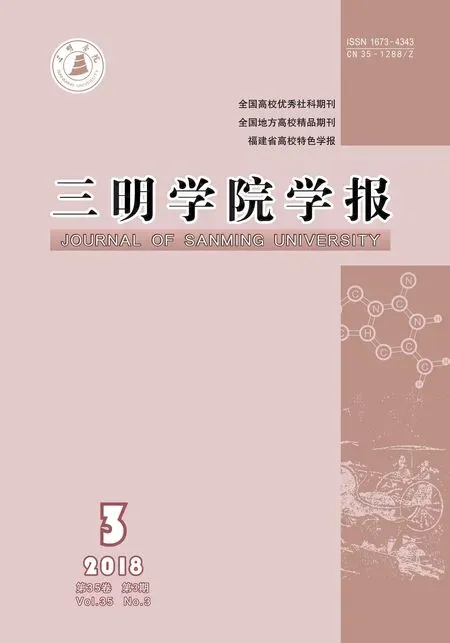清初遗民诗歌中的“雾霭”意象
陈含笑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雾霭”因其变幻无端的“形”与迷离朦胧的“境”,古往今来给了文人们无限的遐想与创作空间,成为许多诗人所偏爱的意象。而清初遗民们对于其生存时代的黯淡迷茫有着深刻的体会,有的遗民明知“复明”无望却仍执着奔走于抗清前线,有的则隐匿于山林之中却依旧难排家国之愤。整个时代的气氛如同被浓雾笼罩一般,故而清初遗民诗歌中常会出现“雾霭”等色泽昏暗的意象。相较与其前代的诗人,遗民诗人们不仅扩大了“雾霭”的表现空间,丰富了其思想意蕴,与此同时,特定的时代之下该群体独有的怅惘心绪亦从“雾霭”意象中可见一斑。
一、古典诗歌中雾霭意象的渊源
雾霭意象在古典诗词中经常出现。李商隐、苏轼都曾写过有关雾霭的诗句,如李商隐的“含烟惹雾每依依,万绪千条拂落晖”,苏东坡笔下的“江边日出红雾散,绮窗画阁青氛氲”。雾霭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气象,某种程度上与风霜雨雪诸类意象相似,它既有客观绘景大自然的一面,也有让文人利用想象与情感去丰富其象征意蕴的一面。总的来说,雾霭意象在古典诗歌中有以下几种解读。
(一)求仙隐逸之境
雾霭形态上的缥缈虚无、似真似幻,令诗人往往将之与隐逸于世外的仙境奇观联系在一起。不少传统仙话志怪小说与游记中描述仙境,通常也以云雾缭绕来衬托神仙道教的 “福地”,使之带上与人间阻塞的仙幻色彩,如《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序)》就有相关的记载:“……则有灵官阀府,玉宇金台。或结气所成,凝云虚构;或瑶池翠沼,注于四隅;或株树琼林,疏于其上。 ”[1](P55)
雾霭意象可以追溯至屈原的 《九章·悲回风》“凭昆仑以瞰雾露兮,隐岷山以清江”和《远游》“叛陆离其上下兮,游惊雾之流波”二句。这两句诗都是屈子在以梦幻之笔还原仙境,以求脱离现实苦难。可见雾霭意象最初的功用便是描绘世人心目中的仙境。后人沿着这个方向对“雾霭”继续进行创作,如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描写唐玄宗与杨贵妃在虚境重逢时,也是巧妙地运用了雾,“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从长安人寰切换到蓬莱宫中,只用一层尘雾将之隔开,将在现实世界无法解脱的痛苦的唐玄宗引往仙境。屈子对“雾霭”充满浪漫色彩的妙笔,使后来那些厌弃世俗、追寻仙逸世界的诗人们也同样采用雾霭意象来绘制仙景,如曹子建曾在游仙诗中感慨云:“人生不满百,岁岁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雾凌紫虚。”想到人世间的欢娱既不能长久,诗人则幻想振翅排开迷雾,凌驾于紫虚仙境之上。
(二)怅惘迷茫之情
王国维曾提出:“昔人论诗,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2](P129)景物意象的注入是为了烘托出主体的“情”,“雾霭”也正是如此。以雾气衬惆怅之情,应当是雾霭作为诗歌意象演变过程中最为普遍的作用。唐代诗人吴融曾写下《武牢关遇雨》,其中有“带雾昏河浪,和尘重客衣”的诗句,作者思乡怅惘与政治上的不得意交杂于心头,眼前的雾景与河浪动态联结,湿重的意象组合造成一种令客“重”的体验,更加衬托出了整首诗中弥漫着的“惆怅”情绪。因雾本身给人带来的茫然、阴沉的直观感受,数米之内望不清前路,这无疑与诗人有时迷惘寻找不到人生出路的心境颇为吻合。故而诗人在描写阴晦黯淡的画面来烘托自己伤感迷茫心境时,通常会选用色调偏暗的雾霭来设色布景,如韩愈“雾雨晦争泄,波涛怒相投”,又如杜甫“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雾中”诸首诗歌皆是此类。
(三)状人摹物之变
雾霭除了描绘仙境与衬托诗人们心中迷惘惆怅的情绪之外,还多用来结合色泽鲜艳或飘逸柔软的意象来摹物衬人,要么是以雾之飘洒来比喻物体的形态,要么是以霭之仙灵来衬托人物的姿态。苏轼就善于将雾搭配以不同的意象组群,并运用通感的手法,巧妙准确地传达出不同物、不同人的特性。他以雾摹写劲健灵动的墨字时是“金笺洒飞白,瑞雾萦长虹”“嘘嘘云雾出,奕奕龙蛇绾”,摹写云巾又是“黑雾玄霜合比肩”,以雾摹写音乐则是“多景楼上弹神曲,欲断哀弦再三促。江妃出听雾雨愁,白浪翻空动浮玉”。除此之外,他还用雾传神地摹写了牡丹海棠、美人乐妓等等。[3](P44-48)可以说苏轼运用他的才力与情思,扩大了“雾霭”的表现能力,为雾霭意象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清初遗民诗歌中的雾霭意象
雾霭意象有其不可替代的象征性与包容性,但相较于大自然中其他的风霜雨雪诸类意象并不算常见,通常只在冬春季节的清晨比较多见,何况有些地区因为地形环境等的限制,并不容易有雾霭天气,导致雾霭意象在诗歌中的出现频率并不高。《全唐诗》48 900余首诗中,“雾”出现 565 次,“霭”出现 317 次[4];《宋诗钞》近15 000首诗中,提到雾的诗不超过100首[5];而在卓尔堪选辑的《遗民诗》16卷共3 000多首诗中,含有“雾霭”意象的也不超过50首。[6]总体而言,雾意象占诗歌的比重并没有特别显著,但是雾霭意象在清初遗民诗人的笔下已经较前代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值得引起注意。
(一)雾霭色泽更为黯淡
雾霭本体是透明的,所以诗人们常常将不同的颜色与雾霭搭配,使之与诗歌的情感基调更为契合,如“翠雾”之葱茏、“紫雾”之祥和、“蓝雾”之旖旎等。从一些具体的诗作看来,“雾霭”的颜色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首诗歌的基调。但是在清初遗民诗人笔下,雾霭不再是作为冲淡万紫千红而设置的朦胧美的屏障,随着诗人们的心境改变,在雾霭色泽的选择上也都开始偏向于冷调。
阎尔梅《天平山》一诗中写道:“前无路迹青霄闭,下有泉声白雾沉。”后半句诗人先闻“泉声”,再以“白雾”从侧面生动描绘出泉落的姿态,虚实结合,可谓妙笔。如果用肉眼远观,雾霭的颜色本就是白色的,“白雾”本应该是写实,可阎尔梅却在后面加了一个“沉”字,再与泉水中的水汽相结合,不由得令人心生寒意,与诗中所透露的悲凉沉痛相契合。而傅鼎铨在《岑副戎持扇索诗写此示之》中的“兴亡底事发哀吟,厉黯南天瘴雾深”,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到雾气的具体颜色,但诗人用了“瘴雾”一词,便足以令读者感受到雾色泽上的黯淡阴沉以及其所带来的压迫感。除了阎尔梅与傅鼎铨,还有其他遗民诗人笔下的雾,结合当时的凄凉苦楚心境,色泽都普遍较为黯淡,如方兆曾《长平坑》中“一时降卒坑俱入,阴雾号风不见天”的“阴雾”,吴牲《寻庐山旧径晚归》中的“青霭近已无,夕阳明复灭”中的“青霭”,还有申涵光在《燕京即事》写下的“山前兔急雁飞号,黑雾黄尘落毳袍”中的“黑雾”等,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二)雾霭姿态更为动态
从“云蒸雾集”这一成语可看出,雾在古人的认知中多是静止不动的,常以悬浮的形式存在于自然空间中,哪怕诗人就算是要给雾搭配上动词,一般也都是搭配“释”“出”“浮”之类比较平和舒缓的动作。古典诗歌中也常常有体现这一点,如讲究用字的杜甫在《梅雨》诗中写道:“茅茨疏易湿,云雾密难开。”这里写的并不是一副静态的画面,而雾也多作为固定不动的背景出现。曹操笔下的“螣蛇乘雾,终为土灰”更是如此,雾在这里只是作为以静衬动的次要部分。
相反,在清初遗民诗中,雾则更多的以一种动态的形式出现。如清初著名诗人兼思想家顾炎武写的“幽严秘洞难具状,烟雾合沓来千峰”,千峰岿然不动,烟雾沓然而来,雾俨然成为了这幅风景画的主要构成部分。如果说顾炎武笔下的雾还处于较为平和的状态,那么许承钦笔下的 “石华朱英寒雾涌,瑶蕤翠葆哀壑奔”中的“雾”则是卷着寒气奔涌过来,而且“涌”字无论从姿态还是从气势上看,程度都更为夸张。除此之外,遗民诗人还纷纷用创造性的词赋予雾霭更富动态的意蕴,如“春烟郁秋愿”“下有泉声白雾沉”与“云聊断霭天光辉”,都是用有力道或是有广度的词来还原诗人心中之雾的形态。
遗民诗人雾霭意象有色泽黯淡的特点,而这种颜色上的晦暗一旦与迅猛冷硬的动作联结起来,便生发了一种别样的效果,雾霭也象征着始终笼罩在遗民心头的压迫感与无奈感,与当时遗民们被迫害的心境极为相似。这也就不难理解雾霭意象在色泽上偏冷淡,雾的形态上却为何多以动态出现了,这两点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三)雾霭所衬托情绪更为悲凉晦涩
唐代诗论家司空图认为“意象欲出,造化已奇”[7](P54),这一句揭示了诗歌中的“象”与诗人的“意”的关系。清人孙连奎对这两句话有过解读:“有意斯有象,意不可知,象则可知。当意象欲出未出之际,笔端已有造化。”[8](P128)结合遗民诗人笔下雾霭意象所呈现出的特点,不难探究其背后诗人更深层次的情感,且多是凄凉悲怆、无法排解的。每逢乱世,就不免会出现归隐避世之人、想要远离政治漩涡之人,隐于山水,心无旁骛。清初也有一批为了逃避清政府的残害而隐于山林的遗民,可卓尔堪《遗民诗》十六卷中几乎没有以雾霭来粉饰太平,或是一味求仙隐逸的诗作,哪怕是诗人通过霭来描写山清水秀的风光,随之而来的也是感叹今非昔比与无以安放的愁绪。如余怀的《金陵杂感》:
六朝佳丽晚烟浮,擘阮弹筝上酒楼。
小扇画鸾乘雾去,轻帆带雨入江流。
山中梦冷依弘景,湖畔歌残倚莫愁。
吴殿金钗梁院皷,杨花燕子共幽幽。
余怀(1616—1696),字澹心,一字无怀,号广霞,自其父辈即流寓南京,明崇祯时为南国子监监生,明亡后奔走于江浙一带,积极筹备抗清活动。这首诗描写了金陵风光,其中“小扇画鸾乘雾去,轻帆带雨入江流”一句中的景致悠远,从手中之扇到眼前的江帆,由近到远将在酒楼上所见的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可谓是写景摹物的佳句。但下一句诗人笔锋一转,随即出现了“梦冷”“歌残”等字眼,虚实结合,现实中的美景佳酿也无法排遣余怀心中的愁绪,迷雾之下,尽是诗人的自伤之情。
三、清初遗民笔下雾霭意象的深层内涵
雾霭意象在清初遗民诗人的流变并不是偶然,而是蕴含着更深层次的内涵——对“复明”的呼喊,这也是“雾霭”在明末清初之际相较于其他悲冷意象的特殊性。
1644年明朝发生了一系列天翻地覆的变化:李自成通过农民武装占领北京,不出数月崇祯皇帝自缢,之后清兵又打着所谓代明讨“贼”的口号,在吴三桂大军的先导下打开了紫禁城的大门。[9]“夷夏之大防”的观念始终根植在儒士的心中,外族入侵,家国一朝覆灭,遗民心中不免对明王朝有着极为深沉的眷恋。
尽管在清政府的打压之下,各地遗民的处境极为艰难,如不得已易僧服的万寿祺,亡命南北数十年的阎尔梅,乃至吴中的遗民志士迫于形势组建成的“逃之盟”等。当时对于他们来说绝非是一个光明的时代。整个时代犹如是被深雾笼罩,看不到一丝光亮,但遗民们仍坚守心志,用血和泪浓墨重彩地写下了历史上可歌可泣的一笔。正如严迪昌在《清诗史》有关遗民的引言中说道:“这是一群‘行洁’、‘志哀’、‘迹奇’,于风刀霜剑的险恶环境中栖身草野,以歌吟寄其幽隐郁结、枕戈泣血之志的悲怆诗人。”[10](P61)
不仅仅是因为时局的晦暗使他们对雾意象有了新的诠释,晦涩、冷硬、悲情应还有更隐晦的指向。“沉雾蔽日”,即隐晦地点出“明”被灰暗的势力所蒙蔽而暂时无法寻见;而在雾霭茫茫天地中,遗民不得不追寻自己的内心,一次次以血泪之笔呼唤重复光明的日子,这与遗民想要实现复明大业却又一次次落空的迷惘心境极为相似。而结合当时的时代特点,“明”不单单指向了时代社会的光明,也巧妙地与朱明王朝的国号“明”相为呼应,故而雾霭意象在诗中即多了一层为了引出“复明”的含义。“雾霭”也处于光明的对立面,象征着当时阻碍“复明”的清廷势力。这也是清初遗民诗人笔下的雾霭,与其他时代诗人所写的雾霭景象最为鲜明的不同。如遗民诗人李沛的托“雾”忆“明”之作《人日雾过樊汊》:
野水孤村合,荒林晓雾霁。
断桥寻宿舸,前路听鸣鸡。
江汉何时净,乾坤此日迷。
白头飘短发,俯仰望朝曦。
此诗看似诗人用纯熟的白描手法绘樊汊之景,但意在言外,心境含蓄。前四句皆为诗人在天将亮之际寻舟渡的所见所闻,从“孤村”到“荒林”,再从“寻舸”到听到鸡鸣,想着年华已逝去,诗人望着茫茫的江汉与灰暗的天空不禁发出忧思感慨,希望能重见光明。现实中“朝曦”会随着明日的到来而到来,可试问诗人心中的“朝曦”何时能来?整首诗歌中,诗人的复“明”之意虽未直接点明,但其渴望“朝曦”以求去“雾”遮蔽后的“日迷”,虽白头心尤不悔的心志,已在迷雾之中愈发坚定。这与李沛同族的遗民诗人李清多写“月明”意象,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有追求“复明”的深层含义。
值得注意的一点,与宋遗民不同,清初的遗民诗人毕竟经受了残酷的新朝文网之灾,当时大部分的遗民都遭受残酷的迫害,许多诗作在流亡中已佚,无法完整保留下来。笔者只能从仅存的部分诗作中分析遗民诗人笔下的意象。尽管如此,这个群体身上所带有的时代悲凉色彩仍能从“雾霭”中感受到。
[1]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道藏:第11册[M].上海:上海书店;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
[2]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中华书局,2016.
[3]赵红.苏轼诗词中的“雾”意象论略[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6(5).
[4]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5]吴之振,吴自牧,吕留良,等.宋诗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卓尔堪.遗民诗[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7]司空图.二十四诗品[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8]畅广元.诗创作心理学——司空图《诗品》臆解[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9]郑天挺.清史简述[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0]严迪昌.清诗史: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