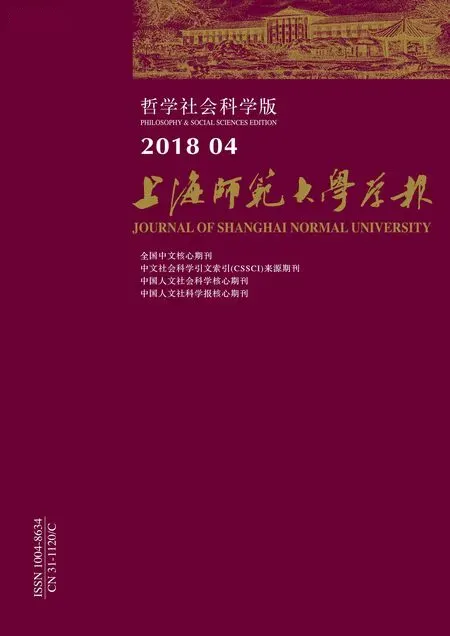《聊斋志异》高珩序发微
——兼与欧阳健相关论述商榷
詹 丹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在蒲松龄《聊斋志异》流传过程中,除了作者的自志,出自作者亲友、作品刻印人、选编以及评点者等的不少序跋,也是理解《聊斋志异》作品、社会背景以及古代小说理论的重要依据,这其中,作者所敬仰的其淄川同乡高珩撰写的一篇长序,有着特别重要的位置。此前,虽然有学者对该小说的序跋理论有过讨论,特别是欧阳健的《〈聊斋志异〉序跋涉及的小说理论》一文(以下简称欧文),[1]对清代流传至今的《聊斋志异》相关序跋所蕴含的小说理论价值做了最为全面的梳理,并提出了一些结论性意见,并不时被他人所引用。从整体看,虽然其对各序跋流变梳理的线索较为清晰,但恰恰是涉及高珩序的分析,显得既笼统又不够准确(结论部分下的判断也比较随意)。故本文在结合《聊斋志异》作品来分析高珩序言的同时,也把欧阳健的相关论述一并纳入讨论范围。
一、从“同而异”到“异而同”
欧文的论述,对《聊斋志异》各种版本的序跋从两个角度进行了分类。第一是以时间发展为线索,即把所有的序跋分为“康熙间的序跋”“雍正、乾隆间的序跋”“嘉庆、道光间的序跋”三个时期;第二是从所有的序跋中概括出三个理论话题,即“辩异”“寄托”和“作文”。而高珩的序言,是作为“辩异”的议题被归到康熙间的序跋中,首先得到欧文详细讨论的。
在欧阳健看来,高珩的序言针对当时社会“不语怪力乱神”的氛围,从儒家经典入手,为“异”定了位、正了名。这样说,自然没有问题。因为高珩的序言开宗明义就提出了“异”的关键问题,并引用旧题孔子撰写的《易传》加以阐发。欧文大略谓:
志而曰异,明其不同于常也。
然而圣人曰:“君子以同而异。”何耶? 其义广矣、大矣。夫圣人之言,虽多主于人事,而吾谓三才之理,六经之文,诸圣之义,可一以贯之。则谓异之为义,即易之冒道,无不可也。[2](P1)
而欧文据此加以了阐释,所提出的主要看法是:
高珩指出,中国传统哲学虽多主于人事,但更强调的是“三才”的辩证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之一,就是对天人关系的关注和重视:文学除了反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之外,还应该反映人与天的自然关系。他进而引《易·系辞上》和高亨注来说明“冒道”:“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高亨注:“冒,犹包也。”高珩就这样借引申发挥圣人的“冒道”即包容万物的思想,为“异”争得了生存的一席之地。[1](P3)
笼统地说高珩是借儒家经典来给《聊斋志异》中“异”的存在争取合法权当然对,但如果说高珩引用“三才”论是为了强调文学除了反映人和人的关系,还应该反映人和自然的关系,则既不符合《易传》的原义,也曲解了高珩的话,更与《聊斋志异》作品的实际相背离。因为所谓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解析,完全是站在现代人立场上的一种理解,这是工业社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断裂以后才有的一种分析观念。而就古代中国来说,天人合一观念的深入人心,也不会将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割裂开来。所以,就高珩来说,他不是要把“人事”与“三才”对立起来,而是要“圣人之言”的“多主人事”与后面的“三才之理、六经之文、诸圣之义”对照起来。或者说,他是侧重于“事”与“理、文、义”的对照,而不是人与天的对照。能够从“事”深入到理、文和义,就能够达到“同而异”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就能够容纳差异,把天下的一切都包容进来。这也就是《易传》用“天下”而不是“天”来概括“冒道”的道理。所以,由“冒道”或者说“异”来概括“人事”,主要指超越眼前的、现实的、习惯了的事,能够把未知、未闻、奇异的事也容纳进来,而不是指既要考虑人与人的关系,也要接受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不论是人与人的关系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都属于人事范畴。
不过,当高珩提出“同而异”的观点时,并没有将其简单化处理。他以一种辩证的眼光,经过一番曲折展开的论述,在论述接近结尾的部分,又提出了“异而同”的立场。所谓:
吾愿读书之士,揽此奇文,须深慧业,眼光如电,墙壁皆通,能知作者之意,并能知圣人或雅言、或罕言、或不语之故,则六经之义,三才之统,诸圣之衡,一一贯之。异而同者,忘其异焉可矣。[2](P2-3)
这种由“同而异”向“异而同”的转换,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原来在高珩看来,“同而异”,并且以“异”来一以贯之,固然可以从局部的、眼前的视野扩大到整体的、开阔的方面,但也容易流于表面,甚至执着于表面的异相而不能自拔,所以就需要有一个由博返约的“异而同”,才能够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而一旦到达这样的境界,就可以如得意妄言般地把“异”忘记了。如果说,“同而异”是从局部发展到整体,从片面发展到整体,追求的是广度,那么“异而同”则是强调从表面到本质,追求的是一种深度。此时所提的“异而同”,近似于佛学家所说的“色而空”或者“用而寂”,即“异”是“色”、是“用”,“同”是“空”、是“寂”。或者,也如理学家所谓的“事异理同”。[3]但由于欧阳健仅仅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理解异,并且认为这种“异”才是高珩序言所肯定的小说价值所在,这样,他就有意无意地回避了高珩序言结尾部分的“忘其异焉可矣”一句,没有注意辨析高珩序言在处理“同”“异”关系时,所具有的一种动态的辩证态度,而干脆把“异而同者,忘其异焉可矣”这一句有意无意间略过了,显示出其在梳理相关文献时的一种片面的、机械的做法。
当然,欧文的论述,不是没有注意到高珩具有的一种全面、灵活的意识。但当其在自己的论述中提出这一看法时,恰恰是建立在误解原文基础上的。这样,他所谓的全面和灵活,不过是无关对象的空洞教条。这一问题我们后文会继续讨论。
二、“解人”“拘墟之士”和“痴人”
当高珩借助引用儒家经典的文意来为《聊斋志异》之“异”正名时,他的辩证意识还表现在,他认为著述的合法地位获得,不仅仅在于著述本身,也在于对待著述的接受态度和接受者的能力修养。由此他提出了理想读者,即“解人”,与“非其人”,即“拘墟之士”的对立。
在他看来,虽然通过对“同而异”的理解,可以为“怪力乱神”的记述内容找到合理、合法的依据,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于读者来说,成为一个“解人”,能够以正确的态度接受这些作品,也是相当重要的。做不到这一点,沦落到“拘墟之士”的话,那么不仅“怪力乱神”的作品他们接受不了,即使让他们接受愿意接受的那些正统的“六经”,也会把书读偏、读歪,好端端的“六经”只会起助长他们恶劣行径的作用,这恐怕也是那些著述的圣人所无法预料的。所谓:
苟非其人,则虽日述孔子之所常言,而皆足以佐慝。如读南子之见,则以为淫辟皆可周旋;泥佛肸之往,则以为叛逆不妨共事;不止《诗》《书》发冢,《周官》资篡已也。[2](P1)
这样,与其斤斤计较著述本身的正统还是非正统,还不如注意读者自身的修养问题。在这里,他提出了与“解人”相对的“拘墟之士”,其所谓的“拘墟”,正是着眼于一种见闻的局限性而言的。而不是如欧阳健那样,把“拘墟之士”理解为只是懂得注意人与人的关系。“解人”除此之外,还能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明白了这里的关键不是在说人与人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就能恍然,高珩恰恰是借助引用有关人事的描写来讽刺处于乡野自然中的人因见闻局限而无法理解所谓“引而伸之,即‘阊阖九天,衣冠万国’之句,深山穷谷中人,亦以为欺我无疑也”。因为其引用的诗句,出自王维的《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描写的基本对象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并不聚焦于欧阳健所谓的人与自然关系。原诗是:
绛帻鸡人抱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
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4](P177)
其中,“九天阊阖”指的是皇宫重重的宫殿之门,而“万国衣冠”则是指前来拜谒的各国使节。其场面的隆重盛大,显然是待在深山野外的人无法明白,也无法想象的,所以就有可能怀疑这一描写的真实性了,而要把人间这样的正与常理解为怪和异了。所以,超越“拘墟之士”的局限而成为“解人”,关键不是超越人与人的关系而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并来考虑,而是要能打破见闻和理解的局限,并且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不论是来自自然还是社会的怪异之相,从而达到一种见怪不怪的境界。
不过,在高珩的序言中,与“解人”相对照的,不仅仅是“拘墟之士”,还有所谓“痴人”。这是在序言结尾部分提到的,即:
异而同者,忘其异焉可矣。不然,痴人每苦情深,入耳便多濡首。一字魂飞,心月之精灵冉冉;三生梦渺,牡丹之亭下依依。檀板动而忽来,桃茢遣而不去,君将为魍魉曹丘生,仆何辞齐谐鲁仲连乎?[2](P2-3)
如果说,“拘墟之士”是对怪异持一种排斥的态度,那么,“痴人”则恰恰相反,是完全沉迷于这种怪异中,如同中魔一样不能自拔。这里就涉及前文所论的,是那种见“异”而不见“同”的,不能见到事之异中含有理之同的本质。也是因为同样有这样的人存在,才需要在提出“同而异”之后,还提出“异而同”的观点。不过,因为作者的基本立场是反驳“拘墟之士”的固执之见,所以对“痴人”的态度用寥寥数语加以调侃外,又以回到其基本的立场为总结,即:“君将为魍魉曹丘生,仆何辞齐谐鲁仲连乎?”就是说,既然蒲松龄当了魍魉的推广者,他就愿意做这一推广激烈的辩护者。这样,通过一种修辞关系,高珩巧妙地把自己置于一个是“解人”然而又高于“解人”的位置。因为即便“解人”确实是高珩所认同的,但毕竟是一类人。至于要能够成为特殊的这一个,形成与蒲松龄对等的特殊位置,就需要提出一个特定的人以便让他自居,而鲁仲连就是属于“解人”却又高于“解人”的一个角色,也是高珩颇为自许的一个角色。
也正是在为蒲松龄辩护而激烈反驳“拘墟之士”的曲折过程中,高珩的一些基本意见得以进一步深化,从而使自己能逐渐超越机械的儒家正统立场。下面结合具体作品来谈论其深化过程。
三、“因果渺茫”的核心意义
高珩在序言中假设了“拘墟之士”的三次疑虑,随后一一加以反驳,其写法犹如传统的答客难。通过这种发难及反驳,使他的主张得以具体而又深入展开,使得读者在这种展开中,不但能领悟关于志怪或者说志异小说的理论特色,而且也有助于理解《聊斋志异》创作的观念以及蒲松龄构思作品的一些创作特色和形象特征。
这其中,因果报应的内容首先受到假设中的“拘墟之士”的质疑,而给出的回答则相对来说最为具体。其内容是:
彼拘墟之士多疑者,其言则未尝不近于正也。一则疑曰:政教自堪治世,因果无乃渺茫乎?曰:是也。然而阴骘上帝,幽有鬼神,亦圣人之言否乎? 彼彭生觌面,申生语巫,武瞾宫中,田蚡枕畔,九幽斧钺,严于王章多矣。 而世人往往多疑者,以报应之或爽,诚有可疑。即如圣门之土,贤隽无多,德行四人,二者夭亡;一厄继母,几乎同于伯奇。天道愦愦,一至此乎!是非远洞三世,不足消释群憾。释迦马麦,袁盎人疮,亦安能知之?故非天道愦愦,人自愦愦故也。[2](P2-3)
我们清楚,因果报应观念与古代小说中有过深刻的互动性影响,多年前笔者就有过初步的讨论。[5]而刘勇强的《论古代小说因果报应观念的艺术化过程与形态》一文则对这方面问题做了更深入思考,并将之概括为三方面的影响,即作为一种宗教观念的影响、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作为与宗教观念和思维方式相关的形象构成的影响。[6]其文章讨论深入和细致,成了当今学术界谈论古代小说与因果观念关系时一篇绕不开的论文。而该论文谈及的这几个方面,在高珩的序言中都约略有所涉及,尽管高珩序言只是短短的一段话,其深度和广度远不能和刘勇强的论文相比。但有意思的是,高珩的序言虽然不是长篇论文,却因为是以假设中的“拘墟之士”的质疑以及自己回答这样的方式展开的,于是,高珩序言中的答客难式对话,在行文表述上,在某个特定方面,稍许有了点刘勇强论文里没有的复杂性。而恰恰是这种复杂性,甚至是理解上的一个陷阱,让欧文的解读产生了失误。
欧文在刚涉及这一问题时,似乎是从辩证的立场加以论述的,他说:
高珩在提倡人人来做“解人”的同时,又不曾将“拘墟之士”的意见一笔抹倒,反映出一种宽容和公正的心态。他承认,他们有些怀疑“未尝不近于正与”。如“政教自堪治世,因果无奈渺茫”,即不应当用因果报应之说来“治世”,应该说是有一番道理的。但另一方面,“阴骘上帝,幽有鬼神”的话,圣人也曾说过,从社会效果讲,“九幽斧钺,严于王章多矣”,确实也是事实。[1](P4)
因为看到高珩有“是也”的回答,就以为他是在部分承认“拘墟之士”的责难,同样也觉得不应当用因果报应来治世了。或者说,这是在承认责难方有道理的前提下,同时也提出了另一方面的理由。像欧文分析时提出的诸如此类的骑墙式的两面肯定,其实并不是高珩回答的本意。也就是说,高珩说的“是也”,只具有一般的客套意义(后面的几处“是也”都可做这样的理解),并不能理解为是在接受责难方的观点。此外,在这一特定的语境中,还有其特殊意味。也就是说,它也只对“拘墟之士”在有关“因果渺茫”这一现象的描述上做出了肯定,但并不因为肯定了“渺茫”这种现象存在,就意味着必然要否认其有治世的功效。其实,在高珩看来,正是因为“拘墟之士”认为的“因果渺茫”在现实社会中无可避免,才需要引入志异小说对于世事人生的更长时段的三生三世的书写,或者深入现实生活无法深入的他人的内心世界。这样就有可能把局限于外在表象的、人的一生一世不能发现报应的前因后果,充分揭示出来,以便传递给世人。所以,在这里,世人无法理解的渺茫,恰恰是需要志异小说来表现因果报应的前提之所在。如果把高珩自己的举例以及《聊斋志异》的相关作品结合起来看,其道理就更为清晰。
比如,他说,孔子的学生贤明的并不算多,属于德行高尚的主要是4人,即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可惜两人早早夭折,一人几乎被继母害死。从世俗的眼光来看,肯定会让人感觉是天道昏暗、不明事理。但细究起来,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人生实在太短暂,所以无法透彻了解三世因缘,心中自然就有疑虑。只有借助高人点破,我们才能知道,像释迦牟尼曾在饥饿中不得不连吃三个月的马草等遭罪,都有前世孽缘。所以,说到底不是天道昏聩而是世人自己糊涂。高珩举出的这些例子,当然都是世人耳熟能详的,而《聊斋志异》的作品中构拟的一些故事,就是在力图突破人生一世的局限,借助于叙说三生因缘故事来获得“政教”的实际效果。这里且举《三生》一篇最为典型的例子。故事叙述一个姓刘的孝廉,能够清楚记得前生之事。当他为缙绅时,德行颇有污点,62岁去世,阎王起初不知底细,还款待他喝茶。因为他觉得这是迷魂汤,所以趁阎王不注意,把茶水泼了。后来,阎王查到他生前作孽记录,勃然大怒,就罚他转世为马,结果被人骑得两肋疼痛难忍,绝食而死。只是因为受罚的期限未满,他又被小鬼押去转世为狗。他看到粪便,知道肮脏,但闻去确有香味,只是克制自己不去舔食。因为无法忍受做狗的日子,他故意咬伤主人,又被主人暴打至死。阎王怒其凶横,又罚他转世为蛇。做了蛇,他发誓不再残害生命,只是吞食果实为生,因为没有生趣,最后在大车过路时,突然从草丛中出来横在路中,被车轮压成两段而死。阎王因其不是由于自己作恶而被杀,所以让他转世为人,这就是刘孝廉了。
在许多志怪小说中,都有关于前世因缘的故事书写,不过这种书写,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真切感觉似乎并不能协调起来。处在现世的人,既无法回忆自己的前世,也难以预知自己的后世。尽管人们会把梦境视为另一世的人生,或者起码是一种暗示,如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就怀疑父亲梦见的僧人就是他的前世,但这毕竟带有很大的猜测成分。所以,在《三生》中,一个细节就变得至关重要,就是在阴间的刘孝廉偷偷把迷魂汤给泼了。这样使得他转世为马、为犬、为蛇时,始终还保持人的清醒意识。作者这样写,当然是出于宣扬因果报应的需要,让人的灵魂和意识寄居于动物时,能够把身为动物时遭受的痛苦一并集聚起来,并使得转世为动物成为人的一种真切的惩罚体验。有学者据此还比较了这篇与《促织》的描写,认为当《促织》写到成名的儿子灵魂出窍寄居于促织体内时,就缺少了一种体验式的描写。[7]也许在《促织》中,是出于小说悬念设计的需要。而就《三生》来说,这一泼洒迷魂汤的设计,既内在于小说情节的需要,因为恰恰是刘孝廉这种耍弄小聪明,使得他转世为动物时有了因保持人的清醒意识才有的难堪的痛苦,这一意识中的痛苦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一种因果报应;但同时,这一设计也是相对于读者而言的,它似乎在告诉读者,恰恰是因为现实中的人在转世时被灌了迷魂汤,所以我们在转世时无法得知自己的前世后世,因果报应问题也就变得“渺茫”起来了。于是,这样的设计,就弥合了小说与现实的断裂,是符合民间有关迷魂汤传说的理解的。
四、“妖邪”“异事”与“幻迹人区”
按照惯例,《三生》故事结尾,也有作者的一段议论“异史氏曰”,而其开头一句特别耐人寻味:
毛角之俦,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然者,王公大人之内,原未必无毛角者在其中也。[2](P74)
这段议论,也可以说部分回答了高珩序言中提到的 “拘墟之士”的质疑,同时为下文高珩的应答做了伏笔。因为设想中“拘墟之士”的“因果渺茫”说被高珩说服了,“拘墟之士”紧接着又提出了新的质疑,所谓:“报应示戒可矣,妖邪不宜黜乎?”其还对小说“驰想天外,幻迹人区”的构思予以了规劝,希望能予以回避。而高珩的回答可说与蒲松龄在《三生》结尾的议论如出一辙:“人世不皆君子,阴曹反皆正人乎?岂夏姬谢世,便侪共姜;荣公撤瑟,可参孤竹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且江河日下,人鬼颇同,不则幽冥之中,反是圣贤道场,日日唐虞三代,有是理乎?” 这种人鬼同处乃至合一的议论,其实具有很强烈的道德乃至更广泛的文化隐喻性。类似的故事,在《聊斋志异》中比比皆是。比如《聂小倩》中的女鬼形象,小倩最初追随宁生到其家时,被宁生之母嫌弃,而小倩为了让宁母忘掉她鬼的身份,为了争取到做人也就是做宁生妻子的权利,她“朝旦朝母,捧匜沃盥,下堂操作,无不曲承母志”,尽了一个女子所能尽的最大努力,终于得到宁母的承认,与宁生喜结良缘。这样一种从鬼到人的转变,不是传统社会出嫁女子具有的普遍经历么?而既然类似的形象具有广泛的寓言性,所以像“拘墟之士”进一步质疑《聊斋志异》在思维方式以及形象构拟上的“驰想天外,幻迹人区”,更是毫无道理了。
仍以《聂小倩》为例,小说写由鬼向人的转变,对形象的构拟特别有意味。作者一方面赋予一个娇丽女子所应有的种种现实特性,另一方面也注意展示她作为一个鬼的幻想特性。将现实与幻想奇妙地糅合起来,不断开拓读者的欣赏视野,恰恰显示了“幻迹人区”组合而成的合理性。写小倩离开宁生家,“从容出门”,是普通人的举止;“涉阶而没”则是鬼的神异性了。“女初来未尝饮食,半年渐啜稀酏”,这是鬼的特性与普通的人性自然衔接。而“女子翩然入,拜伏地下”——人乎?鬼乎?说这是描写人之体态轻盈自然不错,说这是暗示鬼之飘忽也未尝不可。[2](P160-168)
其实,不论是“妖邪”“异事”还是“幻迹人区”,都是受一种因果报应观念制约,也受这种观念驱使,并在《聊斋志异》中把这种观念驱使下的思维方式带入到非常幽深的境界。应该说,高珩的序言,展开到论述“异”的具体合理性,抓住“因果渺茫”这一关键问题讨论,是很有道理的。而“拘墟之士”所谓的“幻迹人区”,意在强调一种非现实性。这种非现实是借助心灵世界的构拟,所谓“驰想天外”,才获得了其合理性的存在。这里,我们再以《聊斋志异》作品中的《促织》为例,来进一步说明。[2](P484-490)
《促织》虽然经常被人提及,但人们较多关注其对底层社会民不聊生状况的抗议,而其由因果报应发展来的构思上的深入,把一种外在的报应转变为一种心理上的内驱力而落实到人间世界,以及一种“幻迹”与“人区”的叠加,却鲜有人提及。
故事大意谓:小说男主人公成名为官府所逼,去寻找供皇帝娱乐的促织。好不容易在“天意”的启发下,找到了名贵的促织青麻头,却被好奇的儿子拍死在掌中。成名之子因恐惧而自杀,成名一家在绝望中无意得到一头不起眼的小促织,却战无不胜,甚至能从雄鸡的大爪下逃脱,叮咬鸡冠而让它败下阵来。在这里,青麻头死于成名之子的手掌中与不起眼的促织落在雄鸡的大爪下,成为全篇两个最扣人心弦的情节高潮。而弱小的促织最终不但能从鸡爪中解脱,甚至让雄鸡大受挫折,其不可思议性充分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但当读者最后明白了促织乃是成名之子的灵魂所化,其“驰想天外”的逻辑力量才能够从神秘的面纱中挣脱出来,并提供了复杂的阐释暗示。
受传统宗教思想浸染的人,会隐约看到其一报还一报的因果关系。促织再小,毕竟是一条生命,所以成名之子拍死它后因恐惧而自杀,可说是一命抵一命。但从人物自身的内驱力看,成名之子的自杀,似乎是对自己莽撞拍死青麻头行为的一种救赎。成名之子不但要以自己化作促织来拯救家庭,同时,也要重新给自己一次机会,让促织能够从另一只手掌中逃脱出来。在促织逃脱鸡爪的一瞬间,当初死于成名之子掌中的青麻头,似乎也逃逸了。这是人对促织的拯救,也是对自己的心理拯救。作者“驰想天外”,显示了对人物心理世界的深刻认识,这种深刻认识,既直接表现在对主人公成名的心理活动描写中,也体现在对成名之子隐含心理的暗示中。[8](P55-59)这样的心理暗示,正是对高珩所谓的“幻迹人区”的形象展示。
五、余论
聂绀弩在许多年前曾撰有《漫谈〈聊斋志异〉艺术性》一文,其中有一节,就是对《聊斋志异》中“因果渺茫”现象、“妖邪”等鬼狐形象以及“驰想天外幻迹人区”的构思予以分析,并把这些概括为作者的“奇想”。他认为,《聊斋志异》有些作品写的是谁也没有经历过的生活,“但一写进作品里去,读者并不感觉它不是日常生活里所有的而不能接受,刚刚相反,而是认为是一种新奇的生活,虽然在现实生活难以碰到或根本不可能有,但那种意境,却是生活中应该有的。这就在无形中提高或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他又认为,作家的创作是有自身的自由度的,特别是在写到鬼神时,不能以人事规律律之,否则就不是在写鬼神妖异了。类似的认识,给人以很大启发。[9](P226-229)
然而奇怪的是,恰恰在欧文中,当他以高珩的序言作为论述的起点,认为序跋体现出的“辩异”“寄托”和“作文”这三大要义,在后世的发展中演易为对“辩异”的舍弃和否定时,他引了聂绀弩的《〈聊斋志异〉关于妇女的解放思想及其矛盾》一文中的话:“这书是有许多鬼神或草木鸟兽虫鱼的精灵,但这些只是形式,是现象。它的内容、实质,却都是人,是人的生活,是把草木鸟兽虫鱼之类变成人,写它们的人的生活,而不是相反,使人变成草木鸟兽虫鱼之类而写它们的生活。”然后他加以总结说,这种见解“充分反映出实用主义的经世思潮的强化和对人与自然关系关怀的淡化与忘却。这种见解看起来似乎是非常‘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但恰恰是所谓反‘迷信’和反‘宿命’的口号,使《聊斋志异》的研究陷入片面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的倒退”。这样的断语,不但说明欧文未能理解聂绀弩这段话的意思,而且拿这样的结论与聂绀弩有关《聊斋志异》的全面论述结合起来看,可以加深我们对欧文自身“片面性”的真正理解。这种自身的片面性,与他有关高珩序言阐释的不全面、不客观是一以贯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