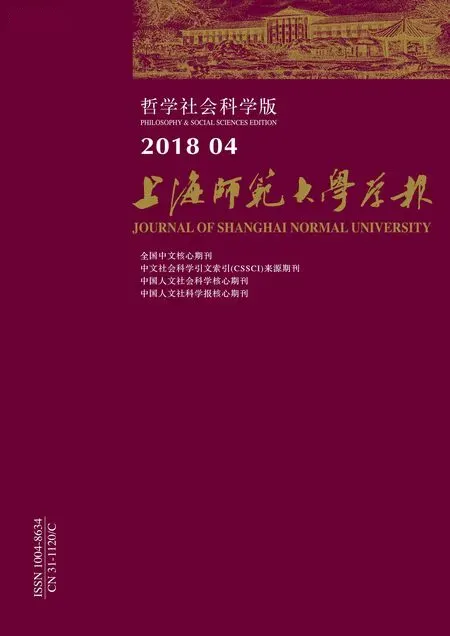玻璃在早期现代建筑中的美学意义
宋凌琦,刘旭光
(1.上海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2.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对纯净和清晰的渴望,对闪耀光亮的渴望,对精确的渴望,对非物质光线的渴望和无尽的生命的渴望,都可以在玻璃中找到。玻璃——这最不显形的,最基本的,最灵活的物质!①
——阿道夫·贝恩(Adolf Behne),1915
在现代建筑中,政治理想、社会愿景需要新的形式来显形,而材料又对形式具有反作用:无论是里格尔所说的作为艺术意志的摩擦系数,还是福西永所说的造成形式变异的变因,都体现着材料对于形式的反作用。回首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建筑历史,没有哪种材料能像玻璃这样具有如此丰富的表述维度和象征性寓意。每一次对玻璃的内在特性的发现、解读和阐释,都伴随着时代意志的转折,对现代性的思考,以及对建筑本质和人类社会命运的深刻理解与深切关怀。因此,本文以玻璃在现代建筑中的应用为对象,诠释通过玻璃这种材料所体现出的现代主义建筑的美学追求。
一、玻璃建筑的社会理想
自19世纪开始,清洁、光滑的玻璃就饱含着一种道德和伦理上健康、卫生的暗喻及训诫;玻璃的透明性更隐喻了一个卢梭式启蒙理性的梦想——一个透明的社会将不再有任何黑暗区域,每一部分都可见而易读。玻璃仿佛是对以上社会理想的一个允诺。
玻璃,这种奇异的物质拥有一种独特的品质——透明。因为透明,玻璃可以任光线穿透,对于人类的理智来说,这种无蔽状态意味着显形,意味着自省,同时也意味着差异和辨认,通过差异和辨认我们的认识得以发轫。在一个有着“眼见为实”“高贵的视觉”的传统里,玻璃的应用对应着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依靠玻璃制造业的发展,牛顿爵士透过棱镜进行的太阳光分光实验发现了光的奥秘;显微镜、望远镜“拓展的不仅仅是人们的视野,而且也拓展了他们的认知”。②正是玻璃所代表的理性、祛蔽的启蒙精神撕开了中世纪的狂热和迷雾,刘易斯芒福德甚至认为,“直到18世纪以前,比冶金技术对人类文明和文化推进作用还要大的就是玻璃制造业的巨大进步”。③
受启蒙理性和科学实证成果的鼓舞和指引,19世纪空想主义先行者圣西门从工业中发现了摧毁封建和神权的钥匙——基于经济节约的效率论和人道主义的改良。在圣西门工业化的社会中,经济生活就是政治学的全部实质。圣西门甚至预言技术的进步、理性的指引不仅可以解决当时面临的社会问题,并且随着“有益的物品”的极大丰富,人类梦寐以求的“黄金时代”也会降临。随着“实业体系的建立……而我们的‘一切通过实业,一切为了实业’这个题词,将是给人们带来幸福的革命的预言,同时也是它的信号”。④
在圣西门主义者⑤的鼓吹下,实业的发展结合了工业的生产和商业的流通。18世纪90年代,随着资本对于城市空间的征服,城市零售空间这一新的建筑形式和场所诞生了。到19世纪中期,铸铁柱、熟铁梁和模数制的玻璃窗一起组成了市区商业中心——市政厅、交易所、拱门街⑥等。随着玻璃工业的成熟,玻璃价格下降,玻璃面积增大,时髦与攀比使得新的商铺和以玻璃为屋顶的拱门街数量激增。通过这些拱门街,光线和商业资本渗透进拥挤、稠密的市中心地带。
作为物品的交易中心,本雅明曾经谈道:“拱门街是豪华工业的新发明。它们是玻璃顶,大理石地面,经过一片片建筑群的通道。它们是本区房主的联合经营的产物。这些通道的两侧,排列着极高雅豪华的商店。灯光(汽灯)从上面照射下来。”⑦当本雅明作为一个犹太裔富商的孩子回忆起20世纪初的柏林时,那拱门街穿透岁月依然充满了诱惑和暗示。徜徉在拱门街内,光线构织出精巧的网格;闪闪发光、轻盈、透明的玻璃显示出工业和技术的竞争性发展;通透而明晰的空间内,丰富的商品的陈设营造出梦幻般的氛围。
随着一段段色彩斑斓的商品凯歌,都市中商品的拜物教出现了。如果说大量的“拱门街”是商品拜物教的街垒,那么世界博览会就是人们膜拜商品的圣殿。1833年,世界上第一座完全以铁架和玻璃建成的建筑物——巴黎植物园温室(Jardin des Plantes)问世了。相较于之前砖石建筑沉闷的体量,圣西门主义者认为,这种铁和玻璃的巨大空间的技术,足以孕育出一种全新的城市空间以疗愈随着工业化出现的现代城市病。到19世纪中叶后,标准铁构件制成的玻璃屋面已经被大西洋两岸的工业城市广泛采用。
在温室建筑的技术成就上,1851年,帕克斯顿主持建造了“水晶宫”——伦敦世界博览会会场。“水晶宫”是工业文明的奇观:“……其内部提供了一个细致优雅的线性网络,没有为我们提供可以借以判断它们离我们眼睛的距离或者它们之真实尺寸的线索……眼睛不用从一头的墙壁移到另一头的墙壁,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扫过一个渐渐融入地平线的没有尽头的远景。我们分辨不清这个高耸的建筑在我们头上有一百还是一千英尺高……因为那里没有光影的跃动使我们的视神经去测量其尺寸……所有的材料都融入了整个气氛当中。”⑧玻璃圣殿内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业汇聚:超过10万件商品来自包括中国、印度等遥远国家。这也是废除了行会制度以来,第一次把消费者和生产者如此紧密而直接地并置在一起。有赖于工业体系和市场体系的联通,商品流动着,在这里凝结出工业和技术的资本果实。
但是,玻璃在现代主义建筑中的应用,本质上仅仅是给出一个水晶一样的谎言。玻璃材料的应用,体现着建筑领域中“预制体系”的到来,而预制体系却是以人的撕裂和劳动的肢解为代价的。
工业体系下,对效率的追求导致了进一步劳动分工的出现,生产被分成若干环节,环环优化,从而降低了对单个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事实上,水晶宫这般的视觉效果很大程度是由于紧张的预算和时间表,使得建筑大量利用了生产线成套预制部件的副产品:564米的长度、约7.3万平方米的无内墙围合、6024根铸铁柱子和1245个精加工铁桁架的制造、运输和装配,在短短的九个月内完成。如此惊人的装配速度如果离开钢铁结构加玻璃的预制体系将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预制体系意味着复杂的创造被简化为机械的重复动作。劳动者的身体成为流水线上的劳动力分配对象。在工厂体系下,劳动的高贵和自由的个体被撕裂了,被分裂开来的并不仅仅是劳动,还有活生生的人。正如拉斯金在1853年的《威尼斯之石》中痛心地提出的,劳动分工把操作者退化为机器,使劳动者丧失了生命、劳动和体验的完整性;异化为生产资料和最终消费者的人被隐匿、撕裂成生命的小残片和碎屑,只能封闭在砖石后的斗室里。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劳动异化现象。本雅明从人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完整的体验出发,在《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中以蒙太奇式的拼贴意象为我们描绘了六段不同的现代巴黎空间。从拱门街、西洋镜、世界博览、巴黎街道、街垒这些公共空间,到市民的内部世界——居室。六个典型图景分别从不同尺度和角度考察了资本主义都市下的商业与道德、艺术与幻觉、政治与理想。其中居室作为市民财产、历史、记忆的空间,收容和暂栖了人的肉体和精神残片。
但无论是困顿还是平庸,其精神状态却是出奇的相似。高度组织化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导致对人的割裂,商品拜物教使生命屈从于非生命。由于生存的需要和感官刺激的加强,人们仿佛不再需要与他人的沟通和情感。每个人都是孤零零的,但同时又紧密地聚集在一起。被颠倒了的生命本能,开始只关心自己卑鄙的安乐,“甚至连被遗弃的女人和流浪汉都在鼓吹一种井井有条的生活”。⑨而水晶宫则从如山的商品和炫目中涌起,也从庞大的聚集和孤独中涌起。这就是机器文明教化出来的野蛮——粗俗的物质主义,一个资本主义鼎盛时代的世界大都市中资本与技术的异化景观。因此,尽管水晶宫的建造忠实于材料,诚实地表现了其结构的原则,并且也合于功能目的,但玻璃这种材料的应用并没有实现人们对它的最初的期待。玻璃让现代建筑成了一个普金(Augustus Pugin)所说的“水晶一样的谎言”。
二、玻璃:材料的“真实”与装饰的“去除”
虽然玻璃似乎仅仅带来了一个谎言,但现代建筑依旧期待从玻璃中获得一种新文化的可能。工业时代,居室成为人的孤独的藏身之地,同时更是人的樊笼;人们用批量制造的工业商品、装饰、痕迹,装点出一个带有温度的、小小的蜗居斗室。
与之对照的却是室外大规模和高速流动的全球性:世界范围的旅行,民主的精神,国际通讯的即时,数字和精确的权威,卫生和舒适的习惯,一切都说明一个新的、现代化的灵魂已经诞生,只是还缺乏一个合适的躯体。没有合适的形式,新的精神只能寄宿于旧世界“虚伪的或者骗取来的经验”中。为了创造和发现新的形式,新的材料必须被引入。而玻璃,以其坚硬、光滑、暴露和解放,成为财产、习惯、伪装和秘密的死敌。因此,新精神寄希望于玻璃的暴露性与解放性能够击碎虚假和模仿,带来新的文化。
首先是玻璃的应用可以摈弃机器导致的材料虚假。过去人们敬畏材料是对于人类劳动的敬畏,对于工艺技术和艺术性的敬畏。而在工厂条件下,对昂贵材料的模仿始于对劳动技艺和工作量的伪造。最坚硬的斑岩和花岗岩都可以像黄油那样切割,像蜡那样抛光,……生橡胶和马来橡胶可以经过高温硫黄处理后做出以假乱真的木、金或石雕仿制品,并大大地超越了被仿制的材料的自然质地。⑩而对材料价格不诚实的吹捧,使得材料偏离了自身的应有价值。对真实的追求体现在材料上,则首先是追求材料自身的形式语言的真实。1898年,正是在关系与真实的立场上,路斯发表了他的《饰面原则》(“Das Prinzip der Bekleidung”)。他认为:“艺术家,建筑师,首先需要感知他想要实现的效果……这些效果由材料和空间形态产生。”同时,“每种材料都有其自身的形式语言,没有什么材料会声称其具有其他材料的形式。因为形式由适应性和材料的生产方式所决定。它们伴随并通过材料显现”。
关于材料如何引入形式而与新的情感得以结合,意大利未来主义者翁贝托·波丘尼(Umberto Boccioni )在1912年的《未来派雕塑的技术宣言》里声称:“必须从欲创造之物的核心开始去发现新的形式,这形式无形地、数学地将其与可见的塑性无限以及内部塑性的无限连接起来。因此,新的塑性将转译为新的材料语言——石膏、青铜、玻璃、木材或任何其他材料以连接和叠加物体的大气平面方式而呈现。我曾将之称为‘物质的超验’(physical transcendentalism,原文为:transcendentalismofisico,首次提及是在1911年5月,波丘尼在罗马艺术协会的名为‘未来主义绘画’的讲座上)可以塑性地带出对同情和神秘的亲和力,这些情感将产生出物体平面之间相互的和形式上的影响。”同时,他还进一步呼吁,雕塑摈弃大理石和青铜等一些贵重材料,而转向各杂类的介质:“玻璃或赛璐珞的透明平面、金属条、金属丝、室内外的电灯等都能够表示一个新现实的平面、倾向、基调和半基调。”
先锋主义者之所以钟情于玻璃这种介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于材料真实基础上的、对文化和艺术的模仿的清洗。19世纪末,文化模仿已经统治了整个建筑行业,装饰开始泛滥。路斯就曾以尖刻的语气模仿了一位自负的承包商:“噢,我亲爱的建筑师先生,我再多花5基尔德,你就不能在建筑立面上多增加点艺术吗?”然后建筑师就按照要求,根据承包商出钱的多少,在立面上添加了相应价值的艺术,而且有时候还会多弄点。这种赘生的装饰,路斯从经济、道德的考量,将其直接贬斥为“罪恶”。而“玻璃这种物质不仅仅坚硬、光滑得任何事物都不能附着其上,而且冰凉、冷静,因为玻璃制品缺乏‘氛围’”。当时建筑装饰行业中盛行的灰泥等材料宜于进行装饰塑造。相对于灰泥在艺术模仿中的便利特性,玻璃的光滑和纯粹成为去除装饰的第一步。在玻璃建造的房间里,人很难留下痕迹。而恰恰是玻璃这种“灵晕”的缺失,很容易达到一种“经验的贫乏”——这是本雅明称之为如“哭啼着躺在时代的肮脏尿布上”“赤裸裸的”新生婴儿的 “经验的贫乏”——一种褒义上的“无教养”状态试图从以往的经验中解放出来,意味着对虚饰的拒绝,意味着对建筑中的历史主义的清洗。舍尔巴特曾说过:“尽管新的社会福利组织、医院、发明或技术革新——所有这些绝不会带来一种新的文化,然而玻璃建筑一定会……当欧洲人担心玻璃建筑兴许会变得不大舒服的时候,他们是对的。它肯定会如此。不过这却不是玻璃建筑的起码优点,因为,首先必须把欧洲人从他们的舒适感中硬拉出来。”
“无教养者”渴望着一种能够纯洁明确表现他们的外在以及内在的贫乏环境,以便从中产生出真正的事物;他们是新时代的设计者,渴望“一张干净的绘图桌”。1892年沙利文在《建筑的装饰》(“Ornament in Architecture”)中谈到,由于表面上的装饰打破了功能、形式、材料以及表现之间的有机联系,因此他建议颁布一个临时禁令,禁止一切建筑的装饰。这是一种通过经验的贫乏而达到的真实。由于贫乏从头开始,由于贫乏绝不瞻前顾后。对时代完全不抱幻想,同时又毫无保留地认同这一时代。
这是一种 “白板”状态。事实上,对玻璃的呼吁也是和实验心理学上那块著名的“白板”息息相关的。受霍布斯和洛克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环境与心理交互影响的理论。该理论认为通过改变外界环境予感官以刺激,从而可以影响人的精神面貌;反之,环境的改变也可以通过对人的精神面貌的改变进而塑造文化。因此,如果要把文化提升到新的水平,塑造新人类,就必须改变住所的封闭性。正如舍尔巴特在《玻璃建筑》(“Glass Architectur”)中的开篇明义:“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封闭的房间里,封闭的房间造就了我们文化生长的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文化正是我们建筑的产物。如果我们希望将文化提升到新的水平,就不得不改变我们的建筑。”舍尔巴特由此引入了玻璃这种材料。“为此我们只能引进玻璃建筑,使日月星辰的光不再仅仅可以穿过几扇可怜的窗户,而是能够穿过每堵可能的墙——这墙几乎全由玻璃建造的,是彩色的玻璃。由此,我们创造新的环境,这环境也必将为我们带来一个新的文化。”
三、林中路——最初的分化
沃林格(Wilhelm Worringer)在《抽象与移情》(1908)中将晶体视为“从无生命的物质中发源的规则律令”,并将之与其形式意志和抽象冲动联系在一起,赋予了在建筑中将不可见的时代内在精神实体化的可能性。进入20世纪,伴随着早期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分化、演变以及之间的相互影响,玻璃这一现代建筑材料语言的应用、道德伦理及形式美感的思考也折射和呈现出现代主义思潮多彩纷呈的面貌。以下即以玻璃的应用进行考察,探究为何玻璃从一种包含道德伦理的材料发展成为纯粹的形式因素,并进一步揭示一战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潮背后的深层思想变革。
首先,对20世纪初的表现主义建筑倾向来说,玻璃的形式意志离不开当时的乌托邦思潮。无论是对千年王国、社会主义还是未来人类,玻璃承载了对于科技、社会、灵魂的思考——作为信念的传达和召唤,给予心灵的净化和提升。历史上,柏拉图以及新柏拉图主义都提到了晶体神秘的彩色光线和虚幻的非物质性,并认为晶体可以与灵魂连接。由于和晶体的内在相似,玻璃也分得了晶体的能力。哥特教堂内洋溢的彩色光线和虚幻效果就是“迟钝的心灵可以通过物质上升到真理”的实证。
借助于色彩和玻璃的结合,1914年布鲁诺·塔特(Bruno Taut)设计了德意志制造联盟(Deutscher Werkbund)科隆展会上的“玻璃宫”(Glashaus)。作为德国玻璃行业协会的展厅,“玻璃宫”的结构依赖于新的玻璃工艺:光通过彩色的玻璃棱柱形穹顶和墙体照亮室内,照亮玻璃踩踏金属楼梯和玻璃马赛克的彩色墙壁。但事实上,“玻璃宫”又是塔特与保罗·舍尔巴特合作完成的,是舍尔巴特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和未来神秘主义的宇宙观理念的实体化。“玻璃宫”上题写着一些舍尔巴特的语录:“彩色玻璃消除敌意”“光需要晶体”……彰显出这是一座奉献给光的宫殿,以呼唤灵魂为目的。也因此,玻璃宫的精神性远远大于其实用性,正如塔特自己所言:“玻璃馆除了表达美以外一无所求。”
1915年舍尔巴特去世,但他对当时的表现主义圈子影响是深远的。甚至在1919到1921年间,当塔特和其他表现主义建筑师之间的联系转入地下,以“玻璃链”(Crystal Chain)的信件形式互相联系时,舍尔巴特还是他们精神上的“玻璃教父”(Glaspapa)。受其影响,与塔特交往密切的格罗皮乌斯也将包豪斯的初创框架搭建在一座社会主义式大教堂的理想之上。在他的设想中,这一隐喻性的未来大教堂将成为对科技文明和社会结构的反思:
让我们来创办一个新型的手工艺人行会,取消工匠与艺术家的等级差异,再也不要用它树起妄自尊大的藩篱!让我们一同期待、构思并且创造出未来的新建筑,用它把一切——建筑与雕塑与绘画——都组合在一个单一的形式里,有朝一日,它将会从百万工人的手中冉冉地升上天堂,水晶般清澈地象征着未来的新信念。
在表现主义者的建筑美学中,是“信念”,而非“功能”,成为建筑的第一诉求,玻璃与普罗提诺(Plotinus)主义的象征美学结合在了一起。塔特在其文章《空中楼阁》(“Haus des Himmels”)中的言论颇能表明当时的思潮:一座房屋除了美而外,将不再有他物;……参观者将被建筑的趣味所充盈,将他的灵魂中所有人类的东西腾空,让灵魂成为神的容器。
另外一种带有表现主义性质的倾向显得更为理性和中立。以密斯(Mies van der Rohe)为代表,将玻璃的道德含义和经济意义搁置,通过对现代城市生活存在状态的描写——而非信念的感召,来获得自身的形式呈现。
1914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正是在这年夏天的德意志制造联盟科隆展上,德意志制造联盟内部路线上规范形式(Typisierung)和艺术意志(Kunstwollen)之间的分歧爆发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分歧不仅是经济和艺术之间的矛盾,也是个体丰富性和社会同一性之间的冲突。都市是个体的极大集聚,其高密度自然意味着两大课题:城市空间上如何处理疏散和聚集;社会心理上如何处理独立的个体与同一的社会之间的矛盾。1903年,新康德主义者齐美尔在《都市与城市生活》一文中,通过对小城镇与都市居民心理、行为差异的对比,总结出现代生活最深刻的问题来自于,个体为了保护其生命存在的自治和独立,从而与强大的社会关系压力、历史遗产、外部文明、生命技术等进行的抗争。因此,无论是城市公共事务对民主的暗喻,还是城市生活对效率的无形而必然的要求,反映在都市建筑上即是公共建筑对“匿名性”和“同一性”的追求。如何解决都市中个体和超个体之间的关系?对此,密斯的态度是中立或者暧昧的。
他认为新时代是一个事实,它存在,不论我们承认与否。它纯粹是种依据,本身并无价值内容。只有一点是决定性的:我们在环境面前确立自己的方式。因此,本着务实的精神,密斯倾向于用表皮的中性在均一性的单调里找到个体表达的丰富,在都市的匿名中找到自己。
密斯早期的职业生涯与表现主义圈子联系紧密,其玻璃运用也显然可以看出舍尔巴特的影响。但密斯作为技艺高超的石匠的儿子,一方面讲究构造的精确性,同时又寻求着玻璃的动感和虚幻。他的弗里德里克大街摩天大楼竞赛方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21年弗里德里克大街竞赛基地是一个三角地块,正对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西侧紧邻施普雷河,为柏林的门户。在144份作品中,密斯的作品也许是最轻盈和简约的,密斯称其为“蜂巢”(Wabe)。其建筑高约80米,平面为对称的三角形平面,仿若三瓣的雪花晶体;交通核位于建筑中心,通体为玻璃墙体。但密斯在这里寻求的玻璃表现性不是通透或净化,而是把玻璃看作一种复杂的反射面、一种“闪亮”的“漂浮”肌理。它纯粹是一种静中的动、一种反射的虚幻。巨大的玻璃墙面映射出周围的城市环境,同时自身又在阳光下不断发生变化。密斯自己认为:
我采用了在我看来最适合于建筑物所在的三角形场址的棱柱体。我使玻璃墙各自形成一个小的角度,以避免一大片玻璃面的单调感。我在实际的玻璃模型试验过程中发现,重要的是反射光的表演,而不是一般建筑物中的光亮与阴暗面的交替。
因此,密斯方案的平面轮廓并非由功能产生,而是根据三项因素确定:足够的室内光线;从街上看过来的建筑体量;以及反射光的表演。可以看出玻璃和建筑的道德意义被搁置,仅通过三项原则分别回应了室内空间质量、城市界面以及表皮自身的表现。
1922年,在另外一个摩天大楼竞赛中,密斯同样提出了一个玻璃方案。这次的平面毫无锐角和直线,是一个有机的形态,宛如鹦鹉螺。其30层的大楼完全由玻璃构成,尽管只是模型,已足以使人预见到人们在走向这样一栋大厦时,其边缘隐没和出现、反射和被反射时玻璃丝绸般的质感和不断改变的影像的虚幻。这虚幻的轻盈以及一系列反射的反射和反射中的移位、扭曲、变形,仿佛是日后德勒兹“游牧”(nomad)的先声,预言了某种城市生活状态的来临。模棱两可的立场,反射而不是通透,这种建筑于构造精确性上的玻璃表现具有一种模糊的超道德美感,成为一种单调城市生活中视觉心理的补偿。
而一种更为理性主义的倾向发展了荷兰人实证、实用的精神。其出于现代建造技术内在的经济性和社会伦理性的考虑,着重于玻璃的功能性,进而发展出一套简化、清晰、紧凑、不带一丝累赘的玻璃审美——将建筑体量分解为空间和表皮,并且这表皮应当是一个“尽可能收敛的、平静的表面”。
玻璃对体量的消解离不开19世纪中叶戈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 )的面饰理论。森佩尔认为:建筑空间由悬挂的饰面围合而成;结构作为一种不可见的附属支撑体系,只是用来固定饰面肌理。饰面围合与结构的剥离,将建筑师从体量中解放出来。表皮与空间成为建筑探讨的重要主题。受此启发,不同的推动力影响着现代建筑师寻找和生成自己的建筑语言。也因此,从这里发端了一种反体量、反纪念性的建筑空间观。
正如ABC集团的著名论断“建筑×重量=纪念性”的逆向推演:独立的玻璃墙表皮摈弃了实体墙,由于玻璃的透明性,外墙仿佛消失了。玻璃的通透否定了古典主义建筑传统关于比例、光影和体量处理的知识,使得千百年来追求体量和光影体积的建筑设计方法突然失效了。建筑转而寻求由平面的相互渗透来达到物体和环境的完全融合。而另一方面,在功能主义者的眼中,玻璃完美的通透性,使玻璃不再具有视觉上的重要性,对采光和透光度的深入研究使得玻璃成为视觉上消除外部与内部之间界限的工具。如同结晶化的一层纤薄空气,仅仅起到隔绝天气变化和噪音的作用。
在功能和反体量性的基础上,玻璃的透明特质与时间维度的发现开放了现代的视觉——不同空间位置的同时感知。例如,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条理清楚、秩序井然的绘画和建筑就彰显了其早期“清晰性、客观性”的纯粹主义主旨,预示了一个以清晰和透明为隐喻的新的空间创建秩序。1909年贝伦斯(Peter Behrens)的透平机车间还只是在钢结构骨架上安装了宽阔的玻璃嵌板,石头拐角处的处理仍残留体量感和稳定感。到1911年,格罗皮乌斯设计的法古斯工厂(Fagus Factory)在体量感的削弱上更进一步——整个立面都以玻璃为主,转角处不用支撑。不仅封闭的室内被打开了,甚至连室内外都已经模糊了。光线和空气自由地穿透,产生一种简单质朴、高度精确的美感。
玻璃的透明性带来的内部空间深度感成为玻璃的另一个重要性质。亚瑟·科恩(Arthur Korn)在《现代建筑中的玻璃》一书序言中将玻璃的透明性作为区别于实体墙和哥特彩色玻璃的最大特征,同时给出了现代主义建筑关于玻璃的经典定义:它在而不在。
然而,历史证明,每种经典概念清晰之日,也是固化之时。尤其在一战后,住房成为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伴随着建筑为“人类最低生活需求”而做的辩论,国际式风格大行其道,玻璃的表现性被剥夺。之后,人们开始对玻璃的透明性进行理论反思。1941年凯普斯的《视觉语言》出版,对“透明性”概念进行了明确定义。而1952年基迪恩在ArtNews杂志发表《透明性:原初与现代》(“Transparency:Primitive and Modern”)一文,解释了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经过柯林·罗和斯拉茨基的推动,透明性——这一曾充满社会理想和道德批判意味的概念,于20世纪60年代变为现代主义单纯的空间构成手法,从而完成了玻璃这一材料美与善的分离——它以其透明性带给现代建筑别样的美感,但它最初许诺的“善”却被遗忘了。
四、结语
材料,仅仅与造价和建构有关吗?还是它应该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曾经善与美在人们的观念中是不可分离的,柏拉图在《菲利布斯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我们可以借由三者捕捉到善,这三者分别是美、匀称与真实。可以认为,三者的结合就是这混合物(善)的唯一原因;也可以认为三者的注入使得这混合物成为善。”
而我们依靠材料的伦理价值判断来获得审美的解放,伴随着价值判断与形式语言的分离,玻璃“经验的贫乏”会不会最终成为视觉盛宴后意义的荒漠?布洛赫指出现代建筑的“贫乏”导致生活的瓦解,因此拒绝相信现代建筑为自由和解放带来希望。或者本雅明自己对于“经验的贫乏”也是矛盾的?不然为何他忧心忡忡地问道:如果没有经验使我们与之相联系,那么所有这些知识财富又有什么价值呢?然而,价值问题又是决定性的。对材料的价值评估中,仅仅考虑其物理属性以及视觉效果将是肤浅的,只有情感认同以及意义赋予被带入后,材料的价值才是完整的。正如密斯所言:我们必须建立新的价值,确定最终目标,这样我们才能制定标准。对于任何时代——包括新时代——正确而重要的是,给精神以存在的机会。
注释:
①Rosemarie Haag Bletter,“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Glass Dream-Expressionist Architectureand the History of the Crystal Metaphor”,TheJournaloftheSocietyofArchitecturalHistorians, Vol. 40, No. 1,20-43: p. 34 (March 1981). See also Regina Prange,DasKristallinealsKunstsymbol:BrunoTautundPaulKlee:zurReflexiondesAbstrakteninKunstundKunsttheoriederModerne(Hildesheim: Georg Olms, 1991).
②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李伟格、石光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页。
③同上,第124页。
④克劳德·昂利,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徐仲年、徐基恩等译,董果良校,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95页。
⑤法国的圣西门主义者大部分来自巴黎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和专业治国论者,强调高速和有效率的交通、通讯联络系统的重要性。
⑥购物长廊。
⑦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78页。
⑧转引自巴里·伯格多尔:《1750—1890年的欧洲建筑》,周玉鹏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0页。
⑨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第167页。
⑩戈特弗里德·森佩尔 :《科学、工业与艺术》(1851年版),转引自肯尼斯·弗兰姆普敦:《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张钦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