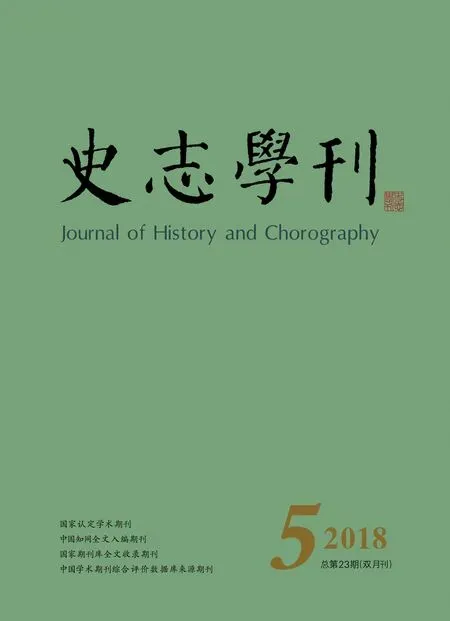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
郭荣臻 郭昊晟
(1.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2.河南大学法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古城寨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曲梁乡大樊庄村古城寨村民组,是新密地区史前时期的一处重要遗址,也是目前所知新密历史上最早的城邑。该遗址于1988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并于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继考古调查、发现、发掘以来,学界对该遗址尤其是龙山时代晚期王湾三期文化时期的城邑展开研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近年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又对该城址开展新一轮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对该遗址相关考古发现、学术研究情况进行综合梳理,以期对更加深入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古城寨遗址的考古发现
199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究会、新密市文物保管所等单位调查洧水流域史前遗址时,对“郐国故城”(古城寨遗址旧称)的城墙给予较大关注,在该城址及其周边展开大范围的考古钻探和调查,并对南城墙局部墙基进行试掘解剖,确定城的年代属于龙山时代[1]蔡全法,马俊才,郭木森.河南省新密市发现龙山时代重要城址.中原文物,2000,(5).。1998—200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究会等单位对遗址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发现遗址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堆积为主,揭露出王湾三期文化时期的城墙、城壕、城内夯土建筑基址、廊庑基址、灰坑、奠基坑、墓葬等遗迹,各种材质的生产、生活用具等遗物。此外,也见有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战国、汉代等多时期的遗存[1]蔡全法,马俊才,郭木森.新密市古城寨龙山城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0.文物出版社,2001.(P190-192)[2]蔡全法,马俊才.新密市古城寨龙山城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1.文物出版社,2002.(P193-194)。
城墙、城壕、城内夯土台基、廊庑建筑等是这座龙山时代城邑最重要的发现。城址位于整个遗址的中部,平面呈矩形。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460米,面积逾17万平方米。西墙被溱水冲毁,仅存北、东、南三面城墙。城墙由地下墙基、地上墙体组成,系夯土版筑而成。城壕在原报告中称“护城河”,北、东、南三面皆存,引溱水、无名河水入其内,形成城墙外的另一道防线。夯土建筑基址编号为F1,可能为城内的宫殿建筑,南北长约28.5米、东西宽约13.5米,面积约383.4平方米,成排柱洞将其分隔为7间房屋。廊庑基址编号F4,围绕夯土建筑基址而建,是宫殿建筑外部的组成部分[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究会.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2).。
201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重新进行考古调查、钻探与发掘,取得一些新的成果与认识[4]张小虎.2016年新密古城寨遗址考古新发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17年度考古工作汇报与交流会发言.河南郑州,2018.。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公布,学界对该遗址的认识将更加清晰。
二、学界对古城寨遗址的研究
21世纪初,这座中原地区龙山时代城邑一经报道,即引起国内史学界(文献史学界、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多年来,考古学者、文献史学者对其展开较为充分的讨论,主要涉及城的族属、相关遗迹性质、城垣建筑技术、器物、聚落形态、社会复杂化进程、生业模式、环境考古等方面。
(一)城的族属
城的族属是古城寨遗址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在考古发掘之前,学界一般将古城寨视作西周时期的郐国都城[5]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郑州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郑州市志·文物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在试掘以后,学界持此见的学者渐少。许顺湛先生以史学问题入手,结合诸多史料考证了《五帝本纪》中“黄帝居轩辕之丘”的地望问题,认为轩辕丘在今新郑、新密,两地仰韶时代遗址以古城寨为首,龙山时代遗址以新砦为首。古城寨城址是证明轩辕丘地望的有力证据[6]许顺湛.黄帝居轩辕丘考.寻根,1999,(3).。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与发掘简报等材料的刊布,越来越多的学者就这座史前城邑的性质发表观点。曹桂岑先生撰文探讨古城寨龙山古城的始建年代,结合相关史料,认为古城寨的地望与黄帝之都的记载相符,该城址即黄帝的轩辕丘所在[7]曹桂岑.新密市古城寨龙山古城始建年代与黄帝轩辕丘的探讨.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二十一辑).三秦出版社,2007.(P98-107)。蔡全法先生则根据考古发现对城的性质作出两种推测:一则史前的鬼氏族南下至今新密,为安全防范的需要,在古城寨遗址修筑城垣;二则中原的华夏部落俘获鬼部落的战俘,命他们修筑城垣。蔡先生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8]蔡全法.一夜“鬼”修龙山城: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遗址.文明,2003,(1).蔡全法.溱洧交流处,黄帝轩辕丘.大河报,2003-11-5,(第29版).。马世之先生结合古代史料与相关考古发现,否认古城寨为“禹都阳城”的可能,提出其与祝融之墟的地望相合,并认为该城到西周时继续作为郐国都城使用[9]马世之,新密古城寨城址与祝融之墟问题探索.中原文物,2002,(6).。
继古城寨龙山城发现后,另一座龙山晚期兴建的新砦城也被揭露出来,学界普遍将后者视为传说中的夏启都城,周书灿先生审慎地提出质疑,认为长期以来学界对《穆天子传》中所载的“启居黄台之丘”的考证阐释歧见纷出,结合《左传》《国语》《世本》《汉书》《后汉书》《帝王世纪》《水经注》《太平御览》等一系列文献考证了夏启活动的地域范围,提出“黄台之丘”在禹州的观点,与新密新砦、古城寨城址无关[1]周书灿.《穆天子传》”启居黄台之丘”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2).。排除了古城寨与夏启所居的关系后,周先生又针对学界流行的古城寨为黄帝轩辕丘、祝融之墟、鬼方等观点,引证《左传》《国语》等一系列史料梳理了祝融之墟的地理问题,根据王玉哲先生考证的鬼方活动区域否定了鬼方与古城寨的关联,进一步结合相关史料,分析了属于黄帝集团的大隗氏在此筑城居住的可能,并论及黄帝与祝融两大集团相互通婚、逐渐融合的可能[2]周书灿.大隗氏与新密古城寨龙山古城.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5,(4).周书灿.新密市古城寨龙山古城的族属及相关地理问题.中原文物,2006,(1).。
综上,就城的性质、族属而言,学者们先后提出了不同的认识。研究路径上基本是根据考古发现情况,结合一系列先秦及后世史料,考证史事,再将考古发现与文献史料记载相结合。何以对同一处遗址,会有不尽一致甚至殊异的认识,是在史前史构建、史前考古与文献史料相结合中需要引起注意与思考的。
(二)相关遗迹性质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宗庙、宫殿的有无长期以来被作为都邑判断的标准。一般认为,史前有垣、壕的聚落未必皆为城市,有宫庙类建筑者则可别论。古城寨的夯土台基、廊庑等建筑的性质作为判断遗址性质的重要依据受到学界的重视,前已提及,发掘者对这些建筑作过解读。近年,杜金鹏先生进行专文探讨,分类剖析夯土台基F1及其附属建筑F4的柱洞、柱础、磉墩、基槽等遗迹,对这两类建筑进行了复原,认为二者仅是建筑群中的一处院落,F1为无堂室分隔的大型主殿,可能是城的统治者施政场所与原始宫殿,F4为对FI起到屏蔽作用的廊庑[3]杜金鹏.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大型建筑基址研究.华夏考古,2010,(1).。就已有的研究来看,学界普遍认同F1、F4的宫殿、廊庑性质。
(三)城建方式
长期以来,筑城技术是古代城址研究中的热点问题。马俊才先生前后两次发文,就古城寨龙山城的城建技术展开讨论,认为该城的城防系统由城墙、城门、护城河三部分组成;并论及墙基的处理方法、城墙主体的分层分段夯土版筑等方法[4]马俊才.四千年古城风尘抖落现真容——河南新密古城寨龙山古城发掘记.文物世界,2000,(6).马俊才.新密古城寨龙山城筑城技术的初步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编.中原文物考古研究.大象出版社,2003.。张玉石先生认为,古城寨城垣版筑技术较郑州西山有较大进步[5]张玉石.中国古代版筑技术研究.中原文物,2004,(2).。曹桂岑先生亦论及该城城墙建筑中的基础槽、坐底夯、版块叠筑等现象,提出改成城墙存在始建、扩建、维修三个时期[6]曹桂岑.河南早期古城建筑考古.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编.文物建筑(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7.(P174-187)。郭荣臻在对史前筑城技术的研究中也着力探讨了古城寨的城建方式,认为该城存在基槽式城墙与版筑技术孑遗,系史前筑城技术流派“中原模式”下“河洛亚模式”的重要组成与代表性城址[7]郭荣臻.简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城垣建筑技术.史志学刊,2017,(4).郭荣臻.河洛与海岱地区史前筑城技术的考古学观察.”唐嘉弘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暨中国古代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国许昌,2017.。就城垣的建筑方式而言,学界几无歧见,相关论者一致认为该城建筑技术高,在早期城市建筑史中占有较为重要地位。
(四)器物研究
关于古城寨器物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考古类型学和器物制作方法两个方面。发掘者根据该遗址陶器形态,将古城寨龙山文化分为四期五段,第一期属于龙山时代前期,与庙底沟二期器物近似,后三期属于龙山时代后期的王湾三期文化[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究会.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2).。鲁晓珂等运用化学分析等科技手段,分析古城寨遗址部分仰韶至龙山时期的陶器,得出三点认识:(1)陶器原料为易熔黏土;(2)部分器物轮制而成,部分器物上的红彩、黑彩系铁、锰元素成色使然;(3)陶器烧成温度多在850℃—1000℃,陶胎吸水率、气孔率较高[2]鲁晓珂,李伟东,王海圣等.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遗址陶器的研究.”2009年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中国北京,2010.(P40-46)。由于简报公布材料有限,以器物为本位的传统考古研究所占权重有限。
(五)聚落考古与社会复杂化
城邑是经济发展、社会分化、社会变革的产物,有学者就古城寨遗址的文明现象、聚落形态等进行过讨论。蔡全法先生针对城址、城墙、城内相关建筑、施釉陶、石器、陶器、卜骨、刻画符号、熔铜炉块等现象,论及该城的政治、经济生活状况、土木建筑技术、意识形态等,认为该城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提供重要依据[3]蔡全法.古城寨龙山城址与中原文明的形成.中原文物,2002,(6).。赵春青先生认为龙山时代已出现主从聚落群的分布格局,古城寨龙山城是城市与乡村分野的重要证据,在聚落小群中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承担着保卫主体聚落群的职责[4]赵春青.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P161-163)。高江涛先生根据学界早年调查材料,认为古城寨及其周边分布的12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构成古城寨组聚落,或谓古城寨聚落群[5]高江涛.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P228-231)。王震中先生进一步认为新砦、洪山庙晚于古城寨,不应作为古城寨聚落群的组成;根据古城寨遗址的社会生产状况、经济面貌、社会分层、复杂化程度等,提出古城寨龙山城邑是早期国家邦国都城的认识[6]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城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P334-336)。李龙对新砦城址从微观、宏观两个维度的聚落形态分析,提出有别于其他学者的见解,认为新砦城址是同时期聚落中的最高等级,古城寨是聚落群中的次中心,可能是该区域的军事城堡或战争指挥中心[7]李龙.新砦城址的聚落性质探析.中州学刊,2013,(6).。虽然学界在论及史前城市、文明起源时以此城的考古发现作为证据[8]学界关于史前城址的研究论著极多,涉及古城寨龙山城的亦为数不少。囿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列举。,但由于所在地的区域系统调查力度有限,宏观聚落形态研究中对该城地位、作用等的认识还有待更多证据支持。
(六)生业模式
生业考古是考古学中的重要研究领域。所谓生业经济,包括以农业、养殖业为代表的生产性经济和以狩猎、采集、捕捞等为代表的攫取性经济[6](P300)。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等是生业考古研究的重要方法。古城寨遗址进行过系统的植物考古研究,据陈微微等分析,龙山、二里头、二里岗、殷墟4个时期出土农作物比重高于非农作物。龙山文化时期,存在粟、黍、藜三种作物,以粟为主,黍次之;二里头文化时期,增加小麦,农作物仍是以粟类为主;二里岗文化时期、殷墟文化时期大致承前,惟小麦麦、藜的比重有提升[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周边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时,采集一批仰韶文化时期遗址的土壤样品。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张居中先生团队研究,古城寨遗址仰韶时代样品中出土有粟及禾本科的野生植物,龙山时代样品中出土有粟、稻及麦瓶草属的野生植物[8](P49-50)。总的来看,该遗址植物考古数据反映以种植业为主的生业模式,惟不同时期的作物组合、构成存在一定差异。此外,该遗址出土有狗、猪、黄牛、绵羊等家畜,熊、梅花鹿、麋鹿等野生动物,成堆成片的田螺壳、零星的蚌类等水生动物[9]栾丰实主编.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郭荣臻在对河南新密史前先民食物结构的研究中,对古城寨遗址的既有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梳理,认为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地处中原腹地的新密地区已经融入史前食物全球化、青铜时代全球化的浪潮之中[1]陈微微.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陈微微,张居中,蔡全法.河南新密古城寨城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华夏考古,2012,(1).。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该遗址不同时期先民的生业模式和食物结构。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样遗迹有限,关于炭化植物遗存比重的认识还不能坐实。此外,由于发掘年代较早,如今常用的微体植物遗存考古方法淀粉粒、植硅体等,人与动物骨骼稳定碳氮同位素等研究手段尚未使用。
(七)环境考古
在上述研究以外,第四纪环境学界对河南省新密市及其临近的溱水、双洎河等流域开展多次环境考古工作。张震宇等对双洎河流域的地质、地貌及32处考古学文化遗址进行野外调查,认为古城寨属于分布在受水流作用痕迹明显的马兰黄土台地遗址[2]贾世杰.郑州商城炭化植物遗存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许俊杰等对新密市溱水流域进行野外考察,分析相关地层剖面,认为古城寨遗址位于溱水下游东岸的二级阶地上,西靠溱水,东望溱水、黄水两条河流之间的平缓黄土梁[3]蔡全法.双洎河流域史前农业及人类膳食结构之探索.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8,(5).。这些研究多是广域范围内的调查取样分析,就古城寨遗址本身的环境考古个案研究亟待展开。
三、相关思考
总的来看,近20年来,学界对新密古城寨龙山时代城址展开了较为详实、深入的研究,多数研究者将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相结合,在既有的文化面貌、性质族属、筑城技术等基础上,又开创环境、生业、社会、聚落等方面的研究领域,从中提取大量的古代社会信息,获得较多的研究成果与阶段性认识。但需要指出的是,囿于种种原因,目前对整个遗址的研究尚未能充分展开,在个别问题认识上,短期之内也难达成共识。
1.就田野考古工作和发掘材料公布程度来看,发掘多年来,仅有龙山时代城址的材料得到较大程度披露。学界对该遗址其他几个时期文化面貌、聚落布局、社会经济状况等诸多方面的认识还很有限。随着新的考古工作的开展与发掘资料的逐步公开,该遗址及其相关的社会历史状况将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2.就多学科合作研究的力度来看,由于发掘时还处在20世纪末,为数不少的新方法尚未在考古发掘中得以推广、运用。以生业考古为例,植物考古方面,虽然采集了部分样品进行浮选工作,但采样数量有限,微体植物遗存层面的植硅体、淀粉粒、孢粉等方面的研究暂付阙如;动物考古方面,系统的骨骼鉴定、统计分析结果并未公布;人与动物骨骼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方面的工作亦未展开,在今后的发掘研究中,若能有针对性地开展这些工作,有利于对先民生业模式与食物结构的深入认知。又如环境考古方面,就单个遗址的环境考古工作尚未开展,在后续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中,若能尽可能多使用地质学、环境考古的相关方法[4]郭荣臻.河南新密史前先民食物结构的考古学观察.农业考古,2018,(3).,结合发掘工作科学系统采样,或能对遗址本身的环境演变与人类回应有更新的认识。此外,随着学科的发展,其他领域的多学科方法[5]许俊杰,莫多闻,王辉等.河南新密溱水流域全新世人类文化演化的环境背景研究.第四纪研究,2013,(5).可以在新的发现与研究中发挥更大作用。
3.就聚落考古研究来看,在社会组织结构的视角下,微观聚落形态、宏观聚落形态的分析亟待展开,聚落内部人与人的关系、聚落之间人群的关系有待解答;充分发掘聚落考古潜力,对科学采样所获的动、植物遗存及人工制品进行空间分析,以便对资源、环境、生业、社会进行综合研究,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工、自然遗物的潜力,最大程度地提取信息,或许有利于对当时社会的进一步认识。
4.就公共考古教育来看,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众所周知,向公众宣传考古发现、普及考古知识,在提高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传承弘扬历史文化方面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新密地区的考古发现日渐增多。如何将这些考古成果向公众推介,使考古学发挥更加重要的社会职能,是需要予以思考的。
结 语
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发现以来,学界对其开展了较为详实地研究,涉及多层次、多维度、多方面,取得一系列阶段性认识,尤其是对该遗址龙山时代城址的认识已经很深入。这些研究对我们认识、了解该遗址的相关社会历史状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囿于发掘较早,部分新的科技手段、新理念、新方法尚未在该遗址的研究中发挥作用,随着新一轮发掘工作和研究的开展,该遗址的面貌将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